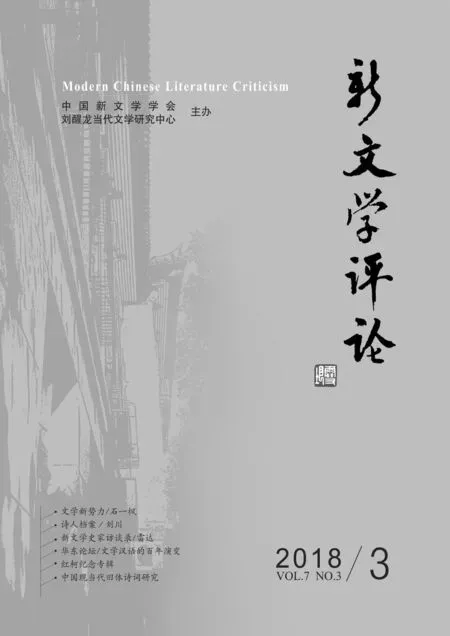“我们”:“被围者”的困境
——论穆旦四十年代中后期诗歌中的人称结构与主体意识
◆ 娄燕京
作为“新诗现代化”的典范,穆旦诗歌具备诸般可供分析的特征,其中“人称代词”的使用是一个突出之点。一方面,在穆旦诗作内部,人称代词频繁位移、转换,构成形式层面的“人称结构”;另一方面,在与日常生活、现代中国战争等“他者”的对峙、渗透中,人称的结构性变化暗示了穆旦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主体意识。正是人称代词这一“内外兼修”的位置,使其成为理解穆旦诗歌较为“顺手”的切入点。
正如梁秉钧在判定穆旦诗歌中“现代的‘我’”时所言:“他诗中的‘我’多少仍带着一种社会、文化或心理的身份,有变化亦有比较可以追溯的特性。他通过现代的‘我’,还是想由小我具体写出时代。”穆旦诗歌的人称问题固然可以从结构主义的角度予以整体性的归类、描述,但却由此忽略了其阶段性的变化,以及此种变化所隐含的主体之历史意识和时代内涵。因此,既要追寻人称代词内部的序列变化,又必然要在“变化点”上定位其所契合的历史节点。在此意义上,“野人山经历”既在穆旦个人生命历程,也在其创作谱系上构成可具解读性的“症候”。
综观穆旦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诗歌,在“野人山经历”之前,其诗作人称变换十分复杂,诸种人称代词弥散在诗歌内部与诗作之间,呈现出在个人的“我”与集体的“我们”之间的犹疑;而从野人山归来之后,穆旦诗歌在人称上的明显表征是“我们”这一复数性第一人称代词的激增,并成为穆旦四十年代中后期诗作(具体指作于1942年2月的《出发》以后的诗歌)的主体性人称代词。基于这种观察,从“野人山经历”出发,立足穆旦在此一历史时间段所处的个人境遇(如“小职员”身份)和历史变动(如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探讨由“我们”所搭建的人称结构、所隐含的主体意识,就成为本文主要的着眼点。
一、 “我们”与“上帝”
穆旦于1942年2月至3月间志愿参加中国抗日远征军,就在临“出发”之际,写下一首颇具谶语意味的诗——《出发》(1942年2月):
告诉我们和平又必需杀戮,
而那可厌的我们先得去欢喜。
知道了“人”不够,我们再学习
蹂躏它的方法,排成机械的阵式,
智力体力蠕动着像一群野兽,
就把我们囚进现在,呵上帝!
在犬牙的甬道中让我们反复
行进,让我们相信你句句的紊乱
是一个真理。而我们是皈依的,
你给我们丰富,和丰富的痛苦。
这首诗一改此前诗作对战争的热烈想象,充满了不祥的预感、残酷的悖论式真相和对于上帝的无奈的诅咒。值得注意的是“上帝”这一形象的出现,及与之前穆旦诗作中“上帝”意涵的不同。就在同年同月的《诗八首》中,也有一个“上帝”:
从这自然底蜕变底程序里,
我却爱了一个暂时的你。
即使我哭泣,变灰,变灰又新生,
姑娘,那只是上帝玩弄他自己。
我和你谈话,相信你,爱你,
这时候就听见我底主暗笑
不断地他添来另外的你我
使我们丰富而且危险。
这里的“上帝”——情诗中的上帝——内在于主体之中,是主体的一部分,表达的是“现代的‘我’”的内在深度和分裂性。与此相反,《出发》中的“上帝”,则完全是一种异己性的他者。而正是“上帝”这一形象的位置的变化,改变了诗歌中人称代词的结构,异己性的上帝对应的不再是现代式的个人,而是一个具有整体性的称呼——“我们”。
如果对《出发》之后穆旦诗歌中的人称作一番统计学的分析,则会发现不仅“我们”这一复数性第一人称代词成为主体性人称,而且“上帝”、“主”的形象、称谓也伴随“我们”而呈上升之势,两者在穆旦诗作中构成了某种对应关系。而正如《出发》一诗所预示的,在“结构”功能的意义上,“上帝”与“我们”在穆旦的诗歌中分别预设了两个“空位”,并在两者的关系中呈现一种“上位”与“下位”的他者性关系。一方面,“上帝”作为一个人称代词之上的“大人称”,显示了穆旦诗作中人称结构的调整;另一方面,在这一新的人称结构的基础上,穆旦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的诗作中重新设置了文本的内部结构,并以这一“形式”的表征,暗藏了自身的主体意识和历史观察。与此同时,问题的关键更在于,穆旦诗歌中这一现象的出现,与穆旦的“野人山经历”有直接的影响关系。在王佐良对这一“经历”的“转述”中,“最痛苦的经验却只属于一个人”,但“他从此变了一个人”。事实上,正如王佐良指出过的穆旦经“三千里步行”后“诗风变了”一样,穆旦自“野人山经历”之后也在诗歌创作和主体意识中有一个内在的转变,这一转变体现在表层的形式特征上,即是上述人称结构的变化。
在此前提下,即使在处理个人的内心景观时,穆旦诗歌中的“上帝”、“主”也不再内在于主体,而是外在于且高于主体:
是更剧烈的骚扰,更深的
痛苦。那一切把握不住而却站在
我的中央的,没有时间哭,没有
时间笑的消失了,在幽暗里,
在一无所有里如今却见你隐现。
主呵!淹没了我爱的一切,你因而
放大光彩,你的笑刺过我的悲哀。
——《忆》(1945年4月)
从你的眼睛看见一切美景,
我们却因忧郁而更忧郁,
踏在脚下的太阳,未成形的
力量,我们丰富的无有,歌颂:
日以继夜,那白色的鸟的翱翔,
在知识以外,那山外的群山,
那我们不能拥有的,你已站在中心,
蓝天之漫游者,海的恋人!
——《海恋》(1945年4月)
两首诗作包含了相同的结构,都是在“我”(“我们”)对“你”(“主”、“蓝天之漫游者,海的恋人”)的观望、寻找、吁求中,呈示“你”之于“我”的“隐现”,即“救赎”与“被救赎”的关系,而穆旦诗作关于此种关系的集中表述,则是经过反复修改的长诗《隐现》。
在穆旦的诗作中,大体有三首诗较为正面地呈现了“野人山经历”:《隐现》(1943年3月)、《活下去》(1944年9月)、《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上的白骨》(1945年9月)。从写作时间、文本容量和穆旦本人的重视程度上看,《隐现》最集中体现了穆旦对“野人山经历”的思考。因此,探讨“野人山经历”对穆旦四十年代中后期诗作中人称结构和主体意识的影响,必然要从《隐现》一诗“出发”。
在《隐现》中,穆旦一方面对战争进行控诉,“一切都在战争”,“我们已经有太多的战争”,另一方面基于这种个人的战争经历吁求上帝的救赎:“让我们看见吧,我的救主。”因此,“我们”与“主”、“上帝”的对应关系成为该诗最为内在的结构,由此造成的文本效果是,“我们”所具有的“被动性”展露无遗:
一串错综而零乱的,枯干的幻象,
使我们哭,使我们笑,使我们忧心
用同样错综而零乱的,血液里的纷争,
这一时的追求或那一时的满足,
但一切的诱惑不过诱惑我们远离;
远远的,在那一切僵死的名称的下面,
在我们从不能安排的方向,你
给我们有一时候山峰,有一时候草原,
有一时候相聚,有一时候离散,
有一时候欺人,有一时候被欺,
有一时候密雨,有一时候燥风,
有一时候拥抱,有一时候厌倦,
有一时候开始,有一时候完成,
有一时候相信,有一时候绝望。
一切的原因迎接我们,又从我们流走,
所有古老的传统,所有的声音,所有的喜怒笑骂,所有的树木花草都在等待我们的降生,
有一个生命付与了这所有的让他们等待:
智者让智慧流过去,青年让热情流过去,先知者让忧患流过去,农人让田野的五谷流过去,少女让美的形象流过去,统治者让阴谋和残酷流过去,反抗者让新生的痛苦流过去,大多数人让无知的罪恶流过去,
我们是我们的付与,在我们的付与中折磨,
一切完成它自己;一切奴役我们,流过我们使我们完成。
在这里,“我们”这一全称性代词不再处于“主语”的位置,而是在“使”、“给”、“完成”、“奴役”、“流过”等动词后面充当宾语。正是这种被动性,让穆旦发出了对“主”的呼唤:“这是时候了,这里是我们被曲解的生命/请你舒平,这里是我们枯竭的众心/请你糅合,/主呵,生命的源泉,让我们听见你流动的声音。”在此种“主”与“我们”的关系中,有必要梳理两者各自的具体内涵。首先,“我们”一词在诗中虽有“全人类”这一指称意涵,但穆旦的思考显然更有现实性,即“我们是廿世纪的众生骚动在它的黑暗里”,而即便如此,“说不出名字,我们说我们是来自一段时间”,“我们”是“说不出名字”的,“在黎明确定我们的虚无以前”。“我们”处于“宾语”的位置,“一切”在上,而“我们”在下,“奴役我们”,“流过我们”。简言之,穆旦虽然赋予了“我们”历史性(“廿世纪”)的内容,但“我们”仍然是空洞的、不断被他物所填充的。而“我们”的“虚无”又导致了与“我们”对应的“上帝”的“空位”性质,“无法形容你”、“你的说不出的名字”使得外在于且高于“我们”的“主”,只能在想象中“降临”:“忽然转身,看见你。”
正如王佐良所说:“穆旦对于中国新写作的最大贡献,照我看,还是在他创造了一个上帝。他自然并不为任何普通的宗教或教会而打神学上的仗,但诗人的皮肉和精神有着那样的一种饥饿,以至喊叫着要求一点人身以外的东西来支持和安慰。”在《隐现》中,穆旦掏空了“我们”与“上帝”的具体内涵,这既联结着穆旦对“野人山经历”即战争的玄学化、抽象化的思考,同时通过“我们”和“上帝”这两个“位置”的设置,保留了给予二者实体性内涵的可能,与这种实体性相联系的则是穆旦在“野人山经历”之后所处的个人境遇(“小职员”身份)和历史变动(现代中国战争)。简言之,《隐现》一诗所呈现的结构构成了穆旦四十年代中后期诗作的“纲”,以此为中心,穆旦开启了一系列更具现实化的思考。
二、 “八小时”与“自然”
在穆旦的早期诗作中,对沉闷无聊的小资产阶级生活有着清醒的批判意识,如《还原作用》(1940年11月):“八小时工作,挖成一颗空壳,/荡在尘网里,害怕把丝弄断,/蜘蛛嗅过了,知道没有用处。”因此,“我要赶到车站搭一九四○年的车开向最炽热的熔炉里”(《玫瑰之歌》,1940年3月),并进而生发出对正在进行的战争的浪漫化想象:“因为我听见了洪水,随着巨风,/从远而近,在我们的心里拍打,/吞噬着古旧的血液和骨肉!”(《从空虚到充实》,1939年9月)所以,在穆旦那里,“八小时”的“尘网”既结构,又限制了“现代的‘我’”,而如何从中逃逸,穆旦寄希望于战争对日常生活的解放、冲刷作用,即七月派诗人阿垅对穆旦的评判——“一种知识青年从军的浪漫主义”。这可以证之于穆旦自述的参军动机:“校中教英文无成绩,感觉不宜教书;想做诗人,学校生活太沉寂,没有刺激,不如去军队体验生活;想抗日。”作为战争局外人的穆旦,无论就战争本身,还是战后生活都存有一种乌托邦式的设想。然而,“野人山经历”却使得穆旦的这一“战前”想象失去了依据。
“野人山经历”给穆旦带来了双重困境,一是就战争本身来说,战争的残酷性打破了穆旦作为书斋里的年轻知识分子的主观臆想,战争经历已经成为某种梦魇似的东西,它持续影响着穆旦的诗歌思维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穆旦对政治,对时局,对社会人生的把握和判断;二是即使战争是残酷的,是非人的,但是在经过战争的洗礼之后,依旧没有带来穆旦在战前所预想的生活。从战场归来之后,穆旦的工作经常变动,收入并不稳定,一直未改变“小职员”的身份,依旧陷入“八小时的网中”,“你未来的好日子隐藏着敌人”(《退伍》,1945年4月)。
在此种个人的生存境遇下,穆旦展开了对“八小时”的“文明社会”的剖析:
从中心压下挤在边沿的人们
已准确地踏进八小时的房屋,
这些我都看见了是一个阴谋,
随着每日的阳光使我们成熟。
——《成熟》(1944年6月)
我们没有援助,每人在想着
他自己的危险,每人在渴求
荣誉,快乐,爱情的永固,
而失败永远在我们的身边埋伏,
这一片地区就是文明的社会
所开辟的。呵,这一片繁华
虽然给年青的血液充满野心,
在它的栋梁间却吹着疲倦的冷风!
——《诗》(1943年4月)
一个圈,多少年的人工,
我们的绝望将使它完整。
毁坏它,朋友!让我们自己
就是它的残缺,比平庸更坏:
闪电和雨,新的气温和泥土
才会来骚扰,也许更寒冷,
因为我们已是被围的一群,
我们消失,乃有一片“无人地带”。
——《被围者》(1945年2月)
相比于早期的《从空虚到充实》(1939年9月)、《蛇的诱惑》(1940年2月)等诗,虽然同样是对“文明社会”的描述、批判,但是四十年代中后期的诗取消了此前对战争的浪漫化想象,从“八小时”的日常生活中逃逸的可能被延宕,“因为我们已是被围的一群,/我们消失,乃有一片‘无人地带’”。而且这一变化,同样体现在诗作的人称使用上,在《从空虚到充实》、《蛇的诱惑》等诗中,主体是原子化的个体,诗中呈现的人类是溃散性的,人物大都有具体的名字(Herry王、德明太太等等),人称也多为单数性的,而在穆旦此一时期的诗作中(包括上述诗作)则将这些个体整合为“我们”。如何理解“我们”的内涵,需要放在“野人山经历”的延长线上来看待。《隐现》等诗作中,“我们”一词被赋予了“廿世纪众生”的抽象内涵,并由此成为对人类全体的代称。而“文明社会”中的“我们”正是“廿世纪众生”的一个更加具体的写照,并暗合了穆旦在“野人山经历”后将战争、现实玄学化的思维方式。更重要的是,由单数人称向复数人称的过渡,是因为穆旦重新设置了从“文明社会”中逃脱的方式,这一方式取代了“战争”对“八小时”的“尘网”的“吞噬”,并在更高的层面上完成了对两者的超越,在穆旦的诗作中,这一方式被命名为“自然”。
在《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1945年9月)中,“人”对“森林”、“自然”有如下自白:
离开文明,是离开了众多的敌人,
在青苔藤蔓间,在百年的枯叶上,
死去了世间的声音。这青青杂草,
这红色小花,和花丛中的嗡营,
这不知名的虫类,爬行或飞走,
和跳跃的猿鸣,鸟叫,和水中的
游鱼,陆上的蟒和象和更大的畏惧,
以自然之名,全得到自然的崇奉,
无始无终,窒息在难懂的梦里。
我不和谐的旅程把一切惊动。
“人”代表的是“野人山经历”中的死难者,但在穆旦的处理中,战争的残酷经历被转换为“人”与“自然”的对话。诗中有一个突兀的“颠倒”:“文明”代表“敌人”,相反,象征着战争创伤的“森林”、“自然”则被认为是“和谐”的,战争的死难者进入“森林”,成为“惊动”“自然”的“不和谐的旅程”,这恰好应和了《隐现》一诗中“我们”对“上帝”的宣吁:“我们和错误同在,可是我们厌倦了,我们追念自然。”正如唐湜所说:“如此,胡康河谷上的战士化成了白骨,无名的野花在头上开满,这壮烈的抗日的战斗的归宿就是原始的自然,人类的故乡。这一去不复返的故乡就是人类历史与自然史的交汇点。”在这一意义上,“祭歌”的结尾句:“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与其被解读为对战争记忆的安放和对死难者的招魂,毋宁说穆旦是借此表达了对战争的玄学化思考,从而以“野人山经历”和“文明社会”(穆旦个人的“小职员”身份)为基准点,生发出回归“自然”的渴望。
同样,在《野外演习》(1945年7月)一诗中:
我们看见的是一片风景:
多姿的树,富有哲理的坟墓,
那风吹的草香也不能深入他们的匆忙,
他们由永恒躲入刹那的掩护,
事实上已承认了大地是母亲,
由把几码外的大地当作敌人,
用烟幕来掩蔽,用枪炮射击,
不过招来损伤:真正的敌人从未在这里。
在这里,“大地”即“自然”成为“母亲”,隐含了某种回归母体的潜在含义。更为重要的是,在“看风景”的“我们”与参加“野外演习”的“他们”之间构成了对立,“我们”“承认了大地是母亲”,而“他们”“把几码外的大地当作敌人”,“我们”渴望某种“自然”所提供的秩序,而“他们”却成为这一秩序的破坏者,由此形成“人和人的距离”,而“我们”也成为一种超越于历史和现实之上的观看者:“也是最古老的职业,越来/我们越看到其中的利润。”
至此,“我们”既是“野人山经历”之延长线上的“我们”,又是“八小时”的“文明社会”中的“我们”;既作为“人类”这一范畴的全称性指代,又暗合穆旦在四十年代中后期的“小职员”身份。在一种抽象的、超越性的想象中,“上帝”与“我们”的救赎与被救赎关系转换为有着更加具体的社会内涵的“我们”向代表着某种恒常秩序的“自然”的回归。正是这一重新调整的“我们”与他者(“自然”不是异己性的,而是属己性的他者)的关系,在国共内战的历史大变动中校正了穆旦的历史抉择。
三、 “神魔之争”
1945年10月,穆旦北归,在途中,写下《从昆明到长沙——还乡记》:

在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上,穆旦表达了对战争,具体而言是对抗日战争的某种伦理性质的判断,仍然延续了其诗作中对战争的超越性思考,并将此最终投射到对“今日的国事”的批评上。因此,问题的症结在于梳理穆旦对现代中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态度,并探求穆旦如何理解“今日的国事”。

多谢你们的谋士的机智,先生,
我们已为你们的号召感动又感动,
我们的心,意志,血汗都可以牺牲,
最后的获得原来是工具般的残忍。
——《时感四首》(1947年1月)
历史已把他们用完:
它的夸张和说谎和政治的伟业
终于沉入使自己也惊惶的风景。
——《荒村》(1947年3月)
因为一次又一次,美丽的话叫人相信,
我们必然心碎,他必然成功,
一次又一次,只有成熟的技巧留存。
——《诗四首》(1948年8月)
在这些诗作中,随处可见的是那些可以获得“我们”,却不被“我们”获得的他者:饥饿、罪恶、暴力、胜利、牺牲、手、面包和自由等等。同样,这些诗作大多发表于同一时间的《益世报·文学周刊》、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文学杂志》、《中国新诗》等杂志。

在《甘地》(作于1945年5月,初刊于1947年4月13日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一诗中,穆旦借颂扬甘地而阐明了诗作内在“人称结构”和个人的主体意识,即“当生命被敌视,走过而消失,在神魔之间/甘地,他上下求索,在无底里凝固了人的形象”。甘地“在神魔之间”所处的“人”的位置,无疑也是穆旦为自己设定,为“我们”预留的位置。而这一结构和意识更加明晰的表达,则是作于1941年6月,重订于1947年3月的《神魔之争》一诗。
《神魔之争》是一出诗剧,分“东风”、“神”、“魔”、“林妖(又分为‘林妖合唱’、‘林妖甲’、‘林妖乙’)”四个角色。在其中,“神”代表着固有的文明秩序:“我是谁?在时间的河流里,/一盏起伏的,永远的明灯。”与此相对应,“魔”则是破坏者、反抗者:“让狡诈的,凶狠的,饥渴的死灵,/蟒蛇,刀叉,冰山的化身,/整个的泼去,/在错误和错误上,/凡是母亲的孩子,拿你的一份!”“神魔之争”一方面延续了穆旦“野人山经历”之后对历史的玄学化思考,并引出一种历史循环论的看法,接近《隐现》一诗中被着重强调的“不变”;另一方面,“神”与“魔”的二元对立也是对正在进行内战的国共双方的直白隐喻,“神魔”高高在上的“争”既是对现实的反映:“多谢你们飞来飞去在我们头顶,/在幕后高谈,折冲,策动;出来组织/用一挥手表示我们必须去死/而你们一丝不改:说这是历史和革命。”(《时感四首·1》,1947年1月)更重要的是,“神魔之争”在上的、“在我们头顶”的位置,暗示了一个“在下”的空间,这一空间被穆旦授予了两个角色:“东风”和“林妖”。其中,“东风”是一个看透历史的智慧老者形象:“O旋转!虽然人类在毁灭/他们从腐烂得来的生命:/我愿站在年幼的风景前,/一个老人看着他的儿孙争闹,/憩息着,轻拂着枝叶微笑。”换言之,一个“看风景”的历史旁观者。而“林妖”则不仅成了历史的受难者,更是充满对历史的无知,正如“林妖合唱”:“谁知道我们什么做成?/啄木鸟的回答:叮当!/我们知道自己的愚蠢,一如树叶永远的红。”因此,《神魔之争》中的人称结构除了“神魔”对立以及“神魔”与“东风”、“林妖”的“上下”冲突外,至为重要的症候在于,“东风”的“我”已经外在于“林妖”的“我们”,“我”与“我们”的分立、裂隙也因而取消了“东风”(“我”)的历史观察的合法性。
所以,穆旦在“野人山经历”之后所设置的“上帝”与“我们”的对应关系及各自内涵已改头换面。“上帝”不再意味着救赎的可能性,而是被“神魔之争”的历史循环法则所替代,并因此决定着“下面”的“我们”的命运,同时,“我们”也不再是一个抽象的“廿世纪的众生”,而由不同的“我们”组成(如《时感四首》中的“我们”与《他们死去了》、《荒村》中的“他们”)且存在不可调和的裂隙,无论是“上帝”还是“我们”都各自溃散了。正是在此意义上,穆旦才将“上帝”与“我们”的对立重新整合为“一”:“我歌颂肉体:因为光明要从黑暗里出来,/你沉默而丰富的刹那,美的真实,我的上帝。”(《我歌颂肉体》,1947年10月)穆旦在“我们”的分化中,最终站在了强调独立的“个人”的那一“我们”中。
基于“野人山经历”的战争创伤和“小职员”的社会境遇,穆旦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的诗作以复数性第一人称代词为支点,展开了个人对战争、历史、现实的思考,并由此生发出“我们”与“上帝”的“人称结构”,这一结构的具体内涵随穆旦主体意识的调整而不断变化,由一种单纯的对人类生存的超越性思考,延伸到对“八小时”之外的“自然秩序”的回归渴望,并在国共内战的背景下,最终由抽象的“我们”落入到更加具体的“中间阶层”,以试图保留个人的自由和独立性。“我们”作为“被围者”,在不断具体化的过程中,也不断溃散,以致“上帝”、“自然”、“神魔”都不再构成救赎的力量,而是回到个人的反抗:“我想要走。”(《我想要走》,1947年10月)而“个人”如何突破“我们”的“被围”,其内在的有效和局限之处,穆旦的写作和行动都为历史的后来者提供了借鉴和反思的可能性。
注释
:① 梁秉钧:《穆旦与现代的“我”》,杜运燮等编:《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怀念诗人、翻译家穆旦》,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4页。
②姜涛:《冯至、穆旦四十年代诗歌写作的人称分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4期。
③易彬:《穆旦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0页。
④王佐良:《一个中国新诗人》,《文学杂志》1947年第2卷第2期;李方编:《穆旦诗文集(增订版)》(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55~156页。
⑤王佐良:《穆旦:由来与归宿》,杜运燮等编:《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怀念诗人、翻译家穆旦》,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⑥《隐现》一诗创作于1943年3月,初刊于1945年1月,后又经多次修改和发表,但“修订本的所有修改几乎都是修辞性的所以,说了归齐,后出的《隐现》修订本和原初的《隐现》初刊本并无大差别”。解志熙:《一首不寻常的长诗之短长——〈隐现〉的版本与穆旦的寄托》,《新诗评论》2010年第2辑。故此,本文采用李方编:《穆旦诗文集(增订版)》(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详细修改情况见解志熙辑校:《穆旦长诗〈隐现〉初刊本校录》,《新诗评论》2010年第2辑。
⑦王佐良:《一个中国新诗人》,《文学杂志》1947年第2卷第2期;李方编:《穆旦诗文集(增订版)》(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60页。
⑧阿垅:《旗片论(穆旦)》,《诗与现实》(第三分册),五十年代出版社1951年版,第259页。
⑨易彬:《穆旦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7页。
⑩唐湜:《笔然的搏求者——穆旦论》,《九叶诗人——中国新诗的中兴》,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