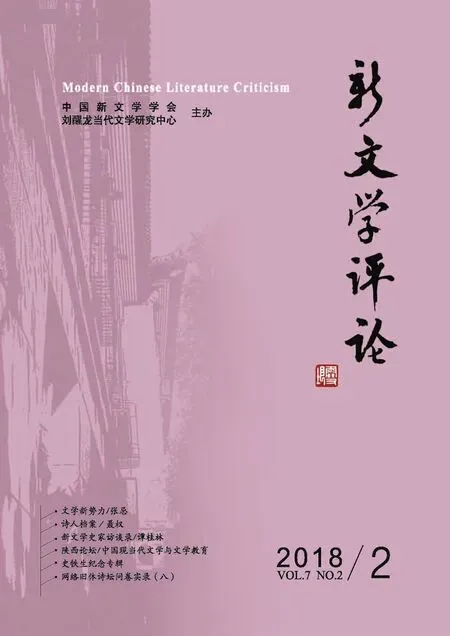一珠千年照万象
——读乔叶《藏珠记》有所思
◆ 谢尚发
写还是不写这篇评论,的确是时至今日人生中碰到的最纠结的事情。出于一个“爱文学者”的热心,以及“行必果”的生活理念,花费了那么长时间读完的一部小说,倘若不写,总觉得可惜。但真要动起笔来,“无法言说”倒也并不意味着失语,关键在于担忧颠倒了的“阅读的双重效应”出现,即忧惧于“爱不释手,常读常新”的反面。阅读已经耗费了不少精力,再来对一部并不能带来智慧或“所得”的小说评论上一番,颇为自己“不值得”。平心静气而言,写或者不写,都有“不公”的嫌疑存在——不写,对创作者和作品本身是不公的,它意味着对于劳作的价值的某种程度的怀疑与忽略;写,则又对读者不公,因为它也意味着对时间和精力的漠视与背弃。终于决定拿起笔来“牢骚一番”,其动力来自“批评与自我批评”、“反思与自我反思”。
这绝不是一个“文学常识”普及的时代,甚至可以说,它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文学常识”的匮乏。毕竟,在这样一个时代,处于“式微”境地的文学,在影视、网络咨询等的挤压之下,已经退守于社会一隅,虽不至于是“文学界自说自话”的一家之言,但“失去轰动效应”也是不争的事实。读图时代的来临,对阅读提出的挑战,已从虎视眈眈变成了既定事实。因此,留给文学“任性”或“一意孤行”的空间已经十分狭小,它可能并不需要谨小慎微,但假若试图肆意妄为,折腾起来,恐怕带来的也只是一场“内耗”。当然,存在着“大众”的文学,也就存在着“小众”的文学,期望作品横空出世,洛阳纸贵,居多是一种幻象。然而,同样可怕的是,当一件事情无可无不可的时候,那么也就意味着它存在或者不存在都无所谓的命运的到来。可惜的是,单就这一“文学常识”而言,不仅仅对普通的阅读者意味着是匮乏的,甚至对写作者和批评者来说,其状况也同样是堪忧的。
一、 一部无法批评的小说
其实,在一个作品“极度繁荣”也同时带动批评“盛极一时”的岁月里,重新思考“我们为什么需要批评”显然是多余的。对于重新勘定“文学批评的价值和意义”的行为,不管是行内还是行外,恐怕都会嗤之以鼻——“以批评为业者”竟然还要中途回首,追问自己所从事的行当的“价值和意义”,岂不是犯了“上了贼船还帮贼吆喝”的愚蠢?不过好在如此,还有亡羊补牢的意义在,总不至于在偏道上中毒过深而无法自拔。这种经常性的追问,是要在反思中,让文学批评获得更为适恰的位置,而非重新定义文学批评的标准。局中人的迷雾总要时时拨弄,否则迷失了航向,“副业成为主业”,真就难以拯救了。毕竟,诚如乔治·斯坦纳所说,在20世纪,“诚实的人要做文学批评,实属不易。有许多迫切的事情要做。评论只是附属品而已。”倒也不是妄自菲薄的贬低,它带有一种恰到好处的自我反思,从而能够在摆正自我位置的同时,清楚自己的职能。斯坦纳接着说,“批评的艺术在于让那些或许最不需要帮助的读者关注文学作品;如果没有较高的文学素养,读者会读诗歌、戏剧或小说评论吗?”充其量,“我们为什么需要批评”所能够厘定的,便是“文学批评”的辅助功能——它不是审判的最后决断,更不是文学史书写的定词终论,它只是在帮助阅读者从茫茫的文学作品海洋中,甄别出值得花费时间去阅读的珍宝,不会在随便选择中浪费有限生命和精力。这当然牵涉到进一步的追问:我们为什么要写作?或者告诉阅读者,我们为什么要阅读?为什么要阅读这一部而非那一部?
在既往的理解中,文学批评更多地被定为在是“私人趣味的学理化”,同样是斯坦纳的话,他还说:“在文学批评中,没有永恒之物的希望之乡,没有确定无疑的乌托邦。就本质而言,评论是个性化的活动。它既不要求论证,也不要求证据一致。”这大概是文学批评价值大打折扣的原因——本来一本正经的“文学批评”,变成了千人千面的“文学意见”,这“意见”根本无法统一,也无需统一。因此,文学批评就被赋予了另外一种职能:发现文学作品的价值所在,而不管这部作品到底在何种意义上以及是否配得上这种“挖掘”。进而,文学批评越发变得“无可而无不可”,成了“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强大阐释力量”和“能对作品发言的万能机”。倘若在这个意义上,回到话题讨论的对象,《藏珠记》绝对是一部值得“言说”的作品——它以纯文学的姿态,接纳了网络文学和影视文学的桥段:类同于见证的逆向穿越的穿越;它在洞明世事的沉思上,追思人性与爱情的种种:三个人,一个坏,两个爱;它以女性的身体作为书写的题材,重审“破处即死”的“处女情结”:贞洁与爱情的较量,拥有了女性主义反思的重量级书写。只不过,同样明显的是,《藏珠记》无法言说的部分也比比皆是——投入通俗文学的怀抱之中,任性恣意地挥洒作者的“小心思”:“这种选择我知道会有人说幼稚、可笑、肤浅,或者别的什么,我统统能够推想得到,没关系,对于读者,我没有期待。这是我满足自己的小说,满足于自己某些厚颜无耻的幻想。”还不待批评的到来,乔叶便已经“全副武装”,摆出“此处不谈”的姿态,批评自然就无话可说了。
文学批评倘若按照斯坦纳的意思,以最卑微的姿态存在,它也应该肩负起自己的“辅助功能”,宁愿耗费自己的时间,也要替更多的阅读者节省时间。但在福柯看来,批评需要筑起更具“尊严”的台基,以便“揭示出隐藏在其符号下面的重大的谜一般的意图”,“所以,只有依据真理、精确性、特性或表达的价值,批评才能分析语言”。文学之所以是文学,便在于它有自己的“真理、精确性、特性或表达的价值”。在一个“文学式微的时代”,文学之所以还在坚守着它的“一隅”而不被影视、读图等所侵占,便在于它不但要完成“语言的表象”,还需要在“语言的表象”之外,提供影视和图片无法给予的“真理、精确性、特性或表达的价值”。这实际上便是阅读者念兹在兹的“有所得”的“得”。讲述一个纯粹的、好玩的故事,描摹一位可爱的、与众不同的主人公假使只限于此,文学真的就无从与影视剧,甚至与《今日说法》进行区分了。因此,当乔叶心心念念地强调《藏珠记》的“偏轻”之时,她大概不会想到,文学批评所试图要帮助阅读者寻找的,恰恰是“轻背后的重”,哪怕这种“重本身也是一种轻”。因此,作为“一部无法批评的小说”,它的核心要素并非是“不能批评”,而是“无从批评”。这“无从批评”的缘由同样也不是拒绝批评,而是批评已经“放弃批评”了。那么,对于一部小说而言,它究竟要“追求什么”?
二、 时间有所思与“为何写”
大致梳理一下《藏珠记》的情节,从中也能够看出乔叶的良苦用心。一位唐朝的女子,机缘巧合之下,吞食了波斯商人赠予的神奇的珠子,从此拥有了长生不老的法宝,从唐朝一直活到了当下。这个经历了千年的女子,保持着青春和处子之身,不意却卷入了一个商人和一个官二代之间的“内斗”。赵耀通过官商勾结的方式,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却被畏罪自杀的金泽的父亲抓住了把柄,以此来让金泽“分红”赵耀的收入,保证衣食无忧。历经千年而不死的唐珠,可谓阅人无数,看透了赵耀的伎俩,也迷恋上了金泽的单纯、干净。两人迅速坠入爱河不能自拔,但唐珠却难以为这样的爱而付出处子之身,因为对于她而言“破处即死”,意味着爱情和死亡被并置在她的命运之中。对于一个女子而言,“无法去爱”自然是残酷。这时,为了成全她“大胆爱一回,哪怕即便死去”的愿念,乔叶设计了一个“U盘”的“扣子”,让赵耀在贪恋她的处女之身和怨恨爆发后,强奸了这个“千年老处女”。唐珠血流不止,奄奄一息,依赖于现代科技的发达,最终保住了性命。结局是“落难公子中状元,奉旨完婚大团圆”——唐珠打破了“处女禁忌”,和金泽不休不止地爱着,并诞下一女,手握那颗从唐朝带来的珠子。金泽参加厨艺比赛获得头名,从此,两人平凡又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据乔叶的后记交代,《藏珠记》的构思或“灵机一动”来源于韩剧《来自星星的你》。但很难厘定两者之间存在着怎样的“重叠”,且同类的故事也不必非得用比较的眼光来加以评价。乔叶显然并不满足于讲一个“电视剧故事”,因此她将“时间”的视角带入到故事之中,试图在“时间的管窥”中来获得小说本身的思想高度,让这个“剧情”略显“狗血”的小说拥有厚重感。因此在行文之中,乔叶将她的“生活领悟”以“哲人的口吻”,宣讲于字里行间。唐珠时常感慨于“千年岁数”中所隐藏着的种种秘密,她说:“活得越久,不相信的就越多,相信的也越多。因为这些相信和不相信,我就活得越来越从容。”她还领悟到:“在这世上,想要万寿,就不能成名成家,就只能做个平凡的人,淹没在人海里。”接着,她又说:“人事人事,所有的事都在人的身上路过、体现、沉淀和爆发着,说到底,事的根基还在于人。”在人事的纠缠上,她告诫道:“要想活得长,最重要的是不能让别人伤害我。不让别人伤害我的最重要前提就是不去惹事儿。惹不起的人坚决去躲,躲不起的人坚决要逃,逃不脱的人坚决能忍,不好处的人坚决不处,好处的人也坚决不长处。若结交得太深,一旦到了不得不永诀的时候,就会伤心。”这类从时间而来的感悟还比比皆是,一一引用实在没必要,因为从一个“千年老人”嘴中说出来的,听上去怎么都感觉,那味道里满藏着“现代人的成功学”秘诀,和街角书摊上随处可见的“心灵鸡汤”。与其说这是唐珠经历了千年之后的“哲人之思”,不如说是现代“办公室政治”的总结。而这些,已经在铺天盖地的电视剧、网络小说、综艺节目等媒介中大量出现了,着实没有必要再硬着头皮,啃一本21万字的小说,并从中来学会这些“办公室政治技巧”。作为一个普通的读者,这促使我们不禁要追问,“为什么要阅读”?但实际上,这个问题现在是提给写作者的,追问他们“为什么要写作”,具体一点是“为什么要写这样一个小说”。
仍回到乔叶的后记上,她说《藏珠记》是一部“满足自己的小说”,写起来是“任性和一意孤行”的,所以“对于读者,我没有任何期待”。这就意味着,这是一部“自娱自乐的小说”,是一部“内收内敛的小说”,它不期待与读者的沟通和交流,甚至不指望读者能够阅读从而抛来橄榄枝。让人颇感疑惑的是,文学写作中,到底存不存在一部“不是给读者阅读的小说”?到底有没有一部“作者写给自己看的小说”?恐怕这种种说法,到头来也都是“虚妄的借口”和“无奈的敷衍与推脱”。因为《藏珠记》毕竟发表了,而且出版了,作为一个“消费品”它总在吁请着“文学消费”行为的发生。倘若真的是“写给自己看的小说”,它就根本没有必要公开发表、出版,藏在私人的抽屉中,时不时拿出来欣赏一二,才是它的“存在之道”。既然如此,就还是需要重回小说本身,来一探究竟。
就整个小说而言,阅读是轻松和流畅的,它故事本身的委婉曲折以及爱情的千转百回都是引人入胜的。但需要追问的是,倘若文学只是提供一个“好的故事”,那么“文学别致的特征是什么”呢?一个阅读者,要消费一个“好故事”,他完全可以备一个水果盘,拿着牙签,一边轻松地吃着,一边欣赏一个电视剧,或者电影,甚至是某类综艺节目,都能满足他的需求。那么他何以仍要坚持“阅读文学”呢?文学之区别于影视、综艺等的东西,难道是一个“好故事”?这其实就是阅读者内心里“有所得”的追求。因此,小说的创作本身,理应在“有所得”上给出一些回应,而不管这些回应是“宏大叙事”,还是“通俗故事”,是命运、人性、道德,还是时间、日常、男女。乔叶完全能够在“千年岁月”的时间宽度和厚度上,作进一步的思考,把由时间积累而来的深度和高度带出来,从而让唐珠与时间共存的故事,不是“穿越的戏码”,而是“站在云端的思考”。当然,这可能根本就不是乔叶的追求,她所信托的就是一个“偏轻”的文本,一部“率性而为”的小说。只是偶尔,小说中随处可见的“廉价的成功学”教条和从“办公室政治”得来的“心灵鸡汤”,背叛了她“任性的初衷”。
三、 作为日常的宴饮与男女,或“怎么写”
如果只是侧重于概括和剖析《藏珠记》的“好看的故事”,就无法认识到乔叶在这部小说中的“苦心”和“挣扎”——本意是带着“任性和一意孤行”的写作誓言的,但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一个作家天然的职责和敏感度,还是有意无意地束缚着她,根本无法抛开既有的“创作经验”,放肆地铺排自我。于是,小说就有一种“前进也不是,后退也不行”的“扭拧”存在,这也明证了一个作家的“创作抱负”绝非是满足于“写作的私欲”。作家当然会把自己的喜好、爱憎、期许等融入作品中,但就作品的完整度而言,乔叶仍然在对之进行各种各样的“包装”和“打磨”。这体现在《藏珠记》关于饮食和男女的书写上。
“食色,性也”,便是日常。乔叶把一个男女之间较为纯情的爱,融入到“吃”上来,也可以看出她试图对爱情进行丰富的追求。但诚如荷尔德林的诗歌所说的,“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拯救”——必须认识到的是,“哪里有拯救”,肯定意味着“哪里就有危险”。把饮食作为日常的核心引入到爱情中来,让小说在宴饮和男女的两翼齐飞中展示更为“鲜活的生活哲学”,这种写作的“苦心”自然不应该被忽略。只是,乔叶这一次太过于将自己的“饮食文化”搬入到小说中来,导致整个小说中宴饮与男女的“磨合度”,令人不忍直视。
按照一般的说法,“小说就是设定一个目标,并设法去完成它”。如果说“写什么”还只是偶然的“灵机一动”的选择,本没有什么区别——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普通民众都是无所谓的。但对于一部作品而言,“怎么写”意味着它的“完成度”如何,才是决定它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乔叶的设计显然是在一个看似俗套的故事上,增加这个故事的日常维度,以此将之与饮食并列起来。在小说中,唐珠是一个“吃货”,千年的经历使她看透了人世间的万象,却唯独无法勘破“食欲”的存在。由吃而精做,便有了小说中大段的关于取水、食材、火候等的详细描摹。以至于日常生活中每一顿的饭菜都详细列上“菜单”,以及时不时地跳将出来的“食谱式书写”,“人间烟火味”十足,但总觉得这吃是游离于人物之外的存在。吃这个菜和吃那个菜,本质上是没有任何区别的,这不得不让人想起,“彻底的日常”也就意味着“缺少了日常”。同样,金泽是一心想当厨师的帅哥,论起做菜来,总能头头是道,以至于“物性”、“惊黄瓜资格证”、“厨师课”、“鼎中之变”等,直接把小说写成了“饮食文化”,尤其是对“豫菜”的大呼其神的笔墨,不但阻碍了小说本身的发展,显得冗余而庞杂。同样,“饮食文化”本身的描绘也显得是一种“照搬照抄”食谱、饮食文化史,缺少了文学关怀下的独特性。小说的两大主题便是“饮食”和“男女”,但两大主题几乎是各行其是,自说自话,导致了小说叙事的分裂和游离,“完成度”自然大打折扣。
为了让小说更加“文学化”,乔叶还采用了“第一人称交替叙述”的模式,让唐珠、金泽、照耀、金顺、松爷等站出来说话,从而相互补充,推动故事情节向前发展。第一人称的叙述好处是,直指内心,将人物个性展现得淋漓尽致。但乔叶写得“太过匆忙”,显然没有认真考虑“人物角色”的个性特征,他们的身份和经历,如何在他们的言语上表现出来,导致整个小说文本“千人一面”、“众口一词”,不是杂语交错的“众声喧哗”,而是“独声部”的“一言到底”。这尤其体现在作为姑姑的金顺的两次“说话”:第一次出场,作为一个乡下妇女,她言辞中时常闪现的“方言土语”,言辞的事故、老道也略显絮烦的劲道,拿捏得十分到位。但等到她第二次出场说话的时候,呈现出来的文本竟然和唐珠、金泽等人的口气、用词差不多一模一样了。乔叶显然也意识到了这种“瑕疵”的存在,以至于想方设法,将许多古诗词、古代饮食书籍,甚至许多不常见的古籍,穿插其中。这自然符合唐珠作为一个“古人”的角色形象,但泛滥的肆意运用,非但没有起到与小说叙述融为一体的效果,却处处显示出某种“刻意”与“牵强”来。尤其是让一个不学无术、醉心厨艺的官二代金泽,随口拈来《吕氏春秋》文本中的段落,着实把这个毛病暴露无遗。融为一体已是奢望,符合身份的效果都难以完成。若加上随处可见的“食谱摘抄”,让人感觉这样一部小说有“杂凑”、“随意”和“粗糙”的嫌疑。
的确,判断一部小说是否成功,不能就题材、思想、故事、人物等单方面地进行评价,而是应该看它本身的“完成度”如何(杨庆祥语)。这体现出写作者对作品的“经营”、“深思熟虑”与“苦心”来——写作的态度认真与否,无关乎作品本身完成的状况,“认真的作家”也会写出“粗心的作品”。“怎么写”对于一个“70后”作家而言,显然早已经不是问题,但一俟作家要“自嗨”一把,任性而一意孤行起来,恐怕再认真的态度,也难以保证一部“作品被高质量地完成”。单就饮食和男女的“契合度”问题而言,可以略举一例《红楼梦》,便能见出究竟。在《红楼梦》中,林黛玉和薛宝钗都身体不适而吃药。林黛玉是常见的病症,吃的却是“人参养荣丸”,用的药材又极其普通,人参、白术、茯苓、当归、甘草等。这一味药恰好应和了林黛玉寄人篱下,需要“养荣”的身份。因了这,她只能服用普通药材,简单易得。但薛宝钗吃的“冷香丸”则大为不同,药材极其讲究,白牡丹、白荷花、白芙蓉花、白梅花的花蕊,以及雨水节气的雨、白露节气的露、霜降节气的霜和小雪节气的雪,其所彰显的贵族气,可见一斑。冷香丸所治疗的,又是“热症”,而且是“娘胎里带来”的。如此,薛宝钗的高贵身份、热衷于仕途经济的个性和思想,也就被烘托了出来。同样是一味药,却能起到画龙点睛、恰到好处的作用。
四、 文学的“切身性”与“写什么”
整体上而言,《藏珠记》写得略显着急、粗糙,想要表达的东西太多,而又没能找到一个核心要素将之串联起来,于是颇显得散碎一地、凌乱芜杂。若要“挖掘”其中的价值,自然不难,随意挑出其中的一个点,就能说上许多“创新和独特性”来,但就小说本身而言,有“混搭”、“堆积”的嫌疑。在这些要素当中,信手写去,最显特色且最能将文学的“切身性”表达出来的,仍是作为女性作家的乔叶最拿手的“女性叙事”。一个作家选择什么样的题材,本来没有任何章法可循,而且在这一点上是拥有自由度最高的。但古往今来的写作实践,无形中形成了一条定律,便是“文学的切身性”——作家总是最擅长写自己熟悉的东西。个人经验的积累,以及将陌生性经验内化为个人经验的能力,是写作过程中一个作家所仰仗的。这是乔叶能够在“女性”这一话题上,将《藏珠记》进行提升的关键要素。
就《藏珠记》的整体小说文本而言,唐珠无疑是核心的人物,赵耀和金泽都只是这个“千年少女的附属物”。当然,这也成了小说的另一个可被诟病的地方——人物塑造的不对称性,导致红花和绿叶都未能刻画成功。作为一个女性,尤其是一个“千年老处女”,唐珠命运中所注定的“破处即死亡”,几乎成了女性身体全部秘密的核心所在。“处女情结”说起来虽然已经是陈旧的话题,但对于女性而言,这一意味着贞洁的身体密码,构成了她们在世的基础。而成长的过程,恰恰是对这一基础的破坏——她们需要爱情,需要性,更需要奠定于破坏而来的生育。“处女膜”的存在在以往的文学作品中的书写,从未上升到关涉“生死”的高度,就这一点而言,《藏珠记》用了一个并不新鲜的“类穿越”故事,做了第一次的尝试。“女人心性”就在保全和打破“处女膜”的纠结上,给彰显了出来。女性的身体秘密,心里符码,于焉和盘托出,它本然地属于女性,当然也本然地属于女性主义的种种话题,哪怕许多人会奋而起身反击。由此而来,《藏珠记》所藏之珠,便是“处女膜”;唐珠之所以能长命千年的秘诀,也在于她守护住了自己“处女膜”的完整性——这种对于贞洁的强调,以及贞洁保全意味着长生的观念,挽救了整个《藏珠记》。但作为女性的无奈,这个能保长命的珠子,却随着性爱和生育到来,必然破裂于本性存在的自然,这恰是女性的命运之所在。生育不仅是对本体生命的延续,也是它的缩短,“儿是娘的夺命鬼”,竟不是一语成谶的“迷信”,而是女性存在的天性!
知乎此,唐珠格外珍惜自己的身体——女性身体,成为乔叶赋予《藏珠记》以迷人色彩的另一抓手。经历千年的风风雨雨,而身体仍旧停留于青春美貌的唐珠,也曾醉心于男性的身体,充满了力量、肌肉的健美的身体,以及靠近女人时永远雄赳赳气昂昂的命根子。但当她意识到自己渴求男人身体的时候,她开始回身关照自己的身体——“这具肉身”充满了魅惑,为了认识它,唐珠“拿着一面大镜子,放在两腿之间,看自己的阴部。阴唇饱满,湿润紧致,指尖抚过之后,还有着淡淡体液的腥气”终至于,她领悟到:“说到底,天生此处,不是为了让自己独戏,而是等待和男人合欢啊。”不唯此,乔叶还对女性的“月事”,有着类似的描写——“每月此时,我必定会胸胀腰沉,冷汗满身,小腹内千转百回痉挛,宫腔里力道疯狂撕扯。可我喜欢这酷刑。我喜欢每月月事来临之时,那汩汩流出的鲜血。这血让我欣慰。”对女性进行“贴身书写”,从“处女膜、阴部和月事的三位一体”中,《藏珠记》命名了女性的“受难、罪责与成全”,偶尔的一笔看上去随意为之,却成全了“千年少女”的人物形象塑造。落实在女性及其身体上,唐珠不老、不死的遭际,就和她不能爱、不能生关联了起来。说白了,“女性的全部命运,系于她的身体”,当是唐珠在千年的岁月中,体会最深刻的领悟。从这些引用文字中,“文学的切身性”便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了。文学依赖于写作者的“私人经验”,并尽量把这种“私人经验”朝着更为宽广的领域扩展——用老腔调来说,叫做“体验生活”;用现代话来讲,便是“文学的切身性”。只有亲自体验过,才会有切肤之痛的领悟,才能写出别具一格的作品。一俟离开这种“切身性”,赵耀的恶便是一恶到底,金泽的美便是帅气和单纯,近乎于呆傻,难免会被“文学批评”指责为是“单薄、扁平或缺陷”。人们总希望看到丰富多侧面的人物形象,看到他们性格的饱满、行为的内在合理性等。正因此,“文学的切身性”就不仅仅体现在作家如何写,还体现为阅读者的消费诉求上。
正如《藏珠记》中那个经历了千年的珠子,照亮人世间的万象一样,这部小说本身也给我们提供了关于文学可资言说的种种话题。文学批评的任务——帮助阅读甄别作品的辅助功能,和凭借“真理、精确性、特性或表达的价值”来分析文学文本;为什么写——在故事、人物、情节、语言等之外,提供“有所得”的东西,不管它是轻的还是重的;怎么写——作品本身的“完成度”问题,以及“文本内部的合理性、完整性”;写什么——强调“文学的切身性”,看中写作者对自我私人经验的挖掘,以及对陌生经验的“内在化吸收”这些文学写作、文学批评和文学阅读的“万象”,在被《藏珠记》这颗“珠子”照亮的瞬间,拷问的不仅仅是写作者,也同样提请批评者的属意——文学批评不但要思考“批评何谓”,还要思考“批评何为”,以及“批评何谓”。正是基于此,《藏珠记》成功与否,意义何在,价值多大,或许已经不是本文所要考量的问题,而是由此出发来思考“文学的万象”,是对作品和作者的负责,也是对批评和自我的负责。
2017年10月18日于人大图书馆圆桌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2016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成果”。
注释
:①乔治·斯坦纳著,李小均译:《语言与沉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
②乔叶:《藏珠记》,作家出版社2017年版,第258页。
③米歇尔·福柯著,莫伟民译:《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83页。
④乔叶:《藏珠记》,作家出版社2017年版,第95页。
⑤乔叶:《藏珠记》,作家出版社2017年版,第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