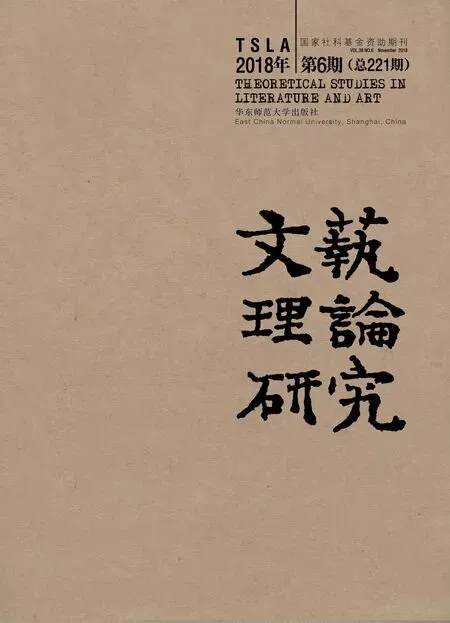杨万里诗学中的意、象、言关系
李瑞卿
杨万里处理意、象、言关系问题在哲学史上具有个性与特别价值,同时,他将这一哲学理论自觉地引入到其诗学体系中,在文学领域形成了独特的意、象、言话语方式。关于意、象、言三者关系的讨论绝不流于经验所得,而是始终以深沉的理论思考探索并深化着这一命题,不仅在学理上严谨自洽,而且内含着儒者的精神诉求。杨万里在诗学上学江西、后山、半山、晚唐,乃至独自树立卓然成家,凡有数变,但最终是以易学为思想渊薮的,其诗学可与其《易》学相互印证。杨万里九种诗集的《序》文,集中在一段时间写成,有的属于后期补写,写作的时间大体在公元1188年左右,也是在这一年,杨万里始作《易传》,又作《易外传序》。《易外传序》论及易道,力主中正、通变,向易求正,向心求易,强调心的感应和通变能力,此种心物关系论与其超越门径、心与物会的诗学方法在逻辑上是一致的;而《易传》中精心结构的意、象、言关系也足以为其诗学讨论意、象、言话语系统提供逻辑基础。值得提及的是,写于1187年的《诚斋荆溪集序》,与杨万里作《易传》《易外传序》几乎在同时,不能排除杨万里以易学思想统摄诗学的企图,更何况在1188年前后,杨万里进行了对诗集序言的补写。而写于1201年的《颐庵诗集序》,重视心物直击,摒弃门径,也将《易论》《易传》中所建构的言、象、意关系渗入到诗学体系中,而有“万象毕来”之论。《易论》是杨万里《心学论》之《六经论》中的一篇,耐人寻味的是,杨万里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尽焚旧作,与笼罩诗坛的江西诗风决裂之时,正是其《心学论》写作时期。下文的讨论将从易学渊源、意象感发、语言表达等不同层面观照杨万里诗学中的意、象、言关系。
一、 意、象、言
关于意、象、言关系的讨论依然是当下文学界无法回避的,尽管现代人眼中的言意关系已非静态的玄学思辨,而是进入到语用层面上的实践与阐释,但我们无法忽视语言运用中文化模式的存在,因为我们无法隔离出原子式的语言,语言往往被建构在一定的模式中来理解和运用。易学中的意、象、言阐释体系就是对中国文化和文学影响深远的一种模式,《周易正义·系辞》(上)说 :“子曰 :‘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 :‘圣人立象以尽意’”(291)。意谓圣人之意的表达需要通过卦象体系来表达,圣人探赜索隐,拟诸形容,立“象”来尽意,也即利用语言、卦象系统来表达圣人之意或天道,从而形成言、象、意的阐释体系。杨万里在阐释《系辞》“设卦立象”章时,也创造性地阐发了这一体系。《周易正义·系辞上》曰:
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261—64)
杨万里认为“象”与辞是用易之功效,并界定“象”与“辞”之含义。《诚斋易传》说 :“此章言君子学易者,必先会易之象辞以为用易之功效也。象者,何象也?六爻之象也,辞者,何辞也?爻辞与象辞也”(205)。圣人设卦,然后有卦,然后有象,然后有辞,所谓“象泯则卦隠,辞废则象晦,卦以象立,象以辞明”。这里的“圣人设卦”,可以看作是圣人之意的达成或对“道”的呈现,所以上述表达是关乎意、象、言之间彼此依存关系的。杨万里还进一步阐明,圣人设卦观象之目的是彰明吉凶,借助对“象”的观察与对系辞的体悟来触及早已蕴含的吉凶之理。《诚斋易传》说 :“谓观其有是象,而吉凶之理已具,系之以是辞,而吉凶之象始明也”,而这“吉凶之理”的产生正是在阴阳结合之后,即“纯阳无吉凶,纯阴无吉凶,或以阳杂之阴,或以阴杂之阳,顺则合,逆则战,逆顺相推,合战万变而吉凶生焉”。至于如何知晓吉凶,需要通过观察爻象当位与否,以及阴阳推移,即《诚斋易传》所谓 :“或以阳居阳,或以阳居阴,或以阴居阴,或以阴居阳,当位则安,不当位则危,当否相推,安危数化而吉凶生焉,故既曰明吉凶。又曰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盖谓某卦之吉凶生于某画之变化,某画之变化生于阴阳之推移”。
卦象的吉凶是事之忧虞,通过吉凶来看事理的得失。杨万里《诚斋易传》说 :“何谓象?物有事有理,故有象。事也理也,犹之形也;象也,犹之影也,不知其形,视其影,不知其事与理,视其象,是故欲知事之得失也。如何?卦爻象之以吉凶,事之忧虞也”,“有失得则吉凶随,有忧虞则悔吝随,此事之形影也。可得而象者也”(205)。这就是说,象就是事理的“影子”,在未知事理之“形”时,可以通过显现的“象”“影”,足以表现事理之实质,也即通过卦象吉凶悔吝可推知事理的得失。
杨万里从设卦、立象、系辞的角度论证了意、象、言之关系,特别强调对事理得失的探赜索隐;他也从学易者玩辞、观象、求道的角度来倡明意、象、言的彼此对应与阐释的关系,他在《诚斋易传》中说 :“君子学易者,因辞求象,象不能外乎辞,因象求道,道不能外乎象”(206)。显然,强调了道不外象,辞外无象,因辞求象的言、象、意彼此依存的阐释路径。而所谓“象”并非抽象地体现圣人之意或道,而是表达着事理。而所谓“言”,是求象之“因”,因辞求象,象不外辞,这与王弼所谓得象忘言、得意忘象之论大异其趣。
在《易论》中,杨万里更有微妙的意、象、言理论,来讨论言与意或道之关系,他认为,如果过分依赖语言,就会“恃此之情,恃彼之愚”,导致“以途为家”而不见真谛;如果忘却言是“道之因”而废弃语言,那么就是“见人之迷于途,而莫之指”,即使民众陷于迷惑而无从得道,导致天下人必然无路可走。杨万里的根本观念还是,在社会实践中,道或意是无法离开语言的,不过需要建构一种微妙的意、象、言系统。杨万里《易论》曰 :“圣人之言,非不能尽意也,能尽意而不尽也。圣人之书非不能尽言也,能尽言而不尽也。曷为不尽也?不敢尽也。《中庸》曰 :‘有余不敢尽。’此《易》与《中庸》之妙也。然则曷为不敢尽也?忧其言之尽,而人之愚也”(《杨万里集笺校》卷843363)。这是对《系辞》中“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创造性阐释。《易论》曰:
圣人之作易,其初有卦而已,象焉在其后。有象矣,辞焉在最后。有辞也,如未始有辞也。杳茫深微,不可得而近也。非不可得而近也,不可得而近者,所以致人之近也。人致于《易》,则近于《易》矣。人之常情,近则狎,远则疑,故《易》之远者,所以投天下以疑而致天下之思也。思则见,见则悦,悦则研,研则诣。故圣人之作《易》也,不示天下以其道之诣,而诣天下以其道之因。(《杨万里集笺校》卷843363)
圣人之《易》巧妙地建立了一套多样的语言系统,首先是设卦,设卦之后立象,立象之后系辞,辞处在这一系统的最末梢。而这“辞”尽管存在,又好似“未始有辞”,“杳茫深微,不可得而近也”。即“辞”与“意”都以消隐的姿态出现,它们在语言系统的最末梢以接近于无的姿态出现,通过远辞及其远意,来“投天下以疑,而致天下之思”,于是,“思则见,见则悦,悦则研,研则诣”,从而获得“道之诣”。这样的语言系统是将道或意的阐释当作一个引起众议、谨慎建构的过程。而言与象似乎最大限度地模仿出了道的原初状态——也指示着道的意义。
二、 万象毕来
杨万里易学中的意、象、言模式对其诗学理论的影响是结构性的。杨万里《易论》的写作与焚其旧作几乎同步,几个重要序文的整理也与《易传》及序文写作时间基本相当。在杨万里诗学中出现了“万象毕来”,以及属于言意问题的“句中”“句外”等重要观念,体现着他对诗学中意、象、言关系的处理方式,或者说,他将易学中的意、象、言模式引入到了诗学当中,而且精巧地完成了哲学话语到诗学话语的转换。杨万里《诚斋荆溪集序》中的“万象毕来”是一个值得论证的、理论内涵深广的诗学命题:
自此每过午,吏散庭空,即携一便面,步后园,登古城,采撷杞菊,攀翻花竹,万象毕来,献予诗材。盖挥之不去,前者未应,而后者已迫,涣然未觉作诗之难也。盖诗人之病,去体将有日矣。方是时,不惟未觉作诗之难,亦未觉作州之难也。(《杨万里集笺校》卷803260)
在此段序文前面,杨万里交代的是他在诗学上的困境,而自从诗学悟道后,他才有此引人入胜的创作体验,这与其诗学与易学的结合存在关联,其中的关键词则应是“万象毕来”。“象”由哲学概念转化为诗学概念以及中国易学与诗学的亲缘关系在理论上是完全可能的,刘勰已然是典范,他将意义与文字、意象关联为一,而不去字外求意,这一点上迥异于王弼。我们需要进一步证明的是,杨万里的“万象毕来”与其易学中“象”之间的内在关联,及其具体含义。
此处的“万象”应当指自然物象。杨万里是在不学唐人及王、陈、江西诸君子之后,步入后园,亲近花竹而获得诗学灵感的。“万象毕来献予诗材”,不可看作是一般的审美表象之类,而是有其审美的路径与独特的文化内涵。张少康先生认为 :“他提出的诗歌创作主张是以自然为师,在现实生活中去寻找诗歌创作的源泉。在这方面他和陆游的观点是一致的,不过陆游偏重在于国家、民族存亡休戚相关的重大社会生活内容,而杨万里侧重在清新秀丽的自然山水景物和富有生活气息的普通悲欢际遇”(179)。张师之论诚是,杨万里正是将目光从对诗法规矩、流派宗脉、模山范水的关注,转移并投射向了活泼自在的自然,从而在自然物象中忽然见道。这当然不仅是诗学上的感悟,而是借助自然物象与心灵的自由会合,获得诗歌与人生境界的超越。因而不得不说,“万象毕来”的情境就是人生的悟道。这里涉及到人心如何感物与感物对象的问题。其中包含两个层面: 其一,什么样的感物方式,使得有此“万象毕来”的胜境。其二,为什么感发对象是自然物象呢?换句话说,感发自然物象即可入道或入于审美自由的理论基础为何?
其一,讨论杨万里的心物关系问题,也即“万象”如何“毕来”。《答建康府大军库监门徐达书》说 :“大抵诗之作也,兴上也,赋次也,赓和不得己也。我初无意于作是诗,而是物是事适然触乎我,我之意亦适然感乎是物是事,触先焉,感随焉,而是诗出焉。我何与哉?天也,斯之谓兴”(《杨万里集笺校》卷672841)。诗歌之作,以兴为上,与外物无意感触,适然逢会,即所谓“我何与哉?天也,斯之谓兴”。意思是说,自我消失了,由自然来言说,而这自然也非纯粹的自然,是中国古人心目中的理想自然,其最终根据则是归源于天理和至善的;我是空无的,物、事是自由的,无心以应而自得天机。这正是“万象毕来”的情境,因无意才能自由自在,才能囊括众象。那么,所谓“无意”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空无状态呢?
此种心物关系模式在《诚斋易传》中是存在着理论原型的。《咸》卦是艮下兑上,《象》曰 :“山上有泽,咸。君子以虚受人。”王弼注 :“以虚受人,物乃感应”(王弼 孔颖达140)。《诚斋易传》卷九解释《咸》卦《象》辞曰 :“山受泽,山之虚,心受人,君子之虚,虚故感,感故应”(97),突出“虚故感,感故应”的思想。《诚斋易传》卷九解释《咸》卦九四爻,主张“虚而照则明”,“无思”而“虚照”。他强调心之作用,反对“废心而任思”。只有虚而照,心中无物,方可无意感知,故而能“穷神知化”。当然“无思”与“虚照”还必须依赖于“心”,没有心之神,即使“无思”也无济于事。《诚斋易传》解释《咸》卦九五爻说,“脢”处膺膈之间,此乃一身“至虚无思之地”,但由于与之相应的“九五”是“膈”,而不是“心”,所以这种感应只能是“无思而不神”的昏懵,而非“无思而神”。杨万里在此突出了“心”的重要性,事实上,杨万里认为圣人是可以聚天地之神于一心的,而“聚于一心之精”、不疾而速的感应,又是建立在万物彼此之间、万物与人心之间建立的感应关系的基础上的。即《诚斋易传》所谓“岂唯心之能神哉?物理亦有之,铜山东倾而洛钟西应”,“其母啮指,而其子心动”(222)。既然不疾而速,超越了时间与空间,这样的感应就是气理相通的精神之感。
其二,我们来看看感发自然物象的哲学理路。中国美学与文学中存在着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那就是通过对自然物的感发与体悟而可以进入自然之道。《庄子》中逍遥境界是无待的,只有无待才能逍遥与自然,后世的哲学家证明了有待也可进入逍遥,于是有向秀、郭象的“与物冥冥,循其大变”、支遁的“物物而不物于物”之论(刘义庆220),从而将对自然之道的把握关联于具体的自然物,这一思路体现在山水诗作家那里即是徜徉于自然山水便可澄怀味道,归于自然。其实,《周易》之易道也是自然之道,而自然物象是自然之道的象征,自然变化通过自然形象来体现。杨万里在其易学思想中对此论证颇多,他在《诚斋易传》阐释《系辞》“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时说,“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何谓也?曰: 有物可见,无物可执之谓象。有物可见,有物可执之谓形。日月在天,象也;山泽在地,形也;天垂日月之象,故易之坎离可见天之变化;地出山泽之形,故易之艮兑可见地之变化。变化者,天地之至神也,孰得而见之者,形象著而变化不可隐矣”(203)。意思是说,自然化生而有形象变化,这些形与象就是日月山泽等自然形象。在阐释“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时说 :“此言天地斡流,而成万化之神,乾坤错综,而生六子之妙也。以乾之刚而错摩坤之柔,以坤之柔而错摩乾之刚,一刚一柔,相推相荡,鼓之以雷霆而为震,莫之鼓而鼓也,润之以风雨而巽坎,莫之润而润也。日月运行,夫寒暑而为坎离,莫之运而运也。然得我之刚者为长男,为中男,为少男;得我之柔者为长女,为中女,为少女,成男成女,莫之成而成也。三才之天地人,易之乾坤其神矣乎!其妙矣乎!”(204)俨然是苏轼“我有是道,物各得之”的思路,但杨万里在苏轼基础上充实了乾坤之外其它六卦的内容,以六卦为六子,而且它们的产生是自然现象变化,所谓“鼓之以雷霆而为震,润之以风雨而为巽坎”,也即强调了自然变化中的雷霆风雨即是变化之因。易道的变化,不仅是抽象的阴阳刚柔,而且还是具有自然内容的具体变化。前文所述,杨万里认为通过卦象可见吉凶,沿着其思路,通过自然现象也一定不难见到事理悔吝。在这个意义上,杨万里认为,通过自然物象完全也可以进入道的境界。类推于诗学,杨万里是通过感发自然物象而进入到审美的境界的。如果说杨万里易学中通过卦象来看事理之吉凶,那么在其诗学中也表现了对事理得失的重视。《诚斋诗话》中说 :“大史公曰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左氏传》曰 :‘《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此《诗》与《春秋》纪事之妙也”(丁福保139)。将《诗经》与《春秋》比类,正是为突显诗歌的纪事之妙。
总之,杨万里将目光转向自然物象,求得“万象毕来”的诗意,是他有意建构的诗学逻辑,有着深厚的哲学基础。重视自然物象及事理也确实是杨万里诗歌的重要特征。《寒食雨中同舍约游天竺,得十六绝句,呈陆务观》其二 :“笋舆冲雨复冲泥,一径深深只觉迟。孤塔忽从云外出,寺门渐近报侬知”(《杨万里集笺校》卷201007)。物象次第出现,直接写来,虽然不做玄远的思考,但不乏深永的趣味。其九 :“城里哦诗枉断髭,山中物物是诗题。欲将数句了天竺,天竺前头更有诗”(201008)。即是以自然物为题,而获得层出不穷的诗意。《丰山小憩》 :“归路元无远,行人倦自迟。野香寒蝶聚,秋色老枫知。得得逢清荫,休休憩片时。江山岂无意,邀我觅新诗”(卷5295)。写归路迟缓,路遇野香、寒蝶、秋色、老枫、清荫,以及倦困休憩,可谓一片江山,满目诗意。
如何去体悟杨万里笔下的自然万象,应当以其哲学观念和处理心物关系的方法论为钥匙。钱钟书先生对杨万里如何捕捉自然物象有所论述,他说 :“诚斋则如摄影之快镜,兔起鹘落,鸢飞鱼跃,稍纵即逝而及其未逝,转瞬即改而当其未改,眼明手捷,踪矢蹑风,此诚斋之所独也”(钱钟书118)。以追踪物象之飘忽递转为杨万里的摹写功夫,这与杨万里本人的审美方法与风格特征并不吻合。不妨细读下面绝句,《寒食雨中同舍人约游天竺,得十六绝句,呈陆务观》其四 :“破雨游山也莫嫌,却缘山色雨中添。人家屋里生松树,穿出茅檐却覆檐。”其五 :“小溪曲曲乱山中,嫰水溅溅一线通,两岸桃花总无力,斜红相倚卧春风”(卷201008)。前一首,写雨中山色,写屋里生松穿出茅檐又覆盖着茅檐,描绘的是自然的光色与姿态;后一首则写两岸桃花无力,斜卧于春风之上,彼此相依,是一番春风沉醉的趣味,从理论上来归本推源,杨万里不过是以虚无之心观照自然物象,从中见道,默然兴会。
钱钟书先生是以苏轼的审美论来阐释杨万里摹写自然的方法。关于苏轼的理路,从《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可窥见一二: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节叶具焉。自蜩腹蛇蚹以至于剑拔十寻者,生而有之也。今画者乃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与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识其所以然。夫既心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不学之过也。故凡有见于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视了然,而临事忽焉丧之,岂独竹乎!
子由为《墨竹赋》以遗与可曰 :“庖丁,解牛者也,而养生者取之。轮扁,斫轮者也,而读书者与之。今夫夫子之托于斯竹也,而予以为有道者,则非邪?”子由未尝画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岂独得其意,并得其法。(苏轼365—66)
文与可为何要如此迅疾?他欲捕捉到物象的神采,欲把胸中之竹淋漓展现,这需要得自然之数,应自然之道;另一方面,也涉及到心手相应的问题,唯有振笔直遂才能得其意思所在。虽是论画,于诗亦然。按照苏轼的逻辑,摹写事物正如庖丁解牛一样是一个得道的过程,而在杨万里这里,自然事理本身就在自然物象之中;从心物关系来看,杨万里是虚照而明的与物感应,唯有如此才能万象呈现,而苏轼则是系风捕影,合于自然之道。对于自然物象的重视在杨万里这里是空前的,他找到了理论上的依据,也在苏轼的基础上有所拓展,以儒家的心态来观察外物之变化,将对自然物的描写日常化、生活化,也将生活化、日常化的描写哲理化,将悟道和诗作融合在平常起居之中,显示出了一种清浅的风尚。这清浅的风格与诗心是依赖于道心的。
三、 意在句中
关于言意关系的讨论在中国哲学史上颇为盛行,以佛道文化为背景的言意论倾向于认为语言无法表达意义,因而主张或放弃语词,不立文字,或者简略其意以期无言之美。不过,如果没有语言的表达,我们无从看到所谓的无尽之意,意义无论如何是要通过语言来表达的,只是表达方式有所不同而已。正如前文所论,杨万里在言意问题上独树一帜,他认为,圣人不是无法尽意而是他们认为直接用语言尽意容易引起误解,正如《易论》所说 :“忧其言之尽,而人之愚也”(《杨万里集笺校》卷843363),所以要立象,然后系辞,而这辞又好像“未始有辞”。简言之,道不外象,辞外无象,因辞求象。言可尽意在中国哲学中是主流,即使是《老子》《庄子》中的语言观,也在强调着言的重要,如果说,无名到有名是必然,那么语言的出现也是必然的;《庄子·齐物论》曰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郭庆藩79)。语言无法不存在,否则不能确认“一”,也因为这语言,世界便演化到无穷。欧阳建作《言尽意论》 :“原其所以,本其所由,非物有自然之名,理有必定之称也。欲辩其实,则殊其名;欲宣其志,则立其称。名逐物而迁,言因理而变,此犹声发响应,形存影附,不得相与为二。苟其不二,则言无不尽,吾故以为尽矣”(欧阳询384)。论证是颇为有力的,北宋邵雍也说“有意必有言,有言必有象,有象必有数,数立则象生,象生则言彰,言彰则意显。象数则筌蹄也,言意则鱼兔也,得鱼兔而忘筌蹄可也,舍筌蹄而求鱼兔则未见其得也”(邵雍,卷13)。明末清初王夫之说 :“天下无象外之道”(王船山212),“言、象、意、道,固合而无畛”(214),深受儒学浸润的文学家在实际创作中也在坚守着言可达意的信仰。刘勰的语言观也是如此,他超出了言尽意与言不尽意的讨论界域,让语言进入到创作的枢机之中,成为与情感同等地位的本体,刘勰《神思》篇说 :“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范文澜493),即相对于语言来说,人的感觉和情思是虚位,意象必须落实在语言中,也即思——意——言是同一过程。《神思》篇说 :“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是以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义在咫尺而思隔山河。是以秉心养术,无务苦虑;含章司契,不必劳情也”(494)。思、意、言三者合一是刘勰的理想,更重要的是这一境界也是语言的世界,而非只可意会、无法言表的心理境界。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的言,不仅指语音而且也指文字,文字是可以表达世界与意义的,或者说文字就是世界与意义,这与站在语音中心主义立场上的胡塞尔不同,也与赞成文字、反对语音中心主义的德里达也不同。德里达在《书写与差异》中认为,记载上帝笔迹的书从未出现,出现的只是其踪迹,“这种神学上的确定性注定已失落了”,从十九世纪开始,这种意识就构成了现代的自我理解的典型特征(191)。不过,德里达虽然重视文字书写,但对文字并不是完全信赖的。哈贝马斯评价道 :“在此过程中,德里达根本没有考虑到‘书写文字的牢固性’,而是首先关注这样一种情况: 书面形式把文本从发生语境中分离出来。书写使言词独立于作者的精神,也独立于接受者和言语对象的在场性。书写媒介赋予文本一种冷漠的自主性,使之脱离了一切生动的语境”(193)。在德里达看来,语言符号与作者之意及世界是割裂的。
杨万里把意义落实在了语言中、文字中,准确地说是落实在句中。我们需要探讨一下著名的《和李天麟二首》其一,其诗曰 :“学诗须透脱,信手自孤高。衣钵无千古,丘山只一毛。句中池有草,字外目俱蒿。可口端何似,霜螯略带糟”(《杨万里集笺校》卷4199)。对于这首诗的解读,马东瑶认为,首先是对“自然”的强调,“句中池有草”是为纠雕镂之弊;其次,“字外目俱蒿”指出诗歌当寄寓作者关怀世事之心,“目蒿”之语出自《庄子·骈拇》 :“蒿目而忧世之患”;其三,“可口端何似?霜螯略带糟。”是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强调诗歌当有言外之“味”(马东瑶36—41)。综其大意是,杨万里主张自然,关怀世事,讲究言外之味——这代表了当下比较普遍的看法。可是,当我们放下先见,重新审视这首诗时,才发现该诗的主要意旨与关怀世事、言外之味无关,而是主张透脱学诗以达到超越门户、直击自然的自由的创作与审美境界。如此信手而来的孤高卓异的境界,也正是杨万里所强调的即目成诗、言象为一的审美境界。在杨万里这里,创作的通脱自由与具体文字句子是相互关联的,句子的存在、语言的表述是整体诗意的基础,所以,他强调“句中池有草”,也即句子中的生机和内蕴,就如同“池塘生春草”——强调句子之内的诗歌语言意象的存在和诗意的盎然滋长。与之相对,“字外目俱蒿”是告诉人们不要在字外来求意,因为语言之外,意义遥远不能看见,求意字外,就是目中尽蒿,蒿草挡目;蒿草细微,最易染尘,故人们昧眼于尘世。清陈大章撰《诗传名物集览》卷9曰 :“《尔雅翼》: 庄子称今之君子蒿目而忧世之患。蒿细弱而阴润,最易栖尘,故以为比,言昩眼尘中而忧世也”(陈大章,卷9)。此解切意,“目俱蒿”首先指的是被遮挡,将“字外目俱蒿”解释为关心世事是不准确的。那么,“可口端何似,霜螯略带糟”就不是比喻言外之味,恰好相反,指的是言内之味。以味论诗不假,但首先强调的是构成诗味的具体内容,也即不依赖玄虚的想象而索求诗味,而是品味构成其句子的元素与成分。
以句子为单位,重视其表达,是杨万里诗学的重要观念。《和李天麟二首》其二也是讨论句子的。它说 :“句法天难秘,功夫子但加。参时且柏树,悟罢岂桃花?要共东西玉,其如南北涯。肯来谈个事,分坐白鸥沙”(199)。句法的秘密是存在的,只要加以功夫即可得法,虽然来自参悟所得,但依旧要回归本义,“柏树”与“桃花”句典出《五灯会元》,据《五灯会元》卷四 :“(僧)问 :‘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赵州从谂)曰 :‘庭前柏树子。’曰 :‘和尚莫将境示人?’师曰 :‘我不将境示人。’曰 :‘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 :‘庭前柏树子’”(普济202)。《五灯会元》卷四“灵云志勤禅师”有一则公案: (志勤禅师)初在沩山,因见桃花悟道。有偈云 :“三十年来寻剑客,几回落叶又抽枝。自从一见桃花后,直至如今更不疑。”沩览偈,诘其所悟,与之符契。沩曰 :“从缘悟达,永无退失,善自护持”(239)。综合两则公案来看,桃花与柏树借以悟道的,但悟道后桃花还是桃花,柏树还是柏树。这一思想进入到杨万里的诗学后,体现为对自然万象的重视。
前期的维特根斯坦在其《逻辑哲学论》中就认为世界是事实的总和,通过引入图像这一概念,将事实解释为思想,然后进一步说明思想是句子所表达的东西,句子和世界是对应的,通过对句子的探讨可以解决对世界的探讨(王路54—59)。杨万里聚焦于句子也有其自身逻辑,事理或意义可以被象与辞表达,那么,句子作为相对完整的意义单位也是诗意所在。比如在《诚斋诗话》中说:
诗有一句七言而三意者,杜云“对食暂餐还不能”,退之云 :“欲去未到先思回。”有一句五言而两意者,陈后山“更尽可无醉,犹寒已自知”诗。有句中无其辞,而句外有其意者。《巷伯》之诗,苏氏刺暴公之譛已,而曰 :“二人同行,谁为此祸?”杜云 :“遣人向市赊香秔,唤妇出房亲自馔。”上言其力穷,故曰赊;下言其无使令,故曰亲。又 :“东归贫路自觉难,欲别上马身无力”,上有相干之意而不言,下有恋别之意而不忍。又 :“朋酒日欢会,老夫今始知。”嘲其独遗己而不招也。(丁福保138)
杨万里句中觅意,指出有一句七言三意,也有一句五言二意,在句子的曲折变化中来表达层次密匝的意义,这与其“万象毕来”的审美感受是两两相应的。将意象凝固在句中,将意义分布于言辞之内,正是杨万里努力的方向。同时,语言文字在其形式化方面也有其独立性,句子含蕴多意的意图和方法,也会促使作者去剖情析采,可见,诚斋体的出现是有完备而深刻的理论支持的,与其哲学观念、语言论密不可分。其中诚斋体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因为其深厚的儒学背景与苦心孤诣的诗学方法,他不去刻意寻找所谓言外之意,尽管他并不反对言外之意义。当然,是否有言外之意也非作家个人主观能控制的。即使出现“有句中无其辞,而句外有其意者”的情况,所谓句外之意依然是通过句子的言辞来达到的。
在杨万里的理论中,意义通过句子的细致表达与言外之意的生成是并行不悖的,言外之意的存在依赖于辞藻字句的精心结撰。《诚斋诗话》说:
唐律七言八句,一篇之中,句句皆竒,一句之中,字字皆竒,古今作者皆难之。余尝与林谦之论此事。谦之慨然曰 :“但吾軰诗集中,不可不作数篇耳。如老杜《九日》诗云 :‘老去悲秋强自寛,兴来今日尽君欢。’不徒入句便字字对属,又第一句顷刻变化,才说悲秋,忽又自寛,以‘自’对‘君’甚切,君者君也,自者我也,‘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正冠。’将一事翻腾作一联,又孟嘉以落帽为风流,少陵以不落为风流,翻尽古人公案,最为妙法。‘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寒。’诗人至此,笔力多衰。今方且雄杰挺拔,唤起一篇精神,非笔力拔出,不至于此。‘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则意味深长,幽然无穷矣。”(丁福保139—40)
在杨万里看来,唐代律诗的魅力与成就是建立在句法和字法上的,句句皆奇,字字皆奇,才能见到效果。因为诗话中的分析实在锋芒毕现、准确到位,所以抄录如上,正如杨万里分析杜甫《九日蓝田崔氏庄》,先说老境遇悲秋,忽然又自我宽慰,又能与君共欢,可谓句奇字奇。而“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两句,杨万里评为“意味深长幽然无穷”,这意味来自扎实的修辞。写眼前嘉会,却遥想明年光景,醉把茱萸之态,如现目前,于是,现在与明年、当下与远景之界限消失,成为永恒之美,意味深长之感便油然而生。体会杨万里的此种发现,我们不得不为杜甫的精工字句和杨万里的修辞敏感折服。“明年”与“此会”、“知”与“谁”、“醉把茱萸”与“仔细看”,是以彼此意义的相互对立却又彼此映照的奇趣来达到意象突显又迷离恍惚的境界的。杨万里对东坡诗中之层叠之意的剖析也非常精彩。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有《诚斋诗话》曰 :“东坡《煎茶》诗云 :‘活水还将活火烹,自临钓石汲深清。’第二句七字而具五意。水清,一也;深处清,二也;石下之水,非有泥土,三也;石乃钓石,非寻常之石。四也;东坡自汲,非遣卒奴,五也”(140)。五种意思的析出无疑是精确的,可谓辨析毫厘,切中要害,从严丝合缝的字里行间读解到丰赡的内蕴。此外,杨万里也从具体的句法和用词来解读苏轼诗,《诚斋诗话》云 :“‘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其状水之清美极矣,分江二字,此尤难下。‘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仍作泻时声。’此倒语也,尤为诗家妙法。即少陵‘红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也。‘枯肠未易禁三碗,卧听山城长短更。’又翻却卢仝公案。仝吃到七碗,坡不禁三碗,山城更漏无定,长短二字,有无穷之味”(140)。“分江”二字确非轻易得来,以小勺舀水入瓶,可称为“分”,所分者无非是水,但这水来自江中,所以不叫分水,而叫“分江”,突出了它的来历以及与江河的一体性。于是,“分江”,既是分又不可分,从而将带着月色、倾入夜瓶之水,与天地日月江河湖海浑沦为一了。
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是,杨万里对杜甫与苏轼诗学精髓揭示或摄取是通过字句层面来完成的。他相信意义是要通过句子来表达的,丰富的意义来于具体而微的修辞,言外之意则根植于表达的竭尽全力与精确性,而非来自故意的含蓄吞吐。另外,对一句之中多层意思的推崇,是与他对事理雏形的敏锐感受不可分的。
注释[Notes]
① 杨万里诗集写作跨度46年,而为诗集作序集中于6年内。参见张瑞君 : 《杨万里评传》(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② 杨万里《易外传序》曰 :“斯道何道也?中正而已矣。唯中为能中天下之不中,唯正为能正天下之不正。中正立而万变通,此二帝三王之治,孔子、颜、孟之圣学也。”不过,通变和中正之道的归结点却在于心,“然则学者将欲通变,于何求通?曰道。于何求道?曰中。于何求中?曰正。于何求正?曰《易》。于何求《易》?曰心。”见杨万里著、辛更儒笺校 : 《杨万里集笺校》第6册,卷84,第3254页。
③ 关于《易论》中意、象、言关系的讨论李瑞卿也有详尽论述 :“杨万里去词去意论发微”,《文学遗产》2(2013): 62—68。
④ 杨万里《易论》曰 :“是故不得离于言。不离于言者,不废其道之因也。不废则恃此之情,恃彼之愚,是故不得不离于言。离于言者,不恃其道之因也。以道之因者,可忘而废言,见人之迷于途而莫之指者也。以道之因者,不可忘而恃言,指人以途而谓之家者也。莫指其途,天下自此绝,指途为家,天下自此愚。”见杨万里著、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第6册,卷84,第3362页。
⑤ 刘勰建构的意、象、言关系与王弼大异其趣,他承认易道中的意、象、言阐释模式。《原道》篇曰 :“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为先。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若乃《河图》孕八卦,《洛书》韫乎九畴,玉版金镂之实,丹文绿牒之华,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文中可见,其一,圣人幽赞神明与庖牺画卦,仲尼十翼(包括系辞、文言)构成的意、象、言符号体系中象可表达意,言可阐释象。其二、神理、《河图》《洛书》,以及玉版金缕、丹文绿牒(文字符号)也构成了意、象、言的阐释体系。《神思》篇中便有意授于思、言授于意的思维逻辑,意、象、言是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神思·赞》中说 :“神用象通,情变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应。刻镂声律,萌芽比兴。结虑司契,垂帷制胜。”在此体现的也是言、象、意结合融创的境界。
⑥ 杨万里解释《咸》卦九四爻曰 :“九四在一卦之体,如一身之心也,不言心而言思,责其废心而任思也。心者身之镜,思者镜之翳,镜则虚而照,思则索而照,虚而照无物也,索而照有物矣,惟无物者见物,有物矣,安能见物哉!故虚而照则明,索而照则昏,仲尼系之曰 :‘天下何思何虑?’,盖此心。何思何虑则虚,虚则贞,贞则吉,何悔之有?今也不然,憧憧焉役思于事物往来屈伸之变,故思未能感通于事物,而事物万绪朋来,从之而不胜其扰且害矣,非如贞吉无思之时,未感而无害也。以思穷物,适以物穷思,安能穷神知化,而成光大之盛德哉?唐德宗之猜忌以之。”杨万里 : 《诚斋易传》(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98页。
⑦ 杨万里解释《咸》卦九五爻 :“王弼云 :‘“脢”者心之上,口之下。’其膺膈之间乎?此一身至虚无思之地也。九五当之,宜其为咸,感之盛也,止曰‘无悔’,何也?盖无思而神则明,无思而不神则昏,神者心也,不神者膈也。膈虽无思,昏懵而已,九五是也。”杨万里 : 《诚斋易传》(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98页。
⑧ 苏轼在秩序的前提下,以“用息功显”为主导思想来讨论乾坤、男女之道 :“及其用息而功显,体分而名立,则得乾道者自成男,得坤道者自成女。夫男者,岂乾以其刚强之徳为之,女者岂坤以其柔顺之道造之哉!我有是道,物各得之,如是而已矣。”参见苏轼 : 《东坡易传》(卷7,四库全书本)。
⑨ 苏轼宇宙观和道论中,认为宇宙由八卦相荡而产生,自然之道自在其中。《东坡易传》卷七中说 :“天地之间,或贵或贱,未有位之者也,卑高陈,而贵贱自位矣。或刚或柔,未有断之者也,动静常,而刚柔自断矣。或吉或凶,未有生之者也,类聚群分,而吉凶自生矣。或变或化,未有见之者也,形象成,而变化自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雷霆风雨,日月寒暑,更用迭作于其间,杂然施之,而未尝有择也,忽然成之而未尝有意也。”见苏轼 : 《东坡易传》(卷7,四库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