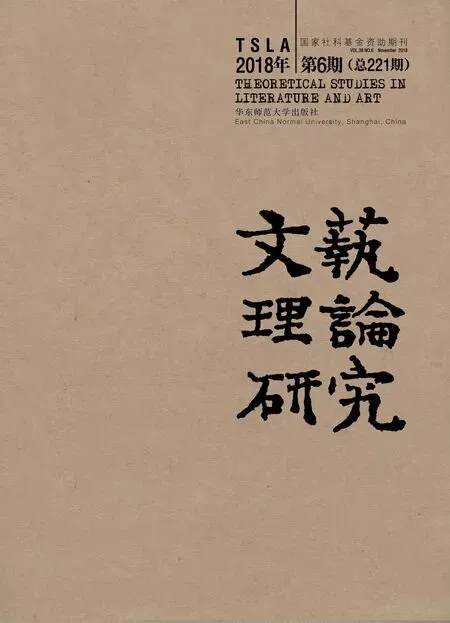“情动”理论的谱系
刘芊玥
近二十年以来,“情动”理论(affect theory)日益成为中西方关注的焦点。许多从事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者已经开始探索情动理论,并将之作为理解经验领域(包括身体的经验)的一条道路,这是超越当时基于修辞学和符号学主导范式的另一种范式。一些消极的词汇在学术研究领域频繁出现,比如“创伤”“忧郁”“无常”“残酷”等等,这些词汇作为一种新的文化现象,体现出“911”之后西方社会的一种普遍忧患意识。它延伸出一种疑惑甚至是质问,其矛头是新自由主义下的当代秩序。在这样的背景下,当代性正脱离现代性的话语范式,呈现一种更加短暂、临时和模棱两可状态的特点。“情动”理论正是在这样一种质问式的写作背景下展开。
“情动”(affect)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始于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后由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瓜塔里(Félix Guattari)将其发展成为有关主体性生成的重要概念。在《伦理学》中,斯宾诺莎将“情动”视为主动或被动的身体感触,即身体之间的互动过程,这种互动会增进或减退身体活动的力量,亦对情感的变化产生作用。斯宾诺莎提出的问题要测度的不是事物的各种状态,也不是去给出好坏高低强弱的标准,他感兴趣的是由一种状态到另一状态的运动和转化,由强到弱或反之的动态,并根据所能受到的影响与所能改变的幅度来定义身体是什么。他将之称为“情动”。德勒兹在其关于斯宾诺莎的著作中,着重阐释了这个概念,并在《千高原》中对其进行了创造性的解释。受德勒兹的启发,当今一大批理论家对此概念进行研究,并借助它解释一些文化现象,以至于当代的文化、艺术、思想、政治等领域中出现了所谓的“情动转向”(affective turn),这成为很重要的理论现象,也是一种新的理论上的景观。
在欧美和澳洲的思想界,对于情动理论的研究大致可以分成哲学本体论意义上的情动理论和女性主义情动理论两部分。前者以斯宾诺莎、德勒兹和马苏米(Brian Massumi)为代表,后者以汤姆金斯、塞奇维克(Eve Kosofsky Sedgwick)、贝兰特(Lauren Berlant)等人为代表。这两条脉络以马苏米为节点,常常相互交织使用。期间还伴随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枢纽人物,霍尔曾经的学生和助手,美国文化研究界最具影响力的学者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他成为带动了文化理论中对情动理论进行研究的生生不息的力量。
一、 斯宾诺莎的先驱意义: 情动的起源和性质
“情动”研究的源头,即有关情动本体论研究的开端,是从荷兰哲学家巴鲁赫·斯宾诺莎开始的,他的思想是当代大多数学者研究这一领域的源头。“情动”是斯宾诺莎哲学体系里的一个概念,正如斯宾诺莎在他的《伦理学》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里讨论的那样,“情动”是一种身心同感觉、情绪相关联的状态。
那么,当我们回到其源头,“情动”何以作为一个问题在斯宾诺莎处被谈论?在《伦理学》中,斯宾诺莎提出他之所以进行情动研究的动机缘于他认为,情动是来自于不适当的观念,是人生软弱无能和变化无常的原因,但它不应该被归结为人性的缺陷,因为这些情绪和自然万物一样,都出于自然的必然和力量,因此情动也有其确切原因和性质,并且可以被理解且值得我们去重视。与笛卡尔试图通过提出一些伦理原则来改良这些缺陷不同,在斯宾诺莎看来,没有任何东西是源于自然和人的缺陷,也没有一个人真正了解情动的性质、分类以及应对它的方法。因此,他决定借用笛卡尔的几何学研究法来反笛卡尔,采纳几何学方法和对数学自明性的信念来考察情动的本性和力量,以及心灵如何可以克制情感,这是斯宾诺莎在《伦理学》中的任务。
在《伦理学》第三部分“论情动的起源和性质”这一章中,斯宾诺莎首先区分了“整全原因”(adequate cause)和“部分原因”(partial cause)、“主动”和“被动”这两对基本范畴。“心灵具有整全的观念时便主动,具有不整全的观念时就被动,心灵拥有愈多不整全的观念,就愈容易陷入激情(passion),反之,愈能自主”(100)。在他看来,如果我们是事情的整全原因,即如果发生在我们身上和身边的事情,都是来自我们自身的本性,只借助我们自己就能明晰地了解此物,那么我们可以称之为主动的;如果我们是事情的非整全原因,如果我们只是发生在我们身上或身边的事的部分原因,我们则被称为被动的。在第三部分的第三个定义中,首次出现了斯宾诺莎对于情动的第一次界定 :“我将情动理解为身体的应变,会使身体活动的力量增强或减弱、滋益或受限,同时也理解为这些应变的观念”(98)。在斯宾诺莎这里,情动首先是一种身体的状态,并是其观念。“观念”在这里强调的是,身体的行动经过心灵的确认,才成其为“情动”,心灵的确认是前提之一,情动仅指人类的情动。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斯宾诺莎开始了对于人类的48种情动的考察和探讨。
斯宾诺莎对于“情动”的探讨,主要分为三种基本类型: 快乐(joy)、痛苦(sorrow)和欲望(desire)。这是三种基本情动。其它情动诸如惊异、轻蔑、爱、恨、偏好、厌恶、敬爱、嘲笑、希望、恐惧、信心、失望等,皆源于这三者。这三种基本的情动类型在斯宾诺莎看来,都是在人作为被动者的情境下产生的。其中,当心灵由较小完满的情感过渡到较大完满的情感,称之为“快乐”;当情感由较大完满的情感过渡到较小完满的情感,称之为“痛苦”。他把“欲望”肯定为人的本质,因为在他看来,人的本质是被设想为会因为任何应变而注定去做某些事,欲望就是意识到偏好本身的偏好,而因为人的本质是受决定去做能促进其自我保存的事,所以说,偏好就是人的本质(146)。而“快乐”和“痛苦”则是所有情动的基础,因为所有的情动都以快乐和痛苦为条件,所有的情动中都包含着快乐或不快乐。斯宾诺莎以几何学的方式将这些“情动”推衍而出,却不对它们的伦理价值做出评判。他对人类的三种基本情动和由此而来的诸种重要情动给予详细的列举和考察。在他看来,所有的情动都没有善恶之分,虽然我们在很多情况下会被外物所扰、徘徊动摇、担心自己的前途命运,然而每个人的一切都由情动所掌控,困于相反情动的人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没有解脱之道,但不受任何情动所动的人则更容易处处摇摆(103)。斯宾诺莎在这里主要论述的是主要的心灵矛盾,而非一切心灵矛盾。一切情动都是不完美的,但不能说因而它们是坏的。
在此基础上,斯宾诺莎提出了他的“心物平行”说,并以此来考察情动。哈特(Michael Hardt)曾说,斯宾诺莎使得我们“每次考量心灵之思考的力量的时候,我们必须同时尝试着去辨识身体的行动的力量,是如何与心灵之思考的力量对应的[……]这一点很重要,就其同时标示着心灵与身体的当下状态而言,情动横跨于这一关系之上[……]从而使得我们不断提出身心关系的问题”(Negri and Hardt 77-88)。在斯宾诺莎看来,心灵思考的力量平行于身体之行动的力量,然而心灵不能决定身体,身体也不能决定心灵,两者是两个封闭的系统,彼此不相来往,它们是两套平行的对应关系。所以,如果说笛卡尔把身与心作为两个分离的实体,那么到了斯宾诺莎这里,他认为只有“神”这一个唯一且无限的实体,身和心不过是一个实体的不同表现模式,前则遵循物理性的因果律,后者遵循的是感觉、记忆和概念的法则。而两者之所以看似有关联和一致性,是因为两者都被一个实体所据定和影响着。在《伦理学》里,斯宾诺莎并没有完全解决身和心的关系的问题,但却将其作为一个问题提了出来。由于弗洛伊德、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及其临床实验的兴起,斯宾诺莎的身—心问题,虽然在理论框架上遭到挑战,但仍构成主导的(核心的)理论问题持续至今。他用一种科学理性几何学的方式对人类的诸种情动作严密的考察和分析,洞悉它们的永恒状况和性质,这在思想史和学术史上都是第一次。
通过此说明,斯宾诺莎将“情动”与被动联系在一起,从而在事实上给予了其消极的评估。后来很多当代研究情动理论的学者对斯宾诺莎赋予消极色彩的“情动”进行了拓展,如有的学者认为斯宾诺莎对于情动“尚未到达”(not yet)的描述是作为一个“希望的承诺”(promise)而存在,在此方面最直率的作品来自于英国女性主义者、文化理论的研究者艾哈迈德(Sara Ahmed)和她的《幸福的承诺》,英国文化政治地理学家安德森(Ben Anderson)的《生成和希望: 朝向一种情动的理论》,美国从事文学、文化理论和批判理论的女性主义学者贝兰特和她的《残酷的乐观》;也有很多学者认为这种“not yet”是一种永远的不确定和没有最终的保证,它也可能会更糟,因此是作为一种“威胁”而存在,如格罗斯伯格在讨论“被接收的(received)”现代性和可替代性、共存的现代性时强调了这样的一种状态;马苏米在《未来的情动起源》里借助美国政治上的一系列行动提出了“威胁”这一观念(“The Future Birth”52-70);克拉夫(Patricia Clough)在她有关资本和物质的情动能力纠葛的分析里也反映出相似的观点(206—25)。因此,情动是一种“希望”抑或是一种“威胁”,这本身而言是当代学术界争论的一个议题。
和上述相关的是,斯宾诺莎在他对情动的界定中,还在本体论的意义上界定了情动的“善”与“恶”的品质,“所谓善是指一切的快乐,和一切足以增进快乐的东西而言,特别是指能够满足愿望的任何东西而言。所谓恶是指一切痛苦,特别是一切足以阻碍愿望的东西而言。[……]我们并不是因为判定一物是好的,然后才去欲求它,反之,乃是因为我们欲求义务,我们才说它是好的”(Spinoza119-20)。后来研究情动的学者也自然而然地将情动分为“负面情动”(bad affect)的黑暗叙述和“正面情动”(good affect)的优雅叙述,前者向人们呈现各种消极的面貌和结果,后者意味着情感理论在政治上积极的影响。尽管这两种叙述常常证明了: 主体比我们想象的更容易受到影响。学界也有理论上的“情动转向”是一种本体论上的转向的这一论说。这一切的影响是斯宾诺莎在提出“情动”这样一个命题的时候便一直伴随而来。
二、 德勒兹的遗产: 情动与观念的生成
德勒兹是从斯宾诺莎过渡到马苏米的理论桥梁和殿军人物。“情动”(affect)和“情状”(affection)变得引人注目是在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和费利克斯·瓜塔里合写的《千高原: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之后。在一篇名为《德勒兹在万塞讷的斯宾诺莎课程(1978年—1981年)记录——1978年1月24日情动与观念》的授课稿,以及他在1993年出版的《批判与诊断》里,德勒兹先后重点谈论了有关“情动”的概念评述。在“情动”的谱系上,德勒兹的贡献主要有三个。首先,他明确区分了“情动”和“情状”,以“强度”(intensity)的概念取消了斯宾诺莎有关身体/心灵二分的观念;其次,斯宾诺莎的情动理论是属人的,而德勒兹赋予它以非人的维度,使之脱离情动须由心灵确认的原初涵义。最后,他将“情动”概念纳入其“流变—生成”的理论体系,进而着重阐发出所谓“积极情动”的面向。
德勒兹首先批评了斯宾诺莎的《伦理学》的诸多版本的法文译本中错误的译法,即在斯宾诺莎用拉丁文写成的《伦理学》原文里,没有对affectio和affectus做出区分,而将其都翻译成了affection。他明确指出,斯宾诺莎用了这两个不同的词在他的哲学著作中是基于一定的理据,在法文中,有明确的对应词,用affection译affectio,以affect译affectus,前者是“情状”,后者是“情动”。为了探讨情动,德勒兹先从对于“何为一个观念”的界定说起,他认为,观念是“一种表象某物的思想样式”,究其表象某物而言,被视作具有一种客观现实,比如三角形的观念就是对三角形进行表象的思想样式。这是区分“观念”和“情动”的出发点。在德勒兹看来,希望和爱并不是“观念”,而是“情动”,因为希望和爱本身并不表象任何对象,但却基于某个被爱者、被希望者观念,因为观念总是先行于情动。这是德勒兹对于观念和情动做出的区分,也是他对于情动的第一次界定。同时他指出,这种观念在具有一种客观现实以外,还拥有一种形式现实,这个形式现实就是“它自身就是某物”。在“所有观念都是某物”的基础上,他再现了斯宾诺莎意义上“观念总是彼此相继的”的观点,即一个观念总是接续着另一个观念,与其说我们拥有观念,不如说观念在我们之中显示自身。这里出现了德勒兹增加的另一维度,斯宾诺莎强调的是观念本身的相互接续,而德勒兹强调的是这种相互接续本身对“我”的影响,也就是说,“在我之中不断变化的某种机制”,与观念自身的接续不同,这是一种“存在之力”(force of existing),或者“行动之力”(the power of acting)。这种“存在之力”会因为相遇到的某物给予“我”的观念的“某种等级的现实性或完备性”的不同而得以增强或减弱。这样一种力的增强或减弱,在德勒兹看来就是“情动”。“affectus就是存在之力的连续变化,而此种变化为某人所拥有的观念所界定”(Deleuze, “Lecture Transcripts”3)。后来在他的《批判与诊断》里,德勒兹再此强调了“情状不仅仅是一个物体(body)对我的身体所起的即刻的影响,而且也会对我自己的绵延(duration)产生影响——快乐或痛苦,高兴或悲伤——也产生着作用。从一个状态转化到另一个状态的,是过渡,是生成,是上升,是降落,是力量(power)的连续不断的变化”。因此,我们将之称之为“情动”更为确切,而不再是“情状”(Essays
Critical
and
Clinical
139)。这样,他就把“情动”与“情状”区分开了。前者指向身体的存在之力的增强或减弱,而这种身体变化是经由内心确认的;后者则是一种与实体相对的状态,它不能独立存在,需要依靠另一个东西才能存在。在“情动”这一术语中,德勒兹更强调的是介于两种状态之间的差异性绵延,而非某一种单一的状态,而是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持续变化。由此,情动表现的“不是被影响、被改变与被触动之后的身体,而是影响、改变、触动、本身成为身体,身体就是能影响与被影响的行动力与存在力”,通过情动,身体成为差异的保证,“我有一具差异于他人的身体,因为我有独特的动静快慢改变,而情动就是这个独特改变的表现”(杨凯麟103)。还有一点需要提及的是,在斯宾诺莎的概念里,“情状”是指“存在于他物之中,并借由他物而能被设想的事物”(Spinoza3);而在德勒兹的语境下,“情状”却增生了另一种不同的含义,它是“一个物体在承受另外一个物体作用之时的状态,是一个效果”(“Lecture Transcripts”4)。在万塞讷的课程里,他不断地强调物体间的“相遇”、强调物体间的混合与相互作用、强调身体的相遇产生的或愉快或不愉快的情动转变,从而为他重点引申的两点做准备: 一是“我们只能认识自身,而我们对外部物体/身体的认识只能经由它们在我们自己身上所施加的情状”(“Lecture Transcripts”5),从而“情状——观念”是一个不充分的观念,因为它们对相互作用或混合的原因一无所知,人又如何能脱离由我们的行动能力的增强或减弱所构成的被动情动呢?二是,德勒兹在这里提出了哲学史上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既然每一个人都具有承受情动的力量,那么一个身体能做什么?“我不停地穿越着这些行动能力之流变,通过我所拥有的情状——观念,我不停地追随着情动的连续流变之线,以至于在每个时刻,我的承受情动的力量都得以完全实现和实施”(“Lecture Transcripts”8)。在这里,一种承受情动的力量,成为一种强度或是一种强度的阈限。德勒兹以强度的方式来界定人的本质,即一个在生活中承受情动能力的极限。
至此,德勒兹将情动置入整个哲学史来思考,也正是在此意义上,他提出了对于积极情动的思考。德勒兹明确区分了悲苦情动和令人愉悦的积极情动。在他看来,悲苦情动会削弱一个人的行动能力,同时意味着个体处于一种与自身不合的有害的关系中。在这种关系里,人无法到达对“共同概念”(common notions)的认识,即个人无法对施加悲苦的物体/身体和你自己的身体所共享之物形成一个共同概念,也即对两个身体或两个灵魂所共享之物的概念。因而,“悲苦不会令人明智”,“对死念念不忘是世间最卑贱的事情。”悲苦的情动削弱个体的行动的能力,愉悦的情动与个体的关系之间彼此构成,“一个小愉悦顿时使我们进入一个具体的观念世界,它肃清了悲苦的情动或那些处于挣扎之中的事物,而所有这些都构成了一个连续流变的一部分。但同时,这个愉悦还推动我们进一步逾越了连续流变,它使我们至少拥有了一种掌握共同概念的潜能”(“Lecture Transcripts”10)。也就是说,愉悦的情动使得我们形成对于施加与被施加情动的身体所共有之物的观念,这种认识有可能失败,但当成功之时,我们会变得明智。情动在这里不仅是一种非常积极、且极具有潜能的所在,德勒兹更将其视为“生命的劳作”,并把它上升到人生的本体论的高度。他不止一次提到,“如果我们知道整个宇宙的所有关系结合于何种秩序中,就能够界定整个宇宙的承受情动的能力[……]如果整个世界化为一个单一的身体,你便真正拥有了一种承受情动的普遍能力: 上帝,作为整个宇宙的原因,本质上具有一种承受情动的普遍能力”(“Lecture Transcripts”11)。直到走到这一步,我们才进入对于原因的分析,进入到一种充分的观念之中,也就是德勒兹所说的“哲学”之中,在这里,唯一重要的事情的是对于生命的沉思,并将其作为生活的方式。在此,死亡仅仅是作为身体某一部分的有害遭遇来体验的。德勒兹在这个地方对于“衰老”的讨论格外动人,他说令他着迷的恰恰是当一个人衰老之际,当他的行动能力趋于衰弱的时候,一个身体可以做什么?他首先提到两类人: 一类人是不接受和恐惧衰老的事实,年华逝去却依然扮成年轻人的样子;另一类人是太快衰老,少年老成,装扮成老者,这在他看来是另外一种成为小丑的方式。德勒兹说,无论是迟于衰老,还是过于衰老,都是一件可笑又可悲的事情,因为无法正面面对正在衰老的事实。所以他说,“懂得如何变老是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在其中,共同概念会令你理解为何一些事物或身体与你自己的身体不相合,于是必然要去发现一种新的优雅,岁月凝练的优雅,其要义是不再执著”。(“Lecture Transcripts”12)这是一种对于死亡的洞察和生命的沉思,最大限度地推动着个体向自身所能承受的情动的强度向前、跌落,找到最高的强度和最低的强度之间的阈限,也是诞生与死亡之间的阈限。德勒兹把斯宾诺莎的体系里存在的三种观念,也称为三种类型的知识(connaissance),如果说“情状——观念”(无因之果的表象)是第一种类型知识,“共同概念——观念”(上升到对原因的理解,它所呈现的是对所有身体或诸多身体来说的共同之物,它是一个普适性的观念)是第二种知识,那么“本质——观念”便是第三类知识。在这第三类知识里,德勒兹区分了“共同概念”与“本质”,认为虽然“我的关系及特征性关系表达了我的本质”,但两者不是一回事,因为后者是“力量的一种等级”,是一种强度之力量,“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脱离我的特殊本质、上帝的特异本质和外在物体的特异本质中的一方去认识另一方”。德勒兹将斯宾诺莎所谓的“本质”命名为一种强度之量,并将这第三个领域——本质的世界理解为一个强度的世界,借此来界定情动,积极情动或至福(beatitude),也即“自发情动”(auto-affect)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德勒兹对于情动的讨论是他从对斯宾诺莎伦理学的阐释中自然引申出来的。他之所以如此重视解释和发挥这个概念和问题域,是因为情动本身在斯宾诺莎那里就构成了一个既重要又困难的问题。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涉及到如何重构斯宾诺莎的形而上学和实践哲学的之间理论过渡。在斯宾诺莎那里,情动问题始终缠绕着实体与偶性这一基本问题,而且也潜在地作用着斯宾诺莎的实践哲学命意。而德勒兹最终在情动概念的进路中,将斯宾诺莎理解为尼采的前驱——对无意识的发现、用好坏代替善恶、贬斥痛苦情感等。这个问题的困难之处在于,斯宾诺莎对于“情动”的实践哲学旨趣的讨论极为复杂。在《伦理学》第三部分,斯宾诺莎从讨论作为身体情状的情动开始,在诸如“被动情动向主动情动如何过渡”以及内部细分和向外涉及的一系列问题中,将论题引向人的奴役与自由。实际上,在这个环节上,主动情动的获得与真观念的获得最终变成了一体两面的问题。因而,也可以说,斯宾诺莎所谓“三种知识”之间如何过渡也相应地会在这个“情动”的问题结构上得到解释,甚至不是简单地解释澄清,而更加是一种“再问题化”。围绕着斯宾诺莎的情动概念,德勒兹展开了精湛的哲学史重构,并交这个概念发展为一种“解辖域”运动。
另一方面,除了“情动”以外,德勒兹还创造了很多其它的概念,对于他本人而言,“情动”并不是凭自身就比其他那些概念更加殊胜的,用结构主义已经充分强调了的一个标准: 系统的要素除了它本身的系统性为之所标示的关系,并没有别的意义。所以,包括“情动”在内,德勒兹看似在说很多东西,创造和使用很多术语、概念,但他从来都是在不断尝试对它们加以调适,使之能够在一个具体的文本中行得通。他用“情动”调适着斯宾诺莎的文本,进而又将其调适到自己的体系里。这个运动在德勒兹的文本中足够激烈和持久。在这一视角下,“情动”这个词(它的解辖域运动)可以被视为体系性嬗变的一个效应。
三、 《情动的自治》与情动理论的纽结点
在德勒兹之后,《千高原》英语学界的翻译者马苏米在他使用的术语笔记里,给予在卷集中论及到的“情动”如下的定义:
情动(affect)/情状(affection),这些词都不能代表一个人的感觉(在德勒兹和瓜塔里那里是“情绪”)。L’affect(affectus)是一种能够影响和受到影响的能力(ability),这是和身体的一种体验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相对应的一种前人格化的强度(prepersonal intensity),意味着身体的行动能力的增强或减少。L’affection(affection)将每一个这样的状态视为被影响的身体和发挥影响功能的身体之间的相遇,这里的身体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包括心灵或理想的身体。(Massumi xvi, “Notes on the Translation”)
马苏米对于情动的界定,强调它是一种能够产生影响、也接受影响的能力,是一种中间状态,是一种“力”或“强度”。在著名的《情动的自治》一文以及随后出版的著作《虚拟的寓言》里,马苏米对“强度”做了进一步的延伸,他于“情动”的理解是同常用的另一个术语相关联的,即“虚拟”(virtual)。具体而言,他认为情动是 :“实际中的虚拟与虚拟中的实际同时互相参与,一方从另一方中出现,又回到另一方中。情动就是从实际事物的角度出发看去的这种两面性,在其感知和认知中表达出来”(“The Autonomy of Affect”96)。在马苏米的理论体系里,“情动的自治”和对虚拟的理解息息相关,而虚拟与人类感知到的外部刺激相连。为了更好地引入“虚拟”的概念,马苏米讨论了一个著名的实验研究案例。这是由德国电视台拍摄的一个实验性的短片故事,其基本情节很简单:一个人在屋顶花园上堆了一个雪人,雪人在午后的阳光里开始融化,他看着不忍心,便把雪人移到了山间阴凉处,然后与之告别。研究小组把这个片子制作成三个版本,即无声版、增加了事实事实说明的事实版、以及在关键转折点上加了表达场景情绪的情绪版,意图检测儿童对这些版本的不同感知和反应。研究人员让一组九岁的孩子观看这三个版本,让他们回忆看到了什么,并根据“愉快”的程度打分。结果最愉快的版本是无声版;排名中间的是情绪版,最容易被记住;得分最低的总是事实版、也最记不清楚。但当这些孩子被要求按照“高兴—悲伤”(happy-sad)和“快乐—不悦”(pleasant-unpleasant)来评价影片里的一个个单独场景的时候,更令人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悲伤(sad)的场景被认为最有快感(pleasant),越悲伤,越快乐。“事实版诱导出最高层面的情绪唤醒,即便它是最令人不悦的,得到的是为时最短的印象。”事实让孩子们心跳得更快,呼吸变得更重,也让他们皮肤阻抗下降。马苏米评价道,这个实验唯一积极的结论是强调了在图像接受中引发感情东西的首要性。马苏米认为人类接收图像(即外部刺激)至少发生在两个层面: 形式/内容,效果/强度。形式/内容与象征秩序有关,因此人们能通过自己的体验去理解他们在这个层面上的感知。相反,在强度/效果这个层面身体对外在刺激的感知是“一个非意识的、永不会成为意识的自主残留”(“The Autonomy of Affect”85),它与任何可以变成叙事的可能性不再相关,马苏米把它解释为“叙事的非定域化”(narratively delocalized)。形式/内容和强度/效果层之间的关系是被修改和修改者的关系,后者是隐形的;只有通过考察强度/效果在形式/内容层面上留下的痕迹,我们才能感受到它的存在。强度不产生意义,但是可以改变它们,“它是一种悬置状态,存在中断和瓦解的潜能”。它在我们试图锁定或描述它的时候消失,但是改变了我们生产出来的叙述。对于马苏米来说,这种对“强度”的强调,其实是对“情动”的强调。他以强度来界定情动,在此出现了情动和情绪(emotion)的根本的区分。在他看来,情绪是个人的,属于自我的领域;而情动是在外或超出自我的,是在主体间发生的一个现象。这意味着一个人可以是情绪的,但一个东西不能称之为情绪的;同时一个东西可以被表达情动,如礼物等,但是一个人很难这样,除非她/他变成一种对象化的存在,最极端的形式是视觉图像——被物质化。情动的魅惑产生于主体间的空间里人与物之间的相遇,所以,我们不必惊讶于马苏米后来的发现——情动实际上存在于事物之中。这便是马苏米的关键论断 :“情动是虚拟的联觉视角,它们定着于(功能上受限于)实际存在,特别是具体体现了它们的事物[……]实际地存在着的有结构的事物,生活在逃脱了它们的东西之内,也通过它们而存在。事物的自治是情动的自治”(“The Autonomy of Affect”96-97)。
将强度作为界定情动的本质界定,这是马苏米对于德勒兹的继承,同时他走得更远。如果说在斯宾诺莎那里,情动只发生在有心灵的主体之间、要经过心灵的确认,那么到了马苏米这里,他对之进行了一种将其“物质化”的强调和处理。对于情动的理解,加之显而易见的德勒兹的影响,这些都使得马苏米采取了一种相当激进的反人文主义的写作立场。他认为,为了准确地描述和阐释情动在社会过程中的所占的结构和构造作用,学者们应该彻底放弃以人类为中心的对社会现实的理解。这个社会现实是一个复杂的集合的理解的影响,这个集合不仅包括人类,还包括非人类。就马苏米而言,这些可以产生情动、压制人类意识理性、塑造人类身体和心灵的多种可能性的东西,是社会过程的复杂性得以概念化的关键,这个复杂的社会进程包含着各种无法解释的以主体和意识形态为中心的理性主义理论。
马苏米从情动的定义、情动之于感觉和情绪的不同入手,用了大量的笔墨细致地剥开了生命体在萌芽状态时内含的诸多形式,探讨了事物即情动发展的前阶段以及它的亚稳定性和非地方性关联。他论述情动像硬币般的两面: 它同时参与现实和虚拟性,并在其感知和认知中显示出来。然后他着重强调,“情动的自治”是在它对虚拟性的参与中敞开的,从虚拟的观察角度出发,视觉隐喻被小心谨慎地使用,因为情动是联觉的,它暗示着诸种感觉彼此参与: 对生命体潜在的交流的衡量标准是,“它将一种感觉模式的效果转化为其他效果的能力”(“The Autonomy of Affect”96-97)。正因为对情动的自治,或者毋宁说是对情动在虚拟中参与的强调,马苏米越来越关注情动在政治文化里的运用,比如他写诞生于未来的情动现实,再现和分析美国自911以后对于诸多尚未发生、且没有足够的真实依据的事件采取真实的政治和军事行动的行为,探讨关于威胁的政治本体论。与此同时,他对情动的研究日益走向一种对于情动政治的探讨。在马苏米看来,意识无法理解身体对于外界刺激的情动反应,这种对理性处理情动的无能,在后现代时代变成了一种政治资源。
马苏米是非常具有学术个性的学者,其学术个性的最鲜明之处在于,他从科学领域借来许多犀利的、让人文学科感到惊奇的“硬词”,并将它们成功地融入到人文学科的写作之中,扩大了人文学科研究多种可能性。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马苏米的作品得到了很多学科强烈的关注和传播。马苏米的情动理论汇聚着当时知识界对认知中心主义、乃至于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种种不满,贯彻着某种德勒兹式的“反”人文主义立场。与之相比,塞奇维克则在汤姆金斯的心理学背景中,发展出一种女性主义的情动理论,使之成为性别研究和身体研究的重要理论工具。可以说,在马苏米和塞奇维克这里,情动理论开始分化,如果说,马苏米继承了斯宾诺莎—德勒兹的本体论路径,那么,塞奇维克则开启了情动理论的女性主义路径。这两条路径以马苏米为理论交叉口,又常常相互交织和相互挪用,逐渐融合进一个系统里。
四、 塞奇维克与女性主义情动批判
在马苏米的理论开始产生影响力的同时,也即在《情动的自治》发表的同一年,塞奇维克在1995年发表了一篇影响深远的《控制论世界的羞耻》,藉以在西方打开了长达二十多年之久持续至今的“情动转向”的风潮。女性主义情动理论肇始于塞奇维克,它的蔚然成风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深受德勒兹的影响,同时又融入了这些学者过往的研究脉络。同时还要提及的是,在女性主义情动理论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已经有不少学者诸如塞奇维克、萨拉·艾哈迈德、劳伦·贝兰特开辟出了一条和德勒兹不同的对于情动研究的路径。
情动理论对于女性主义研究来说或许并不是特别新鲜,因为有关感觉、情感的研究已经塑造了女性主义理论和政治实践,以及它们与日常生活的关系。这一理论摆脱了女权运动的强烈诉求,更专注于具体的学术问题和制度变革。这种理论化知识的学术研究核心是感觉,包括情感类型在内的领域,以及情绪历史的复杂叙述、私人与公共领域之间的关系,还有内在性、主体性和亲密生活的建构。这一代的女性主义学者并没有致力于重建被忽略的女权主义,而是强调小说的流行和破坏文化类型的社会力量,并且受到后结构主义理论特别是福柯的影响,强调性别而不是女性。女性主义情动理论强调道,女性文体固然可以在读者中引发强烈的情感体验,但这个女性文体所体现的社会力量并不总是女性主义的,相反,它关系到巩固和维持中产阶级的权力、促进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议程。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情动”理论的转向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女性主义研究内部的转型,两者是交融共生的。
塞奇维克是女性主义情动理论的先驱和代表,她是在美国和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齐名的性和性别研究专家。她早期致力于性别研究和对酷儿理论的开拓性,突破性的代表作为《男人之间》和《密柜认识论》,尤其是前者,对英国和美国文学史上的一系列文学文本进行解读,来提示同性的社会欲望恰恰是通过异性恋来表达,在“情欲三角”当中,以女性为中介来隐藏男性之间的同性情欲,通过交换女性来稳固他们的同性利益,即我们所谓传统的异性恋结构其实是以女性为交易媒介的男—男关系,以及这一传统结构与同性恋结构之间的博弈关系。性和性别是塞奇维克早期研究的重点,在1991年她身患乳腺癌,以此为转折点,加之对于青少年同性恋者的关注,她以自身的经历和身体经验开始转向了对“情动”领域的研究,并在同一个时期对心理学家汤姆金斯进行挖掘,将对“羞耻”(shame)等情动的研究作为她后期的有关酷儿、身体的学术研究的重心。汤姆金斯是当代情动理论的先驱,他出生于1911年,终身奉献给了心理学的研究。在四十年间他完成了长达四卷本的文集《情动的想象意识》,这个著作是汤姆金斯对心理学理论长期存在的问题的回答。汤姆金斯认为情动或情绪主要有三种类型: 积极的、中立的和消极的。积极的情动包括高兴、趣味、兴奋;中立的情动指惊讶;消极的情动包括生气、恐惧和恶心。根据这个理论,当把积极的情动效果发挥到最大、消极的情动效果缩小到最小,可达到心理健康的目的。理解他的情动理论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情动是对来自外部刺激,尤其是来自脑部刺激的不自觉的反应,行为受情动影响通常是自动的和没有目的意识的。人们的一般情动趋向是到尽量唤起积极的情动的情境里去,而避开产生消极情动的情况。心理学上情动理论的一个目标是避免大脑发射给情动的这种自发反应,当这些种种情动被理解的时候,才有可能改进心理治疗的效果。这个理论转移了自二十世纪以降的主导心理学理论的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学和斯金纳的行为主义。在这个理论之前,心理学界多用弗洛伊德的驱动理论来解释动机,而汤姆金斯认为,是情动而不是本能冲动在驱动着人们。他还描述了情动在人类经验中的作用,探讨了积极情动和消极情动的起源和发展,为情感研究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他尤其试图去理解害怕、愤怒这些激情,去呈现出它们的整体面目,他努力试图通过分析情动的进展来解释个体或一种文化的情动的发展来解释人格的发展。汤姆金斯的学说在卷帙浩繁的学术理论里不久便被掩盖,在他去世后的几年中,塞奇维克由于自身的遭遇开始关注自己身体和疼痛的体验,开始聚焦把身体不仅作为一种物质去审视,也作为一个体验的主体;同时,她对汤姆金斯的工作,尤其是他的情动理论进行了重新挖掘并将其运用到文学、文化领域中去,对过往的研究进行创造性的拓展,这非常鲜明得体现在她后期对于“羞耻”等情动的探讨中。
塞奇维克论述“羞耻”有两个方面非常引人注目而又让人深受启发。一是她试图讲出羞耻和主客体的关系;二是阐述羞耻和身份认同的关系。在羞耻和主客体的关系方面,塞奇维克举了一个操演(述行行为)的例子,她用了一个和奥斯汀在婚礼上的“我愿意”的词——“(你)不要脸!”(Shame on you!)。但是和奥斯汀第一人称述行不同,塞奇维克一直强调要脱离第一人称中心的知识论框架而转向情动研究,因此她在这里的主语以第二人称开始。“我”是被隐藏的,是随着这句话的说出才被召唤出来的,在赋予别人羞耻感的过程中隐藏了自己的主体能动性,是“借着说明它的操演意图来获得自己的操演力,也就是赋予别人羞辱”(“情动与酷儿操演”100)。同时,因为缺少明确的动词,第一人称在这里便处于一种不确定的、延宕的状态,因为不知道这个主体究竟是一个单数亦或是复数,是出于过去、现在亦或是将来的状态,是能动性还是被动性?这些都可能被质疑,而不能被相信。在谈论身份认同方面,塞奇维克从《如何将孩子教成同性恋》的时候,就谈及了社会的医疗体系、教育体系以及公共体系对于青少年同性恋在精神和透体上的压制,以及主流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对于青少年同性恋的忽视。“羞耻”的感觉在年少的时候便伴随而生。塞奇维克在这里也指各种被社会视为不稳定又异常的酷儿,“羞耻”的污名和绝望的无力感相伴而生。“羞耻”是塞奇维克提出来的用来对应“酷儿”一词的历史内涵,假如“酷儿”是个在政治上有力的名词——实际上它也是——那绝不是因为它可以挣脱童年时的羞辱场景,而是因为它把那种羞辱的场景当作一种近乎取之不尽的能量转换来源(“How to” 101)。但塞奇维克认为,羞辱不仅在干扰着身份认同,同时还在建构着身份认同,它不是一个孤立的和内在的心理结构,而是与其他情动一样,是“一种存在于不同人身上或不同文化当中的自由元素,它附着于身体的某个区域、某类感官系统或某种行为举止,并持续不断地强化或改变几乎所有事情的意义”(杨洁9)。塞奇维克在这里富有启发性的思考在于她从这个点上轻轻荡开,从同性恋群体、酷儿群体扩展到整个受到权力压迫的群体,如因种族、性别、亚文化等,她举例说,那些想要解决或消除个人或群体羞耻的策略和口号终将失败,如“黑即是美”同志自豪”等,这些口号并不能进一步让这个个体和群体的羞耻感在每个人的心理上有所减少,因为这种羞耻感不是简单地附加到身体本身,而是它参与了身份的建构和认同。
从塞奇维克在生前出的最后一本书《触摸感受: 情动、教学和操演》中可以看出,汤姆金斯的情动理论对于她后期的转型起到了关键性的影响,使她开始远离早年迷恋的有关“衣橱”或“密柜”的认识论危机,转向以身体体验、感情和亲密研究的现象学路径。在塞奇维克看来,情动理论提供了一个描述人类多样性体验的非常有用的词汇。由此,她和汤姆金斯都认为,理解实质上意味着可能性的扩展,而非可能性的消泯。而对于塞奇维克而言,情动理论恰恰提供一种有效的词汇,可以对人类的多样性体验进行描述。在《触摸感受》中,塞奇维克首先要阐述清楚的一个问题便是: 什么是“感受(feeling)”,它如何被触摸到?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这个“什么”是超出可以清晰表达的范畴的。可是有一件事情塞奇维克知道,尽管触碰感情很难去清晰表达,但是它有“纹理”(texture)和“似乎存在于纹理和情感之间的一种亲密”(Touching
Feeling
17)。塞奇维克的写作是细腻、创新、令人愉悦,但同时也是疯狂的,因为如果不努力理解她在试图做什么,便很难赶上她的思考速度。塞奇维克在书里表达了很多她自己的情感体验,从病痛到偏执的精神分裂和不断修整的教育学,从酷儿理论到文学分析,她提供的体验是一个复杂又在急速旋转的情感状态。她无意提供某种框架式的情感理论,甚至急于摆脱这种处理方式,因而她的思想之流常常冲破所涉问题的边界,甚至将读者扔回混乱之中。正如她自己说的,“我至少想要在这里(通过亨利·詹姆斯的文本来论述耻辱、戏剧性和酷儿操演)提供一个同性恋理论,但是我没有,也不想有”(Touching
Feeling
61),并坚持认为自己这本书的目的仅仅涉及感受的物质性、性、耻辱、教育学和哀悼,以及不提供任何概念的确定理论。在这本书里,塞奇维克梳理了羞愧和酷儿理论的关系,用她的话说,“羞耻感的原型[……]类似于一个洪水即将形成的时刻,一个具有爆发性和破坏性的时刻,一个身份的通道里——构成了情感认同的交流”(Touching
Feeling
36)。在这种意义上而言,情感是超越表达的,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大部分有关酷儿理论的讨论是完全忽略情感状态的,因为它根深蒂固地定义着什么是酷儿,而不是什么像酷儿。正如塞奇维克强调的,酷儿和激进的正是不在有关,实际上,当“酷儿”这个词被大众流行文化接受的时候,它便丧失了原有的意义,酷儿以前意味着激进的政治和因为其特立独行不被社会所容纳。当酷儿告诉直男直女们什么是酷儿、酷儿有哪些行为举止的时候,“酷儿”就变得不再有意义。这是对酷儿原始意涵的完全颠覆。继《控制论世界的羞耻》后,以青少年同性恋为研究对象的专题论文《情动与酷儿操演》集中了塞奇维克后期“情动转向”的主要思想。从她晚年出版的《触摸感受》中的理论观点来看,这个时期塞奇维克对于情动理论的思考已经相当成熟。在弗洛伊德、拉康、福柯、列维-斯特劳斯、德里达以后,在后结构主义和女权主义以后,她思虑的是理论该如何发展?她不仅重新探索了感觉、情绪、情动的重要性,同时认为汤姆金斯开辟了一条理论的科学主义道路,使得理论变得不那么铁板一块,并同时开启了女性主义“情动”理论研究的分支。
玛尔塔(Marta Figlerowicz)在《情动理论档案》中说,当然没有一个关于情动理论单一的定义,情动理论在它的每一个化身中构建了人文学科和生物学或神经科学的桥梁。另一方面,这篇文章回顾了吉尔凯郭尔和斯宾诺莎,刷新了我们关于主体的定义。一些情动理论为“负面”的情动如羞愧、悲伤或孤独的疗效价值作出辩护,它强调“丑陋的感情”不仅是自我认知的来源,更是社会批判的源泉。情动理论可以是与社会学的偶然相遇,可以成为文学研究新的研究主题,可以是没有尽头的精神分析,不疏漏却也不关心是否回答到一个稳定的结果。情动理论也可以拒绝精神分析,努力使感情和感觉为自己发出声音。从问题意识上来讲,情动理论带有学者强烈的个人生命印迹,很多学者在论述情动理论具体运用的结论的时候,不仅用到了各种案例,还结合了深刻的个人身体经验。当现代哲学基于认识论框架下的身体研究无法满足女性主义研究视角时,情动理论的研究恰逢其时成为了女性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作为近十年来女性主义研究的重要趋势,女性主义情动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一系列不同的甚至是相斥的运动与变革。文本研究的退烧是情动理论在学界兴起的开始,“它代表了对于情绪,感受与情动之间之异同的高度关切,并试图着将这种关切置于学术考察之中”(Cvetkovich,Depressing
a
Public
Feeling
131)科学研究对于“客观”的偏爱在这个趋势中受到了挑战,而这个挑战本身亦成为了对情动之经验与理论研究兴趣的复苏。除了塞奇维克以外,众多女性主义与理论家如贝兰特、艾哈迈德在酷儿和女性主义研究中发展了情动这个概念,尤其是体现在其对前瞻性的乌托邦式的欲望和感觉如“耻辱”快乐”的变革潜力的重要探索上对情动理论研究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这些论著着力于个体的情动经历与社会环境对情动的调试。这种研究倾向加剧了情动理论与政治、文化、经济研究的整合,并逐渐形成“社会情动”,从而使得“情动”成为更可靠的反映个体与人际关系之真相的来源。当然,女性主义者对于“情动转向”的运用也留有警惕之心。兹维特科维奇(Ann Cvetkovich)对于“情动转向”一词的使用颇为谨慎,“情动转向一词于我来说并不陌生,因这个词似乎意味着某种新的研究,而事实上,公共情动项目上多年以来已经获得了相关的成果,亦如它成功地在理论与实践上塑造了它与日常生活的关系”(Depressing
131)。从事情动研究和媒体研究的人类学家、芝加哥大学人类学教授马扎雷拉(William T.S. Mazzarella)在他的论文《情动何益》里询问情动可以做什么,美国文学理论家和政治学家哈特教授也写了一篇同名文章《情动对什么有益》来对此进行追问。这些论文不再探究情动是什么,转而去研究情动本身能做什么。思想理论界在情动理论研究上摸索了二十多年,对于情动是什么这样的追问依然会持有异常谨慎的态度,因为这个问题不是那么容易回答。“情动”理论为我们思考文化理论里情感的政治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来源,同时这种思考还暗示了现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里情动的传统性和它的本体论承诺其实是一种强烈的理论化诉求,它或许比它展示的更有争议性。注释[Notes]
① Affect(拉丁语affectus)为斯宾诺莎使用的哲学概念。在斯宾诺莎的用语中,affectus既是心灵的也是身体的状态,是一个名词,也是一个动词。它与感觉(feelings)和情绪(emotions)相关但不等同于后两者。贺麟在《伦理学》(斯宾诺莎著,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1年。)中译为“情绪”和“情感”;管震湖在《笛卡尔和理性主义》(罗狄-刘易斯著,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7年。)里译为“感受”。姜宇辉在《千高原》中将其译为“情状”,后改译为“情-调”,均不甚理想。后来汪民安和姜宇辉在“生产”系列书刊中集体将其称为“情动”。Affect不仅是一种情感表达,还强调一种力的增溢或减损状态,且关注身体、情感和潜在性之间的关系,其本身是流变的、动态的。
在斯宾诺莎和德勒兹看,观念不仅具有一种客观现实,同时还具有一种形式现实。观念现实是指一种表象性的思想样式,形式现实是指观念自身就是某物,比如三角形的客观现实是表象三角形的观念,而三角形观念自身就是某物。斯宾诺莎通常将观念的此种形式现实界定为观念自身所具有的某种等级(degree)的现实性或完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