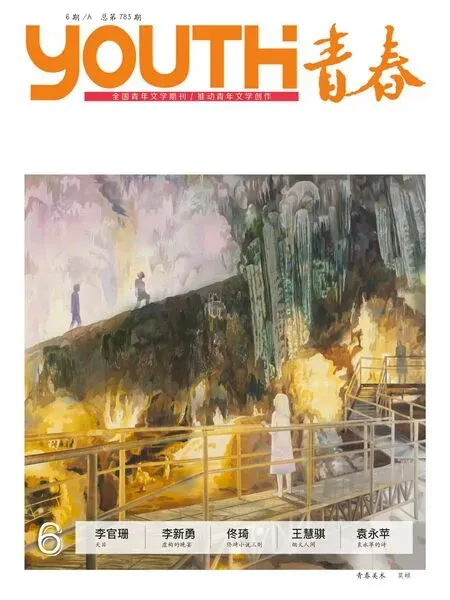烟火人间(七题)
口 王慧骐
在浴室听老人说酒
冬日,去浴室洗澡。浴毕,几个看上去总在六十开外的老哥(有的或许还大点),基本都光着身子,坐在宽约二尺长丈余的阔板凳上凉快,等汗收了好着衣。他们嘴上叼着烟,慷慨点的还朝周边打上一圈。烟不见得多好,却是份待客之礼(当然接烟者多少有点熟的)。
或粗或细的嗓门,扯一些最近在哪儿干一月能苦几个钱之类的闲篇,也议论房价、地铁又通了哪条线,某某老头找了小姐等大事小情。有一回听到他们说酒——对男人极具煽动性的话题。一个说,我一般也就只能喝个二三两;旁边那位,一副当仁不让的架势,说我年轻时,斤儿八两不在话下。一个望上去瘦精精的老头,按捺不住插话了:我们不比一顿的量,要比比一天的,我床上一起来就去摸酒瓶。三顿都要弄一点,还用不着什么菜,熏烧店那种小袋装的花生米,一袋能对付好几天。顶多也就晚上家门口剁两副鸭四件。旁边人笑他,你那叫酒鬼。他抹抹胸前的汗珠子:我才不是酒鬼呢,我越喝越清醒,从不打老婆也不骂孩子,说完有几分自我陶醉地嘿嘿笑了。
也有在道上混见过一些世面的,说当年和老板一块跑东北谈大豆生意,怎样把想弄醉他们的人搞到桌底下;有一个显得有几分城府,说他早几年血压高,心脏不太好,碰到饭局怎么与人虚与委蛇,在酒桌上打太极拳。说哪年哪月何处饭庄吃过怎样高规格的酒席,谁人请的,参加者有哪些显赫的人;还有说和四川佬猜拳行令,喝到大半夜跑到大街上吼几嗓子……
男人们在这个世界上行走,无论干什么的,好像最爱的东西还是酒。哪怕他们老了,喝不动了,但毕竟都有过拿大鼎的时候。所以在这个特定的环境里,把老哥们凑在一起谈酒,还不卸下所有的道具,口无遮拦地说它个气冲斗牛?
在推杯换盏的回顾中,他们无疑可以找回曾经兵强马壮的自己。
萃香轩
两口子在这儿弄一爿小菜馆有八九年了,左左右右的门面旧的去新的来,不知换了几茬的主,而他们还没动过窝。菜馆不大,前面仅几张四人对坐的桌子,后面那包间像是硬隔出来的,逼仄得很,七八个往里一挤,谁也不好乱动。
女人负责外面的事。有一张就够她一人坐的小吧台,没人时她伏着,把手机横过来看看韩剧。一旦有客进来,不紧不慢地把菜单递上,人在一旁立着,帮你合计参谋着点菜。这头刚点上,她一嗓子,已把菜名报进后厨男人的耳里。两口子年纪相仿,四十不到的样子。女的来自苏北丰县,男的家在溧水乡下。有一个女儿,刚开店那会儿才会跑,如今已上初一了,眉眼里都有点大姑娘的神态了。
男人的菜做得不算太好,能吃,大路货而已。有些老客是三天两头来的,一瓶老酒,三五个菜,能搞上半天,讲话声音贼大,还习惯性夹几个脏字。有些穿着斯文,西装革履的,是对面几家房屋中介的年轻人,做成了一笔二手房买卖,准凑在一起庆祝。老板娘说,你还别小看了,我们这儿倒像个房产市场的晴雨表,房子卖得好,这些中介就常过来吃;有一阵不来了,我就晓得一定是低迷了。
山不转水转,这生意还真是靠一副活络的脑袋瓜子来做。除了堂吃,周边小区许多人家都有老板娘手机号,家里来了客或今儿不想弄菜了,打个电话,一会儿就给你送上门。这两年有了“美团”,他们也不甘人后加入进去。中午时分,不声不响的,几十个打包的菜点让“美团”的运送人员拎走了。
看得出这个家是老板娘在当的。她原本有个相差十多岁的兄弟在老家,人挺木讷,她评价说,“是我爸妈的惯宝宝。”这两年跟在姐夫后头配配菜,学点手艺,有叫外卖的,就让他骑部电动车给送去。该收多少钱他姐算好了,找头一并备上,他乐得不动脑子。这兄弟也二十六七了,去年有人给他介绍了对象,所以当姐的除了管他吃喝,每月还得给他开工资。“你不给他,他拿什么讨老婆?”老板娘说话直刀砌墙,兄弟在一旁站着,她也照说不误。
男人大部分时间待在后头,出手也是够快的。但碰上饭点人多,菜还是有些跟不上,便听见老板娘跑后头哇啦哇啦叫,催急了男人也会朝她吼几句。而生意消停时,能在前面看到老板和女儿头挨头地坐一块玩手机。女儿好像多少有点怕她娘。
这小菜馆就在马路对面,我们常去,名字不知谁给取的,还有点夫子气,叫萃香轩。
老 申
老申走的时候72岁,得的是癌症,在病床上拖了几年。患病是痛苦的,但老申这辈子还算得上有福。
他最早在苏北某县的乡下,家里很穷,发了狠要跳出来。考学是当时农村孩子唯一的路,他自然也得从这条道上蹚出来。高中几年抱头滚(意指吃苦),终于考上省城最好的大学。这以后好日子也就慢慢来了,毕业后他被留在省级机关,从小科员一步步干起。打小苦过更知有这一天是几多不易,除了埋下头干活,在领导面前从来都毕恭毕敬,不吐半个不字。他倒也不算平步青云,十好几年熬到正处。老申对组织一直心存感恩,与上级保持一致,大刀阔斧似乎与他无缘,中规中矩、谨慎行事是他一贯奉行的处世之道。
老申读完大学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他的婚姻也如上辈那样遵了父母之命。发妻与他同乡,人老实,长相不出众。婚后一二十年,他们都是两地分居,那时交通不便,老申两三个月才回趟家。而发妻在乡间不只侍奉公婆,还负责抚养两个陆续出世的女儿。直到八十年代后期,老申都四十多了才向组织上提出,把老婆弄来省城,在一个单位干临时工,负责一幢楼的保洁工作。
一家人团圆的日子过了不到两年,老申被组织安排出国。没几日老婆在单位楼梯上扫地时,不小心一脚踏空,颅脑碰在水泥地上严重受损,旋即送医却未能抢回人来。老申在国外接到电召,匆匆赶回,也只能为发妻置办后事了。
大约两年后,快五十的老申再次沐春风,娶了小他二十多岁的女子为妻。这姑娘当时在老申当领导的单位做资料员,是个高中毕业生,因何而看上老申不得而知。想想这小女子也是蛮拼的,嫁与老申,不光鞍前马后服侍一个年近半百的老爷子(老申过惯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单身生活,家务事基本不知如何下手),还得给他两个业已成年的女儿当后妈。
局外人无法论其短长,反正老申再婚后的日子倒也过得消停而美满,婚后不久,这姑娘还为老申生了个胖小子。
老申最后几年得病住医院,全是这女人里里外外的忙乎,汤汤水水的准时准点拎到床前。据说临终前老申拉着她的手,说我这辈子净欠你们女人债了。
珍珍发屋
这间发屋开了有些年头,珍珍是老板娘的名字。这条街上的人大多认识她。她是从安徽肥东过来的。早先有过一个帮手,后来走了。如今是她婆婆给她打下手,洗洗毛巾扫扫地,还帮她弄饭。
她做生意心大,舍不得让进店的人跑掉。这位是来焗油的,她先把染发剂给你涂上,罩上加热器;那边就赶紧把一个简单的头发理了。碰上来烫发的,她笑脸相迎,说什么也要把你留下。早上九点开门,晚上忙到十点是常有的事。她一边干着,一边同相熟的人抱怨自己命苦。一双膝盖上护膝戴好几年了,腰肌劳损也早早地找上她。
她男人是她同乡,先前在店里曾见过,一副老实巴交的模样。在她面前基本不讲话,带一双耳朵听。他早些年跟人推销酒,珍珍说,也没见到他几个钱。后来学驾驶,买了部面包车,在金桥市场和装饰城一带转悠,替人拉拉货。再后来换了部车去开出租,找了个二驾,白班夜班轮流倒,弄得他们两口子一天到黑很难打个照面。
家里挑大梁的应当是珍珍。奋斗了好些年,终于买了套六十出头的二手房,这样,一家人的户口总算落了下来。但每个月一千多的房贷得好几年才能结束。
有一个儿子,二十多了,长得有他妈两倍宽。无论平日里珍珍苦口婆心怎样唠叨,儿子横竖就是不太爱读书。初中毕业上了技校,如今技校读完了,在江宁一家公司找了份活干。每月拿到的工资,自己玩玩手机吃吃饭,估计所剩也不多了。
而儿子正一天天长大,没几年就该娶媳妇了。珍珍肩上的担子也是够沉的。还完了自己的房贷,又得去爬另一座山。
背头陶
十几年前,陶和我是同事,在一家媒体。陶是新闻一部的主任,手下有二十多号记者。陶跑得最多也最得心应手的是商业口子,全市各大商场的老总好像都买他的账。那时空调、家电诸雄纷争,各家商场都有自己主打的品牌,引导消费潮流的纸媒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陶在这个圈子左右逢源、游刃有余,一些拿得出数据和扎实案例的综合性大稿子,非陶君莫属。
陶不摆“头”的架子,出去采访总乐意带一两个年轻的一块跑。开选题策划会,他往往话不多,而标新立异的提法会在文章里同你谋面。陶是一个注重实干,喜欢把活做漂亮的人。那时他也就四十出头,平日里总见他梳个大背头,但头发并不是特别茂密。他说这样利索,每天出门用手扒拉两下,梳子都省了。
陶有相当不错的酒量,那是他年轻时在油田工作练就的。他对我说起过,那会大都是露天作业,歇了工没事可干,几个工友拢一堆大茶缸一端,喝酒!我知道他当时呆过的油田,我也曾在那个县工作过几年。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点,他同我走得较近,有些关于报道的新想法会主动找我来聊。
后来我们共事的早报转向了,陶被领导重新安排了岗位,让他去集团层面跑广告。这可能不是他的强项,尽管有些过去的人脉,但求人的事他不太干得来。他更多时间就坐在办公室里盯着电脑,鼠标在手上划来划去。有一阵他迷上了电脑打牌,烟也是一支接一支的,抽得太多,烟缸里垒起的灰蒂几天都懒得去倒。
他每天骑着小轮子车来上班,那么大个身坯压在小车子上,形象有点滑稽和夸张。听说他喝酒比以前更没节制了,他似乎再也找不回当年四处采访,当晚成稿的忙碌与欢欣了。
那年冬天,集团派他去山东参加一个广告年会,会议结束后安排大伙登泰山。他当时正患感冒,本可以请假不去,但他没好意思开口,爬了泰山又连夜乘车返家。第二天便觉得心脏不行,很快住进了医院。
没料到,陶这一去就不回了。离退休还有四五年,陶却匆匆给自己画了句号。我常常会在脑子里闪过他那饶显个性的大背头。
修脚夫妻店
这间足疗店的门面很窄,像是硬挤在左右两家门店中的。门楼上的店名也做了最大的省略,只打出一个关键字:足。不留心还真发现不了。
太太有脚疾,个把月会找人修一修。先前一家号称“扬州脚艺”的,离我们住处有两站路的距离。其实小伙子不是扬州人,打这牌子有点“傍”的意思。修脚手艺倒说得过去,可人有点古怪,跟他说话他基本不理。人还时常不在店里,几回打车去都扑了空。
这以后就发现了离家不远的悬一“足”字的店。抬腿跨几级蛮高的台阶上去,里面倒还不小,五六张类似沙发的靠椅一字排开,一色的淡蓝布蒙在靠椅上,显得素雅干净。修脚的是一对夫妻,年纪约莫40岁出头。男的个子不高,女的生得几分魁梧。去过几回,慢慢熟了,也愿意同我们拉些家常。两口子来自河北邯郸,说这个店开有五六年了(我们在它门前走来走去的,竟一直没注意到),都是些常来的老客。有周边的,也有从较远地方乘车过来的,还有几位部队离休的老首长,定期有人开车送过来修脚。主要是看中他们的手艺,修、捏、刮、按,一整套的技法都让人觉着到位舒服。
最早他们在老家开过店,但生意不景气;后来经人介绍去了天津,可待的时间不长。有一回给人修脚,不知怎么说到了南京,客人大讲南京如何好,两口子把这话听进去了。私下便合计:虽说此处未曾去过,大着胆子闯它一闯,又有何妨?于是也就哐当哐当乘着绿皮车往这来了,也没费太大的劲便找着了这处门面。平时吃住都在这店里。
两人已有了三个孩子,清一色的“公鸡头”,大的快十三了,小的七八岁,差不多隔两年得一个。现都跟着奶奶在邯郸生活,上的是寄宿学校。暑假把他们接来,在南京住上一两个月。记得夏天时我们在店里见过这三个娃。客人不多的时候,他们就一人躺一张靠椅,手脚放肆地摆成“大”字。也不知悄悄地嘀咕什么,三兄弟突然就笑得咯咯的。外面太热,小店里开着空调,小家伙们都很受用的样子。大个子妈妈对我们说,一年里同娃在一道的时间也就两个月左右(放寒假不接他们来了,一年忙到头,过年总要回老家歇几天的),淘,就让他们淘一点吧。
小店的生意通常在中午饭过后,较忙的是晚上那一段,干到十一二点是家常便饭。但两个人的生活却挺有规律,每天上午8点前一准起身,蹬双运动鞋,往玄武湖跑趟来回。给人做足疗是个力气活,所以上午这两小时的户外锻炼,他们雷打不动。回来的路上,顺便从菜场就把当天的菜给买了(附近的几个菜场都曾一一探访,哪处摊子上的什么菜最便宜,他们都了如指掌)。
修脚的女人不加掩饰地对我们说,家里还有三个半大的娃呢,一块一毛都得算计着花。
女人姓水
叫车时同师傅通了个电话,是女的,等我上了车,后排望去,咋变成了个男的?板刷儿男孩头,握方向盘的手麻杆儿粗细,开车的动作:起步、跟上、穿插迂回,均显得干脆利落,绝对的男人风格。我有点迷糊,好奇地问了,她调转头,还真是个女的。后来的约莫五十分钟车程里,除了我不多的几句插问,主要是她不紧不慢地说自己的故事。
她从小生活在老城南夫子庙一带。18岁当兵,就在省军区小车班,给首长开车,一开三年。有个舅舅当时在公安,说姑娘大了不能老这么东跑西颠的,让她妈发话,赶紧退伍得了。舅舅还有点能耐,把她弄到了海关,但没车开了。只待了一年,由于关系不硬,被人挤了出来。后来去了一家国字头的金融江苏分公司,替一个从北京派来的老总开专车,风风雨雨地跟了他八九年。那老总后因经济问题被抓,没多久她也离开了公司。这辰光年纪也30岁了,经人介绍跟一个在地税局工作的男人结了婚。婚后才发现这男人迷麻将,好赌,夜不归宿几近家常。生了个女儿也没拢住男人的心,全是她一个人对付各类事。说有一回夜里女儿突发高烧,很危险,她给牌桌上的男人打了电话,让他速去医院,结果两瓶水挂完了回到家,也没见他人影。这样的日子她捱了五年,实在看不到半点希望,也只有认栽了。婚是通过法院离的,五岁的女儿判给了他,仅有的一套房子也留给了他们,而她只能回娘家。这一晃又过去十年,她没再嫁,一直就在外面开黑车。眼下这辆新车是她自己“跑”出来的,说这辈子或许就跟车过了。自从滴滴打车上了线,她就专门干这个了,记录上已有了近三千单。她并不是玩命地苦,早上8点出来,晚6点一准收工。生活挺有规律的,哪也不去。她觉得去饭局歌厅是浪费时间;好朋友“三缺一”找她,她把人家呛老远。是麻将把她家给拆了,你说她能不深恶痛绝?那男人后来找了个小他十几岁的,不过日子还是过得结结巴巴,有两个钱也都扔牌桌上了。女儿随了他,并未得到多少爱,时不时地总给她打电话。“手机费她爸不给,我让她绑在了我的号上,话费我来充。”没男人的日子倒也过得波澜不惊,消消停停,寂寞时会放上一段音乐听听。一天的车开下来,人也乏了,沾上枕头就到天亮。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冒失,无意中听了一个女人哀伤的故事。我对她说了这份唐突,可她一再地说多大事啊,那神情是真实的,话语里透着几分洒脱。下车前我问她尊姓,她朝我挥挥手:“姓水,水均益的水。”我笑了,说这个姓好,女人不都是水做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