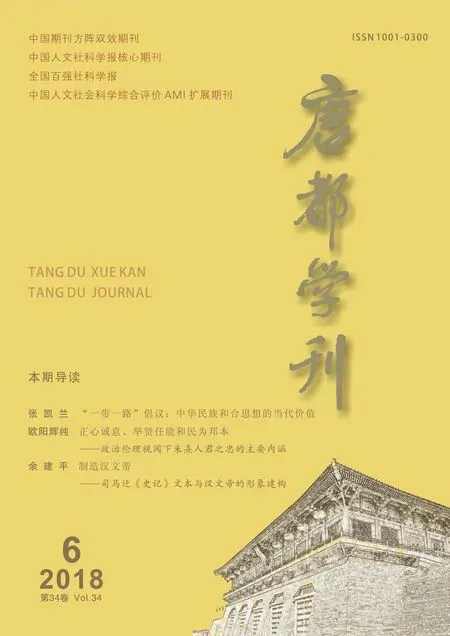菩提达摩付授四卷本《楞伽经》考
赵世金, 马振颖
(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兰州 730020)
一、问题的提出
《楞伽经》与中土禅宗关系非常密切,尤其禅宗初成时期的达摩一系,以四卷本《楞伽经》为最主要的印心传法工具,在达摩之后,被中土禅僧广泛接受。《续高僧传·慧可》中记载曰:“初,达摩禅师以四卷楞伽授可曰:‘我观汉地,唯有此经。仁者依行,自得度世’。”[1]568又《景德传灯录》承袭僧传记载,并对此略加考证,曰:“(达摩)师又曰:‘吾有楞伽经四卷,亦用付汝(此盖依宝林传之说也。按宣律师《续高僧传》可大师传云:‘初达摩以楞伽经授可曰,我观汉地,唯有此经,仁者依行,自得度世’,若如传所言,则是二祖未得法时,达摩授楞伽使观之耳。今传灯乃于付法传衣之后言。师又曰:吾有楞伽经四卷,亦用付汝,则恐误也。兼言吾有,则似世间未有也。此但可依马祖所言云,又引楞伽经文,以印众生心地,则于理无害耳’)。”[2]在达摩付授慧可四卷本《楞伽经》之后,逐渐形成一个以《楞伽经》为传法印心的系统,此经成为早期禅宗最主要的传法工具。对于以修习《楞伽经》为主的禅僧们,我们可以将其称为楞伽禅师。在道宣律师的《续高僧传·法冲传》中对于楞伽系的传法系统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文中载曰:
冲以楞伽奥典,沉沦日久,所在追访,无惮夷险。慧可师后裔盛习此经,即依师学,屡系大节,便舍徒众,任冲转教,即相续讲三十余遍。……今叙师承,以为承嗣所学,历然有据。达摩禅师后,有慧可、道育二人。育师受道心行,口未曾说。可禅师后,粲禅师,慧禅师,圣禅师,那禅师,端禅师,长藏师,真法师,玉法师。(以上并口说玄理,不出文记)。可师后,善老师(出抄四卷)、丰禅师(出疏五卷),明禅师(出疏五卷),胡明师(出疏五卷)。远承可师后,大聪师(出疏五卷),道阴师(抄四卷),冲法师(疏五卷),岸法师(疏五卷),宠法师(疏八卷)。大明师(疏十卷)。不承可师自依摄论者,迁禅师(出疏四卷),尚德律师(出入楞伽疏十卷)。那老师后,实禅师,慧禅师,旷禅师,弘智师。明禅师后,伽法师,实瑜师,宝迎师,道萤师。[1]1079
具体而言,自达摩之后,楞伽师分为两个系统:第一个系统即依慧可禅师修习《楞伽经》,有两种情况,即重视玄理,不出问句的粲禅师、慧禅师等。另外一种情况是重视经典的注疏与讲诵,即有善老师、丰禅师、明禅师、胡明师、大聪师、道阴师、冲法师等人,他们对于《楞伽经》进行注疏,并有遗作传世。另外一个系统,即不依可禅师,而依《摄大乘论》来注疏《楞伽经》者,具体有迁禅师、尚德律师等人。所以慧可门下两系,具体可以分为楞伽经师和楞伽禅师,他们在修习禅法的过程中,对于达摩“藉教悟宗”之说中的“教”与“宗”有不同程度的重视,所以形成不同的修学法门。学界将达摩付授慧可、慧可付授僧璨、僧璨传法于道信、道信又传至于弘忍这个系统称之为如来禅系,与以后的祖师禅进行区别。
达摩将四卷本《楞伽经》作为传法的依据,授予弟子,并逐渐形成中土自己的宗派,那么为何达摩禅师需要以《楞伽经》作为传法工具,并且选择四卷本的《楞伽经》呢?四卷本《楞伽经》与达摩禅法之间有何重要的关系?本文将进行详细论述。
二、《楞伽经》及其注疏概说
《楞伽经》,亦称之为《楞伽阿跋多罗宝经》,是影响中土佛教文化最重要的佛典之一,历来受到佛门释子的重视。《楞伽经》的主要思想以“五法”“三自性”“八识”“二无我”为中心,又多涉及“三界唯心”“唯识”“种性”“禅定”“涅槃”“顿渐”等重要思想,所以这部佛典亦被当作唯识学的基础。尤其是其中的种性论、一阐提论等对于中土佛性论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中土佛教各宗派中,禅宗受《楞伽经》的影响最深,只因早期禅宗诸祖都以《楞伽经》作为传法印心的主要工具。禅宗早期著名公案,即初祖菩提达摩付法二祖慧可,就以四卷本《楞伽经》作为工具。“吾有《楞伽经》四卷,亦用付汝。即是如来心地要门,令诸众生开示悟入。”[3]479b3-b5又“初,达摩禅师以四卷楞伽授可,曰:‘我观汉地,唯有此经,仁者依行,自得度世。’”[1]568在禅宗诸祖大力倡导下,宗门逐渐形成一个以《楞伽经》为最主要传法工具的楞伽宗。
《楞伽经》的梵文原本为印度笈多王朝时期出现的中期大乘佛教经典之一,“此经一般认为在无著以后成立。它与偏重于信仰并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的初期大乘经典不同,而偏重于理论的研究和哲学的思辨。”[4]这部佛教无上宝典在中土共有四个译本。首译本为北凉时期著名佛教译经僧昙无谶译本,据唐代靖迈法师所撰《古今译经图纪》载昙无谶曾译“《楞伽经》一部四卷”,在敦煌文献P.2198唐初圆晖法师所著《楞伽阿跋多罗宝经疏》中载曰:“陈译三藏,忽有四期。朝初晋安帝昙无谶译经成四卷,文没不行。”[5]所以至少在唐代时期,昙无谶译本就已经散佚。其后三个译本都存于当世,即南朝宋元嘉二十年(443)求那跋陀罗译本,这是中土佛教界流传最为广泛的一个版本。南朝宋译本共有四卷,其译文为这部经典的核心,即“一切佛语心品”,现存于正藏中,有北宋文士苏轼、蒋之奇为之撰写的序文。元魏延昌年中,天竺三藏菩提流支亦有十卷本《入楞伽经》的译本,分为十八品,初品为“请佛品”,第十七品“陀罗尼品”,第十八品“宗品”之外,其余十五品与求那跋陀罗译本较为相似。唐代武则天久视元年(700),大周于阗国法师实叉难陀奉敕译七卷本《大乘入楞伽经》,共有十品,在经文之前有御制序文,序文对于此经做了高度的评价,即“所言《入楞伽经》者,斯乃诸佛心量之玄枢,群经理窟之妙键,广喻幽旨,洞明深义,不生不灭,非有非无,绝去来只二途,离断常之双执,以第一义谛,得最上妙珍。体诸法之皆虚,知前境之如幻,混假名之分别,等生死之涅槃”[6]587a10-a15。说明武则天对于这部佛经也较为重视。就现存三部汉译本来说,求那跋陀罗译本语言艰涩,词多倒缀,难以句读。但是与梵文原本较为切合,且受到早期禅宗诸祖的推崇,所以其流传范围最广。相对而言,魏译本则略显文繁而晦涩。唐译本重视意译,强调行文上的流畅性,所以文义畅明,受到佛教界的推崇。许多佛门释子对这三个版本也进行了比较,例如明宗泐言:“若论所译文之难易,则唐之七卷文易义显始未具备,今释从宋译四卷者,以此本首行于世,习诵者众,况达摩大师授二祖心法时,指楞伽四卷可以印心。”[6]343c4-c7另外,这部佛典亦有藏文译本和日本南条文雄所校勘的梵文本。藏文译本与梵文本的内容比较接近。
隋唐时期,有关这部佛经的注疏之学相对非常贫乏,正如P.2198所言,在河洛地区没有这部佛经的注疏本。但是自宋代以后,佛门许多经师、禅师,甚至文人等都对其进行了注疏工作。据《东域传灯录》记载,这部经文的注疏自菩提流支之后不下百余种,兹将藏经所录入者列之表1。

表1 藏经所录入者
当然,《楞伽经》注疏失传者亦不在少数。近代一些佛门龙象以及著名学者对于《楞伽经》也做了较为详细的注疏工作。其中有太虚法师的《楞伽经义记》[7]、欧阳渐之《楞伽疏决》[8]、印顺之《如来藏之研究:〈楞伽经〉的如来藏说》[9]等。而在敦煌文献中圆晖的《楞伽经疏》也是非常重要的注疏本。
在敦煌文献中也发现了大量的《楞伽经》以及其注疏的文献,在敦煌文献中现存《楞伽经》及其注疏之作不下百件,如S.1074《新译大乘入楞伽经》,三藏沙门实叉难陀译(首题)、S1341Vb《楞伽阿跋多罗宝经一切佛语心品第一》、S.1560《大乘入楞伽经卷第六》、S.2268《大乘入楞伽经卷第二》、S.2363《大乘入楞伽经卷第七》、S.2800《佛说大乘入楞伽经》、S.2920《大乘入楞伽经》、S.3383《入楞伽经集一切法品第三》、S.3421《佛说大乘入楞伽经卷第六》、S.3631《大乘入楞伽经卷第二》、S.4396《佛说大乘入楞伽心经卷第七》、S.5311《楞伽经卷第四》、S.6339《新译大乘入楞伽经序》(御制)、S.6479《大乘入楞伽心经卷第七》、S.6657《大乘入楞伽经卷二》、S.6714《大乘入楞伽经卷第五》。从英藏文献来看,除了S.6339号为武则天所制经序之外,其他的多为武周译七卷本《大乘入楞伽经》与南朝宋译四卷本《楞伽经》,也可以看出不同版本在唐宋时期的流行情况。法藏敦煌文献中所存《楞伽经》数量较少,有五件,分别为P.2198《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开题》、P.2204《佛说楞伽经禅门悉谈章并序》、P.2235《新译大乘入楞伽经卷第一》、P.3099《佛说楞伽经禅门悉谈章并序》、P.5589f《楞伽经卷第五佛新品第四》(元魏菩提流支译本)。另外国图藏有66件,《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收录的《大乘入楞伽经》图版清晰,行文稳健大方,有专门的条记目录。从这些经典的写本面貌上来看,这批佛经有可能是达官贵人雇佣专业抄经人来进行整理。写卷的装订形式可以分为两类:一为卷轴装,一为贝叶装。在这些写本中,有一些《大藏经》没有收录的《楞伽经》注疏,比较重要的有P.2198《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开题》,是唐代中期著名僧人圆晖对于四卷本《楞伽经》的注疏,由太子少詹高阳齐澣为之作序,文字美观、整洁,保存得非常完整,是研究求那跋陀罗译本的主要参考资料,也是唐代非禅宗弟子所注《楞伽阿跋多罗宝经》的代表性著作,对于研究圆晖的修学法门以及其对于《楞伽经》的观点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四卷本《楞伽经》为传法简本考
如上所言,达摩传法为何以四卷本《楞伽经》作为传法印心的工具?另外,达摩印心工具是否是求那跋陀罗译本?因为北凉时期昙无谶也有四卷本《楞伽经》译本。对于后一个问题,汤用彤先生亦曾持怀疑态度,他认为:“达摩南天竺人,《楞伽》亦出自南印,达摩原于此经深所默契。及来华先至南方,得四卷译本,故以之自随,授于学者。非必四卷宋译为其所遵,而他译则彼所排斥也。”[10]昙无谶生于东晋太元九年(384),卒于北凉义和三年(433)三月,终年49岁。“大约在北凉玄始十年(421)左右,北凉沮渠蒙逊西来敦煌,昙无谶受其迎接,开始了他在北凉的弘法事业。”[11]在这期间,他在姑臧等地广译佛经,曾译出四卷本《楞伽经》[12],在敦煌文献P.2198中有明确的记载:“晋安帝昙无谶译经成四卷,文没不行”。但目前对昙无谶本《楞伽经》的内容、散佚时间及与求那跋陀罗译本之间的区别,皆无从可考。
现存流传最广的《楞伽经》就是宋求那跋陀罗译本,亦称之为《楞伽阿跋多罗宝经》,是禅宗最为重要的典籍。“求那跋陀罗,此云功德贤,中天竺人。以大乘学,故世号摩诃衍。本婆罗门种,幼学五明诸论,天文、书算、医方、咒术靡不该博。……元嘉十二年至广州,刺史车朗表闻,宋太祖遣信迎接。既至京都,敕名僧慧严、慧观,于新亭郊劳,见其神情朗彻,莫不虔仰。虽因译文言而欣若倾盖。初止祗洹寺,俄而太祖延请,深加崇敬。琅邪颜延之通才硕学,束带造门。于是京师远近冠盖相望,大将军彭城王义康、丞相南谯王义宣,并师事焉。倾之,众僧共请出经于祇洹寺,集义学诸僧译出杂阿含经,东安寺出法鼓经,后于丹阳郡译出胜鬘、楞伽经,徒众七百余人,宝云传译,慧观执笔,往复咨析,妙得本旨。”[13]僧传中记载求那跋陀罗在南朝宋受到上至帝王,下至百姓的普遍敬仰,特别是彭城王刘义康、丞相刘义宣对其执师礼,推崇备至。在《初三藏记集中》列举出求那跋陀罗所译经典共十三部,七十三卷。主要有《新阿含经》五十卷、《大法鼓经》二卷(东安寺译出)、《胜鬘经》一卷(丹阳郡译出)、《八吉祥经》一卷(元嘉二十九年正月十三日于荆州译出)、《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四卷(道场寺译出)、《央掘魔罗经》四卷(道场寺译出)、《过去现在因果经》四卷、《相续解脱经》二卷(东安寺译出)、《第一义五相略》一卷(东安寺译出)、《泥洹经》一卷、《释六十二见经》一卷、《无忧王经》一卷[14]。
求那跋陀罗所译佛教经典在刘宋时期所设立的译场中译出,从所译经典来看,既有大乘经典,也包含了许多小乘经典。当然,对于《楞伽经》的翻译在《禅宗灯录中》多有记载。例如《楞伽师资记》中载曰:“宋求那跋陀罗三藏,中天竺人,大乘学时号摩诃衍。元嘉年,随船至广州,宋太祖迎于丹阳郡,译出楞伽经,王公道俗请开禅训。”[15]1283c25-c29《楞伽师资记》将求那跋陀罗定为第一祖,当然这种做法在其后的《历代法宝记》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认为《楞伽师血脉记》“妄引宋朝求那跋陀罗三藏为第一祖,不知根由,惑乱后学,云是达摩祖师之师。求那跋陀罗自是译经三藏,小乘学人,不是禅师。译出四卷《楞伽经》非开授《楞伽经》与达摩祖师,达摩祖师自二十八代首位相传,承僧伽罗叉后云云。”[16]当然,唐代之后的禅宗灯录,由于受到南北二宗相互分裂、相互攻讦的影响,其传法系统多带有偏见。但是他们均认为达摩所传《楞伽经》为求那跋陀罗译本。
昙无谶所译四卷本《楞伽经》虽然在当时的北方地区没有引起巨大的反响,但是求那跋陀罗译本却与其背道而驰,受到南朝地区僧徒、士大夫的欢迎。特别是经过慧可、僧粲等人的倡导后,四卷本《楞伽经》的地位迅速提升。那么四卷本《楞伽经》与七卷本、十卷本《楞伽经》究竟有什么差别呢?
四卷本《楞伽经》相对于另外两个版本,其流传时间更远,虽然昙无谶所译四卷本《楞伽经》散佚,但是我们不可否认其对于一些禅学僧人或多或少产生过影响。再加上求那跋陀罗译本的广泛流传,所译四卷本《楞伽经》在时间上更加有优势。从内容上来看,四卷本和十卷本《楞伽经》的主要思想体系是一致的,“都专门讨论的是如来藏和阿赖耶识的问题,并要求通过对佛教一系列名相概念的把握而获得佛智,证入佛境,但两者在义理上的侧重有不同。”[17]四卷本只有《一切佛语心品》一品,其主体思想与十卷本中的《集一切佛法品》和《佛心品》大同小异,而十卷本《楞伽经》的精髓在《集一切佛法品》和《佛心品》中。第一品《请佛品》与第十八品《总品》只是概说而已,没有什么具体内容。其余的《路伽耶陀品》《无常品》《刹那品》的中心内容也没有前两品突出。“若论所译文之难易,则唐之七卷文易义显始未具备,今释从宋译四卷者,以此本首行于世,习诵者众,况达摩大师授二祖心法时,指楞伽四卷可以印心。”[6]343c4-c7所以在明代丛林高僧宗泐看来,四卷本《楞伽经》具有两个重要的优势,相对于七卷本、十卷本来说,四卷本最先译出,流传时间最久;另外,受到达摩一系印心的影响,其地位更加突出。当然,文句简古也是其一个重要优势,所以四卷本《楞伽经》可以被认为是传法简本,更有利于所宣传的如来藏和阿赖耶识等思想的传播。印顺禅师亦认为当时在达摩传法之时,四卷本、十卷本《楞伽经》都已经译出。达摩选择四卷本《楞伽经》作为传法印心的工具,其主要原因是语言方面的障碍。“达摩从南方而来,与江南的四卷《楞伽》有关系了。从西天竺来的大德,起初都是不通华文华语的。要弘传经法,由自己传译出来,否则只能泛传大要了。达摩从天竺来,却传授译为四卷本的《楞伽经》,这非长期在中国,通晓华文不可的。这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续高僧传》载曰:达摩初达宋境南越,达摩早在宋代已经到了中国,那么四卷本《楞伽》的传授,也就不足为奇了。”[18]印顺法师认为从时间和语言上来说,四卷本对于达摩传法更具有优势。但是达摩既然精通四卷本《楞伽经》,那么他对于十卷本《楞伽经》的掌握似乎亦不是太难,而其将四卷本《楞伽经》传授学僧慧可,成为传法印心的工具,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四卷本《楞伽经》作为“传宗简本”更有利于早期禅学的弘扬。
传宗简本在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最为常见,例如敦煌本《六祖坛经》就是典型代表。《坛经》版本众多,其中包含契嵩本、惠盺本、德异本、宗宝本、敦煌本,前几个版本的字数都超过了两万,而敦煌本《六祖坛经》只有1.2万,而众多学者认为,敦煌本《六祖坛经》是为最早的版本,但是也有许多学者提出质疑。“敦煌本《坛经》最有可能是神会一系付法传承的节略本,而非最接近曹溪古本的《坛经》版本。”[19]其实,这种情况在中土佛教传法的过程中最为常见,例如《般若经》与《金刚经》、《妙法莲华经》与《观世音普门品》等,所以四卷本《楞伽经》是禅宗早期传法的简略本,对于其名相、心性说都有集中的体现。
另外,达摩本为天竺人,而四卷本《楞伽经》的翻译情况最接近于梵文原本,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达摩比较重视原典的思想。无论是达摩禅法,还是其后的东山法门、曹溪禅法,均倡导重视心性的修炼。而四卷本《楞伽经》就只有《一切佛语心品》一品,强调“诸佛心第一”。正如吕徵先生所言:“事实上,四卷本《楞伽经》只是用《一切佛语心第一》作为品名,而且这个心字,意思为‘枢要’、‘中心’,即是说佛教中的重要意义在《楞伽经》中都具备了,并非指人心之心。”[20]四卷本《楞伽经》中就已经指出了“默心自知,无心安身,闲居净坐,守本归真”的安心法门,这里的“安心”之法与二入四行论中的“安心”意义相同,而这种心也是如来藏思想的核心。
四、四卷本《楞伽经》思想与达摩禅系
菩提达摩被尊为东土禅门初祖,他以四卷本《楞伽经》传授于慧可,慧可之后逐渐形成一个以修习《楞伽经》为主的禅宗系统,后经过僧璨、道信、弘忍等祖师的传诵,禅门发扬光大,早期禅僧都以《楞伽经》作为传法印心的工具,直到六祖慧能孤明先发,将《金刚经》作为禅僧修学参禅的工具,《楞伽经》才逐渐被摒弃。所以,《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在达摩禅系传法印心的这个过程中,其作用与意义非常重要。在《续高僧传》中,有菩提达摩的传记,载曰:“菩提达摩,南天竺婆罗门种。神慧疏朗,闻皆晓悟,志存大乘,冥心虚寂。通微彻数,定学高之。悲此边隅,以法相导。初达宋境南越,末又北渡至魏,随其所至,诲以禅教。于时合国盛弘讲授,乍闻定法,多生讥谤。”[1]565-566对于菩提达摩的生平许多文献中都有记载,而《续高僧传》关于菩提达摩的记载最为真实。“菩提达摩在刘宋时期,经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到达广州南海郡番禺县”[21],在南朝境内进行传法活动,后又前往北魏,到达都城洛阳并且拜谒永宁寺,弘化洛滨,在少林寺面壁坐禅数年。达摩生平充满了许多疑点,兹不赘述。达摩经过海上丝绸之路,首先到达南朝地区,并在南朝地区进行过传法活动,这些事件也都是确定无误的。那么达摩到达之后,势必会受到当时南朝地区已经长久流传的四卷本《楞伽经》的影响。在《楞伽师资记》中说“魏朝三藏法师菩提达摩,承求那跋陀罗三藏后。其达摩禅师,志禅大乘”,暗示两人似乎碰面,但是对于禅宗的一些灯录,我们对其真实性尚待商榷。但是首先可以肯定的是,菩提达摩确实在南朝时期就已经受到求那跋陀罗所译的四卷本《楞伽经》的影响。那么,他将此经传给自己的弟子慧可也具有很大的可能性。
当然,我们对于达摩付授慧可四卷本《楞伽经》并不能仅仅局限于他早已对其熟知。当时南朝宋流行的其他佛教经典亦不在少数,为何达摩选择《楞伽经》作为传法依据?达摩至北魏传法之时,十卷本《楞伽经》业已译出,达摩为什么选择四卷本而不是十卷本呢?
在中土遗留下达摩的著作比较少,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二入四行论”,在《续高僧传》《楞伽师资记》《景德传灯录》中有一些记载。另外在河南等地有一些达摩的碑文,敦煌文献中也有一些有关达摩的著作,这些文献都有利于我们对于达摩的佛法进行详细的勾勒,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其思想与《楞伽经》有许多共通之处。《楞伽师资记》中对于达摩禅法的内容进行了总结,即“如是安心,如是发行,如是顺物,如是方便,此是大乘安心之法,令无错谬。如是安心者,壁观;如是发行者,四行。如是顺物者,防护讥嫌,如是方便者,遣其不着,……夫入道多途,要而言之,不出二种:一是理入,二是行入。”[22]达摩禅法的核心是理入与行入,而其包含四个方面,即安心、发行、顺物、方便四个法门。“二入四行论”在《续高僧传》中亦有详细的说明,“然则入道多途,要唯二种,谓理行也,籍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客尘障故,令舍伪归真;凝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坚住不移,不随他教,与道命符,寂然无为,名理入也。行入四行,万行同摄。初抱怨行者:修道苦至,当念往劫,舍本逐末,多起爱憎,今虽无犯,是我宿作,甘心受之,都无怨对。经云:‘逢苦不忧,识达故也。此心生时,与道无违,体怨进道故也,二随缘行者:众生无我,苦乐随缘,纵得荣誉等事,宿因所构,今方得之……三名无所求行:世人长迷,处处贪著,名之为求。道士悟真,理与俗反,安心无为,形随运转。……四曰称法行:即性净之理也。”[1]566对照两者的说法,内容基本相同,《楞伽师资记》中有关“二入四行论”的说法继承于《续高僧传》,两者都讲求安心,而安心的主要修学方式在于壁观,提倡后来禅宗最为流行的“凡圣等一”的思想,如《六祖坛经》所言:“善知识,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即缘心迷,不能自悟,须求大善知识示道见性。善知识,育人智人,佛性本亦无差别,只缘迷悟,迷即为愚,悟即成智。”[23]达摩禅法以理入为总纲,以行入为条陈,通过教理与实践相结合,贯彻佛法的真理。“达摩的‘行入’禅法的四行都是强调以佛教四法印尤其是大乘佛教法性本净的基本原理来指导实际践行,在实际事行、实际生活中体证佛教的真理……”[24]达摩的“二入四行论”中的思想与《楞伽经》都有相通之处,例如他所倡导的“真心”“凡圣等一”“安心”等与《楞伽经》中的思想几乎一致,《楞伽经》的主题思想倡导如来藏,而四卷本《楞伽经》的核心就是一品“佛语心品”,圆晖法师将这一品的题目理解为“今此经宗名佛语心,即如来藏,故下经文诸佛心,第一又云:远离诸见过,故知经宗是如来藏”,如来藏就是“如来清净之心”,也就是所谓的真心。而《楞伽经》也倡导所谓的“凡圣等一,皆可成佛”,与达摩的思想完全达成一致。所以我们也可以认为《楞伽经》对于达摩思想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作用,那么他选择四卷本《楞伽经》作为传法印心的工具也是可以理解的。
另外,达摩禅法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所以在达摩北上至魏后,其禅法并不受欢迎,因为北方的禅法仍然注重最基本的禅修,对于禅学理论并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这在北方众多佛教石窟造像中就有明确的体现。《楞伽师资记》中有“达摩游化汉魏时,忘心寂默之士莫不归信,取相存见之流,乃生讥谤”,面临诸多困境,所以达摩选择以四卷本《楞伽经》作为普及禅法最基本的圣典。四卷本《楞伽经》讲求如来清静之心,又重视破除妄想执着以显示真如实相,同时也专门谈及禅法,所以对于当时的佛教背景和达摩自身的情况来说都是比较合适的。我们也发现《楞伽经》中的一些思想,确实对于后来的禅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且时间也比较持久。例如对于“文字”“语言”的观点,《楞伽经》倡导文字、语言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工具,是修行“真如”思想的工具之一,并不能执着于语言、文字。总之。达摩禅系与四卷本《楞伽经》保持着非常紧密的联系,这也是其受到达摩一系僧徒重视的主要原因。
综上所述,达摩付授四卷本《楞伽经》于慧可,慧可传之于僧粲,僧粲又传之于道信,祖祖相传,形成一个传灯系统。那么达摩付授刘宋求那跋陀罗四卷本《楞伽经》的原因是什么?据上文可知,四卷本《楞伽经》在时间上占优势,昙无谶、求那跋陀罗所译《楞伽经》均为四卷本,所以他们对于佛教界产生的影响较为深远。相对于七卷本、十卷本《楞伽经》来说,四卷本《楞伽经》思想较为集中,语言简练,更有利于当时的传法、弘教活动。另外四卷本《楞伽经》在思想上、语言上都符合达摩禅系的要求,所以其流传范围更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