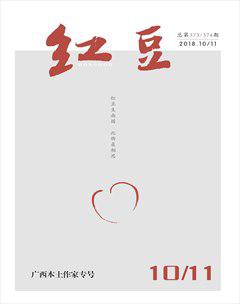草沟人物志(短篇小说)
莫灵元,20世纪60年代出生,广西宾阳县人。出版有作品集《梦若春天》。现为广西作家协会会员、崇左市作协副主席、崇左市小小说学会会长。
草沟村坐北朝南,背后和左右两边是连片的水田、水草和沟渠水洼,村前则是绵延起伏的丘坡土岭。按照地理先生的说法,这样的村子是很难出什么人才的。
事实上,地理先生是看走了眼。
这个村子虽然不大,还有些低洼,但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全村人皆姓陈,另一个是他们都是移民。据说,他们的先祖是从山东过来的,跟随狄青将军南下打仗,后来留了下来,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因为是同宗共祖,村子里每个人都如同大树分出的枝枝桠桠,人人按班排辈,“星汉光辉远,春秋家业长”,就是他们排辈诗的其中两句,同辈分的人都要取诗中同一个字来起名,所以,谁的辈分高低一看名字就能分得出来了。
俗话说:一粒米养出百样人。草沟村是个小社会,天长日久,什么样的人都会有,如果不嫌烦,可以大书一箩筐。
瓜劳卖鱼结亲
草沟村流传这么一个笑话,叫做“母鸡三文糠十八”。笑话的主人公是陈劳秋。
陈劳秋没有上过学,识字不多,算术也差。有一天,母亲把他叫来,吩咐他捉只母鸡和挑一担米糠到集市去卖,换些油盐回来。陈劳秋提了母鸡挑上米糠上了路,母亲再次叮嘱他,米糠卖三文钱,母鸡卖十八文钱,千万记牢了。陈劳秋一路上走,嘴里时不时地默念:米糠三文母鸡十八文,母鸡十八文糠三文……担子从左肩换到右肩,又从右肩换到左肩,走走歇歇,陈劳秋到了集市,担子才放下,就有人过来问价了。“母鸡三文糠十八!”陈劳秋开口就报了这个价,他一路念来念去,颠三倒四的,把母亲交代的价钱弄反了,于是母鸡一开价就被人买了去,可米糠等到日暮散市也没有人买,他只好又挑了回来。一只母鸡才卖了三文钱,而一担米糠倒要叫卖到十八文,母亲把陈劳秋狗血淋头一顿好骂!从此,草沟村人人都知道陈劳秋做了件天大的傻事,明里暗里都叫他“瓜劳”。瓜,是草沟村这一带地方对傻瓜、对懵懂之人的形容词。
村里人,无论老少,都是直来直去呼陈劳秋为瓜劳,就连他的父母也是这么叫。
陈劳秋长到十八九岁,变成了一个英俊的小伙子。他父母托人帮他找对象,他连女方的面都不敢见,走到半道上就开溜了。
瓜,确实瓜。
但瓜人自有瓜福。瓜劳在草沟村却是第一个自己找来老婆的人。
这里,还得说说瓜劳的父亲陈春光。
草沟村三面皆水,无论深浅,都是鱼虾的世界。于是,捉鱼去卖便成了草沟村人重要的经济来源,草沟村男人们的能耐,也主要表现在捉鱼的本事上。
草沟村人捉鱼的手段有布网、撒网、放钓、装鱼笼、吊罾、用篾织鱼具拦堵水口等,有时候也会截滩戽水,涸泽而渔。偶尔,也有炸鱼、毒鱼、电鱼的,不过,这些办法害大于利,尤其是毒鱼,等于自断后路,如同杀鸡取卵,为众人所愤,不轻易有人敢犯恶而为。
陈春光捉鱼,高人一筹。他的本事全在听字上。听鱼。有人说,只要陈春光走过,哪里有鱼,有什么鱼,有多有少,他一听就全知道了。这话可能太夸张,但也并非乱说。陈春光最拿手的手段,是捉塘角鱼。夏秋时节,陈春光常常半夜里挑一对水桶和几个鱼笼出门。他沿渠边湖边一路巡行,细听哪里有“噗噗”的声音。这是塘角鱼冒头换气的声音,常人一般辨识不到,只有他一听到便心知肚明。于是他下到水里,把鱼笼沉埋下去,用笼头堵住鱼窝洞口,这样,塘角鱼出来换气时就须得从笼须钻过,笼须是锥状的,软的,篾片都粘连了,塘角鱼出得来可回不去了。陈春光每隔一个时辰就下去换鱼笼,把捉到的塘角鱼倒到水桶里,水桶盛有适量的水,塘角鱼不会挤死、闷死、压死。陈春光从不把鱼窝里的塘角鱼捉完,他看看收获差不多了就收手,然后回家,吃了早餐再拿到圩场上去卖。
陈春光想把这个本事传给大儿子瓜劳,但是,瓜劳就是不开窍,接不了班。不过,瓜劳学得了另一种本事,那就是捉青蛙。
夏天,瓜劳躲在树荫下面,手执一根长长的钓竿,细细的钓绳末端拴着一只蚂蚱或者别的什么虫子作诱饵。他把诱饵甩到池塘水面的荷叶上,然后轻轻拉动诱饵勾引隐藏在水下或者荷叶间的青蛙。青蛙见到诱饵在跳动,以为是虫子,闪扑过来一口含住诱饵。瓜劳执钓竿的手迅速一提,另一只手持专用网兜伸过去,两手配合得十分默契。青蛙被提起来知道上当后迅即放开诱饵,却已经迟了,掉进网兜,成了囊中物。冬季水退,四野里一片干涸,青蛙冬眠。它们躲进泥洞里,不吃不喝不鸣叫,踪影全无。瓜劳拿一根约一米长的粗铁线,铁线的一端弯成一个小钩,他沿着沟边、湖岸或田埂仔细搜寻过去,看见小土洞有光滑的泥土封住,即把带钩的铁线插进去。铁线可以弯曲,即使土洞是曲的,也可以钻到底,若里面有青蛙,那么铁钩就会滑过青蛙身体把它钩住,铁线拉出来,青蛙也就同时被拉出来了。这种方法顺当好玩,能捉到多少青蛙,关键是会否辨识青蛙洞。
陈春光拿鱼去卖,常常要带上瓜劳,目的就是教他如何叫价,如何称鱼,如何算钱。慢慢地,瓜劳也就学会卖鱼了。
那时候,自行车属于紧缺商品,凭票供应。瓜劳家在本村率先买到了一辆。他家是贫农成分,二叔陈春亮当着生产队长,优先把购车票送给了大侄子。家里平时卖鱼攒了些钱,又刚好卖了一头猪,陈春光也觉得有辆车,儿子驮鱼去卖确实方便,所以遂了瓜劳的愿。
瓜劳学车还算快,摔了几跤,就抬脚从前面上车,跨脚从后面上车,全都会了。赶集的日子,他把鱼桶绑在自行车后座,丁零零,时不时打铃往前奔。一路上,那些赶马车的,挑担的,徒步的,听到铃声,都让着他。
“这是谁家的孩子呀!”
有知道的,也有不知道的。瓜劳骑着车子,都是一闪而过,感覺就是脚下生风,头上风生,风声不断,风光无限。
这样的一个瓜劳,暗地里俘获了李美娟的芳心。
李美娟家住大垌村。这个村由于邻近集市,村民多以种菜为业。几乎,每个集市日子,李美娟都要担菜上圩场去卖。
以前的瓜劳,李美娟也许没注意到,骑自行车的瓜劳,她注意到了,而且越看越喜欢。
那天下午,秋高气爽。瓜劳卖完了鱼,吃了碗猪杂米粉,便打道回家。才出到街头,他又看到了李美娟。
李美娟挑着一副空担子,慢悠悠地走。瓜劳一望就知道是她。
李美娟即使挑着担子也是体态婀娜。她这天穿得一身新,新蓝布长裤,新白底红花短袖,乌黑的头发梳成两条辫子垂在脑后。
瓜劳每次来卖鱼,几乎都碰见李美娟。有一次,她卖完了蔬菜,还去过他的鱼摊,买了几条塘角鱼。从此,瓜劳对这个脸蛋红扑扑、眼睛水灵灵、声音好好听的女子印象深刻。
瓜劳骑车来到李美娟身边时特意放慢了速度,接着竟然下了车,把车子支起来,然后认真查看链子。
车子坏了?
好好听的声音在耳边响了起来。
瓜勞抬头看了一眼李美娟,说,链子可能长了些,有点松。
不是坏了吧?
不是。瓜劳答应着,推起了车子。
经常见你来卖鱼,你叫什么名字?李美娟问。
我叫陈劳秋,草沟村的,你呢?
大垌村的,我叫李美娟。
哦,难怪你经常担菜来卖,大垌村人会种菜,你家的地都是用来种菜吧?
没有,有种稻谷、种玉米、种红薯的,种菜只种了一块地。
哦,你家的菜一定种得很好。
怎么说呢,家家差不多是一样的,只要不偷懒,谁都能种好的。
说的也是。人勤地生金!
你也勤呀!圩圩都见你拿鱼来卖。李美娟笑着回应。
这都是我爸捉的。我爸白天干活,晚上去捉鱼。瓜劳实话实说。
你爸真有本事!李美娟由衷赞叹说。
他们两个一边慢走,一边交谈,最后是李美娟挑着空担子和鱼桶坐到车后座,瓜劳奋力踩着自行车,飞快地行驶在回家的路上。
在那个年代,一对青年男女敢于如此这般凑在一起,那绝对不是一般的关系。
果然,到了次年的国庆节,这一对男女喜结连理,拜堂成亲了。
瓜劳不瓜。
瓜劳自己为自己找来了个好老婆。后来,他们生了五男二女,大儿子陈家文在草沟村第一个考上了大学。
背推哥砌墙为匠
“背推哥”大名陈英秋。
推,是草沟村一带地方对石磨的俗称。
石磨分上下两部分,有大有小。大的要配装长木钩,吊在屋内横梁下面,由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来推;小的一个人就可以操作了,左手放米,右手推磨,用来磨米浆做糍粑做米粉。
“背推哥”陈英秋的花名来自卖小石磨。
陈英秋母亲的娘家在草沟村邻近的高垄村。这个村刚好相反,缺水,但不缺石头。陈英秋的舅舅是个石匠,主要凿制石磨卖。陈英秋常跑去看舅舅,不算拜师学艺,算帮忙或者玩耍也许更准确。陈英秋舅舅卖磨,偶尔会拿到集市上摆,去展示,但更多的是在家坐等买主上门定制,然后送货上门或者买主自己来取。陈英秋帮舅舅,主要是送货。有一天,陈英秋在去往舅舅家的路上,有人叫住了他,问他是不是杨文宝的外甥。陈英秋说是呀。那人高兴地说,我在你舅舅家见过你,这样吧,我正想去你舅舅家,现在就不用去了,你替我告诉你舅舅,帮我做对小石磨,价钱就按老规矩,做好了送到我们村。我是大岭村的,姓黎,叫黎背推,你送磨到大岭村,问谁是“背推哥”,人人都知道。陈英秋听说有生意做,也不问那人要定金,立马就答应了,还说舅舅家有现货,今天就可以送过去。那人说好啊,我下午在家等你。陈英秋到了舅舅家,跟舅舅说了,把小石磨绑上自行车就朝二十多里远的大岭村赶去。到了大岭村,他把自行车锁在村头,然后用肩头扛起石磨就去找“背推哥”。大岭村是个大村,有上百户人家,陈英秋肩扛着石磨,从村东走到村西,从村南走到村北,大街小巷,曲曲弯弯,问谁都不知道有个“背推哥”,问有没有叫黎背推的,也都说没有。问来问去,一些人看着他还想笑,说“背推哥”?背推,谁背推呀?他知道上当了,被人耍了,可一肚子火气又无处可发,只得悻悻地复驮石磨回来给舅舅。舅舅没有生气,他反复念“黎背推”,之后说,孩子,“黎背推”,没有,“你背推”,有,你就是“背推哥”!这玩笑开过头了,以后多长些心眼吧。舅舅说陈英秋时,有上门订货的客人在场,舅舅这么一说,陈英秋的这个花名就被传开了。
高垄村有很多石头砌成的墙。这些石墙是怎样砌起来的,陈英秋曾亲眼见过。他觉得并不难,他也能砌。
他最初的实践,是砌自家的猪圈和围墙。
他砌的猪圈,结实,稳固,只是墙面凹凸不平,墙体也有些歪扭。但总算是一试成功,在草沟村首创用石头做猪圈的历史。
砌了猪圈,背推哥又砌自家门前的围墙。他把原来破败的泥筑土墙推倒,再拉石头回来砌。这回砌墙,背推哥更加上心。他认真挖好地基,砌墙时还拉起了白线绳,目的是把墙砌得更直。每叠高几块石头,他又拿白线绳吊上石头做的垂直线来比对,避免把墙面砌斜了。所以,围墙砌成后,美观度比猪圈高出了很多,引得村上人个个赞赏。
从此,草沟村渐渐兴起了用石头砌猪圈、砌牛栏、砌围墙甚至砌石屋的风气,背推哥当之无愧成为引路人,而且也是砌石头墙砌得最好的匠人。
有这手艺在身,背推哥后来干脆拉上队伍,当起了小工头,在四邻八村专砌石屋。那时候,农村人还不知道钢筋水泥为何物,所以新建房屋能够告别土夯墙改用石头墙,那可是一种时髦。陈英秋的本事派上了大用场,接到的工程在秋冬两季一个等着一个,收入比种田耕地不知要高多少倍。
然而,草沟村一带地方,建石头墙房子就像一阵风,只吹了三四年时间。原因是外地人带来了新工艺,他们挖坑造窑,烧制红砖,用这种建筑材料来建造房子,更加洋气,墙体又薄又美观,所以一下子就受到了人们的青睐。石头墙无可奈何花落去,不可遏止地被取而代之了。
背推哥看家的本事没了用武之地,他当然很是失落。好在,他脑筋并不古板,很快就顺应新形势,重新振作了起来。他对人说,砌砖有什么难,比砌石头容易多了!
接下来,人们看到背推哥做了件似乎是很不划算的事情。他把自家刚建起不久的石头房子拆了,重建,砖砌的。
那个时候,他们三兄弟已经分家。老房子留给三弟陈荣秋和父母住,他和大哥陈勇秋另立门户,到村西头各建了房子。
背推哥陈英秋新建不久的石头房子也就两间半,半间是搭在大房旁边的厨房,矮了一截,仿佛大人背着个小孩。房子的确是不够雅观,也不够大气,不过,还可以住,没必要拆的。但是,背推哥就是拆了。
重建新房子,背推哥没有另请他人,招呼来自己工程队的原班人马动手就干。两个来月工夫,一座五连间红砖青瓦的新房子成功告竣,厨房建在庭院的另一头,用石头矮墙围成一体。为什么还要砌石头墙呢?背推哥说,这些,都是我们的手艺,不能丢的!
再接下来,背推哥的工程队又接到新工程了。
技术就摆在背推哥家里,好不好你自己去看!
后来,县里评选表彰各行各业领军人物,背推哥荣登全县十大能工巧匠榜单。那张装在镜框里的奖状至今一直挂在背推哥家的厅堂上。
现在背推哥已经很老了,他偶尔也看看那张发了黄的奖状,如果有蛛网或灰尘,他要用掸子去扫一扫。
马骝三杀猪装神
杀猪就像过年。谁家杀猪,谁家就像过年。
这是草沟村的盛况,见于生产集体化的年月。
那时候,家庭可以养鸡、养鸭、养鹅,也可以养猪,但不能养牛、养马。牛和马属于集体经济所有,所以体量仅次于牛和马的猪,成了每个家庭发展经济的首选。
养大了猪,还得首先卖给国家,卖一头才可以留一头,由自家宰杀,猪肉拿到圩场去卖。这就叫“购一留一”。
哪家杀了猪,都要灌猪血肠,煮猪骨粥,留下小部分猪肉,遍请左邻右舍的老人小孩过来吃一餐。大方一些的人家,留下的猪肉要多一些,请的人也要多一些。无论请客多请客少,都是热闹的,喜庆盈门,如过年一般。
杀猪不是杀鸡,得请专干这行的屠户,杀猪佬。
草沟村唯一干这个行当的人,是马骝三。
马骝三,本名陈家显。他在同胞兄弟中排行老三。草沟村人习惯以排序称呼小孩,前边加个“阿”字。也有以性情、相貌、诨号前缀的,马骝三就是。
马骝是草沟村人对猴子的俗称。猴子机灵敏捷,马骝三人如其名。
马骝三干杀猪这行当,是在他长大成家自立门户以后。在没有结婚之前,他可是个游手好闲的浪荡仔,偷鸡摸狗、辱老欺幼的事也曾做过。他有一个过人的本事,就是捕野猫。
野猫,抓老鼠,也抓鸡,有的几乎成了抓鸡虎,特招人恨。
马骝三爱养狗。他的狗专为打猎用。
一般是在秋冬季节的晚上,马骝三带着他的狗,头上套着远光灯,手拿一根圆木棍,一个人向村外走去,四处游逛。
有没有野猫的叫声無所谓。马骝三的远光灯四下扫射,若照到了野猫的眼睛,就会看到两点淡绿色或者暗黄色的反光。这时,马骝三把灯光锁定野猫,同时唤他的狗撵过去。他的狗已是训练有素,见到主人唤它,它就知道是什么了,于是沿着灯光的方向勇猛扑去。有时候,狗很快就成功了,追上野猫,一口就咬断喉管;有时候,没有那么顺利,不是野猫死命逃脱了,就是野猫临急爬上了树,得对峙好长时间才能抓到它。马骝三如今左边耳朵缺了一小块,就是在一次捕猎中留下的创伤。那只野猫被狗撵上一棵苦楝树后,他举着远光灯一刻不停地照射它,还不停地吆喝,狗也跟着狂吼。也许是那野猫害怕了掉下来,也许是它暴怒了跳下来,反正它就是直冲灯光扑咬过来的,若不是马骝三慌忙偏头躲避,恐怕伤着他的不是一只耳朵,而是他的整个一张脸。
有人说,那是报应。马骝三从那以后不再捕捉野猫,并且是老老实实做人,老老实实干农活。再后来,他学会了杀猪。
马骝三杀猪,有个讲究。
谁家要请他去杀猪,必须提前三到五天上门到他家去请,口头请还不行,得有纸条子,红纸黑字。马骝三说,这得排队,还要看日子,谁家日子若是不合适就不能杀生。人上门去请,空手去也不行,得带上米和鸡蛋,没有鸡蛋,米就得多带一些。这是选日子要用的,马骝三说。
马骝三杀猪的工具,一条长铁钩、一把柳叶尖刀、一把大板刀、一把剔骨刀、一杆小秤,都装在一个藤条篮子里,在杀猪前一天的晚上就送到要杀猪的人家。送工具去,顺便布置杀猪工序,安排人手。饭是要吃的,酒也要喝,这叫先把喜庆营造出来。
杀猪时间安排在凌晨公鸡打鸣头遍过后。杀猪的主人家,早早烧开了水,做好相应准备。时候一到,主人家暂时避开,马骝三手拿尖利的铁钩把要杀的猪赶出猪圈,赶到预定位置,然后一钩钩到猪的前脚脚跟处,再提起来,让猪跑不掉,三四个大汉迅速跟上去把猪按倒,并使之横躺在地,动弹不得。马骝三接过柳叶尖刀,左手抓猪耳朵,右手执刀捅入猪的颈部,扭一扭,才把刀拔出来,瞬即,一股红红的热血喷涌而出。旁边有人用簸箕托了面盆赶紧送上来,接血。
整个杀猪过程环环相扣,一气呵成。只是,从钩猪开始,被杀的猪一直嚎叫不停,响彻全村,打扰得许多人再也睡不成觉。
猪断气后,马骝三放下杀猪刀,对空遥拜三下,嘴里默念一阵子。他念什么,人们不得而知。问马骝三,他也不说,只是神秘一笑。
随后,是拿开水烫猪刮猪毛,开膛破肚,清洗猪下水,割猪头,把全猪分成两边,等等。
马骝三一刻不停,除了分派人清洗猪下水,其他都是他亲自做。
一头猪整理妥当,便要早早驮去圩场卖。出门前,大家要喝一两碗猪红粥。马骝三说,这叫开门红,喝了百事顺利,猪肉猪骨猪下水统统卖得好价钱。
马骝三还有一个规矩,就是卖完猪肉回来的当晚,他绝不到主人家吃饭,怎么请他都不去。主人家送他的酬劳,他在圩场上就拿了。马骝三说,晚上他还要做功课,把杀猪的事结了,一件还一件,不能拖的。
马骝三搞的什么神道禁忌,村里人不知道,也难知道,因为他从不解释。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马骝三确实吃香喝辣了好长一段时间。后来,改革开放了,商品经济日趋繁荣,从事经商的人越来越多,马骝三便淹没在芸芸众生之中。唯一不同的是,他在草沟村,第一个建起了水泥砖混结构的平顶房,任凭风吹雨打,安稳如山。
陈家文为文入仕
1963年,瓜劳陈劳秋的大儿子陈家文出生。
因为吃过没有文化的笑话,瓜劳对儿子寄予了厚望。到了陈家文能爬动的时候,有一天,瓜劳把小人书、珠算盘、圆珠笔、青菜叶、玉米粒、小石子、泥土块等物件,摆放到孩子面前,小家伙居然伸手就去抓圆珠笔。瓜劳两眼放光,嘴巴都合不拢了。这是当地农村的一种占卜,用来预测小孩的未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农村人并非个个都上学读过书,但这些传统朴素的认知却根深蒂固。孩子的这个喜好,预示着他长大后要拿笔杆子,做识文断字之人。
可是,陈家文上学读书之后,却不怎么上心。他贪玩。
白天,他常常同小伙伴们玩一种叫做“打尺”的游戏。晚上,特别是有月光的夜晚,他们则是玩“点毛差”。一群小伙伴聚在一起,先是一个个伸出一只手,把拳头摞在一起,上拳头握住下拳头的大拇指,接着上下周而复始地数拳头:“点毛兵,点毛兵,点到谁人谁做兵;点毛贼,点毛贼,点到谁人谁做贼……”“兵”和“贼”都分派完后,再让“贼”在规定时间内各自躲藏起来,然后“兵”们分头去找,去捉,直至找齐捉尽为止。一晚上反复这样玩,伙伴们又喊又叫的,乐不可支,不到大人催回家不收兵。
陈家文贪玩,在瓜劳看来,儿子根本不是块读书的料。他放弃了梦想,认命了,因为地理先生曾说过,草沟村村前挡着山岭,地势又往后面仰,人是走不出去的,只能窝在村里,老死家中。瓜劳把儿子的不上进归咎于本村的风水。
然而,谁也想不到的是,陈家文读到初中时,命运改变了轨迹。
这个时候,中国社会发生了变革,恢复了高考制度,连初中升高中也要择优录取。陈家文考取了本县唯一的重点高中。三年后,到1981年,陈家文一毕业便考上了大学。这在草沟村可是件石破天惊的大喜事。瓜劳遍请亲朋好友及左右邻居,欢天喜地办了一场升学宴。
1985年7月,陈家文师范大学毕业,学校将他分配回原籍王塘县安置。9月,王塘县人事局把他分配到三河乡中学当教师。
三河乡是陈家文家所在的乡,乡政府距离草沟村也就七八里地。
回到这么个地方工作,仿佛回家一般,陈家文有些失望。草沟村的老人们看到这样的结果,心里也免不了嘀咕。都是命哪!他们越发相信风水先生对于草沟村人的判定。
看来,草沟村的风水得改一改。
最想改的是瓜劳。
怎么改?先前的风水先生倒是曾出过主意,就是在村后背要造片大林子,挡一挡风,聚一聚气,让村子有个依靠,好发力向前走。
瓜劳去找现任村民小组长陈荣秋。
陈荣秋是背推哥陈英秋的三弟,开口就拒绝瓜劳,说村后背是一片好水田,以前你家当着队干,怎么不改?
这的确是个问题。以前,瓜劳二叔陈春亮当生产队长、老二陈作秋当民兵队长,破“四旧”立“四新”,跟风跟得最紧,连村西边的社公庙都拆了,风水先生若敢在他们面前出此主意,恐怕也被抓来批斗了。
那时候,背推哥一家,因为是富农的后代,在村里是没有话语权的。陈荣秋有高小文化,当时村里“量才而用”,让他做会计,记工分、理账务。
如今,陈荣秋有权了,但也不可以为所欲为。因为分田到户了,他能够去发动村民造林子?不说钱没有,就是地也没有了。
陈荣秋望望天,把瓜劳的提议当作笑话。
陈家文叫父亲不要多管闲事。
他说他不信这个邪。
果真,一年后,县里一纸调令将陈家文调到中共王塘县委机关报《今日王塘》报社,入编当上了专职记者兼编辑。
原来,陈家文心中早有计划,除了认真教书,把所有空余时间都用到了写作上面。他写三河乡各种各样的新闻,也写杂谈、杂感,更多的是写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主投报刊就是《今日王塘》。那时候,各地刚刚兴起创办县级党报,王塘县虽是個山区县,但也不甘落伍。办报纸,需要人才,主管宣传的县委宣传部唯才是用,睁大眼睛在全县范围内搜罗人才。随着陈家文的上稿越来越多,而且又是个多面手,宣传部长一锤定音,把陈家文调到了报社。
陈家文依靠自己的实力实现了离家进城的梦想,而且是进了个体面的单位,还分到了房子,他自己当然高兴,他父亲及叔叔们更加高兴。他办完调动手续、在县城安置妥当之后,回到村里请上下邻居喝了一场酒。他的意思只有一个:他当初说的话不是信口胡说,谁再说草沟村的人走不出去那才是胡说。
陈家文的本事还不仅仅是这个。
又一年后,他娶了县人民医院一名漂亮的医生,结婚成了家。
又两年后,他调到县委办公室。
从此,陈家文官运亨通。他后来官至县政协主席,正处级。
陈家武先兵后警
陈家武与陈家文同龄,是背推哥的二儿子。
他们同时上学读书,只是初中升高中时分开了,陈家武没能考上县重点高中,而是屈身去读乡里的普通高中。三年高中毕业,陈家武再复读补习两年还是名落孙山,于是选择参军,经体检、政审合格,到部队去了。
送陈家武当兵入伍前夕,背推哥也搞了很大的响动,杀鸡杀鸭,鞭炮放了十万响。
村上有人却嗤之以鼻。说人家瓜劳的儿子是去读大学,将来要当国家干部,你个背推哥高兴什么呢?当兵还不是退伍回来扛犁头!
这种话显然说早了。
陈家武去到部队经受锻炼,人越发长得威武英俊。他特别喜欢打篮球,在部队打,回来探亲也打。草沟村这一带地方有个习惯,每年春节都组织民间篮球比赛。陈家武回来探亲时参加过三次,草沟村得过两次冠军、一次亚军。如果没有陈家武参加,草沟村队几乎是第一轮就被淘汰了。
人长得健壮,又会打球,陈家武好比人中龙,很容易被人记住,到哪里都讨人喜欢。特别是一些未婚多情女子,几乎没有不向他暗送秋波的。
陈家武在部队由义务兵转为志愿兵,前后服役有10个年头。1994年,他转业回到王塘县公安局城中派出所工作,由兵变警,长枪换成了短枪。
陈家武在部队当过什么官,草沟村人不知道,他家也说不明白。可是,他一回来就“当公安”,草沟村没有谁不羡慕甚至敬畏的。这个“当公安”,是专抓坏人的职业,在草沟村人看来,比陈家文舞文弄墨威风多了。
陈家武为何能有这样好的运气呢?
这里还得说篮球。
那年冬天,陈家武回乡探亲,到县城去看望一位老战友。这位老战友也是个篮球爱好者,转业回来安排进了农业银行。陈家武来探访老战友,恰好遇上农行同公安局进行篮球友谊赛,比赛中农行队一位打中锋的主力队员扭伤了脚,这位老战友急中生智,请求让陈家武替补上场。友谊比赛嘛,图的就是交流和高兴,当然可以了。陈家武这一上场可不得了,他不仅让农行队最终反败为胜,而且不可救药地俘获了罗秀娥的芳心。罗秀娥何许人也?她是县政法委书记罗高明的侄女,县公安局110办公室的接线员。她身高一米六〇左右,长相不算很出众,但凭着有叔叔罩着,平时心气较高,甚至有些孤傲,不少年轻人对她只好敬而远之。陈家武替补上场打球,罗秀娥一见眼就亮了,尤其是陈家武在球场上生龙活虎的优美身姿,如电击斧凿一般,深深地扎进了罗秀娥的心里。球赛后,她不顾女性的矜持,主动找到陈家武的老战友,打探陈家武的底细。陈家武的老战友冰雪聪明,一看有戏,立即当了这个红娘。也是部队作风,他们两人第二天便见了面,一见就定了终身。县公安局局长业余爱好也是打篮球,罗高明跟他一通气,他二话不说就同意进人了。和罗秀娥结婚不久,陈家武转业到了王塘县公安局城中派出所。
城中派出所是王塘县城区唯一的一个派出所,陈家武在那里干了两年零八个月,就提拔调到三河乡派出所任所长。
回到老家门口当派出所所长,陈家武有一种亲切感,也有光荣感,觉得自己就是一名父母官。
而此时的草沟村,非比往昔,人心几乎都散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村里人互争屋地引起了纠纷,各不相让,甚至反目成仇,并结成了近亲家族联盟,使得全村分成了若干个团团伙伙,平时各顾各的利益,各守各的底线,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惹到自己,则群起而反击。
陈家武的三叔陈荣秋拆除老屋建新楼,他为了横平竖直摆正楼房位置,挖地基时稍稍扩占到了陈家文祖屋的地盘,陈家文的小叔陈得秋差点和他打了起来,至今两家仍然是鸡犬之声相闻,人却全不往来,路上遇见,也是你看过这边,我望过那边,权当没看见。
陈家武在三河乡派出所工作了3年,为保一方平安做了不少的好事、难事,立过一次三等功。但他在草沟村人面前,并没有获得多少好感,甚至是不受人待见。他到村里来抓赌,处罚过一些人;他“手肘向外拐”,在调处一起土地权属纠纷案中,判定本村人无理,并扬言若再争吵惹事就送去拘留;他把一位打架斗殴致人重伤后潜逃回家的后生仔当众铐走,最后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后生仔入狱坐牢。
陈家武是秉公执法,父老乡亲不理解,他无奈,也遗憾。他只能寄希望于时间。
陈家武离开三河乡派出所调到县局担任刑侦大队长。他在这个岗位上依然尽职尽责,一干就是8年,破获刑事案件上百件,抓捕犯罪分子两百余人,而且做到了“命案必破”。陈家武离开刑侦队,是因为他受伤致残。在一次黑夜抓捕伤害计划生育工作人员的亡命之徒中,陈家武一马当先,破门入屋,被歹徒挥舞的长刀砍中左手,不得不截肢,造成了终身残疾。陈家武被树立为英雄,受到了县里和市里的表彰。如今,他在县公安局政工科工作,做他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果局里有篮球、气排球活动,他也必定到场观看——但只能是观看了。他这辈子,再也上不了球場。
陈业兴重设灯酒会
2015年,35岁的陈业兴当选草沟村村民小组长。
陈业兴是马骝三的大儿子,也是个机灵精明之人,可惜没能考上大学。他外出打过工,学过装修,还承包过鱼塘养过鱼,但都干不长。马骝三建议他去学养猪。这一招果然有效。陈业兴去参加县里举办的短期养殖培训班,又去父亲老友大垌村李八叔家的养猪场跟班一个多月,回来后就开始养起猪来。他养猪,不是一般的养法,而是严格按照科学要求来养,养猪场不准旁人乱进,进去要经过消毒室,还要换鞋子,猪一天只喂两餐,吃的饲料都是买来的,等等。他养的猪,四五个月就可以出栏了。卖猪也不用麻烦,有客户自动来买,装上车就可以拿到钱或者记上账。这样养的猪确实长得快,但是猪肉吃起来味淡,无家常土猪肉鲜美,村民们都把这种猪叫做“饲料猪”。
“饲料猪”就“饲料猪”吧。有人吃,有销路就行。
陈业兴抓住市场机遇,不断扩大养猪场养殖规模,仅用五六年时间,他的养猪场就由日养数十头猪增加到上千头猪,一跃而成为整个三河乡养猪业界养猪最多、请的工人最多的养猪场,经济效益自是相当可观。陈业兴被戴上了“养猪大王”的桂冠。
陈业兴的养猪业做得风生水起,他干吗去竞选这个村民小组长呢?
他有他的想法。
草沟村不是贫困村,可就是人如散沙,还分帮结派,集体的事情没人管,谁家办个红白喜事都难找人来帮手。这些年来,几个阿叔阿伯轮着当组长,可都是挂个名头而已,不敢管,不愿管,根本就起不到什么作用。
马骝三说,草沟村先前全村上下一家亲,老年人受尊重,哪家哪户有个争吵,村干部一上门就没事了。村里年年还吃灯酒会,要办什么大事,在灯酒会上一宣布就都定下来了。
老爸说的灯酒会,陈业兴没有见过,但听说过,就是在每年农历正月十一这天全村男人们集中到一起吃饭。大家在晒谷场上摆开张张竹笪,竹笪中间摆放各家各户带来的饭菜,新添男丁的人家必须带有公鸡肉,然后老老少少席地而坐,围着竹笪吃喝起来。一望过去,人声鼎沸,和和美美。
陈业兴认为,解决草沟村的一切问题,首要的是解决人心问题,只要把人心重新拢到一起,就什么事情都好办。
陈业兴当选后,就按他的思路去做。
九月初九重阳节,他首献敬老之心,把全村六十岁以上的老人集中起来吃饭。
春节,他请三河乡舞狮队来草沟村表演。
正月十一,草沟村停滞四十多年的灯酒会热烈回归——
在县城一向很少往来的陈家文、陈家武同车回来了,在外面其他地方工作的叔伯兄弟几乎也回来了。全村家家户户杀鸡宰鸭,捧饭端菜,男女老少齐聚到村前新建的灯光篮球场上,不再用席地而坐,而是端坐在高凳之上,围着二三十张大圆桌,亲亲热热地吃起了灯酒会。
噼噼啪啪的鞭炮响过,陈业兴拿起话筒,简要作了开场白,便恭请91岁的十七公代表全村老人讲话,又请陈家文叔代表本村在外工作的所有人讲话,然后,由他郑重宣读新修订的草沟村村规民约、草沟村尊老爱幼行为准则、草沟村关于设立读书助学奖励基金倡议书。
他最后竟高声喊了起来:“草沟村要做文明村,草沟村人团结一家亲!”
责任编辑 练彩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