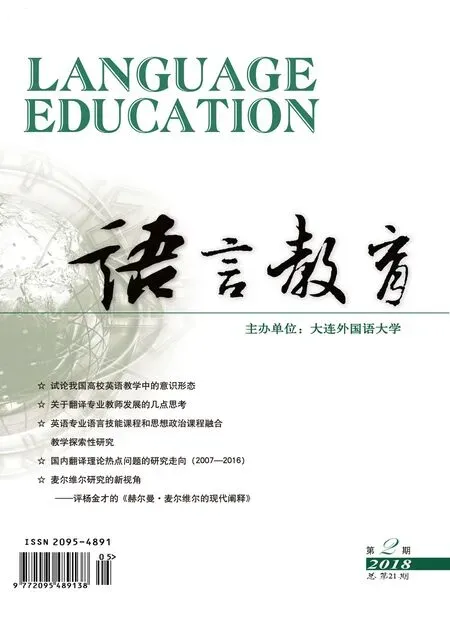向死而生
——《魔山》中汉斯·卡斯托普的死亡变奏曲
赵海燕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
1. 引言
托马斯·曼的《魔山》写于一战前,付梓于战后,以一个看似简单的故事为线索呈现了一部欧洲战前社会精神状况的百科全书。作家用了十二年时间来完成这部作品,这一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托马斯·曼为“德国和欧洲中产阶级发表的一场告别演说”(Stewart,1999)。《魔山》的创作不仅仅是一个文学事件,更是作家清理和提升自身对诸多时代命题认知的过程,这个提升的过程通过汉斯·卡斯托普在被称为“魔山”的疗养山庄的七年成长经历来集中体现。汉斯·卡斯托普不仅仅是作品中的主人公,亦是作家在整部小说中唯一始终使用其全名来称呼的人(汉斯是最典型的具有德国民族特征的名字),某种程度上他是作品中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健全的人的存在,直到故事结尾,他是作品中唯一一位“康复”了的人物。托马斯·曼“让《魔山》的‘主人公’进行的所有精神修养的训练,其目的就在于使他充分理解这种生活本身的和人道主义思想,使他的‘市民思想’扩大为‘世界公民思想’”。(克劳斯·施略特,1992)有着无穷魔力的《魔山》,可以让读者和评论家从诸多不同视角去接近和解读,而笼罩着整部作品,亦即整座“魔山”的重要主题之一就是“死亡”。本文将选取“死亡”这一关键词,描述其在主人公汉斯·卡斯托普思想成长过程中的变奏。
2. 序曲:孩子气的冷漠和就事论事的专注
首先从写作动机来看,托马斯·曼是基于一次对后来成为小说中“山庄”原型的疗养院的探视,以在彼处疗养的妻子的书信描述为写作素材,创作了这部小说。其写作初衷即是换一个视角来延续其两篇旧作《威尼斯之死》和《特利斯坦》中的“死亡”主题。但是在实际写作过程中,作者自身的经历,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导致了写作的中断,使得作者得以进行深刻的反思,由此将一部中篇小说发展成了75万字的两卷本鸿篇巨著,而前述两部小说中被美化的迷醉混乱的死亡主题,在这部作品当中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发展和深化,初始所构思的死亡主题也通过《魔山》主人公的生活经历和反思形成了新的死亡变奏曲。
其次,作品中主人公特殊的成长经历使得他成为最有“资格”去思考和追问“死亡”命题的角色。汉斯·卡斯托普自五岁起在两三年的时间内先后经历了父母和祖父的死亡,这对于一名儿童是十分特殊的经历。事实上我们有理由认为他还没有可能知道如何去对这样的经历做出适当的反应,所以在他的教养允许的范围内,他在灵柩旁的表现就被人看作是一种孩子气的冷漠和就事论事的专注,在第三次他祖父的葬礼上则因为对葬礼的熟悉更添了几分老成世故。
故而卡斯托普在到达“山庄”疗养院之前已经具备了不同于一般青年的对死亡的认知,具体概括起来就是“孩子气的冷漠和就事论事的专注”(托马斯·曼,2006:29)(后文引用作品内容只标注页码)。这些观点一直延续到了他在二十三岁到达山庄疗养院,并在其没有成为魔山的正式成员之前表现较为突出。
第一章第一节“到达”描述道,表哥接卡斯托普从车站到疗养院的途中谈到了山上的疗养院用雪橇运送尸体,这是书中第一次出现关于死亡的话题。卡斯托普在讶异于表哥玩世不恭的语气的同时,他自己的反应却令刚刚开始读这部作品的读者颇感费解,“汉斯·卡斯托普嚷起来,嚷着嚷着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直笑得想忍也忍不住,直笑得胸部剧烈震动,直笑得被夜风吹僵了的面孔也扭曲起来,隐隐作疼。”(10)
另一次面对死亡的大笑发生在卡斯托普第一次正式问及表哥到山上后发生的死亡事件之时。表哥讲到了年轻的天主教小姑娘芭尔芭拉·胡郁丝等将死之人对死亡的恐惧,卡斯托普一方面嘲笑表哥将自己在此事件中背景化的玩世不恭,一方面遏制不住地表现出对于死亡的不尊重行为的愤怒。他对于院方对待将死病人的态度和手段表示出强烈的不满:
“我坚持认为,一个临终者是高贵的,任何一个四处奔波地笑着挣钱填肚子的俗人都比不上他!怎么可以——”他的嗓音变换不定,听上去极为异样,“怎么可以不分青红皂白地对他——”他突然忍俊不禁,大笑起来,话也说不下去了;跟昨天一样,他笑得身子颤抖,没完没了,笑得闭上了眼睛,从眼皮间笑出了眼泪;这是那种从深深的心底涌出来的笑。(55-56)
除这些比较极端和强烈的反应之外,卡斯托普在死亡话题面前有时表现出来的是“孩子气的冷漠”。约阿希姆向他介绍他将要住一阵子的三十四号房间,这个房间之前住的是在他到达前一夜“刚好”死了的一名美国女人,他站在洗脸槽前“漫不经心”地听着这个故事,对于几十个小时之前美国女人的尸体躺过的床铺“几乎瞟也没瞟一眼”。另一次比较明显的是约阿希姆告诉他周围不断有人悄悄地死去并被悄悄地处理掉时,他一边应着表哥的话一边用手杖在地上画着小人儿。
尽管卡斯托普表现出了漫不经心,但是他主动向表哥提出这个话题,包括表示出接近“两个全都”的母亲的愿望,都表明了他对于死亡的态度并不是冷漠,也不是仅仅出于好奇,——从他的童年经历可以得知,他是最不该对死亡产生好奇的。至于他在讨论到尸体和死亡时莫名其妙的大笑,从心理分析的视角来看,那笑到难以抑制,近乎歇斯底里的反应,绝非是出自愉悦,而更出于一种不愿面对,需要逃避的动机。大笑的背后,同样是对于死亡的无法回应的无助。
卡斯托普身上那种就事论事的专注表现在他的最惊悚的论断:“棺材是件非常美的家具,即使空着;而一旦有谁躺在了里面,那它在我眼里就简直变得神圣了”(108)。这一观点来自于他对于死亡尚未能够有足够的能力来应对的孩童时,孩童往往把父母的死亡理解为对自己的遗弃。(Kowalik,1985)对死亡神圣化的描述,于年幼的卡斯托普而言,与其说是宗教的力量和影响,不如说是小男孩自己把对死亡的不理解而导致的恐惧藏在了对宗教的敬畏的背后。
由于在他过早地接触了死亡,汉斯·卡斯托普孩子气的反应背后事实上是一种深深的无助。和他的笑一样,这些表面的冷漠并不是出于他对死亡的敬而远之,反之,这是他因为自己的个人经历而更“愿意”接近死亡,但又没办法去除别人加给他的先前的冷漠的判断,进而没有办法调整自己对死亡的态度,以上一系列因素使得他表现出了怪异的反应。总之,卡斯托普在他还没有充分准备好参与的时候,一脚迈进了死神的领地,开始十分密集地与死亡接触,并被迫去面对、去审视在幼年时期就已经对他施以巨大影响的“死亡”命题。当然,正是此处提及的他的“就事论事的专注”使得他在“山庄”疗养院受到导师(们)的教育和自我研修成为可能。
3. 转调:死亡的舞蹈
虽然身处与世隔绝的“山庄”国际疗养院,汉斯·卡斯托普有机会接触到来自整个欧洲乃至世界各地的形形色色的人物(病人),都在有形无形中对他的死亡观构成影响。在山庄这座精神炼狱中,经历疾病和接触死亡对卡斯托普形成了一种神奇的塑造力量(Brennan,1970)尤其是第一次看见垂死者,第一次在X光机的照射下看见自己的死亡,意识到自己终将会死,汉斯·卡斯托普无法再按照孩童时期形成的模式去注视死亡。频繁地接触“死亡”这一命题,激发了这名青年对“生”的思考。到上卷(第一章至第五章)的最后两节,卡斯托普进一步从思考转向了行动,一个是对死亡的回应,另一个是对爱情的进攻。对死亡的关注似乎注定与爱有关,正如托马斯·曼在《歌德与托尔斯泰》(2013)中所言,托尔斯泰对死亡的拷问与歌德对自然科学天然的爱,两者的根基都是对有机生命的同情。
卡斯托普下定决心参与死亡的舞蹈,更近距离地接触死亡——尽管这个被动的选择里面不无对于爱情的骑士冒险精神之因素。完成“入院宣誓”之后,在考虑到即将来临的冬季时,他还是表现出了忧惧之情。如同大多数文学作品中冬天的意象,在《魔山》中冬天是死亡的象征之一。山上无常的季节变化也正无声地表述出只有死神才是山上真正的主宰。在略有犹疑地加入到死亡舞蹈之中后,汉斯·卡斯托普像个生疏的舞者在舞池中仓皇四顾,而赛特姆布吕尼不失时机地出现,将这名“问题儿童”纳入自己的羽翼之下,义不容辞地开始自己的教育活动:“他一直是泛泛而谈,结论却十分肯定。他是认真的;并非聊天似的随便说说,也不屑于给他的对手以接嘴和反驳的机会,而是在论述终了时压低调门儿,打上一个句号”(142)。在卡斯托普与赛特姆布吕尼第一次关于死亡的对话中,赛特姆布吕尼将死亡看做是一种极端轻浮的邪恶的力量,这种自由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死亡观虽然并没有立刻说服卡斯托普,但是引发他开始去思考并钻研关于人体、关于生命的科学知识,并正式启动了关于生与死的思索。
“死的舞蹈”是上卷中最长的一节,作家在这里把卡斯托普关于死亡的疑问和态度彻底暴露出来。本节的第一句就报告了死亡:马术师死了。但是作家笔锋一转,开始以山庄成员固有的淡漠和闲静从容地叙写圣诞节盛况。究竟是谁对死亡冷漠?卡斯托普自以为是个对死亡有着孩子气般冷漠的青年,所以不同于约阿希姆,他在最开始踏入魔山就表现出一种亲切的归属感。但事实证明,尤其是和周围的疗养客相比,他对死亡的态度却显得过分冷漠。
马术师是魔山上第一个因为疾病引起卡斯托普注意的人,尽管他似乎从未现身,他却是最典型的疾病的代表,他没有出现却又如山上的疾病一样无所不在,马术师的死讯第一次将卡斯托普惊醒,将他从对生死学问的形而上的钻研和探索之中,从对爱情的少年般的欣赏与痴迷之中拉回到现实的存在环境,他开始将视线从书本上移开,开始审视自己所处的环境,他开始行动了。卡斯托普对于死亡的回应首先表现为他开始了对周围病友的慈善关怀。尽管他的动机很复杂,毋庸置疑,他希望用严肃的态度来尊重死亡。
“死的舞蹈”之后就是充满了世俗的欲望的“瓦吉普斯之夜”的描写。该节也是卡斯托普与赛特姆布吕尼师生关系出现裂痕的章节,表面上看这是因为卡斯托普选择了向舒舍夫人表白,向世俗的、肉欲的爱妥协。深层的含义却是师生二人对死亡的态度的分岐,卡斯托普对垂死者的同情遭到了赛特姆布吕尼的嘲弄。在尼采看来同情是无助于疾病的,而赛特姆布吕尼则比尼采更进了一步,同情和疾病一起成为了健康和生命的对立面,干脆被剔除在思考范畴之外。卡斯托普并没有按照赛特姆布吕尼的设想被他塑造成自己想要的样子,而是在赛特姆布吕尼那里学会了理性的思辨,在死亡的舞蹈面前,他通过自己的判断选择了爱情来作为战胜死亡的终极出路。
4. 变奏:为了善与爱的缘故
汉斯·卡斯托普不认同赛特姆布吕尼的死亡观,通过接近死亡来抵消他的导师对他的否定和怀疑,同时企图在爱情中找到征服死亡的终极力量。但是随着爱慕的对象离开“山庄”,他又重新陷入思索的迷宫无法找到出口时,在第六章“又来了一个人”一节,作家引入了列奥·纳夫塔作为赛特姆布吕尼的对立面,让卡斯托普通过倾听来自两个对立思想体系的无休止的辩论与争斗,以第三者的视角来审视“死亡”命题。
纳夫塔的原型据说乃是格奥格·卢卡契(克劳斯·施略特,1992),书中介绍他是犹太教屠夫的儿子,从小直视残忍的屠宰和鲜血的喷涌,使他总是将对宗教的虔诚与一些残忍而极端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如果说人文主义者赛特姆布吕尼是“生命”的象征,那么纳夫塔恰是“死亡”的代表。虽然二人之间思想上的缠斗在作家的表述下多多少少总是带有一丝滑稽的色彩,这并不损害他们所代表的欧洲两大互相冲突的思想体系之间的斗争的严肃性。雅斯贝斯在《时代的精神状况》对那个时代写下了一纸诊断:“事实上,自从法国革命以来,关于当代的时代意义的一种特别新的意识已经盛行。但是,到了19世纪,这种意识分化为两支:一支是相信一个辉煌的未来正在到来;另一支是对一种不可能从中解救出来的深渊的恐怖”(卡尔·雅斯贝斯,1997)。故事接近尾声,象征“中世纪”的纳夫塔在作品最后章节选择自杀这一行为更加深了这场不同思想体系之间的斗争的本质的严肃性及危害性。
两人对卡斯托普心灵和精神的争夺,使其备受折磨。最终,卡斯托普开始冷静下来,跳出这二维思辨形式去独立寻找新的出口。在第六章的“雪”这一节中,作者用相当的篇幅描写了一个十几分钟的梦境,该节堪称现代文学中最著名的场景之一。汉斯·卡斯托普独自深入山中不断前行,无法自我控制地接近死亡的临界线。在这非常时刻,通过梦境中的思辨拷问以及自己醒来后对梦的解析,卡斯托普彻底分辨出两位“导师”对于时代意义的根本认识的区别所在,从而脱离了二者的影响,自然/肉体与精神最终实现了互相统一,并且“也同样通过‘人道主义’这个更高层次的范畴得到了扬弃”(克劳斯·施略特,1992)。卡斯托普此刻“到达”了关键性的结论:
我愿做个善良的人,我不容许死亡统治我的思想!……爱是死的对头,只有爱,而非理性,能战胜死。……为了善和爱的缘故,人不应让死主宰和支配自己的思想。到这儿我该醒了,因为我的梦己做完,已到达目的地。(490)
象征理性和生命的人文主义者塞特姆布吕尼最终占了上风,尽管我们很难预见在现实世界中他是否真正有能力打败代表死亡的极端力量。作家适时地控制住小说的节奏,在卡斯托普醍醐灌顶般的顿悟之后,安排了表哥约阿希姆的死亡。约阿希姆之死为汉斯·卡斯托普的死亡观提供了一个实证,并为关于“生与死”的思考画上了句号。我们应该注意到,死亡在此后还是在发生,一直在发生,但是在约阿希姆死之后,作品中不再对死亡发表长篇累牍的评论,尤其是曾经在作品中以强大的思辨能力,口若悬河的雄辩来对抗塞特姆布吕尼的耶稣会教士纳夫塔,全书中关于死亡的篇幅最短的描述就是他在决斗中自杀的场景。 随着他帮助汉斯·卡斯托普找到答案的使命完成,纳夫塔所代表的思想体系的命运业已注定,作家和主人公都自此对他不置片语。
5. 尾声:解除魔法
第七章(最后一章)照例描写了一系列的死亡事件,其中包括纳夫塔死于决斗的离奇之死。塞塔姆布里尼曾评价纳夫塔,认为他“形式是逻辑,本质是混乱”。这一点精准地指出了纳夫塔的本质问题。黄燎宇也(1991)指出:“托马斯·曼通过这一艺术形象准确地概括了法西斯主义的两个精神根源、表现形式以及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这就是前述的极端浪漫主义和极端理性主义。”从伟大到滑稽只一步之遥,极端分子纳夫塔义无返顾地走出了这一步,而他恐怕没有料到,一如他所代表的思想体系那样虽作垂死挣扎但最终不能摆脱没落的结局,他的死成为整部作品中关于死亡的最诙谐滑稽的描述。
本章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男孩特迪的死亡。在《魔山》当中,卡斯托普是唯一一个动态的、在思想上实现成长的人物,而其他人物从思想认识的角度来看都是相对静止没有成长变化,甚或是直接指向死亡的。特迪是“魔山”上除了卡斯托普之外唯一写出其成长的人,但是因为没有精神上的成长,这名肉体生命成熟的青年同样无法摆脱“魔山”的控制者——死亡。与此相对应,卡斯托普的思想成长已超越了“山庄”带给他的禁锢和死亡给他的困惑,“魔山”的“魔法”对他已然失效。
本章在一开始便暗示出来卡斯托普在找到了问题答案之后的重大转变——还乡之情的滋生。卡斯托普开始听世界各地的音乐,他最钟爱的唱片《菩提树》是五张唱片中唯一的德国音乐和德国歌词的乐曲。“菩提树”(der Lindenbaum)即椴树,对德国人来说椴树通常意味着温馨安宁的生活、关于故乡的记忆。对这首《菩提树》的喜爱,同时也包含着一种内含于德国精神气质自身的东西,托马斯·曼在《一个不问政治者的看法》中指出,“如果浮士德是德意志心灵的代表,他就必须是音乐家;德国人的世界观抽象而神秘,有音乐家气质。”(黄燎宇,1996)叔本华(1982)认为,音乐能让“意志无阻碍地显现出来,以便它在这显现出来的现象中能够认识它自己的本质”。对《菩提树》的钟爱暗示出了卡斯托普潜意识中的返乡情结,尽管这一点可能是连他本人也没有意识到的。
当卡斯托普决定要返乡,要离开魔山,那就必须清算他留在魔山的初衷——舒舍夫人,或者说爱情。佩佩尔科恩和舒舍夫人返回山庄是本章用笔最多之处,可谓是对卡斯托普的爱情经历作一次总结,就像“好样的士兵”一节是对全书中死亡的舞蹈进行了一个小结。再者,佩佩尔科恩作为魔山生活中的最后一位导师,当卡斯托普找到了“生与死”这一大问题答案之后,他的出现帮助卡斯托普进一步去追问精神与肉体,爱与生命等问题的答案。最终,他用自己行动——自杀——来帮助卡斯托普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此外,在本章第一节“海滨漫步”中便反复出现了与山上相对的海滨意象,包括海风、船以及被卡斯托普冷落了许久不肯面对的那本杂志《远洋船舶》,都是山下生活的象征符号。卡斯托普对海滨漫步的追忆和向往,已经不仅仅是在回忆的层面上,更体现了他对未来的规划。
最后要说明的是,为什么卡斯托普不在选择了“生命”,选择了善与爱,选择了赛特姆布吕尼,动了还乡之念的时候马上返回平原地区?这里我们需要弄清楚,卡斯托普的还乡是指解除魔法,离开魔山,但并不是回到上山之前的生活中去。在他七年的沉思、追问与成长的过程之中,卡斯托普的家园早已不是迪纳贝尔舅公和雅默斯舅舅所代表的那个旧式生活方式和生活轨迹。所以他在表哥死后留在山上并不仅仅是惯性使然,而是在思考自己的真正家园之所在。
战争的爆发给汉斯·卡斯托普提供了离开魔山的最佳理由,那就是因为战争破坏了传统的家园,他将在这废墟中寻找自己的真正的家园。由此,在一战的隆隆炮声中,“那位躺在草丛里不知不觉打了七年瞌睡的傻瓜慢慢醒了,坐起来开始揉眼睛……他发现自己已经解除魔法,得到了拯救,得到了解脱……”(709)这一场景正如但丁在《神曲》开篇处的几句诗所描述:“就在我们人生旅程的中途,/我在一座昏暗的森林之中醒悟过来,/因为我在里面迷失了正确的道路。”《魔山》也恰是汉斯·卡斯托普的一次精神游历的记录。
当然,读者可以看到,尽管《魔山》的死亡主题比作家先前同类主题的作品在认识上有所升华,但是在最后的结局安排上,受叔本华及其宣扬的悲观主义和批判理性的思想影响,作家还是感到了对世纪之交人类命运的迷惘和无助。在作品之中,汉斯·卡斯托普最终决定离开这座死神统治的魔山返回到现实生活,他带着七年的思考和成长,带着精神上的充沛生命力回到山下世界,等待他的却是不可逆转的时代的大混乱和动荡。在战争的隆隆炮声中,整个世界变成了一座魔山,整个世界都在跳死亡的舞蹈。汉斯·卡斯托普在炮火隆隆声中从陪他一起成长的读者视线之中消失,带着托马斯·曼对整个时代以及身处其中的人们命运的淡淡的哀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