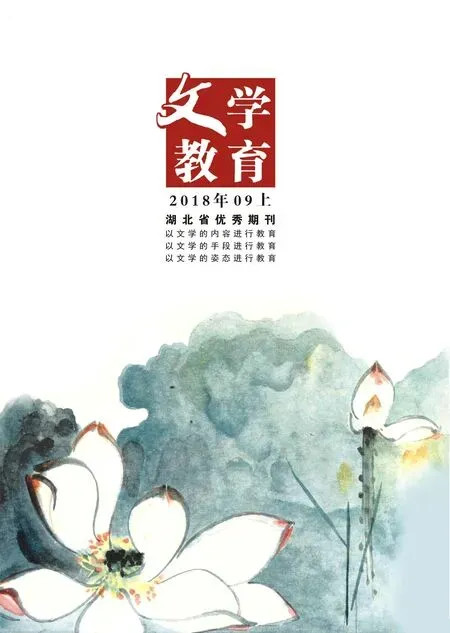《叶甫盖尼·奥涅金》的自恋情结探析
张 旭 韦冬余
弗洛伊德认为自恋是一个普遍现象,在其理论体系中他依据“力比多的投注转”移详细阐释了镜像化自我投射到外界而引发的自恋情结。荣格曾指出:“艺术家无一例外地都是自恋倾向者。”[1]在文学世界中,作家通过文学作品隐秘或明显地传达自我的意识也是极为普遍的,可见自恋情结对文学的创作思想和实践都具有深沉影响。长篇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是19世纪著名的俄国作家普希金的代表作,作品的主人公叶甫盖尼·奥涅金是文学史上第一个“多余人”形象。在奥涅金身上可以看出与普希金相似的精神状态。作者在表现主人公“多余性”时采用了浪漫的诗体和现实的叙事结构相结合的手法,独创了“奥涅金诗节”。作者期待通过客观描写和主观叙事的方式将俄国“时代抑郁症”的本质揭露出来,事实上普希金借助自己高超的文学艺术手法确实实现了这个目的,然而诗体的叙事手法也使作品中作者的声音牢牢占据着主导地位,作品体现作者的自我的主体意识增强。而在体裁方面凸显普希金的自我主体意识的同时,作品的人物性格也处处彰显着以自我为中心的高傲以及沉湎于自我世界的不可自拔。本文希望通过对作者普希金和作品体裁、人物的分析,将《叶甫盖尼·奥涅金》中隐藏的自恋情结展现给读者。
一.“奥涅金诗节”的典范意义
长篇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是19世纪著名的俄国作家普希金的代表作,和果戈理的做法类似,普希金在出版时将他的长篇叙事诗定义为小说,而后者则是将自己的小说定义为了“长诗”。诗体小说是小说,也是诗。其外在特征通过诗歌的格律表现出来。吸收了拜伦十四行诗精髓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在诗体格律上是别具一格的,它根据十四行诗在不同国家,不同作家笔下的变化与发展,融入俄语音节和俄罗斯民族语言后而独创的,因此也被叫做“奥涅金诗节”。然而,这部小说的伟大意义还不止于此,其更广泛的意义还在于对患了时代抑郁症的“多余人”的奥涅金的形象塑造。这是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多余人形象。雪莱曾说过:“凡是他人独创性的语言风格或诗歌手法,我一概避免攀仿,因为我认为,我自己的作品纵使一文不值,毕竟是我自己的作品。”[2]作家如果要真正成为杰出的大师,就必须尽一切可能推翻、改造前人创造的写作法则,与此同时,拓宽文学领域为后人提供新的创作对象,这是所有有创造性作家的共识。杨格也说:“愈和他们相异,愈能和他们达到同等的优越成就。”[3]可见张扬自我创造是主体意识的一大表现。如果普希金从未借鉴拜伦的诗体叙事的独到方式并在后来改造加入俄国本土元素的话,那《叶甫盖尼·奥涅金》的锐意便会削去三分;同样,假若作者从未将目光投向时代背景下的贵族“多余人”现象,那么文学史上便会少一个典范的体式、一个典型的人物原型、一个伟大的文学创作者,普希金也只能是一个庸庸碌碌的贵族子弟而非一个优秀的作家。“自恋”往往带来不可思议的创造,“奥涅金诗节”的典范意义不仅仅在于文学体式的创造与更新,更向我们印证了作家“自恋”的重要意义。
二.第一人称“我”叙述视角
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普希金将叙事与抒情融为一体,在推动故事情节向前的同时,借助第一人称“我”的叙述,将奥涅金的内心世界呈现在读者面前,进而引发读者的思考。当然,值得思考的是作为叙事文学中常见的叙事者的“我”往往只是个个旁观者的角色,即“我”的叙述话语重在阐释而非引导作品的内容和思想的走向。而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则不一样,叙述者“我”是作者的朋友,代表了作者的立场。在作品中,“我”毫无忌讳的把普希金的立场和观点表现出来,表现作者的喜怒哀乐。同时,作者也借“我”之口向读者介绍故事的背景、情节的发展动态。这不仅是出于叙事的要求,还是借以实现传达人物内心活动、暗示故事情节走向的重要凭借。这种处理方式不仅让故事显得真实,也能让读者触碰到作者内心深处。作为一部叙事抒情小说,“我”的作用还不仅仅于此。一方面,作者在小说中借助“我”之口,选用的简练、平白的叙述话语,这在完整作品故事情节,消解诗歌的语言的尖酸生涩上皆有巨大效用;另一方面,作者利用“我”在作品中直接抒情,这些抒情的语言使作品带有了诗的韵味。正是由于这些个人抒情插笔,使得作品形成一种独特的“诗体小说”的格式。作品中抒情部分,真实地反映了作者的内心,表达了作者的生活态度,寄寓了他的人生理想,使作品在客观叙述的同时也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如在第一章中对上流社会的糜烂生活的批判:“唉,由于灯红酒绿的欢娱,我已经把多少生命浪费!”再如第六章中对连斯基死去的感叹,第七章对奥尔加移情别恋的批判等等,以上章节中的抒情的语句无不体现出作者个人的主观意志和情感。可以说,通过叙事抒情小说中“我”的介入,其浓烈的个人情感成功地让读者了解了作者的所思所想,也让故事发展得更为流畅。作品中的“我”成了无形的上帝,“我”对人物的品评也就成了人物定性的唯一标准,在“我”的笼罩之下,作者的个人情感和个人意志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但这也不可避免地给作品打上了深深的“普希金式”的烙印,这也是作家个人“自恋情结”的一种体现。
三.现实与虚幻交织人物塑造
按照古腊神活中关于原始人的传说,人在出生后就被劈为两半,从此他们就不停地寻求着自己的另一半,找到之后两者就紧紧抱在一起.不吃不喝,直至死去。奥涅金是普希金笔下的经典人物形象,其身上展现的时代的多余性的现实来源正是十九世纪一批和普希金相似的俄国思想先进的贵族群体。如果按照古希腊神话的解释,那么普希金是通过文学形象——奥涅金的构建,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并且两者达到高度统一。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奥涅金是一个生活放荡不羁的上流社会的没落贵族,是一个经常出入上流社会的宴会、舞会,深得上层女子的喜爱的形象。现实中的普希金与作品中的奥涅金生长轨迹出奇的一致:出生于沙皇俄国的没落贵族家庭,在贵族化的生活中养成奢靡的生活作风。由于普希金受到了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身上也逐渐聚积起了主观战斗激情;作品中的奥涅金也是一样,启蒙思想的冲击和多年的游历让他的思想也逐渐开阔起来,但是同样,由于脱离实际而陷入了空想,他们身上又都蒙上了一层时代多余性。所以也可以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事实上是普希金自我人生的文学投射。普希金将自我经历作为创作对象,通过作品中作家自我意识的展现,读者也能体会出隐藏在文学创作中的作家的自恋情结。当然,通过主人公展现自己的生活轨迹不是普希金的独创,同样这种创作手法附带的作家的特有的情感,《叶甫盖尼·奥涅金》也非首例。
奥涅金是作品的主人公,在他身上我们也能一窥自恋情结。在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自恋是由于儿时缺失母爱关怀导致力比多投注错位而产生的。在奥涅金身上也可以得到佐证。他早年丧母,以后在管教不严的阿贝先生的陪伴下成长,渐渐的“他便在社交界抛头露面”“他会轻盈地跳玛祖卡舞,鞠躬的姿势也颇为潇洒,还缺什么呢,大家异口同声,说他非常可爱而且聪明”[4],虽然奥涅金的贵族公子的恶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时代环境,但是我们也因看到奥涅金之后养成的勾引女性的习惯和他自身对女性的依赖是密不可分的,而这也就追溯到幼儿时期母爱的缺失。奥涅金还对服饰和自己的容貌分外在意,“这位讲究衣装的模范子弟,在那穿了又脱,脱了又穿。伦敦擅长做服装和脂粉生意……这一切现在却被用来装点,这位十八岁的哲学家的空间”,“他至少要用掉三个时辰,来照那些大大小小的镜子”[5]。西蒙·波伏娃夫人在《第二性》中认为:服饰、聊天和镜子是自恋者塑造内心理想自我的三条途径。在她看来影象对自恋者来说就是认同自我,因为自恋者转入内倾必定有着某些现实原因,而就算不太幸运的人有时也能从镜子中找寻到快乐。至于服饰,在她看来,有野心的自恋者希望他的表达方式与众不同而且变化无穷,外在的光鲜亮丽总能引起人们的关注甚至是喝彩。[6]如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奥涅金为何如此关注自己的服饰和容貌了,自身有着自恋情结的奥涅金在服饰、镜子、谈情的自我消解中逐渐患上时代抑郁症。
总之,自恋情结作为一种大众普遍的心理现象,它在文学创作上表现出特有的创造力,它是文学创新的源泉。因为作家只有关注自我,创作上关注内心世界,才能突破固有的模式,在文学天地中有所作为。《叶甫盖尼·奥涅金》是这方面的典范之作,普希金融汇其中的自恋激发出来巨大生命力,这将使它散发出永恒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