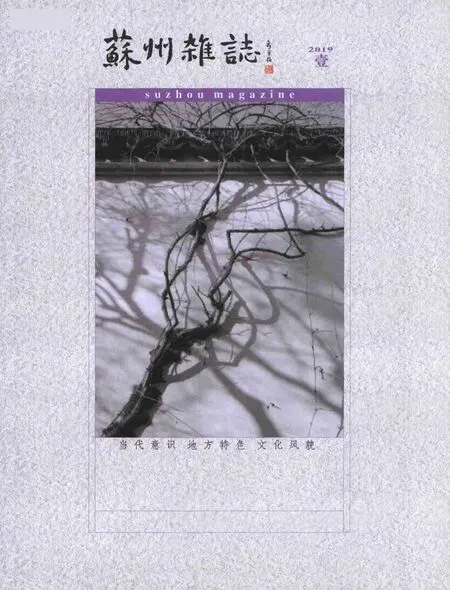史铁 生扶轮问路
范小天
一
1983年秋,我和铁生第一次见面。只是我那时没想到,此后的很多年里,我竟会如此地想念他。
认识铁生,是因为《芒种》的编辑洪钧,我的第一篇拿稿费的小说就是他发表的,那时候,我还是个北师大的学生。洪钧把一大批北京作家介绍给我认识,除了铁生,还有刘树生、刘树华、刘孝存、陈放、晓剑、李剑……因为铁生腿不方便,大家常常在他家聚会。铁生家住在地坛附近,就像他在《我与地坛》中所说:“自从我的祖母年轻时带着我父亲来到北京,就一直住在离它不远的地方——五十多年间搬过几次家,可搬来搬去总是在它周围,而且是越搬离它越近了。我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四百多年。它等待我出生,然后又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四百多年里,它一面剥蚀了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坍圮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砌雕栏,祭坛四周的老柏树愈见苍幽,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得自在坦荡。这时候想必我是该来了。十五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它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那时,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大,也越红。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身影。”
看到铁生的文字,仿佛又回到了他的身边。他微笑着,静静地看着我们在思想碰撞,在生活烟火中喧哗与躁动。前几天在微信上又一次看到这么一段话:“人活着要有底线,你至少得知道:什么是黑,什么是白;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铁生亲和、温暖、崇高,是我仰望的方向。1983年,我到《钟山》编辑部工作的时候,铁生已经是全国获奖作家,他的作品《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获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二
从《现代小说技巧》《西方现代派小说研究》开始,西方各种流派的小说陆续翻译过来了,中国小说迎来了发展的春天。李陀建议《钟山》组织一批作家,写一批探索性的小说。参加这个活动的有林斤澜、史铁生、李陀、陈建功、理由、戴晴、韩少功、何立伟等十七位作家,这便是后来的“十七人协议”。最后一次讨论会也是在铁生家,有一位第一次参加会议的著名作家突然向我发难:“什么是先锋?什么是新潮?什么是探索?”当时我尝试着想回答,却回答不了,记得好多作家帮我打了圆场,包括平和的铁生。现在我已经知道了,这种名词概念,一万本书也写不出个绝对真理。
李陀建议《钟山》组织“十七人协议”的签约作家,办一个笔会。我回编辑部后,吴秀坤告诉我,南海舰队正在和他联系办笔会的事。于是,就有了《钟山》组织的第一次“海南岛笔会”。李陀说:“一定要和铁生一起去。”大家也许都记得,那时候,《钟山》有个年轻的编辑叫苏童,铁生的海南岛之行,不能用轮椅的时候,在部分时间都是苏童背着他的。其实,我也背了N次,也许是因为我“嘴巴老”,没人记得我背了。哈哈。很多年以后,韩少功对我说过,他后来定居海南,其中很大的原因,是那次“海南岛笔会”。
1987年的海南,还是比较原生态的,海口就是一个小渔镇。到海南的第一天,我们入住清澜的军营。当天晚上,以苏童为主力,我们轮流背着铁生去找海滩,走了很远很远,到处都是布满海蛎子碎片的滩涂,很多人的脚都被割破了,没有人感觉到疼,大家吹着海风,开怀大笑。回来的路上,路过一座石桥,大家坐在栏杆上休息,也许是意犹未尽吧,我建议大家玩“成语接龙”,输了的,就手里拿一个竹竿,单脚站在桥中间。大名鼎鼎的、德高望重的文坛前辈,平时摆摆的、文章咄咄逼人的后起之秀,每个人都会输,在大家的哄笑中,遭受“捉弄”与“惩罚”。铁生输了,大家一片放过声,他不,他把轮椅摇到桥中间,手里举起那根破竹竿接受“惩罚”。何立伟说:“像一尊佛的剪影。”
三
铁生的小说越写越好,约稿的人络绎不绝,严重影响了他的写作与生活。万般无奈,他在门上贴了一个小通知,希望大家在每周的某几天来。我忘性大,常常是走到门前才想起来。有那么一两次,我厚着脸皮敲门,铁生的爸爸开门,从来没有一丝嫌意,铁生总是温和地笑着,他知道我是为了他的作品而来。我对铁生说:“你写你的。”我就坐在铁生对面,看着他写。铁生用钢笔写作,只要有一个字写错了,他便会撕掉重新写,即使那一页已经写到最后一行了。我开始不理解,铁生对着我笑,也不解释。很久以后我明白了,铁生其实是在推敲。他撕掉重写的过程就是推敲的过程,他对自己有着非常高的要求,我也由此明白了为什么铁生的作品那么好,大家都喜欢。
我不仅仅是为了索要铁生的作品,还和他聊文学,聊其他方面的书。有一阵子,我们都在看铃木大拙的《禅与心理分析》。铁生说,他想写3篇小说给我,它们是:《原罪》《宿命》《顿悟》。我的心震颤了,我知道他是想用3篇小说表达他对生命的看法,他从哪里来,他经历了什么,他不知道为什么会经历这些,他又将向何处去。我知道他决定把这3篇小说给我,是原谅我“违约”,是欣赏我对《钟山》的热爱,是对我的情义,情重如山。当然,更重要的是对《钟山》的信任。
《原罪》和《宿命》以中篇的形式发表在《钟山》。《原罪》写高位截瘫患者“十叔”每天只能通过7面镜子看到窗外的世界,可他却喜欢给孩子们讲故事,命运困住了他的身体,却挡不住他对生命的思索;《宿命》讲一位中学教师“莫非”在打算出国的路上出车祸导致瘫痪,从此命运改变成了一名作家的故事。铁生对他出车祸的那一秒之前的无数可能性进行思考,命运没有早一秒也没有晚一秒,结果似乎在冥冥之中已被注定。铁生的这两个短篇其实表达的是相同的主题,那就是如何面对命运的不可逆转。
我请我的好朋友——《人民文学》编辑部主任朱伟写了评论。朱伟喜欢《宿命》,我比较喜欢《原罪》,大家有自己的想法,喜欢的不同,不存在高下,只是艺术感悟的不同。中华民族“比”的传统有不好的一面。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审美趣味,都可以有独立判断。朱伟后来由于某种原因,离开了他热爱的《人民文学》。朱伟后来先后做了《东方纪事》、《爱乐》和《生活》的主编。听说北大、清华的学生,曾经把朱伟主编的《生活》评为中国最受欢迎的刊物,真为他高兴。几年前我有事到北京,突然想他,特别想他,给他电话,约好了见面,没想到,当天,我的胫骨骨折。
我也由于种种原因,不得不离开了我无比热爱的《钟山》。铁生没有再写《顿悟》。余华曾说他给《钟山》写稿的激情是冲着范小天的。我不知道铁生是因为说好了《顿悟》由我担任责编,还是他在顿悟的旅途中艰难前行,迟迟不能定稿。
四
铃木大拙《禅与心理分析》中引用了17世纪日本一位伟大的诗人芭蕉的诗:
当我细细看
啊,一朵荠花
开在篱墙边!
铃木大拙用这首诗阐述了他的禅意观:“当你看它的时候,它是多么温柔,充满了多么圣洁的荣华,要比所罗门的荣华更为灿烂!正是它的谦卑、它的含蓄的美,唤起了人们真诚的赞叹。这位诗人在每一片花瓣上都见到生命或存在的最深神秘。” 那时候我怎么也理解不了,就像我30多岁的时候,怎么也不明白“难得糊涂”和“吃亏是福”。
在我的心里,铁生应该早就顿悟了,也许他出生的时候,就具有了佛心与佛性。他在《我与地坛》中说:“此岸永远是残缺的,否则彼岸就要坍塌。”经受了那么多苦难,经受着那么多苦难,还将经受无穷无尽的苦难,他却还是那么平和。铁生的顿悟是高于铃木大拙的,他在我心里,是一尊佛。科学是有限的,科学达不到的地方,唯有信仰去支撑。铁生早就领悟到了,所以他才会说“生命就像琴弦,拉紧了才能弹好,弹好了就够了”。一个心中有信仰的人,是无论如何都不会被命运打败的。铁生离开我们了,他沿着漫漫无边的顿悟之路,向着天堂前行。
铁生离开我们很久了,和他相处的点点滴滴以及他对生命的摸索、感悟和征战,依然会让我在某个思绪的罅隙想起他来,时间不露痕迹地带走了很多,却把铁生永远留在了我的心灵深处。
我现在终于慢慢领悟到了铁生的顿悟。人所不能者,皆是限制,是残疾。铁生若不是早早领悟到这一点,又怎会活得如此通透彻悟呢?
人们常说,若一个人频繁想起以前的日子,那他也就老了。我到50多岁,才慢慢明白什么是铃木大拙所说的顿悟:“好美的一朵花啊”,顿悟是能感受到万物的美。我常常说,一个人,从事妓女行业到70岁,她的内心都可以是纯洁的。记得很多年前,有个熟人发给我一张照片:西方的圣诞节,一对臀部上有了皱纹的老夫妻,和年轻人一起,裸体下海游泳。这位熟人知道,在我心里,哪怕身上都是皱纹、赘肉,也可以是美的。
李陀曾经建议《钟山》帮铁生换一个方便一些的轮椅,由于某种原因,这件事没有成功,成了我心里的永久的遗憾。前些日子,我在好朋友阿海的画室里看到了这幅画:
你看这个和尚多快乐啊。
铁生一定也是这么快乐着。
似乎,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能理解的美的层次更多了。
此时,此刻,我真想,再一次去铁生的房间,坐在他对面,看着他写稿,和他聊一聊我们心中向往的顿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