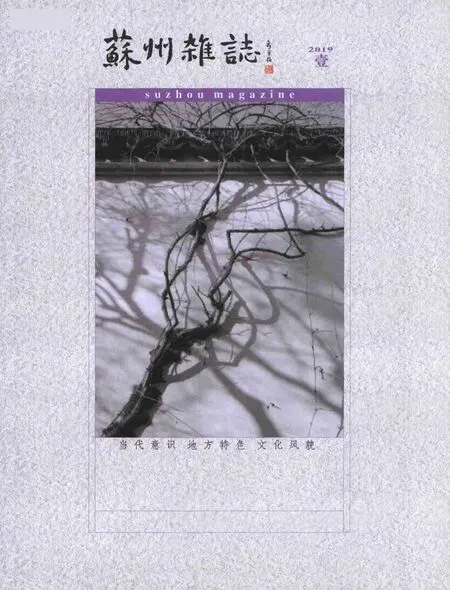惜别小沧浪
周湧
结草庵前石塔重,孤亭耸峙似高峰。
诗人夜向沧浪宿,听尽南禅百八钟。
三百前的诗人尤侗这首写“沧浪”的竹枝词里的意境,与我夜宿“小沧浪”庭院里的感觉竟有些差不多。
“文革”前,一〇〇医院南面“结草庵”中的两座石塔还立在放生池的东西两个小岛中央,直到1966年以后石塔才逐步被毁。而词中所说的“孤亭”想必就是沧浪亭,三百年前它就“似高峰”了,想来当年尤侗看到的“孤亭”应该是沧浪亭才从沧浪池边移建(1695年)到沧浪亭的土丘上不久的景象。再有那南禅寺的钟声,它早在1956年以前就应该消失了,不过,夜晚取代寺庙钟声的声音也是有的,那就是不远处京杭大运河内河上传来的汽笛声了。
幽深的“小沧浪”院落是我童年美好的记忆,可是,1972年的8月,恐怕是我住在“小沧浪”院落里的最后一月了。那一月的每一天对于将要惜别这个院落的我们一家来说似乎每一人一景,一件一物,一草一木都能勾起许多美好的回忆,所以我们特别依恋它。
“小沧浪”院落原本属于沧浪亭范围之内的一个小园子,这个园子东南面有一土丘,丘上有太湖石叠起的假山,假山上有一棵古香椿头树和一棵古糙叶树,另外依稀种了一些竹子、芭蕉等植物。这个“假山小丘”虽与沧浪亭有围墙隔离,但是它离沧浪亭内的“假山大丘”也不过几十步之遥,不知南宋绍兴初年沧浪亭园主韩世忠在两山之间所架设的“飞虹”之桥是否搭在这个小假山之上?可惜这位清凉居士已涅槃了几百年,我们无从知晓当年之盛景。几世烟云过后,“小沧浪”一景之词终于在沧浪亭里的《七友图记》石碑上出现了。不过,时光已经流转到了清道光七年(1827)之后了。据《沧浪亭志》(文汇出版社2016年版)记载,道光七年江苏巡抚陶澍和江苏布政使梁章钜联手重修沧浪亭,并于次年在沧浪亭南空地上增建“五百名贤祠”。那一次的修复,陶、梁两官员在三面环水的沧浪亭西北角“恢复旧观”,“恢复”了“小沧浪”一景。这个“小沧浪”庭院相对独立于沧浪亭主建筑之外,据清代学者朱珔的《七友图记》记载:“吴门节署有园池曰小沧浪”。也就是说,“恢复”的“小沧浪”一景有当作“官衙花园”的功能。再说,次年新建的“五百名贤祠”似如“苏州名人馆”,也有“公共花园”的含义在内。所以有人说沧浪亭是苏州清代以来第一个公园,这依据似乎就在于园中有“五百名贤祠”,从那时起沧浪亭的功能已经从“寺庙”或“私家花园”转换到了“名人馆”。不过,更多的人认为道光时期的沧浪亭是用作“江苏省政府接待处”花园的。这政府“接待处”想来一般百姓还是难以入内的,特别是这相对封闭的“小沧浪”更是难以光顾,只有像陶澍、梁章钜等达官才能在闲暇之日,在假山竹林映照下的庭院之中,邀当地名流,设几架琴,品茶吟诗,尽显风流。
我能入住清代巡抚大人听琴会友的“小沧浪”花园自然是沾了从军父母的光。解放初期苏州市临时实行军管,那时原“吴县公医院”被收归为“苏南军区医院”所有。当年“苏南行署”(省级)在无锡薛福成的“钦使第”里办公,清末薛钦使(驻外国大使)的一百余间豪宅全部收归人民政府所用。而“苏南行署”旗下的“苏南军区”也需要一所医院救助伤病员。“吴县公医院”当初是苏南比较好的一所公立医院,所以被“苏南军区”相中。沧浪亭可能是由于属于前清政府花园的原因,所以民国元年以来经常被军队占用。最初民国二年驻苏第二师第四旅旅长苏谦占据沧浪亭作为他的旅部,抗战时期沧浪亭又被日本军队占用,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占用沧浪亭的一部分用作“伤兵医院”。解放后沧浪亭继续沿袭“驻军传统”,曾用作“华东军区军政大学”二、三团的校舍,而“苏南军区医院”则占据原“伤兵医院”那一块地盘,用于扩建病区和增设家属区。
我家入住原属于沧浪亭的“小沧浪”院落时已经是在1960年了,那时这庭院里的轩廊上方还存有一方金砖刻成的“小沧浪”题匾,而且院子里已经住了好几户医院的老医护工作人员了,他们算是在此地居住了近十年的老居民了。后来,我悉知的“小沧浪”里的故事,都是那些老邻居在夏日微风习习的夜晚,在那支起小桌的庭院里纳凉时,慢慢说给我们这些孩子听的。
“小沧浪”里的故事很多,几夜也说不完,可是我家因新添女孩一人,沿河两间小小的平屋再也容不下不断长大的我们这三个孩子了。我家必须换大一些的房子,父母早已把换房的报告打给了院务处,我们剩下的只是等待。
离别前的等待很漫长。那一年的夏天也是特别漫长。夏夜,我们这个小院和往常一样,每天吊井水冲天井,然后各家支起床铺,捆起蚊帐竹竿,搬好小竹椅,准备讲故事纳凉。而这两年我家的变化是先要把一只摇篮搬出来,然后把它放在家门口最通风凉快的地方,之后才围着这只小摇篮架起两张床,这样能显得我们全家对“千金宝贝”的特别照顾。纳凉讲故事已经是我们这个院子里传统,原先我就爱听隔壁的顾伯伯讲那些真实的战斗故事给我们听。有一次他讲了一个《董存瑞与“木棍子弹袋”战友》的故事很有趣。说是:东北野战军里一个排长老是欺负董存瑞这个新兵,发子弹时只给他发十发子弹,而别的战友子弹袋都是发的满满的,董存瑞很是不满,有一天终于向排长“开火”,说他欺负“新兵蛋子”,偏向“老兵油子”。这个排长不急于回答他,而是等部队集合后让董存瑞自己去看老兵们的子弹袋。起先董存瑞有些犹豫,接着他连续查看了两个老兵的子弹袋,原来这些老兵子弹袋里都塞满了短木棍,这一下使得董存瑞脸红不已。这些参加过战斗的大人所讲的故事有他们的影子在里面,听来十分上脑子,记得住。院子里的其他大哥大姐们可能是故事听多了,他们长大后也会自己讲故事了。那些年孩子们避开院子里的大人偷偷讲的故事是《一双绣花鞋》《绿色尸体》什么的最流行的“恐怖故事”。这些故事当年爱听的人很多,一些不在我们这个院子里住的小伙伴也每晚赶来听“一回”,有人听了“恐怖故事”后吓得晚上不敢回家,非要让我们院落里大胆的人送他回家。那送他回家的人第二天常常笑他,说他手里拿了两块砖头,直到我送到他家家门口时才把二块砖头扔在他家门口的地上,哈哈,真是个胆小鬼!我因为年岁小,大孩子们讲这些“恐怖”或“黄色”的故事时常把我给支开,让我到一边去“乘凉”。不得已,我只能挤到大人堆里听他们说“正经事”。1972年的夏天,小院里大人们说的最多的就是“长沙马王堆”女尸的事情,这长沙马王堆的发掘当年轰动了中国,我母亲是长沙人,她也时刻关心着她家乡的“重大考古发现”。大概是因为母亲的兴趣,我也不由关心起“考古”这事。当时我们“小沧浪”周边古迹众多,那些年最容易在家门口捡到的就是砖雕“老爷头”,乱草丛里随处可捡。可是,如今要离开“小沧浪”院落了,想多捡几个“老爷头”却怎么也找不到了。不过,我还是不死心的,还是想沿着这个熟悉的院子到处转一转,看一看是否拾到可以“炫耀”的宝贝。
“小沧浪”庭院周边的宝贝在“文革”前确实可以找到一些,可是“文革”开始后“造反派”们恨不得连每一块地板都撬起来查一查,看一看有无“四旧”或“变天账”之类的藏在地板下面。后来,1969年医院在“小沧浪”西南的大块土地上开始拆庙,拆祠堂建楼房了,院子里的许多古建筑、古石碑、古代贤者塑像等在经过若干次“破旧立新”和“拆房扩院”后便荡然无存了。那些古祠、古庙只能留在“小沧浪”大院那几个留恋古迹的人心底了。后来根据《沧浪亭志》上的介绍,以及根据1950年代初就入住“小沧浪”的邻居们回忆,我们居住的“小沧浪”正南面的那座古庙基本可以断定就是“韩蕲王庙”,而我们小时候看到的古庙东南角上的那块石碑,也基本可以断定是与“韩蕲王庙”配套的黄省曾书写的“韩蕲王庙碑记”。黄省曾,明代知名学者,他留下“旖旎绿杨楼,侬傍秦淮住。朝朝见潮生,暮暮见潮去”这首脍炙人口的《江南曲》给了富饶又美丽的江南。可惜,一〇〇医院宿舍区毕竟是个军营,属于“武夫之家”,没有人去研究那些“之乎者也”之类的烂碑文,更没有人用昂贵的120黑白胶卷去拍摄那座一文不值的古碑。至于那个古庙,东南角一间长期用作邻居陈医生家女儿的“闺房”,而疑似供着“韩蕲王”的那个大间则当医院木工房使用至古庙拆除为止,一点都不在乎它所谓的“历史价值”。自然,依恋古碑、古祠已经是跨过中年以后的事情了,儿时的依恋还是门前那口可以冰西瓜的古井和窗前那汪可以钓鱼摸虾的池水。
一直等到8月中旬,母亲回家说,你们可以把你们自己的东西准备一下了,明天我让我们科室里的几个同事来帮搬家,刚才我已经去大礼堂那里看过房子了,两大间房,足够我们一家子住了。
那时搬家简单,家具基本都是问医院“营房科”借的,主要是搬锅碗瓢盆、衣物杂件等,几黄鱼车就可以解决问题了。8月正缝暑假,大礼堂许多“新邻居”都是我的同学或儿时的玩伴,所以这新家一点也不觉得陌生。不过,熟悉也有熟悉的坏处,因为有人说:“你现在搬到我们大礼堂了,你就应该参加我们大礼堂的暑期‘小小班’了。”当初小学流行课外办“小小班”的学习制度,所以我感觉他说得很有道理,于是就在大礼堂的“小小班”里混了几天。可是,过了几天“小沧浪”组的小组长传话来说:“放假前吴老师安排你在我们沧浪亭小小班里一起做作业的,这几次我记了你旷课,你再不来我们小小班的话我开学后要报告吴老师了!”无奈,我只能再一次到“小沧浪”大院那里去办“小小班”。8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我刚从“小沧浪”的“小小班”里出来,恰遇在拆除一〇〇医院新建在人民路旁边的大门。那时我似懂非懂,只是出于好奇挤在人群里围观“拆大门”的热闹。人群里闲话不少,有一个大人说,这回上级机关要求医院领导全面落实“中发[1972]28号文件”精神,撤除大门,恢复原状。
是啊,恢复原状!可是,“小沧浪”院落已非我家原状,那间房门上熟悉的挂锁早已被人换上一把陌生的大铁锁。雁过无痕,人走茶凉,原状何有?人有聚散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还是散了吧,我的邻居,我的玩伴;难别也别了吧,我门前那口古井,那丛假山。好在沧浪亭前还有一池溪水,它可以载着我的相思流向很远,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