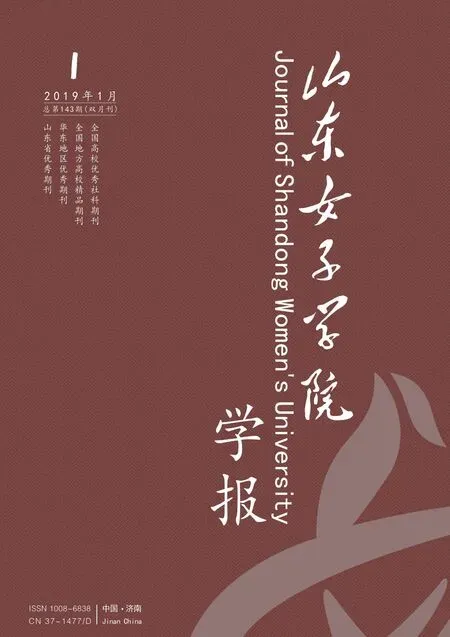大众传播中的女性形象研究综述及对女性主义中国化的思考
卢 敏
(北京大学, 北京 100871)
大众传播为了扩大市场、吸引受众,其所展现的女性形象经历着不断分化、加强、打破、重塑的过程。对大众传播中女性进行形象研究,有助于我们认清大众传播对社会性别的刻画和表现,同时有助于发掘媒体与现实世界的互动关系。在中国学者开始关注女性主义和女性形象之后,对相关理论进行本土化建构,使之适应中国社会现状,又成为我们应当关注的问题。
笔者将首先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对关于大众传播中女性形象建构的文献进行整理。纵向维度,即研究随着大众传播技术和传播方式的发展,大众传播中的女性形象表现出的特征和性质;横向维度,即在大众传播的生产和接收过程中,对参与其中的女性角色及其自我形象建构进行分析。同时,借助以上的女性形象分析,回归中国社会现实,笔者提出对中国女性主义研究本土化的几点思考。
一、纵向维度:传统媒介与互联网媒介中的女性形象
大众传播经历了从传统印刷媒介报纸、杂志等到广播、电视媒介再到当下互联网时代的网络媒介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大众传播中的女性形象也经历着变化。然而,由于大众传播媒介对社会性别理解的僵化与局限,使得大众传播不同阶段的女性形象有着一定的继承性和同一性。
传统媒介主要指报纸、杂志等印刷媒介与广播、电视等电气时代的媒介形式。在传统媒介阶段,大众传播中的女性形象有如下特征:(1)缺失性。媒界中男性形象为主导,女性在数量和表达力上仍然处于缺失的地位。(2)被动性。女性多是“被要求”“被塑造”的形象,与男性形象的主动性形成鲜明的对比。(3)刻板性。女性形象主要停留在甜美可人或贤妻良母的阶段,显得僵硬刻板。(4)另有部分学者认为在传统传媒方式中,女性形象正在逐步变得丰满,体现了女性主义的价值观念。
(一)传统媒介中女性形象的缺失
女性形象的缺失首先体现在新闻报道中女性话题的缺失。刘利群等发现在五个新闻节目——江苏卫视《江苏新时空》、广东卫视《午间新闻》、天津卫视《12点报道》、安徽卫视《每日新闻报》、青海卫视《午间360度》中,2013年全年的新闻话题中有93%的新闻未涉及女性话题,而在剩下的7%的新闻中,涉及女性与婚姻、家庭的新闻仅7条,而且都是关于女性如何勤俭持家、做贤妻良母的报道,这直接体现了女性形象在电视新闻媒体中的缺失[1]。
其次,刘晓红、卜卫也提出,在电视(主要是电视剧)中,男性出现的几率远大于女性。她们认为,20世纪50年代~80年代在北美电视节目中男性出现的比例远远高于女性;同时,她们用内容分析的方法研究了中国传统媒介对女性形象的展现,发现女性在报纸、教科书等主流纸质媒介中的出现次数也比男性更少[2]。
再次,中国传统媒介中女性形象的缺失也在电影中有所体现。戴锦华在《不可见的女性:当代中国电影中的女性与女性的电影》一文中提到,文化中的“女性”变成一种子虚乌有,女性、女性的话语、女性的自我陈述与探究,由于主流文化中性别差异的消失,成为非必要的与不可能的[3]。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到“文革”时期的电影中塑造的女性形象,主要是“解放的妇女”“女英雄”,从而成为了群体“非性化”的一员,并不是真正的女性,例如谢晋导演的《红色娘子军》。
(二)传统媒介中被动的女性形象
首先,劳拉·斯·芒福德在《午后的爱情与意识形态:肥皂剧、女性及电视剧种》一书中,详细分析了美国肥皂剧中的女性形象。她认为,肥皂剧中的女性形象都是被动的,例如,只有坏女人才会主动地知道自己怀孕,女性也不能自己控制是否要堕胎等等。同时,肥皂剧中常常塑造因为其他女人怀了丈夫(未婚夫)的孩子就退出这段关系的“好”女人,这种品德的塑造,也体现了女性形象的被动性[4]。
其次,传统媒介也着力塑造女性“被观看”的被动形象,这同时赋予了男性“主动观看”的地位。格雷姆·伯顿在《媒体与社会——批判的视角》中提出,许多女性杂志的封面图片上所展示的女性都具有“照相机意识”——摆出各种姿态,向读者炫耀她们的服饰,这体现出杂志阅读中的女性“被观看”与男性“观看”地位的对立。同时,伯顿也分析了肥皂剧中的女性形象,认为肥皂剧中“女家长”形象的设置,也是女性被动形象的一个体现:“女家长”通常拥有对家庭的强大控制,通过这种形象的塑造,肥皂剧构建出了一个关于“母性”的神话,这样的神话对于女性的独立自主并不能够提供任何帮助,相反却在某些情况下导致了男性利用女性来满足私欲[5]。
再次,女性的被动形象在电影中也一样有所体现。在戴锦华看来,中国第五代电影的部分作品中,男性欲望的视野再次出现,大银幕上的女性形象变为被动的、“被观看”的。女性形象中的性感要素被放大表达,例如张艺谋的处女作《红高粱》、周晓文的《疯狂的代价》,女性形象的复现是为了完成对男性文化及其困境的呈现与消解[3]。李攀着重研究了近年来兴起的“小妞电影”,他提出,中国“小妞电影”传达出当代女性的焦虑情绪,电影中的女性越是反叛男权社会,就越是体现了女性的被动地位,反映了现实中女性的焦虑与无奈[6]。
(三)传统媒介中刻板僵化的女性形象
默克罗比的《女性主义与青年文化》一书第四章“杂志《杰姬》:浪漫的个人主义及十几岁少女”中提到,《杰姬》着力塑造柔弱、可爱的女性形象,且少有变化,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漂亮。作者认为,本杂志强调性别角色间绝对和天然的差异,女孩需要漂亮且不自负,男孩可以多变,但女孩只能有女孩样。这种角色设置,生动地体现了杂志对女性形象的刻板描摹[7]。同时,中国学者罗慧也认为,时尚杂志在以女性为表征对象方面突出了女性“被看”的特点,同时这些杂志用整页广告蛊惑女性消费,使得女性主体意识的表征被不断弱化[8]。
在电视媒介出现之后,女性的刻板形象被进一步强化。刘晓红、卜卫在《大众传播心理研究》中对电视媒体中的女性刻板形象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归纳:电视上的女性形象大都是温柔、迷人、少竞争性、性感、情绪化、依赖男性的形象;男性则多是理性、智慧、坚强、勇敢的重要的社会角色。在职业、能力的层面上,女性是无知的家庭角色,在社会层面上,女性是承受暴力的对象。她们认为,这种刻板印象与受众的心理过程相适应,符合她们对女性形象的期待,因此会被反复提及[2]。
(四)非主流声音:女性形象的上升
在众多学者批判大众传播中女性形象建构的缺失、边缘化、刻板僵化的同时,也有学者认为,女性在电视剧中的主导性正在增强。
陆晔通过对女性题材电视剧中女性角色设置(男女主角数量对比)的分析发现,女性形象在电视剧中的主导性增强,且电视剧中的女性形象日趋复杂,女性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状态,这体现出中国女性正朝着现代女性迈进[9]。他认为,中国电视传播中女性形象的上升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女性电视从业者的介入使电视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更具女性意识;其次,受众对电视女性形象的看法产生了社会影响力,自强自立的女性更受观众的欢迎;再次,电视文本的结构方式与女性形象的呈现有相互作用。
然而,在已有的大众传播与女性形象研究中,这种乐观的声音仍然处于非主流地位,且多集中于某一时段的中国学者对中国电视作品的分析中。
二、互联网媒介中女性形象研究
通过梳理互联网媒介中的女性形象建构相关研究发现,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时代,大众传播中的女性形象建构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女性形象仍然处于缺失和边缘地位;第二,以网络新词为表现的女性形象的污名化;第三,互联网媒介对女性形象的多向塑造与表达。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在女性形象建构方面,传统媒介与互联网媒介的传承性和同一性。
(一)互联网媒介中的女性形象仍处于缺失和边缘地位
首先,与传统媒介中的新闻报道相似,在网络新闻中,女性形象仍处于缺失和边缘状态。顾冬梅在《网络传播:性别仍未平等》一文中,对2004年上半年国内几大门户网站的新闻报道统计发现,当时的互联网仍缺乏对女性群体的关注,而且对女性的报道主要集中在体育、娱乐、社会、生活等非主流方面,而在政治、财经、科技、商业等对社会起主导作用的相关领域,女性的报道被严重边缘化[10]。
其次,有学者通过分析网络环境中的女性议题和女性的公民身份来展现网络媒介中女性形象的缺失和边缘化。例如周翠芳在《网络媒介对公民身份的文化建构》中分析了网络环境中女性声音被压抑的现状,提出女性形象很少出现在政治、军事、经济议题中;网络中大量“女性频道”并没有成为女性汲取知识的平台,而只是为女性提供了一个消遣娱乐的场所,所提供的“知识”也大都是教女性如何变美,没有脱离女性“被观看”的身份。作者认为,网络中的女性形象依然遵循着社会对女性的印象,困囿于家庭的范围之内,作为男性的附属和陪衬,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11]。
再次,与传统媒介相比,互联网媒介传输速度更快、画面感和表现力更强、传播范围更广,因此更有利于图像、视频等多媒体的传播方式。在这种条件下,不少学者提出,网络上女性形象“色情”意味更浓,这也是女性形象边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例如曾长秋、李斌在《性别与传播——网络媒体中“被看”的女性形象》中提出,“网络对女性形象的建构,除了将居家育儿、婚姻情感等类型的栏目归之于‘女人’名下之外,更是将‘女’与‘色’结合起来,极力渲染美貌、性感与女性的关联”。各种富有挑逗性的文本以及与色情淫秽有关的信息泛滥于网络之中。这种现象进一步扭曲了社会性别印象,抹杀了女性的主体性和多元性,更影响了真实世界中男女受众对性别角色的认识和重新建构[12]。
(二)以网络新词为表现的女性形象的污名化
近年来,互联网的快速传播使得网络新词迅速生成,与女性有关的网络新词也层出不穷,“绿茶婊”“网红脸”等正在重新定义着网络上的女性形象,一些学者由此提出了网络中女性形象的“污名化”。曹晋等在《新媒体、新修辞与转型中国的性别政治、阶级关系:以“绿茶婊”为例》一文中提出,“绿茶婊”在网络的出现,集中地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符号、身体与性三者的商品化、市场化过程展现出来;在讨伐“绿茶婊”的网络混战中,新媒体为中国都市底层青年男性与权贵阶级的矛盾提供了宣泄与可见性的平台,同时也将一大批女性形象置于被戏弄、玷污的境地[13]。
同时,一些与女性形象相关的传统语境中的“正常”词汇,在网络中也呈现出污名化的趋势,例如“女司机”。胡宏超认为在当前的环境下,网络媒介对女性的报道存在形象建构的偏差,例如“女司机”已经被贴上了“马路杀手”的标签,这种形象建构的偏差进一步强化了莽撞的“女司机”形象。作者提出,在互联网中,传统男性中心主义仍占主导,女性群体在公共领域缺乏必要的敏感性和主动性,商业文化与消费主义也对女性形象污名化这一现象起到了催化作用[14]。
(三)互联网媒介对女性形象的多向塑造与表达
除却以上对互联网媒介中女性负面形象建构的研究,不少学者也认识到互联网媒介对于女性形象的正面塑造和女性争取话语权的积极作用。例如,在《性别与传播——网络媒体中“被看”的女性形象》一文中,作者提出,互联网也塑造了一大批积极的女性形象,这体现出性别文化与性别意识在媒介技术中的反映。作者呼吁,网络用户个人要反思落后的性别观念,同时需要从法规、制度和技术三个层面建立网络媒体的社会性别检测机制[12]。
其次,在女性话语权争夺方面,王蕾在《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网络媒介传播——以网络女红人为例论女性表达》中提出,网络媒介使一直被归于私人领域的女性得以进入公共领域,借助网络这个平台,女性获得了交流空间、话语空间和多元化的交往对象,她们抛弃了现实生活中所有的性别束缚和顾及,让自己的话语在公共领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传播,这为女性提供了倾诉的话语场,女性由此能够逐步进入性别秩序内部[15]。
综上所述,从以报纸、广播、电视为代表的传统媒介到互联网媒介,学者对大众传播中女性形象建构的研究集中在其负面,主要论述了女性形象的缺失与边缘化、女性形象的被动与僵化,以及女性形象的污名化。然而,随着社会平等意识的提升,不少学者也注意到大众传播作为一个话语场域,对女性形象塑造与女性话语表达正在发挥着越来越积极的正面导向作用。
三、横向维度:大众传播中的女性生产者与女性受众形象
在大众传播的过程中,生产与接收是两个重要的环节,生产者(如记者、编辑、导演等)与接收者(即受众)是大众传播中至关重要的角色,直接影响着传播内容、传播范围以及在此过程中社会意识的建立。对女性生产者和女性受众的研究,也是女性形象的研究者的学术重点。
(一)大众传播中的女性生产者形象
对大众传播中的女性生产者的研究,有助于把握传播大环境中的女性话语权,展示女性生产者的外在形象及自我定位。综观目前的研究,对女记者和女导演的研究较为充分。对她们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整体传播环境中,女性生产者仍处于弱势地位;第二,女性生产者正在发挥女性优势争夺大众传播中的话语权。
1.女性生产者的弱势地位。女性生产者在大众传播中的弱势地位,首先体现在媒体中女性生产者的数量不多、地位不高。《睡美人如何醒来》一书中收录的《营造一个小气候》一文中提到,1990年代中期,在新闻机构的编委会中,女性不到9%,部门主任中,女性不到18%,但在整个新闻工作者中,女性占三分之一以上。直到21世纪初,在传播和媒介产品制作的决策层中,仍然存在着严重的性别不平衡[16]。这种性别层级的不均衡,体现了女性生产者在整个媒体行业中的边缘与弱势地位。
其次,随着女性进入传播行业人数的增多,女性生产者在数量上有了明显提升,但是部分学者认为,即使在数量上占了优势,女性生产者的话语权仍显不足。刘利群等通过统计发现,在其监测的五档节目中,女性主播共出现634次,男性主播共出现352次,在数量上女性主播占很大优势,但是播报主题有性别上的差异,即文化和社会相关报道更倾向于使用女性播报,而经济科技等主题则更倾向于由男性播报。同时,女性主播都年轻、形象好、气质佳,是节目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也意味着她们承担着节目“花瓶”的角色。作者认为,这种男女主播角色的分化,是女性生产者边缘化地位的体现[1]。
再次,在当前许多女性生产者已经在媒体中占有一定地位、享有知名度的同时,部分学者也看到了她们光鲜背后被物化了的尴尬形象。李兰青在《透视女性名记者的性别尴尬》一文中,提出了关于女记者的成功与性别差异之间关系的问题。从逻辑上讲,利用女性自身优势可以与被采访者进行更好的沟通,也可以使受众不再仅仅看到来自男性视角的新闻报道;但事实上,对性别差异的突出和对女性身份的强调使得女性记者成为媒体利用的对象和受众猎奇、欣赏的客体——女性既扮演着媒体角色,同时更加扮演着被物化、对象化的审美客体的角色。例如同样是报道“非典”的记者,王志被展现出的是专业、敬业、执着、睿智的优秀记者形象,而柴静则被形容成“诗一样的女孩子”,被卷入了观赏者的视野[17]。
2.女性生产者对话语权的争夺。与其他女性相比,媒体女性生产者与话语权距离更近,具备争夺话语权的天然优势。众多女性生产者在争取话语权的过程中,塑造了一批批勇敢但又略显尴尬的生产者形象。
首先,不少女性生产者,尤其是女导演,通过将自己“男性化”来获得自己在业界的地位。戴锦华认为,最重要的主流电影、艺术电影的女性制作者,是成功的“男性扮演者”,她们中的大多数都公开地或间接地表示她们对女性主题、女性电影的漠视或轻蔑。在这个过程中,这批成功的女导演塑造的是略显尴尬的女性形象,但是至少她们让外界听到了女性的声音[3]。
此外,有不少学者认为,已有许多女性生产者在大众传播中占有了一席之地,传播了女性主义价值观,塑造了良好的女性生产者形象。例如,同样是对电影的分析,华晓红认为,中国女性导演往往通过对男权文化范围内的传统观念的柔性解构来突出女性主体性。女性创作者身为女性,对女性的生存状态、文化处境、心理情感有着最为深刻的体验,这对女性意识的逐渐清醒和自觉、女性主体身份的建构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其本身就意味着对男权文化围城的强力突围[18]。张会军在《影像中的感性情感——女性电影导演研究》中,从女性导演与女性的电影、女性电影导演创作现状、女性电影导演典型范例三个主要方面进行了论述,他认为女性导演用感性情感和独特风格创作的作品,为女性的意识表达、艺术创作和电影市场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强调,当下的电影艺术领域体现出了对女性电影导演的尊重,女性导演具有优势地位[19]。
同时,也有学者对女性记者的自我定位及自我形象建构进行了充分肯定。卜卫对《人民日报》女记者卢小飞的新闻作品进行了解析,认为她的作品鲜明地体现了女性主义的文化特征。她提出,卢小飞从少数民族社会的发展、妇女儿童的发展和贫困地区农村发展的角度来透视社会,这是典型的女性主义视角。同时,她的作品还展示了女性积极追求发展和张扬个性的一面。卜卫强调,女性视角对妇女、少数民族等的关注可以补充主流文化生活,在大众传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
(二)大众传播中的女性受众形象
在传统媒介时代,女性的电视收视行为是学者们的研究重点;在互联网媒介时代,女性对互联网及移动客户端的使用,也正在走进学者们的研究视野。通过对文献的总结归纳发现,大众传播中的女性受众形象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女性是大众传播中的被动受众;第二,女性受众正在通过媒介积极塑造新形象。
1.女性是大众传播中的被动受众。首先,在最早受到关注的家庭电视观看行为中,众多学者认为,女性是家庭电视使用的主体,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她们掌握着电视的主动权,也不意味着她们能够通过电视建构自身独立、自主的媒介使用习惯。戴维·莫利在《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一书中分析了家庭收视行为中如何看、看什么的问题,并提出男女在收视行为中有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是由男性和女性在家庭中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决定的:女性倾向于将家庭定义为“工作空间”,因此女性出于家庭责任感,只能够间断地、充满负罪感地去看电视,而男性则主要将看电视当作是休闲。访谈也发现,男性在家庭中掌握着遥控器的操纵权,女性则处于被动地位[21]。
同样地,格雷姆·伯顿在《媒体与社会——批判的视角》一书中提出,以批判的视角来看,肥皂剧一方面要求女性观众认同于其所承担的家庭角色,另一方面也要求她们不加批判地接受现状。如果说这种性别化角色体现了肥皂剧中的“社会写实主义”倾向,那么这种写实主义同样也是意识形态的体现。社会现实中女性的被动性,被带入到了电视收看行为中,女性变成了被动的电视观众[5]。
同时,有学者认为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的使用中,女性也是被动的受众。例如卜卫认为,大量研究发现,在互联网时代,妇女并没有像男性一样得到“主体地位”[22]。经验表明,女性地位并不能随着传播新技术的发展自然地得到提高,其权力也不能随着传播新技术的发展自然得到增长,女性常常被新技术置于更边缘的地位。
2.女性受众正在通过媒介使用塑造新形象。首先,不少学者认为,媒介使用可以使得女性更加适应当代社会的要求,方便她们履行自己的角色职能,拉近她们与时代的距离。在众多研究中,曹晋对上海家政钟点女工的手机使用分析是经典案例。这项研究旨在透视中国农村妇女在中国都市家务劳动市场化、社会化进程中,如何发挥手机的功用来适应新的都市生活与家政劳动,并在异地以电话遥控的方式来监督儿子,履行“母职”。作者借此探索传播新技术的普遍使用重塑妇女的阶级与社会性别位置的过程,也展示了新技术在重塑女性身份和角色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23]。
其次,女性在媒介使用中形成的对自我的认同,也得到了学者的关注。格雷姆·伯顿在《媒体与社会——批判的视角》中提到,女性杂志的使用是为女性读者所熟悉的表达模式,这使读者不仅能够具备处理日常生活的技巧,也给她们带来了快感,甚至让她们上瘾,因为女性读者在阅读这类杂志时,感到个人得到了“召唤”,同时也获得了女性群体的归属感[5]。
再次,媒介使用可能赋予女性自我减压、自我解放的机会,从而有利于她们对自我形象的建构。论著《媒介研究:文本、机构与受众》第三部分重点介绍了媒介传播中的受众研究,作者提到,女性阅读浪漫小说所传达的也可能是一种反抗性信息;阅读小说可以免除她们在看电视时的负罪感,又能给自己留出独立的时间[24]。学者卜卫在2000年前后针对女性互联网用户和非用户的定量研究发现,在使用互联网之后,女性用户比非用户有更多的接近信息与娱乐、表达与交流的途径,更能满足个人需求,在社会价值观念方面更加开放,因此对自己的认识更为丰满、深刻,对自己的形象塑造更加自主、主动[22]。
总之,在大众传播的横向维度,即媒介的生产和接收过程中,女性生产者和女性受众虽仍然没有摆脱被偏见、被边缘化的地位,但是女性生产者通过电影、新闻等作品,正在表达着自己的女性观念,积极塑造着正面的女性形象;女性受众在媒介接收过程中,也获得了获取知识渠道和观点表达的途径,这对于她们对自身形象的认同和塑造有着积极意义。
通过对以上内容的综述研究,对大众传播中的女性形象描述可总结出“刻板性-多样性”(主要涉及对女性形象的第三人称呈现)、“被动性-主动性”(主要涉及女性形象的自我定位与认知)两个衡量角度,将以上讨论的各种女性形象放入这两个角度框架中,形成如下所示的“大众传播中的女性形象描述图”:

图1 大众传播的女性形象描述图
如上图所示,传统媒介中的女性形象更为刻板、被动,而互联网媒介中的女性形象则更呈现出多样性和主动性的倾向,但总体上仍然是刻板且被动的。在生产者和受众的角度上,传统媒介中的生产者主动性较强,但仍然有刻板性;而在互联网媒介中,生产者不仅主动性有了提升,更因为信息传播渠道的丰富,以记者为代表的生产者形象更加多样。传统媒介中的女性受众主要是被动接收信息,但是可以在接收信息的过程中产生对女性身份的共鸣,因此形象的多样性较为突出。而在互联网媒介中,女性受众接收信息的主动性有了质的提升,对个人形象的建构也更加多样。
以上总结只涉及到了各个类别中女性形象的主要方面,并不是全面的展示,然而从中我们也大致可以看到大众传播中的女性形象的发展过程: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纵横维度上的媒界中的女性形象,都在向着多样性和主动性发展。
四、对当前环境下女性主义研究中国化的思考
在前文的综述中可以发现,无论研究者是否为女性主义的支持者,对大众传播中的女性形象研究,始终在女性主义的框架之内。因此,要更好地研究中国社会大众传播中的女性形象,就要首先做好女性主义的中国化。
由于西方国家对女性主义的研究历史时间长、研究内容丰富,不少中国学者倾向于直接将西方的女性主义思想代入中国,全盘接受,有对西方女性主义神圣化的倾向。对于这一点,有不少学者持反对态度。董丽敏在《女性主义:本土化及其维度》中提出,如果无甄别地借鉴西方女性主义思想,将会使得女性主义的本土化出现基本判断上的偏离——对女性主义的讨论更多是在文明与愚昧、西方与东方这样的大格局下展开,而不是完全贴近男性与女性这一基本性别框架。笔者认为,由于中国社会形态的独特性,女性主义的中国化也需要有“中国特色”[25]。以下是笔者在以上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关于研究大众传播中的女性形象与女性主义本土化的几点思考:
(一)中国的女性研究与民族解放运动相结合
西方女性主义来源于性别不平等的社会根源,女性对女性政治权利、社会地位、独立自主意识的追求,形成了最初的女性主义。可以说西方的女性主义是建立在男女性别二元对立的基础上的。然而,中国女性主义的最早缘起却是来自近代中国对封建社会和外来侵略的反抗斗争。尤其是上世纪中叶的中国社会媒介传播水平与西方社会差距很大,因此更不能在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方面照搬西方研究成果。
在中国近代的反抗斗争中,涌现出了大量女记者、女诗人,从女性的角度洞观中国社会,以女性的力量争取民族的解放,并由此产生了女性对社会权力、自我意识的要求和呼吁。这种吁求是建立在国家和民族的危机之上的,而不是女性自觉自醒地与男权文化作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思想被一度认为是女性主义的吁求。然而现在看来,这是在国家建设的特殊时期,女性对于国家号召的回应,更多地传达着爱国情怀,而并非女性与男权社会的对抗。反之,这种要求男女完全平等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有违西方女性主义对女性独特性和主体性的要求。
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女性主义的渊源不是女性与男权社会的对抗,而是在整个民族觉醒过程中女性群体的觉醒,它与外来侵略相斗争,与国家面临的恶劣环境相斗争,而不仅仅是为女性争取自由、独立和解放而斗争。
(二)对中国女性的研究要与中国特殊政策相结合
近年来,中国社会出现的许多与性别相关的现象引起了媒体和社会的关注,例如“天价彩礼”“丈母娘推高房价”等。这些现象常常被解读为中国女性地位的提升,媒体也常常通过此类新闻渲染当代中国女性,尤其是适婚女性对生活品质的追求,这个现象对当代女性的自我定位和自我形象刻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甚至被部分民众标榜为“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
以上现象的出现,其实与中国1980年代初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密切关系。在“计划生育”政策与中国社会“重男轻女”传统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社会的男女比例受到了重大影响。根据国家统计局2015年人口抽样调查,25~29岁性别比为102.24∶100,20~24岁性别比为108.51∶100,15~19岁性别比为116.12∶100,10~14岁性别比为118.59∶100。在这样悬殊的男女比例下,社会对高彩礼、房、车的追捧主要来源于男性娶妻的急迫性,而非女性地位的提高。相反,个人认为,婚姻关系中对物质的强调,在当前情况下,体现出的是社会对女性进一步的物化倾向。因此,对中国女性主义及大众传播中的女性形象研究,不能仅看社会现象的表面,还应分析这背后的政策原因和制度根基。
(三)对中国大众传播中女性形象的研究要注重互联网的影响
在西方,在时间关系上,对大众传播中的女性形象研究是与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相伴随的,即逐渐从电视、杂志等研究发展到互联网媒体中的女性形象研究上来。
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对媒介与性别的研究兴起之后,就遇到了互联网的大潮。互联网信息的快速、大范围传播,使得它在形象塑造、价值观塑造等方面有着传统媒介不可比拟的强大力量。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研究大众传播中的女性形象,面临着巨大的机遇,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事实上,互联网对社会性别形象和性别关系模式的深刻影响,已经初见端倪。刘利群等在《中国媒介与女性发展报告·总报告》中提出,2013~2014年,在大众传播中出现了一些新兴的性别形象和性别关系模式,丰富了性别文化内涵[1]。例如“女汉子”,在大众传播中常被描述为职场上的技术标兵与劳动模范,是具有独立自主、坚强积极气质的女性力量;而“暖男”则是懂得理解女性需要的一类男性,这种形象的构建和传播反映了社会对多元男性气质的期待和需要,也反映了当代女性对两性关系模式需求的变化。这种变化在上世纪中期的学者看来,是不可想象的,更是不能单纯地放在传统西方女性主义框架下讨论的,必须根据当前的社会形态,进行因时制宜的讨论。
总之,要充分研究中国大众传播中的女性形象及其对女性主义话语的表达,就必须将女性主义置于中国当代社会的现实中进行讨论,要找出中国女性主义的真正来源,考虑中国的特殊人口政策,并充分意识到互联网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而不是对西方女性主义生搬硬套,只有这样才能摸清中国本土的女性主义发展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