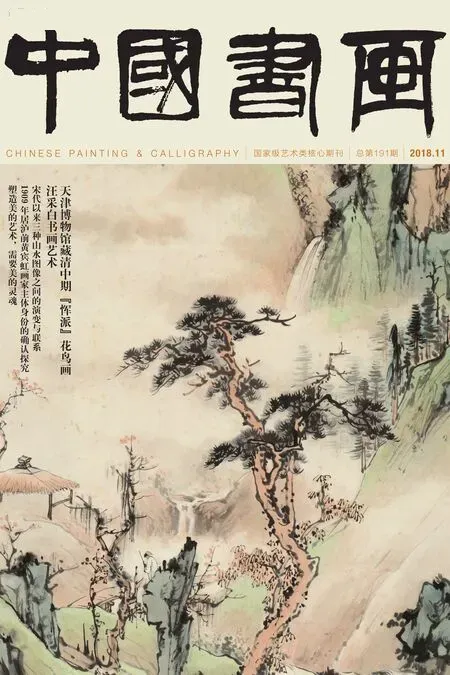为文求平朴 问艺尚深沉
——侯开嘉教授访谈
◇杨帆

侯开嘉,1946年出生于四川省宜宾市。现为四川大学艺术学院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学术委员会委员,第三届、第六届中国书法兰亭奖评审委员,中央文史馆书画院院部委员,四川省书学学会副会长,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其书法作品在1988年湖南电视台举办的国际书法电视大赛上获金奖,在第五届全国书法篆刻展上获“全国奖”。《中国书法》2011年第2期《经典与当代》栏目专题介绍其书法艺术与成就。《中国书法》2018年第6期《人物·风采》栏目专题介绍其数十年来理论、创作、教学探索的历程。应邀到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画院、四川美术学院等处举办专题学术讲座。主要著作有《中国书法史新论》《书法史求真录》《中国近现代名家书法集·侯开嘉》等。
杨帆(以下简称“杨”):侯老师上午好!今天这个访问,主要就书法的多方面问题展开,希望能对现今的书法创作与理论研究有所助益,对有志从事书学研究的年轻人亦有所启发。
侯开嘉(以下简称“侯”):行。那就随便谈,不对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杨:您出生于新中国成立前三年的四川宜宾市,现已七十有三了。自1981年参加中国书学研究交流会至今,您便一直活跃于书坛,在书法创作、书法理论、书法教学诸方面的成就和影响都是广为人知的。但大多数朋友并不清楚所以成就侯开嘉的背景和经历。据我所知,您年轻时没上过大学,却当过工人、木匠,还游走养过蜂,后来又调到宜宾书画院做专职书家,再后来才调到四川大学当教授。能否谈谈这三个阶段经历对您书法产生的影响。
侯:我1966年高中毕业,正好遇上“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乡”,其经历和全国的年轻人大体相似,是所谓的“蹉跎岁月”,就不谈了。我学书法是在17岁那年,其目标就是赶上班上写字最好的同学。幸运的是我碰上两个好老师,名叫高步天、银际霖,是我家乡的“宿儒”。在那个时代学习书法是不合时宜的,有一定政治风险。现在回想起来,这现象反映了中华文化有顽强的生命力,能生生不息吧。是这两个老师把我带进了书法殿堂,让我感受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看见了美,因此就迷上了书法。在以后任何困难的时刻都有它相伴,生活就不寂寞,成了我生命的依托。
杨:您多次提到您人生经历中主要做的三件事:写字、研究、教学。可是,社会上很多人就不能都如您这样幸运,他们做的仅仅一二件而已。于是便将此三者对立起来,认为搞理论的人创作不行,搞创作的人不一定要懂理论。您是怎么看待的?
侯:是的,人到老年都喜欢怀旧,回顾一生,发觉所做之事不多,也简单,仅写字、写文章、教学生三件事而已,还不敢自信这三件事都做好了。我之所以能做这三件事,还要感谢有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否则将一事无成。我学书法之初和现在一些年轻人不同,即学书法时同时关注书法理论。我认为实践和理论是学书法的双翼,只有并重,才可能飞得高。教书是我年近半百之后。在高校教书和以往书法传授是不同的,不能仅靠自身的一些经验。教育是有严格的科学性的,这须向国内外先进的教育学习,走出自己教育的特色。教育搞得好不好,培养出的学生水平高低,即是检验教授水平的试金石了。

侯开嘉 篆书史繇孝道五言联 143cm×30cm×2 纸本 2017年
至于如何看待书法创作和理论研究,二者的关系怎样,我认为二者不是一回事。书法创作需要形象思维,而理论研究需要逻辑思维。二者虽然不同,但又相互联系。对个人而言,在两者之间,可以有所择重,却不可能不知。如果研究理论的人不懂创作,那研究出的理论可能是空中楼阁,深入不到哪里去。如果认为搞创作的人可以不关心理论,认为理论无用,那么他的创作很可能是“短命”的。我从20世纪80年代进入书坛,几十年来,可谓阅人多矣,“各领风骚三五年”的现象令人喟叹。当今书坛创作跟风现象如此严重,就与不懂理论有关。至于一些从书法复兴到今仍活跃在书坛者,其身后必有学术背景为其支撑,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你真的热爱书法艺术,愿为之奋斗终生,不关注学术,不懂理论,实为不智!
杨:记得很早以前,您就提出书法理论要具有新、争、深的品格。我以为创作也要具有这样的品格。一个人的创作与理论,不能大家都说好,也不能都说坏。没有新意和深度的作品,也不会因职位、名气等非书法因素而长久存世。请您谈谈书法理论与创作在现今背景下如何保持较高的品位。
侯:是的,我很早就认为一篇优秀的理论研究论文必须要具备“新、争、深”三个特征。学术论文不同于一般的文章,如果没有对原有现状的突破,那这篇论文就毫无价值可言,是在浪费精力和纸张。从事书法创作也类似。书法创作大约分继承型和创新型两种。我们熟知书法史的人都知晓,留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基本是创新型书家,而继承型的书家很难在书法史上找到位置。书法创新很难,必须有继承才有创新,离开了继承是断难创新的。那种轻视传统,甚至抛开传统去走所谓“创新”的捷径,是不可取,也不会成功的。书法创新的确很难,相当难。若无“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付出,就不要去搞创新了。即使如此,还不一定会成功。现实中,创新失败者是大多数。但你不去探索创新,却永远也不可能成功。另外书法创新还有一个误区,就是以为只要和其他的不同就是创新了。记得石鲁先生说过一句话:“艺术第一要新,第二要美。”“新”和“美”是相关联的,缺一不可,只新不美不是成功的创新。当今书坛就存在着这种创新倾向,新则新矣,但不美,就很难得到观众的认可。这个问题值得作者反思,不要把所有反对的观众都视为愚氓。因为当代艺术的现代性表现,就是要与观众互动,离开了观众参与的艺术,很难认可它是当今时代的艺术。批评对艺术家和作品都很重要。但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所有人都说好的作品一定是最好的作品吗?不一定!不少人说你的作品不好就一定是坏作品吗?也不一定!现在有人很怕批评,一听批评就跳了起来。其实任何一个有作为的艺术家都会被批评,如王羲之、颜真卿、苏轼、米芾、王铎、邓石如、吴昌硕等都被批评过,只是被批评不倒而已。没有被批评的书家只有两种:一种水平差不值得批评;另一种是权势重,不敢批评。你到底属于哪种书家呢?不过现在书坛的批评有点变味,基本上是吹捧的居多,很难见到很有见地的批评文章了。另外,我认为真正的好作品,必须经过时间的检验,这要待到你百年之后,那时品鉴你的作品好坏,与身份无关,与身前炒作无关,只面对单纯的作品本身,如此才能反映出真实的价值和艺术地位。

侯开嘉 隶书节临张迁碑 168cm×50cm×2 纸本 2017年
杨:优秀的学术作品不仅充实,亦有光辉。您行走书坛几十年,著述并未等身,书页亦并非大部头,前后就《侯开嘉书法论文集》《中国书法史新论》《书法史求真录》几本三十二开论文合集,这在今天评价体系下会被认为单薄。请谈谈您满意的作品,与大家分享一下。
侯:我毫不讳言,情况确如你所说。世上有聪明人和笨人两种,我是属于比较笨的那种。我从事书学研究正好四十年了,回首往事,发觉值得看的文章不过二十多篇,论文集不过两本而已。比起著述等身的朋友,真的显得太寒碜了。我十分羡慕那种才子型的学人,我知道,有的朋友一夜之间就能作文一两万字。而我有的一两万字论文,从始到终,往往要花上近一年的时间。如《俗书与官书的双线发展规律》(1989年)一文,至今还被有的高校指定为硕、博研究生必读论文;《隶草派生章草今草说》(2001年)发表后被《人大复印资料》和《新华文摘》转载,至今未见有质疑的文章;《齐白石与吴昌硕恩怨史迹考辨》(2012年)发表后引起书画界强力关注,文章被多种刊物转载、摘登,甚至被剽窃,在网络、微信上着实火了一把。另外,还有《西学东渐与清代碑学兴起思辨》(2003年)、《西域文明的东播与颜真卿的书法创新》(2009年)、《以学术激活艺术——乾嘉学派与清代碑学》(2015年)、《元代书法生态新论——从颜体书法在元代的际遇谈起》(2017年)等文也是花了近一年时间完成。此外,另有几篇文章写的时间要稍为短些,但也花了好几个月时间,如《题壁书法兴废史述》(1996年),此文参加第二届中国书法史论国际研讨会,当即被媒体评论为对晋唐书法史“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新的突破”。《论竹简与纸的发明对书法艺术的重大意义》(1999年),此文被2001年《中国书法年鉴》列为十篇优秀论文之一。《论破体书法的缘起和发展》(2007年),此文参加在香港召开的“第六届中国书法史论国际研讨会”,是第一次从书法史的角度来正视破体书法。情况大体就是这样,文章不多,但却是我心血所凝。另外,还说明一点,我写文章纯属爱好,只写想写的文章,而不是为了评职称,或去申请课题一类的。
杨:学术研究理路与习惯,往往因人、因题而各有特点。人文社科领域各面的大家,其研究往往又异曲同工。想知道您这么多年的一些惯常研究理路、方法、写作习惯、写作风格等,比如,如何选题?如何搜集和分析新材料?如何订纲立论?如何书写?
侯:我研究的重点是中国书法史。关于学术界对中国书法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近几十年,时间不长。说实话,只要你深入研究,需要研究的地方比比皆是,不愁无处着笔,这就看你的眼光了。我除了熟悉中国书法史外,比较关注学术界研究的信息,特别是一些学术前沿的信息。另外,对书法新资料的出现必须关注,如考古发掘出的新资料。我对书法史,从不孤立地去看待,要把它放在整个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去认识、去掂量,它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的关系和受到的影响。这样写出的研究文章比较有深度,也比较客观。我写文章是从断代史入手,譬如我研究的重点是清代碑学,几十年抓住不放,对清代碑学的研究可以自信地认为较为前沿。但我着眼并不仅是清代碑学,关于书法史各个时期我都有所涉猎。当一个研究的选题确定之后,我就大量地收集资料,在收集资料地过程中,往往会对事先的选题作出修正或更加深入,当资料收集完后,就列出文章的提纲,最后才开始动笔作文。我喜欢晚上写文章,晚上作文效果特好,是白天效果的数倍。因为多年的习惯,改变了我的生物钟,即使不写文章,半夜也要起来做其他事。我写文章的文风,是追随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大师们的文风,文章要求平实,从不故作玄虚,力求深入浅出,所以朋友们说我的文章“干货”多!

侯开嘉 篆书临虢季子白盘四条屏 180cm×48cm×4 纸本 2017年
杨:古人作书,多遵循人书俱老,我亦深信不疑。对应这个问题,您曾写过《书法创新的年龄规律》作为首届中国书学研究交流会的宣讲论文。我看您中青年时代所写作品,比较注重形式的奇崛与新意,在当时算是形式探索的先行者,但随着您进四川大学以后这二十余年沉浸学术的时光,您的作品又将外显的形式内化于书写之中,简静中透平和。现在有些老年人写字,故作铺排,如猛药亢进,有些中青年则故作龙钟苍老之态,我极不以为然,因为创作是在遵循年龄规律、历史规律、书体发展规律下的个性创新。对于此,您有什么意见?
侯:20世纪初,书法艺术刚从中国大地复苏,在习惯中,人们认为书法是老人艺术。从全国首届书展到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参与的人员基本上都是老人,对此我有感而发,写了《书法创新的年龄规律》一文,没想到入选1981年召开的全国首届书学研讨会,还被列为大会五篇宣讲论文之一(另外宣讲论文的四人是沙孟海、黄绮、陈方既、陈振濂)。现在回过头看这篇文章,的确写得比较浅薄,但是在当时还起了点现实作用,为八九十年代中青年成为书坛的主力军提供了理论依据,因而多被媒体转载和引用。那时,我的书法追求创新,讲求形式,讲究变形,还得到了不少的赞誉。后来,这样做的人多了,觉得没意思,就改弦易辙,大概这与年龄增大有关。孙过庭说:“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当然,此平正,非彼平正也。我认为,书法艺术发展到了当代,其观念与传统的观念应有所改变,而与美术的观念比较接近。若上届获奖的美术作品,在下届仍然这样做,可能就不会获奖,甚至落选都有可能,书法作品也应如此。因此,我在创作书法作品时,尽可能不要重复,每幅作品都要有独立的理念。虽然不可能完全做到,但我力求这样去做。在多种书法表现形式中,又能体现出我的个人风格,让人一看就知道是我写的。我一生的书法都在追求壮美,这与我性格有关,而表现秀美与我无缘。

侯开嘉 隶书问道诗轴 180cm×73cm 纸本 2018年
杨:您是国内书法理论界的代表人物之一,尤其在碑派书法理论的总结与阐发上时出佳构。这与您的创作品格在整体上都是一致合拍的。从继承传统角度讲,碑派书法的材料载体多为铜器、碑石、摩崖等,因年代久远、风雨侵蚀而产生若干非原本书写的蚀痕。但由于真实易拓,也就成为碑学大播于清代中晚期的重要原因。可是,现今印刷发达,都能将碑帖印到逼真效果,在这样一个与清代迥异的范本条件时代,如何发扬碑派书法之美,并将晚清以来的碑学成果继续推进?
侯:碑学建立之初,攻击帖学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刻帖不断翻刻失真,而新出土的碑版更能体现古人书法的精神,因此应该去学碑而不学失真之帖。这个理由当时得到大家的认同,连帖学家也不否定,为碑学的建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随着时代的进步,照相印刷水平的普及提高,“翻刻失真”的问题已经不复存在了。那么碑学是否也应消失呢?如果这样看就太浅薄了。碑学的出现是时代变革的必然结果,在清中晚期整个时代都要求变革,书法的变革仅是其中之一,没有这个理由也会找出另外的理由来进行变革的。而清代碑学的变革为中国书法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因为有了清代碑学,中国一切实用的古文字,都成了观赏性文字,都能创作出书法作品。特别在篆隶书上取得的成就,超越千年,碑学大大扩展了书法表现领域。因为清代碑学的出现,确立了“金石气”新的审美标准,与传统的“书卷气”并立。清代碑学是“二王”体系外的新体系,所取得的成就不容小觑,是我们应该如何去认真总结、继承、发扬光大的问题。在现代,聪明的年轻人利用电脑的熟练操作,书法“尚态”成为十分容易的事,甚至强化训练、魔鬼训练,几十天后,作品就可以入选全国展或获奖。这种急功近利的现象深为有识之士所担忧。一位朋友与我说:“八九十年代的优秀书法作品给人的印象深刻,而现代这些得奖作品,看了就记不住了。”中国书法是在改革开放时才开始复兴的,前期有近三十年的断层。因此,对清代碑学的认识是模糊的,不像老一辈书家如林散之、陆维钊、于右任、沙孟海、王蘧常等,他们的认识就很深刻。“不失篆分遗意”的理念贯穿于书法创作之中,所以他们能留名书史。我想,当今聪明的年轻人要想真正有所作为,还得向老一辈书家学习,下点笨功夫。林散之对弟子说:“先写三十年隶书后再去写草书。”真经验之谈也,值得有志的年轻人去思量思量。

侯开嘉 隶书帆影驼铃五言联150cm×35cm×2 纸本 2018年
杨:作为您的宜宾小老乡,我知道在您调四川大学前的十多年,宜宾多数习书者都受到您的指导和影响。我作为晚辈,能最终走出去学习,先国美后南艺,逐步思考和对自身书法作否定之否定,也都是您楷模在前。后来您在四川大学又先后指导了三十名左右研究生,现在退休了,仍义务给博、硕士学生例行每周一次的授课和不间断交流。请谈谈您这两个阶段的教学特点和区别,以供广大社会上书家和在校师生参考。
侯:我在四川大学任教之前,在宜宾书画院主持工作十四年,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阶段,为家乡的文化作了应尽的努力。现在宜宾书法界不少的人都说是我的学生,其实我仅起了个学科带头人的作用。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信息不如现在畅通,那时我把书坛先进的理念带回来,同大家一起研讨,经常组织大家一起看稿,甚至把看稿会带到县里去召开,以期带动县里的书法水平。看稿中,我们坚持以批评为主,哪些该改进,该调整的,如何改进和调整,都能畅所欲言,认为不怕内部批评得如何厉害,只要拿出去别人说好就行。记得每届的国展宜宾都有人入选,甚至还有获奖的,所以大家对这种研讨形式都比较认可。另外,我还打算辅导一些人搞学术研究,进行了这方面的尝试,也有的人写了论文在《书法研究》上发表,但我最终发现做不下去,主要是资料太缺,不具备学术研究的客观条件而终止了。在宜宾书画院工作期间,我的经验是要团结热爱书法同仁,特别是注意扶持青年人。主持人必须要无私,甚至作出必要的牺牲。用川话俚语说:“吃得亏,才打得堆!”这样才能把事情搞得好!
1997年初我调到四川大学艺术学院任教,情况又不同了,用不恰当的比喻:原来我带的是游击队,现在我带的是正规军了。正规的高校教育是有严密的科学性的,因此我对此进行了仔细的考量,发觉国内北方的高校书法偏重于理论,而南方偏重于创作。因此,我决定对我校的书法教育,采用理论和创作并用,办出自己的特色。在具体实施中,书法创作的教育比较容易,根据学生各自的特点,提出指导性意见,指出主攻方向就行了,因为这些学生大都有一定的基础。而困难在理论教育,因为从事学术研究对学生完全是新课题,他们在读研之前都没有搞过,不做学术研究叫什么研究生呢?因此对这问题我还是费了一番心思的。一要求学生多阅读与书法有关联的书籍,扩大学术视野;二要改变本科学习的思维方式,阅读时,要有问题意识,对相同的书,比较出它们的不同,要有怀疑精神。我教学时采用了西方的一些启发性的上课方式,即老师不讲课,把主动权交与学生,每个学生必须把平时看书遇到不解的问题在课堂上提出,由大家讨论。这种课上起来比较生动活泼,氛围热烈,很受学生欢迎。但这课对主持老师的知识面是个挑战,老师对学术信息和学术前沿都必须了解。当在讨论时要敏锐地发现其中有学术价值的东西,就指导学生抓住不放,深入下去,往往一篇学术论文就可能这样产生了。指导学生写论文,如何去选准学术的切入点?如何去查资料?如何思辨性地阐述自己的观点?这些都必须老师亲自指导,只要学生成功地写好第一篇论文,以后写论文就容易了。在读研期间,学生必须学会治学的方法。另外,营造学习氛围也很重要。我是带研究生的第三年才把这个氛围营造起来的。那时学生学习非常自觉,竞争也激烈。你的作品参加展览了,我也必须参加。你的论文发表了,我的也要很快发表。老师在旁对此良性竞争,乐观其成,这样老师也就轻松多了。根据我带研的经验,我认为学生读研期间,三年的学习历程应这样:第一年努力补习应掌握的知识,扩大阅读范围,深入了解专业知识,在下半年开始发表论文。第二年是大量发表论文时间,下半年毕业论文开题。第三年完成毕业论文,通过答辩。这是正常的学习轨迹。学生只有先写好几千字的论文,才有能力写好几万字的毕业论文,只有写好几万字的硕士毕业论文,读博时才有能力写好几十万字的博士毕业论文。没有这样循序渐进的学术训练,很难培养出合格的硕、博研究生。
杨:人到晚年,对生命的体悟会比年轻人更深刻。书法就是我们书法人的生命状态之一,但又非全部,能将您现在的状态分享给大家吗?
侯: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当步入古稀之年,不由得要想到这个问题。俗话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长生不老是不可能的。即使你长命百岁,在宇宙的长河里也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瞬,只要这问题想通了,就释然了!况且,人生应该活得有意义,而有无意义并不取决于生命的长短。就如一本书那样,其价值不在厚薄而在内容。王羲之活了59岁,王献之活了43岁,鲁迅活了56岁,我已经73岁了,比他们活得都久。我想,如果我能有他们一半的成就,我也愿意早早离去。书法伴随了我一生,我视它如第二生命。“各领风骚三五年”这种短命书法的谶语,我已经小心躲过了。我希望在臭皮囊离开之后,我的书法依然还存在(还需接受时间的检验),希望我的学术还未过时(也需接受时间的检验),希望我的学生有出息(看他们争不争气了)。作为物质的生命肯定要离开的,但它可以通过你的事业成就得到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