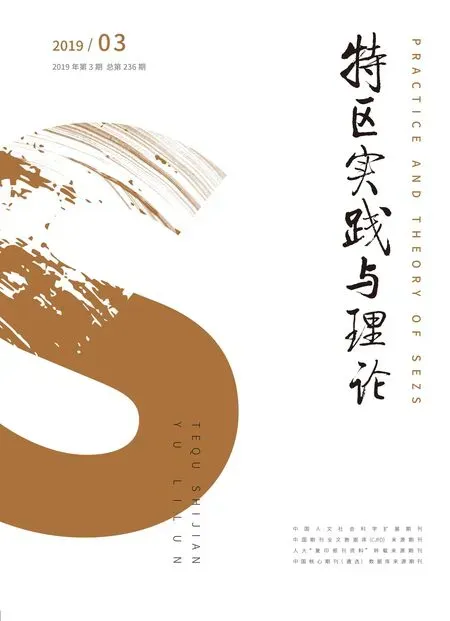公共行政的西西弗斯神话
[美 ]卡米拉·斯蒂弗斯 撰 赵 琦 李 钊 译
如果世界上存在着地狱的话,那它一定是学术领域。在这个领域的人注定要无休止地进行同样的对话。公共行政似乎像西西弗斯一样被判了一种永恒的命运:我们的使命是为我们的调查逻辑而战,但这些努力永远不会有结果。
似乎没有什么希望来改变现状,但作为一个天生的乐观主义者,我还是希望做力所能及的尝试。自20世纪50年代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与德怀特·沃尔多(Dwight Waldo)之间的史诗般的论辩以来,批评者一直在告诉那些有科学头脑的人:“你不符合自己的科学标准。”这些人回答说:“不,我们符合科学标准。你看不到的唯一原因是你不懂科学。”有时,科学家会抓住机会发起进攻,说:“你的工作质量低劣,因为它不符合我们的科学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反驳之词是,“我们的标准并不低劣,只是不同而已”。当前拉里·卢顿(Larry Luton)与几位经验主义者(他这样称呼他们)之间的冲突尽管策略细节各不相同,但他们论辩的背景和主线基本上与50年前一样。而我们认为索姆河战役(the Battle of the Somme)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斗争!
我们的论辩不能停留在“你不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和“接招,你这个卑鄙的后现代主义者”的层次,我们需要超越这个层次。我最喜欢卢顿(Luton)文章中的一句话:“客观现实可能只是公共行政现实中的一小部分”。①Luton, L. Deconstructing public administration empiricism[J]. Administration & Society,39(4), 2007(537-544).一旦你开始走向这个方向,就请思考一下这句话意味着什么?
我们先不考虑论辩双方(在当前的对话中)都没有非常仔细地界定客观现实。为了便于讨论,我们首先规定:现存的实在形式与任何人类对其的感知是相互分离的。包括后现代主义者在内,极少有哲学家否认确实存在一些外在于我们的东西。困难在于人类研究者所拥有的接触客观实在的唯一途径是人类自身。这会导致什么不同呢?科学断言应在研究过程中将这种差异的影响降至最低。严格地遵循科学的方法确保我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剔除人类的影响,调查的结果至少在概率上与目前的情况吻合。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超越人类现状的努力。自从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以来,许多哲学家都认为不可能与客观现实(本体)有接触,我们所知道的只是我们的感官传达给我们的东西(现象)。就像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曾经说过的那样,试图绕开这一点,就像试图不用眼睛看东西一样。事实上,自从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以来,科学家们似乎已经基本上放弃了证明任何关于客观现实本质的断言,并将证伪当作他们所能期望的最好结果。然而,所谓的科学方法,仍然是公共行政的黄金标准。
在我看来,这部分的辩论并不是很有趣。科学是人类的追求,这似乎是无可争议的。更有趣的问题是,这是什么样的追求?它追求的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想首先请求暂停使用“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t)一词来描述——不,是谴责——任何认识不符合正统的科学方法,特别是那些控诉我们糟糕信念的人。对于科学家来说,任何对诸如婴儿死亡、大屠杀、贫穷、酷刑、种族主义等世间罪恶的麻木不仁都不可避免地偏离狭窄的正道。这种指责不仅反映了对后现代主义的深刻无知,而且还引出了如下问题:这些现象的“客观”信息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能的,以及这种客观性构成了什么的问题。
从科学的观点来看,客观性包括定量的测量。然而,概念自身又是来自何处?它们不会从大自然的额头上冒出来,是我们建构了它们。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存在!这意味着我们对吸引自己或引发关注的事务才进行测量、观察与表征。①Paulos, J. A. We’re measuring bacteria with a yardstick[J]. New York Times.September 21, 2007.当我们选择关注这些现象时,我们就进入了与它们的关联之中。事实上,我们重视它们,至少在我们宣布对它们感兴趣的程度上是如此。
上面列出的每一个概念在定义方面都存在争议。因此,衡量一个概念的方式反映了对“什么可以视为该现象的一个实例”的共识。例如:婴儿存在多种死亡方式。但是 “婴儿死亡”(“infant deaths”)的准确数量在给定的任何时间期限内都能确定这一观念是一种幻觉。将婴儿死亡率作为更适当的社区健康指标的代表是一项公约,这是公共卫生专业人员达成协议的结果。它源于人们认识到合理准确地估计这一比率是可能的;一个被认为很高的比率有可能会让公众感到震惊;而且很少有其他的社区健康指标具有这样事实性和规范性的双重合法性。换句话说,婴儿死亡的概念是以各种方式进行社会建构的。任何一个特定幼小生命的死亡却不是社会建构物。
然而,对数字测量的迷恋会导致理智的人做出奇怪的事情。几年前,我代表一个社区心理健康中心参加该州所有中心代表的会议。会议的目的是提出一种门诊心理健康客户功能级别的指标体系,早期尝试毫无疑问是指绩效评估。人们很快就明白了,这将是一个数字尺度。我天真地问道:“我们怎么知道‘紧张症’和‘回应简单的口头暗示’之间的距离与‘自给自足’和‘能够在提供抚养便利的环境中工作’之间的距离相同?我同意你的等级序列,但这些数字是从哪里来的呢?”我得到的回答是:“我们必须使用数字,否则我们无法获得平均值和标准化偏离。”但问题在于:这些事情是否构成了与客观现实的接触?
我们已经在相对不那么吸引人的问题上花费了太多的篇幅,让我来谈谈一个在我看来有趣的问题。除了客观的现实外,还有什么其他种类的现实呢?公共行政部门为何压迫与之接触呢?
受篇幅所限,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似乎最难以忽视的问题上:主体间的或社会现实。这就是在共享空间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所产生的现实。它涵盖了几个层次的意识,包括显性的、隐性的和无意识的。这种社会现实是合作性或竞争性的言说和行动。它产生、维持和转变关于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共同(或有争议的)含义、规范和理解。尽管这类现实主要表现为语言形式,但却不限于语言。
对社会现实已经被哲学化并以经验的方式进行了研究。进行这项工作的哲学家包括胡塞尔(Husserl)、海德格尔(Heidegger)、梅洛庞蒂(MerleauPonty)、舒茨(Schutz)、伯杰(Berger)、卢卡曼(Luckmann)等。经验研究者包括韦伯(Weber)(在他的解释性化身中),戈夫曼(Goffman)、加芬克尔(Garfinkel)、西尔弗曼(Silverman)、齐默尔曼(Zimmerman)、维德(Wieder)和威克(Weick)。顺便提一下,这种研究模式完全与迈耶(Meier)和奥图尔(O’Toole)所遵循的模式一样是“经验性”的(“empirical”)。这种研究依赖对实存之物的仔细研究。这并不意味着接受如下前提,即:研究者可以将自己与实存事物分开;也不是基于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或量化研究。这是一种以特殊方式开展的定性研究。
基于现象学(phenomenology)、符号互动(symbolic interaction)、民俗学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和其他解释哲学的研究开始于这样的前提:要研究社会现实,研究者不能像调研一样,对预先设想的问题之个体化回应进行添加、分割与裁剪。这种进路必须触及实在的非个体形式。它不能只关注于因果解释,而应该关注于对人们委身于其中的社会境况之意义的阐明。
为什么这种研究形式对公共行政如此重要?因为公共行政大部分是在社会现实和主体间的过程中进行的:组织、团队、网络、协会、管理中心、机构等等。这些都是公共行政部门很少接触到的现实,以至于我们倾向于把它们中发生的事情称为“黑匣子”(“the black box”)。它们是我们所有人都存在的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过程和理解,但我们通常不会注意到这一点。然而,作为社会研究者,我们忽视它们会带来危险。我们无法量化和客观化的反驳并不是一个好的借口。例如,如果我们真的想提高组织绩效,那么许多最有希望的策略都与改善人际关系过程有关。想要结果吗?然后研究人们如何在团队和委员会等共享的意义空间中相互交流。
30多年前,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说道,人是“一种被嵌在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对这些网络的分析“不是一门探索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门寻求意义的解释科学”。值得注意的是,格尔茨并没有叫崇尚定量分析的经验主义者闭嘴。他仅仅指出了人类生活的一个维度,一个必须从按照自身条件加以研究的基本的维度。
难道我们在公共行政领域无法就以下事实达成一致?接触现实的方法不止一种,也不止存在一种可接触的事实;除非与其正在研究的事实不符,否则并不存在某种劣等的方法论;不同研究进路有不同的标准,所以应尊重那些沿着其他路径进行研究的学者。
我已经厌倦了一次又一次地将巨大的石块推到山顶,因为这么做仅仅只是为了让它从我身边滚下并再一次坠入谷底。让我们将西西弗斯(Sisyphus)送去沐浴,并开始构建一种主体间的现实。这类事实会为那些对全面认知公共行政工作具有严肃兴趣的学者创造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