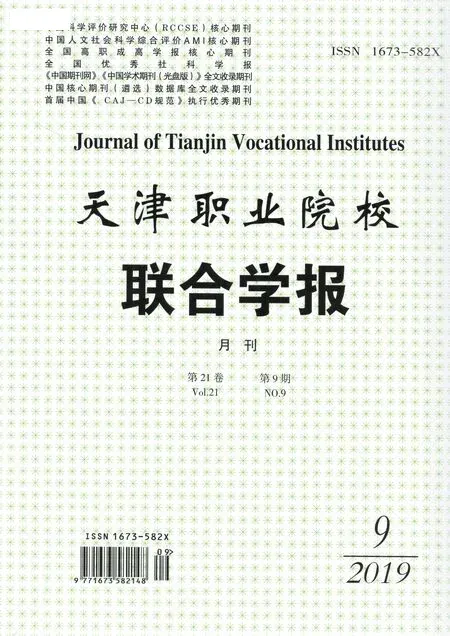帕·怀特小说中双性同体式生存理想与形态探究
(天津商务职业学院,天津 300350)
澳大利亚作家帕特里克·怀特(Patrick White,1912—1990)毕生共创作了12部长篇小说,其中,多半以女性为第一主人公,而且女性往往是生活中的强者,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坚不可摧的意志力,如洗衣妇戈德博尔得太太(《乘战车的人》)、亨特夫人(《风暴眼》)和艾伦(《树叶裙》);而男性形象或者是生性懦弱、平庸无能之辈,如亨特先生(《风暴眼》)、罗克斯巴勒先生(《树叶裙》),或者是自傲自大实则可怜、可笑之人,如伯恩纳先生(《探险家沃斯》)、亚瑟(《坚实的曼荼罗》)、巴兹尔(《风暴眼》),或以上帝、超人自诩,渴望通过精神探索,超然于世俗世界之外,最后经由受难等途径,重新认识自我有限性,如斯坦(《人树》)、希梅尔法布(《乘战车的人》、沃斯(《沃斯》)等,从中,我们看到了怀特解除父权桎梏,进而提升女性价值,最终实现两性平等与和谐、重建人之完整性的持续性努力和美好愿景。
一、父亲“缺席”与“母亲神话”解构
在男权文化体制下,男性位于“第一性”的优势地位,是历史的创造者,掌控话语权和主动性;女性则是“第二性”,是男性目光凝视下的他者和客体,应以谦恭、柔顺、沉默为美。然而,怀特有意识地弱化、消解男性,尤其是父亲形象的力量,甚至使其处于精神缺席或事实缺席的地位,以此表达对男权社会既定两性秩序的质疑和评判,为女性主体性构建和地位提升创造了空间。
怀特小说中的父亲形象多为现实生活中的无力、无能之辈,“虚弱的‘菲勒斯’成为怀特否定男性威权的一种手段。”《人树》中,作为父亲的主人公斯坦,无法与子女有效沟通,亲子关系淡漠,儿子雷最后走上犯罪道路,与父亲的无效教育有必然联系。《沃斯》中,以父辈形象出现的伯恩纳先生,是典型的物质至上主义者,在自认为是世界主宰的幻觉中,迷失了自我本性。《树叶裙》中,罗克斯巴勒先生生性懦弱,缺乏生命活力,自认为具有主宰和改造他人(尤其是妻子艾伦)的权力和能力,实则无法经受任何现实力量的抗击,因此,根本不具备成为父亲的资格,在遭遇海难后,既失去了孩子,也丢掉了自己的性命。《乘战车的人》中,希梅尔法布和杜博两位男性主人公终生没有获得父亲身份,洗衣服戈德博尔得太太的丈夫汤姆,虽然具有父亲的身份,但是没有家庭责任感和担当,最后走上不归路,处于精神和事实双重缺席状态。
在消解、颠覆象征权威意志的父亲形象的同时,怀特对“母性神话”也发起了挑战,进一步深化了对男权制社会的批判。波伏娃主张,“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被加诸于女性身上的“妻性”和“母性”,均是由整个人类社会文化(男权文化)所决定的,因为“根本不存在母性的‘本能’”。对女性而言,只有挣脱“母性神话”的精神牢笼,才有可能真正享有生命自决权,并获得与男性平等的生命价值。
怀特笔下的多数女性形象,距离男权社会所期待和要求的贤妻良母相距较远。西奥多拉(《姨妈的故事中》)、黑尔小姐(《乘战车的人》)两位女主人公始终没有进入为人妻母的角色;《人树》、《树叶裙》中,作为妻子的艾米、艾伦均未能经受诱惑,与其他男性发生了婚外关系;作为母亲的艾米,与儿女的关系呈疏离状态;腹中胎儿之死与丈夫之死,则将艾伦从妻子和母亲的身份束缚中彻底解放了出来;《风暴眼》中,亨特太太只是因为亨特先生的财富,才自主选择与之结婚,婚后不久,便争取到了自己所希望的生活状态;作为母亲,亨特太太甚至在古稀之年,凭借自身魅力,夺走了女儿的情人,母亲与儿女的关系,不仅仅是彼此疏离,甚至相互对立、仇视。
二、双性同体与“曼荼罗”式圆满之境
虚化父亲形象、解构“母性神话”,从表面上看,是作家与父母间不和谐关系的一种折射,但是,从深层次看,其中蕴含着作家对两性关系的构想。在父权制下,只有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男性的强势力量,剥离掉被强加在女性身上的传统妻性、母性观念的束缚,方能为女性潜能的释放、女性价值的提升提供可能,从而逐步消除两性间的种种不平等,重建两性和谐关系以及人之自我完整性。经过毕生的探索,怀特逐步将双性同体式生存方式确立为实现两性和谐的可行路径,并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引领现代人走向曼荼罗式的圆满之境。
两性和谐乃至双性同体观念古已有之。“双性同体”代表着人类精神上最初的浑然完整的圣洁状态。在远古神话时代人类的原始思维和意识中,宇宙万物和人类的创造即是由两性通过合体形式共同完成的,人们所虔诚崇仰者也多为双性同体之神。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5)提出了人类最初本是半阴半阳的观点,并以此解释男女之间恋爱和结合倾向的根源:人被主神宙斯分为单性别的两半,他们渴望重新结合、复归整体。苏格拉底(前470-前399)也认为,人起初是圣洁的,本无性别之分。
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1856-1939)主张“每一个人都是自己性别和相反性别的气质混合体,不管他的外在生物特征是什么”;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提出了著名的“阿尼玛”(anima)和“阿尼姆斯”(animus)理论,用“男性的女性意向”和“女性的男性意向”,说明人类先天具有双性化的生理和心理特点。
怀特并未明确提出“双性同体”的主张,但是在自传意味极强的小说《特怀旁的故事》中,他通过主人公埃迪之口,表达了自己对人身上兼有的异性特质的理解:“真正的友谊——如果还有什么完全真正的东西的话,当然是在友谊方面——来自于男人身上的女人特性和女人身上的男人特性”,并在其自传《镜中瑕疵》中指出,“澳大利亚人性格中那一点微妙之处在于,女性中蕴含着男性本能,而男性中蕴含女性本能。”此外,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1882-1941)对“双性同体”的倡导对怀特有着直接且深刻的影响。伍尔芙相信多元性是人类的本质特征,并提出了摒弃性别歧视、超越性别对立的“双性同体”观。她认为,世间不存在纯粹的男性与女性,男性在气质和思维方式上或多或少地杂有女性的特征,反之亦然:“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有两个力量支配一切,一个男性的力量,一个女性的力量……最正常,最适意的境况就是这两个力量在一起和谐地生活,精神合作的时候……只有在这种融洽的时候,脑子才变得肥沃而能充分运用所有的官能。”而以双性同体者为主人公的小说《奥兰多》,可以说就是伍尔夫实践自己主张的一个具有创造性的大胆尝试。在英国求学时期,怀特经常向其亲密的同性伴侣R推荐、甚至逼迫他去读《奥兰多》,由此可知,他对这位女作家及其作品的喜爱和推崇程度之深,在这种推崇之中自然包含着对“双性同体”观的认同。而产生这种认同的原因,首先在于同性恋倾向使他同时具备了男女双性气质,以及从双重视角思索和洞察世界的能力,较易接受双性同体观。其次,更为更深刻的原因在于,怀特对实现两性和谐,进而重建人之完整性即“曼荼罗”之境,有着自觉且执着的追求。荣格将“曼荼罗”视为心理完整性的原型与象征。怀特受荣格思想的影响,坚信确实存在着曼荼罗式的“完整”和“圆满”,并借“曼荼罗”来表现人与宇宙万物间的整体关系,表现人身上存在的各种复杂矛盾性之间的和谐,并将对“曼荼罗式圆满”境界的追求贯穿其生命和艺术创作始终。换言之,双性同体是怀特对人之完整性的一种理想化构想,也是作家为现代人走向圆满之境提供的一种可能性路径。
三、怀特式双性同体的表现形态
在怀特的小说中,具有双性化特质的人物形象为数不少,但是,怀特在塑造双性化人物形象的过程中,先后采取了不同策略。具体而言,作家主要通过塑造“生活在(自己)身体里的爱侣”、同性/异性双胞胎形象,乃至能够自由切换身份的双性人等方式,表达了对双性同体式生存方式的认同和追求。
(一)两性互为“生活在(自己)身体里的爱侣”
在怀特早期作品《姨妈的故事》中,作为女性的西奥多拉因长有胡须,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男女共体性,但此时,作家对双性同体的探索是初步的。在小说《沃斯》中,作家对双性同体的思考和表现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小说男女主人公沃斯和罗拉的精神成长同步发展、遥相感应、彼此支撑、互为补充,共同经历了自我圣化、受难以及自我超越的三个阶段,最终对人在天地间的本体性地位,即“人是斩了首的上帝”有了深刻体认。小说最后沃斯被土著人斩首,罗拉在经过以放血为象征的斩首仪式后,继续生活了下去。在怀特笔下,如沃斯所宣称的,罗拉是“生活在(自己)身体里的爱侣”,是另一个沃斯;而沃斯从本质上说,也是以另一种形象出现的罗拉,因而,他们各自是“本初的精神双性同体的一半”。
(二)双胞胎式双性同体
在《坚实的曼荼罗》中,怀特塑造了一对特殊的同性双胞胎兄弟。哥哥沃尔多个性的核心是怨憎与恨,而宽容与爱则是弟弟阿瑟的本质特性。兄弟二人在日常生活中朝夕相伴、形影相随,既相互排斥又彼此依赖、共存共亡,表明,他们只是形象化和夸张化了的一体两面的存在体,根本不可分离。怀特如此安排主人公的命运并非偶然,而是源自他对人性和谐与完整的执着追求。如前所述,在作家的理解中,曼荼罗隐喻着统一的趋势和整体的意识。他将实现曼荼罗境界的希望寄托在爱与宽容之上,包括与自己相对立的一切,因此,最理想、最完美的状态是沃尔多、阿瑟两种存在方式的共在与统一。
《风暴眼》中的亨特姐弟是怀特塑造的一对异性双胞胎。亨特姐弟在母爱缺失以及物欲横流的世界中迷失了自我身份,当得知母亲病重后,回到了家乡库杰里。虽然他们回乡的直接目的是获取遗产,动机卑劣,但是作家暗示我们,姐姐多萝茜的虚荣和贪婪在某种意义上源于她对“精神上的父亲”的追求;弟弟巴兹尔在潜意识中,则“一直不自觉地希望看到某种生命的永恒状态”。因而,他们的返乡行为就具有了深层的内涵:回归故里、回归童年,即是对自我完整性的追寻,对生命个体的本真身份的追求。此外,亨特姐弟对病榻上的母亲的冷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作谋杀母亲的一种表现形式,而正如克里斯蒂娃在《黑色的太阳》中所主张的,“杀死母亲是我们个体化的必由之路”。亨特姐弟之所以选择“杀死母亲”,并在父母床榻之上发生乱伦行为,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失去母亲或者不曾得到母爱的孩子最终只有回到母亲身边从生命之源中重新汲取力量,才能获得对自己的爱,最终拥有自我的力量。”因此,他们选择了回到新生命开始的地方,回到象征意义上的母性子宫,在两性之爱与结合的过程中,重新构建自我的完整性:“在梦里,他们要求成为双胞胎,我(亨特太太)听到他们在我肚子里呼喊——他们骂我,因为我阻止他们互相爱恋”。
(三)性别身份的自由切换
《特怀旁的故事》塑造了一个具有双性同体特征的人物特怀旁。“特怀旁”的英文拼写由Twy和born两部分组成,意即两次出生,隐喻主人公的双性恋。小说中,兼有男女双性意识特征的主人公,先后以两种性别身份分别扮演了三种不同的社会角色:老年希腊富商的年轻夫人、澳大利亚农场看管羊群的佣工以及妓院鸨母。尽管从表面上看,主人公的生命历程颇富传奇性,性别身份的转换似乎不可思议,但事实上,在“不可思议”的传奇故事的框架之内,深蕴着作家本人极其坦诚和深刻的人生态度与思索。在毕生创作的所有作品中,《特怀旁的故事》是涉及作家自身经历最多的一部。怀特青少年时期的两次主要经历——中学毕业后,在澳大利亚牧场做帮工以体验生活,以及二战前后在伦敦的生活,甚至他与希腊人曼诺利的伴侣关系在主人公身上均有所体现。可以说,特怀旁在不同身份之间的抉择和对生命完整性的追寻,正是作家在身份认同问题上,基于自身特点及现实社会特征,所做出的严肃思考与探索的一种文本折射。
跨越性别界限,寻求两性的和谐统一,在《扮演多种角色的女人》中得到了更进一步的表现。小说中的怀特,虽然只是以女主人公格雷的编辑的身份出场,但实际上,格雷与作为编辑的怀特,乃至现实生活中真正从事小说创作的怀特本人,在精神特质上是一体的。关于“格雷—怀特”的关系,小说中有如下阐释:“我(即作为编辑的怀特)是个伟大的自我创造,当亚历克斯?格雷还是个天真的姑娘时,我就占有了她的生命,用这个生命创造了许多我所需要的形象,展现了萦绕在我内心的情感,这些情感既有文学上的,又有真实生活中的。……噢,对了,我们两个不相欠,却谁也摆脱不了谁。”此外,格雷去世后,编辑怀特直接入住格雷的寓所,占用她的床铺,格雷的女儿希尔达也如同服侍母亲一般照顾他。这一情节安排暗示出格雷与怀特之间本为一体的独特关系,二者的性别差异也由于两人生理上的异化而降低到了最小程度。尽管二者之间仍然存在着种种的不和谐,但相互排斥又相互依赖的关系贯穿始终,表明格雷和怀特虽然在不同情境中存在角色扮演上的差异,但没有本质性的差别。怀特一直在努力探求一种最佳方案,以消除两性间被本质主义思维先在化定的性别鸿沟。他在有生之年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扮演多种角色的女人》中,终于为长久困扰他的两性关系问题作出了自己的解答:彼此对话与关爱是两性关系走向和谐的有效路径,而双性同体是最完美、最理想的生存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