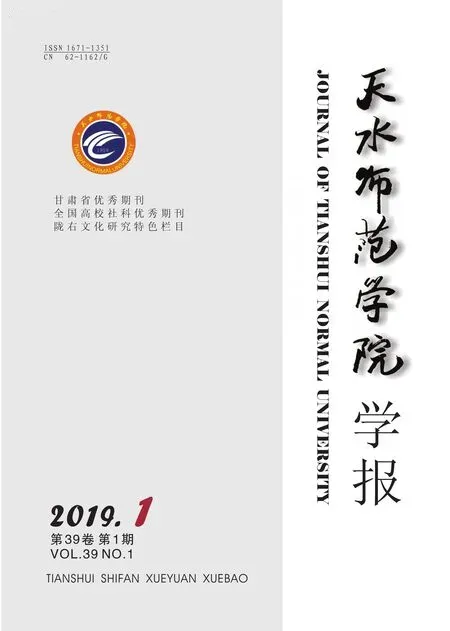古典译论“五不翻”之考辩及新解
郭亚文,郝 倩
(1.西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2.兰州财经大学 外国语学院,甘肃 兰州 730030)
直译和意译源于三国时期的“文质之争”,两者是翻译活动中长期存在并行不悖的翻译方法,而音译之法则肇始于我国东汉时期,和前两者具有同等重要的历史地位。直译之说在《法句经序》中已见端倪,而后来兼通梵汉的鸠摩罗什则主张意译,乃至玄奘提出“五不翻”之说,对五种情况下需要音译的条件做了规定性的说明,至此,直译、意译、音译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翻译方法体系。“五不翻”之说不仅对我国早期的翻译实践具有指导意义,而且对于近代文学翻译和科技翻译也影响深远,诸如梁启超、朱自清、胡适等知名学者从古典译论的角度对“五不翻”之说都做过阐释,但是由于资料有限,学界对“五不翻”之说本身的考辨依然存在不完整的地方,关于其出处和思想渊源的结论值得商榷。本文旨在通过对玄奘“五不翻”的考辩,修正和补充“五不翻”之说的出处和思想源泉,并在此基础上重新诠释其对翻译研究的启示。
一、“五不翻”之追根溯源
(一)出处
谈及音译之法,我国翻译史上最早的系统论述非“五不翻”莫属。梁启超在《佛典之翻译》一文中举鸠摩罗什和玄奘之例,论述翻译中的音译现象,认为“五不翻”理论最早见于南宋周敦义所撰写的《翻译名义序》,[1]曹仕邦在1979年通过考证指出“五不翻”理论最早见于南宋法云所著的《翻译名义集·十种通称》的“婆伽婆”条中,周氏不过节引而已。[2]
周敦义的引文对原文有删节,如将“阎浮树”误写为“阎净树”,后来梁启超引文对此做了修订,但是却删掉了说明性文字。曹仕邦虽在1979年就提出了对“五不翻”理论出处质疑,但是却没有引起学者的重视。方广锠曾在2006年的《玄奘“五不可翻”三题》一文中列举了大陆学者误引“五不翻”出处的几个例证,[3]如马祖毅[4]在《中国翻译简史》、杨廷福[5]在《玄奘论集》等中提及玄奘“五不翻”时均称其出于周敦义《翻译名义序》。笔者也发现王秉钦[6]在《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汤用彤[7]在《隋唐佛教史翻译之情形》中提及“五不翻”时也是引用周氏的《翻译名义序》,王宏印[8]虽然在《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从道安到傅雷》中比较了大亮法师和玄奘“五不翻”理论的异同,却未指出大亮的“五不翻”实则非其一人所立。
曹仕邦和方广锠的考证似乎给玄奘“五不翻”之说的出处盖棺定论,但是根据现有史料记载,前者对于玄奘“五不翻”之说最早出处的说法还是存有疑点。根据笔者的考证,唐末僧人景霄[9]早在其大作《四分律行事钞简正记》卷二中就提到玄奘的“五不翻”之说,在此基础上他还提出了自己的“正翻”和“义翻”理论。那么景霄是何许人也?根据现有资料,景霄的生卒年已难考证。《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中是这样记录的:
景霄,五代时僧。台州丹丘人,俗姓徐。性严毅,寡与人交。住金华白华山,奖训初学。著《简正记》二十卷,日价益高。吴越钱镠召住临安竹林寺。天成二年,请于北塔寺临壇。终住杭州真身宝塔寺。
由此我们可以通过考证“吴越钱鏐”和“天成二年”来判断景霄所在的年份。钱鏐(852~932年)是吴越国武肃王,钱塘临安(今浙江省临安县北)人。唐末节度使,吴越国建立者。在位26年,病死,终年81岁,葬于今浙江省萧山县茅山。而上文中提到的“天成二年”指的是927年(农历丁亥年),据此可以判断景霄和钱鏐为同时代人。
而《翻译名义集》为南宋平江(治所在今江苏苏州)景德寺法云所编。旧刻依原稿分为七卷,首有绍兴二十七年(1157)周敦义序及作者自勉短文。
由此可见景霄早在公元927年之前就在书中提到了“五不翻”,比法云的记载早了230多年。可是学界言及“五不翻”之说必称其最早见于周敦义的《翻译名义集序》或是宋代法云所著的《翻译名义集》,忽略了景霄的记载,此实为译界之憾事。诚然,景霄距离玄奘(602~664年)的时代也有两百多年,这期间肯定有学者提到该理论,只是由于资料的缺失,还有待后来的学者继续考证。但同时还需要指出的是,若从学术规范的角度来讲,此种做法的确有失严谨,但引用者倘若未删改原文文字,对于讨论“五不翻”而言,则无实质性的影响。
(二)渊源
“五不翻”之说是音译的系统概括,影响深远。那么“五不翻”是否为玄奘首创?我国佛经翻译历史悠久,在佛经翻译实践中,音译之法应用甚广,难道之前就没有关于音译的系统理论吗?杨廷福在《玄奘论集》中指出玄奘在实际翻译中,基于音和义的问题,在广亮法师“五不翻”的基础上,提出了“五不翻”论。这里的广亮法师实为广州大亮法师。[5]曲军锋在《玄奘法师在翻译事业上的贡献》一文中称:“广州大亮法师曾立“五不翻”。……(玄奘)法师在自己多年的翻译实践中,又提出“五种不译”的经验总结,比广州大亮提出的“五不翻”更加完备”。[10]这说明“五不翻”的翻译思想并非玄奘首创。方广锠通过考察隋灌顶撰《大般涅盘经玄义》,发现“五不翻”之说也非大亮一人所立:[3]
按照灌顶《大般涅盘经玄义》的记载,南北朝、隋初有五家主张对“摩诃涅盘”一词采用音译,广州大亮只是其中一家。因此,说广州大亮立“五不翻”,恐怕是误读灌顶《大般涅盘经玄义》的结果。
可惜灌顶并未提及其余四家,据现有史料也很难考证。但由此可推断,“五不翻”之说非玄奘之前的大亮所立,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灌顶做了总结,后经玄奘之手使之系统化,成为我国佛经翻译理论史上影响深远的一种思想。
二、五不翻之新解
“五不翻”非指五种不翻的情况,而是指五种音译的原则。
(一)“秘密故”
“秘密故”是指经书翻译中有许多具有神秘色彩的词语,如果意译成汉语,则神秘之意顿失,因此需采用音译的方式,保留其梵文的发音,以使读者在诵读时有所感悟。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由于诵经口耳相传,音译的文字基本保留古音,与现代发音有很多不通,如“陀罗尼”不读tuoluoni,而读作talani,“日”读音应为zi.
咒语一般含有驱邪、避凶、趋吉之意,有的甚至含报复、报仇和泄愤等损人利己之意。翻译咒语时自然不能从心所欲,因此音译成了最好的选择。这样可以使信众在反复诵读咒语时感受咒力的加持(能量场),体验真言。如果将咒语意译,则会让读者束缚于文字语义,多一层困惑。由此可得,关于经书中神秘色彩词语的翻译,其根源在于人们对语言的崇拜,持咒语者相信长期诵读咒语如同掌握了开启智慧之门的钥匙,也是由于他们相信语言有种神秘的力量,可对物质世界和肉身产生影响,引起感应对象的变化。而语言作为音形义和文化的结合体,如果改变其读音,则会影响语言的效应。
任何一种语言都有其独特的发音,具有独特的魅力和感应力,日常的翻译中也有神秘色彩的词语出现,比如每种语言当中都有人类模仿宇宙天籁、自然万物原音以及具有独特文化色彩的词汇,有时候音译也能保留其语言本身的名族文化特点,推动文化多元化的发展。如汉语词汇中的人名、地名、商标名(莫言Mo Yan,贵州Guizhou,金利来Gold⁃lion)、文化空缺词汇(阴阳Yin and Yang,风水fengshui,道Dao/Tao)等莫不如是。
(二)“含多义故”
“含多义故”指的是语言中一词多义的现象,意译容易造成误解或原意的缺损,因此选择音译诚为上策。
英国学者奥格登和理查兹在1923年出版的《意义的意义》中提出“语义三角”理论,从而构建起传统的语义学模型。书中提出的语义三角理论是公认的关于意义的理论。该理论认为符号、概念和所指物三者处于一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关系之中。它强调语言符号是对事物的指代,指称过程是符号、概念和所指物发生关系的过程。英国语言学家杰弗里·利奇(Geoffrey Leech)[11]将语言符号的意义划分为七种不同的类型,分别是:概念意义(conceptualmeaning)、内涵意义(connotativemeaning)、社会意义(socialmeaning)、情感意义(affectivemeaning)、联想意义(reflectivemeaning)、搭配意义(collectivemeaning)、主题意义(thematicmeaning)。索绪尔[12]也注意到语言符号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关系。他在把研究重心调整至共时语言学的同时,并没有忽视考察历史、地理和文化等因素对语言的历时作用。
由于语义和符号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符号、概念、所指相互作用,研究语义必须兼顾其共时和历时变化,考虑到其所处的各种语境,所以语义永远不是一个静态的结果,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鉴于以上原因,几乎所有的语言中都存在一词多义的现象,而对于一词多义的翻译,不存在所谓的普遍法则。“五不翻”原则在翻译实践中可以降低原语语义的模糊性,保持权威性,既能解决语义的含混,又能使原文不被曲解保持其权威,成为翻译“含多义故”的不二之选。
(三)“此无故”
“此无故”指的是语言对应中的词汇空缺现象。词语文化内涵的不对应形成语言之间的文化空缺现象,出现了大量的“文化空缺词”。“所谓文化空缺词指的是只为某一民族语言所特有,具有独特的文化信息内涵,既可以是在历史长河中逐步形成的词,也可以是该民族独创的词。”[14]翻译不仅是语言意义的转换,更是文化意义的交流,由于不同民族的历史、地理和文化环境迥异,语言不可能完全对应,翻译中的“词汇空缺”并不鲜见。音译和直译可以归为异化策略,例如中国文化中独有的“天干地支、阴阳五行”等,由于在英语中的文化形象完全空缺,可以直接采用音译加注的方法。
(四)“顺古故”
“顺古故”指的是翻译中的有些词汇随着历史演变和译者能力的提升虽然可翻,但是其音译由来已久,已被广为接受,所以保留音译,此所谓约定俗成。
《荀子·正名》:“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这说明“名与实”并无内在的联系,形式和意义只是约定俗成的结果。翻译不是一时的灵感涌现,而是在前人不断累积基础上的深思熟虑。笔者认为,对于约定俗成的“名”,译者要给予充分的尊重,不可为了哗众取宠的目的随意改动。因为对于翻译而言,抛弃经过历史验证,被人们广为接受的说法,徒增一些译者自认为精妙的词汇,造成译界理论认知的困惑,并无益于翻译学科的发展和翻译实践的推进。但是同时也要认识到,约定俗成并不意味常用的“名”就是亘古不变的真理。语言中的约定俗成,除了久经考验的真理,由于历史、地域和文化的局限,也难免会出现一些“以讹传讹”的约定俗成。僧睿(约371~438年)认为:“如果译文中名实不谨,则对经义的理解将南辕北辙。”所以,“首先是详细地理解原意,并反复考虑汉译名之是否对等(交辨文旨),然后才能正确定名(审其文中,然后书之)”。[15]张顺生认为“只要译语中不存在某种说法,有时甚至误译也能够约定俗成”。[16]因此真正的尊重不是不加分辨地全盘接受,而是秉着求真务实的精神,勇于考辩,追求语言使用中“名”的正确性、合理性。
维特根斯坦认为:“意义寓于用法之中。”[17]我们要抛弃语言意义的静态观,追求语言意义的动态观,因此对于“名与实”的关系考辩,要随着语言的应用不断深入下去。这就要求我们一代又一代的翻译工作者不可尽信古人之言,要带着批判的眼光审视语言中的“约定俗成”,不断推进翻译实践,丰富翻译理论成果。
(五)“生善故”
“生善故”指的是采用音译的方式来保留原语的特殊效果,即原文的庄重典雅、真言的至高无上等效果。比如“般若”所指的意义不仅涵容智慧,而且超越了智慧,因此采用音译之法,以避免其意义的流俗。
这些音译现象的背后,其实都离不开译者和目的语读者对于原语符号、原语文化的尊重。新的词汇最初被翻译时,译者或多或少对原语和原语文化带有一种崇敬的心理,为了不减损原语的特殊效果,而采用了音译之法。这种尊重的背后其实是译者和目的语读者对于强势文化的“崇拜”心理。我国早期的佛经翻译是国人对强势的印度佛教文化的膜拜,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则是国人对于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推崇,而晚清至民国的翻译显然是国人出于对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高度认可。至于改革开放以后的翻译,随着汉语文化对外的大量推介,逐渐体现出国人对待西方科学技术和民主思想的平等心态,同时也反映出西方人对日益呈现出强势姿态华夏文化的尊重和接受。
三、“五不翻”理论的启示
虽然“五不翻”之说距今已有一千四百多年的历史,但笔者认为其对当下的翻译研究有如下启示意义:(1)我国早期的翻译史是我们翻译研究的宝藏,因此需要不断深入进行文献考古,由于过去的研究资料不够全面,前人的研究可能会有疏漏之处,因此,我们不可盲从权威,而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继续进行大胆细致的文本挖掘;(2)“五不翻”的应用可拓展到多个翻译领域,玄奘本人也是中国翻译老子的第一人,[18]可见他的翻译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中国哲学思想的影响,因此“五不翻”之说对于旅游[19]、科技、文学翻译也有指导意义;(3)翻译研究要历时和共时结合。翻译是动词不是名词,是过程不是结果,因此对于历史上翻译大家的理论研究要跨越时空的局限,但同时也不能完全以现代人的目光去品鉴。对古代翻译家所提翻译理论的评价要结合其本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翻译实践活动的全貌,不可断章取义,横加指责,也不可推崇备至,容不得反面意见,而是要客观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