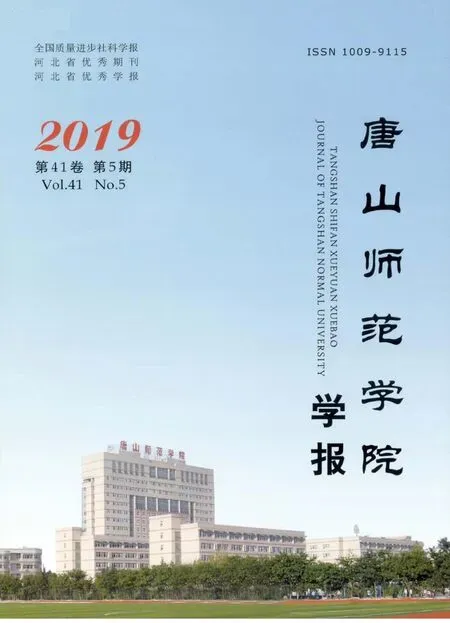论君特·格拉斯《猫与鼠》中的多重反抗
王宏健
(天津师范大学 中文系,天津 300382)
《猫与鼠》出版于1961年,是德国著名作家君特·格拉斯“但泽三部曲”中的第二部作品。以往对《猫与鼠》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猫与鼠”象征意义的解读[1],马尔克的悲剧人物形象的分析[2]和对社会历史、战争记忆及个人身份认同的批判[3]等方面。从另一个角度看,作品叙述的那段历史和当时的社会现实对人和人性造成压迫,必然会激起人的反抗,组成“压迫——反抗”这组二元对立的结构。面对“压迫”的些许“反抗”虽然微不足道,但进一步深化了批判的主题和意蕴,传达了君特·格拉斯所倡导的文学观,也暗含着作者对于荒诞和启蒙的思考。
一、“猫”与“鼠”的个体反抗
《猫与鼠》的“反抗”由个体行为开始,因此有必要分析作品中人物的反抗行为及其含义。约阿希姆·马尔克是《猫与鼠》的主人公,作为战争年代的德国的一个普通青少年,他遭受了身世、身体、和思想三种形式的压迫。对此,他的反抗行动通过叙述者皮伦茨的书写得到表现,构成了整部作品的情节和主干。
1.家庭原因造成的反抗
马尔克生活在没有父亲的单亲家庭中,作为独子,他是母亲和姨妈的寄托与骄傲,但是在他的成长中始终缺少父亲这一原始的榜样和崇拜,他的内心必然有一种孤独感。再有,与当时弥漫于学生间的狂热的战争理想不同,马尔克的理想非常简单和普通,“他好不容易学会了游泳;他毕业后想到马戏团当小丑,为人们逗乐”[4,p21]。马尔克是最后学会游泳的,与“笨拙”相伴的是与周围人格格不入的理想,而这难免会在学生之间受到嘲笑。作为成长中的青年人,他在身世上得不到来自家庭的帮助和支持,又因为自身普通的性情在当时的环境中与其他同龄人相左,得不到来自学校和朋辈的认可和理解,反而招来嘲笑与鄙视。这种先天和原生的“压迫”,使马尔克成了一个边缘人物和“集体压力下的一个孤独者”[4],由此开始了他寻求身份认同的“反抗”。从多次表演潜水打捞上来沉船中的物品给皮伦茨和同伴们展示,到对战争荣誉象征的奖章的迷恋和寻求,“原来马尔克摸上来的是一枚铸有毕苏斯基元帅肖像的奖章。此后两周,马尔克一门心思地寻找奖章”[4,p16-17]。奖章成为马尔克实现自身认同的载体,他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反抗平凡的身世和性情带给他的不受重视和不被认可,是一个处于集体压力下身心饱受煎熬的孤独者寻求他人认同的个人反抗的悲剧。
2.身体原因造成的反抗
马尔克由于自己具有畸形怪异的硕大“老鼠”喉结而遭受歧视和嘲笑,进一步加剧了他与自我认知的隔阂。为了掩饰这种缺陷,他做出了一些反抗行为,比如经常在喉结下方挂着一把改锥,以求分散人们对他喉结的注意,后来改成佩戴流苏,想为他的喉结带来一些好处。然而这种凸显自身价值的替代物无法长久地实现自我认知。马尔克为了能够继续与众不同、引人注目,把得到战争荣誉“糖块”——铁十字勋章作为自我认知的实现形式,为他悲剧性的反抗结果埋下了伏笔。从词源上看,喉结的德语词Adamsapfel与英语词Adam's apple相近,汉语意为“亚当的苹果”。人类的祖先亚当由于偷吃智慧树上的果子在伊甸园犯下罪孽,喉结即是人不得不继承的一种原罪遗产的象征,想摆脱或是掩饰都是徒劳的,因为“从第一个人至今,不和谐、痛苦、病魔和死亡代代相传,成了人的命运”[5]。马尔克的“老鼠”与这种原罪相对应,它的畸形和怪异也突出了这种罪孽的沉重。尽管马尔克采取各种方式去掩盖他的喉结,逃避和反抗命运之中“猫”的追逐和迫害,但他无论如何也找不到解决的方法。他的反抗是徒劳的、无力的和悲剧的,但却是必要的。像皮伦茨所说“海面上没有猫,但是老鼠却在逃窜”[4,p162]。马尔克的反抗也必将如同“猫捉老鼠”一样一直持续下去。
3.热衷于战争和荣誉的反抗
一方面,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达对这种主流的价值取向的追求和认可;另一方面,在周围狂热的战争氛围中,他实现自己价值的行动却保留了一种冷静和谨慎的态度。皮伦茨观察到在众人疯狂地对讲台上海军上尉的战争宣传鼓掌呐喊时,只有马尔克矜持地坐在那里。在这里,马尔克对自我身份认同的反抗态度与他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产生了矛盾。习惯了从自己与他人的不同中寻找自我价值实现的马尔克,由于置身战争狂热氛围中,即使面对使他感兴趣的战争话题,也会表现出一定的排斥和抗拒。在征兵报名时,“马尔克没有报名。他不仅再一次破了例,而且还说:‘你们大概是头脑发胀了!’”[4,p93]由于锲而不舍地追求与其他人截然不同的价值认同,使他得以暂时跳出集体的盲目和无意识,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对战争行为本身的反抗和反思。马尔克的反抗行动是逐步深化的,最后变成对反抗行动自身的反抗,由单向的“求同”反抗走向复杂的“求异”反抗。
4.《猫与鼠》的叙事者皮伦茨的“反抗”行为
尽管他也是排斥马尔克的集体的一员,但是他对于马尔克却有着一种特别的态度,甚至可以称作是友谊。他到圣母院辅助古塞夫斯基司铎是为了去看马尔克在圣母玛利亚面前真诚的忏悔,他对于马尔克从沉船中打捞留声机给大家放音乐的行为显示出恭敬和钦佩之情,他在文中反复称马尔克为“伟大的马尔克”,为马尔克设法弄到战时限量供应的蜡烛,和校长克洛泽说情允许马尔克在礼堂演讲,最后协助马尔克进行逃亡。在集体对一个“孤独者”的歧视和压迫下,皮伦茨用自己的反抗呼应和支持了马尔克的反抗。皮伦茨作为叙事者对马尔克经历的记述,其实也代表了作者君特·格拉斯的态度,“我现在真该把自己的外壳涂上一层洋葱汁,让它也像我当初一样体会一下那些年里污染整个德国、西普鲁士、朗富尔区、东街、西街并且祛除了弥漫于各地的尸臭的洋葱味”[4,p114-115]。洋葱在格拉斯的作品中是一个重要的概念,是格拉斯本人经历过的那段黑暗历史的象征,剥开洋葱代表把历史和真相抽丝剥茧进行展示。《猫与鼠》在这里通过书写一个具有典型性的受集体迫害的普通德国青少年的命运,让人们对战争、历史、创伤和罪责保持一种反思的态度,避免遗忘,这是皮伦茨和他的代表君特·格拉斯反抗性书写的深层含义。
二、虚构和真实的历史反思
无论是马尔克对自我身份认同的反抗,还是皮伦茨对马尔克的反抗行为及其命运的反抗性书写,都包含着对二战德国那段黑暗历史的回忆和思考。《猫与鼠》所要表达的反抗主题通过揭露和批判历史的形式得到表现。
君特·格拉斯在他的谈话录《启蒙的冒险》中说道:“当我回想起《铁皮鼓》和《狗年月》时,我还会为50年代的那种疯狂地歪曲历史,疯狂地压制人们的思想意识的做法而恼怒,为人们称德国民族是个可怜的、被诱惑的民族的论调而生气,而且这种论调还不胫而走,在当时社会上颇有市场。”[6]《猫与鼠》作为“但泽三部曲”的第二部,夹在《铁皮鼓》和《狗年月》之间,也是基于50年代盛行于联邦德国的对二战历史罪责的故意淡化、遗忘、甚至是美化的反拨。《猫与鼠》作为君特·格拉斯与反历史潮流抗争的武器,以主人公马尔克的反抗和作者的“传声筒”皮伦茨的叙述,把历史的真实和残酷揭露出来,以求把民众从蒙昧中解放出来,实现思想和道德的启蒙。
《猫与鼠》与“但泽三部曲”的另外两部《铁皮鼓》和《狗年月》除了以反抗性的书写反思战争罪责和但泽小城的历史遭遇之外,君特·格拉斯还指出它们的第三个共同点,即对真实概念的表达可以通过想象将可见的事实和可虚构的事物相替换来实现[7]。对罪责的反思和对真实概念的诉求贯穿了《猫与鼠》和君特·格拉斯其他所有的小说创作。不同于传统的反思历史作品对战争和创伤的直接描写和揭露,《猫与鼠》中君特·格拉斯的创作通过讲述一个发生在当时的“童话”模式的故事,实现对真实概念的拓展和启蒙的使命。
君特·格拉斯从德国浪漫诗人那里继承了拓展真实概念的艺术观。因为童话包含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来源于现实而又上升为艺术化审美化的现实,所以童话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能够创造更为高级的真实,为后人打造一个继续生存的空间[8]。猫和老鼠的故事在《格林童话》中有所提及,君特·格拉斯把它创造性地用于《猫与鼠》之中。“猫”即是作品中纳粹军国主义支配下社会、学校、学生的象征,“鼠”代表了马尔克这个在战争氛围里平凡普通、寻求身份认同、不断逃避的孤独的反抗者。“猫捉老鼠”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自然传统,通过童话形式得到定型,内化为一个民族集体性的文化记忆。“鼠”马尔克对“猫”集体的压迫表现出逃离和反抗,活化了这个传统的童话故事,“鼠”预示着德国千千万万的“马尔克们”的命运,“猫与鼠”成为二战德国社会压迫与反抗的悲剧写照,君特·格拉斯的童话书写使“拓宽了人的生存的真实成为可能”[9]。由此,君特·格拉斯不仅从德国浪漫诗人那里汲取了经验,还借助童话衍生而来的想象拓宽了真实概念,使《猫与鼠》中的“反抗”通过他创造性的写法把历史真实和现实认知进行了补充和协调。
《猫与鼠》中反抗性的书写还通过叙事者皮伦茨的设置得到反思历史和揭露创伤的目的,通过虚构和自白明确了真实概念的范围。批评界常有人提到君特·格拉斯的叙事是虚构和现实的交织,君特·格拉斯借皮伦茨之口说出这部作品,无论是故事情节还是其中的人物,都是假设和虚构的,给读者消解了直面真实历史所带来的压力。然而君特·格拉斯不满足于讲述一个虚构的故事,他把自己投射到皮伦茨的身份上,将真实从虚构中和盘托出。君特·格拉斯在《剥洋葱》中说:“这是不愿张扬的耻辱,就在那个稀松平常、随手可取、能激活记忆的洋葱的第六层或第七层皮上。我写这种耻辱,写这种尾随着耻辱而来的内心羞愧。”[10]君特·格拉斯本人就是战争的经历者,扮演了皮伦茨的角色,是追逐“马尔克们”的“猫”,也承担着战争带来的罪责,一定程度上也曾认可德国当局对历史的逃避和掩饰。这种耻辱折磨他的内心,激起了一个有良知的作家理性的反抗,君特·格拉斯虚构的《猫与鼠》故事包含了他本人在战时和战后的心路历程,激起了那一代“猫”与“鼠”们的共鸣,《猫与鼠》的反抗性通过君特·格拉斯超越历史真实而虚构真实,把对历史、战争、创伤和罪责的反思推向了高潮。
三、荒诞的感知和启蒙的反抗
君特·格拉斯的小说创作广泛地运用了虚构的艺术手法,而虚构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则会呈现出某种令人感到荒诞不经的表现形式。从第一部小说《铁皮鼓》开始,这种“荒谬”贯穿于“但泽三部曲”之中,在《猫与鼠》里尤为明显。无论是虚构的叙事者皮伦茨夸张的描述、主人公马尔克传奇的人生经历和对圣母玛利亚超乎寻常的虔诚崇拜,亦或是对“猫捉老鼠”概念的现实戏拟,都让人产生荒诞之感。君特·格拉斯在《猫与鼠》中创造的荒诞不单是艺术表现的手法,更与他本人的思想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荒诞是作品中人物生存状态的起点,君特·格拉斯让人体验荒诞并与之进行反抗和斗争,最后获得文学启蒙的现实意义。
分析《猫与鼠》中的荒诞和反抗,首先要认识君特·格拉斯“荒诞”艺术和思想观念的形成。“荒诞”(英语absurd,德语das Absurde)也译作“荒谬”,作为一个哲学术语,源于拉丁语词absurdus,是一段自相矛盾、不合逻辑的论述,可以说是一种悖论。存在主义哲学为其明确了内涵,它的先驱尼采并不试图弥合人与世界之间的鸿沟,人追求理性和世界的非理性之间的矛盾成为人的生存状态,这种状态就是“荒诞”[11]。加缪继承了尼采的观念,进一步提出:“从智力上看问题,我可以说荒诞不在于人(如果这样的隐喻有意义的话),也不在于世界,而在于两者的共同存在。眼下,荒诞是统合两者的唯一联系。”[12]人对单一性和透明性追求的欲望与世界的不可捉摸性之间的矛盾无法调节,而理性对这种状况的认识就是荒诞,进一步表现为人对自己生存意义的追问,判断人生究竟值不值得活,这是加缪思考的荒诞哲学的根本问题。生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浩劫中的德国青年,经历着战火的洗礼、纳粹军国主义思想的荼毒、种族屠戮、信仰和自启蒙运动以来的乐观主义精神的丧失。君特·格拉斯本人就是这些迷茫和困惑中的青年们的一员,当理性、信仰和对德国时代与社会的认识被战争的阴云笼罩,他所能感受到的荒诞是十分深刻的。战后,他对荒诞的体验和思考与加缪产生了共鸣,为其笔下的西西弗斯所吸引,形成了怀疑一切的观念。
君特·格拉斯在《猫与鼠》中实践了他的荒诞观和怀疑精神,他笔下的马尔克是有着荒诞体验的典型。一方面,马尔克作为一个极其普通、不起眼甚至行为和性格具有缺陷的德国青年人,在与同辈人的对比中被当作异类,他对世界的认识首先转化成对自身价值和自我认识的寻求。此时,上至国家下到学校的纳粹战争宣传给了马尔克证明自己的机会,狂热的战争热情和荣誉野心成了马尔克对自身的价值认同,这种非理性充斥在马尔克和那一代青年人之间。马尔克即使得到了梦寐以求的荣誉,衣锦还乡,还是无法实现自我认识的最高诉求——去学校礼堂作报告,凭借理性获得认可最终成为徒劳无功的泡影,荒诞由此而生。另一方面,马尔克对自身荒诞的状态也有一定的认识和反抗,无论是没有像一众学生一样狂热地给讲述战争经历的少尉鼓掌、面对驶出去海湾参战的潜艇挥手致意,还是上文提到的破例没有参军,都是源自他通过战争的非理性认识自身时产生的偏差和某种怀疑。对于这种荒诞,马尔克还寻求另一种形式的反抗。他不相信上帝和他的代言人,宗教并不是他用来反抗荒诞状态的武器,马尔克因不满生存状态的孤独的个体反抗,对爱、理想和自我认识的同一性的追求,内化为对圣母玛利亚近乎病态的偶像崇拜,反复在文中出现。就像加缪笔下西西弗斯的生存状态,反复把滚落的巨石推到山上,并在与这种荒诞现实的反抗中找到自身的价值和存在的意义:“反抗不创造任何东西,表面上看来是否定之物,其实它表现了人身上始终应该捍卫的东西,因而十足的成为肯定之物。”[13,p21-22]圣母玛利亚就是马尔克所要捍卫的东西,在他受到荒诞现实和荒诞集体迫害时,为他提供了庇护和倾诉的对象,成为他反抗荒诞的武器,反抗价值目标的获得成为身份认同的前提。对荒诞的体验和反抗也像“鼠”马尔克逃避“猫”、西西弗斯无止境地推石上山一样,永远没有终点。
上文提到叙事者皮伦茨是君特·君特斯的代言人,因此皮伦茨的荒诞体验也代表了君特·格拉斯的态度。首先,皮伦茨称马尔克为“伟大的马尔克”,并不时表现出崇拜之情,最后参与协助马尔克逃跑,他可以说是“反抗者”马尔克的同路人。加缪指出:“反抗并不仅仅产生于被压迫者身上,当人们看到他人成为压迫的受害者时,也会进行反抗。因而在这种情况下,他将别人看成是自己。”[13,p18]君特·格拉斯让皮伦茨从马尔克的生存体验中看到了相同的命运,尽管出身不同,那个时代中个别的德国青年多少有对于战争的迷惘、思考和追求自身价值而不得的荒诞感受。君特·格拉斯有相同的体验,通过皮伦茨的行动,倾注了自己反抗荒诞现实和荒诞命运的态度。其次,皮伦茨对马尔克表现出复杂的态度,一方面支持他的反抗行为,另一方面则是把猫放到马尔克喉结上的迫害者,他的诱导间接导致了马尔克的死亡。君特·格拉斯在《剥洋葱》出版时提到自己也曾是纳粹党卫军的一员,他对自己有集体上的身份认同。加缪认为,恶产生于人一味追求一致性的行动中,会导致无规则和混乱,人的理性面对这种恶会在心底呼唤正义。君特·格拉斯对追求一致性的“恶”有足够深的体会,战后更体验到人们自以为是地遗忘历史和粉饰太平的荒谬,他本人在《猫与鼠》中采用调侃、滑稽模仿和反讽手法对基督教表达批判态度,写皮伦茨去做弥撒只是为了去看马尔克。在这里,君特·格拉斯通过皮伦茨的行为反映出荒诞现实中“恶”的滋生和对信仰的怀疑,并要反抗随之而来的对待历史的虚无主义思想。最后,皮伦茨在文中多次表现出必须要把马尔克的故事写出来的态度,这包含了君特·格拉斯本人对待启蒙必要性的认识。青年君特·格拉斯同大多数德国人一样,在纳粹军国主义思想的环境中也曾缄默不语,对荒诞的历史缺乏反抗的意识,直至战争结束,他才认识到这是造成一直延续到战后的虚无主义的根源。他十分认同加缪笔下西西弗斯的反抗方式,把那段历史通过荒诞和非理性的行为加以展现,由此实现对理性的启蒙的目标。君特·格拉斯通过《猫与鼠》中皮伦茨和马尔克的故事,不断向人们传递认识生存的荒诞性和启蒙反抗的文学信念。
四、结语
《猫与鼠》中人物的反抗行为表现了战争中个体对于自身肉体和精神压迫的不满,其反抗的复杂性也通过对文本的分析得到揭示;个体的反抗行为必然切入历史反思的层面,把历史的真实性通过君特·格拉斯虚构性的艺术手法加以突出;历史层面的反抗源于更深层次的哲学层面,作品中人物的处境是荒诞的,认识荒诞并与荒诞作斗争是无止境的,这是君特·格拉斯和《猫与鼠》所要传达的“启蒙反抗”的观念。
以马尔克为代表的一代德国青年人是受黑暗战争历史迫害的典型,他命中注定的悲剧命运更加凸显出有限的反抗行为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君特·格拉斯通过皮伦茨的视角把马尔克的经历展示出来,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进行对历史的反思,体验那段荒诞的时光,并且反抗战后企图忽视伤痛和罪责的荒诞思维的延续,呼唤理性的复归。《猫与鼠》通过个人、历史和思想三方面反抗体系的建立,系统地传达了君特·格拉斯实现文学启蒙的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