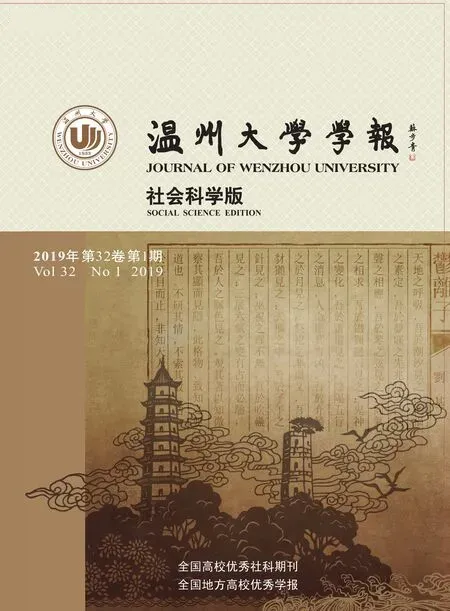随其资质 与之形貌
——叶适碑志文写人艺术探微
郑 玲,钱建状
(1.池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安徽池州 247000;2.厦门大学中文系,福建厦门 361005)
经历了北宋古文运动洗礼后的南宋时期,在欧阳修等创作大家的影响下,碑志文的创作进入一个重要发展阶段。此时,碑志文创作在遵循体制的基础上,往往能注入真性情。在此背景下,叶适继承前贤,其碑志文创作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叶适集》中收录叶适碑志文计148篇,墓主身份不一、行迹各异,有名臣良吏、文士儒生,也有布衣处士、节妇孝女,再现了12世纪末13世纪初活跃在政坛、文坛及民间的各类人物形象。叶适能根据墓主不同的身份地位、事迹功业、性格言行等方面的差异进行描写,“廊庙者赫奕,州县者艰勤,经行者粹醇,辞华者秀颖,驰骋者奇崛,隐遁者幽深,抑郁者悲怆,随其资质,与之形貌,可见文章之妙。”[1]563这种打破碑志文写作程式、力求书写法式与风格多样的行文标准,展现了高超的写人技艺。
一、以事述人:突出人物主要事迹与个性
叶适给不同的人写碑志,并非一味颂扬悼念死者、安抚宽慰家属,他以事述人,有美不隐美,写得翔赡光辉;无美不虚美,写出了人物的真实心性,再现了南宋各类人物栩栩如生的形象,大大增加了碑志文的史料含量,这种“以事述人”的写作手法值得借鉴。
(一)围绕同一历史性大事件描写多位墓主,以史写人
叶适碑志文描写人物重历史事实,以史笔写人,注重其真实性。“水心作《汪参政勃墓志》,有云:‘佐佑执政,共持国论。’执政盖与秦桧同时者也,汪之孙浙东宪纲不乐,请改。水心答云:‘凡秦桧时执政,某未有言其善者;独以先正厚德故,勉为此。自谓已极称扬,不知盛意犹未足也。’汪请益力,终不从。”[1]558求真务实,客观公允的评价而不溢美是叶适遵循的创作准则。
叶适在处理人物与事件的关系时,并非事无巨细,全部录入,往往刻意剪裁,抓大放小,注重“而又有大者”[3]319。“自淳熙后道学兴废、立君用兵始末、国势污隆、君子小人离合消长,历历可见”[1]560绍熙内禅,《宋史·本纪》[2]709-710以编年体粗线条记录此事,较简略。叶适则围绕此事件,在蔡必胜、黄度、徐谊等的墓志中均有诸多描述。《蔡知阁墓志铭》[3]319-320中,叶适用了740字详细描写绍熙内禅事件来龙去脉,孝宗、光宗父子关系、群臣“相率攀上衣裾”苦谏光宗、宰相留正无计可施、“中外讹言益甚”所导致的社会动荡、知枢密院赵汝愚等臣僚策划内禅诸事宜、嘉王接受百官拜礼等,并对墓主蔡必胜在此事件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予以充分肯定。此外,叶适在其他同涉此事的人物墓志中,补充了关于绍熙内禅的其他史料。如他在《故礼部尚书龙图阁学士黄度墓志铭》中描写:绍熙二年,黄度担任御史期间,为讽谏“光宗始以疾不过重华宫”[3]394,黄度上书谏言,谏而不听,则乞去之。在《宝谟阁待制知隆兴府徐公墓志铭》中记载:光宗内禅时,徐谊上书,“三代圣王,有至诚而无权术。至诚不息,则可以达夫德矣,愿陛下守而勿失。”[3]402皆是研究绍熙内禅直接或间接相关事件的重要史料。
叶适围绕如绍熙内禅、庆历党禁、南宋对金和战对策等重大军国大事,以史笔写人,描摹刻画了一批活跃在南宋政坛,且与重大国事联系密切的肱股之臣。叶适在描写名臣良吏类墓主时,大多采用了此种写作方式,择取墓主一生中重大的历史事件,突出墓主的身份与主要性格特征,“随其资质,与之形貌”。
(二)选取墓主一生的典型事迹,以事述人
叶适写人,摒弃常规墓志对仕历行实的程式化书写,紧紧围绕人物一生的主要行状事迹,巧妙剪裁、精当取舍,结合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才华学识与高尚品格,精心挑选典型事例刻画人物,彰显志主学行操守。如《郑仲酉墓志铭》专写郑噩善治狱一事,“君治狱察辨而坚明”[3]271,并通过断孟友谅二妻纠纷案件、僧人惠果诉范模诈骗案件予以阐明,读之使人信服。《宋武翼郎新制造御前军器所监造官邵君墓志铭》终其一篇,只写邵叔豹“监岱山盐场时事”。虽身居低位,仍能忠于职守的品格令人感动。叶适对此评价甚为精辟,“自名司显吏之外,碎曹猥局,无不因人废兴。其职任虽卑近,而倖门弊穴,更为深远而难治,傲胥豪客之所噬攫,官人徒缩气首肯,反得善誉,奋而自为,未尝无祸也。”[3]275通过叶适的精心刻画,一名具有身居“碎曹猥局”而勇于自任,品行高尚的古代官吏形象,跃然纸上。《舒彦升墓志铭》只写舒杲辅佐叶适自己革除铁钱法弊端一事,“教其人使择利害避就,有不及不以为罪,教之如初。所铸轮郭肉好,皆为式于后不可改,故私钱遂绝而官铸流通至今。”[3]435由此可知,彦升宽刑审虑,以善道之法趋利避害,使绍熙以来的铁钱法弊为之一除,维护了地方稳定。墓志集中展现了舒杲宽刑有量、行治有法的良吏形象。
叶适与“永嘉四灵”的关系甚密。“四灵”是生活在南宋时浙江永嘉(今温州)的四位诗人赵师秀、徐照、徐玑和翁卷,他们“皆尝游于叶适之门”[4]。在为徐照、徐玑二人撰写的墓志铭中,叶适高度评价与称许了“四灵”的诗歌创作精神和他们首倡学习唐诗之功。在徐照、徐玑二人的墓志中通篇以志主的诗歌创作观、创作风格等为主要书写内容。如在《徐道晖墓志铭》中称徐照[3]321-322:
盖魏、晋名家,多发兴高远之言,少验物切近之实。及沈约、谢眺永明体出,士争效之,初犹甚艰,或仅得一偶句,便已名世矣。夫束字十余,五色彰施,而律吕相命,岂易工哉!故善为是者,取成于心,寄妍于物,融会一法,涵受万象,苓、桔梗,时而为帝,无不接节赴之,君尊臣卑,宾顺主穆,如丸投区,矢破的,此唐人之精也。然厌之者,谓其纤碎而害道,淫肆而乱雅,至于廷设九奏,广袖大舞,而反以浮响疑宫商,布缕缪组绣,则失其所以为诗矣。然则发今人未悟之机,回百年已废之学,使后复言唐诗自君始,不亦词人墨卿之一快也!惜其不尚以年,不及臻乎开元、元和之盛。
在志文中,叶适评价徐照以寻常语入诗却意境浑成,能使读者吟叹不已,称誉有加。继而志文又叙述了徐照在诗歌创作上对唐诗的效法,对魏晋诗歌创作“多发兴高远之言,少验物切近之实”的批判。因此叶适认为,唐诗“取成于心,寄妍于物”的诗歌创作观主导了徐照的诗歌创作。叶适同时也流露出对徐照早逝的惋惜之情,认为如果他不早逝的话,诗歌成就或可与“二元”诗歌相媲美。
《徐道晖墓志铭》通篇围绕徐照诗歌的艺术成就以及他首倡唐诗的贡献而展开,文中的夸饰溢美之词,体现了叶适对墓主的肯定和赞美之情。
又如在《徐文渊墓志铭》中,叶适如此书写徐玑[3]410:
初,唐诗废久,君与其友徐照、翁卷、赵师秀议曰:“昔人以浮声切响单字只句计巧拙,盖风骚之至精也。近世乃连篇累牍,汗漫而无禁,岂能名家哉!”四人之语遂极其工,而唐诗由此复行矣。君每为余评诗及他文字,高者迥出,深者寂入,郁流瓒中,神洞形外,余辄仰终日,不知所言。然则所谓专固而狭陋者,殆未足以讥唐人也。
叶适在叙述徐玑行迹治绩之后,又重点介绍了徐照、徐玑、翁卷和赵师秀四人对近世诗歌、尤其是江西诗派诗歌“连篇累牍,汗漫而无禁”创作现状的批评态度,叶适并且认为,“四灵”在诗歌创作中,语言“遂极其工”,为唐诗的复兴作出贡献。
对徐照、徐玑诗歌创作的评价,反应了叶适的诗歌理想。“作为永嘉学派的宗主,叶适的文学思想无疑对四灵有直接影响,他既反对朱熹的贬抑唐诗,又不满于江西诗派只学老杜一家的局限,因而大力肯定四灵的复尊唐体。”[5]
大力肯定却非一味谀颂,叶适与四灵诗歌理想的终极指向并不完全一致。叶适推崇的是盛唐诗歌,对于四灵尊晚唐体,他在墓志中亦表达了遗憾之感。对徐照、徐玑二人有扬有抑的态度,闪烁着叶适诗论思想光芒,而这两篇墓志亦成为后世研究四灵的重要文献资料,尤其可以用来考察叶适与四灵之关系。
碑志文写作应当遵循“书其学行大节;小善寸长,则皆弗录”[6]叶适正是从这样的行文法则出发,一反墓志铭叙述族源、世系、行治、婚宦等固定化、程式化书写法式,精心挑选典型事迹,摹写人物主要事迹品格,使得人物主要形象更加突出。作为封建小吏,突出他们为福一方的艰勤;作为文士儒生,突出他们卓尔不群的才华学识,围绕墓主一生的典型事迹品格,以事述人。在不长的篇幅中,抓住人物的核心精神实质,于读者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三)旁见侧出,未见其传已识其人
叶适常采取互见的谋篇布局方法,将与墓主有密切联系之人的生平、事迹、功绩、才华等,写入一篇或数篇墓志中,且参错互见,彼此相补,一方面构建出墓主生平交游网络,有助于更为全面与独到地表现人物、刻画形象;另一方面,也有助于表现同时代其他相关重要人物的生平事迹等,于史料保存有较大贡献。叶适并未给王十朋作墓铭,但是在其子王闻诗墓志《提刑检详王公墓志铭》中开篇即述[3]314:
初,龙图阁学士太子詹事王公十朋,以太学生对策,请收还威福,除秦桧蔽塞之政,天子即日施用。入馆,论事益无避。为侍御史,首荐张丞相,力赞复仇,遂与张公俱去。素负大节,慕袁安、杨震为人也。时北方余学未衰,耆老先生尚多有,既闻公风声,服其行事,莫敢雁行者,故绍兴末、乾道初,士类常推公第一。嗟夫,富贵何足道哉!能以公议自为当世重轻,斯孟轲所谓豪杰之士欤!
此段文字语极简洁、洗练,寥寥数句,所包含信息量十分之多,有墓主之父王十朋为人品行、政治主张、学识素养等,看似轻描淡写,却能成为对王十朋的盖棺之论。相较南宋汪应辰所作《龙图阁学士王公墓志铭》的平铺直叙,叶适在处理谋篇布局上显然技高一筹。
在同时期文士刘夙、刘朔以及陈鹏飞的墓志中,写艾轩先生林光朝,有助于后人了解林光朝其人其事[3]302,230:
及少南以文字起,多所接纳,而江左俊秀李冲、詹左、张相、范端臣、林光朝等应其选,由是绍兴之文见矣。
二公及刍盖师中书舍人林公,事之终身。林公名光朝,莆人所谓艾轩先生者也。
林光朝(1114 - 1178年)字谦之,福建莆田人,专意圣贤之学,以诗礼治身,南渡后,以伊、洛之学倡东南,为理学名士,且与朱熹交游密切,著有《艾轩集》。叶适在两篇不同墓志铭中均谈及了志主与林光朝之间的关系,可窥探志主的交游网络,其人物形象得以丰满。
叶适并未给朱熹、韩侂胄作墓志,但通读其碑志文,朱熹、韩侂胄形象宛然在目。据统计,在《著作正字二刘墓志铭》《陈叔向墓志铭》《黄子耕墓志铭》《胡崇礼墓志铭》及《中奉大夫直龙图阁司农卿林公墓志铭》这5篇墓志中,叶适都附带提及朱熹,主要围绕其伟大思想家身份,展现其渊博的道学思想和广泛教授子弟的情况。在《朝议大夫知处州蒋公墓志铭》《中奉大夫太常少卿直秘阁致仕薛公墓志铭》《袁声史墓志铭》《故礼部尚书龙图阁学士黄公墓志铭》《宝谟阁待制知隆兴府徐公墓志铭》等15篇墓志中,叶适附带提及韩侂胄,主要围绕其政治家身份,结合重大政治事件如绍熙內禅、庆元党禁而展开书写。在这些墓志中,叶适总是能抓住这些非墓主人物的主要身份与个性,突出其主要事迹,为后人了解这些历史人物及与其相关的历史事件的真相,保存珍贵的史料。
不容忽视的是叶适所写148篇墓志中,浙江籍墓主共92位,其中以温州籍墓主为最多,达50位,占了1/3多,几乎将同时期活跃在文坛、政坛及民间的浙东名士“一网打尽”,足以说明叶适所作墓志在当地受欢迎之程度。南宋浙江地区文士辈出,其中不乏碑志文创作名家,如文章家吕祖谦创作的44篇墓志,“能根据传主的不同情况而采用多种文笔,并在行文布局上下功夫,避免了单一化和概念化的毛病,再加上其独特的语言风格,使他的墓志铭呈现出斑斓的色彩和鲜活的灵气”[7]。然与叶适比较,名气远不如。当时浙东地区但凡有家人或亲属去世,多以求得叶适碑志铭文为荣,但叶适却严守墓志创作原则,不为他所熟知之人拒绝为其作传,“余未尝知君……使余无所依以为述也,辞之五六反”[3]236。即便是亲戚,不熟识、“无所依”,也不愿为其作传。
在书写浙江籍人氏的墓志中,叶适或为父、子各作志,或为翁、婿各作志,或为兄、弟各作志,或为夫、妻各作志。以浙东籍墓主为例,统计如下表1:

表1 叶适以互见法为浙东籍墓主所做墓志
值得注意的是,上表所列墓志中,叶适采用了互见方法,具体而言,即在父亲的墓志中写其子事迹,儿子的墓志中追忆父亲功绩;兄长的墓志中描述其弟才华,弟弟的墓志中兼写兄长生平等等,彼此互补,可谓构思巧妙。此类墓志刻画出了叶适同时代浙江地方的重要人物形象,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二、以景写人:烘托人物品行与操守
碑志文大家如韩、欧,在墓志中大多以人物行言刻画其形象,极少抒情性描写。而叶适则创造性的援景入文,往往以墓主生前优美的居地环境来烘托人物高尚德操与品行,在写人技法上突破前人,使碑志文真正走出应酬性文体的窠臼,大大丰富了碑志文的表达方式,写来富有诗意,且与文学性散文并无二致。
以景写人这一写作方法并不适用于叶适笔下所有墓志,在叶适笔下,写作技法的选取是与墓主身份、个性等特征紧密相联系的。在叶适14篇以景写人的墓志中,包含终生未仕的布衣和担任底层官职或长期奉祠赋闲的官员,其中,尤其以布衣身份居多,共计9篇。我们也注意到,叶适为名臣良吏所作墓志文中无一篇是兼带写景的。叶适这一创造性的写作技法,对墓主高洁品行的凸显有着重要作用。由此,叶适能根据人物的身份与个性,采取不同的写作手法,“随其资质,与之形貌”。
叶适通过对隐士、布衣居住环境的描写,烘托出他们高洁的品行和不俗的旨趣。在《墓林处士墓志铭》中,叶适描写何傅,“所居墓林巷,城中最深僻处也。……草木稀疎而不荣,败屋才三间,悉用故《唐书》黏之。”[3]232所居环境之偏僻、房屋之破败,凸显出墓主处贫贱而自得、临冻饿而自守的高洁品行。在《姚君俞墓志铭》中,叶适描写姚献可,虽为落第秀才,然其生活“若山人异士”,与农夫无异,居所附近“蔽着松襟间,行吟绣川湖岸,望山际桃杏花”[3]269。碧水青山环绕的一片桃花源式的乡村风光,呈现于读者眼前。读者自然能体会到,居于此中之人必然具备了陶渊明的隐居情怀!
在《叶君宗儒墓志铭》中,叶适写乡间之贤良如乐清叶士宁,家资雄厚,“有百年之宅,千岁之田”,往往能周乡人之急难,“不吝其力之所及,德施于人而身忘其忧”,其居所“前临清流,旁接高阜,亭院深芜,竟日寂寂”[3]356,“故人邑子常候门下,行路惟闰棋声出空虚。山遨谷嬉,意到不择。每樵歌夜动,櫂讴早发,水边林表,往往睹坠杯遗屐焉”[3]356。以清流、高阜、深院、山谷等衬托棋声、歌声,一静一动,如此诗意的居住环境,烘托出墓主的不俗。黄岩丁世雄多“义举”,礼敬有名之士,资助穷乏之人,被乡人称之为“丁君”,在《丁君墓志铭》中,叶适描写其居所,“萦山带水,菊蕙成行,起高堂温室,朱绿照映,而穷村陋墅,焕然焉王侯贵人幽奇闲丽之境”[3]261-262。叶适碑志文中写景并非目的,景物描写总是围绕墓主生平事迹而展开,并最终为突出人物主要性格特征而服务。
以上墓志中,墓主均为布衣处士或乡绅名流,叶适援景入文,通过侧面描写烘托人物的高洁品行。
此外,叶适还描写了担任底层官职或长期奉祠赋闲的官员,他们虽担任官职,却也怀归隐之思。因此,书写此类墓主的尘外之趣就显得格外重要。
黄仁静虽担任官职,却一心向隐,等到其子黄度中进士第,便筹划归隐,无奈老母仍在,“年高多疾,卧起须公”,等到老夫人一去世,立马过上了隐居的生活。(在《朝奉大夫致仕黄公墓志铭》中,叶适写到,“松柏迷道,庭花合围,公着山人衣,曳杖挟书行吟,宾送烟月于林蒨中”[3]284,凸显了黄仁静的闲旷之风。在《奉议郎郑公墓志铭》中,叶适描写莆田隐士郑耕老中进士第,担任国子监主簿满秩,即“不朝集,遂归南陂,移梅种竹终焉”[3]280。归隐田园后,常常往来于“南陂木兰溪有草堂”,“具舟楫琴书,晴光月夕,不从宾御,夷犹溪上,忘其近逮,溪北野农,常吹箫擎鼓送迎之”[3]280。叶适笔下的墓主,居住清雅的环境,往来于乡间,爱好种菊弄兰、操琴读书的日常生活,其高洁品行跃然纸上。在《故朝散大夫主管建宁府武夷山冲佑观周先生墓志铭》中,叶适还描写了长期奉祠的官员周淳中,出仕之日少,退休之日多,所过生活与农夫无异,“买废山,躬执锄镰,烧地种木”,居所“大竹长杉,回合蔽亏,绮岚绀池,焕霍房户”[3]239。而墓主对这种生活状态甘之如饴,“常终岁闭门,花香鸟鸣,畅然怡适,不问外事”[3]239。在《中奉大夫太常少卿直秘阁致仕薛公墓志铭》中,叶适描写永嘉薛绍,薛季宣从侄,登进士第,“由少奉常领祠官”,居所“公园池不多,而花草疏阔,游止自在”,在此“楼甚低小,而江山隐辅可识;书画精麤杂,而观者各有取;惟灵壁石旧物也,相与考击为乐”[3]365。
除外,叶适在写到与墓主相关的其他人物时,也常常援景入文,侧面烘托,别造新境,使得碑志文更富有诗意。在《庄夫人墓志铭》中,写庄夫人之子王植求学场景,“于时士相禁以学,立之宰相家子,匿姓名,舍辎重,从余穷绝处,水村夜寂,蟹舍一渔火隐约,而立之执书循厓,且诵且思,声甚悲苦”[3]297。水村夜晚的寂静,渔火一盏的清苦,诵读声时远时近,构成一幅富有诗意的画面。这不仅描写出王植刻苦求学的情景,且流露出了作者本人在庆历党禁时的悲苦心境。在《林正仲墓志铭》中,叶适描写林正仲之父林元章,新造之屋宅,“东望海,西挹三港诸山,曲楼重坐,门牖洞彻,表以梧柳,槛以芍药,行者咸流睇延颈”[3]311。将居住环境与人物身份、个性相结合,在碑志以事写人的范式下另辟蹊径,体现出叶适高超的写人技法,对后世碑志文创作产生了极大影响。
综上,叶适在碑志文创作中,坚持重视“有所依以为述”的准则,继承了史传文学以事写人的写作手法,并加以突破。叶适能根据墓主的不同身份、个性,展现出不同的风格特点,“随其资质,与之形貌”,彰显出多样的写作风格以及高超的写人艺术。“在行文上,往往设例取势,因人而变;在叙事上,常常随事赋形,各肖其人。”[8]围绕军国大事写名臣,详赡描摹,真诚颂扬;以典型事迹写良吏和文人,富有传奇色彩。同时,描写具有尘外之趣的布衣处士、乡绅名流,则以景写人,烘托人物的品行与操守,将事与景相结合,以事件为中心,大量援景入文,一实一虚,正面描写与侧面烘托相结合,获得了极高的艺术效果。叶适的碑志文前继韩、欧等古文大家,后启南宋碑志文创作新变,“自觉地打破了墓志文体的程式化,有意识地扩展了墓志的价值取向和功能范畴。将墓志这种应‘四方之邀乞’而运行的‘世俗应酬文字’融入其整个散文的创作体系之中,既追求‘关教事’、‘补世教’的价值与功能,又追求为文之‘工’”[8]。叶适的墓志文刻画传主往往能“随其资质,与之形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宋代散文发展史上具有不可小觑的地位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