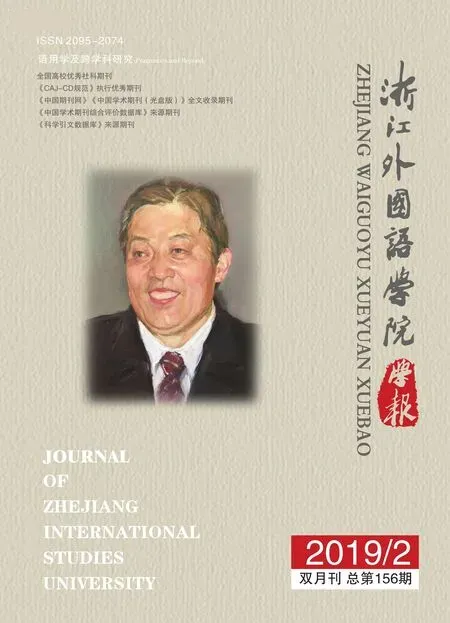甲午战后梁启超的赞助人身份考察
雷炳浩,马会娟
(北京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北京 100089)
一、引言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一生游走于学术与政治之间,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奔走呼号,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翻译活动作为梁启超学术活动的重要一维,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重视。笔者以“梁启超”“翻译”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上检索到相关文献28 篇①最后的检索日期为2018年6月1日,文献来源为CSSCI 来源期刊、扩展版来源期刊(2017—2018)。。这些文章对梁启超的翻译实践和翻译思想进行了比较充分和深入的探讨。比如,劳陇(1996)从梁启超的佛经翻译研究中发掘出梁启超关于翻译本质、翻译方法的观点;廖七一(2006)以梁启超译拜伦《哀希腊》为例,分析了梁启超如何协调政治目标和翻译规范、翻译策略的冲突;罗选民(2006)从意识形态角度分析了梁启超的文学翻译实践。遗憾的是,这些文章鲜有提及梁启超对我国翻译事业的赞助行为,即使偶有涉及也不甚系统,未能全面评价梁启超对翻译事业的贡献。
本文参照美籍翻译理论家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的赞助人理论,对梁启超的赞助人身份进行考察,主要探讨了两个问题:1)梁启超的赞助人身份是如何确立的;2)梁启超是如何履行赞助人职责的。笔者希望借此拓宽梁启超翻译贡献研究的范围,引起学界对我国历史上翻译现象的重视。
二、勒菲弗尔的赞助人理论
勒菲弗尔深受结构主义学派的影响,他将文学系统视为文化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认为在文化系统中文学子系统与其他子系统相互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赞助人理论。勒菲弗尔认为,社会中存在两个控制因素,以保证文学系统不与社会中的其他子系统脱离太远。第一个控制因素位于文学系统内部,是以批评家、评论家等为代表的“专业人士”。第二个控制因素通常位于文学系统外部,勒菲弗尔称之为“赞助人”。赞助人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出版社、媒体、政党等团体,他们与“专业人士”相互“合作”,影响着文学作品,确保文学作品符合意识形态和诗学的要求(2004:14-16)。
勒菲弗尔还指出,赞助人包含三个要素:一是意识形态要素,影响作品形式和内容的选择;二是经济要素,赞助人必须解决“专业人士”的生活问题,包括提供金钱或职位;三是地位要素,赞助人除了提供物质赞助外,还帮助“专业人士”融入某些团体以及适应这些团体的生活方式。这三个要素有时集中在同一个赞助人身上,但有时是分离的(2004:16-17)。
三、甲午战后梁启超赞助人身份的确立
甲午战争后,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有识之士积极向外寻求救国之道,译印欧美、日本的书籍遂成潮流。原来处于权力边缘或外围的新型知识分子积极致力于此项事业。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梁启超成长为颇具影响力的翻译赞助人。1895年,梁启超与康有为联合在北京参加会试的举人发起了“公车上书”,要求清廷拒和、迁都、变法,社会影响热烈,维新派从此正式登上中国历史舞台。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诏书,由此拉开了“百日维新”的序幕。虽然戊戌变法最终失败了,但梁启超等人的思想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郭沫若在回忆录《少年时代》中说,“梁任公的地位在当时确是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他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有力的代言者”(1979:112)。为了配合新思想的传播,梁启超参与创办了大同译书局、广智书局等出版机构以及《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报刊,出版具有维新思想的著作或译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梁启超已是一个较有影响力的出版商。同时,为了团结志同道合者、培养改革力量,梁启超还参与创办了一些学会。“公车上书”之后,梁启超在京师组织强学会,支持者甚众。通过维新运动、办书局报刊和组织学会等一系列活动,梁启超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具备了赞助人的三个要素。
四、梁启超履行赞助人职责的具体路径
参照勒菲弗尔的赞助人理论,笔者从译者的确定与培养、翻译的选材以及译者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的提高三个方面具体探讨了梁启超履行赞助人职责的具体路径。
(一)译者的确定与培养
在办报纸和创书局的过程中,梁启超十分注重选择具有较高水平的译者。“公车上书”之后,康梁等人在京师组织强学会,他们对译书十分重视,一有可能,即请人翻译。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称“余居会所数月,会中于译出西书购置颇备,得以余日尽浏览之”(2003d:17)。从中可知,他们确实组织过译书。现有资料表明,至少到《时务报》创办,梁启超等人已经开始聘用专业译员。梁启超在《创办〈时务报〉源委》中写道,“聘请英文翻译张少塘,系公度托郑瀚生司马代请者;东文翻译古城贞吉,系由公度托日本驻上海总领事代请者;所立合同,亦出公度之手”(2005a:46)。可见此时,梁启超等人不仅聘请专业译员来翻译,而且还聘有不同语种的译员。这一时期,梁启超的翻译活动主要是通过雇佣译员的方式进行的,雇佣的译员主要有东文翻译古城贞吉,英文翻译张坤德、李维格、孙超、王史、曾广铨,俄文翻译刘崇德,法文翻译郭家骥等。《时务报》发表的翻译类文章基本都出自梁启超等维新人士和雇佣译员之手。《时务报》39 期后开辟“时务报馆译编”,开始接收社会人士的译稿,开启了专业译员翻译与稿件征集相结合的模式。
在译者培养方面,梁启超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1896年,梁启超发表了《变法通议》,系统阐发了他的变法主张。在该文中,他提出“欲求译才,必自设翻译学堂始”。梁启超主张“养能译之才”,认为“凡译书者,于华文、西文及其所译书中所言专门之学,三者具通,斯为上才;通二者次之;仅通一则不能以才称矣”(2003a:68-76)。在梁启超看来,一个好的译者不仅需要精通汉语和外语,还应该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在主持变法事宜期间,梁启超更是将翻译人才的培养提上了日程。1898年9月,梁启超呈《拟在上海设立编译学堂并请准予学生出身折》,请求清廷开设编译学堂,广招生源,培植翻译人才,还请求恩准这些学生毕业后可享受与科举生员同等的待遇(2005b:48-49)。虽然戊戌变法最终失败了,但梁启超的翻译人才培养方案并没有随着变法的失败而告终,而是得以延续下来,促进了我国翻译人才的培养。
流亡日本期间,梁启超并未停止办报纸和创书局的活动。虽然外报翻译栏没有像《时务报》的古城贞吉那样有名的翻译撰稿者,但他仍没有停止履行翻译赞助人的职责,这一时期比较有名的译者有罗普、周桂笙等人。梁启超组织翻译活动的方式由最初的主要依靠专业译员进行翻译到后来的向社会征稿,促进了我国翻译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二)翻译的选材
戊戌变法前,梁启超将翻译活动与维新救国紧密联系起来,主张“择当译之本”。梁启超认为,过去的翻译以兵学书籍为主,然而“西人之所强者兵,而所以强者不在兵”,并指出律例章程、学校教材、法律书、史书、政书、农书、矿学书、工艺书、经济学书、哲学书等才是中国的“当译之本”(2003a:66-71)。他还提倡译书“以东文为主,而辅以西文,以政学为先,而次以艺学”(2003b:58)。在此期间,梁启超参与了强学会和大同译书局以及《万国公报》《时务报》等报刊的创办,翻译出版了大量西方政治书籍。此外,梁启超的翻译选材行为还深深影响了当时社会的翻译行为。杨寿清据《译书经眼录》做过一项统计,结果显示光绪末年共翻译西书533 册,其中翻译自日本的有321 册(杨寿清1946:23-25)。梁启超自己也说过,“壬寅、癸卯间,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然皆所谓‘梁启超式'的输入”(2003f:71)。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意识到自上而下的变革并不能挽救中国,因此将其救国的途径转移到“新民”上来。如何培育“新民”是梁启超一直苦苦思索的问题。早在戊戌变法之前,梁启超就在《变法通议》中把“说部书”与“识字书”“文法书”等并列,并主张“专用俚语,广著群书”以“振厉末俗”(2003a:44-60),但尚未得到有效执行。流亡日本期间,梁启超继续寻找培育“新民”的有效途径。在考察日本变法的成功经验时,梁启超注意到“于日本维新之运有大功者,小说亦其一端也”(2003e:41)。考虑到清末的社会现实,梁启超认为小说因其通俗性和娱乐性拥有较广的读者群,社会影响广泛,是开启民智的理想工具。为此,梁启超发表了《译印政治小说序》和《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两篇重要文章,鼓励翻译日本的政治小说。20世纪初,梁启超参与创办了广智书局,并开办《新民丛报》《新小说》等报刊,大力倡导小说翻译和创作。仅以《新小说》为例,《新小说》从创办到停刊的短短几年共出了2 卷24 期,先后登载译著小说26 种。虽然出版期数不多,但并不妨碍《新小说》在当时的影响力。1902—1911年间,受《新小说》的影响,“小说杂志更是不少,一半也归功于梁启超的《新小说》杂志”(包天笑2009:356)。当时的《绣像小说》《新新小说》《月月小说》《中外小说林》等,刊物的主编者身份、背景虽各有不同,但是其办刊宗旨却与《新小说》十分相近,都是借助小说这种文学形式来批评社会,启蒙大众,培养新道德,改良群治。吴趼人(1906:4-5)也说:“吾感夫饮冰子《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之说出,提倡改良小说,不数年而吾国之新著新译之小说,几于汗万牛充万栋,犹复日出不已而未有穷期也。”从中可见,梁启超确实在当时的翻译选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译者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的提高
梁启超的社会声誉,加之特定的时代背景,使得其所办之报刊行销海内外,受到知识分子的追捧。这里以《时务报》和《新民丛报》为例,即可略窥一斑。据梁启超个人回忆,“甲午挫后,《时务报》起,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2003c:52)。另据《新民丛报》所载,1903年初其在海内外有代派处87 处,除日本横滨、东京、长畸,范围还包括仁川、上海、北京、天津、广州等44 个地区(佚名1902a:广告页)。从中可见,《新民丛报》影响范围之广。报刊的畅销和受欢迎也使其译者受到海内外人士的喜爱,从而有益于译者社会影响力(地位)的提升。作为《新小说》的主要译者周桂笙,就是典型的例子。周桂笙,名树奎,字桂笙,曾用笔名惺庵、知新子、知新室主人等,江苏南汇(今属上海)人。1902年,应梁启超之约任《新小说》译事。1906年任《月月小说》总译述。转聘至《月月小说》后,该刊曾在刊内广告中载:“(本社)特聘我佛山人、知新室主人为总撰、译述。二君②二君指吴趼人和周桂笙。前为横滨新小说社总撰译员,久为海内所欢迎。本社敦请之时,商乞再三,始蒙二君许可,而《新小说》因此暂行停办。”《月月小说》另刊封底广告亦云:“本社总撰述我佛山人吴君趼人、总译述知新室主人周君桂笙,昔皆任横滨《新小说》撰译事,二君之著作久为小说界所欢迎,毋庸赘述。自本社延聘后,《新小说》因此停刊,久已不出。”(转引自郭浩帆2002:225)根据Pierre Bourdieu 的文化资本理论,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1986:241-258),上文的例子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该理论。
主持《时务报》期间,梁启超为译员提供了比较丰厚的酬金。据有关资料显示,刘崇惠担任《时务报》“俄文报译”翻译报章时,每月交稿三四次,“每次交二三千字来”,报馆则“照章送津贴银廿元”(黄遵宪 2003:460-462)。《时务报》首任“英文报译”张坤德月薪“七十元”(梁启超 2017:1686)。继任者李维格初欲“每月得馆榖百金”(李维格2017:527),汪康年、黄遵宪等觉“过多”,认为“以百金聘翻译”当在“一二年拓充后”(黄遵宪2003:467),最终结果不见明确记载,后可能涨至百元。就当时上海的物价和消费水平而言,百元收入即可养家糊口而衣食无忧,可见《时务报》译员的工资已属不低(陈一容2010:101)。1897年,梁启超等在上海创办大同译书局,他在《叙例》中说:“海内名宿,有自译自著自辑之书,愿托本局代印者,皆可承印,或以金钱奉酬,或印成后以书奉酬,皆可随时商订。”(2003b:58)虽没有公布具体的标准,但已经强调酬劳可以随时商订,或者给金钱,或者赠送印成的书籍若干册作为(抵当)稿酬。1902年,《新民丛报》第十九号上刊出《新小说社征文启》,这是为即将创办的小说杂志《新小说》向海内外广泛征稿的启事,其中明确规定对于所采用的稿件分别给予数目不等的稿酬(佚名1902b:4-5)。
梁启超组织翻译活动由最初的依靠雇佣译员进行翻译到向社会征稿,并为采纳的稿件支付较高的酬金,很好地履行了赞助人的职责。
五、结语
梁启超作为赞助人为我国翻译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本文参照勒菲弗尔的赞助人理论,对梁启超的赞助人身份进行了考察,探讨了梁启超赞助人身份得以确立的条件,并从译者的确定与培养、翻译选材以及译者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的提高三个方面分析了梁启超履行赞助人职责的具体路径,希望能够进一步拓展我国翻译研究的视野,引起国内翻译学界对梁启超翻译贡献研究的重视。
本文得到北京外国语大学2018年度秋季学期校级大学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改革开放与中国形象——从美国翻译出版的莫言小说的副文本看中国形象的建构”的支持,特此致谢。文章初稿曾在2018年10月西安外国语大学召开的“新时代语境下翻译研究与外语学科建设新方向”高层论坛上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