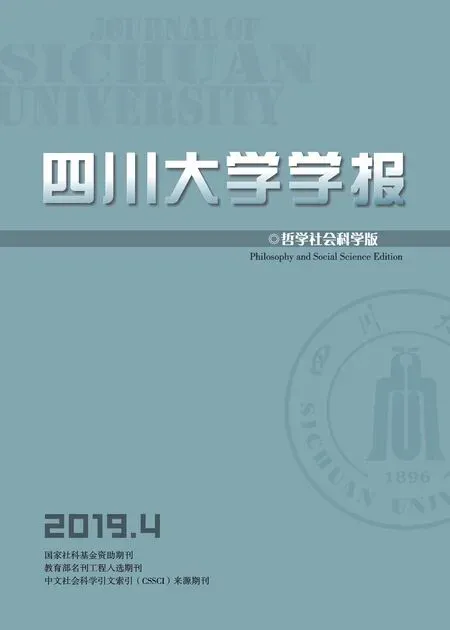改革开放40年中国创新治理的回顾与展望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和创新演进趋势,持续不断地推进创新治理变革。40年创新治理发展历程,以不同时期的发展任务、工作重点、治理主体和改革目标为特征,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既彼此独立又互为关联的阶段。其中存在着两条上下贯通的线索,一是中国创新治理变革始终作为中国整体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服从于并服务于整体改革的需要,依据不同时期经济改革的目标任务而侧重不同的工作重点,并通过创新治理变革助推中国经济改革不断走向全面深化。二是中国创新治理变革始终与创新理论发展密切相关,创新理论发展深化了我们对创新主体、创新过程、创新网络、创新环境和创新体系的认识,进而推动中国政府依据不同时期内外部环境和创新规律制定阶段性的目标任务;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创新治理变革的深入又积累了大量实践经验,对这些实践经验的总结归纳反过来又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创新治理理论。
4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中国经济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跨越,中国的创新要素、创新主体、创新资源和创新环境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政府积极应对这种变化,创新治理思路逐渐清晰,创新治理范围逐步扩大,创新治理层面日益深入,渐渐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实验主义创新治理模式。这种创新治理模式如何协调多元创新主体关系?创新治理机制如何实现动态调整并筛选出有效政策?都是中国实验主义创新治理框架需要回答的问题。基于创新三螺旋理论和实验主义治理理论视角,本文归纳梳理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创新治理发展历程,总结提炼创新治理的中国经验、中国方案,有望丰富拓展现有的创新治理理论框架。
一、中国改革开放40年创新治理历经的四阶段
根据发展任务、工作重点、治理主体和改革目标的不同,40年间的中国创新治理发展历程大致可归为四个既彼此独立又互为关联的阶段。
(一)1978—1992年技术引进阶段
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突破口,中国政府从中央层面陆续推出多项发展战略,通过“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等政策试点手段,赋予试点地方政府多项经济发展自主权打开改革开放局面,希望通过地方试点“以点带线、以线连面”,循序渐进地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大局,实现国家现代化。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是这个时期中国创新治理实践的标志性事件。
1984年中国沿海14个港口城市建立第一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通过各项投资、土地、税收优惠等政策措施,吸引外国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兴办一批现代企业,带动区域经济发展。1985年中央发布《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全面启动了科技体制改革。1986年中央启动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以前沿技术研发为重点推动中国科技发展。1988年中国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计划——“火炬计划”开始实施。各地纷纷结合本地资源禀赋和发展目标创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大力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升中国经济活力,形成了以政府为创新治理主体、以经济技术开发区为创新治理实验区域、以兴办高新技术企业为创新治理手段,以促进经济增长为创新治理目的的一系列措施。[注]朱孟珏、周春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新区开发的演变历程、特征及机制研究》,《现代城市研究》2012年第9期,第80-85页。
总体上看,该阶段中国创新治理的政策工具并不具体,政策目标也不清晰,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阶段性任务为改善国民经济形势,服务于对外开放政策大局。
(二)1992—2003年市场化改革阶段
该阶段以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确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标志,中国创新治理主体开始了市场化转型。该阶段中国的创新治理着重围绕两个领域推进,一是通过市场化改革增强企业创新活力,释放市场机制在创新资源配置领域的作用;二是继续推进完善“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代表的政策实验,实现产业整合与技术驱动,提升创新绩效,推动经济增长。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后,中国创新治理伴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深入进入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为中国创新主体的充分发育提供了外部环境,通过十多年的市场化改革,中国创新主体发育和创新体系发展日渐成熟,为创新治理进一步完善奠定了基础。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对全国科研院所进行结构调整试点。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推动应用型科研机构向企业转制。
在该阶段,中国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为标志的实验积累了大量创新治理经验,但这两种政策实验本身缺乏对创新治理的顶层设计,逐渐暴露出诸多问题。[注]周姣、赵敏:《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新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科技管理研究》2014年第10期,第1-6页。在政策目标上,中央和地方政府偏重区域经济增长目标,创新的其他发展目标处于从属地位;在政策内容上,各地政府偏重企业与产业层面招商引资的数量和规模,对创新能力提升和创新环境营造缺乏关注;在政策工具上多采取财政、税收优惠和国有土地划拨等手段,缺乏对创新要素流动及创新网络优化的政策激励。
(三)2003—2012年治理转型阶段
该阶段以党的十六大明确创新的国家战略地位为标志,政府开始治理转型,构建国家创新体系。2003年党的十六大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以创新为驱动力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上升为国家战略。自2003年始由国务院牵头,经过两年的研究酝酿,于2005年12月公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2006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2006年2月发布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的若干配套政策,这三份文件突出强调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发展战略。以此为契机,中国开始了构建国家创新体系、营造创新环境的探索,创新治理开始全面推进。
2004年,深圳、杭州等地方政府自发制定了本地“创新型城市发展规划”。2008年国家发改委批准深圳为中国首个“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并向各地推广。2010年科技部、发改委牵头批复了36个“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随着“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实验主义创新治理的推进,政府意识到以城市为空间区域的创新治理在创新要素流动、创新网络覆盖、创新政策协调和创新产业联动上的不足,需要在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协调整合。[注]章文光、李伟:《创新型城市创新效率评价与投入冗余分析》,《科技进步与对策》2017年第6期,第122-126页。2009年中央通过陆续在各地建立“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方式,试图构建区域性的创新增长极,完善区域内创新产业布局与创新资源配置,在更高层面和更广范围内优化创新治理路径。
在创新治理主体关系上,政府开始着眼于调动创新资源,着力优化“政府—企业—科研机构”三螺旋创新主体关系。2002年6月国家出台了《关于充分发挥高等学校科技创新作用的若干意见》,2006年6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工作的意见》,2006年12月出台了《国家大学科技园“十一五”发展规划纲要》, 2010年7月发布了《国家中长期科技人才发展规划(2010—2020年)》,这四份文件在时间上彼此衔接、在内容上相互配合,都着眼于提升政府—企业—大学三个创新主体的自主创新能力。
(四)2012年至今全面深化阶段
该阶段以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创新驱动国家战略”为标志,强调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中国创新治理进入全面深化阶段。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立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宏观布局,中国创新治理进入整体推进全面深化的快车道。
2012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首次以中央文件形式强调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创新驱动,标志着中国创新治理迈向构建和完善国家创新体制,提高创新治理效能的新方向。2012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再次强调加强和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并将改革重点放在统筹政府调控和市场资源配置的关系上来。2016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完备地提出了中国创新治理的系统性目标,将新兴产业培育、创新人才培养、创新基地建设、创新体系发育、创新网络形成、创新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等作为全面提升中国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举措。
在创新治理实践上,中国继续全面铺开“央—地”政府间的实验主义治理模式,同时提升统筹创新试点层级,深化不同创新政策实验之间的配合协调。首先,“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迈入高速增长期,覆盖区域从最初的东部沿海发达城市向中西部内陆省会、枢纽和区域中心城市扩展。其次,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将此前开展的创新治理政策实验的经验进行整合归纳,并在更高层级上统合协调。[注]章文光、宋斌斌:《从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看中国实验主义治理》,《中国行政管理》2018年第12期,第89-95页。201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了《关于在部分区域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的总体方案》,开始推广国家“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建设。最后,从顶层设计上对创新治理谋篇布局,并有意识地结合此前开展的“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实验,形成在行政权力、资源配置、制度安排和空间区域上由中央到地方的纵向立体式的多层级、多维度创新治理政策实验体系。
二、中国改革开放40年创新治理的重心、主体及路径变迁
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创新治理始终在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和创新规律的治理路径,不同时期的治理重心、治理主体和治理路径都有不同。
(一)创新治理重心转变
梳理改革开放40年中国创新治理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在第一、二阶段创新治理目标更强调技术的引进、吸收和升级,创新治理主体更多着眼于企业主体作用发挥以及产业结构优化,对政府和大学的主体作用较为忽视。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高和市场功能的完善,尤其是中国创新治理实践经验的积累,中国的学术界人士、政策制定者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企业层面的技术开发升级之外,创新过程中的组织重构、制度完善、主体间协同等都对国家创新体系的构建有所需求。[注]Elinor Ostrom,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132-153.在知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和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高度依赖于创新和知识转化能力。一国经济发展的成功与其获取、吸收、扩散及应用现代技术的能力紧密相联,而这种能力正体现在国家创新体系之中。[注]Mary Crossan and Marina Apaydin, “A Multi-Dimensional Framework of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A Systematic Review of Literature,”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Vol.47, No.6, 2010, pp.154-191.因此,中国创新治理发展的第三、四阶段将构建国家创新系统作为创新治理的关键手段,将创新体制机制改革作为整体提升中国创新治理水平和创新治理能力的重要抓手,通过理顺企业、政府、大学三螺旋创新主体关系优化创新生态环境,以创新为核心动力引导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资源配置方式的优化、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创新主体的迭代。
总体而言,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和市场社会发育程度的变化,中国创新治理重心有了方向性调整,从改革开放前20年以政府直接扶持企业和产业为重点的创新治理,转向改革开放后20年以政府间接完善创新生态环境,构建国家创新体系,培育创新文化为重点的创新治理。这种创新治理重心变迁带来了一系列创新政策理念、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的差异。在创新体制上,从以政府为创新主体,科研院所改革为突破口向创新制度优化、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转变;在创新路径上,从跟踪模仿技术向加强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转变;在创新目标上,从经济目标为主向经济与社会目标并重的多元价值取向转变;在创新方式上,从注重单项技术的研究开发与国外高科技企业引进向多种创新资源、创新要素、创新目标的融合与集成创新转变;在发展部署上,从以研究开发为主向优化创新激励机制与培育创新吸收力并重转变;在国际合作上,从一般性科技交流向主动利用全球科技资源的开放型创新转变。
(二)创新治理主体演进
现代创新理论摒弃了传统线性创新观点,认为创新过程具有非单一的起点和方向,各种创新活动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不分前后、相互交织。既有网络节点又有辐射作用区域,已远远超出了线性乃至链式模型。在非线性创新过程中,企业、政府与大学间的关系日益复杂多样。知识生产者的边界变得日益模糊,企业与各种规模和范围的学术及其他混合型实体,成为更广泛创新网络的一部分。[注]R. Jacob and Z. Merle, “Utilization of Social Science Knowledge in Science Policy: Systems of Innovation, Triple Helix and VINNOVA,”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Vol.45, No.3, 2006, pp.431-462.创新主体间的界面出现了“前移”“交叉”“趋同”等新趋势,创新主体复合和边界模糊日益成为创新活动的新特征。
创新活动发展新趋势对政府在创新过程中的作用提出了新挑战。政府作为创新主体之一,与其他创新主体互动日益频繁,其组织边界具有“开放性”,组织功能呈现“弹性化”。这要求政府能够根据创新环境变化和创新阶段性需要,适时拓展自身边界,调整自身功能,形成所谓的“自反机制”。与此同时,在大量的前沿领域,知识同时是理论的、实践的、可商业化的和公开的,即知识的“多价性”。[注]G. Vertova, “The State and National Systems of Innovation: A Sympathetic Critique,” 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Series, No.823, 2014, pp.401-424.这种“多价知识”进一步打破了传统的线性创新模式,意味着创新在多元主体内部和彼此交叠的互动中随时产生,促成了创新主体中组织设置的多元重叠关系,形成大量的政学合作研究院、高新企业孵化器、国有高新技术企业等混合型创新组织。[注]J. Wonglimpiyarat and P. Khaemasunun, “China's Innovation Financing System: Triple Helix Policy Perspectives,” Triple Helix, Vol.2, No.1, 2015, pp.1-18.这种创新知识、创新组织、创新过程、创新网络的新变化,需要政府适时拓展和优化其边界与功能,形成新的治理模式和治理思维。政府—企业—大学间创新三螺旋理论为我们分析知识经济和科技创新系统提供了新思路,也为探索政府在创新过程中的边界和机制提供了有效框架。随着市场主体的充分发育和对创新规律认识的深化,中国创新治理实践过程中的创新治理主体也体现出阶段性特征。
1978—1992年的第一阶段。在实践层面,中国从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大量的创新基础设施尚未完善,市场主体没有充分发育,以国有企业和计划体制为代表的传统经济主体和运转模式制约着中国创新治理实践的空间。在认识层面,缺乏对创新非线性过程和创新多元主体作用的理解,因此创新治理主要以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为重点,忽视了政府、大学等其他创新主体的联动。该阶段“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运转模式主要是政府运营模式、投资运营模式和土地运营模式。
1992—2003年的第二阶段。在实践层面,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方向,多元创新主体开始发育,创新基础设施和科研院所逐步完善和壮大,企业和政府的有机结合成为各级政府创新治理的有效途径。在认识层面,国家战略层面仍然将赶超和学习作为发展战略的核心,未确立自主创新的地位,各地方政府的创新治理实验空间有限,各创新主体作用难以有效发挥。该阶段“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运转模式主要是政府服务运营模式、产业运营模式等。
2003—2012年的第三阶段。在实践层面,以科学发展观提出为标志,创新驱动作为国家发展战略被首次明确提出。政府意识到自主创新是推动经济长期稳定可持续增长的核心动力,陆续出台了各项创新发展规划。在认识层面,作为创新治理主体的大学和科研机构等知识生产组织的地位日益提升,系统性地协调企业、政府和大学三螺旋创新主体关系的创新政策实验被中央和地方层面广泛尝试。以2004年启动的“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2009年启动的“自主创新示范区”两大国家创新战略为例,从中央到地方层面都推出了优化创新环境,保护知识产权、培养和引进创新人才,建设一流科研机构、研究型大学和创新型企业等创新治理措施,三螺旋创新主体的系统治理成为中国创新治理实践的重要内容。
2012年至今的第四阶段。 “十八大”后中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中国政府将自主创新的意义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强调创新治理既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也是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践层面,中国政府日益重视混合型创新组织在创新主体网络关系中的作用,主动调整创新治理思维和治理方式,日益重视对创新治理的顶层设计和混合型创新主体的融合发展。以2015年推出“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和2016年出台《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为标志,政府日益关注对政—学融合的合作研究院、政—企融合的国有高新技术企业、产—学融合的高新企业孵化器等混合型创新主体的治理与相互间动态关系的优化。这标志着中国创新治理思路日渐成熟,创新治理方法日趋多元,创新治理路径日益清晰。在认识层面上,随着创新理论的发展,人们认识到在知识型社会中,公共和私营部门、科学和技术、大学和企业之间的界限正在模糊化,从而形成一种重叠交互系统。创新主体三螺旋理论发展打破了市场与政府治理结构的二元对立,赋予了政府参与创新活动的新角色和新功能。[注]Z. Todeva and R. Emanuela, “Governance of Innovation and Intermediation in Triple Helix Interactions,”Industry and Higher Education, Vol.27, No.4, 2013, pp.263-278.知识生产者的边界变得日益模糊,产生知识的机构越来越多地在关键行为者之间的关系网络中发挥作用。由于大学、企业和政府毕竟属于不同系统,如何把三个创新主体的力量有效匹配、整合,推动国家或区域创新活动,是考验政府创新治理能力和水平的一项挑战。政府的创新政策不单只是提供诱因与减少管制,还要主动针对互动过程与体系加以改造。
在创新治理主体关系上,该阶段以完善企业、政府、大学等创新主体协同互动的创新生态系统,形成主体间交互融合的开放型创新网络为重点。一系列中央文件都将创新孵化器培育,创新平台建设、创新人才培养,科研院所创新转化能力和“政府—企业—大学”三螺旋创新主体间的互动作为创新治理的重要内容。系列文件中多次提到“构建涵盖科研院所、高校、企业、中介机构等各类创新主体,覆盖从基础研究、技术开发、技术转移到产业化等创新链各个环节的产业、财税、金融、人才、知识产权保护以及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政策体系”,在创新治理主体的目标内容上也更为丰富,不但涵盖此前的促进发展、创新引领等经济性目标,也涵盖了环境保护、公平高效、开放协调、资源节约和公共服务等社会性目标。
(三)创新治理路径优化
创新不确定性意味着,决策者如果没有明确认识到哪种技术发展途径更有可能产生最大的经济社会产出,那么制定成功的创新战略可能是一项艰巨任务。[注]S. Bartholomew, “National Systems of Biotechnology Innovation: Complex Interdependence in the Global Syste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Vol.66, No.3, 1997, pp.353-366.为了克服这一困难,决策者越来越多地利用实验主义治理的方法来制定科学和技术政策,通过加强长期的、面向未来的方法来提高决策质量。实验主义本质上是一种递归决策,即多个公共行动主体为达成某种政策目标,在统一框架下分散决策、彼此互动,在不断评估中相互学习,并根据自身条件和环境变化及时修正各自的行动方案。[注]K. Mattias, “Constitutionalism and Experimentalist Governance,” Regulation & Governance, Vol.15, No.1, 2012, pp.147-163.实验主义治理强调横向的学习和问责结构,将地方政府的表现放在网络状框架之下,定期交互接受横向监督与同行评议。在实验主义治理框架下,基层组织被赋予更大的能力和权力,其核心在于通过向下赋权来“改变现状”。在中国创新治理实践中,中央与地方长期通过实验主义方法,即“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路径探索、实验、矫正和优化创新治理政策工具。[注]W. T. Woo, “The Real Reasons for China's Growth,” The China Journal, Vol.30, No.2, 1999, pp.228-258.
1.在1978—2003年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中国政府尝试通过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在中央和地方政府间,通过一系列权力下移、政策倾斜、利益重新分配改革中国产业政策,在多层级政府间以竞争、学习、扩散为手段实验创新友好型产业政策。由于在当时环境下中国经济基础较为薄弱,市场发育不健全,创新治理还未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各项创新治理手段多从属于经济增长目标。随着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的经济实力日益增强,创新资源趋向多元,创新环境日益改善;与此同时,长期以要素投入推动经济增长模式的副作用日渐显现,非均衡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亟待转轨,创新作为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核心动力日渐被政府重视,创新治理开始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中央政府开始尝试创新友好型政策工具,打造国家创新体系。面对各种不确定因素,如何检测创新政策的有效性?怎样推广有效的创新政策?如何矫正创新政策的偏差?中国政府采取实验主义方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治理路径。
2.在2003—2012年的第三阶段,随着2003年创新驱动成为国家发展战略,中国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开展多层次、大范围的创新政策实验,通过“干中学”的方式推进实验主义创新治理,在2004年和2009年推出了“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两种创新治理实验。这两种实验模式既有相似也有区别。相似在于两者均为“试点—筛选—扩散”的政策实验方式,在多级政府和创新主体间,通过渐进式、协同式、往复性的多层次多维度共同学习形成信息网络,强化三螺旋创新主体正反馈过程,同时通过实验来检验政策效果并决策是否强化或矫正政策工具。区别在于其覆盖地域、赋权方式和实验重心有所不同,从覆盖地域来看两种实验分别为省级(地级)市和特定区域;从行政层级来看两种实验批准单位分别为发改委、科技部(正部级)和国务院(正国级);从赋权方式来看“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以地方分权、自主试验、中央较少干预为主,“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以地方分权、区域协同、中央协调为主;从实验重心来看“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以地方实验为主,央地共同学习和地地自发扩散为辅,“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以制度改革,中央权威推动扩散为主,地方执行和央地共同学习为辅。这两种实验主义创新治理模式在此阶段日渐成熟,通过“央—地”政府间共同学习筛选出合适政策工具,并在创新网络中快速扩散,赋予了创新治理较强的灵活性和纠错力。
3.在2012年至今的第四阶段,随着中国创新治理的推进,政府发现构建完善的国家创新系统,需要协调多元创新主体的复杂关系,完善信息交互机制,优化创新网络,加速扩散进程。而这些都要求政府打破自身边界,重塑自身功能,在更大范围和更高维度上完善顶层设计,提高创新治理能力和水平。在此阶段,中国继续完善和优化“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两种创新治理实验,并于2015年推出了“国家创新改革试验区”,试图构建完整的创新治理实验谱系。与此前推出的一系列政策实验相比,“国家创新改革试验区”也是一个涵盖“试点—筛选—扩散”,通过“央—地”共同学习形成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的创新治理实验。但也有其鲜明特点,从覆盖地域来看,“国家创新改革试验区”覆盖范围更大;从行政层级来看,“国家创新改革试验区”由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核认定,希望从顶层设计上打破原有的行政边界、重塑政府作用;从赋权安排来看,“国家创新改革试验区” 以中央集权、推广试验为主;从试验重心来看,“国家创新改革试验区”以中央权威推动扩散为主,地方执行和“央—地”共同学习为辅。总体而言,“国家创新改革试验区”是中国政府试图从国家层面打破限制创新的系列约束,通过治理改革释放制度红利,尝试利用中央权威推动创新友好型政策快速扩散的一种实验主义创新治理模式。这种实验模式与上述其他阶段推出的一系列实验主义创新治理模式,共同构成了中国探索和优化中的创新治理路径。
总体而言,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40年的创新治理过程中,逐步形成了适应中国发展目标和阶段性资源禀赋的创新治理发展路径,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创新体系建设各项举措,走过了“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自主创新示范区”→“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的历史沿革。各项举措渐次推进,牵头部门从部级向国级甚至更高级提升,参与的地方政府由区域内向跨区域合作扩展,所强调的过程由小规模试点向大规模扩散,中央政府政策目标由纲领性走向具体化。一方面,这些试点举措的发展沿革体现出中国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方向上的阶段性变化。在深化对创新规律认识和深刻总结创新治理经验的基础上,中国政府从单纯的“地方分散试验—央地共同学习—中央集中推广”的“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实验模式转向“发挥行政资源优势、汲取制度改革红利,持续高位推动,中央权威加速扩散”的“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实验模式,实验主义治理目标日渐清晰,政策工具日益具体,治理路径逐步完善。另一方面,在“央—地”交互学习检验政策工具和实验主义模式探索创新治理路径的同时,中国政府也不断加速推进自身治理能力和水平的提升,通过打破行政层级,汲取多方创新资源,融合多样化创新目标的方式来适应创新的非线性过程,进一步优化政府自身治理功能,与企业和大学一起形成更为完备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
三、中国改革开放40年创新治理的经验总结及未来展望
从世界范围来看,如何对国家创新系统进行有效治理?政府在创新治理中作用的边界和机制是什么?什么样的治理模式有利于国家创新系统的绩效?这些问题是各国政府普遍面临的挑战。事实上,通过创新治理实践不断检验、矫正或强化创新政策组合并对国家创新系统进行动态完善是各国政府在创新治理过程中的常态。[注]H. Cai and D. Treisman, “Did Government Decentralization Cause China's Economic Miracle?” World Politics, Vol.58, No.4, 2006, pp. 505-535.研究表明,政府不单需要纠正创新过程中由于外部性、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完备性带来的市场失灵,更需要从治理角度纠正各创新主体间的系统失灵。[注]C. Xue and Y. Xu, “Influence Factor Analysis of Enterprise IT Innovation Capacity Based on System Dynamics,” Procedia Engineering, Vol.174, No.1, 2017, pp.232-239.因此,构建国家创新体系及完善政府创新治理是从系统角度思考创新问题在治理逻辑上的自然延伸。从创新治理重心、创新治理主体以及创新治理路径三个维度对中国创新治理发展的四个阶段进行分析,发现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创新治理始终处于灵活且富有弹性的动态调整之中。这可以理解为中国政府在创新治理发展过程中为平衡短期阶段性增长和长期可持续性发展,通过多样化政策试错所做的种种努力。通过40年改革开放实践中的不断摸索完善,中国创新治理呈现出颇具中国元素的特点。
(一)改革开放40年中国创新治理的基本经验
1.融合式共同学习:多元创新主体的开放网络
知识经济时代,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创新与知识重组的复杂性导致组织边界渗透性增强,组织需要从外部获取知识和技术来超越自身界限,以更开放的方式与外部环境和利益相关者互动。[注]Jacob and Merle, “Utilization of Social Science Knowledge in Science Policy: Systems of Innovation, Triple Helix and VINNOVA,” pp.431-462.中国政府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对创新规律的认识,日益重视对“政府—企业—大学”创新主体三螺旋关系的治理。从最初阶段以政府为创新治理单一主体,通过直接政策干预推动创新,转向后来重点构建企业、政府和大学协调发挥作用的国家创新体系,通过优化创新生态环境推动创新。打破国家创新体系中政府作用边界“分界线”的概念,在“政府—企业—大学”三种创新主体的“接触面”上形成有效的协同合作网络,以融合式共同学习的方式在主体间推动创新的持续发展,为信息传递、知识产生和创新扩散提供更为便捷高效的渠道,从而回应内部多元创新主体诉求。
2.动态式调整:政府创新治理的作用机制
知识的生产、转移和产业化是一个动态的、非线性的过程,政府在其中的作用也不再是一个静态概念,而是一个动态的作用机制过程。[注]Crossan and Apaydin,“A Multi-Dimensional Framework of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A Systematic Review of Literature,” pp.154-191.在中国创新治理实践过程中,通过一系列“混合组织”实现多种创新主体作用的动态调整,例如:政—学结合的研究院、产—政结合的国有创新企业以及产—政—学结合的高新企业孵化器等等。这些“混合组织”的有效运转离不开完善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制度、政策支撑条件,包括通过多样政策工具来规范、引导创新产品市场、知识和技术市场、人才市场、资本市场等。改革开放40年的创新治理发展过程中,中国政府一方面通过自身改革适应创新治理多元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另一方面通过优化市场支撑条件作用机制对创新体系的整体网络运行效率和总产出产生重大影响。
3.适应性识别:实验主义创新治理政策的制定路径
创新活动的路径演变迅速,且探寻创新治理的道路本身也是一个不断调整、试错的动态过程。在此背景下,政府作用边界和作用机制需要通过政策试点、筛选和扩散等方式不间断地调整政策工具——观察政策绩效——反馈到下阶段政策调整。[注]Ostrom, Governing the Commons, pp.132-153.纵向来看,中国创新治理发展历程呈现出典型的实验主义治理适应性识别特征。回顾中国创新治理发展的四个历史阶段,不难发现,在每个历史阶段中国政府都推出了阶段性的带有典型“试点—筛选—扩散”特点的创新政策实验,并赋予其阶段性的政策目标任务和较为明确具体的政策实验角色。政策实验过程中,中央与地方政府通过多种政策工具组合以及与多元创新主体间权力、资源的实验性再分配,试图找到一条创新治理的多样化发展之路。在试点区域通过府际共同学习、“央—地”交互评估、中央权威筛选进行政策试错,最终选择符合中央政策目标优先顺序的“典型经验”加以权威性推广。[注]S. Heilmann, “Policy Experimentation in China's Economic Rise,”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43, No.1, 2008, pp.1-26.这种渐进式的实验主义方式成就了中国创新治理渐进式改革的高效,避免了“一刀切”带来的政策风险,赋予了地方政府分散决策的政策空间,借助中央政府政治资源实现了高效推广,并随时根据实践发展和认识深化加以矫正。[注]S. Chung, “Building a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through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Technovation, Vol.22, No.8, 2002, pp.485-491.
(二)新时代中国创新治理的未来展望
在改革开放40年创新治理长期实践和阶段性总结的基础上,中国探索和完善了一套机制相对稳定,富有环境适应性、政策灵活性和高效纠错力的中国式实验主义创新治理框架。在该框架下,政府通过“融合式共同体学习”的内部机制逐步调整创新治理主体间的创新网络,协调在更大范围更深程度上不断融合迭代的创新混合机构;通过“动态式调整”的外部机制逐步拓展创新治理的外部边界,扩大创新主体与包括知识、技术、人才和资本等创新市场资源的接触面;通过一系列政策“试点—筛选—扩散”的实验主义方法优化创新治理路径,检验创新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的匹配程度,并随时根据创新治理效果对创新政策实验进行调整、强化或纠偏,最终以创新网络合力探寻最优化的国家层面战略性创新政策。随着创新理论和经济进程的发展,未来中国的创新治理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优化治理方式,提升治理能力。
1.创新主体层面:主体赋能,形成多元治理的三螺旋主体关系
知识经济条件下,创新是个非线性的螺旋式上升过程,各创新主体(包括政府、企业、科研机构)之间只有组织有效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分工协作网络,才能形成从知识的产生到转移再到推出最终产品和服务的螺旋上升的途径。[注]R. Agranoff and M. McGuire, “Expanding Intergovernmental Management's Hidden Dimensions,” 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Vol.29, No.4, 1999, pp.352-369.这就需要对创新三螺旋主体进行赋能,发挥政府、企业和科研机构的主体作用,使各创新要素合理分工和协作,实现创新系统的高效运行。由于中国尚未形成完备的公共需求表达渠道,作为创新政策供给方的政府与创新政策需求方的其他创新主体间横向沟通网络很弱,存在大量显性和隐性治理障碍。因此,需要政府进一步放权推动主体赋能,鼓励多元主体充分发挥作用,形成多元创新治理的格局。
2.创新机制层面:多层治理,打造国家创新体系
创新体系是创新治理的着力点,它由不同的行动者、组织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组成,他们既受地域边界的限制,也能够跨越边界与其他国家创新系统中的行动者产生联系。因此,创新治理要突破行政边界制约,通过各种隐性和显性规则,在不同层面上协调治理主体多方参与。[注]L. Fuenfschilling and B. Truffer, “The Interplay of Institutions, Actors and Technologies in Socio-technical Systems: An Analysis of Transformations in the Australian Urban Water Sector,”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Vol.103, 2016, pp.298-312.这就要求治理权力和治理范式的转变。[注]G. Marks and L. Hooghe, “Unravelling the Central State, But How? Types of Multilevel Governan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7, No.2, 2003, pp.233-243.然而,中国各级政府和创新行动者往往基于自愿合作参与创新治理过程,这种自发协调下的各级政府面临着缺乏正式制度框架以及规则制定权限的限制,需要制定规范完善的多层次创新治理框架,厘清城市、区域和中央政府的治理重点和治理方向,形成定位清晰且富有弹性的国家创新治理体系。
3.创新路径层面:政府重塑,完善中国实验主义创新治理路径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在实践中形成了极富特色的实验主义创新治理路径,通过整体式“试点—筛选—扩散”、融合式共同学习、动态式集(分)权和适应性识别等机制对公共政策进行验证、强化或纠偏,最终形成较为稳定的创新治理政策试验模式。[注]章文光、宋斌斌:《从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看中国实验主义治理》,《中国行政管理》2018年第12期,第89-95页。地方城市政府作为创新政策实验的主体,享有较为完备的政策试错主动权,并在中央柔性规制下完成多级政府间信息沟通与共同学习。然而,在现实中这种创新治理模式面临着中国行政体制和创新主体关系建构的双重挑战,创新不确定性和不同地方多样化的创新资源禀赋也进一步增加了创新治理风险。因此,需要重塑“中央—地方”各级政府职能,通过基层实验和顶层设计的有效结合优化实验主义创新治理框架。同时结合国家创新体系对区域功能定位的影响和作用方式,构建市场主导下区域创新的政策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结合东中西部分类、新型区域战略分类、省区分类、创新型城市分类等不同维度,对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自主创新示范区、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等实验效果进行量化分析,明确各区域的优势与不足,指出各区域创新驱动功能定位和未来发展方向,提升中国区域创新体系的优化布局和协调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