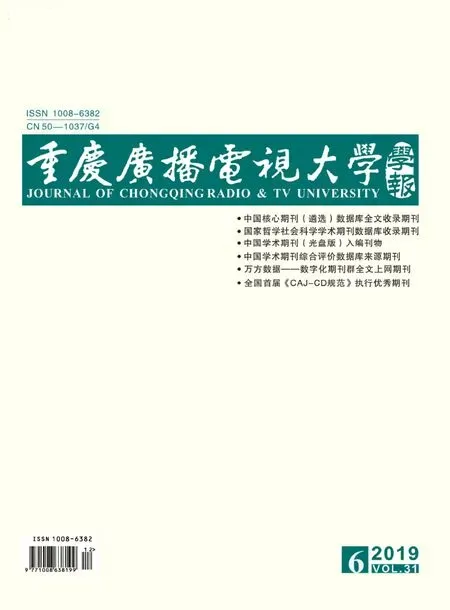梦叙述的符号修辞
方小莉
(四川大学 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梦的研究在东西方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人们总是试图找出梦的意义。“意义是一个符号可以被另外的符号解释的潜力,解释就是意义的实现。”[1]2为了探索梦的意义,释梦几乎成为全世界共享的活动。雅柯布森认为符号文本包含6个因素:发送者、文本、对象、媒介、符码与接收者。当其中一个因素成为文本的主导时,就会导向某种相应的特殊意义解释[2]169-184。本文在各种释梦方式的基础上,尝试从符号修辞的角度解释梦的叙述。由于人既是梦的发送者,又是梦的接收者,因此释梦活动总是侧重于梦文本的“情绪性”(emotive)和“意动性”。现有的释梦方式主要关注的是隐梦,也就是梦的解释。由于获得了梦的解释意义,似乎梦文本本身就不重要了,因此释梦倾向于讨论梦对人类有何启示和作用,要么是关注梦者的压抑与愿望满足,要么则是讨论梦对接收者产生的启示,研究接收者做出何种反应。梦的符号修辞研究主要以梦文本为核心,更加关注梦的“诗性”。
一、梦的解析与功能
梦具有何种功能,主要取决于它的解释方式。解释所调动的元语言不同,梦的功能便不同。古代的详梦认为人类可以通过梦境来了解神的旨意,梦可以预知未来。而在现代,不同的学科在不同的时期对梦的解释不同,从而所得出的梦之功能也就不同,可以说梦的功能是被解释出来的。梦的研究一直以来都偏向于心理学的方式,自弗洛伊德开始历经一个多世纪,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本文在此无须赘述。解释方式会造成梦的意义和功能的差异,本文试图跳出心理学研究的桎梏,不把梦仅仅看作是一种心理或生理现象,而是将其视作一种具体社会历史语境下的产物。
不同历史语境下,人们对梦的解释也各异,梦也就具有不同的功能。对梦的解释,除了心理学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以外,还涉及哲学、历史学、人类学、文学等。虽然各个学科的解释方式不同,但值得注意的是,各个学科都力图解释梦的意义,探讨梦与现实的关系,从而进一步讨论梦对现实所起到的作用。
早期的哲学家们主要关注梦对未来的启示、对自我的认识以及对人类生存及认知等方面的作用。从古希腊时期开始,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认为想象可能为认知提供未来的知识。在真梦里,关于未来的想象能够在醒来后被记住。而亚里士多德在其哲学中也承认真梦具有预兆性。斯多葛学派认为人越伟大,则越具有做真梦的自然能力。如果心灵纯洁而安静,那么一个人甚至在清醒时都可能获得启示。到了中世纪,由于宗教的影响,中世纪的犹太哲学家主要强调真梦的预见性元素,而鲜有考虑其他心理方面的因素[3]1-19。当然,也有学者提出在中世纪的文化中,梦的一个功能是为梦者提供关于自身的启示性洞见[4]387,而迈蒙尼德认为梦中意象来源于自己,来自于日思。梦以创造性的新方式将这些日间思想结合起来。梦的内容是一种新的知识、方法、政治议程和对未来的想象。对迈蒙尼德来说,梦并不提供超自然的内容,而真梦也并非是日常生活的普遍构成。它们是非凡的,为日常生活提供实用知识[5]43-5。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梦的超自然元素或预见性,可以确定的是人们认为梦对经验世界的个人或集体有影响。
对梦的哲学研究由于受到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冲击反而在现代走了下坡路,梦不再成为哲学普遍关心的问题。但是,哲学中所关心的这些问题,却并没有消失,而是被认知学等其他学科继续关注。20世纪80年代发展起来的认知学进一步讨论了梦对于自我的了解以及对于人类认知发展发挥的重要功能。认知学研究结合了认知哲学与认知心理学即实验科学,更多关注梦对于人类认知发展的重要作用,以及梦如何促进人的自我认知,同时也关注梦的表征方式与认知的关系等。在对梦的认知功能的研究方面,认知学首先关注梦与记忆的关系,认为梦的认知功能是将人们的记忆,无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无论是日间余思,还是梦中产生的进行整合。而且,梦不仅整合巩固记忆,还将新旧的记忆材料进行重新组合,创造出新的意义,从而能够更好地认识个体自我。除了探讨梦与记忆的关系之外,梦的认知学研究还关注了梦的视觉意象和情感主导与自我认知的复杂关系。
文化和历史学家主要从广义的角度,探讨了梦的不同社会功能,也就是在不同时期,解释梦如何对不同的文化、政治、宗教等产生作用。
梦之所以能够成为推广宗教、政治、文化等社会观念的重要工具,不仅跟梦的特点有关,也跟梦的解释方式有关。梦被认为是处在现实与幻想,未来与过去的边缘。这一点可能让大家更易于接受梦能够传递宗教信息这类观点。由于梦本身的神秘性,它与神自然被联系起来,被解释成为神向大家传递信息的方式,从而在过去推行宗教或政治文化观念时十分有效。埃德加(Iain R. Edgar)认为,人类有能力将梦的意象运用到不同的政治、历史、宗教、集体和个人的语境中,创造出社会事件中各种明显或隐含的权威[6]79-92。也就是说,人们可以有效利用梦的意象来建构和巩固各种权威。最常见的是,梦由于其自身独特的特点,被用作推销宗教、政治、文化等观念的有效工具。柯尔特(Bart J. Koet)提出,梦常常用来促进宗教或是宣传宗教,或对政治起到积极的宣传作用。因为梦可以用来表示神的帮助,因此是推销观念的完美工具[7]267-279。同样的观点也出现在人类学家的研究中。与文化研究者和历史学家的宏观探讨略有不同,人类学家更多的是通过田野调查,选择某个特定的群体来探讨梦对于该群体发挥何种功能,从具体的例子中窥探梦在人类历史和文化中扮演的角色。
梦作为一定文化历史语境下的精神产物,对现实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或是成为推行政治、宗教、文化的工具;或是成为搭建人与精神世界或有灵世界的桥梁。无论是哪种关系,都可以看出梦虽然看似是一种虚幻的精神活动,却影响着人类的现实世界。从以上对梦之功能的研究可以看出,梦的意义及功能与梦的解释方式和文化、社会、历史语境等都是分不开的。现存的梦的研究,无论是从历史、文化、哲学、人类学或文化认知方面来看,都比较偏向于通过研究和解释梦来揭示其意义和功能,也就是偏向于弗洛伊德所说的隐梦的解释,而不太关注显梦的表达形式,也就是梦文本的诗性。在下文中,笔者主要是从符号修辞的角度来讨论梦文本的形式构成。
二、梦叙述的隐喻与转喻
对现代社会来说,大家最为熟知的解梦方式源自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弗洛伊德认为“梦是某种愿望幻想式的满足,它是通过幻觉式的满足来排除干扰睡眠的心理刺激的一种经历”[8]115。也就是说,人类压抑的各种欲望可能产生某种心理刺激从而影响人类睡眠,而梦则通过幻觉体验的方式满足了人类的某些欲望,从而保证了人类的睡眠不受干扰。而后来的荣格则认为“梦是心灵的自然产物,具有一些平衡内部或自我调节的功用,并且遵守生理规律,促进人适应机制,以配合个人的判断、成长、生存之要求”[9]60。受到荣格一派的影响,现代心理学普遍认为梦不仅与一个人的童年经历有关,同时与我们应对困难、压力以及欲望的方式也息息相关。对梦境的正确解读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梦境是表达智慧、恢复力量的渠道,它们让你能够明白自己的秘密和渴望,解读身边的压力源,恢复平静心绪。”[10]3
梦的修辞研究与现有研究最大的不同是关注梦文本的构成,也就是说对梦的修辞研究是能指优先的研究,重点不是放在隐梦的意义上,而是关注显梦本身。事实上,心理学研究虽然认为被压抑的隐梦的意义更为重要,但是人类做梦的时候,只能接收到显梦,而隐梦的意义只能通过分析显梦才能获得,因此弗洛伊德有关梦的解析早就关注到梦的构成、梦文本的诗性。只不过弗洛伊德认为梦的运作方式遵循的是一种压抑机制,梦是愿望幻想式的满足,是被压抑的欲望变形的表达。人被压抑的欲望不能直接表达,为了躲避审查,梦的运作是通过凝缩和移置来构筑梦的意义。凝缩和移置两种作用事实上都是使梦的材料发生变形,从而避过审查,显梦是梦的真实意义的变形与伪装,梦压抑了本我对真实欲望的表达。与弗洛伊德不同,史戴茨认为梦的运作并非遵循压抑机制,反之,梦是思想的表达,他认为梦可能是最不受压抑的一种思想形式[11]20。在史戴茨看来,梦并非是压抑性的,而是表达性(expressive)的,梦将人们的心之所想变为可视性的[11]26。因此,史戴茨认为梦的变形并非是为了伪装逃避审查,而是为了更好地表达意义。早期荣格也有类似的观点,在荣格看来,“梦是一种自然现象,梦没有欺骗的意图,而是尽力将所要表达之事表达清楚”[12]161-162。
在弗洛伊德的“压抑说”中,梦的变形是一种伪装,也是一种防御机制,目的是为了逃避梦的稽查作用;而在史戴茨的“表达说”中,梦的变形则是为了让梦的意思表达得更清楚。温森(Jonathan Winson) 也提出,“梦的变形不是防御机制而是普通联想过程的反映,经验正是通过这个过程得到解释和整合”[13]214。史戴茨认为,大脑是一部修辞机器,“梦中发生的行为不是稽查或伪装,而是大脑通过修辞把感觉、情感或思想转化为它们的图像对应物”[11]71。也就是说,弗洛伊德所说的变形,从梦的修辞角度来说,是大脑采用了修辞策略,把抽象的情感与思想图像化或具体化,从而能够更好地表达意义,因此在梦中“我们需要隐喻和修辞不是为了伪装意义而是为了表达纯用语言无法表达的意义”[11]92。
在史戴茨的表达说中,转喻和隐喻是梦运作的主要策略,而提喻和反讽则是辅助性策略。转喻是梦运作第一阶段的关键,它通过压缩将感情和抽象的梦念转喻式地变形转化为图像,可见转喻的基本作用与凝缩相似。“大脑通过转喻产生图像,标志梦的开始”[11]100,也即是说,梦通过因果关系或者邻接关系,将情感或意念凝缩转化为梦中的图像,从而产生梦。梦中图像的产生是情感或意念的图像对应物,它们通过某种关系连接起来,或是因果,或是邻接,也或许只是偶然相关。所以,在史戴茨看来,“转喻是一种具体化”[11]181,因为它是梦产生的第一步,将感情压缩为图像。
提喻作为转喻的辅助性策略也与梦将情感压缩转换为图像的过程相关。史戴茨提出提喻是一种对关系性的暗示,这种关系性是指以部分暗示整体,部分携带着整体,或整体由各部分构成。因此,当这种以部分代整体的关系以图像的形式出现在梦境中时,它不仅仅是一种“象征性的替代,而且是一种对整体性的表达,这种整体性代表着结构性或融贯”[11]182。也就是说,提喻作为转喻的辅助性策略,与图像的产生有关,在情感变形转化为图像的过程中,提喻发挥作用,通常以部分代整体的形式辅助转喻构成图像。由于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部分不仅只是象征性地替代整体,同时部分还携带着整体的意义,也就是梦事实上在用部分的意义表达整体的意义。事实上,在梦中图像产生的过程中,梦通过转喻将情感压缩成为图像,然而图像只是人类心灵情感的一个提喻,只不过图像不仅只是对整体的替代,同时也表达梦者情感的整体意义。因为提喻作用,部分携带着整体意义,梦者就使得梦的意义表达具有整体性和统一性。这也就是史戴茨所谓的:“提喻的任务是保证所有的部分都与整体相关。提喻是想象的编辑,它确保所有的图像都属于同一个整体。”[11]182-183
如果说转喻与提喻跟梦中图像的产生有关,那么隐喻则推进了梦的发展。史戴茨将梦视作是一种思维活动,是人类想象产生的。构成梦的图像按照一定的序列,从一个图像运动到下一个图像,这一运动连续进行从而构成梦境。在史戴茨看来,图像的产生可以通过转喻和提喻,而图像之间发生关联构成序列则靠隐喻机制。他认为“隐喻是从一个图像运动或发展到另一个图像”。“这里强调的不是相同或相似,而是驱使修辞性的大脑去找出相似性。”[11]182梦从一个图像向前运动到另一个图像依靠隐喻,即是说大脑以一种隐喻的方式能够寻找到图像与图像之间的相似点。图像A的某一点,引发图B与之联系,因为A与B之间有某种相似点,依次类推,从而使梦通过隐喻的方式向前运动推进。值得注意的是,梦在遵循隐喻机制向前推进的过程中也可能会遭遇突然或难以预测的转折,从而造成反转,这便是史戴茨所认为的梦的结构性反讽。反讽的产生使梦境中的某个时刻突然发生转折,这一转折打破了大脑对相似性的寻找,从而使梦不能按原来的方向向前推进,而是临时转方向或停止。
从上面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史戴茨看来,梦的转喻与提喻跟梦的开始有关,因为转喻与提喻将情感压缩转化为梦中的图像,而推动梦向前发展则是通过隐喻和反讽。通过隐喻机制,某个图像的某一点由于相似性原则与另一个图像关联起来,从而构成了图像序列,梦从一个图像运动到下一个图,则推进了梦的发展。在特殊情况下,这种寻找相似性的运动被中断,梦境发生了突然的转折,便是反讽的作用。
从史戴茨关于梦的修辞研究来看,梦的凝缩可以对应于转喻与提喻,与图像的产生有关,而移置则可以对应于隐喻,与相似性构成关联。只是在弗洛伊德那里,梦的修辞是为了伪装、隐藏意义,而史戴茨则认为修辞是为了表达意义。两种理论似乎相互对立、无法调和,然而事实上,两位学者只是关注点有所不同,本文尝试从符号叙述学的角度调和压抑说与表达说,把两位学者的观点结合起来,更为全面地来考察梦。
三、梦叙述的组合与聚合
从叙述学的角度来看,叙述都能表达意义,而任何表达意义的叙述文本都存在伪装与变形,因为叙述总是具有高度的选择性,梦叙述与任何叙述一样都包含表层文本和潜层文本。弗洛伊德推崇伪装说,因为他更关注潜层文本,认为表层只是潜层的变形与伪装,也就是更关注符号文本的解释项;而史戴茨推崇表达说,是因为他更关注符号文本本身,或者说他更关注文本的诗性。在史戴茨这里,能指优先,因此他强调梦表层文本的修辞。
梦是一种虚构性叙述,任何叙述都是被媒介化的再现,而任何再现都具有高度的选择性,那么在这层意义上说,任何叙述都是一种变形。弗洛伊德和荣格等心理学家都认为梦境是潜意识的产物,“梦是潜意识心灵活动直接的表达”[14]75。既然梦是潜意识心灵活动的表达,那么其就是一种意义的传达活动。意义的传达必然有一个接收方。潜意识发送意义的接收方显然是处于睡眠中的梦者。瑞克罗夫(Charles Rycroft)把做梦视作是“私下的,自我对自我的一种交流”[15]72, 既然将梦视作一种交流,那么必然涉及到发送者、媒介和接收者。一般的叙述发送者与接收者是不同的主体,而梦叙述作为一种私下的自我交流,只能是“主体的一部分,把叙述文本传达给主体的另一部分”[16]52。日间余思与记忆是构筑梦的基本材料,但这些材料无法事无巨细地全部进入梦境,因此梦的叙述者在讲述故事时必然要经过筛选,而梦的叙述必然是有选择地呈现,也必然发生了变形。梦不仅在从情感到图像的转化中发生了变形,更重要的是“梦提供的不是我们经验的一个副本而是经验的重构”[11]25,也就是对经验材料的挑选、组合与变形。
修辞学从传统的定义来说就是一种“说服”术。一个主体采用某种策略说服另外一个主体,或是对另一个主体产生影响。由于梦的特殊性,梦叙述中的修辞并非发生在两个主体之间,而是发生在同一个主体内部。赵毅衡认为弗洛伊德实际上把梦看成是潜意识的一种意义文本,其中贯穿了修辞方式(1)赵毅衡.回到皮尔斯[J].符号与传媒,2014(9):1-12.。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弗洛伊德认为梦的修辞方式是为了伪装意义,逃避审查,而从修辞的角度来说,梦的叙述者为了能够向梦者更好地传达潜意识的意义,在意义传递过程中贯穿了修辞方式,这样可以起到说服作用,也是为了更好地表达。在弗洛伊德的压抑说中,梦分为显梦和隐梦,因此梦的伪装不是不表达意义,而是在用显梦表达隐梦的意义,只是弗洛伊德重隐梦而轻显梦。弗洛伊德注重的是显梦表达了什么深层意义,而史戴茨却更注重显梦如何表达意义。本文接下来将从叙述学的角度来探讨隐喻与转喻作为两种主要策略如何构筑梦叙述来表达意义。
在史戴茨对梦运作的修辞研究中,转喻和隐喻是梦运作的主要策略,辅之以提喻与反讽。梦产生的原理是转喻将情感或意念压缩转化为图像,而梦的过程的推进和继续发展则是大脑通过隐喻机制去发掘相似点,相似点让一个图像唤起下一个图像,梦则从一个图像运动到下一个图像,构成梦的图像序列。史戴茨公开反对弗洛伊德的压抑说,他主要关注梦文本如何构成,也即是弗洛伊德理论中的显梦。弗洛伊德认为显梦伪装和掩藏了梦的真实意义,必须要通过显梦去分析隐梦之意;而史戴茨则认为梦的变形是一种修辞策略,本身就是为了清楚表意。本文将梦视作是一个叙述文本,一定程度上结合了弗洛伊德的压抑说和史戴茨的表达说。当我们把梦视作一个叙述文本,那么梦就应该由表层文本与潜层文本所构成。梦以显梦伪装隐梦,也即是以显梦作为表层文本,来表达隐梦的潜层意义。
任何叙述文本都具有高度的选择性,选择必然涉及聚合与组合的双轴关系操作。“聚合轴可称为选择轴,功能是比较与选择”,它是根据相似性原则进行比较与筛选,因此是隐喻性的。“组合轴可称为结合轴,功能是邻接与黏合”[1]160,它是以邻接关系进行组合,因此是转喻性的。梦叙述同样也涉及聚合与组合的双轴关系操作。梦的叙述者需要根据自己要传达的意义来筛选组成梦世界的材料。为了能够有效地传递信息,梦的叙述者必然要经过比较与选择,并对选上的材料根据关联性进行有效的组合。梦文本通过双轴关系的操作完成后,其组合段显现,属于表层结构;而聚合段是隐藏的,属于深层结构。梦的深层结构,或说梦背后更深层的意义就是指被隐藏的聚合关系。释梦可以重新考察梦的聚合关系,考察聚合轴上被“选上”或“选下”的部分,从而获得梦的隐意。也就是说,梦作为一个叙述文本是组合与聚合双轴操作的结果,也即是隐喻与转喻运行的结果。在聚合轴上,通过隐喻的相似性原则找出适宜的图像,而在组合轴上,根据转喻的相关性原则将图像联系成事件序列。只不过要注意的是,双轴关系是同时进行的,不分先后。隐喻与图像的产生,与梦的开始相关,而转喻则跟梦的情节化相关,推动梦的向前发展。梦的产生和梦的情节推进是隐喻和转喻共同作用的结果。不过梦叙述似乎是一种偏向聚合原理的表意方式,隐喻性较强。对于大多数梦来说,人类接收到的都是各个片段。从这个角度来说,梦靠相似性推进,梦这种诗性特质,以意象并置为主的形式又与史戴茨的修辞观点不谋而合。当然,少数梦也有可能情节性较明显,即组合关系突出,这样的梦比较容易被理解和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