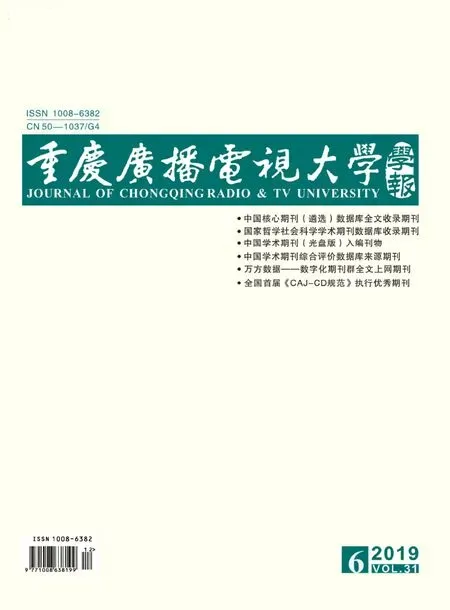文学批评与认知隐喻
张 旭
(四川大学 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一、引言
认知隐喻或概念隐喻是认知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也是认知语言学发展的源头之一。传统的隐喻观认为隐喻作为一种修辞,是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只属于诗歌和文学。而现代的隐喻观提出,隐喻不是一种语言现象,而是一种思维方式、认知机制,来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并影响人们的行为[1]。因此,现代隐喻理论认为,日常语言中包含了大量的隐喻表达,日常规约化语言是建立在隐喻机制基础之上的,而“隐喻的根源完全不是语言,而是用一个心理域(mental domain)来理解另一个心理域”[2]199。这一观点可以追溯到Reedy的研究生毕业论文TheConduitMetaphor,作者通过对“管道隐喻”这一个例子的系统分析,论证了隐喻存在于思维而非语言中,这是对传统隐喻观的第一次强有力的颠覆[3]。Lakoff和Johnson受这一观点的启发,进一步系统地建立了现代隐喻理论体系,其主要研究领域是日常的概念体系,并得出日常概念体系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隐喻体系,而“大部分日常语言也是以该隐喻体系为基础”[2]201。因此,现代隐喻理论的研究焦点为日常规约化隐喻,并认为诗歌隐喻或者文学隐喻是建立在日常隐喻的基础之上的,而诗歌隐喻被当作一种“新奇隐喻”研究,其目的是对日常隐喻体系的补充和进一步论证。Mark Turner 在1987年出版的《死亡是美丽之母》(DeathIstheMotherofBeauty)就是利用日常隐喻体系对诗歌隐喻进行分析,其中着重论述了“亲属隐喻”(kinship metaphor)在诗歌中的运用[4]。Lakoff和Turner在1989年共同发表的专著《超越冷静的推理:诗歌隐喻使用指南》(MoreThanCoolReason:AFieldGuidetoPoeticMetaphor)是对文学隐喻如何运用日常隐喻体系的进一步论证[5]。在Lakoff, Johnson和Turner的研究基础上,利用现代隐喻理论对文学的分析大致分为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Todd开始的利用认知语言学的相关概念和认知隐喻对文体学进行研究[6];另一个是以Freeman为开端的利用认知语言学和现代隐喻理论对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进行研究[7]。Freeman在系统吸纳认知语言学理论知识的基础之上,首次在2000年发表的论文中提出认知诗学(cognitive poetics)这一文学研究方法或文学理论。认知诗学是以“认知语言学理论为根基,将文学作品看作是一些认知主体(cognitive minds)的创造产品,对文学作品的解读来自于另外一些认知主体,整个文学作品创作和被阐释的过程都发生在一个具有物理和社会文化双重结构的世界中”[7]253。之后的研究大多数是建立在认知诗学这一理论基础上,或者是对这一理论的简单运用,或者是补充完善。Müller以Rainer Maria Rilke 的诗歌作品为例论证了认知语言学在文学解读中的有效性[8];William利用认知诗学理论对德国诗人Zehra Çirak的诗歌进行了研究,并讨论了在多元文化背景下,认知诗学如何帮助我们更好地解读诗歌作品[9]。林建宏和张荣与利用隐喻理论中的具体的意象基模(image schema)对《小王子》的篇章构造进行了分析[10]。此外,Kimmel[11]和Pena Cervel[12]分别运用认知诗学理论对康拉德的《黑暗之心》和《麦克白》进行了研究。
国内这方面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大部分的文章为硕士论文,利用认知语言学对文学作品进行简单的分析,笔者只找到两篇相关主题的博士论文:司建国利用认知语言学中隐喻和转喻相关概念对曹禺的几部代表性戏剧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当代隐喻、转喻理论在文学批评中的功能性价值[13];郭琳以西方文学理论历史为背景,追溯了隐喻这一概念的演变,并将其与中国新时期理论研究中的发展成果相结合,通过对比研究,探讨“隐喻”在当代中西方文学理论研究中的价值所在[14]。由以上我们可以看出,认知语言学已被当作一种方法或者手段引入文学批评。本文以文学批评的本质性特点,即批评中无可避免的批评家自身的主体性和个体性为出发点,来反观认知语言学,尤其是认知隐喻及相关的隐喻原则。Freeman提出了认知诗学这一文学理论的前提,他认为现有的文学理论受制于其理论立场,只能从心理、社会、历史或者结构主义等某一方面对文学作品进行解读,而无法提供一种全面充分的解读[7]253。同时,他认为现代隐喻理论可以做到这一点,而认知诗学的目的就在于此。本文的观点恰恰是建立在反对这一观点的基础上的,并试图以具体的隐喻为例,探讨现代隐喻理论自身对于概念的把握存在局限性,而这一局限性来自于人自身的思想表达和视角受制于社会时代背景、自身的价值观念和表达发生的具体语境。因此,这一局限性是无法根除的,而对于隐喻的语义分析,只能帮助我们看清表达者或者阐释者本人的价值取向和思想观念,以及表达中体现出的自身的情感态度。
二、认知隐喻
现代隐喻理论首先区分了“隐喻”和“隐喻表达”:隐喻是“概念体系中的跨域映射”;隐喻表达是这种跨域映射的外在表现,即隐喻性的单词、短语或句子。而在传统隐喻理论中,“隐喻”就是“隐喻表达”[2]199。因此,隐喻可以看作是一组这样的跨域或跨域阵的映射,而隐喻表达是其中的一个具体的例子。为了便于标记概念体系中的映射,Lakoff和Johnson采取的策略是用助记符号来命名映射,其形式是“靶域是源域”或者“靶域即源域”[2]204。在现代隐喻理论中有两个重要的原则:“上位层次(superordinate level category)映射”和“恒定性原则”(Invariance Principle)。例如在“爱情是旅途”[2]209这一隐喻中,靶域为爱情域,源域为旅途域,具体的映射即爱情对应运载工具、爱人对应旅行者、爱情的目标对应旅行的目的地。其中,运载工具和爱情均属于上位层次概念。而“映射一般发生在上位层次,而不是基本层次”[2]209,也就是说不会出现“爱情像汽车”这样的映射。同时,较低级层级的映射会“承袭”上位层级的映射的结构,比如“爱情是旅途”这一映射就承袭了“生活是旅途”这一上层映射的结构。而为什么会有“爱情是旅途”这一隐喻?如何理解、认知一个隐喻?这就涉及恒定性原则,即“被隐喻映射保留下来的是与靶域内部结构相一致的源域意象图式结构”[2]213。因此,隐喻不是源域的内部结构强加到靶域上,而是两者的内部结构本身具有相似性,隐喻恰好揭示出这样一种对应关系。“恒定性原则”保证了“靶域中固有的意象图式不能被破坏,而且靶域的固有意象图式会自动地对被映射的方面进行限制”[2]214。这两个原则使得认知隐喻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具有了稳定性,并对于隐喻的语义分析增加了效力。
但是,如何得知一个概念的固有的内部结构(意象图式)?尤其是像爱情、生活这样复杂抽象的概念?因此,认知隐喻理论具有一种循环的风险,即先从大量的隐喻例子中抽象出这样一种内部结构,再将其用于这些隐喻的映射关系的解释中去。面对这样一种风险,认知语言学给出的解决方案是这些内部结构、意象图式是来自于日常的生活经验,具体包括视觉经验、运动经验、身体感觉等最基础的感知经验[15]15-16。事实上,认知语言学家对于这些基本的生活经验的解读与阐释往往来自常识的假设与推导,而不是来自于认知心理学或认知科学的实验研究,实验设计的难度在于现实生活中影响人们的认知因素太多,无法精确控制变量以得到绝对可靠的实验结果。因此,显而易见,认知语言学家对于人们日常生活经验的归纳、阐释和解读无法做到真正的客观,即无法避免自身的主观性,其对于隐喻的解读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讨论的方便。在认知语言学家看来,隐喻的主要目的和功能在于认知,隐喻的使用和分析是为了帮助人们对原本复杂难以捉摸的概念有更好的理解,而在对概念更好的理解的基础上,采取恰当的行为予以应对。因此,对隐喻的解读和隐喻机制的构建,语言字面意义的关注和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做到客观,但是对语义的过分关注往往就会忽略语言固有的情感色彩和表达者表达时的意图和状态。而语言首先作为交流的工具和手段,在大多数情况下,除了信息的交互之外,还要充当情感和态度交流的媒介。其源头在于人无法摆脱自身的主体性与个体性,任何表达都会受到说话时的意图、当时的感受和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的影响。
本文通过具体的例子来进行分析论证。首先是对“爱情是旅途”这一著名隐喻进行重新解读,看这一隐喻是如何反映表达者表达时的情感、态度和其中包含的价值观念。其次,看关于爱情的其他相关隐喻是如何作为反例的,论证隐喻机制的建立和隐喻的语义分析与文学批评对于文本的解读一样,都无法避免地受到阐释者自身主体性和个体性的影响。最后得出,所谓概念固有的内部结构往往是分析者强加在概念上的,而其操作的基础还是传统隐喻理论中隐喻表达中的相似性。认知隐喻的解读和隐喻机制的建立与文学批评对文学本文的分析根本上是一致的,差别只在于后者自觉于自身的主体性和个体性。因此,对隐喻的语义分析无法得出客观公正的解释,但这种分析也有不可否认的价值,就在于它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说话人和该隐喻背后隐藏的意图、态度及反映出的其自身的价值观念。
三、“爱情是旅途”
认知隐喻中最有名的一个映射即“爱情是旅途”,在这一隐喻中:
“——情侣对应旅行者。
——情侣关系对应运载工具。
——情侣的共同目标对应其共同的目的地。
——情侣关系中遇到的困难对应旅途中的障碍。”[2]204
而“爱情是旅途”这一隐喻本身是“将旅途知识映射到爱情知识上,其目的是认知,即我们通过这样的对应来用旅途知识理解爱情。因此,如果恋爱中的一方说:‘我们陷住了’(We’re stuck),这时,我们就需要旅行知识来帮助我们理解爱情”[2]204。
爱情和旅途这两个概念之间存在很多相似点(或者可以说两个概念的内部结构很相似),并且这些相似点很容易被发现,而人们在运用隐喻时,很容易只关注两个概念之间的相似点,而忽略两者之间的差异。而实际上,这种所谓的内部固有的结构往往是分析者在总结两个概念之间相似性的基础上,从中抽象出来,而后又反过来强加在概念之上的,但是对隐喻的语义分析可以更好地帮助人们看出表达者自身的态度、意图和价值观念。而在“爱情是旅途”这一映射中体现这一点的地方是表达者对于旅途的理解,即旅途中存在“共同的目的地”。而这一表述可以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表达者本人对于爱情和旅途的看法或者对两者的评价是以结果为导向的,即成功的旅行是到达目的地的旅行,而爱情也是如此,成功的爱情一定要完成既定的目标。但是,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即大多数人对于旅途的理解是一个向着某个目的地进发的行程,或许这也是字典中的定义,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有一些旅行是没有目的地的,并且大多数人都会承认旅途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获得快乐,而快乐来自于目的地的到达还是来自于沿途的风景,这一个问题中包含着无可避免的冲突,即以结果为导向和以过程为导向的两种价值观念的冲突。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根本的矛盾,我们来看一下关于爱情的另外一个著名的隐喻。
莎士比亚在他的喜剧《皆大欢喜》中说过这样一句名言:“全世界是一个舞台,而男男女女不过是一些演员。”[16]52(All the world’s a stage and all the men and women merely players)如果世界是一个舞台,那么人生就是一场戏,每个人都是演员,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而爱情不过是人生这场戏中的一幕戏,每个人都在爱情里扮演恋人的角色。“爱情是一幕戏”就是“人生是一场戏”这一上位层级映射的一个次级映射。而当我们把爱情比喻为一幕戏的时候,爱人作为戏中的演员,其目的就是演好这幕戏,为别人呈现一幕精彩的戏,或者说其共同目的是一个完美的落幕,喜剧的收场。这一隐喻的两种不同解读之间的差异实际上反映了读者自身对爱情和表演两个概念的不同价值取向。而这恰恰是文学批评中一个根本性的现象。每一个批评家都是从自己的理论立场出发对文学文本进行解读,而其解读的价值所在并不是离文本的“真相”又进了一步,而是在于其解读中体现出来的自身的价值观念。文学的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可以帮助读者认识自己,这体现在面对一个文学作品,读者更倾向于哪种解读。“爱情是旅途”和“爱情是一幕戏”这两个隐喻的不同解读实际上是对Lakoff提出的隐喻机制中“恒定性原则”的挑战,其认为概念的语义或者内部结构是多变的,变化是历时也是共时的,不同的社会时代背景下对概念的理解是不同的,而每个人的经历和成长环境也是千差万别的,这就导致了对于概念的理解会存在大量“偏见”,而这种“偏见”直接来源于人作为有限的存在无法摆脱来自物质世界和精神文化世界的多重制约。另外,在具体的交流语境中,只针对表达进行语义分析容易忽略表达者此时此刻的情感状态和说话意图。
可以看出,所谓的概念的内部结构不过是分析者强加于概念之上的,其目的是为了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理论体系。但是,笔者并没有否定这样操作所拥有的价值,即语义分析可以帮助我们看清分析者或者表达背后隐藏的价值体系。下一部分,笔者会继续讨论关于爱情的其他隐喻,而这些隐喻在进一步证明论点的同时,也是现代隐喻理论中“上位层次映射”这一原则的反例。
四、关于爱情的其他隐喻
苏格兰享誉世界的诗人罗伯特·彭斯的一首著名的诗歌《一朵红红的玫瑰》(ARed,RedRose)的开头两句将爱人比喻为“一朵红红的玫瑰和一支甜甜的乐曲”[17]3。爱情是一种人类情感,其根本的属性是其关系的相互性,即只有两个人互相爱慕,这样才称得上是爱情,而单相思这种情况我们一般不会称之为爱情。因此,当恋人中的一方把另一方比喻成玫瑰和乐曲时,我们不应忽略“爱情”这一情感本身发挥的作用。如果对这一对隐喻进行语义分析,把它们当作是跨域映射,我们会得到这样两个隐喻:“爱人是玫瑰”和“爱人是乐曲”,而当我们把玫瑰花的相关知识和乐曲的相关知识用在爱人身上时,我们不会有任何认知上的收获,因为我们无法找到“爱人域”“玫瑰花域”和“乐曲域”这些概念本身固有的内部结构,而实际上这类对爱人的比喻可以无限增加,如爱人是明月,爱人是蜜糖等。实际上,这一隐喻的实质是“爱人是美好甜蜜的东西”,而这一映射的上位层级映射是“爱情是美好甜蜜的东西”,这样的隐喻是说话人的一种情感的表达——对爱情的赞美。对其进行语义分析并不能让我们对爱情这一概念有更好的了解,只能反映出说话人在当时对于爱情的感受,而一个人的感受是受各种因素影响并且是瞬息万变的。处于热恋中的情侣之间的所有表达甚至是所有行为都可以归结为一句“我爱你”,诗歌也只是其中的一种方式,而很多时候情侣间的表达在句义上是混乱的,在句法上是不符合规则的,但是这些都可以理解为“爱的表述”。这时候,我们回到“爱情是旅途”这一映射中,当恋人中的一方对另一方说“我们陷住了”(We’re stuck)的时候,用旅行的知识来理解爱情的知识是于事无补的,因为说这句话的人想要表达的真实内容是“我不那么爱你了”或是“我们不能再相爱了”,这时候被陷住的绝不仅仅是“爱情”这一“运输工具”,而是两个恋人本身和他们之间的恋爱关系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因此,对于隐喻的分析,并不会让我们对隐喻中涉及的概念本身有多少认知上的进步,但是这样的分析可以让我们对表达者的态度、价值观念有更好的把握。
另外一个对于爱情的隐喻是对映射只发生在上位层次这一原则的挑战,那就是“爱情是火”。这一隐喻是很常见的,在中文里我们就有很多类似的表达,比如轰轰烈烈、干柴烈火。火虽然是一个具体的意象,一个基本层级的概念,但在“爱情是火”这一隐喻中我们很容易找到一组对应的映射:
——情侣对应燃料或者燃料和氧气。
——情侣关系对应燃烧的火焰。
——情侣的共同目标对应燃烧的时长或者剧烈程度。
——情侣关系中遇到的困难对应氧气不足、缺乏燃料或者被浇水等。
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很多类似的隐喻,如“爱如潮水”“爱如闪电”等等,而且我们也很容易在其中找到一组对应的映射关系,究其原因正是Lakoff否定跨层级映射的理由:“基本层级具有丰富的心理意象和知识结构。”[2]210恰恰因为基本层级具有这样丰富的“心理意象和知识结构”,我们才很容易在其中抽象出我们需要的内部结构,而这要归功于人类的想象力,隐喻就是人类想象力最好的体现。同时,这也证明了所谓概念固有的内部结构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人对它的解读和想象。但在“爱情是火”这一映射中可以看到,火是人类生存必须的东西,它可以帮助人取暖、烹饪食物和抵御野兽,火也是光明的一种象征。与此同时,火也是一件危险的东西,稍有不慎它就会演变成一场火灾,又是毁灭的一种象征。因此,对“爱情是火”这一映射的具体分析,让我们看到的是,作这一比喻的人对于爱情的态度,其爱情观中包含的矛盾和对立的思想是根本性的。
对于爱情的其他隐喻的对比分析,证明映射只发生在上位层次概念之间这一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而“基本层级具有的丰富的心理意象和知识结构”刚好可以让人类的想象力得到自由充分的发挥。所谓概念中固有的内部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对概念的认识、解读和想象。但解读和想象并不是天马行空的,而是为了更好地表达自己当时的感觉、态度或价值观念。
五、结语
现代概念体系实际上是传统的二元对立思想的解构,是对语言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去语境化”倾向的一种纠正。因为隐喻的认知机制来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而隐喻又是无处不在的。但是,对隐喻表达的语义分析没有发生在语言所发生的具体的语境、场景或者框架之下,而是只关注隐喻表达的字面意义,这就使得对于隐喻的语义分析和关于隐喻机制原则的建立都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对于隐喻的研究,其最初目的是为了认知,帮助人们更好地把握日常概念体系,但实际上,我们通过隐喻表达的语义分析看出的是,表达者或说话人讲话时的态度、意图和本人的价值观念。本文从文学批评的视角出发,认为批评家和读者对于文学文本的解读和阐释往往只能体现出批评者自身的思想、情感和价值取向。本文通过对“爱情是旅途”这一隐喻的重新解读、关于爱情的其他隐喻的分析和对比,指出映射只发生在上位层级概念这一原则是站不住脚的,而跨层级概念之间的映射是常见的,这恰恰是因为基本层级所具有的“丰富的意象和知识结构”可以让人类的想象力得到自由的发挥。从这些例子的分析中也可以看出,所谓概念内部固有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表达者和分析者的解读和想象,这往往都是为了表达或分析的方便而强加在概念之上的。但是,对隐喻和隐喻表达的语义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更有效地看清表达者或分析者自身的态度、意图和价值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