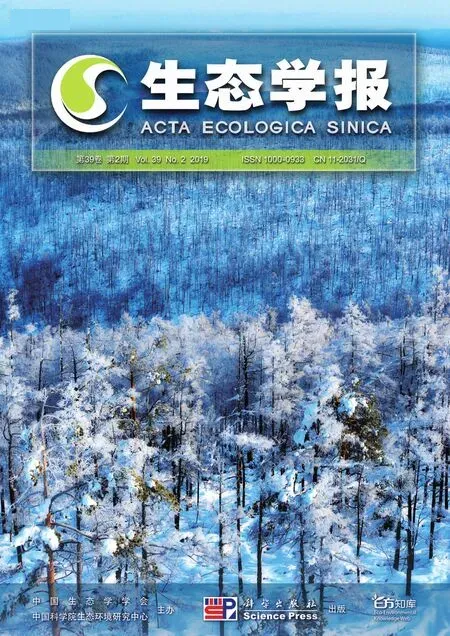城市绿地可达性和居民福祉关系研究综述
屠星月,黄甘霖,*,邬建国
1 北京师范大学地表过程与资源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人与环境系统可持续研究中心,北京 100875 2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自然资源学院,土地资源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北京 100875 3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和全球可持续性科学研究所,Tempe, AZ, USA 85287
城市绿地是指以自然植被和人工植被为主要存在形态的城市用地。其中包含了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内用于绿化的土地,以及城市建设用地之外,对城市生态、景观和居民休闲生活具有积极作用、绿化环境较好的区域[1]。城市绿地提供了丰富的生态系统服务,包括调节局地气候[2-3],减少噪音和空气污染[4- 6],以及节约能源[7]。同时,城市绿地还为居民提供了健身锻炼、聚会交流、休闲游憩等休闲服务,对改善居民健康,维持良好社会关系,提高生活质量,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8-9],对提升居民福祉和提高城市可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10- 14]。国内外学者已对城市绿地的生态环境效应开展了大量的研究,此类研究探讨了绿地对城市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结构以及城市环境条件的影响[15- 17]。而围绕绿地对人类福祉的影响即绿地对满足人类需求,提升居民健康、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的贡献开展的研究还较少[18-19]。从城市生态学,可持续科学的角度,更深入的探讨绿地景观格局与居民福祉的关系,能够帮助我们更全面的理解城市绿地对城市居民福祉以及城市可持续性的贡献,为城市规划建设提供依据,因此有必要对此类研究进行梳理和展望。而居民对绿地的可达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绿地对居民福祉的影响,是连接绿地与居民福祉的重要桥梁。
本文以城市绿地可达性为桥梁,讨论绿地可达性所表征的绿地景观格局如何影响居民使用绿地和居民健康,并梳理绿地可达性与居民需求以及社会经济水平的关系,为城市居民福祉和城市可持续研究提供参考(图1)。本文内容主要包括以下4个方面:1)城市绿地可达性的计算方法和空间分布;2)绿地的特征和可达性对居民使用绿地以及居民健康的影响;3)绿地的空间分布及其可达性与居民社会经济水平的关系;和4)基于城市绿地的供给和居民需求,对绿地满足城市规划要求或居民需求开展的评价。

图1 城市绿地与居民福祉的关系框架图Fig.1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greenspace and residents′ well-being图中列举了绿地可达性、绿地景观格局、绿地使用和居民福祉的主要研究内容。箭头指示了四者的关系,虚线表示了绿地可达性连接绿地与居民福祉的桥梁作用
1 城市绿地可达性的计算方法
城市绿地的可达性是指居民前往绿地的难易程度[20]。多数研究基于居民居住地与绿地之间的距离或行程时间评估绿地可达性[21]。在此基础上,有研究将可达性的涵义进行扩展,除距离和行程时间以外,还考虑绿地面积、绿地质量、交通成本、人口密度等其他因素[22- 27]。除了对客观因素进行评价之外,还有研究分析了居民主观认知的绿地可达性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如果居民认为某个公园较为安全,或园内其他访客与自己具有相同的文化背景,那么居民会主观地认为该公园的可达性较高;收入较高的居民,以及经常步行或骑车前往公园的居民主观认知的公园可达性也更高[28]。
1.1 绿地可达性的计算方法
度量绿地可达性的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四种(表1):行政或统计单元计算法、最小邻近距离法、服务区法和引力模型法。行政或统计单元计算法,是对每一个行政单元,如区、县、街道等,或统计调查单元,如美国的普查统计单元(Census track)等,计算该单元内的绿地面积或绿地数量等指标。该方法简单易行,并且可以直接与统计调查或普查的社会经济数据结合,常用于以行政区或普查单元为分析单元,对比评价国家、区域、城市、区县等尺度的绿地可达性以及绿地可达性与居民社会经济水平的关系[29-30]。在实际情况中,行政边界并不会阻碍居民前往绿地,居民常常会访问其他行政单元中的绿地。因此该方法并不能很好地模拟居民访问绿地的实际情况。但是,由于简单易行,该方法依然被广泛用于评价绿地供给和绿地可达性。

表1 绿地可达性的常用估算方法
最小邻近距离法,是以居住地到最邻近绿地的距离或行程时间作为可达性的度量。该方法常用于分析绿地可达性与居民身体锻炼水平及居民健康的关系[31-32]。依据对距离的估算方法,可分为直线距离法、累计阻力法和路网分析法。直线距离法将居住地与绿地的直线距离(欧氏距离)作为二者之间的距离[33-34]。累计阻力法首先假设城市中的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对居民前往绿地具有不同程度的阻碍作用,确定各土地利用类型的阻力系数,然后搜索居民前往公园累计阻力最小的路径,将该路径的累计阻力作为居住地与绿地之间的距离[20,35];路网分析法,是在道路网络拓扑地图的基础上,利用网络分析法,计算居住地到达绿地的最短步行、公交或驾车距离[21]。三种距离估算方法中,直线距离法最为简单易行,仅需居民区和绿地空间位置即可计算,但所得距离通常小于实际情况中居民前往绿地的距离;累计阻力法在空间位置的基础上,考虑了城市景观的空间异质性,但需要结合土地利用数据进行计算,且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阻力系数需要依据当地社会经济情况确定,因此计算结果具有一定主观性和不确定性。路网分析法需要使用详细的路网数据,计算量大,实现难度较大,因此在研究中的应用不多,但是其所得结果更接近居民前往绿地的实际距离,模拟效果较好[36]。在数据资源和计算能力允许的前提下,选择该方法会更好。
服务区法,是以居民所在居住地在一定时间或距离内能够到达的绿地面积或数量来衡量绿地可达性。通常以绿地为中心生成一定大小的区域,即绿地的服务区,认为该区域内的居民能够在一定距离或时间内到达该绿地。或者,以居住地为中心生成一定大小的区域,认为居民能够在一定时间或距离内到达该区域内的所有绿地。不同的距离估算方法生成的服务区也不同。其中,缓冲区方法较为常见,该方法以绿地或居民区为中心生成圆形服务区,即该区域内所有点到达中心的直线距离小于圆形半径;也有研究是基于道路网络使用网络分析法生成服务区,即该区域内所有点与中心的最短路径距离小于设定的值[37- 39]。服务区法在距离的基础上,还可以考虑可达绿地的面积和数量,能够更全面地反映绿地可达性,常用于绿地可达性空间分布制图。但该方法的计算结果受到研究中设定的可达绿地的距离或时间阈值所影响,该阈值需依据当地社会经济水平及居民偏好进行设定,不同研究所设定的阈值往往不同,因此难以进行对比。
引力模型法,源自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假设居民访问绿地的意愿或概率与绿地的吸引力,以及居民的需求正相关,与居住地到绿地之间的阻力(通常为距离)负相关[40]。该模型的基础表达形式见式(1),其中距离衰减函数f(dij)通常是幂函数形式[31],也有研究使用了负指数函数和高斯函数的形式[41]。该方法在绿地距离和数量的基础上,还考虑了绿地吸引力和居民需求等影响绿地访问的因素,更有助于评估居民访问绿地的行为。引力模型法已广泛应用于估算各类公共服务设施或资源的潜在服务范围制图[42-43]。
(1)
式中,Zij为绿地j对居住地i的服务潜力,Sj为绿地j的吸引力,dij为绿地j与居住地i之间的阻力(通常为距离),f(dij)为距离衰减函数。
1.2 绿地可达性计算中的数据来源
绿地可达性估算所需的数据主要包括绿地分布数据和居民信息。绿地分布数据来源一般有两类,一类是由相关主管部门提供的城市绿地数据,除位置和边界外,通常还包括绿地中的植被类型和配备的公共设施等详细信息[21,44]。另一类则是通过解译遥感影像获得绿地的空间分布数据[38,45]。
居民的相关数据来源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人口普查数据[21,37,46]。该类数据的优点是内容丰富、数据连续性和可比性较好,缺点是数据的统计单元面积较大,难以表达小尺度上的空间异质性。为了获得更细尺度的居民信息,有研究发展了分区密度制图的方法(Dasymetric mapping),通过分析单元的空间叠置,将人口普查数据细化到居住区,在利用了人口普查丰富数据的同时提高了数据的空间分辨率[47-48]。第二类是通过问卷调查获得居民信息[39, 44, 49]。问卷调查的优点是可以按照研究需求设计问卷问题和采样方法,不受已有数据在内容和统计单元上的限制,缺点是成本较高,且不同研究之间的可比性较差[50- 52]。
2 绿地可达性对居民使用绿地和居民健康的影响
研究表明,绿地能够为居民提供锻炼身体的场所,促进居民的身体健康,减少死亡率和慢性病发病率[53-54]。大量研究表明居住地的绿地可达性与居民进行身体锻炼的频率相关[19, 55- 57]。例如,居民的锻炼水平与居住地附近的绿地总面积[58-59]、绿地数量[60],以及最邻近绿地的面积[31,61]正相关,与居住地到最邻近绿地的距离[31-32,62]负相关;绿地中的锻炼设施,如健步道、健身器材、儿童游乐设施等有助于提高居民使用绿地的频率[61]。
不少学者对绿地可达性与居民健康的关系进行了验证。研究发现,居民自评的总体健康状况与居住地附近的绿地面积比例正相关[59],与居住地到最邻近公园的距离负相关[63]。绿地与居民肥胖和超重水平的关系(通常使用身体质量指数即Body Mass Index(BMI)表征,BMI高于特定数值为肥胖或超重)的研究发现,居住地附近的公园数量与女性的BMI负相关[60];表征居住地植被覆盖度和植被生长状况的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 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与居民的BMI负相关[64];居住社区内可供人行走的非观赏性绿地对延长老年人寿命具有显著贡献[49]。
另外,绿地不仅与居民的身体健康相关,还对居民的心理福祉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65]。研究发现,居民的心理健康水平与居住地附近的绿地面积[66]、居民在绿地中停留的时间[67]以及居民使用绿地的频率正相关[68]。有学者针对绿地的可达性和特征以及绿地中的自然体验对各类正面及负面情绪的作用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居住地的绿地可达性[69]和生物多样性[70]能够促进居民放松心情;城市居民在绿地中接触自然或独处有助于减少压力,放松紧张情绪[71- 74]。
3 绿地可达性空间分布及其与居民社会经济水平的关系
3.1 绿地可达性的空间分布
由于对居民的身心健康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绿地被广泛认为是重要的公共资源和环境优质品。但大量研究显示,城市居民所享有的绿地可达性存在较大差异。
绿地可达性空间分布的相关研究发现,绿地可达性在城市的不同区域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尤其是在城区-郊区梯度上。例如,研究发现,美国巴尔的摩市(Baltimore city)城郊较富有的居民享有的400 m步行距离内可达的人均公园面积比城市中心较贫穷的居民更大[75]。有研究指出,美国洛杉矶市发行的公园发展债券,更倾向于在新发展的城郊建立公园[10]。也有不少案例研究发现城区的公园可达性优于郊区。例如,有学者对上海市的公共绿地可达性进行评价,将绿地按照面积大小分为三类,对每一类公园划定可达的距离阈值分别计算可达性,并结合专家打分的公园质量对上海市公共绿地可达性进行评价,发现城区的公共绿地可达性高于城郊,学者指出这可能是由于城市的绿地规划对城郊的忽视,以及政府规定的城区和城郊绿地可达性最低标准不同所造成的[76];沈阳市的公园可达性分布研究也发现,城区能够在15 min内到达公园的人口比例高于城郊[77]。北京市的研究发现,能够1 km内到达公园的居民区面积比例从城市中心向城市外围递减[36]。
3.2 绿地可达性与居民社会经济水平的关系
绿地分布不均的现象不仅体现在空间分布上,还体现在享有绿地的居民社会经济水平上。从环境公平和正义的角度出发,研究者比较了不同种族、文化背景和社会经济阶层的居民,在绿地可达性上的差异。不少研究表明,少数族裔和在社会经济文化方面处于弱势的居民,所享有的绿地通常更少[10,29,52,78- 80]。例如美国亚特兰大市(Atlanta)的一项研究表明,黑人居民较多或社会经济状况较差(收入、家庭经济状况、教育程度、就业状况等)的社区,绿地可达性较低[26]。英国中部的雷彻斯特市(Leicester)的绿地资源丰富,几乎达到英国专家委员会推荐标准的两倍,但是居民中印度人、印度教人和锡克教人(Indian, Hindu and Sikh groups)的绿地可达性仍显著低于其他居民[21]。我国学者在广州中心城区的研究也发现,居民本地化水平和社会经济水平越高,实际享有的绿地越多[39]。
然而,以上发现在不同地区和不同研究中并不一定总是成立。例如,英国苏格兰格拉斯哥市(Glasgow)[81]、美国布里奇波特市(Bridgeport)[82]、和罗克福德市(Rockford)等地[83]的研究发现城市公园可达性与居民的社会经济水平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相关性。而伊朗德黑兰市(Tehran)的研究发现社会经济水平低的居民,其公园可达性更高[34]。我国的相关研究也呈现了多样的结果,例如,北京市城六区的研究中发现街道的居民社会经济水平对城市公园可达性的方差解释率(R2)小于8%,即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实质上的相关性[36]。杭州市市中心42个高人口密度街道的研究表明,不同社会经济水平居民的绿地可达性不存在显著差异[84]。上海市中心城区的研究表明,社会经济水平低的弱势群体公园可达性更高[85-86]。各地区研究呈现的多样化结果,可能是由各地区多样的城市发展过程、历史和规划实践等因素的不同而造成的。例如,我国的城市规划和绿地建设,多由政府决策部门主导,依据城市生态及社会需求“自上而下”地确立和执行[36],并且居民区之间的隔离度相比于西方国家城市较低。同时,绿地和公园的来源多样,既有城市规划建设的成果,也有大量历史遗留的园林[84]。这使得绿地格局和可达性的分布格局更加复杂,而并不仅仅呈现出简单的“富人享有更多绿地资源”的格局和结论。在一些西方城市,绿地与居民的关系也同样受到了历史过程的影响,表现出复杂的关系[75]。因此,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社会经济过程,以及城市管理规划策略如何影响各社会经济阶层居民的绿地可达性是该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
其次,绿地可达性指标和计算方法的差异也会对研究结论产生影响。例如,有研究发现,居民社会经济水平与可达公园的数量负相关,与可达公园的面积正相关。而在将社区安全等影响公园使用的因素纳入公园可达性计算中后,社会经济水平与可达的公园数量及面积都呈正相关[87]。另有研究发现,可达性与居民社会经济水平的关系还受到绿地类型的影响,不同类型公园的可达性与居民社会经济水平的关系也不同[88-89]。所以,在探讨不同研究或不同地区所得结果的差异时,还应当考虑可达性指标和计算方法对结果的影响。
4 城市绿地供给与居民需求的评价
通过合理的城市规划和绿地建设,使绿地能够均等地服务于各个社会阶层的居民,满足居民的需求,是城市绿地可达性研究的重要意义所在。为了在城市中保留人们接触和享受自然的机会,研究者、政府和各种环保组织都试图设定绿地供给的“最低标准”(表2)。绿地供给标准的设定与城市规模、绿地资源以及社会经济背景有密切关系,不同地区及组织所设定的标准差异很大。例如,欧洲环境局(European environment agency)将15分钟内能够到达绿地作为欧洲城市环境质量评价的标准之一[90];为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延长居民寿命,美国的国家娱乐及公园协会(National Recreation and Park Association, NRPA)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10-Minute Walk项目来保证居民能够在10 min内到达公园[91];为了保证居民体验自然的机会,提高居民生活质量,英国的Natural England组织建议所有居民应当能够在300 m内到达面积不小于2公顷的绿地[92]。我国的国家园林城市评审标准规定,城市各城区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不低于5 m2[93]。北京市的绿地系统规划文件,综合考虑可持续发展和宜居城市的要求,将人均绿地40—45 m2以及人均公共绿地15—18 m2设定为2020年之前的绿地建设目标[94]。上海市绿化市容“十三五”规划将人均公园绿地10 m2设定为2020年前的城市绿化建设目标[95]。还有研究指出,当考虑绿地供给时,需要考虑不同类型绿地服务半径的差别[37],不同类型的绿地不能完全相互替代。例如,森林公园不能弥补社区公园的缺乏[96]。英国的Natural England组织为不同规模的绿地规定了不同的服务半径(表2)。
研究者通过估算城市绿地供给和居民需求的分布来识别城市绿地供给不足的地区,为未来的城市绿地规划和管理提供依据。此类研究主要基于居民到绿地的可达性估算绿地的供给水平。除此之外,也有研究基于绿地的自然属性、历史文化特点、活动空间规模、安静程度和设施水平评估绿地对居民的吸引力[45,97],从而更加全面的评估绿地供给。
居民对绿地的需求,通常通过人口数量或密度进行评估[33,98-99]。有研究通过“拥挤指标”耦合绿地的供给和需求,估算在特定情境下的绿地拥挤程度。“拥挤指标”的范例包括,当居民都使用可以在5 min内到达的绿地时人均享有的绿地面积[27],或者居民都使用离家最近的绿地时人均享有的绿地面积[75]。除此之外,一些研究还结合居民的年龄、性别、收入、生活方式及偏好等方面来评估居民对绿地的需求[46,97]。

表2 各地区绿地供给标准
5 结论和展望
目前,国内外学者已广泛开展了城市绿地可达性的相关研究,为深入理解城市绿地与居民福祉的关系提供了科学依据。学者针对不同的研究需求,发展了行政或统计单元计算法、最小邻近距离法、服务区法和引力模型法等多种绿地可达性估算方法,估算中所考虑的因素也更加全面。绿地可达性对居民使用绿地以及居民身体健康和心理福祉的正面影响已得到广泛证实,但大量研究发现绿地的空间分布在城市不同区域内存在较大差异。并且,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低社会经济水平的居民绿地可达性更低,这也带来了环境不公平的问题,但这样的关系在其他地区并不成立。绿地空间分布与居民社会经济特征在不同地区呈现不同的关系,其中原因还有待进一步探讨。为保证居民能够均等的享有绿地,各地学者、政府和组织设定了多种多样的绿地供给最低标准,并结合人口信息,来评价绿地的供给与居民需求的关系,从而识别绿地供给不足的区域。绿地可达性相关研究已得到学界和决策者的广泛关注,本文在梳理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为该领域的未来发展方向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未来研究需要对绿地特征进行更全面的量化。目前对绿地的定量化表征多是基于绿地与居住区的距离、绿地面积以及绿地NDVI进行的。对绿地内部的生物多样性、景观组成和配置、设施水平、活动空间等绿地内部特征的量化研究较少。并且,多数研究只针对少数几个绿地进行实例研究,缺少系统性的研究。因此,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对绿地吸引力进行系统性的量化,探讨绿地的内部特征如何影响绿地与人类福祉的关系。
其次,研究还应当更广泛地考虑不同的绿地类型对各方面人类福祉的影响,在不同区域开展多尺度研究。一方面,目前已有研究中,关注公园对人类福祉的影响的较多,而对其他类型的绿地,如小型公共绿地、社区农圃、住宅私有绿地开展的研究较少,有待进一步探讨。另一方面,目前研究主要是探讨绿地对居民健康的影响,而针对人类福祉的其他方面,如社会关系,社区安全感、恢复力[100]等方面的研究还较少,亟待进一步的拓展。另外,不同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下,绿地对人类福祉的影响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未来还需要在不同区域和不同尺度上开展大量案例研究,探讨绿地与居民的距离,绿地景观组成和配置等因素如何影响居民的福祉,同时在论证中明确表述绿地的类型、使用的指标、研究尺度和分析方法等以便进行综合比较。
第三,有必要进一步开展时空动态研究,探讨绿地与居民福祉的动态关系。目前相关研究多为单一时相的横断面研究,在较短的时间内收集绿地格局、居民的绿地使用情况及居民健康水平信息,分析绿地与居民福祉的关系。未来还需要更多基于多时相的绿地格局以及人群队列的纵向研究,探讨绿地的时空变化对居民使用绿地以及居民健康的影响,分析绿地对居民锻炼习惯以及健康状况的长期影响。同样,绿地可达性与居民社会经济水平的关系也多是单一时相的研究,从空间分布上分析绿地分布的环境公平性,未来的研究应当将城市发展过程、居民人口变化以及规划管理政策变化与绿地的时空格局结合,探讨形成绿地分布格局的社会经济过程,为城市规划管理提出合理建议。
最后,我国在绿地可达性空间分布及绿地供给和需求评价方面积累了大量的案例,但针对绿地如何影响居民访问绿地的行为以及居民福祉开展的研究还较少,亟待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为提升居民福祉和城市可持续性提供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