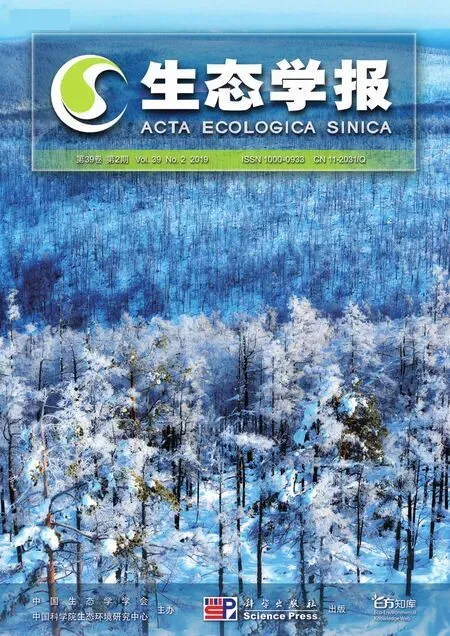基于人林共生时间的森林文化价值评估
樊宝敏 ,李智勇,张德成,魏玲玲,谢和生
1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科技信息研究所, 北京 100091 2 浙江农林大学学科建设办公室, 临安 311300
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是人类文明诞生的摇篮,具有生态、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种服务价值。如何通过科学评估和提升森林价值让森林造福人类?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成为林学家、生态学家们研究和关注的热点问题。1993年,北京林业大学徐化成教授发表《森林的价值观》一文,讨论了森林价值观的相关问题,提出了“充分协调森林各种价值的多重价值观”,并认为“它决定了今后林业发展的方向”[1]。1997年,R. Costanza等学者[2]对全球生态系统服务和自然资本的价值进行了评估,在全球引起广泛关注。2005年,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委员会公布《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综合报告)[3]。2011年,英国发布《英国国家生态系统评估:技术报告》[4]。上述研究都关注了森林和生态系统的多重价值,其中文化价值也包含在内。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对森林经济和生态服务功能价值的量化评估方法已相对成熟,然而对于森林文化价值的量化评估方法却仍处在探索中,并未找到公认的科学方法。李文华院士在2008年出版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的理论、方法与应用》中写道:“由于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科学认识的局限性,目前对于生态系统的一些服务功能还无法进行定量化描述和评价,如一些文化服务功能、对生命价值的估计等”[5]。近期,尽管在中国(不含港澳台,下同)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研究[6]、中国森林资源核算研究[7-8]领域都取得一些新的成果,但是这些研究主要还是侧重森林的生态和经济价值。中国森林资源核算研究项目组(2015年)在研究展望时指出:“此次研究仅开展了林地林木资源和森林生态服务两个方面的核算,还不是一个完整的森林资源核算。今后,还需要进一步开展森林社会文化价值……核算等。”[8]近年来,国外学界Edwards D.[9]、Tabbush P.[10]、Edwards D.[11]等学者通常采用指标体系法[12],或者概念分析法[4]对森林文化价值进行评估。宋军卫[13]、朱霖[14]、潘静[15]、王碧云[16]等国内学者尝试采用条件价值法(CVM)、AHP-模糊综合评价法评估公园或区域的森林文化价值。因此,在当前国民对于生态环境和生态文化的需求不断增长的情况下,研究森林文化价值评估的理论与方法,对于充分认识和培育森林价值,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绿色生活需求,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应用价值。
1 森林文化价值的含义
1.1 内涵与外延
森林的文化价值是森林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森林对人类的健康和精神生活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和满足程度,直接影响着人民的健康状况、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关于森林的价值(或效益),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农业卷》(1990年第一版)中的“森林效益”词条认为包括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3个方面。其中,社会效益,表现为森林对人类生存、生育、居住、活动以及在人的心理、情绪、感觉、教育等方面所产生的作用[17]。国外通常是将森林文化价值作为森林生态系统服务的主要内容之一,称之为“森林的文化服务”。在全球层面,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将生态系统服务划分为对人类具有直接影响的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文化服务以及维持这些服务所必需的支持服务。其中,文化服务是指通过精神满足、发展认知、思考、消遣和体验美感而使人类从生态系统获得的非物质惠益。同时,报告明确指出,文化服务中的精神和宗教价值以及美学价值正在退化[3]。总之,森林文化价值内涵丰富,包括森林教育、审美、健康、艺术创作等许多方面。
1.2 价值构成
森林有益人体健康,森林常成为疗养的理想场所之一。森林还可为人们提供游憩的场所和陶冶性情的环境条件。同时,森林还可为多种科学研究,如遗传、进化、生态和水文研究等提供科研材料或基地[17]。美国环境伦理学家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环境伦理学》(2000年)中,提出了自然生态系统的14种价值:生命支撑价值、经济价值、消遣价值、科学价值、审美价值、使基因多样化的价值、历史价值、文化象征的价值、塑造性格的价值、多样性与统一性的价值、稳定性和自发性的价值、辨证的价值、生命的价值、宗教价值[18]。《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将生态系统的文化服务概括为:文化多元性、精神与宗教价值、知识体系、教育价值、灵感、美学价值、社会关系、地方感、文化遗产价值、消遣与生态旅游10个方面[3]。森林文化价值体系对森林体验者的影响通常是作为整体而起作用的,同时其价值实现又随森林和体验者的具体情况而千差万别。
2 森林文化价值的评估方法
2.1 价值评估相关理论
森林的文化价值评估,所评价的是森林与人交际中所产生的文化现象,是从价值的角度评估森林对人的服务能力或者满足人的需求的能力。这涉及到以下相关理论:(1)时间价值理论。森林的文化价值,与人在森林中逗留、互动共生的时间成正比。时间越长,表明森林的文化价值越高。(2)劳动价值理论。森林中,凝结有人的劳动,人的劳动也是森林文化价值形成的重要因素。(3)自然价值理论。森林的文化价值是自然价值的重要体现,价值的高低与自然力的作用、自然要素的组合都有密切的关系。(4)协同理论。森林文化价值作为一个价值系统,由诸多子系统构成,它的价值并不是各子系统价值的简单相加,而是整体协同的结果。如Mourato 等人[19]所做的绿地对房价影响的分析,作为环境背景总体的舒适价值。(5)梯度理论。在不同区域的森林中,森林的文化价值存在梯度差异。这些理论为评价和发展森林文化价值提供了理论基础。
基于上述理论,我们通过深入的研究和分析进而认识到,森林的文化价值实质上反映着森林对人的吸引力和服务能力,是森林的人气指数和服务水准,可用“人与森林共生时间”(简称人林共生时间)的长短来衡量。它有两种表达形式:一是从森林角度,森林文化价值可用一年之中人们在该片森林中生存的时间总和来体现;二是从人的角度,用一年当中人们平均在(标准化)森林中生活的时间来反映。
2.2 公园尺度的评估方法
在森林公园尺度,森林的文化价值用游人在森林公园中逗留的时间来反映。对于免费的森林公园而言,其森林文化价值的计算公式为:
(1)


表1 森林的文化价值计量单位“文年”的含义
对于收取门票的森林公园而言,其森林文化价值还需要将门票收入折算成时间累加进去。因为门票收入的真正涵义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付出,而且这种付出表明了社会对森林公园文化价值除了直接时间付出之外的又一种认可。所以其计算公式为:
(2)
式中,VFC为收费公园的森林文化价值,I为门票收入,GDP/p为年度人均GDP。
根据森林公园的面积(或者以及森林所占公园比重),可求得单位森林公园面积上森林的文化价值。即:
(3)

2.3 区域尺度的评估方法
研究认为,区域范围内森林的文化价值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基本价值,即区域常住人口与森林共生的基本生活时间所反映的价值。因为森林的文化服务具有溢出效应,即使人不进入森林,森林也会对附近的人产生一定的文化服务,如医疗保健价值[20]。而且服务水平的高低与森林资源的丰富度及质量有密切关系。二是专项价值,森林文化活动(森林旅游为主)过程中人林共生时间所反映的价值。计算公式为:
(4)

(5)
式中,VLT为区域活立木总蓄积量,sL为区域土地面积,0.06为单位森林厚度条件下的标准化的人林共生时间(a),FT为森林厚度指标(单位:mm)[21]。即研究认为,区域的人均基本森林共生时间,与区域活立木总蓄积量成正比。活立木蓄积量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不仅是森林质量、森林文化服务能力的重要标志,而且它是森林在时空中长期积累的结果,是森林凝结的时间长度,在本质上也是人与森林共生的时间长度。作为蓄积量转化为时间的参数0.06,是基于一个理论预设:即中国森林资源最丰富的台湾省,森林厚度10 mm、森林覆盖率60%条件下,人均森林共生时间设定为0.6 a,以此为标准值。
依据区域森林文化价值计算结果,可以相应地计算出以下3个平均指标数据。
(6)

(7)

(8)

上述3个平均指标表达不同的含义。地均森林文化价值指标,表达单位面积土地上,每平方公里的人与森林共生时间的高低,反映土地利用效率,对土地的森林文化价值开发的程度。人均森林文化价值指标,表达每个公民享受的森林文化福利的高低。林均森林文化价值,表达单位面积林地上的人与森林共生时间的多少,反映林业(或园林绿化)部门对森林文化价值开发利用的效率。
3 森林文化价值的评估结果
3.1 公园尺度两个公园案例及全国森林公园评估结果
以山东曲阜为例。山东曲阜的孔庙、孔府和孔林(简称“三孔”),是国人纪念孔子、推崇儒学的圣地。这里生长着1万多株古树名木,是我国面积最大、古树最多、文化价值最高的古树群。它们早已成为儒家文化的精神象征,具有重要的历史、科学和精神等文化价值。根据实地调查、征询曲阜市林业局、旅游局等部门获取相关指标的年度统计数据,通过测算得到了“三孔”森林的文化价值的评估结果。(1)森林文化总价值。2013年,“三孔”接待国内外游客4×106人次,三处景点平均每人次大约游览6h,则共计2.4×107h,因为一年为8760h,故折合2739.7 c.y.。另外,门票收入1.5×108CNY,2013年,人均GDP为33530 CNY,故门票收入换算成价值为4473.6 c.y.。二者相加,得“三孔”文化价值量为7213.3 c.y.。若按森林占总面积的70%,则“三孔”森林文化价值为5049.3 c.y.。(2)单位面积森林文化价值。据“三孔”森林面积161 hm2,可计算出单位森林面积的文化价值为31.36 c.y./hm2。
同样方法,通过到北京植物园的调查,以及咨询北京市园林研究所科研人员,收集并核实游览人数、平均游览时间、门票收入等相关数据,得到北京植物园2011年、中国全部森林公园2015年的森林文化价值[22]。结果见表2。

表2 森林文化价值评估实例
从表2中发现,曲阜“三孔”的森林文化价值最高;北京植物园次之;中国森林公园整体水平最差,且与前者差距巨大。我国各地森林旅游发展极不平衡。接待游客量前30位的国家森林公园,接待了超过20%的全国森林公园的游客量,只占全国森林公园总数的不到1%。很多森林公园建设和服务水平与民众旺盛的森林旅游需求很不相称,这也充分表明我国森林文化价值提升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
3.2 对全国及各省森林的评估结果
基于全国第八次森林资源清查(2009—2013)中活立木蓄积量数据[23],以及国家统计局、国家林业局官方网站公布的2015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常住人口、森林面积、森林旅游人次等数据,通过运用区域尺度森林文化价值评估方法开展模型计算,得到中国及各省份2015年森林的文化价值,如表3。

表3 2015年中国及各省(区、市)森林的文化价值
通过分析上表数据可知,(1)我国各省统计数据(全文数据中,尚缺乏我国台湾、香港、澳门的统计数据)的森林文化价值总量存在很大差异。从青海2.57×104c.y.,到四川1848.28×104c.y.。排在前五名的是四川、广东、云南、福建、黑龙江;排在后五名的是青海、宁夏、新疆、西藏、天津。
(2)地均森林文化价值,从青海0.04 c.y./km2,到上海328.32 c.y./km2。排在前五名的是上海、福建、浙江、广东、北京。这反映在这些区域对土地的森林文化价值开发充分。排在后五名的是青海、新疆、西藏、宁夏、内蒙古,这些区域受自然条件的限制,森林文化不发达,在总体上属于草原和沙漠绿洲文化区。
(3)人均森林文化价值,见图1,从青海0.004 c.y./p,到福建0.342 c.y./p。排在前五名的是福建、吉林、云南、黑龙江、四川;排在后五名的是青海、宁夏、新疆、天津、甘肃。高的地方,反映人的森林文化福利优厚。人均森林文化价值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与森林资源的丰富程度有关。天津、上海排名靠后主要因其森林资源匮乏;北京排名落后则因其森林质量差。河北、山东、江苏、河南等省水平不高,则与这些地方因发展农业而导致的森林覆盖率过低有关。
(4)林均森林文化价值,从青海0.01 c.y./hm2,到上海28.93 c.y./hm2。排在前五名的是上海、天津、江苏、北京、河南;排在后五名的是青海、新疆、内蒙古、宁夏、甘肃。高的地方,反映对森林文化价值的需求旺盛,且多属于人口稠密的省(区、市),在这些地区需要加大森林文化建设。

图1 2015 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人均森林文化价值Fig.1 Per capital forest cultural value of China and every province in 2015全国数据中未包含港澳台数据
4 结论和讨论
4.1 “文年评估法”是森林的文化价值评估的可选方法
森林的文化价值得到学界和社会的广泛认同,但同时其价值高低也存在着难以量化评估的问题。这成为一项世界性科学难题。《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MA)》和《英国国家生态系统评估报告(UKNEA)》的文化服务评估部分,试图找到这样一种合理的量化方法,但没有成功[3-4]。森林的文化价值评估的难点在于其不确定性,导致以往的研究都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评估方法。要么采取繁琐的多指标的模糊打分综合指数评估方法[13,16],要么采取偏重主观的问卷统计的条件价值评估方法[14-15]。不同的人运用这些方法,会得到不同的结果。课题组认识到以往评估方法存在的弊端,研究消除森林文化价值不确定性的方法,经过反复讨论,提出用“人林共生时间”的长短来衡量森林的文化价值的观点,提出“文年”的概念,终于找到了一种准确、客观、同时包含人和森林双方因素的评估方法。应该说,该方法找到了森林文化价值评估的正确途径,是一项重要的科研创新成果。
用“文年”作为森林文化价值的计量单位,比用“货币”或许更为科学。这不仅是因为时间的客观性和可比性都优于货币,而且是由森林文化价值本身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国外学者们也大多主张,生态系统的文化服务和价值主要体现在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伦理关切和美学判断,而这方面是不能从金钱方面来进行有意义的表达的[4]。
研究表明,森林文化价值的评估适合采取整体价值评估的方法。本研究提出的“文年评估法”,没有按照以往评估方法的思路,即先划分各项指标进行单项价值评估、再加总求算整体价值的传统方法,主要是考虑到各指标之间会产生协同效应,先分后总的评估结果与总体评估结果会有很大差异。与以往评估方法相比,文年评估法的优点在于计量客观、简便易行;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的;既可评估总价值,又可评估单位面积森林的价值,便于不同森林之间的比较。因此该方法可供选择,值得推广应用。
需要说明的是,本方法所评估的森林的文化价值是整体价值、一年当中实际产生的价值,所以本方法适用于森林文化价值的年度的实际产生的总价值评估。至于其价值是如何构成的,各占何比重,本方法没有涉及,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予以分析解决。本方法不能取代以往的评估方法,如指标评估法、条件价值评估法等,它们也有一定的优点和特定应用范围。在评估实践中,本方法可与其他方法结合应用,在整体评估的基础上,运用Delphi、层次分析法等确定不同文化价值的比重,进而分解评价。
本文讨论的是“森林的文化价值”,而非“森林文化的价值”。虽然两者有密切的关联,但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两者的关联在于,通常情况下前者是过程、原因,后者是产出、结果,后者由前者演生而来;但后者对于前者又有放大和促进作用,很多情况是人们先通过一定文化传播途径知道了某片森林,而后才进入了那里。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森林对人的文化价值,必须是人涉足了这片森林或者森林所在区域才会产生;后者则是森林文化产品(如与森林有关的诗词、画作、影像等艺术作品)对人的文化价值。当然,“森林”本身不一定是天然林,也可以是包含许多人类创造的带有艺术性的产品。关于“森林文化的价值”评估方法,在学术界也有讨论[24-25]。
4.2 建议在公园和区域两种尺度开展全国森林的文化价值评估
森林文化价值的及时监测与准确评估,是价值提升的认知前提。通过对公园和区域尺度上每块森林的科学评估,明确其文化价值所处等级,判断其优势和存在问题,提出未来改进的方向和途径。
建议在公园尺度上,包括国有林场、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森林文化教育基地、森林康养基地等,在观测统计游客或参与人数的同时,增设人员停留时间指标的观测数据。这方面今后可应用智能化大数据等科技手段,进行精准统计、实时更新。根据参与人数、停留时间、门票收入等指标,计算森林的文化价值。本文提出的公园尺度评估方法,主要考虑了时间、人数、门票因素,没有考虑森林质量、景观等内在机制影响因素,这是在实际建设中需要注意的。
在区域尺度上,包括全国、各省、市、县域等不同范围,参照本文提出的方法,统计森林文化活动相关指标,开展森林的文化价值评估。同时,结合开展森林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评估,对森林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及其服务能力做出整体评估。
4.3 建议着力提升我国森林的文化价值
森林价值有高低之分,研究建设包含文化服务的高价值森林,意义重大。高价值森林,是一种多功能森林,其生态、经济、社会、文化多种功能协同发挥。单一功能虽不很高,但综合功能一定很强。森林的多种功能和价值不能相互割裂,而是互相影响,必须统筹考虑、系统协同。
增进人民的生态福祉,重在提升森林的文化价值。核心是运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通过培育优质森林、建设人居森林,让人们走进森林、生活在森林,扩展人林共生时间。从监测评估、森林建设、设施完善、生态教育、运营服务等方面采取综合有效措施,建设“高文化价值森林”,推动我国森林价值由低到高的不断跃迁。尤其是在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河南、山东、河北等人口稠密、经济社会发达的省(区、市),对森林文化价值需求强烈,应着力增加森林资源数量,提高森林质量,努力提升森林对社会的文化服务水平。对于人口相对稀少的地区,则应通过科学调配水资源,改善交通和宜居条件,逐步增加森林和人口,从而提升森林的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