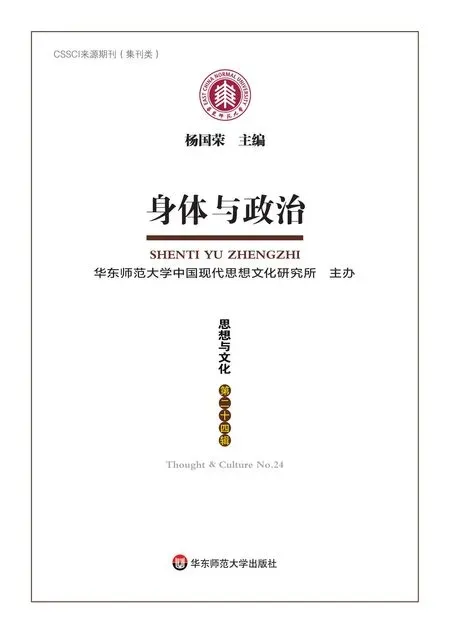何为儒家政治哲学?
——一种比较和建构的视角
越来越多的儒学研究者开始思考作为当代政治哲学研究对象的儒学,如何在经历西方学科化冲击以及西方政治哲学洗礼后,以清楚的政治哲学研究方式和问题意识予以诠释。对这个问题的讨论,除了要有对儒家政治思想精准的把握之外,还需要对如何借鉴西方政治哲学理论体系研究儒家政治哲学有着正确的理解。时至今日,对儒家政治哲学的研究很难说有了学界公认的成果,有诸多争论还是在“借鉴英美政治哲学分析方法”和“立足中国政治思想史”之间做选择。(1)冯友兰对西方分析方法很推崇,认为“用逻辑分析方法解释和分析古代的观念,形成了时代精神”(冯友兰: 《中国哲学简史》,涂又光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30页)。但同时他又认为分析方法不应该是儒学研究的唯一方法,分析方法作为一种“正面的方法”应该与“直觉的方法”(负面的方法)结合使用,因为分析的方法是有局限性的,“古代哲学家的观念,其原有形式,不可能像现代解释者所表述的那样清楚”(冯友兰: 《中国哲学简史》,涂又光译,第382页)。笔者认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既用了西方逻辑分析方法,又重视中国思想史,是二者很好的结合,值得儒家政治哲学研究者借鉴。笔者认为儒家政治哲学研究需要首先破除关于儒学的中西之争和“史”“思”之争,搁置类似儒家政治哲学合法性的讨论。儒家政治哲学不同于西方政治哲学,有其自身独特的研究对象,重视对丰富的儒家政治思想史材料的研究,包括对社会历史背景、文献考证以及经典诠释等问题的研究。儒家政治哲学又不同于儒家政治思想史,需要充分借鉴西方政治哲学方法论架构,其根本哲学问题意识是建构普适中西的儒家政治规范性。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建构主义源自罗尔斯的政治哲学理论,属于一种全球性的建构主义,试图涵盖所有规范性问题,其理论体系对探讨如何建构儒家政治规范性有着重要借鉴意义。
一、 建构儒家政治规范性的“实践观点”和“慎思过程”
在当代西方哲学理论中,关于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理论派别有多种划分,包括康德建构主义、休谟建构主义、本土建构主义和全球性建构主义等等。(2)C.M. Korsgaard, “Realism and Constructivism in Twentieth-century Moral Philosophy,”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Research, 28(2003): 99-122; C.M. Korsgaard, The Sources of Normativ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罗尔斯将建构主义与理性直觉主义进行对比,认为理性直觉主义是由关于良善理性的不言自明的真理(self-evident truths about good reasons)构成;这些良善理性由一种道德秩序所确定,而这种道德秩序先于并独立于我们关于人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的概念。(3)J. Rawls, Collected Papers, Samuel Freeman(e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344.罗尔斯认为,与理性直觉主义不同的建构主义是基于正义原则的确立程序——原初状态各方的选择过程,并且这种程序在政治活动中经常被用来阐释某种特定的道德秩序。(4)J. Rawls, “Kantian Constructivism in Moral Theory,”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1980, pp.515-572.按照建构主义的观点,建构规范性的最终目标就在于解释这种道德秩序如何能够对个体产生约束。同样,建构儒家政治规范性的目的就在于解释儒家政治思想中所蕴含的以“为政以德”和“政以正人”为基础的“王道”和“仁政”理论如何能够对现实政治生活中的个体产生约束。
罗尔斯政治哲学建构主义思想最为显著的一个特点是试图摆脱有争议的关于价值问题的形而上学预设。(5)J.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95-120.与罗尔斯的观点类似,劳思光将儒学解释为“成德之学”,也是为了摆脱儒学价值问题中的形而上学预设。劳思光对在价值问题中寻找形而上的道德秩序持怀疑态度,认为对儒家义理的讨论应该诉诸孔孟的主体自觉,不应走“宇宙论”进路,不能将道德问题建立在外在世界所谓的“客体”之上。劳思光指出:“吾人如确知价值问题不是可通过客体性以解释者,则凡一切诉于存有以说价值之理论,无论如何复杂精巧,基本上必不能成立,由此,一切以形上规律或宇宙规律为依据,而欲解释价值之说,亦皆有其根本困难。”(6)劳思光: 《新编中国哲学史》第二卷,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7—89页。笔者认为,儒家政治哲学研究也要放弃形而上学进路,避免在儒家政治思想中寻找或预设某种客观独立的规范性事实。
关于是否存在客观独立的规范性事实,除了建构主义以外,当今西方哲学理论中的各种实在主义(Realism)和表述主义(Expressivism)都试图给出自己的解答。实在主义认为存在客观独立的规范性事实,而表述主义和建构主义则认为不存在独立于个体实践观点(practical point of view)的规范性事实。笔者认为,表述主义更多持一种自然主义立场,重点研究规范性如何能够在不诉诸独立的道德秩序的前提下,更好地表述逻辑和语义学世界。建构主义则批评实在主义无法证成规范性的客观性和权威性;此外,建构主义认为实在主义所坚持的客观独立的规范性概念,在某种程度上会束缚个体,减少个体所能掌控的领域,从而损害个体的自主(autonomy)。(7)罗伯特·斯特恩(Robert Stern)认为实在主义可以康德式地解决自主性的问题,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客观独立的规范性带给个体的“义务”,这种义务既不是外在某种权威强加给个体的,也不是限制个体自主性的客观价值概念,应该把义务理解为个体自我提升道德修养时体会到的一种紧张,具体而言,就是不完美的且经常受非理性驱动的现实个体,在遇到客观的道德规范时所体会到的紧张。参见R. Stern, Understanding Moral Obligation: Kant, Hegel, Kierkegaar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210-223。概括而言,建构主义认为规范性起源于个体自我概念化的慎思活动,其最终目标是解释道德秩序如何能够对个体产生约束。(8)J. Lenman & Y. Shemmer, Constructivism in Practical Philoso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3-6.
按照华莱士(R. Jay Wallace)的观点,建构主义和表述主义其实是针对不同问题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在其对克里斯汀·科斯伽德(Christine Korsgaard)的建构主义批判中,华莱士认为尽管建构主义和表述主义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不同,但两者关于规范性的分析是相容的,都是围绕个体实践观点(practical point of view),特别是建构主义认为规范性事实就是建立在个体实践观点之上的。(9)华莱士认为,建构主义者可能会参考表述主义关于规范性的语义学分析,同时坚持自己的关于规范性的客观性和权威性的立场。(R.J. Wallace, “Constructing Normativity,” Philosophical Topics,32(2004): 451—476.)关于建构主义和表述主义的分歧,当今元伦理学界多有争论,詹姆斯·雷曼(James Lenman)同意华莱士的观点,认为建构主义和表述主义不但可以相互结合,而且这种结合还会同时提升这两种理论。(J. Lenman & Y. Shemmer, Constructivism in Practical Philoso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戴尔·多尔西(Dale Dorsey)也支持华莱士关于建构主义和表述主义之分歧的分析,但多尔西认为如果建构主义采纳了一种语义学的分析路径,就会陷入一种关于规范性意义的循环论证,由此多尔西认为建构主义应该坚持对规范性的形而上学分析,此外认知主义者的语义学理论会阻碍建构主义关于规范性的形而上学分析。(D. Dorsey, “Subjectivism Without Desire,” Philosophical Review, 121(2012): 407—442.)在建构主义者看来,“实践观点”是慎思个体(deliberating agents)基于自身政治文化背景而产生的各种关于道德秩序的观点,主要受到慎思个体“意动态度”(conative attitudes)的影响,这些态度包括各种情感欲求、信念以及意图等等,同时实践观点蕴含在慎思个体所做出的评估性的判断之内,赋予个体各种规范性判断真值。(10)S. Street, “What is Constructivism in Ethics and Metaethics?” Philosophy Compass, 5(2010): 363-384. M.E. Bratman, and J. Lenman, “Constructivism, Agency, and the Problem of Alignment,” Constructivism in Practical Philosophy, (2012): 81-98.
很多受西方哲学影响的现当代儒家学者都强调儒家思想的实践倾向,认为儒家思想理论体系的建立总是以道德实践为目的,而且很多理论主张也是建立在实践观点之上。(11)笔者赞同劳思光所言:“我愿意诚恳地表明,我确信中国哲学的基本旨趣,不在于思辨,而在于实践。说得更确切些,中国哲学是以‘自我境界’为主题的引导性哲学。”参见劳思光: 《关于中国哲学研究的几点意见——代发刊辞》,载刘笑敢主编: 《中国哲学与文化(第一辑)》,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页。例如,劳思光坚持把以道德实践为导向的“陆王心性论”视为宋明儒学的中心,而对更具思辨色彩的“周张宇宙论”和“程朱形上学”进路提出批评。(12)参见劳思光: 《新编中国哲学史》第三卷,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同样,为突出儒家的实践进路,牟宗三将宋明儒学分为两种形而上学:“只存有不活动”的形而上学和“即存有即活动”的形而上学。牟宗三认为程朱理学是“只存有不活动”的形而上学,是“别子为宗”的“本质伦理”,发展的是缺乏实践活动的静态道体;以“周、张、程颢、五峰、陆、王、蕺山”为代表的是“即存有即活动”的形而上学,是重归孔孟的“方向伦理”,是在道德人心上有着实践功效的儒家正宗(13)牟宗三说“别子为宗”,并不是说程朱理学不合法,而是说程朱理学所论非早期孔孟儒学的核心。牟宗三认为,孔孟儒学的核心是围绕仁义,其后的儒学也应该从不同方面对仁义进行解读以承继孔孟;而程朱理学与道家甚至西方抽象形而上学思路接近,因而不是孔孟“嫡传”。关于谁才是儒学正宗,谁是儒学本质,牟宗三有过具体论述:“自今日观之,孔子后有二百年之发展,有孟子,有荀子,亦有不能确知作者之名之作品,如《中庸》,如《易传》,如《大学》,时时在新中,究谁能代表正宗之儒家?究谁是儒家之本质?孟子固赫然之大家,然荀子又非之。在先秦,大家齐头并列,吾人只知其皆宗孔氏,并无一确定传法之统系。吾人如不能单以孔子个人为儒家,亦不能孤悬孔子于隔绝之境,复亦不便如西方哲学史然只以分别地论各个人之思想为已足,则孔子之生命与智慧必有其前后相呼应,足以决定一基本之方向,以代表儒家之本质。此点可得而确定否?如能确定,则于了解儒家之本质,孔子生命智慧之基本方向,必大有助益。如不能确定,则必只是一团混杂,难有清晰之眉目。”(牟宗三: 《所谓“新儒学”: 新之所以为新之意义》,《心体与性体》,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0页。),其背后坚持的是自孔孟时期开始的实践观点——“孔子以人格之实践与天合一而为大圣,其功效则为汉帝国之建构。此则为积极的,丰富的,建设的,综合的”(14)牟宗三: 《道德的理想主义》,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第12—13页。。正是依据这样的实践观点,牟宗三认为良知通过“坎陷”而致民主政治,儒家政治思想一定会在现实中实践为现代民主制度。
牟宗三通过讨论“人具有智的直觉”强调了儒家思想的实践观点。借鉴康德的“智性的直观”概念,牟宗三从“思辨的证立”和“实践的证立”(15)郑家栋: 《本体与方法——从熊十力到牟宗三》,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70—279页。两方面论证“智的直觉不但是理论上必肯定,而且是实践上必呈现”(16)牟宗三: 《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台北: 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193页。。牟宗三认为:“智的直觉不过是本心仁体底诚明之自照照他(自觉觉他)之活动。自觉觉他之觉是直觉之觉。自觉是自知自证其自己,即如本心仁体之为一自体而觉之。觉他是觉之即生之,即如其系于其自己之实德或自在物而觉之。智的直觉即本于本心仁体之绝对普遍性、无限性以及创生性而言。”关于“智的直觉”如何可能,牟宗三认为这不是理性思辨所能确证的,必须要依靠“实践的亲证”。例如《易传》中“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成之者性”,牟宗三认为其中前半句“一阴一阳之谓道”是基于经验现象所做的理性思辨,而后面“继之”的过程则要依靠个体自身“智的直觉”的实践。牟宗三进一步指出:“理解不只是知识意义的理解,还有实践意义的理解。我们不只是思辨地讲理性之实践使用,还有实践地讲理性之实践使用。不只是外在的解悟,还有内在的证悟,乃至澈悟。”(17)牟宗三: 《心体与性体》(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44—145页。
牟宗三基于儒学的实践观点对“人具有智的直觉”的分析,与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建构主义围绕实践观点对规范性的分析有很多相似之处。如上文所述,建构主义认为规范性源自个体自我概念化的慎思活动;实践观点受个体背景和意动态度影响,蕴含在慎思个体所做评估性的判断之内,赋予个体各种规范性判断真值。在牟宗三看来,“智的直觉”受到个体实践观点的驱使,同时基于个体思想文化的背景,“自觉觉他”地建构出能够在实践中呈现并能依据个体实践评估的规范性判断。按照牟宗三和建构主义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将建构儒家政治规范性理解为运用“智的直觉”的慎思过程。
这样一种建构的活动过程具体到底应该如何理解?斯蒂芬·达沃尔(Stephen Darwall)、阿兰·吉布特(Allan Gibbard)和彼得·雷尔顿(Peter Railton)认为:“建构主义者一般都是过程主义者,他们根据一些设想的过程判定道德标准的组成原则……并且坚持所有关于道德事实的探讨都不能脱离某种特定的过程。”(18)S. Darwall, A. Gibbard, and P. Railton, “Toward fin de Siecle Ethics: Some Trends,”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1992): 115-189.当代政治哲学建构主义者的一个普遍共识就是关于规范性的讨论总是基于某种过程的结果,而这种过程往往是一种慎思活动过程。具体而言,个体规范性的本质源自个体基于各种实践观点而进行的慎思活动过程,并且我们愿意接受这些慎思活动所蕴含的基本道德秩序的约束。这种慎思活动在早期儒家中较为明显,例如沈有鼎在《中国哲学今后的开展》一文中对秦汉时期的儒家文化做了总结:“以儒家的穷理尽性的文化为主脉的……充满着慎思明辨的逻辑精神的……是刚动的、创造的、健康的,理想的、积极的、政治的、道德的、入世的。”(19)沈有鼎: 《中国哲学今后的开展》,载郭齐勇主编: 《中国哲学史经典精读》,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46,249—250页。笔者认为像孟子的“求其放心”,陆九渊的“先立其大者”和“发明本心”,还有王阳明的“致良知”等,本质上都是强调关于道德实践的慎思活动。从这一角度,我们或许可以更好理解上文所述牟宗三对“即存有即活动”和“只存有不活动”的区分,牟宗三之所以将“即存有即活动”的陆王心性学视为孔孟嫡传的儒学正宗,正是因为“即存有即活动”强调基于道德实践的慎思活动过程。
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建构主义对于建构规范性过程的理解,也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例如纳迪姆·侯赛因(Nadeem Hussain)认为规范性的建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规范性,因而也是其他某种过程的结果,如果建构主义者坚持过程主义,将不可避免地陷入无限倒推。(20)N. Hussain, and N. Shah, “Misunderstanding Metaethics,” Oxford Studies in Metaethics, 1(2006): 409-426.同样,如果将运用“智的直觉”视为一种规范性的建构过程,那“智的直觉”又是如何能够独立于其自身而被证成的呢?在笔者看来,建构主义者可以假想一系列过程来阐释某种规范性,当然也可以相应地同时假想另外一系列过程来阐释某种相反的规范性,但难题在于,建构主义者无法依据任何内在的规范性事实对这平行的两个系列过程做出评判,如果诉诸外在的某种规范性事实,则又会建构出新的平行的两个系列过程,然后这种难题会不断重复。
面对上述问题,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规范性建构过程的内在机制和依据。科斯伽德认为规范性的建构过程本质上是一种自主选择的过程,正如罗尔斯提出的正义原则就是其所设想的“无知之幕”背后各方进行自主选择的结果。笔者认为,儒家政治规范性的建构背后也有一种自主选择过程,即儒家政治哲学研究者自主选择儒家政治思想的主体地位。在牟宗三看来,西方民主政治的落实必须要首先坚持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即坚持“三统”——“道统之肯定,此即肯定道德宗教之价值,护住孔孟所开辟之人生宇宙之本源……二、学统之开出,此即转出‘知性主体’以容纳希腊传统,开出学术之独立性。三、政统之继续,此即由认识政体之发展而肯定民主政治为必然”(21)牟宗三: 《道德的理想主义》,第3页。。
有些学者可能会提出,强调这种自主选择行为,似乎只重视主体选择的“自愿”,而忽视主体选择的“理性”。(22)A. James, “Constructing Protagorean Objectivity,” Constructivism in Practical Philosophy, (2012): 62-65.在建构儒家政治规范性的过程中,儒家政治哲学研究者是否仅仅需要考虑“自愿”坚持儒家政治思想的主体性?坚持“三统”的依据是什么?是否仅仅出于对儒家思想的“温情和敬意”?这背后是信仰还是有理性依据?当自由主义学者批评一些儒家学者对“圣人之言”的推崇只是基于“非理性”的信仰时,这种自由主义的批评本身是否就一定是“理性”的?阿隆·詹姆士(Aaron James)认为,在建构规范性的过程中个体的自主选择必须遵循一定的理性依据,但是个体必须首先要具备评判自身或者他人的哪些选择行为是理性的理性能力,才能确立所谓的理性依据。(23)A. James, “Constructing Protagorean Objectivity,” Constructivism in Practical Philosophy, (2012): 70-71.笔者认为阿隆·詹姆士的观点部分回答了上述问题,但仍然面临一个显著的困难,就是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个体的理性能力千差万别,到底应该如何评判不同个体的理性能力呢?如果存在一个评判标准,我们又是如何保证这个标准并不诉诸任何独立于个体选择行为的规范性事实呢?
试验结果数据以平均数±标准差(±s)的形式给出,采用SPSS 13.0统计软件进行试验的数据统计分析。其中小鼠骨髓细胞微核试验采用双侧t检验、小鼠骨髓细胞微核试验采用Wilcoxon秩和检验、90 d喂养试验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行统计处理。
刘述先对“理一分殊”的现代阐释似乎能够部分回答这个问题,“理一”只是预设一种类似普适价值的评判标准,是理想性和终极性的存在,但是却不是实体性或构成性的存在。“没有人可以给予‘理一’以完美的表达,我们只能向往‘理一’的境界。它不是实现宇宙的构成分子,故不是‘构成原则’(constitutive principle),而是我们向往的目标,乃是‘规约原则’。”(24)刘述先: 《理一分殊与全球地域化》,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76页。“分殊”是说“理一”这一理想评判标准在现实实践中有不同的表现。(25)关于刘述先“理一分殊”的讨论,参见陈鹏: 《“理一分殊”的现代重建——论刘述先儒学探索的核心线索》,《哲学研究》,2017年第7期。按照这种理解,在儒家政治思想中,“为政以德”或行“仁政”的“圣王”只是我们所向往的一种理想目标或境界,可以作为“规约原则”实现对现实执政者“理性能力”的评判,但是这种评判只能是终极意义上的。究竟如何“为政以德”,什么才是“仁政”,谁是“圣王”,在不同政治文明思想和实践中对这些问题有着不一样的理解和回答。刘述先的“规约原则”终究只是在理想层面预设了存在“理一”,却无法独立于各文明思想中的理性而证成存在客观的“理一”,因而很难在现实实践层面说明到底如何制定评判标准。
阿隆·詹姆士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个体在现实实践中无法知晓他者的选择行为是否基于某种理性能力,因而个体无法依据这些选择行为制定任何评判标准。阿隆·詹姆士认为基于个体自主选择行为的规范性被建构的前提条件,并不是非要有什么唯一普适的评判标准,也不必须从他人的理性能力中寻找客观的依据,只要这种建构的过程是个体运用自身的理性能力进行思考的过程。(26)A. James, “Constructing Protagorean Objectivity,” Constructivism in Practical Philosophy, (2012): 73-74.阿隆·詹姆士的这个回答看上去可以很好地解决建构规范性过程中的评判依据问题,但是对于儒家政治哲学研究而言可能会带来新的问题。如果不需要“唯一普适”的评判标准,也不需要考虑他人的理性观点,那么一些儒家政治哲学研究者完全可以将自己在他人眼中的“信仰”解释为运用自身理性能力的思考过程,如此一来,儒家政治哲学研究,特别是儒家政治规范性的建构可能会陷入彻底的“多元相对”。(27)篇幅所限,笔者在本文不再过多讨论关于“相对主义”的一些哲学论说,而主要基于当代新儒家(大陆、港台和海外)一些观点,在儒家政治哲学的框架内探讨这个问题。
深受西方多元主义影响,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杜维明提出儒学知识分子的概念,即“这种知识分子不一定要属于中国。任何一个知识分子,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只要是知识分子,就会碰到儒家的问题。这种知识分子的终极关怀,可以来自基督教,可以来自佛教,可以来自伊斯兰教,可以来自各种其他的精神文明,但它的问题是儒家的”(28)杜维明: 《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495页。。杜维明的论述一方面坚持了某种多元主义,对“儒家知识分子”背景不做任何限定,但同时又预设了某种普适的“儒家的问题”。杜维明关注的是多元现代性以及不同文明间的对话,其最终目的在于论证儒学有可能创见性地回应西方重大普遍性问题。(29)“儒学有没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这个问题,是建构在一个基本的设准上的。这个基本设准是,儒学能否对西方文化的重大课题做出创建性的回应。因为儒学不能只是停留在中国文化的范畴里,也不能只是停留在东亚文化这个范畴里。儒家文化一定要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而西方文化是指现代的西方文化。”(杜维明: 《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第486页。)虽然杜维明一直强调他只是在讨论一种“可能性”,似乎“习惯于西方开放多元的方式”,对儒家价值“正当性”和“终极性”的“担负远没有上一代那么沉重”,但是杜维明一直坚信存在普适其他文明的“儒家的问题”,并提出“儒家基督徒”、“儒家伊斯兰教徒”的概念。(30)参见刘述先《港、台新儒家与经典诠释》,载《儒家哲学研究: 问题、方法与未来开展》,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干春松也同意存在普适的“儒家问题”,但认为“问题的源起则必然得来自于中国及其周边区域”,担心杜维明的“世界眼光”反而遮蔽“中国问题”,也就是说,“当儒家成为多元维度中的一元,其价值的独立性和终极性会被虚无化。最终,儒家在由东亚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消失在‘世界’中”(31)参见干春松: 《儒学史的叙述与建构反思》,《学术月刊》,2015年第11期。。笔者部分赞同干春松的观点,属于“儒家的问题”的儒家政治规范性可以是普适的,但为了承认现实中存在对儒家传统的“温情和敬意”以及避免理论上“儒家的问题”被“世界眼光”所遮蔽,儒家政治规范性的评判标准必然是“多元”的,同时要意识到建构“普适”的儒家政治规范性的前提条件必须是如詹姆士所说的“运用理性能力进行思考的过程”。本文接下来将具体讨论这种过程对于中西比较视域下儒家政治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二、 中西比较中的“输入阶段”和“输出阶段”
一些西方政治哲学建构主义者,像迈克尔·布拉特曼(Michael Bratman)、莎伦·斯特里特(Sharon Street)、杰·华莱士(R. Jay Wallace)等,将本文所述“运用理性能力的思考过程”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输入阶段,即提交个体想要证成的基于理性能力的规范性判断,第二个阶段是评判阶段或输出阶段,即接受个体其他基于理性能力的规范性判断的评判。(32)M.E. Bratman, “Intention, Practical Rationality, and Self—governance,” Ethics, 119(2009): 411-443.笔者认为现在部分大陆新儒家立足公羊学,强调国内政治文化担当(33)关于大陆新儒家及其主要观点的界定学界尚有争议。王达三认为大陆新儒家“是指当下中国大陆的一批以儒家情怀、儒家理念、儒家立场登台亮相的中青年文化保守主义者,代表人物是蒋庆、陈明、康晓光”(《“大陆新儒家”与“现代新儒家”——方克立先生信读后》)。李明辉认为其“是主要以蒋庆为中心,包括陈明在内的一小撮人的自我标榜”(《李明辉: 我不认同“大陆新儒家”》)。“澎湃新闻采访了大陆儒学界的一些学者如干春松、白彤东、李存山、曾亦、方旭东、唐文明等,就李明辉提出的一些问题进行回应,采访内容分别以《港台新儒家未必切近大陆现实》(1月26日)、《港台新儒家对传统中国政治肯定得太少》(1月27日)和《儒学复兴需要代际接力》(1月28日)为题发表。还有其他一些关心儒学与未来中国走向的学者也通过媒体发表自己的看法。3月28日,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组织台湾儒学界十几位学者以‘儒学与政治的现代化’为题举办‘李明辉澎湃新闻专访座谈会’,与会的大多数学者都提交了正式论文。4月7日,新浪历史频道发布对蒋庆的长篇专访《王道政治优胜于民主政治》,其中蒋庆就相关争论的各个方面谈了他的看法。”(唐文明: 《“回到康有为”与陆台新儒家之争》,《中华读书报》,2015年5月20日。),其实是属于布拉特曼的输入阶段,即自我确证阶段,其首要目标是将儒学证成为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基准。而一些港台以及海外儒家立足心性学并强调国际多元文明沟通,则属于布拉特曼的输出阶段,即经受评判,其首要目标是使儒家政治规范性经受住西方政治文明中的规范性判断的评判。这两个阶段之间并无矛盾,其最终目标都是为了建构普适的儒学政治规范性。这两个阶段看似有先后,但是如果儒家政治哲学研究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即基于近代以来几代儒家学者的中西比较的研究成果,则有可能使得“输入”和“输出”同时进行,但前提是必须有效应对“输入”和“输出”阶段中的各种“压力”。
具体而言,布拉特曼认为在输入阶段,那些等待被证成的基于理性能力的规范性判断,会受到源自个体自身各种实践观点的压力,如上文所述,这种实践观点源自个体自身政治文化背景,主要受到个体“意动态度”(conative attitudes)的影响,这些态度包括信念和各种情感欲求。(34)M.E. Bratman, and J. Lenman, “Constructivism, Agency, and the Problem of Alignment,” Constructivism in Practical Philosophy, (2012): 81-90.具体举例而言,如果我们将当下一些大陆新儒家关于政治儒学的研究视为处于这种输入阶段,或许能更好理解,为什么这些大陆新儒家更强调儒家政治文化担当,试图回到康有为关于“保教”的问题意识(35)干春松: 《宗教、国家与公民宗教——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孔教设想与孔教会实践》,《哲学分析》,2012年第2期。,甚至借公羊学讨论“儒教之国”的问题。(36)曾亦: 《公羊学与中国传统政治的基本特点——以“王鲁”说为中心》,《思想与文化》,第24辑。这主要是因为大陆新儒家不仅要面对西方学科化冲击以及西方政治文明的影响,还要面对自身对儒家传统的“温情和敬意”甚至“信仰”所带来的压力,从而“护教心切”。(37)这里一些大陆新儒家的“护教心”类似刘述先所论述的第二代新儒家的“护教心”。刘述先认为一些港台和海外新儒家,作为第三代新儒家“习惯于西方开放多元的方式,负担没有上一代那么沉重,以其只需说明,在世界诸多精神传统之中,儒家能够站一席地,便已经足够了。他们不再像第二代新儒家,由于面对存亡继倾的危机,不免护教心切,要突出儒家价值之正当性与终极性,以致引起一些不必要的争议”。(刘述先:《港、台新儒家与经典诠释》,载《儒家哲学研究: 问题、方法与未来开展》,第277页。)按照布拉特曼的理论,对各种压力影响下的一些大陆新儒家的“护教心”,不应简单地用“主观”和“客观”,或“保守”和“激进”去理解,而应该在中西比较视域下,将这种“护教心”视为完成建构儒学政治规范性的“输入阶段”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这一点笔者会在后面关于建构主义“自展”陷阱的讨论中做进一步阐释)。
布拉特曼认为在输出阶段存在的压力更为明显,这些压力来自于一些评判标准。这些评判标准作为个体预设的规范性事实,在个体评判自身和他者各种基于理性能力的规范性判断时,会受到其他规范性事实评判的压力。(38)M.E. Bratman, and J. Lenman, “Constructivism, Agency, and the Problem of Alignment,” Constructivism in Practical Philosophy, (2012): 91-98.具体而言,如果将一些港台及海外新儒家关于儒家政治思想的研究视为布拉特曼所讨论的输出阶段,我们很容易地发现其面临诸多压力。首先,一种压力来自于,这些港台及海外新儒家在“输出阶段”预设了民主政治作为评判儒家政治实践的规范性事实,同时忽视了或故意规避了现实政治实践中两个重要的规范性事实: 一个是二战之后,西方民主制度给很多国家带来了一段较长时间的和平稳定和经济繁荣,这个事实(假设成立)(39)有些学者可能依据最近的一些民主实践认为这个事实不成立,特别是考虑到2008年经济危机,中亚地区的民主化进程,英国公投脱欧,以及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等等。本身并不意味着当代中国人有义务在现实政治实践中接受西方民主思想的约束;另一个规范性事实与第一个相类似,即儒家政治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特别是思维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个事实(假设成立)(40)有些学者可能认为这个事实不成立,特别是考虑到自儒家成为“游魂”之后,港台和大陆部分地区现在或许还有儒家传统,但更多的还有西方资本主义传统和苏联传统。经济全球化以及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迅猛发展所带来的西方现代和后现代文化的影响,以及大陆实行三十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等等都对以孝悌为核心的儒家政治伦理产生巨大冲击。当下中国人的政治生活是否还有儒家这个标签,这个问题需要通过很多实证性的研究做进一步探讨,本文不是社会科学或心理学研究,在此只能假设事实成立。
为了应对由于没有直面上述两个规范性事实而导致的压力,中西比较视域下的儒家政治哲学研究需要反思现实政治实践,不仅要深入探讨西方民主制度,区分民主理论和民主实践,同时更要思考如何在当下中国政治实践中拯救儒家传统。正如李泽厚所言:“因为传统还活着,还活在尚未完全进入现代化的中国亿万老百姓的心里,发掘、认识这种经千年积淀的深层文化心理,将其明确化、意识化,并提升到理论高度以重释资源,弥补欠缺,也许,这才是吸取、同化上述欧风美雨(引者按: 指“外王”(政治哲学)上自由、民主的美雨欧风,“内圣”(宗教学、美学)上的“后现代”同样的美雨欧风)进行‘转化性的创造’的基础。”(41)李泽厚: 《论儒学四期》,载《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45页。很多大陆新儒家也认为如果不首先将“儒学本身确立为当下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基准”,那么进一步引出的“儒学与其他文化之间共存和对话的问题,就只能是无源之水”。参见干春松: 《儒学史的叙述与建构反思》,《学术月刊》,2015年第11期。
“输出阶段”的另一种压力来自于一些港台及海外新儒家预设西方哲学研究范式作为评判儒家政治哲学学术研究的规范性事实,以期儒家思想能融入西方学术研究,从而与西方文明平等对话。这种压力促成了熊十力的本体论,冯友兰用“唯心、唯物”去解释儒学,牟宗三提出的“道德的形上学”,唐君毅的“原性、原道、原教”的诠释体系,方东美的价值中心的超本体论和存在论等等。但是陈荣捷提出,熊十力、冯友兰等新儒家基于西方哲学基本问题而提出的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知识论等等,往往会被批评对西方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解不够深入,而且在具体讨论中,经常为了迎合西方哲学研究思路而曲解中国哲学思想。(42)陈荣捷: 《冯友兰的新理学》,载单纯、旷盺主编: 《解读冯友兰》(海外回声卷),深圳: 海天出版社,1998年。李泽厚也认为,现代新儒家的研究并未有什么理论上的突破,“在现代条件下,现代新儒学搞出一套道德形而上学,去继承宋明理学,但根本理论并没超出宋明理学多少,并没有脱出宋明理学的基本框架,仍然是内圣开外王,心性第一,只是略微吸收了一些外国哲学,但也不多,词语、观念、说法新颖和细致了一些而已,它远不足开出一个真正的新时期”(43)李泽厚: 《为儒学的未来把脉——在马来西亚的演讲》,载《杂著集》,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292页。。虽然这样的论述充满李泽厚的个人色彩,但一些港台和海外新儒家的部分论述确实过多创造性地借用西方概念术语和分析方法(44)李晨阳认为在北美中国哲学届,用广义分析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并与西方哲学进行比较已经成为潮流。(李晨阳:《北美学界对中国哲学的分析和比较研究》,《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第103—110页。)信广来也指出:“在比较研究中存在一个趋势是: 从西方哲学的角度,参照西方哲学的框架概念及问题意识来研究中国思想。”参见Shun, Kwong-loi, “Studying Confucian and Comparative Ethics: Methodological Reflections,”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36(2009): 3,455-478。,一些理论观点经常显得过于晦涩(45)李泽厚批评牟宗三忽视儒学通俗性,“把儒学弄成玄奥思辨的书斋理论,因而使其与大众的生活脱节”。参见李泽厚: 《论语今读》,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第3页。,态度含糊而且不能自恰,难以在学界形成共识。(46)安乐哲认为过多套用西方哲学概念,会使“中国哲学成为西方哲学的低劣变奏”。(安乐哲: 《差异比较与沟通理解》,载《和而不同: 比较哲学与中西会通》,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1—23页。)姜新艳也认为“在中国哲学研究中过于重视分析方法可能会忽略中国哲学的特有优点,矮化中国哲学于西方哲学”。参见Xinyan Jiang, “Introduction,” The Examined Life: Chinese Perspectives, Xinyan Jiang (ed.), Binghamton: Global Academic Publishing at Binghamton University (SUNY at Binghamton), 2002, pp.xiii-xxv。
按照一些建构主义者的观点,上文所述的“输出阶段”面临的两种压力,主要是因为一些港台和海外新儒家在现实政治实践和学术理论层面分别预设的两种规范性事实(民主政治和西方哲学研究范式),只是形式上的规范性判断,并不是唯一绝对的评判标准。莎伦·斯特里特(Sharon Street)对形式上的规范性判断和实质性的规范性判断做了具体的区分,她首先提出“规范性判断的评判标准存在于该判断接下来基于实践观点(Practical Point of View)所做逻辑的或工具性的论述”(47)S. Street, “Constructivism about Reasons,” Oxford Studies in Metaethics, 3(2008): 210.。然后斯特里特在文章中区分了两种建构主义观点,一种是与科斯伽德相关的实质性的政治哲学建构主义观点,认为存在一些实质性的规范性判断,即理性主体所必须遵循的规范性判断或道德命题。(48)S. Street, “Constructivism about Reasons,” Oxford Studies in Metaethics, 3(2008): 211-213.按照这种观点,在儒家政治哲学研究中,相比西方民主制度(代议制民主或直接民主),孟子在“义利之辩”中提出的“仁政”更应该成为规范性判断的评判标准。具体而言,民主无论是在逻辑上还是在工具性意义上都不是最优的政体,民主只能通过对现实政治实践的直接描述,而获得一种相对意义上优越性(不比其他现存的或过去存在的政体更坏),因而民主或许可以成为经验性判断的评判标准,但是无法成为规范性判断的评判标准。相比之下,孟子的“仁政”是基于春秋战国时期“出于利”的政治实践而提出的逻辑的或工具性的论述,虽然是“出于仁义”的“不切实际”的理想,但是单纯在逻辑上或工具性意义上可以被论证成为一种理论上的最优政体,因而可以作为规范性判断的评判标准。此外,借鉴科斯伽德的观点,“仁政”本身可以被视为一种实质性的规范性判断,在终极意义上,行“仁政”就是政治活动中的主体所必须遵循的行为宗旨。
斯特里特还讨论了一种她自己支持的形式上的建构主义观点,其中的核心思想是围绕科斯伽德提出的“我们是否有能够辨识理性的理性?”的问题。斯特里特认为科斯伽德的问题是假问题,因为它内在预设了科斯伽德自己所反对的某种实在论。斯特里特提出,关于规范性的真值以及其背后的理性能力的讨论,必须认识到个体的各种规范性判断之间之所以能够相容,完全取决于个体的各种规范性判断之间适宜且严格的相互评判,这些评判具有相对性和偶然性,除了个体自身运用理性能力的思考活动过程,向外在世界寻找任何评判标准都没有意义。(49)S. Street, “Constructivism about Reasons,” Oxford Studies in Metaethics, 3(2008): 220-245.概括而言,斯特里特认为没有什么特定的作为评判标准的规范性判断是个体所必须遵循的,换句话说,作为评判标准的规范性判断只是个体不同规范性判断之间相互评判的结果,因此这种规范性判断并非是实质上绝对的,而只是形式上相对于个体其他规范性判断而言的。(50)S. Street, “Constructivism about Reasons,” Oxford Studies in Metaethics, 3(2008): 213-215.
如果斯特里特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西方政治哲学家所讨论的民主与儒家政治哲学中的“王道”、“仁政”等论述本质上都是基于个体自身对于一些政治原则的理解,都可以被视为形式上的规范性判断。民主强调程序正义和对个体自主的保护,而“王道”、“仁政”等儒家政治思想追求“为政以德”和“政以正人”,关心全体民心的向背和实现人的美好生活。(51)杨国荣: 《政治、伦理及其他》,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35—42页。这些规范性判断都可以作为评判标准,但都不是实质上绝对的。
斯特里特的观点受到一些质疑。迈克尔·里奇(Michael Ridge)认为斯特里特的讨论并没有什么创新,其实是走了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以及其他哲学家的老路,只是提出了一种复杂形式的主观主义而已,并且认为斯特里特的观点由于过度重视个体现实主观思想,从而导致规范性判断自身丧失实质内容。(52)M. Ridge, “Kantian Constructivism: Something Old, Something New,” Constructivism in Practical Philosophy, (2012): 138-158.斯坎伦(T.M. Scanlon)认为,斯特里特对科斯伽德关于理性能力观点的批评,看似是反思均衡的过程,但其实并不能用来确证理性能力,因为这种过程本身已经预设了什么是理性能力,从而可能存在循环论证。(53)T. M. Scanlon, “The Appeal and Limits of Constructivism,” Constructivism in Practical Philosophy, (2012): 226.
笔者认为斯特里特的观点尽管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对于儒家政治哲学研究有重要意义,这不仅仅是因为儒家思想重视对理性能力(智能)的讨论,而且与佛教和道教相比,儒家思想更具政治现实生活中的个体道德实践倾向。(54)参见牟宗三: 《圆善论》,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杜保瑞: 《董仲舒政治哲学与宇宙论进路的儒学建构》,《哲学与文化月刊》,2003年第352期,第19—40页。此外,尽管斯特里特认为评判规范性判断有偶然性,但她又强调在某些人性的重要方面,例如个体的意动态度(包括个体的各种情感、欲求和信念等,参见本文第一节),存在绝对的规范性判断的评判标准。斯特里特用爱打了比方,爱上某个人是很偶然的,但是认识到这种偶然性并不会让我们感到爱的能力有所减弱,因为爱作为一种情感欲求是人性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以至于一旦丧失了爱,我们也就丧失了对外界事物的评判能力。(55)S. Street, “Constructivism about Reasons,” Oxford Studies in Metaethics, 3(2008): 207-245.
建构儒家政治规范性的过程也必然会受到个体意动态度的影响,其中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理解很多儒家学者对儒家传统的“温情和敬意”,这种“温情和敬意”已经内化在很多儒家学者的情感欲求和信念之中。刘笑敢提出儒学学者要坚持“现代学术身份”,在学术研究中摒弃个人情感欲求,追求中立、客观和真实(56)刘笑敢将中国哲学学术研究者的身份划分为“现代学术身份”、“民族文化身份”和“生命导师”,提出学术研究者必然会身份混同,但同时要有身份自觉,“民族文化身份”和“生命导师”必须基于“现代学术身份”,而“现代学术身份”要求研究者必须追求客观和真实。(刘笑敢: 《诠释与定向: 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探究》,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7页。),但是这种“中立客观”在现实儒家政治哲学研究中很难实现;按照斯特里特的建构主义观点,刘笑敢的“坚持”在理论上可能也是行不通的。笔者认为,受到个体实践观点影响,带有个体意动态度的学术研究,在建构儒家政治规范性的过程中是必然存在的也是必不可少的(笔者在后文将对这一点做进一步探讨)。
除此以外,如果我们接受了斯特里特的观点,就会发现布拉特曼所讨论的输入和输出两个阶段存在前后不一致。如前文所说,布拉特曼认为在输入阶段,个体待评判的规范性判断,很大程度上会受到个体的情感欲求和信念等意动态度影响,这些意动态度根据斯特里特的分析,是属于绝对的、无条件的,不会受到个体其他规范性判断的影响;而在输出阶段,由于要接受各种形式上的规范性判断的评判,个体的规范性判断必然会受到个体其他规范性判断相互评判压力的影响。换句话说,难题在于到底如何实现从输入绝对无条件的、不受任何外在压力影响的规范性判断,到输出受到个体其他规范性判断评判压力的规范性判断。
如果据此反思儒家政治哲学研究,我们会发现在中西比较视域下,建构儒家政治规范性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同样的难题。在输入阶段,儒学研究者侧重的是诠释儒家政治思想史中的规范性判断,只关涉儒学家自身对于这些规范性判断的态度,不受到外在压力影响,是绝对无条件的。而在输出阶段,儒家政治哲学研究者更多依据中西政治哲学理论中的规范性判断,对儒家政治思想史中的规范性判断进行评判。其实关于儒家政治哲学研究的“中西”之争以及“史学”与“哲学”之争,本质上可看作是输入“无压力”的规范性判断与输出“受评判压力”的规范性判断两个过程之间的纷争。冯友兰认为,作为儒学研究的哲学家,而不是儒学研究的史学家,应该不仅仅停留在诠释古代中国哲学家的思想,而且要借鉴西方逻辑分析方法对古代中国哲学家进行评判,“从纯哲学家的观点看,弄清楚过去哲学家的观念,把他们的理论推到逻辑的结论,以便看出这些理论是正确还是谬误,这确实比仅仅寻出他们自己认为这些观念和理论的意思是什么,要有趣得多和重要得多”(57)冯友兰: 《中国哲学简史》,涂又光译,第382页。。虽然冯友兰的观点体现了他作为哲学家的一面,在儒家哲学研究方向的选择方面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仅从谁更“有趣”或更“重要”的角度去讨论儒家政治哲学研究的“中西”、“史哲”之争,是简化了该问题的内在机制和本质。笔者认为,对该问题更为深刻的理解应从儒家政治规范性判断的评判标准入手。
三、 儒家政治哲学研究的评判标准和内在困难
一般而言,规范性判断的真值总是与该判断的含义相联系,而戴尔·多尔西(Dale Dorsey)认为只有打破这种联系,才能解决关于规范性判断评判标准的困难。(58)D. Dorsey, “Subjectivism Without Desire,” Philosophical Review, 121(2012): 407-442.然而如果规范性判断的含义与该判断的真值相分离,那么规范性判断的评判只能诉诸一些客观独立的规范性事实,但建构主义者一般不同意实在主义者所认为的存在客观独立的规范性事实。多尔西对此的回答是,就算客观独立的规范性事实不存在,我们也不能据此认为规范性判断的真值是无法判定的,例如,缺乏融贯性的规范性判断就是错误的。多尔西希望能够从实在主义语义学的角度思考规范性判断的含义,同时反实在主义地理解规范性判断的真值。但这样做的困难在于,如何理解这种关涉真值的融贯性,因为关于一系列规范性判断是否融贯这个问题本身并不属于规范性问题,从而对规范性判断的评判将横跨规范性领域以及非规范性领域,由于同时涉及规范性和非规范性的语句和假设,我们将很难厘清其中的逻辑联系。多尔西对此的回答是,我们可以更为宽泛地理解“真值”,即区分规范性领域内的真值和非规范性领域内的真值,在特定的领域讨论特定的真值。(59)D. Dorsey, “A Coherence Theory of Truth in Ethics,” Philosophical Studies, 117(2006): 493-523.
在儒家政治哲学研究中,我们同样可以借鉴多尔西的“跨规范性”视角下的“融贯性”原则对儒家政治规范性的建构进行分析。具体而言,“融贯性”原则对儒家政治规范性判断的评判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儒家政治规范性判断的“真值”必须首先与儒家自身传统,即儒家的内在精神和理路融贯,这样才能保证建构的儒家政治规范性是“儒家的”,这是整个建构过程的活水之源。同时,依据上文多尔西的观点,必须反实在主义地理解这种“活水之源”,即其自身也是一种建构过程,是“流动”的而不能是“预设的”或“静态的”。
另一方面,依据多尔西从实在主义语义学角度理解规范性判断的“含义”,儒家政治规范性判断的“含义”必须努力与西方政治哲学所能接受和理解的话语体系融贯,这样才能实现理论上的普适性。正如沈青松所言:“如果一个人自己的哲学或文化传统的语言能被转化为另一个传统的语言或其所能理解的语言,那么这个人自己的哲学或文化传统具有普适性。”(60)沈青松: 《关于跨文化哲学与中国哲学的一些反思》,载姜新艳主编: 《英语世界中的中国哲学》,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50页。
乔纳坦·谢莫(Yonatan Shemmer)认为多尔西的融贯性原则相比其他原则具有优先性,其地位就像宪法一样,对于其之后建构规范性的原则有约束,但如果我们要承认这种优先性,就必须同时承认我们建构规范性的过程不是完美的,必然存在一些根本性的缺陷。(61)谢莫认为多尔西的融贯性原则其实是对一致性原则的补充,规范了个体在建构规范性时对目标的选择,同时融贯性原则自身也应该是建构主义研究的对象。但是如果我们不将融贯性原则视为必然的普适原则,那么坚持融贯性原则也要接受建构主义的证成,从而当我们在规范性层面对融贯性原则进行讨论时,就很有可能会陷入到一种循环论证。笔者在此不再对这一问题做进一步阐述,参见Y. Shemmer, “Constructing Coherence,” Constructivism in Practical Philosophy, (2012): 159-181。据此,笔者认为在儒家政治哲学研究中,我们可以优先将融贯性原则纳入对儒家政治规范性判断的评判,但同时要注意克服由于建构过程存在根本性缺陷而产生的内在困难。华莱士将这些困难总结为三种建构主义陷阱:
第一种陷阱是关于“心理主义(Psychologism)”。建构主义者在讨论规范性的时候总是预设了一种心理上(意动态度)的必然性,即个体在心理层面要求个体的行为必然与规范性判断相一致。(62)R.J. Wallace, “Constructivism about Normativity: Some Pitfalls,” Constructivism in Practical Philosophy, (2012): 23.但我们同时要问,这些规范性判断到底为什么可以主导个体的意志。在儒家政治规范性的建构过程中,“心理主义”的陷阱主要出现在“输入阶段”。回顾上文所讨论的,在输入阶段中,一些大陆新儒家出于对儒家传统的“温情和敬意”而怀抱着“护教心”,立足公羊学系统,试图重建中国人政治生活中的儒家文化自觉和自信。但这种“护教心”在一些大陆新儒家的心理层面有可能会预设“儒学教义”,即预设能够主导个体意志的规范性事实。这里的关键问题不是论证这种“儒学教义”是否具有合法性,因为“合法性”本身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教义”,关键要思考如何防止关于“儒学教义”的讨论落入“心理主义”陷阱,即成为必然性的、独断的问题意识。若如此将会对儒家政治哲学研究产生很多消极影响,包括选择性忽视或干脆标签化西方较为复杂的政治哲学研究成果,导致理论观点不够深刻和自洽,研究过于“独树一帜”而缺乏说服力。
第二种陷阱是关于“自展(Bootstrapping)”,这种“自展”类似一种“自我立法”的过程。建构主义者认为个体的慎思活动会让个体遵循一些个体预设的规范性事实,这种遵循本身源自并强化个体对于这些规范性事实的意动态度。但是仅仅依据意动态度而非运用理性能力预设的规范性事实可能是不正确的。如果个体坚持基于意动态度的遵循,则个体有可能将潜在的有漏洞的规范性判断确立为规范性事实,即“自我立法”式建构规范性。(63)R.J. Wallace, “Constructivism about Normativity: Some Pitfalls,” Constructivism in Practical Philosophy, (2012): 29.回到上文,笔者在对布拉特曼“输入阶段”的讨论中,提出应将“护教心”视为完成建构儒家政治规范性的“输入阶段”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之所以不是充分条件,是因为某些“护教心”有可能只是“自展”的结果,例如一些大陆新儒家学者可能会有意识或潜意识混同康有为的行为和康有为的问题意识,基于政治实践目的或理论创新,视自身为孔教“立法者”,而非“续命者”,其预设规范性事实的理论自信仅仅是源自自己所处学术共同体的意动态度,而缺乏运用理性能力的思考过程。对于建构儒家政治规范性而言,“自展”的消极影响在于有可能围绕一些伪命题和假问题形成某种封闭系统,既不为外人所信服,为防自身理论崩塌,也不愿与外人沟通,扭曲了“护教”本心。建构主义者对于“自展”批评有多种回应,其中一种最常见的回应是认为,如果剔除那些仅仅依据意动态度而未运用理性能力预设的规范性事实,那么建构过程中关于“自展”的漏洞是可以避免的。
建构主义者对第二种陷阱的回应引出了第三种陷阱——“谬误理论(Theory of Error)”,即在建构规范性过程中,个体无法分辨意动态度与理性能力,或是个体意动态度与理性能力发生冲突,所导致的结果是建构的儒家政治规范性并不是基于儒家的“实践观点”或者不具备普适性。(64)R.J. Wallace, “Constructivism about Normativity: Some Pitfalls,” Constructivism in Practical Philosophy, (2012): 33.对于第三种陷阱,笔者尚未思考出有效的应对方法,只能期望在建构儒家政治规范性的过程中,儒学政治哲学研究者能努力协调现实政治实践中的意动态度与学术理论研究中的理性能力。
四、 结论
当代很多儒家政治哲学研究者试图从全球性视角出发,或是在宪政制度层面,抑或是从文明教化角度,使儒家政治思想在现代社会获得新的生命力。这些努力本身固然值得称赞,但结果有时并不如人意。内圣不应急着开出新外王,而应首先着重自我确证,在心性层面将儒家政治哲学根基打牢,确保儒家政治哲学的内在精神得以延续,然后在此基础之上思考儒家政治文明与世界其他政治文明的会通融合。儒家政治哲学或许可以拯救世界,但我们首先要拯救儒家政治哲学,在笔者看来,这种拯救需要通过建构儒家政治规范性来实现。而理解“建构儒家政治规范性”,首先需要正确把握其中“建构”和“规范性”的内涵和意义,研究儒家政治哲学的学者自身对儒家文化充满“温情和敬意”,因此这种带有个体情感欲求的研究本质上是一种“建构”。建构者摆脱西方学科化的束缚,将自己视为儒学的续命者,以“局内人”的身份思考儒家政治思想自身的内在问题、概念范畴和理论观点。
关于“规范性”的作用,在《二十世纪道德哲学中的实在论和建构主义》(“Realism and Constructivism in Twentieth-century Moral Philosophy”)一文中,科斯伽德提出规范性不能被用来描述现实,但是会有助于我们解决一些特定的实践问题。(65)C.M. Korsgaard, “Realism and Constructivism in Twentieth-century Moral Philosophy,”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Research, 28(2003): 99-122.瓦莱丽·泰比瑞厄斯(Valerie Tiberius)认为这些特定的实践问题必须足够开放,能够容纳多元价值,同时不预设唯一的评价标准。此外对这些特定的实践问题的解决,必须满足建构主义进路中的一些核心要求,包括在理论上对所有个体都具有权威性,经验上必须可靠而且对实际行动能有指导作用。(66)V. Tiberius, “How Theories of Well-being Can Help Us Help,” Journal of Practical Ethics, Vol. 2 No. 2 (2014): 1-19.笔者认为这同样也是儒家政治哲学研究最本质的特征,即在中西比较视域下探讨以“为政以德”和“政以正人”为基础的“王道”、“仁政”等规范性判断如何在理论上能够普适中西,在实践中能够切中实用(67)蒙文通认为秦汉之际的儒学之所以能独尊是因为“宗儒者综诸子而备其制,益切于用……于是孔氏独尊于百世”。参见蒙文通: 《题辞》,载《儒学五论》,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页。,对当下中国现实政治实践中的个体产生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