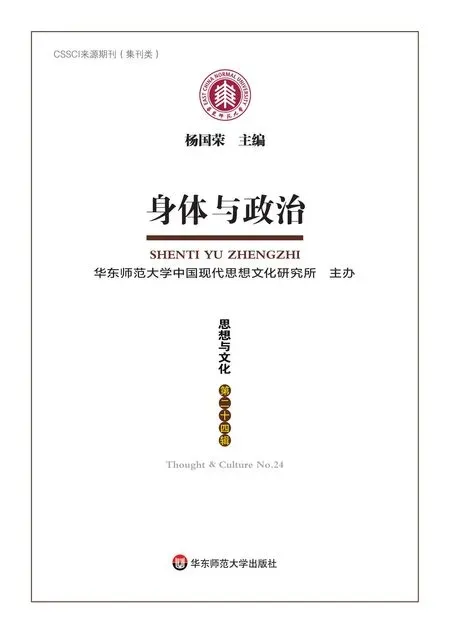禅学的“涉身化”及其对宋明理学的影响
随着“身体”在哲学视域中的凸显,它必然带来我们对中国哲学史思想认识的全新改观。下面,我们试图以作为中国哲学中重要一环的禅学为例来阐明这一点。
一、 从“祛身”到“涉身”
当佛学最初以“佛”来命名自己时,就已经命中注定了它与“唯心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因为,“佛”者,觉也。而觉之所以为觉乃心之觉,从而究源以竟委的“究竟觉”乃“以觉心源故,名究竟觉;不觉心源故,非究竟觉”(《大乘起信论》)。这种所谓的“心源”说,不正是佛学“唯心主义”性质的最好的脚注吗?
故从华严宗的“三界唯心”到法相唯识宗的“万法唯识”,从天台宗的“一心三观”到其“一念三千”,从《大乘起信论》的“一心开二门”到《金刚经》的“应无所住生其心”,都无一不以“心”为宇宙的造始端倪,无一不以“心”为世界万法的真正依据。因此,释氏“以心法起灭天地”(《正蒙·大心》),宗儒张载对佛学的这一批评无疑是一语中的的。在他看来,这种“唯心主义”不仅流于“以山河大地为见病之说”,而且以其“人见之小因缘天地之大”之弊,正如“夏虫疑冰”般地不可理喻、愚不可及。
正是这种如痴人说梦般的学说,却一进入中国就呈势如破竹、所向披靡之势,就一时间使上至皇帝下至百姓万众顶礼。这一切的出现并非偶然,它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乘弊而起的产物。中国传统文化力挺人伦日用、极重世俗化的倾向虽无可厚非,但与此同时,却使其缺乏以纯精神观照的方式俯视红尘的超脱,更遑论对自己切身生死的参破。因此,当西土人士以“心”为筏渡越生死河界之际,中国人却要么如儒家“未知生,焉知死”那样对生死关头视而不见,要么如道家耽溺于“羽化成仙”那样使自己的企求无异于蒸沙以成饭。
固然,中国古人亦讲心,如孟子谓“尽心知性知天”,谓“求其放心”。但此心并非彼心。如果说佛教的心是一种身心分离的虚灵明觉的超越之心的话,那么,中国古人的心则为一种身心一体的道德端倪的内在之心。也正是由于这种独立的、超拔的心的缺失,为中国传统文化留下了一个巨大“心的空场”,使中国文化不啻是一种“无心的文化”,使中华民族不啻成为一种“无心的民族”,并最终导致了在中国文化中一种极其激进的唯心主义的佛学的乘虚而入。
然而,一种学说将其身心分离的唯心主义推向极致之际,也恰恰是以这种唯心主义向身心一体开始回归之时。外来佛学日渐涉身化的禅学在中国的兴起即其显例。
这就不能不使我们去真正了解佛、禅之别。一旦涉及佛、禅之别,人们往往或以“不离文字”和“不立文字”为其分判,或以“渐悟”和“顿悟”为其分判。实际上,追本溯源,二者之别不外乎体现为“祛身”和“涉身”的各执一端。
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先从禅学无上强调的“自性”谈起。众所周知,“自性”乃禅学之为禅学的真正的“正法眼藏”。无论是神秀与慧能的禅宗衣钵之争,还是六祖慧能对于“自性”的空前发明,如所谓“一切万法,不离自性”(《坛经·行由品》),如所谓“若识自性,一悟即至佛地”(《坛经·般若品》),如所谓“自性本自清净”、“自性本不生灭”、“自性本自具足”(《坛经·行由品》)如此等等,都无不表明禅学实乃以“自性”为宗。故慧能尽管也讲“心”,但其所谓的“心”是“明心见性”的心,“自性”之“性”才使心之所以为心成为可能。
这种“自性”,用孔子的表述,即其“为仁由己”的“己”;用周易的表述,即其高标的当机显现“时”或“几”;用海德格尔的现代表述,即其“根本本体论”的“此在”。这样,正如“此在”就其具体的“此时此地”而言始终是海氏“在世之在”的存在,即梅洛-庞蒂的“走向世界”的“身”那样,禅宗的“自性”亦不过是“自身”的别称。故禅宗的“见性成佛”实不外乎密宗所谓的“即身成佛”、“现身成佛”。或易言之,禅宗哲学乃为一种地地道道的“涉身化”哲学。所以,才有了慧能所谓“佛是自性作,莫向身外求”(《坛经·疑问品》),所谓“自身中有三身佛”(《坛经·忏悔品》),所谓“三身元我体”(《坛经·机缘品》)等等如是之说。
我们看到,从佛的“祛身”到禅的“涉身”虽仅仅涉及对“身”的取舍,却从中为我们开出了二者的天壤之别,并为我们迎来佛学的中国化这一有如翻天覆地般的根本性、划时代的理论变革。
正是这种涉身性,使禅宗从出世走向了入世。故慧能称“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坛经·般若品》),并一反故常地提出“善知识,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坛经·疑问品》),而实开后来的百丈怀海所创立的脱离禅僧寄住律寺之制的先河。一旦从“出世”走向“入世”,从“出家”走向“在家”,那么这不仅意味着禅学以其“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坛经·疑问品》),以其宋代大慧宗杲禅师所提倡的以“忠义之心”入世,走向了对儒家世俗伦理的肯定,还意味着禅学一如海德格尔从“此在”之“在世”推出“烦”的哲学那样,其明确断言“烦恼即是菩提,无二无别”(《坛经·护法品》),以一种所谓“淤泥定生红莲”(《坛经·疑问品》)的主张,将佛学的“不破烦恼,不入涅槃”这一至胜教义彻底推翻,而不啻对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精神的再次回返。这样,禅宗所顶礼的世界已不再是唯心的寂空世界而为现实的“生活世界”。故慧能告诫信徒“不可沉空守寂”(《坛经·机缘品》),宣称“不离见闻缘,超然登佛地”(《坛经·机缘品》)。此即禅宗所谓的“于相离相”。而这种“于相离相”带给我们的既是一个“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苏轼语)、“乾坤大地,常演圆音。日月星辰,每谈实相”(东林常总偈语)的禅意化的世界,又使参禅者成为不折不扣的“大隐隐于世”的“尘世隐者”。
正是这种涉身性,使禅学从知走向了行。故慧能谓“念念若行,是名真性。悟此法者,是般若法。修此行者,是般若行”(《坛经·般若品》),并从这种“般若行”出发,不仅以“我不会佛法”(《坛经·机缘品》)自诩,而且宣传“乘是行义,不在口争”(《坛经·机缘品》),对“只成个知解宗徒”(《坛经·顿渐品》)的佛学取向给予激进的力辟。也正是沿此方向,禅宗一反传统佛学对译经、解经、谈经的痴迷,主张行往坐卧皆是禅,语默动静无往非禅。以至于佛性就体现在“运水搬柴”之中,“饥来吃饭,困来即眠”之中,以至于马祖断言动心起念、扬眉瞬目等日常活动皆为佛性,从而标志着佛学从“识心见性”向所谓“作用见性”的历史性转变。与此并行的,我们还看到,一方面,是由百丈怀海禅师首创的丛林制度的兴起,该制度以“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为座右铭,它与其说是体现了一种新型的农禅佛教经济,不如说意味着禅宗从“知解”向“践履”的彻底皈依;另一方面,是由众多高僧大德所引领的禅僧“行脚”运动的风靡,“一钵千家饭,孤僧万里游”,这种禅僧的“行万里路”与其说是旨在参礼名师和圣迹,不如说是旨在把“头脚倒置”的人的生命重新颠倒回来,用足的行走来取代脑的思考,以期重返中国古老的那种有别于所思之“理”的所行之“道”。
正是这种涉身性,使禅学从本体走向工夫。这里所谓“本体”是指关乎宇宙“是什么”的,而对宇宙本身穷根追底的究极真理;这里所谓“工夫”是指关乎我们行为“如何作”的,而旨在实现人的目的的实践技能。在佛学中,慧学与定学二者的推出正是这种本体与工夫的集中反映。众所周知,在传统佛学中,一种“唯识主义”的主导倾向决定了,其虽讲定慧双修,实际上却是重慧轻定、以定辅慧的。但佛学发展到中国化的禅学,宗风为之一改,人们把定禅连称,“禅定”成为禅学的核心,不是慧学而是定学更让信众情有独钟、翕然信从。而慧能的“定体慧用”说的推出即其明证。该说主张“定是慧体,慧是定用”(《坛经·定慧品》),并用“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用”(同上)对这种“定体慧用”加以生动的阐明。值得注意的是,此“定”并非彼“定”,如果说传统佛学之“定”是所谓的“住心观净”、“静坐内观”的“定”的话,那么禅学之“定”则为一种身心一体、动静一如的“定”。由此就有了慧能所谓的“住心观净,是病非禅”(《坛经·顿渐品》)、“常坐拘身,于理何益”(同上)之论,就有了怀让禅师“磨砖不成镜,坐禅岂成佛”这一醍醐灌顶的警喻,也就有了禅祖达摩所谓“是欲见性,必先强身”之语(1)尊我斋主人: 《少林寺拳术秘诀》,北京: 中国书店,1984年影印本,第40页。,并以一种“禅武合一”的方式,使名扬中外的“少林功夫”在中华大地喷薄而出。同时,也正是基于这种身心一体、动静一如的禅定,才使慧能得以宣称“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坛经·行由品》),从而也才使禅宗由“渐悟”转向“顿悟”成为真正的可能。因为“顿悟”之为“顿悟”,与其说是知解上的顿然领悟,不如说是知行合一意义上体知的不假思虑,是行为与环境互动中的“当机解缚”。
更深入地讲,这种“当机解缚”之“缚”乃执着于语义之“缚”。这就不能不使我们对禅学的“涉身化”的探讨进一步鞭辟入里,深入到语言学层面的领悟。因此,正是在这里我们不无意外地发现,“全部哲学都是‘语言批判’”这一现代西方哲学命题,对于中国古代的禅学哲学也同样成立。
二、 从“语义”到“语用”
如前所述,如果说传统佛学所倚重的本体涉及世界“是什么”的话,那么禅学所强调的工夫则涉及我们行为的“如何作”;同时,如果说世界“是什么”与“合规律性”有关的话,那么我们行为“如何作”则与“合目的性”有关。进而,如果说“合规律性”最终为我们指向了如如本是、本在的“体”的话,那么“合目的性”则为我们指向需用、功用、作用的“用”。职是之故,禅学才有了马祖道一的“作用见性”之论,对于禅宗来说,终极性的“自性”就体现在为我所用的“用”之中。
这种对“用”的肯定不仅是对佛学的“真如实相”的消解,从中也使一种中国式的“用具形而上学”得以证成。而这种“用具形而上学”与其说是导向亚里士多德式的理性形式与感性质料的支离二分,不如说使海德格尔式的对世界的“一举把握”(at-hand)成为可能。故禅学讲“用即了了分明,应用便知一切”(《坛经·般若品》),讲“应用随作”(《坛经·顿渐品》),也即禅学认为,用既决定了我们对世界的了解,又决定了我们身体行为的取舍。进而,既然在实际需用中,我们身体行为的取舍离不开我们自身身体所处的机遇和处境,那么,在禅宗学说中,一种因时、因地而制宜的“方便”法门就随之应用而生了。故禅学称“欲拟化他人,自须有方便”(《坛经·般若品》),称“大善知识,岂无方便”(《五灯会元》卷第十一),称“随方解缚”。无疑,这种“方便哲学”与中国古老的“权变机智”一起,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化。以至于它使中国文化虽屡经变迁,却始终不越所谓“与时偕行”、“见机而作”这一大易的经典之见。
如果说外来佛学的唯识哲学是以意识与对象的两两分离为前提的话,那么,禅学的这种“方便哲学”则是以人身与环境的有机关系为依据的。故禅宗更为看重的,并非是意识认识对象的真理如何成立,而是人的行为与环境的有机关系如何实现。由是就导致了临济禅师的“人境调节论”的推出,也即其所谓的“有时夺人不夺境,有时夺境不夺人,有时人境两俱夺,有时人境俱不夺”(《五灯会元》卷第十一)。对于禅宗而言,也正是通过这种人境关系的种种时机性调节,在行为的合目的性与环境的合规律性两者的互为一体之中,一种实用论的方便法门最终得以实现,从中不仅使法、我二执彻底消解,也使禅的大机大用豁然开显。
因此,禅宗在中国的兴起,乃是对佛学中执迷于佛经的“义学”取向的一场革命。追溯佛学东渐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长期以来,中国的佛教徒,尤其是那些佛教的精英、高僧更为看重的,乃是译经、读经和解经的义理之学而非践行之功。从鸠摩罗什所谓“当使焚身之后,舌不焦烂”之谶,到道安、彦琮、罗什、玄奘、窥基等佛经翻译家的文字能生般若的愿念,无一不是其体现。然而,事实上,浩如烟海的佛经、高深玄妙的佛理,不独使一般信徒望之却步,即使身为一代宗师的玄奘对之亦不能不“未尝不执卷踌躇,捧经佗际”(《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值此之际,禅学却通过慧能这一目不识丁的一介樵夫,经由其自己切身的生命体验,为我们洞开了通向佛谛的方便法门。借助于这一法门,不仅高深莫测的佛理成为随机显现的日用之道,而且随之“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人们对衣被着神启的佛经语言文字的痴迷,随着“不立文字”的“语用学”大潮的兴起而开始风光难继乃至彻底消匿。
笔者曾借镜维特根斯坦的后期语言哲学,把禅的语言学思想视为中国语用论的语言观的集中代表。(2)参见张再林: 《中西哲学的歧异与会通》,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4年,上编七。这种语用论的语言观集中体现为以下三点:
其一,这种语言观主张语言是工具的使用而非涵义的指示。
一反唯实论的传统语义学的“涵义的神话”,后期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不过是一种使我们方便地解决现实问题的工具。这一点对禅宗的语言观同样成立。故慧能提出“应用随作,应语随答”(《坛经·顿渐品》),也即他认为语言的要旨恰恰体现于现实问题的解答。也正是基于这种不无实用性的语言工具论,才有了禅宗著名的“指月之辨”。这种“指月之辨”提出,正如庄子提出捕鱼之筌并非鱼,捕兔之蹄并非兔那样,以指指月,但指本身并非月。同理,也正如庄子主张“得鱼忘筌”,维特根斯坦主张“上楼撤梯子”那样,禅宗主张“不执义解”、“不落唇吻”、“不涉言诠”、“不立文字”。以至于禅宗提出,对于语言我们应“随说随扫”;以至于《指月录》直陈“世尊云: 吾四十九年住世,未曾说一字”;以至于禅学宣称“曾见郭象注庄子,识者曰却是庄子注郭象”(《五灯会元》卷第二十),借此将禅的为我所用的工具主义思想表现到了无以复加之地。明白了这一切,我们就不难理解何以禅“因人设教,因境设语”地从语言工具走向了非语言的隐喻,从努眼、吐舌、摊手、掴掌、拧鼻、翘足、跳舞、掀床、棒喝等等这些以势示禅,到不无文学化的种种“意象说法,意境传道”,在棒如雨点、喝似雷奔之中,在青青翠竹、郁郁黄花之中,为我们传达出那种“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难以言喻的禅韵、禅境。
其二,这种语言观坚持语言的严格语法的消解而非确立。
一如西方逻辑原子主义的语言学所认为的那样,语义学不惟认为语言是涵义的指示,而且认为这种指示活动是通过严格的语法规则加以组织而得以确立的。相反,一如后期维特根斯坦所说,语用学则认为语言的应用并非受一成不变的严格规则的制约,在语言中存在的仅为一种“任意的规则”。无独有偶,这一观点恰与禅学的语言观不谋而合。因为,与《金刚经》所谓“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的观点一致,禅宗亦提出“无一法可得,方能建立万法”(《坛经·顿渐品》),提出“大用现前,不存轨则”(《五灯会元》卷第四),提出“圣凡无异路,方便有多门”(《五灯会元》卷第十六)。故正是基于这种“无法之法”的语用学,在禅宗语言里,我们看到的是被语义学奉为圭臬的合乎科学的形式逻辑的斯文扫地,是语言中的不胜枚举的矛盾百出和情理乖戾。如,赵州和尚因僧问:“狗子还有佛性也无?”州云:“无!”兴善惟宽问:“狗子还有佛性否?”师云:“有。”又如,梁傅大士所谓的“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人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这一禅诗,更是把这种矛盾百出和情理乖戾表现得淋漓尽致。除此之外,在禅宗的语言里,还有那种答非所问、有意误读、隐语双关、信口开河、指鹿为马、循环答复,如此等等都体现对严格语法规则的彻底消解,并借助于这种消解,使禅学语言的那种无一定说法而要当机解缚的权巧方便得以真正显豁。
其三,这种语言观强调语言所指并非是确定性的而是非确定性的。
一旦我们把语言视为使用的工具,那么正如工具的使用者身处不同场合,则工具的用途就不同那样(例如一把螺丝刀在不同场合或可作启螺丝的工具,或可作撬门窗的窃具,或可作伤人的凶器),这一情况同样也适用于禅宗对于语言的运用。也就是说,在禅学的语言学里,与那种主张一词一义的指称严格对应的语义学大相径庭的是,其语词的所指和工具的用途完全相同,它永远都是开放的、不确定的。故禅宗提出“一切修多罗及诸文字、大小二乘、十二部经,皆因人置……一切经书因人说有”(《坛经·般若品》),主张“因人设教,因境设语”,主张“说似一物即不中”(南岳怀让禅师语),主张“开口即错”(《指月录》),主张“我向尔道”已是“第二义”(清凉文益禅师语)。无怪乎赵州和尚动辄让人“洗钵去”,因为他的本意恰恰是对他人原问的阻断,令其无言开显,以期避开人们执于义解的“死在句下”之嫌。也无怪乎创立一指禅的天龙大师的“刀劈断指”故事被视为禅宗公案的美谈,因为该故事既体现了对“执指为月”的纠弹,又表明了在禅宗语言学里,其突出的语用学倾向所导致的语言所指具有难以穷尽的内涵。这样,正如维特根斯坦的语用学以绝对所指的消解,使自己最终趋向以终极真理为宗的哲学的终结那样,禅宗亦以同样方式使自己宣告了以真如实相为宗的佛学的覆灭。故禅宗最后宣称“这里无祖无佛,达摩是老臊胡,释迦老子是干屎橛,文殊普贤是担屎汉,等觉妙觉是破执凡夫,菩提涅槃是系驴橛”(《五灯会元》卷第七)。也就是说,禅从“不立文字”的顿悟成佛,一变为德山、临济二宗的呵祖骂佛,这与其说是禅宗的又一场革命,不如说是禅宗语用学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
本来,从“礼佛”到“辟佛”,使禅学历时数百年的波澜壮阔的运动可以划上一个休止符,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在宋明理学那里,一场新的佛禅较量仍将继续,虽然这场较量的表现形式与先前大异其趣。为此,我们不能不转向下一个议题,即禅学涉身化与宋明理学的关系。
三、 禅宗的涉身化对宋明理学的影响
禅宗的“涉身化”取向既明,它与宋明理学的关系亦随之一起得以澄清。也就是说,一如佛学的中国化即禅学化是一不断涉身化的过程那样,这一过程同样也体现在宋明理学的历史演变之中。以至于我们可以说,一部宋明理学的历史既是一部“唯心化”、“唯识化”的历史,同时又如同佛学的禅化那样,是一部不断涉身化的历史。惟其如此,才使宋明理学不失为“合内外之道”的中国“道统”的忠实继承;惟其如此,才使宋明理学之所谓“儒佛合流”得以真正阐明。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克服这样一种误解,也即长期以来人们更多地把宋明理学看作是远溯《易》、《庸》的结果,而无视它同样也是近援禅学的产物,换言之,无视惟有禅学才是前宋明理学向宋明理学过渡的直接中介。当然,我们在提出这一观点的同时,并不否认即使在这里为我们所强调的禅学,就其思想基因而言,它本身最终亦可追本溯源于先秦儒学。
为了说明这一点,就不能不从集“理学”之大成的朱熹理学谈起。尽管朱熹理学是对程子“自家体贴出来”的“天理”思想的承续,尽管朱熹曾对佛教的异端取向大兴问罪之师,但不无遗憾的,寻本而追源,他的“天理说”实际上却是佛教华严宗“理事说”的移花接木之举。
华严的“理”缘于“法界缘起”,而此法界就是一真法界,亦即真心。此即宗密《注华严法界观门》所谓的“统唯一真法界,谓总该万有,即是一心”。故朱熹的“理”与之别无二致。他的“理”是“一切唯心”之理。因而,在朱熹那里,才有“理在事先”、“理本气末”之说,才称理是与“山河大地”无关的,理是“净洁空底世界”。此世界也即朱子援用“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能为万象主,不逐四时凋”这一佛学偈中所描述的世界。故牟宗三以其“认知的静涵静摄之系统”的性质,断言朱子乃“继别子为宗者”的判定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持之有据的。此外,朱子理学与佛教唯心主义的内在深刻联系,还可见之于朱子所谓“佛学于心地上煞下工夫”(《朱子语类》卷一二五)、“佛家说心处尽有好处”(《朱子语类》卷五)这些由衷的赞誉。
人们看到,正是有了朱子这种佛教化“唯心主义”的风靡,才有了陆王心学这一堪称又一轮“新禅学化”思潮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兴起。固然,与朱子一样,陆王亦大力提倡所谓的“心”。但此心并非彼心,如果说前者主张的“心”是一种一味外索的识见之心的话,那么,后者所强调的“心”则为一种切己自返、逆觉体征的道德之心。故陆王所谓的“心”,恰恰不外乎禅宗所谓的“自性”。因此,尽管陆王标炳自己的心学乃孟子“尽心”思想的承继,却因其近援禅的“自性”,而使自己与禅宗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缠和关系。这一点,不仅可见之于陆王二人均有参禅的经历,还可证之于朱子、朱子后学乃至作为阳明后学的刘蕺山都对心学有所谓“流于禅”之讥。
一俟我们把心学的切己的“心”理解为禅宗的自性的“性”,那么,正如禅宗“自性”之“自”导致对“当下”的肯定那样,这种肯定同样也体现在心学“切己”之“己”中。无论是陆象山的“欲知自卑登高处,真伪只须辨只今”,还是王阳明的“学者能时时当下,即是善学”(《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五》),无不是其明证。同理,正如禅宗从“当下”的“此时此地”趣向“在世界中”、“走向世界”的“身”那样,心学亦如此。故阳明诗云“莫谓天机非嗜欲,须知万物是吾身”,并称“无心则无身,无身则无心”(《传习录》卷下)。以至于在他那里,以其身心一体的性质,“心学”已成“身学”的代称,并标志着唯心化的宋明理学的“涉身化”转向由此而奠定。
这样,和禅宗一样,心学的涉身化必然导致对“入世”的肯定。故一反佛学“外人伦,遗事物”的取向,王阳明宣称“吾儒养心未尝离却事物,只顺其天则自然就是功夫。释氏却要尽绝事物,把心看做幻相,渐入虚寂去了;与世间无些子交涉,所以不可治天下”(《传习录》卷下);他还宣称“佛怕父子累,却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却逃了君臣;怕夫妇累,却逃了夫妇。都是为了个君臣、父子、夫妇著了相,便须逃避。如吾儒有个父子,还他以仁;有个君臣,还他以义;有夫妇,还他以别;何曾著父子、君臣、夫妇的相”(《传习录》卷下)。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切既可视为对佛学的力辟,又可视为对朱子学的旁敲侧击。原因在于,尽管朱子看似对佛学不遗余力地抨击,但他的“未有这事,先有这理”的提出,却不仅意味着其学说实际上与“外人伦,遗事物”的佛学暗通款曲,而且也意味着其学说与阳明“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传习录》卷上)这一“即事见理”说迥然异趣。而从哲学上看,这种“即事见理”说恰恰是儒家之所以坚持“入世”的坚实依据。
继而,和禅学一样,心学的涉身化也必然导致对“行”的肯定。按牟宗三的观点,朱子学说乃以《大学》“格物致知”为宗旨,以“穷理”为鹄的,以渐教、他律、重智为特征,这一切恰与“从知解上入”的唯识佛学不约而同。与之相反,阳明心学也同样讲“知”,但其所讲的“知”是“良知”之知,而这种“良知”之知,用梅洛-庞蒂的表述,即“用身体知道”的知,用阳明自己的表述,即“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传习录》卷中)的知。易言之,对于阳明来说,真正的知恰恰体现在价值的合目的性与事实的合规律性相统一的人的身行践履之中。故阳明才说:“《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知行如何分开?此便是知行本体,不曾有私意隔断的。”(《传习录》卷上)他还说:“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传习录》卷中)也正是基于这种知不离行、即行见知的思想,才使阳明提出“一念发动处便是行”(《传习录》卷下),而与禅宗的“是名真性”的“念念若行”的观点灵犀相通。也正是基于上述思想,阳明力纠门人为学上所流于的守寂泥空,而以所谓“在事上磨练”的力倡,既与孟子的“必有事焉”的思想一脉相承,又为自己的思想打上那种主张“行住坐卧、语默动静皆是禅”的禅宗的鲜明烙印。
再者,和禅学一样,心学的涉身化也必然导致对“工夫”的肯定。实际上,对“行”的肯定不可避免地走向对“如何作”的工夫的肯定。诚然,不可否认,朱子的理学亦讲工夫,但囿于其学说的那种不无佛化的“唯心主义”,他所谓的工夫只能流于并无确定实质内容的“空头涵养”(刘述先语),也即所涵养的充其量不过是一个虚灵明觉之心,从而其工夫论亦最终流于一种近于佛的守寂沉空的工夫论。与之不同,一种良知即是行的观念决定了阳明所谓的“事外无心”,也即阳明所谓的“目无体,以万物之色为体;耳无体,以万物之声为体。鼻无体,以万物之臭为体。口无体,以万物之味为体。心无体,以天地万物感应之是非为体”(《传习录》卷下),而这种“事外无心”又决定了“吾儒养心未尝离却事物,只顺其天则自然就是功夫”(《传习录》卷下),决定了我们只能在良知本体的“发时”、“发处”用功。这使阳明心学不惟极重工夫,而且还使其工夫“未发工夫已发上用”,所谓“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乃成为一种亦知亦行,动静一如和体用一源的真工夫。不难看出,这种真工夫既可视为力斥“住心观静”的禅宗工夫思想的继续和深入,又不失为后来由刘蕺山发展的一种更为自觉、更为成熟的工夫理论之先行基础。
一种思想史的考查表明,在阳明之后,受禅学的影响,其后学的涉身化更是愈演愈烈,呈万牛莫挽之势。如果说阳明心学的涉身化尚不离“心”,尚以“心”的名义而体现的话,那么,其后学的涉身化则“图穷匕现”地使“心学”一变为“身道”,一改其先辈犹抱琵琶半遮面之姿,从宗心径直走向宗身,不是“心”而是“身”已名正言顺地成为其学说的真正核心。
在这方面,作为阳明学嫡传的泰州学派无疑可视为最为激进的先锋。如王艮提出“止至善者,安身也;安身者,立天下之大本也”(《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案一),提出“道重则身重,身重则道重”(同上),“以天地万物依于身,不以身依于天地万物,舍此皆妾妇之道”(同上);如罗汝芳提出“方信大道只在此身”(《明儒学案》卷三十四,泰州学案三),提出“吾之此身,无异于天地万物,而天地万物亦无异于吾之此身”(同上);如李贽提出“一元统天而万化生于身矣”(《九正易因》)。
这样,正如阳明对心的切己性的发现导致了其对“此在”的“此时此地”的肯定那样,阳明后学对“亲己之切,无重于身”的“身”的发现,则把这种肯定再次置于理论的重心。因此,阳明之后,被禅学封为圭臬的“当下”、“即此”重新被阳明后学靡然宗之。故阳明后学宣称“千年万年只是一个当下”(《明儒学案》卷十六,江右王门学案),宣称“当下者,学之捷法”(《明儒学案》卷三十四,泰州学案三),宣称“当下自身受用者,便是有下落”(同上),宣称“当下即是工夫”(同上),宣称“即此便是净土”(3)转引自刘聪: 《罗汝芳与佛教的因缘》,载张新民主编: 《阳明学刊》第五辑,成都: 巴蜀书社,2011年,第484页。。
刹那生灭的当下之身被佛学视为如泡如影,而今一变为被如此无上强调的实存,那么这必然使阳明学的在世性、知行合一以及真工夫之旨被阳明后学进一步蔚为光大地发明。
于是,我们在阳明后学中看到的,是王艮的“人有困于贫而冻馁其身者,则亦失其本,而非学也”(《语录上》),是罗汝芳的“人于何处求神佛,堂上双亲即是佛”(4)转引自刘聪: 《罗汝芳与佛教的因缘》,载张新民主编: 《阳明学刊》第五辑,成都,巴蜀书社,2011年,第481页。,是颜山农的“制欲非体仁”(《明儒学案》卷三十四,泰州学案三),是何心隐的“从心所欲,非欲乎”(《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案一),是李贽的“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焚书》,答邓石阳),是李贽的“夫厥初生人,惟是阴阳二气,男女二命耳,初无所谓一与理也,而何太极之有”(《初潭集》,夫妇篇总论)。显然,这些掷地有声的话语,既是对佛学“外人伦,遗事物”的出世之旨的力辟,又不失为对朱子理学不无佛学化的“新清教主义”取向激进的反戈一击。
接着,我们在阳明后学中看到的,是王艮以仆僮动作不假安排处指示“道”,是颜山农主张“平时只是率性所行,纯任自然,便谓之道”(《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案一),是罗汝芳宣称“此捧茶童子,却是道也”(《明道录》卷三),是罗汝芳以“举杯辄解从口,不向鼻上耳边去”(《明儒学案》卷三十四,泰州学案三)来说明知行合一之机奥。尤值得一提的是,对于知行合一,阳明后学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故黄宗羲称泰州学派诸公个个都勇于“赤身担当”,以至于赵大州赴贬所而山农与之偕行,波石战没沅江府而山农寻其骸骨归葬;以至于无论是何心隐还是李贽都是那样义无反顾地“立身行道”,即使殁身狱中也始终不改其行之所往,从而使其先师的“知行合一”之旨以惊天地泣鬼神之势得到阐扬。
最后,我们在阳明后学中看到的,是禅宗不无机动的“禅定工夫”一变为阳明“致良知”的真工夫,再变为王艮对“百姓日用即道”的高扬,终又以李贽所力揭的更为自觉的“后理学”的“语用学”为其绝唱。
如前所述,中国古代源于庄子的语用学思想,惟有殆及对“义学化”的佛学施以力纠的禅学的出现,才得以真正大明。但是,随着宋明理学这一新的“义理之学”勃然兴起,语用学思想又面临新一轮的灭顶之虞。这是因为,朱子理学实际上是以一种一物一义的“本质主义”的“语义学”为其前提,朱子所谓“格物致知”的提出恰恰与之完全一致: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大学章句·补格物传》)
在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那种坚持事实与语义(个理)对应,作为事实总和的世界和整个语义系统(天理)对应的西方不无理想化的语义学的中国版。但正如谐语所言,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人们一旦将之付诸实践,就会发现它实际上是很难兑现的。阳明“格竹子”不逞的故事恰恰证明了这一点:“先儒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谓一草一木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传习录》卷下)。在阳明看来,朱子理学这种本质主义的语义学不仅导致了事物表象向语义本质过渡的困难,而且出现了认识上“自在的语义”与“为我的语用”之间难以消解的悖反。正是针对朱子学这种不无顽劣的“语义的专政”,在宋明哲学中,以禅宗丰富而深刻的语言学思想为借鉴,从语义学重返语用学已势所难免。
陆象山无疑可视为这种重返语用学大潮中的第一人。他的“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语录》卷上)思想堪称石破天惊。这一“六经注我”思想既以其从“作者中心”转向“读者中心”,为我们开出中国古代的一种全新解释学的先声之鸣,又以其从语言“指示论”皈依语言“工具论”,乃为在中国思想新时期对禅学语用学之道的重振和再申。此外,论及这种语用学在宋明时期的中兴,明儒湛若水的“随处体认天理”(《明儒学案》卷三十七,甘泉学案一)观点亦不能不提。按湛若水的理解,这种“随处体认天理”并非指无论何处都可体认天理,而是指“天理非在外,特因事之来,随感而应耳”(同上)。故这里所说的,不正是禅宗所谓的“因人设教,因境设语”,因而是对朱子理学那种一物一理的严格语义学思想的大力抨击吗?因此,虽然表面上湛氏的“随处体认天理”是针对阳明心学而发的,实际上其真正矛头恰恰指向了朱子理学之弊。
但是,在宋明哲学中,真正师承禅学思想,而使中国语用学思想登堂入室的,则不能不公推秦州学派的大哲李贽。正是这位李贽,不仅以提出“六经注我”的象山的口吻,主张“惟大学问乃是自己受用”(《柞林纪谭》),而且还“不顾他人非刺”地敢于以所谓的“自私自利之学”自诩自命(《焚书》),从而在他那里,人类言说的为我所需、为我所用的性质已一览无余地彻底大白于光天化日之中。正是这位李贽,从对语言之“为我”的肯定,进而走向对语言使用者的实际处境、语境的肯定。故他对语言“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同上)的极力强调,既突出了语言“与时消息”的重要性,又从中必然引申出“经史互为表里”这一深刻论断。以至于他认为,无论是《春秋》,还是《诗经》、《书经》乃至《易经》,都具有亦经亦史的属性,并明确提出“故谓《六经》皆史可也”(同上)。这实为后来章学诚“六经皆史”思想的真正先声。也正是这位李贽,从语用的历时的变易性中,为我们发现了看似确定的语义实际上的不确定性。用他的表述,即所谓“时异势殊,则言者变矣。故行随事迁,则言焉人殊,安得据往行以为典要,守前言以效尾生耶”(同上),所谓“因病发药,因时治病,不得一概,此道之所以为大也”(同上)。由此出发,他不仅上宗孟子,为我们发出了“执一便是害道”(《藏书》)的呐喊,还旁援禅学,抨击“死在句下”的书奴,为我们留下了“书奴却以读书死”的警句。而李贽所谓“解则不执一定,不执一定即是无定,无定则如走盘之珠,何所不可。不解则执定一说,执定一说即是死语,死语则如印印泥,欲以何用也”(《焚书》)的提出,就其将语义的解答与死语的解缚完全打并为一来说,则使他当之无愧地可被视为人类“解构主义”的真正先驱,令以哲学“新锐”自居的现代西方解构主义大师们望尘莫及。
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禅学与李贽学说两者之间的惊人一致。如果说禅学的语言学对语义的破执导致了对“文字障”的解缚,那么,李贽对语义的解构则“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黄宗羲语),那种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圭臬的“名教”业已彻底威风扫地。如果说禅学的这种破执最终导致了其“呵祖骂佛”之举,那么,李贽的这种解构则使“非汤武,薄周孔”成为其学说发展的应有之义。而这里非薄的与其说是圣人本身,不如说是以“绝对真理”为潜台词的那种出凡入圣的话语体系。
因此,可以断言,惟有对作为绝对所指的“终极真理”彻底破而扫之,中国哲学才称得上是真正取得了理论上对佛学的最终胜利。也就是说,一如“言语道断,心行灭处”所指出的,恰恰在佛学的“言语道断”之际,才是佛学的“心行灭处”,也即佛学的唯心主义彻底地寿终正寝之时。
——从体、相、用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