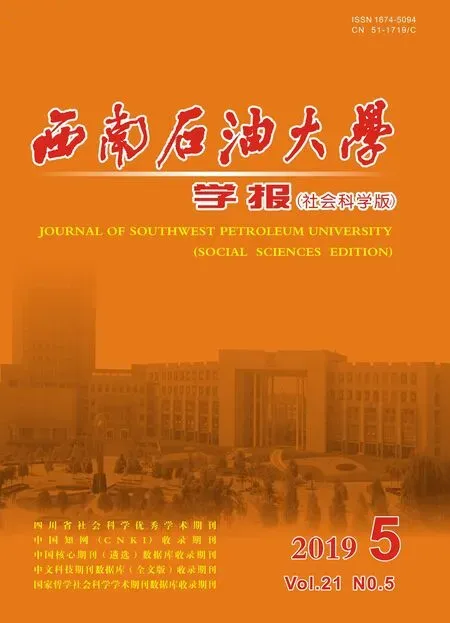论王国维的“本色”观
——基于王国维对元曲的评价
尹 超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引言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举足轻重的学术大师,熟谙中学和西学,他曾言:“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1]他早年学习西方哲学、美学,受叔本华思想影响极深,后转向对国学的研究,在古典词曲评论、甲骨文、史学等领域做出了丰硕成果。在对古典词曲的研究过程中,他借鉴西方美学的观点,提出不少精辟论断,不仅丰富了古典文论的理论内容,同时为古典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王国维先治词,后治曲,他对戏曲的评论延续了治词的角度和观点。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染,王国维品评词曲的理论内涵中继承了前人的评论观点。最为显著的是,他继承了明清曲家的“本色”观,并对其加以适当的改造,这在《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等著作中皆有体现。尽管在概念的使用上,“本色”一词出现的次数不多,而是用“意境”“境界”等概念建构起自己的美学体系,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十分密切,这为我们认识王国维的文艺美学思想提供了新角度。
1 王氏称元曲为“活文学”的原因
就笔者所见,在王国维的词曲著作中,“本色”一词仅出现于《宋元戏曲史》的“元剧之文章”一章,称关汉卿的杂剧“一空倚傍,自铸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为元人第一”[2]103。在《人间词话》中,他则使用“意境”“境界”等概念,如“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3]3,“言气质,言格律,言神韵,不如言境界。境界,本也。气质、格律、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三者随之矣”[3]127。他的“境界说”以作品有无“真情”为首要标准,如“境非独谓景物也,感情亦人心中之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3]9。他认为,作为抒情文学的词作必须有作者的真情实感蕴藏于内,卖弄文采、空洞无物之作即使用词华丽也称不上佳作。因此,“真情”是“境界”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真情则有境界。
对于“真情”的理论内涵,王国维也给出了自己的定义。他说:“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一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诗词皆然。”[3]91“沁人心脾”指的是言情要感人肺腑,“豁人耳目”指的是写景要真实动人,“脱口而出无一矫揉装束之态”则指的是用辞自然,不装腔作势。可以说,“真情”是王国维文艺美学思想的基础,也是其“本色”观的重要内容。
正是对“真情”的看重,才使王国维着力于对元剧的研究。关于治曲的原因,按他本人的说法,既出于传统文人的责任感,也受到词曲同源观点的驱使。他在《曲录序》中说道:“国维雅好声诗,粗谙流别,痛往籍之日丧,惧来者之无征,是用博稽故简,撰为总目”[2]143。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强烈责任感、使命感的知识分子形象。词曲同源的观点始于明代,王世贞在《曲藻》中说:“曲者,词之变。自金、元入主中国,所用胡乐,嘈杂凄紧,缓急之间,词不能按,乃更为新声以媚之。”[4]25自明以降,这一观点为大多数的文人所接受。王国维有言:“因词之成功而有志于戏曲,此亦近日之奢愿也”[5]189,证明他也认可这种观点,因此他说:“粤自贸丝抱布,开叙事之端;纤素裁衣,肇代言之体;追原戏曲之作,实亦古诗之流。”[2]142除上述原因,不视戏曲为末技、小道,不以文体论雅俗也是他治曲的另一原因,“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永叔、少游虽作艳语,终有品格。方之美成,便有淑女与娼伎之别”[3]50,这表现了他的文艺思想中进步的一面。
然而,从他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元杂剧抱有极为矛盾的态度。从戏剧艺术的角度,他对元剧十分鄙视,对明清传奇较为赞赏。例如他说,“元曲诚多天籁,然其思想之陋劣,布置之粗笨,千篇一律,令人喷饭。至本朝之《桃花扇》《长生殿》诸传奇,则进矣”[2]119,“吾中国文学之最不振者莫戏曲,若元之杂剧、明之传奇,存于今日者尚以百数。其中之文字虽有佳者,然其理想及结构虽欲不谓至幼稚、至拙劣不可得也。国朝之作者虽略有进步,然比诸西洋之名剧相去尚不能以道里计”[5]189。他在《录曲余谈》中也说:“至明,而士大夫亦多染指戏曲。前之东嘉,后之临川,皆博雅君子也;至国朝孔季重、洪昉思出,始一扫数百年之芜秽,然生气亦略尽矣。”[6]225他在《红楼梦评论》中,亦是将《桃花扇》与《红楼梦》做悲剧性的比较,而非“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的《窦娥冤》《赵氏孤儿》等元杂剧。
但从文辞的角度,他对元剧则十分欣赏,称赞其“优足以当一代之文学”[2]104,“千古独绝之文字”[2]77。正是这个原因,他没有研究明清传奇。在日本学者青木正儿拜谒他,言及自己打算撰写明清戏曲史的想法时,更是冷冷答道:“明以后无足取,元曲为活文学,明清之曲,死文学也。”[7]7王国维称元曲为“活文学”,与元曲作者蕴于其中的“真情”有莫大关系。他说过:“诗词者,物之不得其平而鸣者也。故欢愉之辞难工,愁苦之言易巧。”[3]124元曲作者正是处在“不平而鸣”的时代:科举考试中断几十年,文人的进身之路受阻,满腹才华无处施展,常使他们怀有抑郁悲怨之感。再者,元朝统治者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分治下民众为四等,汉人处于卑贱的第四等,倍受欺凌。另外,贪官污吏随处可见,权豪势要轻贱人命时有发生,有正义感的文人虽然满腹悲愤却无计可施,只好借助元曲进行宣泄。因此,王国维称元曲作者“彼但摹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流露于其间”。“胸中之感想”“时代之情状”“真挚之理”“秀杰之气”共同构成元曲的“真情”。
这也解释了为何王国维以西方悲剧、喜剧的标准观照古典戏曲,“明以后,传奇无非戏剧,而元则有悲剧在其中”[2]98。因为“不平而鸣”多与悲剧有关,相较于喜剧,悲剧有更多的真情寓于其中。明清文人的地位与生活远非元代文人可比,他们对待戏曲的态度也与元代文人不同,仅仅视其为消遣娱乐、卖弄才华的手段,这导致了明清的戏曲创作出现了不少不良倾向,如明代的“骈绮风”“时文风”,清代的案头化创作等等。由此,不难理解王国维称明清传奇为喜剧,明清之曲为“死文学”的原因了。
2 王氏“本色”观的内涵
王国维对元曲的研究基本延续了治词的角度和观点:只谈文本,不涉场上;只论曲辞,鲜及科白。青木正儿称其道,“然先生仅爱读曲,不爱观剧,于音律更无所顾”[7]1,诚非虚言。因为首重曲辞,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的“元剧之文章”一章中,先论元曲,“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他笔下的“元曲”与“元剧”的内涵不同,“元曲”包括小令、套曲和杂剧,“元剧”专指元杂剧。元曲之“自然”专指曲辞,与情节结构、思想主题、角色形象无涉,因此他说:“关目之拙劣,所不问也;思想之卑陋,所不讳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顾也。”[2]98论元剧单论文章,元剧之文章亦不包括思想结构,专指唱词,他将词论中的“意境”概念直接移用于此,说道:“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明以后其思想结构,尽有胜于前人者,唯意境则为元人所独擅。”[2]99不难发现,他在这里化用了《人间词话》中的“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等语,证明其词曲评论的理论一致性,论曲仍以“真情”为首要标准。
与词论不同之处在于,王氏曲论中的“意境”概念有新的内容,即“述事则如其口出”,这既是他对戏曲作品语言上的要求,也体现了他对戏曲艺术叙事性特点的准确把握。在治曲之前,他就说过:“然词之于戏曲,一抒情一叙事,其性质既异,其难易又殊。又何敢因前者之成功而遽冀后者乎?”[5]189写情、写景皆可以抒情性语言为之,但戏曲是叙事艺术,剧中人物的语言必须符合剧中身份,并能够推动剧情发展方为当行之作。因此,“当行”也是他的“本色”观的组成部分,是其“本色”观比“意境”说在理论范围上更为广阔之处。在这一点上,王国维继承了传统曲论的相关观点。王骥德说过:“引子,须以自己之肾肠,代他人之口吻。盖一人登场,必有几句紧要说话,我设以身处其地,摹写其似。”[4]138李渔也说:“填词义理无穷,说何人肖何人,议某事切某事,文章头绪之最繁者,莫填词若矣”[8]26,“言者,心之声也,欲代此一人立言,先宜代此一人立心。......务使心曲隐微,随口唾出,说一人肖一人,勿使雷同,弗使浮泛。”[8]54王国维的“述事则如其口出”体现了戏曲艺术的代言体、叙事性等特征,是对前人观点高度凝练化的表述。
除此之外,王国维对词曲中的使事用典也有自己的看法。他在《人间词话》中说:“人能于诗词中不为美刺投赠怀古咏史之篇,不使隶事之句,不用装饰之字,则于此道已过半矣。”[3]92他批评沈伯时的观点,说:“沈伯时《乐府指迷》云:说桃不可直说桃,须用‘红雨’‘刘郎’等字。咏柳不可直说破柳,须用‘章台’‘灞岸’等字。若惟恐人不用代字者。果以是为工,则古今类书具在,又安用词为耶?”[3]54他还以此为标准评价白居易和吴梅村诗作的优劣,说:“以《长恨歌》之壮采,而所隶之事,只‘小玉’、‘双成’四字,才有余也。梅村歌行,则非隶事不可。白、吴优劣即于此见。此不独作诗为然,填词家亦不可不知也。”[3]93由此看出,王国维从“真情”的角度出发,反对利用词作“美刺投赠怀古咏史”,反对过多使事用典、使用替代字。他结合戏曲艺术的特点,反对曲辞用语艰涩难懂,“惟语取易解,不以鄙俗为嫌,事贵翻空,不以谬悠为讳”
[2]142。他对元剧作品的评论也体现出这样的观点,例如评关汉卿《谢天香》第三折和马致远《任风子》第二折的[正宫端正好]一曲“语语明白如画,而言外有无穷之意”,评《窦娥冤》第二折的[斗虾蟆]一曲“此一曲直是宾白,令人忘其为曲”,评《倩女离魂》第三折的[醉春风][迎仙客]曲辞“此种词如弹丸脱手,后人无能为役;唯南曲中《拜月》《琵琶》差能近之”[2]99。这也体现出他对传统曲论的继承。王骥德说:“夫曲以摹写物情,体贴人理,所取委曲宛转,以代说词,一涉藻缋,便蔽本来。”[4]122李渔也说:“诗文之词采贵典雅而贱粗俗,宜蕴藉而忌分明;词曲不然,话则本之街谈巷议,事则取其直说明言”[8]22,“总而言之,传奇不比文章。文章做与读书人看,故不怪其深;戏文做与读书人与不读书人同看,又与不读书之夫人小儿同看,故贵浅不贵深”[8]28。
3 王氏“本色”观与吴梅“本色”观的不同
上文对王国维的“本色”观做了简要探讨,这里不妨将其与吴梅的“本色”观做一对比。吴梅是与王国维同时代的另一位研究古典词曲的学者,著有《词学通论》《顾曲麈谈》《中国戏曲概论》等著作,被认为是古典曲学的集大成者和现代曲学的开创者。王、吴二人的研究视野有诸多重合之处,却结论殊异。如评周邦彦词,吴梅大为推崇,“至用字发意,要归蕴藉。露则意不称辞,高则辞不达意。二者交讥,非作家之极轨也。故作词能以清真为归,斯用字发意,皆有法度矣”[9]400;王国维则稍有微词,“美成深远之致不及欧、秦。唯言情体物,穷极工巧,故不失为第一流之作者。但恨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耳”[3]51。二人对古典戏曲的态度也颇为相似,王国维认为元曲“自然”的原因是“盖元剧之作者,其人均非有名位学问也;其作剧也,非有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之意也。彼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2]98。吴梅推崇传奇的原因与之相类,“余尝谓古今文字,独传奇最为真率。作者就心中蕴结,发为词华,初无藏山传人之思,亦无科第利禄之见,称心而出,遂为千古至文”[9]985。不同的是,王国维写出《宋元戏曲考》之后,研究视野转向甲骨文、史学等领域,吴梅则耗尽毕生精力研究词曲,并培养诸多弟子,为曲学的传承做出了不朽贡献。
吴梅治曲的角度和观点延续了古典曲论的传统,其“本色”观亦然。首先,在其著作中多处使用了“本色”一词,兹举数例如下:
曲之胜场,在于本色,试遍看元人杂剧,有一种涂金错采,令人不可句读否?[9]5
实甫曲如“颠不剌的见了万千,似这般可喜娘罕曾见”及“鹘伶渌老不寻常”等语,却是当行本色。关汉卿《续西厢》,人瑞大肆讥弹,实皆元人本色处,圣叹不之知耳。[9]70
此曲绝佳,亦本色,亦妍丽,直是元人真相。[9]75
余独爱其字字本色,直夺关、马之席,明人北词,似此者少矣。[10]
词虽工,非元人本色也。[9]949
可以看到,吴梅曲论中的“本色”亦以元曲为圭臬。
吴梅的“本色”观亦注重“真情”,其言:“大抵剧之妙处,在一真字。真也者,切实不浮,感人心脾之谓也”,但他的“真情”没有新的内涵,仅是对前人观点的复述。此外,他讲“真情”非仅从文学评论的角度,还出于世俗性、功利性的考虑。他说:“风俗之靡,日甚一日。究其所以日甚之故,皆由于人心之喜新尚异。剧之作用,本在规正风俗。顾庄论道德,取语录格言之糟粕,以求补救社会,此固势有所不能也。就人心之所向,而为之无形之规导,则不妨就末流之习,渐返于正始之音,故新异但祈不诡于法而已。”[9]88从这里可以看出,他继承了古典曲论中“戏曲教化”的观点。
对作品的评论,吴梅与王国维只重曲辞的案头评论大相径庭。他擅长唱曲、度曲、作曲,熟于音律,虽有言曰:“尝谓传奇之道,首论事实,次论文字,次论音律。”[10]但他更多地是从排场角度分析、评价作品,尤其对洪升的《长生殿》推崇备至。兹举数例如下:
且文字之美,远胜有明诸家,《弹词》之[货郎儿],《觅魂》之[混江龙],虽若士、海浮,犹且敛手焉。至于音律,更无遗憾,平仄务头,无一不合律,集曲犯调,无一不合格,此又非寻常科诨家所能企及者。[10]
余谓《牡丹亭》衬字太多,《桃花扇》平仄欠合,皆未便效法。必不得已,但学《长生殿》,尚无纰缪耳。[9]60
惟其词句采藻,直入元人之堂奥。所作北词不在关、马、郑、白之下,且宫调谐和,谱法修整,确居云亭之上耳。[9]155
顾《桃花扇》《长生殿》二书,仅论文字,似孔胜于洪,不知排场布置、宫调分配,昉思远驾东塘之上。......余尝谓《桃花扇》,有佳词而无佳调,深惜云亭不谙度声,二百年来词场不祧者,独有稗畦而已。[9]307
从音律排场的角度评论戏曲作品,是古典曲论一以贯之的方式,也是吴梅对王国维曲论的纠偏、补充之处。
对作品的用字,吴梅亦崇尚自然,同时又有所保留。他在《词学通论》中引彭孙遹和吴衡照的观点为佐证,彭孙遹有言:“词以自然为宗,但自然不从追琢中来,便率易无味。”[11]721吴衡照亦言:“词患堆积,堆积近缛,缛则伤意。词忌雕琢,雕琢近涩,涩则伤气。”[11]2403由此看出,吴梅亦以“自然”为上,反对堆积词藻,用字“追琢”而不“雕琢”。他论曲亦是这个观点,“曲则不然,有雅有俗,雅非若诗余之雅也,书卷典故,无一不可运用,而无一可以堆垛。……以曲中所长,在乎超脱,正不必以情韵含蓄胜人也。至于俗则非一味俚俗已也,俗中尤须带雅。......盖烹炼者笔意,自然者笔机。意机交美,斯为妙句。若只顾烹炼,乃至语意晦塞,是违填词贵浅显之道矣,又安足取哉”[9]98。吴梅对这一问题的论述比王国维细致、丰富,注重用字要“烹炼”,但“烹炼”的目的是为语句达到“自然”的程度,而非“语意晦塞”。对曲辞的雅俗有程度上的要求,太雅与太俗都不可为,讲究浅显易懂,还应做到谐耳方为佳作。这比王国维的“不以鄙俗为嫌”更注重戏曲艺术的品格和观众的审美需求。
4 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王国维之所以称元曲为“活文学”,在于元曲中洋溢着时代之“真情”。首重“真情”构成王国维“本色”观的理论基础,同时吸收了古典曲论的“当行”论,讲求语言符合角色身份,用语浅显易懂。他的“本色”观比“意境说”有更广阔深刻的理论内涵,在吸收古典曲论的同时,将西方戏剧理论的因素做了恰当的融入,从而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古典曲论的面貌,使之获得新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