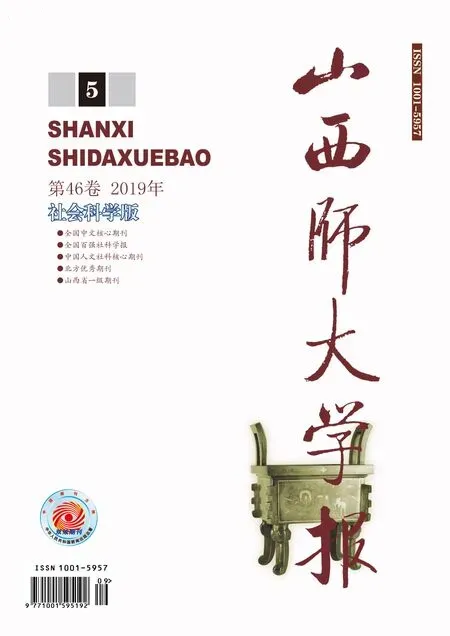孟荀之外的第三条儒学进路
任 剑 涛
(清华大学 政治学系,北京 100084)
近期关于儒学现代发展进路的主张,大致有二:一是或光大孟子心性儒学传统,或发挥荀子政治儒学统绪。这是源远流长的一种传统。二是举孟旗行荀学、统合孟荀。这是李泽厚、梁涛两位的主张。后两种言说进路,其实都是想促使儒学走出个体心性修养的狭小天地,着力为儒学寻找现实政治出路。在这两种大思路之外,真正秉承董仲舒进路以开拓现代儒学发展新境,或许是儒学发展应予重视的第三条进路。
一、政治儒学的凸显
说起来,进入当代中国学术场域的政治儒学已经有一段历史了。早在1991年蒋庆发表了纲领性的政治儒学文章《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论当代新儒学的另一发展路向》[1]80—91,算是政治儒学的正式登台。在此没有用他后来出版的《政治儒学》《再论政治儒学》和《广论政治儒学》作为政治儒学登台的标志。因为人们有理由相信,将那篇文章作为政治儒学正式表述的出台标志是完全成立的。从那个时候算起,政治儒学发展到今天将近30年了。这是一种将孟荀、或者说将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判然二分的主张。
今天政治儒学已经颇有声势了。但分析起来,大部分的政治儒学其实是反政治的。这个断言不带有任何价值判断的意思。而是想强调,既然将儒学的理论形态命名为政治儒学,那它就必须鲜明地体现出它的政治性。不过,政治儒学实在不是政治地思考(thinking politically)政治的结果,而是道德地思考(thinking morally)政治的结果。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因为政治儒学的论述,本是想弥补孟子高悬于超越层面而对政治事务重视不足的“缺陷”,努力将政治儒学经验化、政治化。李泽厚、梁涛两位兼综孟荀(李)或统和孟荀(梁)[2][3],都存在打开儒学经验层面的意图。但实际上李、梁二位还是没逃掉反政治的儒学思维羁绊。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李、梁以及倡导政治儒学的蒋庆,都是在人文学科的范围内看待政治的,他们对实际政治事务并不关心,所论便必然是一种书斋政治儒学。在我看来,书斋政治儒学要么是反政治的,要么是疏离政治的,唯独不可能是政治的。因为限于书斋玄想,政治只能是玄想者的价值偏好表达,而与实际政治事务难以关联起来。
所谓政治地思考政治,就是不将政治视为观念之争、价值偏好表达,而是尝试通过讨价还价、程序安排、妥协机制等实践导向的进路来理解和处置政治事务。符合后者的即是政治地思考政治,不符合的就叫非政治和反政治的思考。[4]151这不是说非政治或反政治的思考就是错误的思考,而是说那对揭示政治真相的价值有限、对构造能够实际运行的政治制度的效用不大。
现代政治儒学已经展开了多种路径。我关注的是其中两种路径,一种是孟荀分离,即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分离。这是蒋庆的路径。他特别强调自己主张的政治儒学与心性儒学的重大结构差异。为此明确指出心性儒学存在的四大极端化缺陷。这是蒋庆对政治儒学之别于心性儒学的原初、系统的表达。近期蒋庆表达的政治儒学越来越圆润了,剑拔弩张的说法很少见到。我认为他原初的纲领性表达才是他廓清两种儒学判然有别的学术边界的明晰说法。
他指出了心性儒学的四大缺陷。一者,他批评港台新儒家的极端个人化倾向。在我看来,这是蒋庆误读的结论。新儒家的个人化倾向,完全就不彰显——他们对张扬个人价值有态度,没立场,无论证。只是在支持民主的情况下申言个人的价值,但实际上没有对个人主义的系统阐述。一旦进入传统儒家思想的阐述,其实都还是集体主义。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乃至于整个大陆的新儒学研究,在我看来都没有重视个人。忽视个人是中国现代儒家政治理念的一个基本缺陷。进而言之,在中国现代思想世界中,个人只存在于文学世界之中,而且是以个性的面目来表现的。此外,中国的现代个人一直处在严重的压抑状态。
二者,他批评港台新儒学的极端形上化倾向。这对心性儒学也有些不公。港台新儒学第四代代表李明辉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对此进行了辩驳。[5]人们确实很难把港台新儒学对民主科学的开怀拥抱说成是极端形上化的。他们也关注形下问题,只不过因为牟宗三是通过康德三大批判及其翻译并作为理论参照来建构自己理论体系的,所以蒋庆有此一说。这就把牟宗三“外王三书”的形下关怀遮蔽了。所以这是个不公平的断定。
三者,他批评港台新儒学的极端内在化倾向。这也是一个需要辨析的断言。尽管港台新儒家确实走的是一条从内圣开出外王的路子,但只要承诺了“良知的自我坎陷”,也就给予了政治儒学以相对独立的地位。所谓“理性的运用表现”与“理性的架构表现”之别,确实敞开了儒学向下运思的门径。
四者,他批评港台新儒家的极端超越化倾向。港台新儒家确实大力张扬“内在超越”观。但他们虽然极为关注个人内在的生命与心性,却并不将之作为自己思想的唯一主题。他们也关注社会政治问题,并且对港台的民主政治转型做出了重要理论贡献。况且,在政治世界中看,他们采取的既超越传统儒学、又超越现代民主的立场,配合内在超越的儒学特质之论,确属一种理论创制进路。
蒋庆在指出港台新儒家四大缺陷的基础上,明确采取一种孟荀分离的进路,或者更宽泛地讲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分离的立场,来处理政治儒学建构问题。他确实将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鲜明区隔开来,并且刻画了一条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的“大陆新儒学”建构路子。蒋庆的这一断定非常强势。他认定,当代新儒学只有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才能解决当代中国所面临的政治问题,从而完成自己的现代发展。[1]在蒋庆这里,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是当代新儒学开出新外王的必由之路。除此之外,不做他想。
二、对立,抑或综合孟荀
不同于蒋庆的另一条进路,是李泽厚和梁涛的路子。在他们看来,实际上儒家内部存在一种儒法对立且互补的结构。儒门有兼综儒法思想的大家,荀子就此洞开大门:孟子为儒学设定了道德理想主义的进路,因此是儒家讨论政治正当化问题的理想派;荀子则从政治视角坐实儒家的政治制度安排,因此是儒家实际介入政治事务的务实派。因此李泽厚讲“举孟旗,行荀学”,梁涛主张“统合孟荀”。两者似乎都心存一种弥合分裂性地处置儒学古典遗产的对立。这对现代儒学的重建也许不失为一种解决同室操戈困境的思路。
不过人们可以看到,两种进路都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理论与实践难题。就蒋庆进路看,要凸显一条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的“必由之路”,起码需要满足两个排斥性假设:一是其他儒学进路都完全没戏了,因此明灯孤悬,只好走蒋式政治儒学之路。二是他单纯突出了儒学的政治品格,相比而言,似乎心性儒学就不那么儒学了。前者显然为其他现代新儒家学者所不同意,后者需要蒋式政治儒学接受政治检验。但因为蒋式政治儒学严重与现实相疏离,而且是一种绝对逆转现实、回到传统的政治思路。显然,这就将必须进入儒学政治设计场域的其他各家各派排斥在政治商议的范围之外了。故而它明显是一种非/反政治的思路。这既然是一种不够政治的政治主张,因此只能是一个个人政治主张的理想化表达。这样的表述,还不能叫作政治学表述,其“政治”儒学的命名就令人生疑了。
蒋庆所强调的政治儒学九大特点,在我看来都不那么“政治”。一是他强调政治儒学能够体现儒学本意的说法,很难成立。儒学“本意”的说法,其实就是寻求“原教旨”(fundamentalism)的说法。而“原教旨”在其最严格的层面上,就是恪守教派最初的理想设计,但离开教派原创者即孔子本人的阐述,谁也不能僭越到孔子的位置扬言自己所说是儒家“本意”。今时今日儒家中人声称的儒家本意,要么是一种修辞,要么是一种争夺学术支配权的表现,实际意义非常有限。
二是他认定政治儒学才是关注社会的儒学。其实,如李明辉所言,港台新儒学不会不关注社会。梁涛重视的儒学之推己推恩,对之政治儒学在讲,心性儒学也在讲。关注社会的儒学自然是关注现实的儒学,而关注社会的儒学建基于心性关注,两者之间不能够绝对切割。蒋庆对两种儒学的区分确实有些牵强。此外,他所说的政治儒学九大特点,循此归纳为三四点足矣。他之所以将二者的差异性罗列出九点,不过是想暗示人们,政治儒学跟心性儒学的区别太大了。蒋庆自己是学法律出身的,对类型学的表达不太在意。在我看来他区分为三点的内容其实谈的是一个问题,如政治儒学是关注政治实践、当下历史、现实状态的儒学,其实都是同一个关注而已。
三是他认定政治儒学是主张性恶的儒学。这对孟荀差异的认定太过硬性。性恶性善,孟荀的分析是殊途同归。(21)见前引梁涛文的分析。另见任剑涛《伦理政治研究》第三章第二节“人性善恶:政治抉择的德性凭借”,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8年出版。蒋庆的区分存在停留于孟荀直接文字表述上面的嫌疑,性善是用来凸显良心仁性的道德根基重要性的,性恶是用来批判人性凸显政治矫正价值的,两者指向的都是儒家的仁心仁政这回事情。像蒋庆那样认定唯有政治儒学才能标示儒家的政治理想,就意味着他还是在表达一个理想层面的儒家政治理念,并没有落实在政治事务之中讨论政治理论。蒋庆对政治儒学特点的其他罗列就不再一一讨论了。
简单强调一个事关儒学理论类型分类的意思,就是论者长期对荀子的理论类型定位是不确的。荀子并不是真正解决政治问题的儒家“政治学”现实主义,他的政治思想其实是另一种理想主义,而不是现代背景条件下人们一般认为的那种政治现实主义或者经验主义。基于此,可以说无论是分离孟荀还是统合孟荀,都是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断然二分的视角给出的结论,颇可商榷:蒋庆分离孟荀,或者更广泛的讲,将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分离的方案,确实有一种双失的危险:一方面,他守持原始儒家的立场不够坚定。另一方面,他的政治儒学之现代政治品格又不足够。所以他冒着双失的风险言说的政治儒学,并不是因应于中国的现代变迁提出的儒学论说,而是一种基于个人政治偏好的一己表述。秋风认为蒋庆是60年来唯一思想家[6],这样的表彰有些过甚其词了,实在是一种小圈子的相互赞美而已。李梁统合孟荀,同样有一种双失的风险:一方面,他们想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一锅煮,可能两头不靠岸;另一方面,由孟及荀,后者由荀及孟,或者兼综孟荀,都有一种将二人政治关怀打为两截的危险,一种后起的两截尝试,可能就不是孟荀自己的意愿,而是尝试连接两人主张的第三方的第三种论说了。
蒋庆1991年对政治儒学理念的表达,简洁明了。以此对蒋庆政治儒学的特征进行概观,也就更为准确。后来蒋庆在应对各种批评的情况下,对政治儒学进行的修正性表述,好些已经丧失了他原本立场的鲜明性,变得模糊、含混起来。假如论者关心蒋庆学术观点的流变,就会忽视蒋庆的原初表达,甚至对基于这篇论文论述蒋庆政治儒学观点感到愤慨。人们会觉得蒋庆的修正性观点才是更准确反映他政治儒学主张的说辞,岂不知那是蒋庆面对批评时的一种事后矫正,反而不能作为论述他政治儒学立场的首要论据。
蒋庆截然对立儒学内部的两种立场,并以此作为自己申述政治儒学的前提条件,确实存在校正的余地。人们可以承诺,人的物理本性、生理本性、社会本性、道德本性从来都是可以在分析上清晰区分开来的,而它们在实践中却是可以紧密贯通的人性特征。就此可以说,统和孟荀不是什么实践难题,但在理论分析上确实是一个难题。从实践的视角看,孟荀确实不存在人们想象中那么大的差别。在这个意义上讲,荀子的理想性是面对政治事务而显,孟子的理想性是面对道义性而现。实际上在儒学的绵延史上,现实主义和经验主义从来都无从入门。梁涛为统合孟荀辩护了半天,就是试图打开儒学的现实面向。岂不知梁涛并没有真正为经验敞开大门。因为孟荀是那么容易统合的话,那么如何解释千百年的儒学大师分裂性的主张,难道是他们智力不及?或者他们不知道孟荀的关怀非常一致?或者拘守孟荀一端不能自拔?与蒋庆的表达相类,梁涛的表达只不过是跳到了蒋庆的另一极:分离孟荀的主张看到了传统儒学的分析性差异,统合孟荀看到了传统儒学的实践统一性。但试图在理论与实践上通观孟荀,无论是蒋庆还是梁涛,都不如李泽厚来得聪明:所谓举孟旗,行荀学,就是在理论上或分析上承认两者的差异,但在实践上将政治正当性与政治事务性对接起来。人所共知,李泽厚的举孟旗,行荀学,是他整个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的一个构成环节。所以搜索出他这篇“举孟旗,行荀学”的文章,并不是一个具有系统性的理论阐释,只不过是表达一种立场而已。在这篇文章里,李泽厚只有三段话论及这一主张。
他的论述很简单明了,就是良知良能,不足以解决内在心性修养向外推的政治外王问题。外推得靠荀学。因为荀学强调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为)也。人为的东西就此引申而出,不会像孟子那样将儒家的政治主张憋死在心性世界里。李泽厚“举孟旗,行荀学”是有些反讽意味的。因为之所以他乐意“举孟旗”,就在于孟子强调人的良知良能,且将政治正当性深深扎根在道义沃土中。否则这个孟旗怎么举得起来呢?这个高飘的旗帜就是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旗帜。如果孟旗不是一面道德理想主义的旗帜,我们就完全没有必要“举孟旗”。你举着孟旗说我要干实事儿,就把旗帜当成了口号,就不但亵渎了道德理想主义不说,而且遮蔽了政治事务讨价还价的实在性。而之所以需要“行荀学”,就是因为政治事务不是举着道德理想主义旗帜就可以连带解决的,需要人们对制度与举措高度关心,并且将之作为解决政治现实问题的不二法门。如果你“行荀学”却躲进道德理想主义的硬壳之中,就不仅无法投入现实政治世界,而且根本就无从求解政治治理之道。
所以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肯定是两回事情。在这个特定的意义上讲,梁涛试图统和孟荀,实际上处在意愿与结果统和不了的窘境。因为孟旗、荀路对举的时候,前者是一种战略思维,后者是一种策略思维;前者看的是未来和长远,后者着重在当下和程序,两者完全无法打通。无法打通,又如何统合呢?跳出人文学科的思路,按照社会科学思维,人们就会知道,政策决策的过程从来都是当下诸要素互相博弈的结果(22)参见戴维·H·罗森布鲁姆等著《公共行政学:管理、政治与法律的途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七章“决策”对政治决策的描述与分析,尽管其论述是在现代背景条件下展开的,但具有一般的适应性。而不是申言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就可以顺带解决的事情。
李泽厚主张的“举孟旗,行荀学”,有可能把举旗与走路当成分别来做但统归于一的一码子事儿。但在举旗与走路之间,似乎缺少一个贯通两者的必要环节。为此,梁涛特别强调儒家的心性论还是个必要的中心与中介。围绕这个中心与中介,举什么旗的问题自然得到解决,同时,走什么路的问题也就有了一个前行的灯塔。这简直是一条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的路子。其实这是中国人一个莫名其妙的、不切实际的盼望。这个盼望给人一种滑稽的感觉。这不是说梁涛滑稽,而是说这个理想滑稽:仰望星空得务虚,脚踏实地要务实,又虚又实,那是人绝对不可能同时做到的事情,因为这是两条难以兼得的实践路径。须知,理想的确立、德性的修为,与资源的需求、实际的配置,以及政策的决策、具体的执行,完全是两码事情。仰望星空的时候,人们根本不必要有任何的政策考虑——向上,政策决策需要考虑的最重要根据是政治、法规与欲求;向下,政策决策与执行重视的是妥协、商量与满意。行政权力是连接决策与执行的关键环节,这正是现代政治体制中行政管理成为重要事务的理由。在政治理想与现实之间,悬着一个复杂的政治博弈环节。这是理想不能捎带解决的难题,也是政策实施不会关注的问题。而这正是政治之为政治,且必须经由程序机制、商议过程与妥协安排才能得到满意解决的问题。
在我看来,梁涛实际上试图把李泽厚举旗走路之分离前提下的贯通性考虑在起点上就统和起来。他们二人与蒋庆是完全对立的思路吗?答曰不是。李泽厚的考虑,是蒋庆分立孟荀过渡到梁涛统和孟荀的一个实用性方案。梁涛觉得在这里李泽厚可能会遭遇一个危险,举着孟旗却行的是荀学,怎么坚持儒学的价值立场呢?实践岂不是单独决定着儒学的前途与命运了?儒学的价值立场会不会因此丧失呢?在我看来,这是大陆讨论儒学对自己设置的障碍。可以设问,儒学坚持仁爱立场是不是就够了?还是一定要坚持内圣外王?内圣外王是现代儒学界定何谓儒家、儒学的一个临时性概念,将之作为儒家的核心,是对儒家精神的不解。这个不解,不是在道德意义上讲的,而是在学理意义上讲的。因为儒家更重视的不是内外问题,而是本末问题。“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所谓三纲八目,就此才能得到准确理解。[7]82—94在这个特定意义上,李泽厚试图将荀学往下行的力量往上提,提到孟子旗帜高扬的地步;同时又将高举的孟旗仅仅作为旗帜,让其飘扬在荀学政治务实的坚实土地上空,两全其美,各得其所。问题也因此出来了:举旗走路,各行其是,儒家岂不是价值主张与政治实践完全分裂了?梁涛的统合孟荀主张,实在是想替李泽厚补锅。
三、另辟蹊径:董仲舒的知行双关进路
蒋庆及李泽厚、梁涛的两种政治儒学方案,其实都可能造成一个双失的局面。什么双失呢?首先,就是坚守儒学立场的一个设定,是在儒学的流变上下手,而没有真正坚守儒家创始人的“本真”理想。他们没有走到孔子处寻找儒家的真精神。在某种意义上,梁涛统和孟荀,其实是把荀子提升为孟子,把孟子略为下降成为荀子。孟子当然不是原来的孟子,荀子也不是人们理解的荀子了。在这一点上,梁涛自有其一片苦心,人们会对之产生一种强烈的呼应感——唯有如此,儒家的政治理想关怀与政治现实主义应对,才能不被区隔,才能维系内圣外王的传统机制。但在我看来,梁涛的这个主张,可能有点委屈荀子了,他把荀子事实上置于孟子之下了;同时又可能有点委屈孟子了,因为他会把孟子的关注点下落到荀子的关注点上,结果可能会将荀子提拔到孟子之上了。这还不如像李泽厚那样干脆举个孟旗,走着荀路来得干脆。其次,就是坚守儒学的立场,其实是在坚守古代儒学的立场,而没有以正视“现代”为前提条件来审视儒学的现代重建处境与问题设定这两个关乎建构“现代” 儒学的决定性问题。结果,“现代”已经隐而不彰,“现代”儒学又从何建构起来呢?因此,“现代”儒学很大可能只是在现代时间范围内的儒学而已,并不具有实质上的“现代”精神特质。一种被古代儒学严重限制了价值视野与问题设置的儒学建构,就势必成为一种不古不今、不中不西的悖谬产物。[8]
比较起来,梁涛的政治性品格比李泽厚弱,比蒋庆就更弱。梁涛把统合孟荀搞成了一种政治愿望。当统和孟荀变成政治愿望的时候,其论说的政治品格就出不来了。换言之,梁涛的论说理想性,让他无法走向一个程序化的政治安排。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怎么去考虑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的问题,本身就成了问题。如果说存在一个与心性儒学不同的政治儒学,或者说我们要建立一个面向现代的新外王论说,面对传统儒学的中坚组成部分,也就是孟学与荀学,究竟是统是分,都无法达成起码的共识,都无力在一个儒学体系中安顿二者的位置。结果就是现代儒学陷入不可自拔的内部讨伐,处在一种内部判教的精神紧张之中。不屑儒学或反对儒学的人们,只要笑对儒家内部的分歧,看惯儒家的内部判教,就可以置儒学于不顾,那么儒学中人又怎么可能既解决心性问题又解决政治问题呢?退而言之,儒学又怎么能有效解决心性问题、政治问题呢?
这是一个怎么有效处理儒学的传统资源和儒学的现代面向的两难问题。在儒学内部,究竟按照他们三个人的两组方案往哪个方向去走,就此成为一个难以两全的问题。政治儒学的政治品格和原初儒家或孔子路径显著不同。这是需要矫正的。我觉得,按照梁涛给我们提示的思路,统合孟荀,是要看到儒家走到荀子,已经展现出了两种理想主义,道德理想主义与政治理想主义。问题常常在于,人们不把荀子的政治思想当理想主义看。人们以为,只要一提荀子政治思想的现实面向和经验导向,他就是儒家处置政治事务的具体方案设计者。这是对荀子的误解。如果人们愿意区分理想政治和政治理想,就有了区分孟荀思想的一对概念:孟子谈的是理想政治,仁心仁政就是理想政治最简单的刻画。虽然它来自良知良能,而不来自柏拉图《理想国》的几何学知识根基,但它确确实实是排斥现实约束,而具有强大的、时空超越的规范性力量。换言之,他的方案可以不接受经验检验。一种政治经验成功了,或是失败了,既无法验证、也无法推翻孟子的道德理想主义。它永远是一个最高的政治标的,它就放在那里。就像共产主义一样,人类只能永远朝这个方向逼近。如果你强行把理想政治硬生生摔到桌面上并制造一套实施方案,那就一定会陷入道德专制的泥淖。当人们一定要把理想主义变成现实方案,就会将理想庸俗化为现实,理想与现实就会一同被埋没了。
荀子的政治理想主义有一种误导人们的特质:人们常常以为理想政治之下只存在具体实行的政治方案。其实不是。荀子设计的所谓王道政治——“王者之人”“王者之制”“王者之法”“王者之言”等,很多人认为它是王道政治的实施方案,这是一大误解。自然,王道政治的最高理想方案要到《孟子》那里去找。但荀子所提供的,也只是王道政治的次级理想方案,绝对不是实施方案。以理想主义眼光来看待政治问题,理想政治是最高标的,政治理想是次级标的。后者确实是面向政治的,但不是具体处理政治事务的。政治地对待和处理政治事务,实际上是荀子的学生开出来的。但是他们已经走向了法家。儒家因何联姻法家,构成“儒表法里”的政治思想结构,是一个“务为治者”的政治问题注定了的事情。从荀子往下走,走到政治世界之中,才真正开始处置具体的政治事务。但秦的“万世之基业,二世而亡”,证明法家也没有真正处理好政治问题。汉代董仲舒与汉武帝的成功对策,才将理想政治、政治理想与政治事务关联起来处理,那是一种旨在融通诸家并切入政治世界的进路,而非对立或贯通孟荀取向的结果。这其实代表了儒家走出天真的理想主义政治天地、走进真实的政治世界的第三路径。而这已经是处在孟荀之外的政治思考进路了。
需要强调的是,这样的进路,并不是蒋庆着力阐释的董仲舒春秋公羊学的进路,而是董仲舒着力以儒学为核心对诸家的吸纳,以政治事务的处置为中心通盘考量儒学建构的路数。蒋庆对董仲舒春秋公羊学遗产的挖掘与发挥,是值得肯定的一条儒家式政治思想进路。但蒋庆重公羊学传统胜于重公羊学实践,因此无法理顺董仲舒方案实施的关键条件。董仲舒的建构是在古代政制运行的机制中展开运思的。他设置的限制皇权的大思路:天人相副、天人感应与天人谴告学说,仍然是一种既不能伸张限制皇权意图的挂空神权,也不能坐实为一个水平面上的权力相互限制的实在分权,仅仅是以心理恐吓(天对人的谴告)为支撑的准神权思维的产物。就神权限制皇权的一端来讲,因为董仲舒根本缺乏教会制度的想象,因此也就缺乏世间神性的负载者,一旦大胆妄为的皇帝心理、性情格外坚强,不受恐吓的阻遏,董仲舒对限制皇权就无计可施了;就皇权受分权机制的限制来讲,董仲舒就更是付诸阙如了。这不是什么令人羞耻的事情。同一时期,除开罗马一个特例以外,没有其他古代国家实现了类似的突破。我们也没有理由强求古代先祖实现这样的突破。而今眼目下,这正是我们自己需要承担的时代责任。如果今人试图秉承儒家宗旨,那么董仲舒的第三条儒学路线,就是一条具有真实的政治现实品格的进路。也许,从蒋庆的公羊春秋学再往前推,坐实董仲舒未能凸显的限制皇权的两个基本条件,政治儒学就有可能真实得降临人世?
在蒋庆思路之外,董仲舒对儒学的汉代之兴所发挥的极大推进作用,最具当下启示作用的一点是:董仲舒将儒家学理的建构与儒家政治实践方案内在嵌合起来加以高度综合。这是此前的儒学均未完成的思想任务与实践切入。对孔、孟、荀三人来讲,孔子确实开辟了儒家旨在恢复“天下有道”政治的神性进路,但他自己的政治实践明显是不成功的。后起儒家只能对孔子以“素王”目之,可谓最准确凸显孔子的政治实操的尴尬,与政治思想深远影响和政治实操影响力的不对称。孟子与孔子一样,奔走列国、凄凄惶惶,终究只能下帷讲学、教育弟子。以司马迁评价孟子的“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便知道孟子已经明显偏离孔子路线而走上了高远的道德理想主义之路。荀子对战国后期的思想界影响极大,其三为齐稷下学宫祭酒便可知这一影响力。但荀子以一兰陵县令的身份,是绝无实践其“王者之治”的机会的。倒是董仲舒,引诸家,尤其是阴阳家的天人之际思路入儒,而将诸家学说熔冶一炉,创造了秉承儒家宗旨,但森严儒学理念的学说体系。同时,借助“天人三策”将儒家理念深深切入汉代政治操作过程,直接塑造了汉代政治风格,并深远影响整个中国古代政治。儒家在理论体系建构与实践方案设计上真正在诸家中力拔头筹,并取得全面的、真正的成功,始自董仲舒:所谓“推明孔丘,抑黜百家”(《汉书·五行志》)。正彰显了前者的特质,“更化”政治正展现了后者的特征。正是这一进路,对后起的、同时具有理论和政治雄心的儒家中人预制了一条实现其两种想象的基本理路。
董仲舒真正让儒学站在了理论与实践双关的巅峰:在儒家学理的建构上,由于董仲舒综合了诸家之长,尤其是让儒学立于“天人之际,甚可畏也”(《天人三策》)的神性基点上,并成功建构起神—人与人—人相互双重关联的庞大思想体系,这一思想成就是先秦诸子的其他各家后继者完全无法企及的。同时,董仲舒将儒学理念成功引入政治运作过程,真正实现了儒家扭转“天下无道”局面,恢复“天下有道”秩序的预期目标,因此将儒学理论建构与儒家政治实践内在嵌合起来。董仲舒的这一惊人成就,让儒学成为两汉数百年的主流政治方案,并深刻、广泛而持久地影响了整个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生活局面。倘若人们试图理解作为中国古代政治意识形态主流的儒家,非经董仲舒无以知其门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