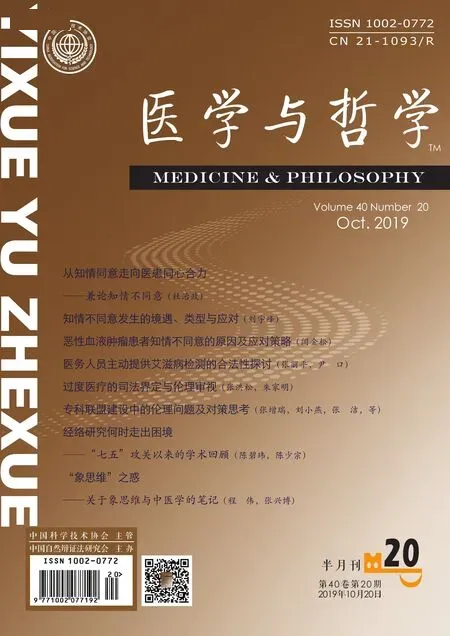非恶性呼吸疾病患者缓和医疗应用的探讨
张馨予 万群芳 吴小玲
缓和医疗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出以来,发展至今主要应用于晚期癌症患者及其家庭,帮助其减轻痛苦,提高生命终末期的生活质量。近年来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疾病谱和死亡谱已发生较大变化,部分慢性非恶性疾病因疾病呈现进行性恶化、不可治愈、疾病症状重等特点也被纳入缓和医疗的应用范畴。相比肺癌患者,非恶性呼吸疾病患者生命终末期对于缓和医疗的需求不容小觑。但由于后者疾病发展轨迹不确定、预估生存期困难、缓和医疗转诊时机不明等原因,其缓和医疗的开展相对困难。本文通过介绍缓和医疗的发展与应用、非恶性呼吸疾病终末期的发展特点,探讨其应用缓和医疗的必要性以及策略和建议,为临床实践提供经验。
1 缓和医疗概述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缓和医疗(palliative care)自临终关怀(hospice care)发展而来,主要为身患癌症、长期患病的患者缓解疼痛及其他不适症状,使其平稳地度过生命最后几周或几个月的没有痛苦的日子[1]。世界卫生组织对缓和医疗定义为[2],是一种通过对疼痛和其他身体、心理和精神问题的早期识别、严谨评估和有效治疗,预防并减轻痛苦,从而改善面临威胁生命疾病的患者及其家人的生活质量,满足其所有(包括心理和精神)需求,提高面对危机能力的系统方法。有研究表明,接受缓和医疗服务的患者往往能够在家中得到照顾和支持,从而提高了患者及其家人的满意度,减少丧失亲人的长期悲伤和创伤后应激障碍[3]。缓和医疗的实施明显减少了患者终末期的急诊就诊、住院和ICU治疗的几率,避免了医疗资源和费用的过度支出[4-5]。
2 非恶性呼吸疾病的特点与应用缓和医疗的需求
马潇[6]对我国缓和医疗相关研究的系统评价结果显示,癌症患者占总人数的87.5%,包括肺癌、胃癌、盆腔肿瘤等各个系统的癌症。癌症已经成为全球首要死因,发病率和死亡率仍在逐年上升;由于诊断和治疗水平的限制性,很多癌症患者确诊时已经处于疾病中晚期,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无法治愈;癌症患者症状负担重,癌性疼痛使其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因此,基于以上癌症的疾病特点,自缓和医疗提出以来,发展至今主要应用于晚期癌症患者。其中,肺癌预后不佳,一直居于我国恶性肿瘤发病首位和死亡首位,约85%的患者确诊时已为晚期,Ⅳ期非小细胞肺癌5年生存率低至0~10%,遭受着咳嗽、呼吸衰竭、疼痛、咯血、恶病质等痛苦症状,缓和医疗需求较大[7]。Temel等[8]对151例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进行早期缓和医疗干预,研究结果显示相比单纯抗癌治疗组,接受早期缓和医疗的联合抗癌治疗组患者生活质量有所提高,抑郁症状减少,中位总生存期延长了2.7个月。
近年来随着疾病谱和死亡谱的改变,慢性非恶性疾病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其中呼吸系统慢性非恶性疾病(以下简称“非恶性呼吸疾病”)包括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支气管扩张症(bronchiectasis)、间质性肺疾病(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ILD)等[9]。随着雾霾天气、工业废气及汽车尾气排放日益增多,空气污染日益严重,加之吸烟、吸二手烟等原因,非恶性呼吸疾病患者日益增多,且具有和肺癌相当的症状负担。COPD患者呼吸困难发生率高达90%,在全球人群中的发病率约为10%,居当前疾病死亡原因第四位[10]。支气管扩张症患者由于反复炎症,肺组织和肺功能严重受损,最终可突发呼吸衰竭而死亡,英国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其死亡率是普通人群的两倍[11],高出COPD大约50%[12]。特发性肺间质纤维化预后差,确诊后的中位生存期只有2.5年~3.5年,生存期之短堪比癌症[13]。
与肺癌相比,Walke等[14]研究发现COPD患者症状中疼痛、疲乏、抑郁的发生率与肺癌相似,而焦虑和呼吸困难的发生率高于肺癌。Chou等[15]研究也发现,COPD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呼吸困难和痛苦的程度均高于肺癌患者,COPD患者具有与肺癌患者相当的缓和医疗需求,但却未受到相应的重视。Goodridge等[16]回顾了1 098例死于COPD或肺癌的患者数据发现,能够在医院、医疗机构、家中接受缓和治疗的肺癌患者分别占47.6%、12.7%、37.4%,而COPD患者占比仅为5.1%、1.3%、2.8%。
缓和医疗是每一位生命终末期患者应该享受到的权利,但由于疾病发展的特点,慢性非恶性疾病患者的缓和医疗需求极少得到满足[17]。与肺癌具有较为明确的疾病转归相比,非恶性呼吸疾病发展轨迹不确定[18],ILD患者的病情可在短短2个月内迅速恶化,有些发展机理仍不清晰,COPD往往会出现病情突发急性加重,甚至引发突然性死亡,因此很难预估疾病生存期,也给选择采取何种治疗方式造成了严重的困难。非恶性疾病缓和医疗转诊很难统一标准,Wallace等[19]的研究表明非恶性疾病患者大多在濒死阶段才被转入缓和医疗服务机构,部分患者及照顾者没有意识到非恶性疾病可以威胁生命。
非恶性呼吸疾病患者的症状负担和对正常生活能力的影响并不低于肺癌患者,加之病情反复发作,同时缺少缓和医疗的支持,其生活质量远低于肺癌患者。
尽管接受标准治疗,疾病进展仍会造成非恶性呼吸疾病患者进行性肺功能降低,日常活动被主要症状限制,出现慢性肺衰竭(chronic lung failure)。当慢性肺衰竭患者出现终末期疾病症状时,如在半年内因COPD加重住院两次,需长期氧疗,或在家中进行长期无创通气等,便会出现终末期肺衰竭(terminal lung failure),预期寿命仅为几周或几个月。丹麦呼吸协会建议在出现慢性肺衰竭时就应启动缓和医疗,在控制终末期患者症状的同时,改善其生活质量[9]。
3 非恶性呼吸疾病患者终末期缓和医疗应用的策略和建议
缓和医疗的首要任务是症状控制,减少疼痛和其他痛苦症状,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其次,要加强医患沟通,明确治疗目标,同时为其提供心理支持系统,减少患者及照顾者的灵性痛苦。
3.1 症状控制
非恶性呼吸疾病患者在生命终末期其生理和心理上对缓和医疗的需求至少与肺癌晚期患者一样严重,相关研究中多次提及的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和生命存活的症状负担有呼吸困难、焦虑、抑郁、厌食、疲乏、体重下降、肌肉萎缩、失眠、恐惧等。
3.1.1 呼吸困难
呼吸困难在呼吸系统疾病中最为常见,应最大限度地进行支气管扩张剂治疗,如长效β受体激动剂联合长效抗胆碱能药物[20],使支气管持久扩张,满足患者日间活动的最低需求,同时保障夜间睡眠质量,进而可以减少患者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的发生。根据患者的病情需求,必要时可辅助氧疗或是进行无创呼吸机通气治疗[21]。氧疗可以改善患者的低氧血症,目前研究推荐每日氧疗至少15小时,可以减缓肺动脉高压进展,改善神经心理健康。但是,长期氧疗的必要性和有效性还未得到充分证实,Lacasse等[22]的研究发现长期氧疗的COPD患者存在更高的焦虑抑郁发生率、生活质量低,甚至过早死亡等现象。使用无创呼吸机通气是符合缓和医疗原则的,既避免了气管插管或气管切开等有创治疗,又可以保留患者在生命终末期的自主性。
肺康复在呼吸慢性病患者中被强烈广泛推荐,终末期患者同样也可以因其受益。但由于患者严重的疲乏和活动受限,肺康复必须在专业呼吸治疗师或康复治疗师的指导和监督下进行,如指导患者进行呼吸控制训练、放松训练,通过纠正姿势找到省力体位等[23]。还有研究报道了湿化空气、风扇吹风、开阔视野等改善呼吸的方法[24],尽管效果比较微弱,但也可以为终末期的患者及照顾者提供一些努力的方向。
除此之外,低剂量强阿片类药物治疗呼吸困难被越来越多地推荐,如每天一次性给予20mg硫酸吗啡缓释剂治疗难治性呼吸困难是有效并且安全的,同时辅助使用苯二氮卓类等抗焦虑药物效果更佳[25]。
3.1.2 焦虑抑郁
非恶性呼吸疾病患者在终末期因呼吸困难、活动受限等原因,活动范围被限制在家中或医院里,逐渐丧失活动和交往能力、依赖氧气、被氧气管限制、嘶嘶作响的供氧声音等都是导致焦虑抑郁高发生率的原因。英国一项对209例死于COPD的患者病历数据研究发现,77%的患者情绪低落,53%的患者出现过惊恐发作[26]。同时呼吸困难与焦虑相互影响,恶性循环。
目前,苯二氮卓类药物治疗焦虑抑郁应用较多,如使用低剂量地西泮已有较多研究报道[20,23]。
除药物治疗外,发挥缓和医疗服务中的人文关怀和心理护理也是非常重要的,如医生与患者、照顾者进行充分的沟通,发挥缓和医疗团队中如社会工作者、志愿者、心理治疗师等人员的作用等。
3.1.3 其他
良好的气道管理可以改善非恶性呼吸疾病患者咳嗽、咳痰的症状,教会患者及照顾者日常拍背、有效咳痰、使用振动式排痰仪,掌握简单的气道管理技巧。有条件者可使用负压吸痰装置及时清理呼吸道,改善患者体验。
对于出现厌食、体重下降的患者,需要在营养治疗师的指导下均衡饮食营养,可通过提高食物的色、香、味来增加进食。对于重度活动受限的患者,无法一次性完成进食时,可采取少量多餐的形式,保证患者的进食安全。
非恶性疾病患者终末期大多合并高血压、糖尿病、房颤、关节炎等病症[27],这需要与全科医生仔细讨论治疗方法,缓解患者的症状负担和心理负担。
3.2 沟通交流
3.2.1 多学科团队合作
缓和医疗作为关注生命终末期患者及其家庭生理、心理、社会等全方面需求且不同于一般常规医疗的医学亚专业,其工作的开展必然依赖于多学科合作的、专业的缓和医疗团队。对于非恶性呼吸疾病来讲,该团队的核心人员应是具备缓和医疗能力的全科医生或肺科医生,尤其擅长治疗呼吸困难、及时准确判断缓和医疗介入时机、与患者及家属时常进行充分有效沟通等。由于非恶性呼吸疾病进展轨迹不确定,准确判断缓和医疗介入的时间是其工作开展的难点之一。Vermylen等[28]通过研究COPD等非恶性呼吸疾病患者死亡的预测因素,来为缓和医疗介入提供参考依据,如年龄≥75岁、一秒用力呼气容积(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in one second,FEV1)<30%(辅助评估呼吸困难程度)、病情频繁加重导致半年内两次入院、长期氧疗、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18kg/m2等。Murray等[29]还推荐了英国初级医疗体系中基层医生用作缓和医疗补充筛查工具的“生命意外之问”(surprise question),即医生自问:“如果我的病人在12个月内死亡,我会感到意外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应考虑在目前干预治疗中逐渐介入缓和医疗。
针对非恶性呼吸疾病患者出现的呼吸困难、肌肉萎缩、厌食等主要症状,呼吸治疗师、康复师、物理治疗师、营养师等能够专业地为其缓解痛苦。
除此之外,缓和医疗团队中还包括社会工作者、志愿者、音乐治疗师、按摩治疗师、精神照护者、牧师、病案管理者等专业人员[30],主要缓解患者心理及社会层面的负担。对我国来讲,缓和医疗起源于国外,是个舶来品。在借鉴学习的同时,应该结合我国国情,而非完全照搬。传统理念下面对死亡,中国人更倾向于家人儿女陪伴在身边,了却生前事是最好的解脱。所以社工、志愿者、牧师等人员配置在我国可转化为对家属或照顾者的缓和医疗教育培训,进而满足患者的灵性需求。
3.2.2 早期照护计划与沟通
早期照护计划(advance care planning,ACP)在国际文献中被多次提及,丹麦呼吸指南对ACP的定义为终末期患者、照护者和多学科缓和医疗团队之间的沟通交流,其重点是(但不限于)伴随疾病和痛苦症状的生活,包括医学治疗的限制性、痛苦症状的缓解、生命周期结束的决定、倾向的死亡地点、生前遗憾及心愿等。ACP通过医患双方多次的交流沟通,使医生更了解患者,患者更了解自己,让医生在制定医疗计划时更果断,让患者在生命终末期更具自主性。研究显示,ACP应选择在患者病情稳定期进行,且需要安排一个相对宽松足够的时间,而非急性加重或住院期间[31]。ACP的目的并不一定是减少或停止治疗,而是促进了解患者的愿望及需求,确保均衡的治疗[32]。
3.2.3 关注照顾者的缓和医疗需求
临终患者的照顾者也是缓和医疗需要干预的对象,其身体、情感、社会、精神以及经济方面的需求往往严重复杂得多[33],如与患者一起经历反复急性加重入院、时刻目睹患者呼吸困难的痛苦、同样被疾病“禁锢”在床旁、日益加重的照护负担却又看似病程遥遥无期、患者去世后又遭受永别的哀伤等。
普通人群在面对临终和死亡时都会感到恐惧,并且束手无策,缓和医疗鼓励照顾者与患者之间充分的沟通交流,同时还要对照顾者进行专业的信息传输,如对生死和生命自然的解读、患者的疾病特点和病情进展、缓和医疗的介入和实施等。还可教给照顾者简单的急救应对方法,提高照护能力,如上文所述的缓解呼吸困难和厌食疲乏的物理方法。
3.3 远程医疗
随着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远程医疗逐渐在医疗资源相对匮乏的非中心地带应用起来。目前,由于能够提供专业缓和医疗服务的医院或医疗机构相对较少、终末期患者转诊不及时,以及患者及家属更倾向于在家中接受缓和医疗与照护等,远程医疗在缓和医学领域的应用有重要意义[34]。Vitacca等[35]对10例晚期COPD患者进行远程辅助居家缓和医疗,通过专业讲解使其明确在发生非常严重的呼吸困难时可以选择气管插管、无创通气、氧疗或药物等,并于出院后每月进行一次缓和医疗护士电话随访,评估随访前后患者的焦虑、抑郁、生活质量、沟通质量等。经过6个月的远程干预,2名患者从气管插管改为药物和氧气治疗,5名患者最终死亡,但都表示有明显地满意度提高。Marquis等[36]对15例无法参加肺康复的终末期呼吸疾病患者进行远程指导,发现肺功能和生活质量有所改善。
在缓和医疗服务尚不完善的今天,专业的缓和医疗人员对一般住院或居家患者进行远程指导,以此满足其对信息的需求,促进对选择的理解和症状的管理,同时还能减少对“被抛弃”的认知。
4 我国非恶性呼吸疾病患者缓和医疗发展的启示
相比其他医学亚专业,缓和医疗在我国的发展并不突出,目前仅以“点”的形式在经济发达、医疗资源充足的城市有所发展。2015年经济学人智库发布的全球死亡质量指数报告显示,在全球80个国家中,中国临终死亡质量排名第71位,低于南非、乌干达等非洲国家。在呼吸系统疾病中,我国关于缓和医疗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肺癌晚期患者,非恶性疾病的文献较少。
在缓和医疗实施过程中,涉及三个主要方面的力量,即政府、医疗人员和患者。政府层面,政策支持和财政投入是缓和医疗发展的前提。英国、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无一例外都制定了保证缓和医疗实行推广的法律法规或医疗政策、战略,在医院、社区、养老机构鼓励设立缓和医疗病房,同时还将其纳入到国民医疗保健体系中[37],而这两点是目前我国尚未具备的。医疗人员方面,专业的多学科团队是缓和医疗发展的主体,除培养专门的缓和医护人员外,还可以加大缓和医疗教育力度,对全科医生、专科医生、护士等进行缓和医疗培训,扩大新生力量[38]。患者层面,也是公众层面,目前我国普通人群大多已经认识到癌症晚期患者可以通过如临终关怀、姑息医学、安宁疗护、缓和医疗等享受“优死”的权利,但对于非恶性疾病并没有共识。家属,特别是患者子女在患者生命终末期坚持对其治疗的执着是缓和医疗实施最后的障碍,因此应加大公众教育,提高普通群众对非恶性疾病应用缓和医疗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