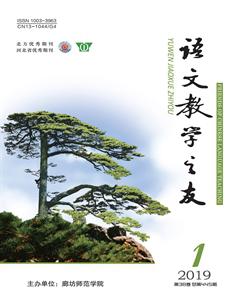试论中语教材文本中审美错位造成的情感张力
摘要:中学语文课文中常有些许矛盾,有些地方不合情感逻辑,给读者带来不少困惑,但困惑背后往往蕴含巨大的审美空间,亟待读者探究挖掘。在审美过程中,情感的张力并不一定存在于崇高美好的事件中,相反,有些张力是在一种错位和断层的情况下呈现,这需要读者能够细细斟酌,感受那份错位背后的魅力。
关键词:反崇高;疏离化;恐怖化;错位;情感张力
文学作品是作家们“以我观照”,并将情感融入其中“着我之色彩”的智慧结晶。而文字则是一种载体,作家借助文字表达自己独特的审美,所以艺术作品中塑造出的典型形象以其独特的视觉折射着生活的深刻,鞭挞着时代的不公,这往往能引起读者的阅读期待,并将之内化于心。
文学期待承载着审美的感悟,让读者追随生命本真的轨道,领略人生真谛之光华。但遗憾的是,读者常常被文字的表层含义所遮蔽,在他们的潜意识中,审美价值的表现形态是较为单一的——崇高的人格、挚爱的亲情均由赞叹的口吻娓娓道来,而丑陋的形象、遗憾的失败则用疏离甚至冷漠的文字进行庄严地审判。这是审美的误区。其实,情感表达与文字抒发上的不和谐乃至错位断层,才是大师手笔,是刻意而为之的奇崛之美。在文学作品中,情感与文字并不一定重叠映衬,相反,常会呈现疏离状态,即“错位”——情感和文字的差异,二者离心力越大,越能引发思考。笔者认为,美学的“误差”(错位)的方式有反崇高、疏离化和恐怖化等几个方面。下面将从这几个方面来探究中学语文教材文本中“错位”背后的情感张力。
一、反崇高的错位:用笨拙展现亲情,用渺小书写高大
学生在诠释父爱之崇高的时候,喜欢用真善美的语言,进行崇高而诗意地刻画,塑造出亲情上的“高大全”,文字也就自然流于“假大空”,没有感染力,让人感到厌俗无味。
其实,崇高与美好如果等量齐驱,美好就会失去某些意蕴。在朱自清的《背影》中,美好恰恰存在于那几个笨拙的动作之中。父亲老而胖,着装普通,难登大雅之堂,可他偏偏要在月台上蹒跚,他艰难的“攀”“缩”本身就不崇高,反而很市井:他没有规则意识,不体面。但这却能令读者为之动容,这背后的情感渗透,远高于描写父亲玉树临风的“正面”形象。可见,父亲这种不顾形象、老态龙钟的身影,也能让我们洞察他内心中儿子高于一切的信念。
这时候,越是不崇高越能逼近生活的本质,进而引发我们的共鸣——曾经,我们是否也因为父母的普通而拒绝将父母引见给朋友?所以这更能击中我们的内心。因此,情感审美的主观性和反诗意描写的客观性错位相交,反而形成如盐化水的亲情张力。于朱自清,那是一份痛感,于读者,又是一份审美的快感。至此,情感的张力达到顶峰。
朱自清用笨拙展现亲情,而胡适用反诗意的语言来颂扬母爱。读过《我的母亲》的人或许会怀有这样一种疑问:文章前三段形同虚设,应该存在吗?但正如契诃夫所说:“如果在第一幕里边出现一把枪的话,那么在第三幕枪一定要响。”这说明前三段的存在一定饱含匠心。我们来仔细研读:胡适19岁出国留学,归国后当了北大教授,著作等身,引领着文学革命的浪潮。胡适的成就无疑与母亲的辛苦栽培分不开。但母亲是真的事事都做得完美无瑕吗?文章第一段“小时不曾养成活泼游戏的习惯”“失掉了学做画家的机会”,有人提议吹笙或吹笛却遭到“族里长辈反对”,这些虽是一笔带过,却不难根据海明威的“冰山原理”推导出母亲位列其一。母亲为了把儿子培养成读书人,或许剥夺了胡适一些游乐的机会,固执地为胡适划定了学习的界限,不可逾越,甚至连我们现在大力提倡的音乐艺术和绘画艺术都一点不让沾边。可以说,这样的教育有些许狭隘的成分。“又因为我确是喜欢看书,故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过儿童游戏的生活”“别的方面都没有发展的机会”第一句话意味深长,作者极力制止自己内心的“小确丧”,以平静的口吻出之,你又是否能读出他淡淡的遗憾?
《我的母亲》一文前三段的口吻如此平和,仅仅只在个别字眼透出隐隐的遗憾,这其实是一种离间效果。作者并不是完全心悦诚服,他平淡的语言就此形成了一种陌生感,但他能体悟母亲的用心良苦,于是疏离之中又带有理解与尊重。所以,在《我的母亲》一文中,母亲的严厉是一份情感审美,而母亲偶有的过错也是一种审美,只是这份审美造成了情感的离间色彩,多年后,当时小胡适的遗憾、心酸、落寞和无奈慢慢积淀成了陈香的佳酿,通过一种情感的皈依,将这份错位的亲情阐释得淋漓尽致。
二、疏离化的错位:用悲剧书写崇高,用失败彰显深刻
《伟大的悲剧》顾名思义,就是希望在悲剧中挖掘人性的闪光点,在已经被毁灭的美好中寻找另类的成就。我们向来只对第一名歌功颂德,却习惯性忽略第二名。可是,茨威格却展现给我们一个陌生化的典型——失败者的崇高。在这篇文章当中,精神层面崇高的人文之荣耀和现实层面遗憾的失败之耻辱已经形成了审美价值和实用价值的错位,而这样的错位无疑给我们带来了一场情感的冲击。在失败的阴霾下,我们看到的是一场人格和灵魂的博弈——奥茨格悲壮地走出帐篷迎向死亡、威尔逊带着岩石样本长途跋涉、斯科特用绝望书写科研日记,厄运可以毁灭生命,却摧毁不了尊严。这份伟大毋庸置疑,但现实是,他们失败了,行动上的伟大和结果上的悲剧形成了巨大的疏离。他们本可以在国内悠闲地喝着咖啡,但他们却选择用生命来换取对宇宙探索的进步。他们的付出,作者用“鲁莽”来形容,这分明是一种情感的悖逆。他们“鲁莽”地闯进人类的禁地,当死亡的闸门庄严地落下,读者的审美体悟也达到巅峰,对“鲁莽”一词在内心也重新作了界定——鲁莽就是那份在困顿中上下求索、坚持不懈的毅力!正是这份失败和毁灭,铸就了一份高贵和伟大。如果换个角度,书写阿蒙森在风雪之中挥斥方遒,或许我们的快感仅仅停留在成功者的喜悦中。真善美高度统一,对于文学审美来说或许不是一件好事,而疏离化的错位,用悲剧凸显英雄,贬词褒用,则更能彰显情感的喷涌。
除了利用典型创造疏离化的个人和结局之外,还有一种形式,就是用平凡和普通的人物来表现深刻的主题。《背影》中的父亲、《最后一课》中的韩麦尔先生和小弗朗士都是如此。小弗朗士是一个普通的,甚至“不合格”的学生,他上课分神,被提问到的时候甚至“开头几个字就弄糊涂了”,还“摇摇晃晃”:或许在老师们眼中他就是一个较为头疼的滞后生。可就是这样一个“不合格”的学生,在最后一节法语课上,内心深层次的情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从厌学到内疚,从害怕老师到崇敬法语,这样的转变不是通过老师的责骂所表现出来的暂时的悔过,而是在特定情境下(国家遭受侵略)打破内心惯性的情感体验,重组心理结构的表现。学生是平凡的,而老師呢?“40年来,他一直在这里”,这40年来,他的工作状态是时常让学生停下功课帮他浇花,甚至停课自己去钓鱼,所以40年了,作为老师的他,却没有任何进步和升职。可以说,他是一个极为普通的乡间教书匠,可就是这样一位普通的人,让自己高大的背影镶嵌在和平的午祷声中,展现着法兰西帝国不灭的国魂。
以平凡人为支点,撑起宏大叙事和崇高主题,这样的悖离,就会因错位而造成巨大情感张力,渲染出超强的审美效果。
三、恐怖化的错位:用丑陋定格美好,用可怕引起深思
前文提到了情感的悖逆,意即明明情深意重,却轻描淡写,明明痛心疾首,却用一种没有温度的语言来描写不忍的画面,这份“错位”又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审美张力?
《老王》中“辞路”的片段就是一例。作者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社会底层人物的宽和、憨厚、知恩图报的人性光环。他临终前送来了鸡蛋和香油。这是一个社会的底层人,却对作者一家怀着感恩和照顾之心。一般而言,我们要塑造这样的一个形象,一定会用上溢美、怀念之词,更何况这是一个已经故去的人物,就更加值得缅怀。可是作者却用一种毫无温度的文字来描绘他。实际审美和精神审美二者之间往往有着截然不同的取向。实际审美是用客观冷静的描述来真实再现一个人物当时当地的情景,这很有可能会是一种丑陋的甚至有点恐怖的画面,但在这极丑的表象背后,则是灵魂的崇高。作者眼中的老王是:“面如死灰,两只眼上都结着一层翳。”“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这是对生命垂危者的写照,作者本该用一种悲天悯人的口吻来书写,但其却用“僵尸”来形容自己当时的害怕和直接的反应。作者愈是不假思索地将自己当时的恐惧写出来,就愈加能够将日后明白老王的一片苦心后的愧怍表现给我们。如果说,當时对他近乎刻薄的印象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怜悯和评判,那么,到最后明白老王要的只是一份友人之间平等、相知的尊重和关心之后,作者马上就转向仰视——对一个社会凉薄人高贵的品性,自己不但没有理解,反而对他的病态感到害怕,对于老王真情的馈赠,自己不懂得以朋友之格相待,反而用金钱打发。这其中的悲剧意味就浓浓地显示出来了:我把你当至亲,你却客套多于友情。老王满以为自己倾其所有,就能换取自己在世上唯一的挂念和尊重,没想到却被拒之千里,但他身上的人性闪光点却让我们仰视。
终此,文学的文字和本质不一定有着高度的契合,而作者精心呈现给我们的也不一定是表面浮动的情绪,而应该从反崇高、不诗意、疏离化甚至恐怖化的文字背后去品味独特的情感体验,只有这样,审美的张力才能带给我们巨大的快感。所以,珍惜那份“误差”,品读一份人生。
作者简介:吴萍萍(1987—),女,福建省厦门第六中学二级教师,主研方向为中学语文阅读和写作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