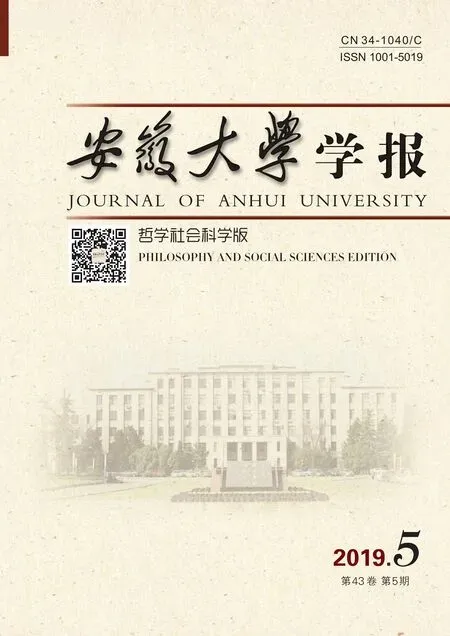“寻根文学”对传奇叙事的择取和拓新
郭冰茹,郭子龙
传奇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传统,确如希尔斯所言,是一种“历经延传而又持久存在或一再出现的东西”(1)希尔斯:《论传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1页。。在漫长的文体发展史中,传奇逐渐衍变成一个内涵丰富和外延宽广的概念。一方面,它涵括了自身独特的读解系统、精神模式和价值规范,另一方面,它异乎寻常的“旨趣”又可以延伸出很多供发掘、认识和阐释的资源。从某种程度上说,“传奇小说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是多层次的。选材立意、布局谋篇、情节结构、人物造型、审美趣味、语言表达……几乎是全方位的”(2)石麟:《传奇小说通论》,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79页。。反映在当代文学中,则突出地表现在传奇传统对“寻根文学”的构思模式、审美方式和叙述方式等方面产生的规范力和制约力。
一
就中国小说发展史而言,传奇叙事总是或隐或显地穿插其中。这主要涵括了三个维度:其一是由于中国传统小说对故事和情节“情有独钟”,这使传奇一脉在这种“深得人心”中得到发展;其二是“无奇不传,无传不奇”的小说惯性使然,这使传奇一脉的辐射面愈发深广;其三是教化与娱乐之间形成的某种张力,让写作者总是对传奇一脉念念不忘。由此,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书写总会在不同程度上承续、激活和创新传奇传统。
如果我们梳理传奇衍变的语境,会发现这一概念本身就是一个内容多样、内涵丰富的聚合体,关于传奇之名在不同时代也莫衷一是。“宋人以诸宫调为传奇;元人以杂剧为传奇;明人又以唱南曲为主的戏曲之长者为传奇,以区别北杂剧;近代又以专写英雄人物的小说为传奇小说。”(3)周中明、吴家荣:《小说史话》,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第43页。以至于对于它的定义、发展和变化,历来学界也总是众说纷纭。石麟在追溯传奇小说的“前世”时认为:“传奇小说是从先秦两汉史传文学蘖变而来,由‘杂传’和‘志怪’相结合而产生的一种极具文学性的文言小说形式。”(4)石麟:《传奇小说通论》,第6页。可以说,传奇作为古典小说的一脉,脱胎于史传,具有史传的叙事性,但随后因“志怪”而被赋予了传奇的特色。换言之,传奇文体是在纪实与志怪交错的背景下逐步具有了相对新颖多面的内容展现和艺术追求。陈国军在此基础上概括了传奇的文体特征:“传奇是指‘文备众体’,‘尽设幻语’‘作意好奇’和‘假小说以寄笔端’,也就是具有综合性、虚构性、新奇性和寄托性的一类文言小说。”(5)陈国军:《明代志怪传奇小说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5页。对照这一界定,唐传奇便是这一文体系统中非常典型的一脉,它突出地呈现了这一文体的核心特质。
因此,本文将传奇的文体特征定位于唐传奇,借此讨论传奇文体之于“寻根文学”的影响。事实上,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已将唐传奇视为传奇的典型文本,他称其为“传奇文”:“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轶,然叙述婉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由显者在是时则有意为小说。”(6)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54页。由此可知,唐传奇之于小说文体的革新在于作者创作意识的自觉勃兴。从这个意义上说,唐传奇确立了小说文体的独立,也开辟出一个崭新的文学场域。
中国现代小说虽由“西方”催生,但对中国古典叙事传统的择取从未中断。比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唐宋传奇集》中对传奇文体的意义探寻,并且在《故事新编》中借助神话故事和志怪传奇对传奇有所创新;郭沫若在《牧羊哀话》《柳毅传》《喀尔美罗姑娘》《骑士》等作品中建构出传奇般的奇遇故事和人物形象(柳毅、端华宁、金佩秋等);郁达夫的《过去》《青烟》《迷羊》等,也是在异乎寻常的传奇故事中传达出一种情绪和感怀;沈从文在《月下小景》中用《龙朱》《神巫之爱》《媚金、豹子与那羊》等文本建构出一个个新奇的故事,在奇特的氛围中凸显了小说的传奇色彩;张爱玲“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7)张爱玲:《传奇》,上海:上海“杂志社”,1944年,第1页。,她的《金锁记》《倾城之恋》《茉莉香片》等小说都是此类善于用“凡”来显“奇”的典型代表。
中国现代小说在题材选择、叙事细节和小说意旨等方面内蕴了传奇文体的精妙之处,这种承续和新变在当代文学中也有着明晰的体现,其中“寻根文学”表现尤其明显。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韩少功、莫言、李锐、张承志等为主力军的一批作家以“寻根”的理念,在对文化传统的追溯中探测到传奇叙事丰富的内涵,并将传奇这一文体蕴含的巨大张力变为最有效的抒写方式。以“寻根”视角搭配传奇色彩成为一种自然的写作实践,这主要表现在审美维度、书写对象和意义指向三个层面上。
在审美维度上,如前所述,虽然神话史传深刻地影响了小说的发展,但在唐传奇之前,那些以文字的方式记录下来的奇闻逸事仅仅是停留在表象上的“传世”或者“警世”,基本没有清晰的文学创作意识,也就谈不上写作技巧和文学想象。小说作为对现实的一种艺术再现,内蕴其中的审美性是不可或缺的,因而中国古典小说的审美维度主要在教化与娱乐之间徘徊。从唐传奇开始,小说逐渐获得了文体的独立,并在审美维度上开始注重文学的本质。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界对“纯文学”的讨论实际上就是对文学审美的诉求,而“寻根文学”在审美追求这一向度上靠近了传奇一脉。而且,“寻根文学”的产生基于一种“世界文学”的文化语境,中国文学对“西方”拿来主义式的文化接受所带来的身份焦虑,在某种程度上促使作家追溯本土文化资源和叙事传统的意识愈渐明晰,在对文化传统的探寻中也对文学新的审美诉求进行了再选择。
在书写对象上,传奇的“征奇话异”影响了书写对象的选择,并创造出一种陌生化的审美效果。“寻根文学”在书写对象的选择上呼应传奇传统,小说文本对物奇、人奇、事奇、心奇等新奇对象的描摹成就了“寻根文学”的基本特征,而“这些超出一般读者感受和经验的地域风情,会给不熟悉当地文化的读者带来审美上的陌生感,从而营造出一种传奇化的效果”(8)郭冰茹:《当代小说的写作技术与“传奇”传统》,《上海文学》2018年第9期。。于读者而言,陌生化的阅读效果带来了全新的阅读感受;于作者而言,这也是他们积极摆脱预设思维的一种努力。
在意义指向上,传奇作家“在撰写一些神异故事时,并没有将这些东西看成‘真实’,而是借此而言彼。或借神异而状写现实生活,或借荒诞来表达某种思想,有的甚至就是借题发挥的讽世之作。因此,他们的‘好奇’‘传奇’,并不是以‘奇’为‘实’,而是借‘奇’写‘实’”(9)石麟:《传奇小说通论》,第338页。。而“寻根文学”也以寓言的方式表现出作者的社会责任和文化使命。他们借助带有寓言气息和象征色彩的文本将神秘气息融入其中,意在挖掘和探求民族传统文化的流变过程、构成方式以及新的发展等问题。这些文本如同原始“神话”的构建方式,在一个光怪陆离的氛围中营造一个具有隐秘性的神秘世界。这些“神话”潜藏着一个民族幽深的文化机理,并蕴含着这个民族的文化之根。
二
“寻根文学”对传奇文体的拟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专注于“地域”性的书写,陌生化的阅读效果令文本显“奇”;二是通过有意的“错位”和“失真”,形成表达上的寓言性,呼应着传奇传统;三是审美追求上的“逾规越矩”,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既定思维,回应了传奇的精神。可以说,以上三点使得“寻根文学”在承续传奇叙事的实践中显得更有张力,这些内容相对集中地反映在“寻根文学”对边缘地域文化的展现上。
就地域文化的书写而言,寻根文学与此前的当代文学有着很大的不同,比如“十七年文学”时期,包括新时期的初始阶段,决定小说观念的核心因素是政治意识,文学创作基本呈现为单一的政治视角。作品中所描摹的地域文化大多作为模糊的背景而存在,起着烘托场景、渲染气氛的作用。作家无意于通过对特定地域的人文地理、风土人情、日常习俗的开掘来思考社会问题,也无意于借助对有限的地方风物的描绘去浓缩一个民族的历史、现状和对未来的想象。“寻根文学”不同,它择取了传奇传统的“作意好奇”,冲破规范化程式,聚焦于边缘地域的书写,开掘出颇具传奇色彩的边缘文化。因此,相对于主流文化而言,这种书写对象所带来的陌生化效果令文本显得非常“标新立异”。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回避了主流文化的“不规范的传统文化”是对传奇叙事的一种拟用,也是它对传统的一种认知。
所以,我们不难发现,被纳入“寻根”旗下的许多文本关注的不都是主流的汉文化,而是那些原始的、野性的、边缘的甚至是神秘的新奇文化。郑万隆说:“我企图利用神话、传说、梦幻以及风俗为小说的构架,建立一种自己的理想观念、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观念和文化观念。”(10)郑万隆:《我的根》,路文彬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料文论选1949—2000》,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第403页。“寻根”作家在原始的边地寻觅鲜活的素材,借助传奇叙事将这种独有的神秘气息勾勒出来,意在挖掘和探求民族文化传统的流变过程、构成方式以及发展的可能。于是,我们看到韩少功借古老的湘西追逐楚文化的影子,李杭育在葛川江上访问吴越文化,郑万隆深入东北乡村发掘山林文化,贾平凹用“商州系列”来寻绎秦汉遗风,郑义则以太行山村的书写来体会晋地文化等等。从某种程度上说,“寻根”作家们意识到了地域文化中所蕴含的巨大能量,借助传奇叙事让它们化身为民族文化心理的代言人。当然,地域文化中既存在着可以称颂的民族文化品格,也存在着不堪的民族劣根性。所有这些都无一例外地记录了一个国家风雨蹒跚的发展史,并承载了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传奇精神。
这种精神背后潜藏着一个民族幽深的文化寓言。“寻根文学”通过有意的“错位”和“失真”,来实现这种寓言性,并以此回应传奇传统。换言之,作家依靠对“根”的想象所虚构出来的世界,本身具有一种寓言和象征的色彩,指涉的便是现实世界之外的传奇。于是一个个带有地方情调和民族色彩的独特世界被营造出来,记载和传达了这些地方的风土人情及其背后承载的民族文化。在此基础上,作家们并不是在重现某种生活,而是借助一个个神奇怪诞的故事,在某个特定的地域中完成超越性的书写。从某种意义上说,传奇正是以隐喻和寓言性作为落脚点,试图新建一个世界,并以“传奇”的世界来折射某种“现实”的人生。“寻根文学”借传奇故事的荒诞来反思现实的荒谬,暗合了传奇的这一特征。
韩少功、郑义、王安忆、贾平凹等作家都善于用寓言的方式来建构神话世界。比如韩少功笔下的“鸡头寨”就有很多古怪的风俗和传说,作者不惜花费大量篇幅来描绘,使得整部小说都弥漫着一种巫楚文化的基调。鸡头寨就是一个寓言世界,这其中不仅有着夸张的情节、奇特的环境和古怪的人物,而且推动故事发展的也是作者尽力营造的不加节制的神秘感和荒诞性。鸡头寨中那些拜神祭祖、卜算卦象以及探求巫术的怪异行为自不必说,令人惊异的是,作者通过一个傻瓜丙崽的怪异行为,以及村民对丙崽态度的转变勾勒出一个关乎民族传奇的巨大寓言。它隐喻出一种与现代文明相悖的落后的生活样式,并折射出这种封闭空间的隔绝与愚昧。在这个象征的视域之内,作家意在思考中华民族的文化如何处理这种固有的隐疾之痛。除了韩少功的鸡头寨,王安忆的小鲍庄、贾平凹的古堡等等也都有着非常丰富的隐喻性,它们在一种几近停滞的空间中将传统和现代放在交错的时间轴上,用意会和含蓄的象征显现出一个虚无缥缈闪烁不定的民族文化世界。而莫言的“红高粱”,张承志的“大河”,阿城的《棋王》等文本,则通过寓言的方式表达出民族文化中一种遒劲的文化精神和辉煌的民族气度。
“寻根文学”充满寓言性的小说文本,表现出了一种对既定成规的质疑和反抗,这也因此与传奇传统遥相呼应。“传奇小说之叙事或发自达官贵人的消闲赏玩活动,或生于落魄文人的‘白日梦’。无论是‘征异话奇’式的群体兴趣表达,还是‘舒解块垒’般的个体情绪淘泻,均可视为某种灵魂拯救。”(11)李桂奎:《传奇小说与话本小说叙事比较》,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4页。从某种意义上说,“寻根文学”也承担着民族传奇精神的拯救之任,借此来建构属于本民族的文学形态和文化理念。在张承志、莫言、阿城等作家的文本中,我们都可以读出一种横亘在现实世界之上的传奇故事,现实世界越是不完满,文本中对传奇精神的挖掘就显得越深重。
比如在莫言的“红高粱”系列中,主人公们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伸张正义、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尽管这片土地上有无恶不作的匪徒、无所事事的乞丐和败坏家风的烟鬼,但就是这个集最美和最丑于一体的地方充斥着勃勃奋发的原始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折射出的不是主流意识形态中那种循规蹈矩的文化,而是不顾一切、义无反顾的原始野性之美。作者在这些鲜活的人物形象中融入了原始的生命力。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对某种一成不变的规范的质疑和反叛。在张承志的《北方的河》中,贯穿其中的北方河流如同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之“根”,它们在永不停息的流动中展现了原始的、强劲的和深沉的“传奇”精神。在郑万隆的《异乡异闻》中,穷山恶水反而磨炼了黑龙江边女真人的性情,他们自由奔放、不拘一格和野性四溢的性格中蕴含着民族文化的真性情。
三
鲁迅认为传奇文体的价值在于“文采和意想”,这也是传奇可以从子史叙事中挣脱出来的重要因素之一。于此基础上,“唐人传奇进一步扩大了野史杂记、志人志怪小说与正统史著的这个差异,从正统史著不屑一顾或无暇顾忌的地方开始了自己的事业……与正统史书相比,不仅是内容的转向,而且是内容的廓大”(12)董乃斌:《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72页。。值得肯定的是,“寻根文学”正是延伸了“文采和意象”的内涵。
文学作品在为教化和为娱乐之间始终存在着矛盾和张力,传奇一脉所体现出的“文采与意想”便是对文学自身想象力、抒情性的追求。换言之,如果将小说视为纯粹的审美活动,便能体会到传奇之于中国小说的意义。“寻根文学”以一种回溯传统的方式对当代文学和民族文化进行重新建构,在挖掘传统的同时也在书写新的传统,其中的一些文本实践打破了既定的文学书写模式,在彰显“文采和意想”时也将时代的复杂性充分显现出来。
由此也可以看出,“寻根文学”在传奇的不断演变中对其进行选择性的吸收,这也是它如此热衷于“新奇”“怪诞”“边缘”等内容的原因之一,但这背后潜藏的是两个核心因素——对现代性的焦虑和对民族文化传统(也即文化之“根”)的焦虑。也正是在此背景中,“寻根”作家对传奇传统的扬弃为当代文学的艺术探索提供了新的思路。
首先是书写现实世界时选择了讽喻(寓言)的方式。这种选择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追求有关。所谓现代性,按照马克思·韦伯的思路是指着重于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发展出的一套关于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理论,这个理论的出发点“在于所谓现代性的发展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从西方的启蒙主义以后、理性的发展、工具理性、工业革命到科技发展、甚至到民族国家的建立,到市场经济的发展,加上资本主义,这一系列的潮流似乎已遍及世界各地”(13)李欧梵:《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页。,但是,在现代性发展蔓延的同时,西方社会存在一条始终批判现代化的思想传统,或者说反抗现代性的传统,那便是对现代性所带来的严重危机和负面影响的清醒认识,反映在文学书写中便是讽喻(寓言)的表现形式的大量使用。现实在被寓言化的过程中呈现出碎裂和拼贴的形态。寻根作家在回溯传统时,也借鉴了西方现代文学的这种表现方式,韩少功、李杭育、郑万隆、贾平凹、郑义等都借助讽喻使其表现对象发生变形甚至颠倒和错乱。可以说,现实世界在讽喻性的描绘中既显现出传奇性,同时又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寻根”作家不断地追寻传奇故事背后的指向性,是因为体悟了讽喻性背后的价值和意义,从而使“征奇话异”的文学书写具备生命力。
其次,“寻根文学”虽然多描写“边地”景观,但这并不完全是“寻根”的题中之意,他们只是借助传奇笔法去触达传统。我们不妨借用本雅明的“拾垃圾者”对他们进行界定。“此时此地有这么个人,他在这个大都市收捡前一天的垃圾,任何被这个大城市扔掉、丢失,被它鄙弃,被它踩在脚下碾碎的东西,他都分门别类地收集起来,他审视着这些纵欲的历史见证,这些日积月累的挥霍。他对它们进行分类,作出精明的取舍,如此这般宛如一个守财奴看护着他的财宝,这些财宝将在工业女神大嘴的吞吐中成形为有用之物或令人欣喜的东西。”(14)[德]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王才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99页。于“寻根”作家而言,在被主流文化“淘汰”掉的“垃圾”中,很可能寻到文化之“根”。
在这个意义上,“寻根文学”在书写传奇故事的同时,着重强调其中的精神指向性,并借此希望在中国社会的现代性焦虑中找到中国文学的出路,呈现出一定的积极意义。一方面,就传奇本身而言,虽然叙述强调“作意好奇”,但其背后的精神蕴涵仍值得玩味。那些奇人奇事多是经过文化传统长期浸染过的特殊产物,同时也是可以对传统进行反省和批判的文化标本。虽然它们原本只是特殊时空中的奇异题材,但是经过小说家们“文采与意想”的渲染,则呈现为打上厚重历史印记的文化传奇。另一方面,新时期的中国经历了思想解放的潮流,在“西学热”的冲击下,面对“现代”的冲击和“传统”的失落,产生了一种现代性的焦虑。中国社会的经济转型和对现代的追寻的确让人们的价值理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不加辨析地追求现代,盲目地崇拜工具理性也会产生各种社会问题。“寻根文学”正是在此语境中,尝试汲取传奇的精神内核,激活传统资源,来摆脱中国文学的某种现代性困境。
虽然“寻根文学”对传奇传统的择取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但其创作中为传奇而传奇的倾向也会导致精神探索无法真正深入。唐传奇的确是“大胆地将目光投向史乘不屑一顾的市井闺阁、村野山林、寺观道院、旅邸旗亭,以一班无望厕身史册的落魄举子、倡优女妓、商贾渔樵和僧道者流人物为自己作品的主角,将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乃至诸般琐碎猥杂的‘小小情事’,写得‘凄艳欲绝’、‘撰述浓至’”(15)董乃斌:《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72页。。“寻根文学”在书写对象的选择上也极力突破了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原则的成规,他们一开始就将关注点放在“非规范”的传奇之物上,这样的选择意味着“寻根文学”在一定意义上是回避正统或主流文化的。这些文本对传奇故事的呈现由于太过刻意,反倒更像是悬浮着的空中楼阁。也正因为此,一些寻根文本没能在传奇的脉络下真正融入文化传统的挖掘中。
与之相关的是,“征异猎奇”并非传奇文体的核心所在,换言之,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并不仅仅局限于为读者讲述一个传奇的故事,而是蕴含在文本中的精神寄寓。唐传奇的作者“不愿意像志怪小说那样,把自己的任务确定为只是‘传录舛讹’,也就是以写实的态度记录传闻,而是把笔触开始转向现实,写现实的人,写现实人的独特命运和情感,或者干脆就写自己的故事,展示自己的情感世界”(16)蔡铁鹰:《中国古代小说的演变与形态》,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100页。。但是由于这些作者相对单一的文化身份,客观上导致了唐传奇所能反映的社会生活十分有限。而且,这些作者比较专注于离奇新异的故事,无意于具有更宽泛的精神指向的题材,这种局限也使唐传奇的题材范围相对狭小。“寻根文学”中的部分文本在某种程度上也陷入了同样的窠臼,由于执着于对边远地区的“奇风异俗”的刻意探寻和无节制的开采,却缺乏精神升华的空间,反而在无形之中限制了小说精神深度的开掘。
尽管如此,“寻根文学”为当代文学重新认识传统,重新处理文学与传统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文本实践。在新时期中国文学求新求变的过程中,在中国文学融入“世界文学”的格局中,一种新的文化样式的诞生与对传统的继承和扬弃息息相关,对传统的择取和拓新同时也是对传统内在精神的置换和重构。只有这样才能“使代与代之间,一个历史阶段与另一个历史阶段之间保持了某种连续性和同一性,构成了一个社会创造与再创造自己的文化密码”(17)希尔斯:《论传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页。。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寻根文学”对传奇传统这种有选择、有目标的文学实践充满着文体自觉和逻辑思辨,成为当代文学汲取古典小说叙事资源的有益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