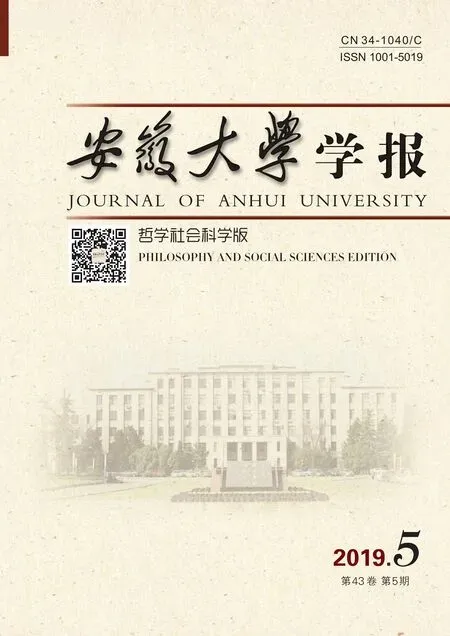传统诗学视野中的白居易感伤诗
叶跃武
白居易的诗学观念对后世影响深远,但论者多集中于白氏讽谕诗学的探讨。其实白居易对感伤诗的类分、阐释和价值判断,同样蕴含着复杂而深刻的诗学思想。白氏于元和十年(815)自编其诗时,把作品分成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和杂律诗四类,前三者为古体,后者为近体。元稹在长庆四年(824)循此体例再编白诗。但此后白氏感伤诗的写作便趋于衰微。白氏在写于元和十年的《与元九书》中论及以上诗歌分类的依据,同时对感伤诗作出“时之所重,仆之所轻”(1)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795页。的价值评判,并表现后人再编其诗时,可将此类诗删去。这种看似一己偏好使然的写作选择和价值观念,其实正根源于深刻的思想和诗学传统。现有研究往往是在综合探讨白诗四分类的时候,或多或少地谈及感伤诗成立的依据(2)例如陈寅恪《论元白诗之分类》(《岭南大学学报》第10卷第1期,1949年12月,又收入其《元白诗笺证稿》)、王运熙《白居易诗歌的分类与传播》(《铁道师院学报》1998年第6期)、钱志熙《元白诗体理论探析》(《中国文化研究》2003年春之卷)等等。,但并没有与“诗缘情”等诗学传统结合起来。学界也尚未充分揭示出白居易的感伤诗学所蕴含的诗学史意义。本文认为,作为诗类,感伤诗成立的依据在于屈骚以来的写作传统、诗缘情的诗学观念以及中国古典人性论。白居易又从诗教观与性情之辨的角度,做出轻视感伤之情和感伤诗的价值判断。白诗作为体现唐宋诗歌转型的典型之一,他对感伤诗的认识和态度,有助于理解“宋人的诗扬弃悲哀”的问题。
一、感伤诗的内涵与诗学渊源
(一)感伤诗的基本内涵
《白氏文集》中有“感伤诗”四卷。由于元稹编排《白氏长庆集》时的综合考虑,感伤诗卷三实际上包括白居易写于离开江州之后至赴任杭州刺史之前的所有五言古诗,换言之,也自然包括该时期的闲适诗,以及可能有的讽谕诗(3)参考拙文《白居易早期古体诗分卷问题——以“闲适诗”为中心》,《新国学》第十四卷,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年。。所以这里在分析感伤诗的基本内涵时,以白居易《与元九书》中对感伤诗的界定为准,同时参考感伤诗卷。
白居易《与元九书》从“感物起情”的角度,阐释感伤诗的基本内涵:“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一百首,谓之感伤诗。”(4)《白居易集笺校》,第2794页。“情理”是理解该句的关键点之一。它不是“情”与“理”的合称,而是偏指“情”,是“情绪、思虑”之义。白居易在《祭微之文》中也有类似用法:“《诗》云‘淑人君子,胡不万年’,又云‘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此古人哀惜贤良之恳辞也。若情理愤痛过于斯者,则号呼壹郁之不暇,又安可胜言哉。”(5)《白居易集笺校》,第2794页。被“愤痛”修饰的“情理”当指“情感”无疑。唐代其他著作中亦可见此类用法,如《礼记·乐记》有“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之句,孔颖达《礼记正义》疏:“反情,谓反去淫弱之情理,以调和其善志也。”(6)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329页。即以“情理”释“情”。这不仅在语义统计学上能得到确证(7)如《汉语大词典》“情理”条只有两个义项:一是“人情与道理”,此项显然不合文义;二是“情绪;思虑”,此项为是(2.0版光盘,商务印书馆(香港)编辑制作,2002年)。,从该词语的文化语境也能得到检验:之所以有“情理动于内”,是因为“有事物牵于外”,即内在之情理是由外在之事物引起的,这其实就是渊源久远的“感物起情”说,即《礼记·乐记》所言:“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8)《礼记正义》,第3310页。;又说“情动于中,故形于声”(9)《礼记正义》,第3311页。,这种“动于中”的情,也就是“感于物而动”。白居易自己诗文中就多次提及这种观念,例如《寄李十一建》:“外事牵我形,外物诱我情。”(10)《白居易集笺校》,第291页。《孟夏思渭村旧居寄舍弟》:“时物感人情,忆我故乡曲。”(11)《白居易集笺校》,第560页。
白居易对感伤诗的阐释,并不是对传统感物生情之创作发生论的简单重复,它其实还蕴含着白氏对感伤诗独特内涵的概括,即情感体验的感伤性。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这里有必要参考白居易对讽谕诗和闲适诗的定义。从《与元九书》对讽谕诗和闲适诗的论述中,能看到诗人对二者之独特性的交代:
自拾遗来,凡所遇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谕诗;又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12)《白居易集笺校》,第2794页。
无论是“所遇所感”,还是“吟玩情性”,都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是白居易一贯的诗学主张。但讽谕诗的情感是有关“美刺兴比”,是基于社会关怀所具有的情感。闲适诗的情感则是“知足保和”,是基于佛道思想而具有形而上意味的情感。所以白诗对感伤诗的阐释,虽然没有直接指出情感的类型,但其有所专指则是可以肯定的。其实,在对感伤诗的界定中,“有事物牵于外”的“牵”字已指明所起之情感的非愉悦性。“感伤诗”的“感伤”一词更直接道破。这也可以从白氏自己的作品得到印证。从对感伤诗的阅读,很容易生成这样一个印象:感伤诗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其情感体验的消极性。这种情感包括哀亡叹逝、饥寒衰病、亲友离别、身处异乡、仕途不遇等等之感伤,如《将之饶州江浦夜泊》《秋暮西归途中书情》写“忆归复愁归,归无一囊钱”(13)《白居易集笺校》,第499页。的贫苦与漂泊之情,《曲江感秋》《登村东古冢》是悲秋叹逝之作,《晓别》《秋将送客》表现别离的愁苦伤悲,《念金銮子》《哭李三》则悼女哭友,《琵琶行》《初入峡有感》写身世不遇之感。它们多是白居易个人日常生活的感伤之情,其中以“歌行曲引”为题者虽不一定反映诗人自身的经历及其感受,但也多写人间日常愁苦之事,如《长恨歌》《生离别》等题目所示。
由此可见,白居易是从情——而且是感伤之情——的角度理解感伤诗,并基于此将之独立成类。
(二)骚怨传统与感伤诗
如果说,上述《与元九书》中对感伤诗的阐释,是从诗学评论的层面切入,那么,《序洛诗》中的相关论述,则可以视为从诗歌史的角度对感伤诗进行溯源:
予历览古今歌诗,自风骚之后,苏李以还,次及鲍谢徒,迄于李杜辈,其间词人闻知者累百,诗章流传者钜万。观其所自,多因谗冤遣逐,征戍行旅,冻馁病老,存殁别离,情发于中,文形于外。故愤忧怨伤之作,通计今古,什八九焉。世所谓文士多数奇,诗人尤命薄,于斯见矣。又有以知理安之世少,离乱之时多,亦明矣。(14)《白居易集笺校》,第3757页。
这段论述是从“闲适诗”对立面的角度进行梳理,意在突出闲适诗之难得。但它对理解白居易观念中的感伤诗传统,极有帮助。引文中提及的“谗冤遣逐,征戍行旅,冻馁病老,存殁别离”等场景,跟白居易感伤诗的创作背景相近,白居易少小漂泊,挨饿受冻,身体病弱,遭遇贬谪,这从前文感伤诗的举例中即可看出。先秦之风骚、两汉之苏李,以至南朝之鲍谢和唐代之李杜,各是其所在时代最伟大的诗人,他们诗中多“愤忧怨伤之作”,正说明感伤诗传统的渊源久远,以及其在汉语诗史中的主流地位。屈原之伤时,宋玉之悲秋即开启这一传统,例如李白即言:“哀怨起骚人。”(15)《古风·其一》,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87页。元稹亦云:“骚人作而怨愤之态繁。”(16)《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元稹集》卷五十六,第690页。故此,这一传统亦称为骚怨传统。两汉也存在以悲为美的风尚。感伤之作在重视真情的六朝文论家那里,甚至被视为诗之正宗。萧绎将文学定义为吟咏哀思:“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17)萧绎:《金楼子·立言》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75页。(须知《礼记·乐记》中即言:“亡国之音哀以思。”(18)《礼记正义》,第3311页。)王微也称:“文词不怨思抑扬,则流澹无味。”(19)沈约:《宋书》卷六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667页。钟嵘在《诗品序》中罗列诗歌创作发生之场景时,绝大多数是引起伤怨之情的遭遇,例如:“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20)曹旭集注:《诗品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56页。这是那个时代的文学主张,以致出现江淹《别赋》《恨赋》这种专咏感伤的抒情篇章。由此可见感伤诗流脉的强大。
(三)诗缘情与感伤诗
那么感伤诗的合理性在哪?作为个人之情的书写,它没有像讽谕诗那样有儒家思想的论证,也没有像闲适诗那样有佛道思想的加持。其合理性就在于它是人性使然:
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21)《礼记正义》,第3327页。(《礼记·乐记》)
心术,指喜怒哀乐等情感。《乐记》认为情感的产生是受外在事物之触动。《诗大序》也说:
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22)郑玄注,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第567页。
虽然强调诗歌要“止乎礼义”,但它也在确认“发乎情,民之性也”。这种思想的意义在于,它证明情感存在的正当性,即它是一种人生而然的感受,是基于人之“血气心知”。当人心中有情感之激荡时,就必须要发泄出来。例如《乐记》中对音乐发生的表达:“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23)《礼记正义》,第3311页。《诗大序》也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24)《毛诗正义》,第563页。韩愈的“物不得其平则鸣”(25)韩愈:《送孟东野序》,岳珍、刘真笺注:《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982页。,也是一种常理上的论证。这其实是汉代以来很明确的创作思想。司马迁在解释《离骚》的写作时,也使用这一思想:“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26)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482页。“人穷则反本”,如呼天地,喊父母,都是出于人之本能,自然不过。屈原写作《离骚》,也是受冤穷困时一种本能的表达,这就是“自怨生”之意,就像呼天一样自然而然地发出。班固说乐府歌谣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何休注《公羊传·宣公十五年》曰:“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27)何休注,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十三经注疏》,第4965页。,亦是此意,都是在人性自然这个层面提出。
在此种诗学传统中,陆机提出“诗缘情”,并且没有用“止于礼义”予以规定,便不足为奇。陆机在诗文中多次使用“缘情”一语,其语境都是指哀伤的一己之情。例如《思归赋》:“彼离思之在人,恒戚戚而无欢。悲缘情以自诱,忧触物而生端。”(28)陆机著,刘运好校注:《陆士衡文集校注》,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146页。这是怀归之悲伤。又如《叹逝赋》:“顾旧要于遗存,得十一于千百。乐心其如忘,哀缘情而来宅。”(29)《陆士衡文集校注》,第189页。这也是因旧友多亡而兴感。但陆机都没有用礼义予以规范。这便是对《诗大序》“诗言志”说的突破。因为陆机此说影响颇大,故此种诗学传统也可称为“诗缘情”传统。
钟嵘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行诸舞咏。”然后罗列各种激发诗歌写作的场景,最后说:“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30)曹旭集注:《诗品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56页。诗歌可以起到发泄内心压抑之功效,从而“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正是人之难以抑制的心灵感荡,以及表达出来后,能让人内心获得安顿的功效,使得感伤诗的创作获得天然正当性,尤其是在“吟咏情性”的诗学文化传统中,更是如此。换言之,诗歌之写作,是人性之有情使然,又是人性安顿之需要。这也便是“诗缘情”传统的合理性所在。
综言之,结合理论上和诗作上的解读,可见白居易是从“情”的层面来把握感伤诗,并认为“情”是由具体事物刺激于人而引发的心理体验。这种情的内涵偏于个人日常生活的感伤,它区别于讽谕诗所彰显的社会情怀和闲适诗所体现的闲乐。白居易感伤诗写作,其合理性是基于哲学层面的人性论、诗论层面的缘情说,以及诗歌史层面的感伤诗创作传统。其中,哲学层面的人性论,也是“诗缘情”说之合理性及其被广为接受的原因所在。
二、诗教观视野下的感伤诗
既然白居易是从“感伤之情”的层面理解感伤诗,那他对“感伤之情”的态度,自然也就影响他对感伤诗的价值判断。白氏诗文中蕴含着浓烈的贬情思想,这与一般印象中白氏重情相去甚远。这种贬情思想主要包括诗教观和性情之辨两种观念。
诗教观源于对《诗经》的接受。《诗三百》在儒家思想中被尊为“经”,也被后世视为诗歌写作的典范。《诗经》中的“大雅”“颂”类诗歌以颂美为主,为此生成雅颂传统;其“小雅”“国风”类诗歌则多有怨刺之作,这些在《诗大序》中被称为变风变雅,对后世影响也极为深远。这两种传统合而言之就是美刺。美是颂美,刺是怨刺。孔颖达《礼记正义》在疏解《经解》时说:“以诗辞美刺讽谕以教人,是诗教也。”(31)《礼记正义》,第3493页。白居易最为看重的讽谕诗类,便包括颂美和怨刺两大内容。这两种传统中无论哪一种,都否定感伤之情。首先来看雅颂传统。前文所引《序洛诗》中白居易对骚怨传统的论述中,其实已经蕴含着另一个视角——对感伤诗的批判,这即是基于儒家诗教观的立场。引文最后两句认为感伤诗反映出两种形象:一是个人层面的“命薄”;二是社会层面的“世乱”。个人之命薄其实也指向“理安之世少,离乱之时多”。这些评价都是负面的。白居易把“愤忧怨伤之作”与“世之离乱”关联起来,其实是从雅颂传统出发对感伤之情的批判。被奉为圣典的《礼记》,其《乐记》篇即言:“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32)《礼记正义》,第3311页。《诗大序》引用这段话,并据此解释《诗经》中的伤怨之作:“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33)《毛诗正义》,第566页。隋唐时期将哀怨之作视为王道衰、诗教坠的思潮,即肇始于此。隋代王通已有“变风变雅作则王泽竭矣”(34)王通撰,阮逸注释:《文中子》卷三,上海:扫叶山房,1926年,第37页。之论。张九龄作为盛唐著名宰相,也说:“《诗》有怨刺之作,《骚》有愁思之文,求之微言,匪云大雅。”(35)张九龄:《陪王司马宴王少府东阁序》,见熊飞校注《张九龄集校注》卷十七,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875页。风骚被排斥在大雅之外,由此可见雅颂正声之权威地位。李白的言论可作为佐证:“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36)李白撰,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87页。楚骚被认为是大雅正声衰落之后的作品。古文家之批判更为激烈,如盛唐李华云:“屈平、宋玉,哀而伤,靡而不返,六经之道遁矣。”(37)李华:《赠礼部尚书清河·公崔沔集序》,见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三百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196页。柳冕也明确指出:“《大雅》作则王道盛矣,《小雅》作则王道缺矣,《雅》变《风》则王道衰”(38)柳冕:《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见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五百二十七,第5354页。;“骚人起而淫丽兴”(39)柳冕:《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见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五百二十七,第5357页。。可见,基于儒家思想以及《诗大序》以大雅为正声的诗教观是唐代处于意识形态地位的诗学思想。从白居易在《序洛诗》中对闲适诗性质的阐释可以看出,他深受这种观念的影响。白氏在解释闲适诗的内涵后,写道:
予尝云:“理世之音安以乐,闲居之诗泰以适。”苟非理世,安得闲居?故集洛诗,别为序引。不独记东都履道里有闲居泰适之叟,亦欲知皇唐太和岁有理世安乐之音,集而序之,以俟夫采诗者。(《序洛诗》)(40)《白居易集笺校》,第3758页。
这便是从大雅正声的角度,指出闲适诗的价值。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论诗推崇“六义”,如今却将“六义”阙如的、表现独善的闲适诗,也往诗教的框架里硬套。这正说明诗教观的影响之大。
白居易论诗,既有大雅正声的视角,但有时也采用变风变雅的立场。后者体现于《与元九书》中对屈骚诗歌的评价:
《国风》变为骚辞,五言始于苏、李。诗、骚皆不遇者,各系其志,发而为文。故河梁之句,止于伤别;泽畔之吟,归于怨思。彷徨抑郁,不暇及他耳。然去《诗》未远,梗概尚存。故兴离别则引双凫一雁为喻,讽君子小人则引香草恶鸟为比。虽义类不具,犹得风人之什二三焉。(41)《白居易集笺校》,第2790~2791页。
这是从风雅“六义”的视角评论屈骚,一方面批评其“止于伤别”和“归于怨思”,另一方面却肯定其兴寄精神。这显然有别于雅颂正声的视角。但白居易那些关乎一己之经历的感伤诗,既缺少楚骚和汉古诗那样的兴寄精神,也没有类似雅颂之安乐情调。所以如果置于宏观的诗论史视野,其被批判的处境便可想而知。白居易从诗教观的角度批判感伤诗,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基于讽谕诗理念对感伤诗的观照。
三、性情之辨观念中的感伤诗
从政教层面批判感伤诗,这是白氏以前就存在的诗学传统,它甚至是唐代诗学的主流,所以白氏取用之,并不奇怪。但此外还有另一种思想史资源成为白居易批判感伤诗的立足点,这便是“性情之辨”。性情之辨是中国古代哲学史的核心论题之一,它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情与性的二元区分,这是“事实”上的判断;另一层是价值上的判断,即它们在价值上的正负性。儒释道发展至中唐都具有明确的性情之辨观念。白居易对儒释道三家兼容并蓄,这一点前人已有充分论述。他具有性情之辨观念,这不仅能从其知识结构中找到线索,还可以从其作品中得到印证。下面即从儒释道这三个思想谱系来揭示白居易情性之辨观念的可能来源,并结合其作品进行解读。
儒家一系有从西汉董仲舒等汉儒杂阴阳以论性仁情贪,至中唐李翱援佛理以言性明情昏。董仲舒基于阴阳的观念,整合孟子性善说和荀子性恶说,提出性、情二元对立和性善情恶的思想:“天之大经,一阴一阳;人之大经,一情一性。性生于阳,情生于阴。阴气鄙,阳气仁。曰性善者,是见其阳也;谓性恶者,是见其阴者也。”(42)董仲舒撰,苏舆义证,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卷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84页。此观念被写进东汉具有官方意识形态色彩的《白虎通义》,对后来思想史影响深远。后世学者在从人性论层面解释社会上的善恶时,往往重复着这种观念。白居易在《策林·五十四:刑礼道》中认为“礼者可以防人之情……道者可以率人之性”(43)《白居易集笺校》,第3525页。,一防一率,正透显其情恶性善的观念。如果说董仲舒是从宇宙论层面解释性情之辨,那么李翱则是从心性论层面进行阐述。儒家思想在中唐进入心性论转向,其标志之一就是李翱引佛入儒的《复性论》。李翱是白居易的朋友。白居易贞元二十年(804)在李翱家住过,说明他跟李翱不止一面之交。《复性书》是在贞元十六年(800)前后写成的,所以白居易在写《与元九书》之前也极可能知道。《复性书》中说:“人之所以为圣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皆情之所为也。情既昏,性斯匿矣,非性之过也,七者循环而交来,故性不能充也。”(44)李翱:《复性书·上》,见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六百三十七,第6433页。这其实也是白居易情性之辨观念的背景。
道家一系则有从庄子保真性而摒哀乐,到嵇康重修性而轻爱憎,再到唐代道家(道教)的全性灭情。《庄子》之人生态度被白居易奉作圭臬,这从其闲适诗即可看出。庄子云:“悲乐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过;好恶者,德之失。”(45)庄子撰,郭庆藩集释:《庄子集释·刻意篇》,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542页。他在这里对人之成见所引起的“情”予以否定,认为理想的人生境界就是“人而无情”(46)庄子撰,郭庆藩集释:《庄子集释·德符充》,第320页。,这样才能守护住人分殊自天地大道的真性。他谴责“损性”“伤性”“失性”的行径,而追求“全性”“保真”的人生。于此可见庄子尊性贬情的观念。这种性情之辨的观念,被嵇康和道教从保性与养生的角度进一步发挥和实践。嵇康对白居易的影响同样巨大,白氏诗中即大量言及嵇康。嵇康在其《养生论》中说:“修性以得神,安心以全身,爱憎不栖于情,忧喜不留于意,泊然无感,而体气平和。”(47)嵇康撰,戴明扬校注:《嵇康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146页。这里主张修性安心,而对爱憎忧喜等情感则避而远之。道教在唐代一度上升为国教,包括白居易在内的唐代众多文人不仅与道士亲密交往,而且还亲自炼丹服药。道教以长生为目标,有“性命双修”之论,例如吴筠便宣称:“生我者道也,灭我者情也。”(48)吴筠:《玄纲论》,见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九百二十六,第9656页。性与情处于互不兼容的对立态势,而保性则是养生之基础:“情亡则性全,性全则形全,形全则气全,气全则神全,神全则道全,道全则神王,神王则气灵,气灵则神超,神超则性彻,性彻则反复通流,与道为一。”(49)吴筠:《玄纲论》,见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九百二十六,第9656页。保性与养生通过形、气、神等而圆融贯通。但由此也可见,道教在一定程度上还吸取传统医学的气论,从情与气之关系解释养生问题。《黄帝内经·素问·举痛论》便写道:“余知百病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50)郭霭春主编:《黄帝内经素问校注》,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2年,第510页。情影响气从而影响健康。这从白居易自己的诗作中即可看出:
自知气发每因情,情在何由气得平。若问病根深与浅,此身应与病齐生。(51)《病气》,《白居易集笺校》,第847页。
正如“此身应与病齐生”所言,白居易是一体弱多病之身。他把生病归因于体内之气的失衡,进而又认为这种失衡的制造者之一就是情。白居易有时也越过“气”这一环节,更为直接地表达“情”与“病”的关系,如“早衰因病病因愁”(52)《自问》,《白居易集笺校》,第1267页。,就把病与感伤之情(“愁”)之间的关联更明确地表达出来。“年少已多病”,并常常担忧“此身岂堪老”(《病中作》(53)《自问》, 《白居易集笺校》,第770页。,诗下原注:“时年十八”)的白居易,岂能不对伤身害命的“情”避而远之?但道家和道教对白居易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养生层面,白居易同样重视保性灭情而得到心灵的清静、平和与自由,这从其表现“知足保和”的闲适诗可以看出。
佛教的性情之辨可以说是性净情染和性觉情迷论,对“情”的否定是其基本教义。作为情欲的贪、嗔、痴,就被视为三毒。与白居易同时的华严宗五祖宗密在阐释牛头宗的宗旨“本无事而忘情”时说:“言本无事者,是所悟理,谓心、境本空,非今始寂;迷之谓有,所以生憎、爱等情;情生诸苦所系,梦作梦受。故了达本来无等,即须丧己忘情;情忘即度苦厄,故以忘情为修行也。”(54)宗密:《圆觉经大疏钞》卷三之下,《新纂续藏经》第十四册,第534页下栏。白居易是唐代习佛极为深入的士人,他在《赠僧五首·自远禅师》题下自注:“远以无事为佛事。”(55)《白居易集笺校》,第1924页。白氏诗中多处将自己视为“无事人”(《玩新庭树,因咏所怀》),又说自己“心与无事期”(《夏日独直,寄萧侍御》)(56)《白居易集笺校》,第284页。。佛教这种否定情的观念对白居易深远影响,他后来便追求“置心世事外,无喜亦无忧”(《适意二首·其一》)(57)《白居易集笺校》,第317页。的生活,甚至把禅的真谛概括为“忧喜心忘便是禅”(58)《白居易集笺校》,第1011页。!这是追求心灵的平和与自由,此层面与道家之追求相似。
由此已能清晰看出,情,尤其是感伤之情,受到来自各个层面的攻击:儒家的性善情恶论,道家的性真情伪,道教的性真情邪论,佛教的性净情染论等等。这些观念在白居易的思想中融为他自己的情性之辨。
性情之辨作为一种价值判断,它同时也是人生修养之依据:既然性利情弊,那么人生之方向就是舍情取性。白居易在此种观念的指导下,逐步把感伤之情从生活中清除出去,如“以道治心气,终岁得晏然”(59)《夜雨有念》, 《白居易集笺校》,第540页。,“所以达人心,外物不能累”(60)《感时》, 《白居易集笺校》,第270页。,又如“外顺世间法,内脱区中缘。秋不苦长夜,春不惜流年”(61)《赠杓直》, 《白居易集笺校》,第352页。。白居易闲适诗中记录着大量“知足”“齐物”“委命”等自我安顿的例子。随着其适性生活的张扬,记录感伤之情的感伤诗也就自然而然地衰歇:
自三年(引注:大和三年,即公元829年)春至八年夏,在洛凡五周岁,作诗四百三十二首,除丧明哭子十数篇外,其他皆寄怀于酒,或取意于琴,闲适有余,酣乐不暇,苦词无一字,忧叹无一声,岂牵强所能致耶,盖亦发中而形外耳。(《序洛诗》)
闲适有余而忧叹无一,可见这个时期感伤诗的写作,已经衰微。此后更是如此。其实白氏感伤诗数量的剧减,是开始于长庆元年(821),其原因与生活境况改善有关,因为此前一年,他正结束长达六年(815—820)的贬谪生涯,回到朝廷任职。但更关键的原因,还是在于常年来心性修养所带来的精神觉解能力,因为诗人于贞元十八年(803)至元和六年(811)也在长安任职,但却写下为数不少的感伤诗。“苦词无一字,忧叹无一声”便是咏写适性生活的闲适诗。这便说明“性情之辨”的观念对白居易人生,进而对白居易诗歌的影响之大。“丧明哭子”等诗不能免去,诚如柳冕所言:“骨肉之恩,斯须忘之,斯为乱矣;朋友之情,斯须忘之,斯为薄矣。”(62)柳冕:《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见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五百二十七,第5357页。白居易后期也有悲悼好友如令狐楚、刘禹锡的诗作。这也正是白氏兼容儒释道之体现。
白居易对性与情的或重或轻,可以用他自己的诗句来概括:“雅哉君子文,咏性不咏情。”(63)《祇役骆口驿喜萧侍御书至兼睹新诗吟讽通宵因寄八韵》,《白居易集笺校》,第502页。虽然这是白居易用以赞美其友人的诗句,但也可以看作是诗人基于自己识见的诗歌见解。白居易的闲适诗也可称为“咏性诗”,因为这些诗所表现的,便是其适性、遂性、任性的生活体验(64)例如《登天宫阁》:“委形群动里,任性一生间。”(《白居易集笺校》,第1957页)《春日闲居三首》:“鱼鸟人则殊,同归于遂性。”( 《白居易集笺校》,第2465页)《春池闲泛》:“飞沉皆适性……鱼跳何事乐,鸥起复谁惊。”( 《白居易集笺校》,第2499页)。。因此,道释视野下的性情之辨,某种程度上也是闲适诗和感伤诗的价值之辨。白氏重闲适诗而轻感伤诗,根源之一即在于此。
四、关于“宋人的诗扬弃悲哀”的问题
白居易贬抑感伤之情以及感伤诗,这看似白氏个人的偏好。但如果将之放置在更大的思想史和诗学史视野中,便可发现,它是某种文化兴起后的伴随现象。如果放在中唐至北宋的视野中,这“某种文化”便是基于儒家思想的诗教观与基于心性论文化的性情之辨。
由于《礼记·乐记》《诗大序》在传统文化中的经典地位,诗教观是一种渊源久远的诗学思想,历代学者都清楚意识到它,南北朝如此,唐代如此,宋代亦如此。宋代诗教观既有以大雅正声批评骚怨,例如北宋杨亿说:“若乃《国风》之作,骚人之辞,风刺之所生,忧思之所积,犹防决川泄流,荡而忘返;弦急柱促,掩抑而不平。今观聂君之诗,恬愉优柔,无有怨谤,吟咏情性,宣导王泽。其所谓越《风》《骚》而追二《雅》。”(65)《温州聂从事云堂集序》,见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二九四,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376~377页。也有接受白居易讽谕精神的影响,肯定骚怨中的兴寄美刺精神,例如梅尧臣说:“圣人于诗言,曾不专其中,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自下而磨上,是之谓国风。雅章及颂篇,刺美亦道同。不独识鸟兽,而为文字工。屈原作离骚,自哀其志穷。愤世嫉邪意,寄在草木虫。”(66)梅尧臣:《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汝见赠述诗》,见朱东润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336页。梅尧臣对屈骚自哀的肯定是建立在“愤世嫉邪意”,如果离开此点,自哀便会受到否定。欧阳修与梅尧臣同为提倡诗学的政治功能,当他单就屈骚之自哀而论时,便说:“可笑灵均楚泽畔,《离骚》憔悴愁独醒。”(67)欧阳修:《啼鸟》,见刘德清、顾宝林、欧阳明亮笺注:《欧阳修诗编年笺注》卷七,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789页。可见,对骚怨无论或贬或褒,其出发点都是教化或讽刺的功利诗学,同时也摒弃日常生活中没有兴寄意味的悲哀感伤之情。
相比较而言,性情之辨虽然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同样可以追溯到先秦,但直至唐代,其在诗学话语上的体现还极其有限。东晋玄言诗中有“除情累”之论,如许询《农里诗》云:“亹亹玄思得,濯濯情累除。”(68)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94页。又如陶渊明《形影神·神释》中说:“正宜委运去,纵化大浪中,不喜亦不惧。”(69)陶渊明撰,袁行霈笺注:《陶渊明集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47页。都是通过玄思或理性来解除“情”对人生的困扰。但这一方面很难说是基于性情之辨观念的自觉思考,另一方面也没有在诗学上形成强势话语。这与哲学演变进程中心性论及性情之辨的地位有关。孔子不谈性与天命,老子重在论天道与无为,庄、孟虽有心性之论,但并未为当时人所重。汉代重宇宙论,魏晋重本体论,直至东晋后,佛教汉化过程中以其自身心性论之长,融合中国传统人性论,从而做出深入而精致之阐发,使得世人知心性论之微妙,最终才反过来推动儒、道对心性论的探索。可以说,时至中唐,“情性之辨”已不止是一种观点,而且是一种思维模式。这表现在儒释道思想学说都在使用它,而且是在不同的含义上使用(见前文)。这种心性论文化正契合唐代士大夫安顿人生的精神需要。柳宗元在批评韩愈辟佛的行为时,说道:“退之所罪者其迹也……退之忿其外而遗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韫玉也。”(70)柳宗元:《送僧浩初序》,见《柳宗元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674页。柳氏指出佛教在心性修养上的优越性。中唐士大夫间少有不受佛教影响,就连想从心性理论上驳斥佛教的李翱,也是使用佛教心性论的资源。白居易早年也谈到僧人凝公教给他“心要”(《八渐偈并序》)。这都说明心性论是文人士大夫接受佛教的主要层面之一。白居易说“释教治其心”(71)《醉吟先生墓志铭并序》,《白居易集笺校》,第3815页。,更是一语道明。这些都在指向一种或隐或显的社会意识:中唐文人士大夫已多从心性层面理解人生。他们接受心性论是在寻求人生内在超越的精神资源,而性情之辨是心性论的进路之一,因为它在回答人何以能超越的依据和途径:依据在于人之性,途径在于去情复性。这是白居易性情之辨观念的时代思潮背景,其“咏性不咏情”之说即是该观念的诗学表述。虽然当时人应者寥寥,但却是性情之辨观念深刻影响诗学的范例和先兆。
宋代儒学继承中唐韩愈、李翱推动的儒学心性论转向,兼综道释,并将之与形而上之道德本体关联起来。王安石从体用论角度解说性情之辨,张载引入“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视野,程颐更将性情之辨推向理欲之辨,从而有存天理灭人欲之论。此种思潮深刻影响宋代文化(72)参考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也影响宋代的诗学。性情之辨观念极强的宋人,不失儒家之社会责任的担当精神,同时也追求体道自适的人生态度。二者其实是统一于具有道德色彩的心性(理学家认为此种心性分殊自形而上道德本体)。此心性对社会之显用即是兼济天下,对自身之显发即是体道自适。前者的表现就是“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73)欧阳修:《镇阳读书》,见《欧阳修诗编年笺注》卷七,第739页。,前论诗教观即是其诗学话语。后者的体道自适则以穷处之际的豁达为典型。被视为宋代士大夫文化开启者的范仲淹即强调:“未大用间亦处处有仁义。”(74)范仲淹:《与韩魏公书》,见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三八三,第715页。作为仁宗朝后期文坛领袖的欧阳修,也有类似的主张。他在景祐党争中遭贬,到谪所后至书友人:“路中来,颇有人以罪出不测见吊者,此皆不知修心也。”并勉励被贬的同党“慎勿作戚戚之文”(75)欧阳修:《与尹师鲁书》,见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居士外集》卷十九,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998页。。范仲淹与欧阳修都是宋人极为仰慕者。作为宋诗中的代表,苏轼更是以其旷达形象闻名于世。旷达即是对恶劣环境及一己悲愁的超脱。对士大夫而言,贬谪往往就是人生中最大的打击之一。宋人在此之际尚且豁达,于日常生活便不太可能沉溺于悲愁感伤。这表现在诗文写作上,就是“意气未宜轻感慨,文章尤忌数悲哀”(76)王安石:《李璋下第》,见《王安石全集》卷二二,上海:上海大东书局,1936年,第139页。。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更概括道:“宋人的诗扬弃悲哀。”(77)[日]吉川幸次郎撰:《宋元明诗概说》,李庆、骆玉明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3页。其反映在宋代诗学中,便是看重体现于诗作中的格韵。宋代对“格韵”的追求即是对一己之悲戚的否定。晚唐诗歌正以其悲哀与艳情而被宋人批判为体格卑弱。其表现在诗歌典范的选择上就是对襟怀高妙的陶渊明诗歌的无上推崇。
综上而论,白居易的感伤诗写作,是基于屈骚以来的写作传统、诗缘情的诗学观念以及中国古典人性论。但唐代诗教观对屈骚以来哀情传统的批判,儒释道性情之辨观念中对感伤之情的贬低,都深刻影响追求兼济和独善之人格形象的白居易,使他做出轻视感伤诗的价值判断。随着人生境遇的改善和修身养性的追求,白居易感伤诗创作的衰微也就不言而喻。诗教观和性情之辨观念也深植于宋代文化,宋诗扬弃悲哀的现象可以从中找到原因。这同时也是性情之辨这一思想观念深刻影响文人生活和文学的例子。可以说,白居易作为一大诗人,活动于“百代之中”的中唐,其对感伤诗的写作、分类和评论,是基于对诗学传统的理解和总结,而透过白氏感伤诗学,又有助于理解中国诗学中的感伤传统,以及古典诗学对此思想观念之合理性的辩护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