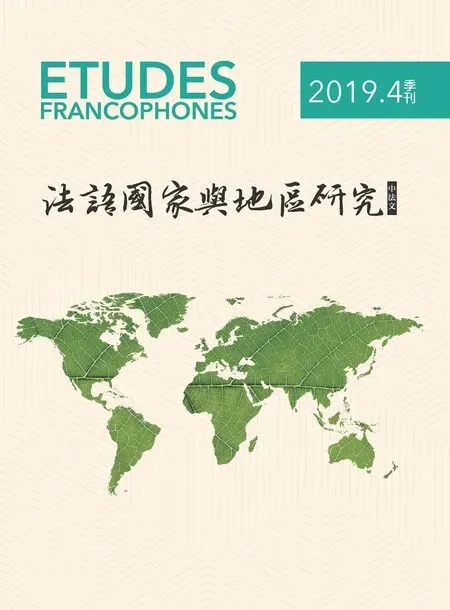论吉奥诺《再生草》动物描写中的生态伦理思想及其矛盾性①
张兆龙
内容提要 法国作家让·吉奥诺的短篇小说《再生草》通过塑造诸多家养与野生动物形象以及阐释人类物种与非人类物种的关系,传递出作家复杂而矛盾的生态伦理思想:一方面,关心动物的内在生命价值,强调其非工具性价值,表达敬畏动物生命的生态价值诉求;将动物设为喻体来刻画人的个性特质,阐释人与动物的平等地位;关怀动物的情感体验与尊严,强调人与动物的互为依赖。另一方面,重视动物的工具性价值,视人类的基本权利重于动物的基本权利,与弱势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不谋而合。
引 言
二战前,法国乡土作家让·吉奥诺(Jean Giono,1895-1970)的作品多以家乡马诺斯克镇为背景,小说叙事中融入自然景观的描绘,生态意蕴丰富,传递出尊重自然、敬畏生命的生态伦理观。在吉奥诺所构建的文学世界中,土地、植被等自然要素所占笔墨固然浓重,但动物形象从未缺席:《再生草》(Regain)中鸟类的活动言说着四季的更迭,在远离城郊、交通不便的高原地区,几近与世隔绝的乡民依靠观察动植物的季节性现象来判断时节,准备农事;《种树的男人》(L’homme qui plantait des arbres)中孤寂的老人在宁静的乡野中默默无闻地种树造林,陪伴他的只有一条谦卑安静的狗,动物俨然成为了人类情感的依靠和忠实的朋友;《序幕》(Prélude)中一只野鸽被人虐待,作者借潘神的化身质问施虐者“你有什么权利抓住它,折磨它?……有什么权利扼杀这个灰色的小东西的生命?……它像你一样有血液”(吉奥诺1994:14)②本文所引用吉奥诺作品的译文均出自安徽文艺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的罗国林先生译本《庞神三部曲》,“庞神”,今译为“潘神”。。在吉奥诺的笔下,动物化作有感情、通灵性的存在,“是人类与非人类主宰之间的媒介,同时,一个神秘的世界也借此逐渐显现出来。”③Chonez C.Giono par lui-même.Paris:Éditions du Seuil,1964,p.46.;《山冈》(Colline)中龚德朗在地头杀死一只蜥蜴,他觉得除了心头的恶气,但转念“羞惭之感袭上他的心头”(吉奥诺1994:49)。从农家蓄养的畜禽到高原野生的飞禽走兽,吉奥诺将普罗旺斯大地上的万物生灵与一草一木皆绘入自己的作品中,家乡的生态景观得以呈现,作家对故土的依恋之情得以告白。
国内外对于吉奥诺作品的研究数不胜数,但在崇尚自身文学研究传统的法国,对于发轫于美国文学领域的生态批评,前期反应冷淡④Posthumus S.« État des lieux de la pensée écocritique française ».European Journal of Literature,Culture and Environment,2010,1 (1):148.,尤其是法语文学生态批评的研究仍处于发展中⑤Blanc N.,et al.« Pas de côté dans l’écocritique francophone ».L’Esprit Créateur,2017,57(1):123.,因此,法国学者对吉奥诺作品中动物形象的研究多立足其象征义(Bourcier 2004),而非生态意义。而国内对吉奥诺生态观的研究多聚焦在树木(柳鸣九 2000;陆洵 2014)或土、气、水、火(杨柳 2013;陆洵 2016)等自然元素之上,忽视了其中的动物形象的生态价值。发表于1930年的《再生草》是吉奥诺的短篇小说之一,小说中共出现15 种家养及野生动物,它们与人类的种种关系体现了吉奥诺复杂的生态伦理思想:一方面,动物与人共生共荣,既呈现了吉奥诺家乡物种丰富的生态环境,也传递出作者对待动物的生命和生活的关怀之情;另一方面,男主人公的猎人身份,注定众多的野生生命将耗尽于他的手中。在人类物种与动物物种利益的博弈中,作家最终选择视人类的生命价值高于动物的生命价值,致使其生态伦理思想呈现出矛盾形态。而这种选择的前提条件,即出于维护人类的基本生存权利的需要,合理地解释了这种矛盾性的成因。
一、《再生草》中的动物书写及其积极的生态价值诉求
小说《再生草》描述了一座名为奥比涅纳(Aubignane)的村庄的人事变迁:“死气沉沉”的奥比涅纳村土地贫瘠,生活着三位居民:壮年猎户庞图尔(Panturle)、寡居老妇玛迈什(Mamèche)和年迈铁匠戈贝尔(Gaubert),三人互帮互助。但随后,戈贝尔搬离,玛迈什出走,独留庞图尔。曾一度孤寂无望的庞图尔与阿苏尔(Arsule)相遇,两人开始新的生活,归置家当、造犁耕地,随之而来的是麦田丰收、喜得佳邻、孕育新生,奥比涅纳村重获生机。一如吉奥诺二战前的其它作品,《再生草》细致描绘了自然中的草木与生灵,强调了动物自身的内在价值;借动物与人的共性,搭建以物喻人的修辞,阐释了动物拥有与人同样平等的地位;动物的情感不容忽视,动物与人互为倚靠。无论在现实世界,还是吉奥诺的小说天地中,生活在同一个生态系统中的植物、动物与人均是价值主体。自然的存在或描绘绝非仅仅是为了现实的或虚构的人物的存在而存在,自然以及生活在自然中的动物本身自有其存在的固有价值,因此,动物拥有生的权利,应当给予动物的生命和生存必要的道德关注。
首先,动物物种的历史早于人类物种的历史,动物本身的生命意义并不依附于人类而体现,动物具有固有的生命价值,自有其生命目的性。高原地区的奥比涅纳村,远离喧嚣城市,山区的原始风貌得以保留。农家篱落之外的山野里,人迹罕至,生活着多种野生动物:麻雀、画眉、乌鸦、喜鹊、黄莺等鸟类,野兔、獾、狐狸、鼠等兽类,生命悦动,这些动物与植物、山川形成自然界一片和谐之色,勾勒出一幅饱含生命气息的生态之貌。时而出没的动物身影,为人烟稀少的村庄增添了生命力,“房檐下,宛如风扬起的一把麦糠,一小群飞舞的蜜蜂,正在瓦楞间寻找地方结巢。”(吉奥诺1994:329),“两只小喜鹊在学习飞翔,尾巴上的羽毛扇子般张开,像两个皮球滚落在枯草丛里。”(吉奥诺1994:338),“乌鸦们全飞来了。先是一只接一只,大声聒噪着互相召唤,接着成群地飞了来,好似秋风卷起的大片大片的树叶。”(吉奥诺1994:398),生命如此繁盛,世界如此美好,寂寥的乡村因此而平添诸多动感。于生态意义而言,吉奥诺家乡生物物种的多样性得以体现。同青山绿水一样,动物是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拥有同等重要的、不容忽略的生态价值。
其次,动物的生命不仅应受到尊重,更应该享有同人一样的平等地位。该小说与另外两部短篇小说共同收录在《庞神三部曲》中,此外,主人公庞图尔(Panturle)的名字亦含有“潘神(Pan)”一词,而希腊神话中的潘神是掌管树林、田地和羊群的神,呈半羊半人的形象。因此,小说中的庞图尔拥有潘神半人半兽的秉性,兼具人性与动物性。英国动物学家莫利斯在将人类行为与动物行为进行比较后,曾尖锐地指出“尽管人类博学多才,可他仍然是一种没有体毛的猿类”⑥莫利斯.《裸猿》.何道宽,廖七一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1.。在吉奥诺的眼中,人类时时呈现动物形态,他使用大量明喻将人拟作动物,描述人类的一些本能的、无意识的行为:失去孩子的玛迈什“就像一头野兽扑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吉奥诺1994:281),突如其来的意外夺走了玛迈什唯一的亲人,难以承受的丧子之痛使她情绪失控,几近发狂的行为如“野兽”一般,这也是母爱不自觉的迸发;性欲发作时的庞图尔“像一头野兽”(吉奥诺1994:338)般狂奔,人到中年的庞图尔仍孤身一人生活,春天到来之后,无处释放的“力比多”使他狂躁不安,甚至几度失去人的理性,这是原始性欲的本能冲动。生活稳定之后,庞图尔精神愉悦,“喜悦的滋味,他要细细咀嚼,慢慢品尝它的液汁,就像傍晚时分,羊儿在山冈上咀嚼青草一样”(吉奥诺1994:409)。吉奥诺正是抓住人与动物在行为和情感上的共性,搭设动物性比喻,模糊人与兽之间的界限,突出人的动物性,人物形象的个性描写也更加形象生动。但吉奥诺此举并非否定人类的进化,而是以此强调人与动物不是二元对立的,他们是生态系统中彼此平等的物种个体。
最后,动物的情感应当被尊重,动物也会成为人的依赖。庞图尔将喂养的母羊卡洛利纳(Caroline)视为伙伴,亲昵地唤它“卡布洛”(Cabro)。姓名本是人类社会特有的文化现象,姓沿承自父辈,名由长辈深思熟虑而取定,名字饱含了长辈对子女的爱与期望。小说中,身为动物的羊同人类一样享有专属于自己的名字,庞图尔在平日又常用昵称唤它,宠溺之情可见一斑。女主人阿苏尔到来后,对母羊也是宠爱有加。她唤羊出圈时,叫羊“小乖乖”,装作手拿干草引诱羊,并模仿羊亲昵的咩咩叫,“鼓励”羊出来。当羊贴在女主人身上磨蹭时,女主人又一次唤它“乖乖”。“鼓励”本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心理交流,由衷的鼓励可给予对方以心理慰藉。女主人极富耐心地引诱、呼唤羊,而非用蛮力将羊牵扯出来,充分尊重羊的意愿,希望羊自己主动走出羊圈。由此可见,女主人将羊视为一个平等的个体,不强求于羊,不将自己的意愿暴力施加在动物身上,充分尊重动物的选择,顾及动物的感受。在母羊卡洛利纳不产奶后,庞图尔盘算着为它找头公羊。表面看是为了满足人类对羊奶的需求,而实际更暗示了动物像人类一样需要性伴侣,需要养育幼崽,繁衍生息。“动物也拥有同等的天赋价值”……“它们也拥有获得尊重的平等权利”⑦雷根.《关于动物权利的激进的平等主义观点》.杨通进译.哲学译丛,1999,(4):30.。《再生草》中通过对母羊卡洛利纳的描绘,强调动物同人类一样,拥有丰富与博大的情感世界,有着自己的快乐与痛苦,对幸福与悲伤自有体会,而且动物具有情爱和母爱等多维情感,其求偶与繁衍后代的权利应当被尊重。
卡洛利纳一直陪伴庞图尔左右,当奥比涅纳村只剩庞图尔一人之时,唯有卡洛利纳听他倾诉,卡洛利纳俨然化身他的精神伴侣。阿苏尔陪邻居家的孩子溜达一天后,产生了抚爱孩子的强烈欲望。她于是“在卡洛利纳肚皮下摸来摸去,在那暖烘烘的羊毛里拍一拍,掏出一只羊羔来,接着她往母羊旁边的干草上一坐,把羊放在膝盖上,抚摩着。”(吉奥诺1994:405)。当阿苏尔渴望成为母亲,抚育子女时,她将自家的羊羔爱抚一番。作家将人与人之间的友情、亲情转移到人与动物身上,说明动物拥有与人同样的丰富感触,能够理解人的情感,抚慰人的心灵创伤,动物成为聆听人类情感倾诉、慰藉人类心灵的“密友”。戈贝尔搬离奥比涅纳村后,客居独子家以享天伦之乐,含饴弄孙之余,“常把喜鹊放在花盆下,教它们说话”(吉奥诺1994:364),聊以解闷。照此看来,这些游走荒野的生灵,与人类为邻,是人类孤独心灵的陪伴者。人与动物都是自然界的居民,彼此间互无敌意,相安无事,共同分享自然馈赠的各类资源。
二、吉奥诺生态伦理思想的矛盾性与复杂性
如果说《再生草》传递出作家珍视动物生命、关怀动物生活的生态哲思,那么其前提条件是人类与动物各居其位,两者利益互不交涉,方可和睦共处。然而,在小说中,多处描写与此呈现矛盾的关系:突出动物在人类社会生产中的工具性价值;强调动物具有用以维继人类生命的食用价值和保障人类基本生活的经济价值;相较人类的基本生存需求,动物的生命退居次要地位,这与弱势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不谋而合;同时,重视人类的基本利益不意味着肆意掠取动物资源,在人与动物的利益取舍中,人类应当坚守自己的生态底线。
首先,动物与人之间存在着互惠关系,动物具备可供人类利用的价值。在生产工具落后、生产要素匮乏的年代,受经济条件的限制,农户豢养于家的往往是有利于农牧业生产的动物,这正是看重了动物的工具性价值。《再生草》的开篇是马车夫米歇尔(Michel)赶马车运载乘客的大幅场景描写,庞图尔日后换取生活必需品也是经由米歇尔。在崎岖的高原地区,使用马车运载乘客,辅助交通运输,为交通载体提供全新的动力来源,既解放了人力,也方便人们出行和联系外界。马匹也用以助力农耕生产,即便像庞图尔这样孔武有力的猎人,在开垦荒地时也需要铸铁造犁,并去邻村借马拉犁。畜力与铁器相结合辅助农耕,既减轻了人力负担,也极大提高了劳作效率,在他人麦田欠收之时,庞图尔却收获了颗颗“似弹丸般沉甸甸的”麦粒(吉奥诺1994:381)。同样作为运载工具和辅助耕地的牲口还有骡子和驴,成为农民之后的庞图尔在春耕之前筹谋未来时,盘算着买一匹好骡子。奥比涅纳村复苏之后,新邻居迁入时用自家骡子搬运行李。相比之下,没有钱买驴的热得米斯(Gédémus)需要靠阿苏尔帮他拉车,在失去阿苏尔之后,庞图尔用钱补偿他,让他买驴拉车。可见,在工业化进程尚未蔓延至山区农村的年月,村民的交通外联离不开动物的辅助,农业生产需要合人力与动物之力辛勤躬耕,才可确保收成,动物俨然是人类劳作中的“工友”。此外,野生动物的出没与迁徙传递出季节交替或天气变化的种种信息,无形中参与了人类的生产生活。庞图尔与玛迈什依据动物的活动和风、大气的变幻来判断季节时令,安排生活,准备农事。总之,在机械化生产工具和精密仪器完全普及之前,动物为人类的精耕细作提供了条件,促进了生产力的进步,最终提高了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率和个体的独立生存能力。
其次,在人与动物的共生中,两者之间的友睦关系并非一成不变,将他们置于对立关系的正是人的一种基本需求,那就是生存,人类利用动物的食用价值和经济价值满足自身的生存需要。“食”便是为了满足对生的渴望。虽然,吉奥诺热爱动物,生活中“驯养狗、猫为伴”⑧Citron P.Giono 1895-1970.Paris:Éditions du Seuil,1990,p.143.,但他本人并非动物中心论的素食主义者,他曾言最爱的菜肴之一便是焖牛肉⑨Grosse D.Jean Giono Violence et création.Paris:L’Harmattan,2003,p.24.。《再生草》中的人物虽然对动物珍爱有加,但是他们的餐桌上并不拒绝肉类,因此人类对动物的爱并非绝对的。小说开篇提及米歇尔的马车赶路时,乘客拿出“小香肠、鸡蛋、奶酪”(吉奥诺1994:276)充饥。母羊卡洛利纳供给奥比涅纳村的三位原住民羊奶饮用,在物质上给养人类。这些均是利用动物的食用价值的体现。当然,小说提及这些食物时,轻描淡写而过,并不过分强调食品由哪种动物的肉类加工而成,没有给读者造成强烈的视觉冲击感。参照食物链,人类居于其中一环,食用肉类是维持生存的需要,也符合自然规律。
庞图尔出场时,被赋予猎人的身份,这种身份注定了他与野生动物之间的矛盾关系。他喜爱动物,可作为猎人,追踪、捕杀动物是稀松平常的事情,是他生活的一部分。尤其是在寒冷的冬季,严寒使庞图尔的性情变坏,他“总是随身带把刀和设陷阱用的铁丝,四山游猎”(吉奥诺1994:300)。当然,庞图尔内心深处并不希望从事这份职业,他认为打猎“太没保障”(吉奥诺1994:362)。他游猎山野是因为“他需要肉”(吉奥诺1994:300)充当食物补给或用以交换生活必需品。奥比涅纳村地处高原,土质坚硬,“这块孬地……,毫无办法……比石头还硬,撂荒的时间太长了……板结得死死的,连刀子都进不去”(吉奥诺1994:348),仅在村下的斜坡坡脚处“才有一点松软的泥土”(吉奥诺1994:283),土壤条件和地理环境阻碍了当地农耕生产的实现。毫无田间收成,为了填饱肚皮生存下去,庞图尔不得不杀戮动物。他的邻居玛迈什虽无猎人身份,但在冬季,为了果腹,她也诱捕麻雀。对于这些经济赤贫的乡民而言,打猎实为一种生存方式,绝非有钱人的猎捕游戏。“环境伦理观的形成与其所处社会语境密切相关”⑩方红.《环境伦理观与社会语境——对比研究〈老人与海〉与〈沙乡年鉴〉》.当代外国文学,2010,(4):64.,饥肠辘辘的山民无处耕种,只能通过打猎维持生计。伴侣阿苏尔到来之后,吉奥诺的生活逐渐整洁、条理。两人的饮食结构发生变化,“有一次家里正好有兔肉,阿苏尔却光煮了一大锅土豆”(吉奥诺1994:352)。当人类的基本生存需求可以通过其他手段得以保障之后,人与动物之间的对立关系不再如以往那么尖锐。庞图尔认为真正的家中应该有面包,对面包的渴望实际传达的是内心深处对农耕的向往,对渔猎的排斥。最终,庞图尔实现了身份的转换,他从猎人变为农民。往日靠猎取野生动物为食物或用以换取日用品,而今的生活方式发生质的变化,面包成为了主食,余粮确保了经济收入,人类对动物的食用价值和经济价值不再那么倚重,这一切都得益于农田的收成,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利益冲突也因为主人公身份的变更而暂时缓解。
小说中另有一段宰剥狐狸的情节,刻画细腻且血腥粗暴:庞图尔一日抓住一只年岁不大的狐狸,他“猛地双手使劲一攒,随后双臂往两边一分,狐狸的骨头咔嚓一声,便顺着脊梁直至胸部被撕成了两半”(吉奥诺1994:332),庞图尔“两只手直到腕部血淋淋的,甚至有一缕鲜血一边流一边凝固,一直流到胳膊上的汗毛里”(吉奥诺1994:332)。与文中其它捕猎和用餐场景的简单勾勒截然不同,吉奥诺细致地描绘了人类如何用双手屠杀、解剖一只幼狐,狐狸撕裂的肉体赤裸裸地呈现纸面,屠夫血淋淋的双手将人类的残暴袒露无疑。人类亲手结束了动物的生命,动物的生存权被剥夺,弱者的尊严被强者无情地践踏。吉奥诺曾写到“一切都有生命:动物、植物”(吉奥诺1994:51),动物与人类“一样有权享受阳光和风”(吉奥诺1994:14),人类没有权利肆意扼杀动物的生命。这样的情节是否与吉奥诺的一贯思想相违背?然而,紧随其后,小说描述了庞图尔杀生之后的内心写照:当主人公“被召回到人世间”(吉奥诺1994:333)之后,他顿觉自己“像一个卑鄙小人”(吉奥诺1994:333),“想到自己的双手在血泊中摸过,不禁脸上热辣辣一阵羞愧”(吉奥诺1994:334)。可见,庞图尔心里认为自己残暴杀狐是因为附了魔,如此令人不堪的举动并非有意为之,当他的意识再度清醒之后,他自身的道德情感修养斥责之前的残忍卑鄙之举。后来庞图尔亲口对阿苏尔解释此事时,提及他“以前不这样,一个人孤单无伴时变得很坏,跟天气有关”(吉奥诺1994:344)。庞图尔自认为当时几近疯狂的举动是“坏”的体现,跟气候有关,是内心孤独所致。实际上,这是一种强烈性欲催化下产生的人的原始情感冲动,而这种冲动促使庞图尔迷失了自我,导致他暂时放弃个体的道义,做出反常之举。庞图尔一直未娶,他渴望一位伴侣的出现,在春天到来之际,这种渴望尤为明显。正是在“性欲的驱使”⑪Bourcier D.La symbolique animale dans l’œuvre romanesque de Jean Giono.Poitiers:Université de Poitiers,2004,p.42.下,庞图尔才丧失理智,做出如此着魔般的举动。然而,与其说是性欲膨胀,不如说这是繁衍子嗣的需求,因为庞图尔期盼村庄重生,他对孤独的惧怕、对女性的渴望,实质上是对生命延续、村庄再生的一种急切心愿。正如法国哲学家史怀泽(Albert Schweitzer)所言“所有生命,包括人的生命和一切生物的生命都是神圣的”⑫史怀泽.《敬畏生命》.陈泽环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9.。人类对于动物也应施以道德关怀,伤害动物的行径值得反省。在庞图尔或吉奥诺看来亦是如此,因为只有对动物生命怀有敬畏之心的、对动物生存权利抱以尊重之情的人类,才会检讨自己剥夺动物生命的举动。
除了食用价值以外,对于一无所有的村民而言,动物本身的经济价值亦十分重大。庞图尔成家之后,新妻的勤劳改变了原先粗陋的生活,一切逐步安顿就绪,当妻子提出使用火柴替代火石时,庞图尔拿着一张兔皮去找车夫换取火柴等生活必需品。“尊重自然并不意味着要放弃或忽略人类的价值。”……“在其他物种的善和人类价值的实现之间的冲突对我们来说就是相互竞争的道德要求的冲突。”⑬泰勒.《尊重自然:一种环境伦理学理论》.雷毅,李小重,高山译.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65.。生存不仅是人类的基本权利,也是动物的基本权益。弱势人类中心主义“关心人类的整体利益和终极价值,但也同时承认自然的权益及其内在价值”⑭林红梅.《生态伦理学概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39.。诚然,人类与动物共同享有生的权利,但是生活在同一生态系统中的人与动物之间的利益并非永远协调一致。居于奥比涅纳村的荒原瘠壤之上,村民只有靠猎杀动物才能解决暂时的温饱。为了生存下去,人类不得不暂时忽略生态环境,忽视动物的生命价值。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认为“当人的利益与自然的利益发生冲突时,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高于生物和自然界的利益;但是生物和自然界的生存高于人类的非基本需要”⑮Ibid.p.77.。换言之,虽然人类热爱并关怀动物,但是这种爱并非绝对盲目,而是有序的:人类只有优先满足自身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后,才会考虑动物的基本权利。当人与动物的基本利益发生摩擦或冲突时,人类首先顾全自身的权益。但决不允许为了满足人类的非基本需求而擅自残害动物的生命。在这一点上,吉奥诺的生态伦理观与弱势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不谋而合。
最后,吉奥诺生态伦理思想呈现的矛盾形态正是其复杂的生态伦理思想的体现,在吉奥诺看似矛盾的生态理念中,始终蕴藏着自己的生态原则:吉奥诺认为众生平等地生活在宇宙天地之间,然而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基本生存需求,可以消耗动物的生命价值;但是与此同时,人类对动物的消耗不是无度的、任意的。他笔下的主人公庞图尔在狩猎时,坚守自己的生态底线:不伤害雌性动物。发现动物是雌性时,他“便不再惊动他们”,因为“雌兽肚子里怀的小兽,是他的储备物”(吉奥诺1994:330)。雌性动物负责孕育新生、繁衍后代、延续物种,因此,雌性动物是生命的象征。自然资源虽然体系庞大,但绝非永续不竭,保护繁育期间的雌兽,留给动物繁殖生存的时间和空间,是对生态平衡的一种追求,是生态多样性的一项保障。取用有节的生态行为是可持续发展生态意识的具体体现。同时,在小说中,这种生态意识与行为呈现出自觉性和主动性。荒无人迹的山野,无需他人监督或制度约束,庞图尔便自觉遵守内心的生态原则,主动守卫生态的多样性,这也从侧面传递出吉奥诺对家乡环境和动物发自内心的热爱。
结 语
《再生草》中的动物与村民共享一片蓝天,同饮一江水,共栖一方山地。丰富的动物物种不仅为小说画面增添了盎然生机,也勾勒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栖居环境。对于吉奥诺生态观的审视,不应忽视其笔下动物角色的生态价值及其生态伦理观的多元性。在他的文学世界中,人与动物共同栖居于广袤的自然中,两者具有某种共性,他们既是自然界中互为平等的成员,亦是唇齿相依的个体,是“生命共同体”中地位等同的要素,均享有生存的权利。任何对非人类物种资源的残酷掠夺行径,必将破坏生态食物链,导致生态失衡;作家通过小说书写将动物置于道德关怀之下,然而,有时为了确保自身的基本利益,人类不得已需要割舍动物的基本权益,但这并非等同于人类可以肆意戕害动物或漠视动物的生命价值。
吉奥诺的生活环境、文学经历以及时代背景综合作用,影响了他的生态伦理思想。他自幼喜欢亲近自然,常独自置身于乡野怀抱,因此,他与自然之间有着天然的亲密感;他偏爱雨果等浪漫主义作家的作品,但又超越浪漫主义的生态视野;一战的参战经历给他留下深刻的影响,亲眼目睹过战争的血腥和残暴,他反对战争,渴望和平,因此也更珍爱生命。作家怀揣对生命的敬畏之心,抒写自己的物与之怀,警醒世人回归生态关怀的维度,关爱一切人类和非人类物种的生命,厚爱自然、善待生态才能彰显人品、完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