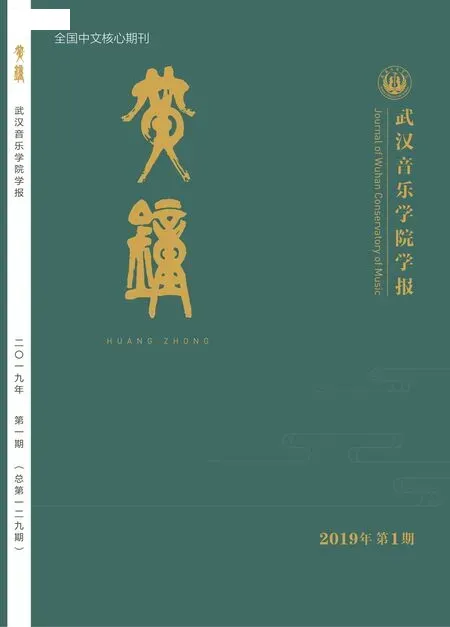鲍曼对比较音乐学历史发展的阐述
麻 莉
反观历史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看清当下与把握未来。一门学科的历史发展也是人类认识世界与自我的过程。作为现代民族音乐学前身的比较音乐学,诞生于19世纪末的德国和奥地利,是从音乐学延伸出的一个分支。比较音乐学关注的是对“欧洲之外的民族”及“无文字流传的文明”中的音乐进行记录、整理、描述和研究。历史上比较音乐学受到欧洲中心论的影响,认为其他文化中的音乐是欧洲艺术音乐的早期形态表现,这主要是基于进化论和文化圈理论的影响。研究的重点也一直放在对音乐本体的记录、整理、声学分析、乐器分类上,希望通过对音乐本体比较的方法揭示出不同文化发展之间的关联性。自从这门学科的出现,学者们对音乐的认知和理解从以前的欧洲转向了世界,从对一种音乐的研究转向了对世界各种不同音乐的研究。比较音乐学的出现是对传统音乐学的一次革命,虽然这门学科在初期还伴有欧洲中心论的色彩,但在后期的研究发展中学者们已经清楚的意识到不同文化对音乐发展所起的作用和意义,为后来的民族音乐学转向奠定了基础。
“比较音乐学历史面面观”是马克斯·皮特·鲍曼(Max Peter Baumann)①关于马克斯·皮特·鲍曼(Max Peter Baumann)的个人信息,参见麻莉:《鲍曼关于“世界音乐”作为跨文化策略的研究》,《黄钟》2018年第4期,第67页。教授于2017年12月4日至8日在南京艺术学院为期一周讲学中的第一讲。作为曾长期担任德国柏林“国际比较音乐研究所”所长的鲍曼教授,在这一次讲座中,详细梳理了比较音乐学的形成与发展,尤其是比较音乐学与时代背景、各种学术思潮和理论发展的关系脉络。从当今德国民族音乐学家的角度,解读了比较音乐学的历史意义和当代范式的转向,引导我们从历史的宏观角度剖析学科的具体研究方法,反思如何借鉴和吸取历史经验。笔者在此对鲍曼教授的讲座做了一个整理,希望较详实的反映讲座的内容。
一、观察者的角度
鲍曼教授在讲座的开始首先阐明讲座的主题——“比较音乐学的历史面面观”中涉及的主要问题是“谁在观察这个世界?”他认为,作为一个观察者来说,观察世界的角度决定着内容的不同。在欧洲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习惯于用比喻的方法来表现被观察的事物。他列举和讲解了德国班贝克国家博物馆中,收藏的一副大约16-17世纪名为“音乐女士”(Frau von M usica)的画。这幅画中的各个符号都象征着人们对音乐理解的不同层面。

图1“音乐女士”图②
在图画的中央端坐着一位“音乐女士”,她是我们观察的中心,她的耳朵象征着听觉,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说,听觉与认知科学和心理学联系在一起。“音乐女士”一只手的拇指与食指作出丈量的动作,代表着经验和从数学的角度测量世界的方式,另一支手握着的鲁特琴(德文Laute,英文Lute),象征历史的维度。因为鲁特琴是从阿拉伯国家传入德国,后成为德国的民间乐器。除此之外我们还能看到社会层面的因素,例如地上的提琴象征着艺术音乐,单簧口琴则象征着民间音乐,不同弦长的竖琴象征着测量和乐器的制造,地上一组装笛子的套子象征着文化的相关性,在鲁特琴的下方卧着一只鹿,象征着精确敏感的听觉,也包涵自然和文化的意义。在“音乐女士”的身后还可以看到树木和田园,象征着自然、时间和空间。隐藏其中的小教堂代表着音乐的宗教维度等等。可以说,在这样的一副隐喻性的画面中,包含了关于音乐的所有层面。鲍曼教授认为,画面中的每一个符号都非常开放,有着多重含义,也就是说那个年代的人,不像今天的科学家们对一些具象的事物用一些特定的抽象术语对其下一个定义。这一抽象化了的定义将符号本来所蕴含的多重含义单一化。这也印证着哲学家维特根施坦(Ludw ig W ittgenstein,1889—1951)的话:“科学或者科学的语言就像是一场语言游戏,用游戏来展开概念。”
接下来鲍曼简短的概要性梳理了从18、19世纪到当代欧洲的音乐家们,对世界各地音乐产生兴趣和对其提出追问的视角:18世纪的时候,欧洲的音乐家们对世界各地的音乐主要从历史的维度和文学的兴趣角度进行研究。例如从历史的维度对音乐的起源、音乐的民族意识形态、音乐史的层面等进行研究;从文学的兴趣角度主要从音乐作品中的诗歌、记录和文本的追问等层面切入。19世纪,人们的兴趣转向了民族志和人类学的角度,关注的是音乐的背景、功能和文化的行为等层面;之后又增加了社会理论的角度,例如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所说的回归自然、对家乡的守护、环境的保护以及今天的全球化问题等等。此外对音乐的兴趣还可以从道德教育与政治层面切入,探讨的是人本主义者对“道德的改善”、民主化以及意识形态化等等问题的思考。19世纪末至当代,人们开始从心理学的认同分类的角度关注音乐,诸如个体与集体的认同关系;从文化间性与对话的视角来关注音乐,在自我与异己之间调解冲突。最后他从跨文化的角度,引用德国当代哲学家沃尔夫冈·韦勒式(Wolfgang Welsch)的观点,即跨文化协调作为观察视角的出发点,在接纳异文化的同时,可以更容易的看清和认识自己。
二、历史上的比较音乐学派
从观察者视角分析,鲍曼将主题引入到历史上的比较音乐学。自从1880年代开始,伴随历史音乐学出现了“比较音乐学”,1884年左右,弗里德里希·克里斯德(Friedrich Chrysander,1826—1901)、菲利普·施匹塔(Philipp Spitta,1841—1894)和圭多·阿德勒(Guido Adler,1855—1941)3人组成了一个小组,即所谓的维也纳学派,他们创立了一本刊物《音乐学季刊》(VierteljahresschriftfürMusikwissenschaft)。1885 年 圭多·阿德勒在这本刊物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比较音乐学的范围、任务和目的》③Guido Adler:Umfang,Methode und Ziel der Musikwissenschaft.(比较音乐学的范围、任务和目的)Vierteljahresschrift für Musikwissenschaft(音乐学季刊),Leipzig1.Jg.,1885:pp5-20.的文章,对比较音乐学作出了如下阐述:“比较音乐学是音乐学中的一个全新的,很有思考价值的领域,这门学科的任务是对声音产品,尤其是对不同民族、国家和区域的民歌从民族志的角度进行比较,对它们的特点进行分类、归纳和总结。”④Guido Adler:Um fang,Methodeund Ziel der Musikwissenschaft,P.14.阿德勒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词:民族志(Ethnographic)和音乐学(Musicology)。这里的德语音乐学(Musicology)不同与一般德语中的音乐学(Musikw issenschaft)而是特指“比较音乐学”。在此鲍曼教授特别强调在1954年之后,民族志和音乐学这两个词合成了一个词,即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遗憾的是民族志或者种族志这个词在纳粹时期被滥用。鲍曼认为“民族”(Ethno)这个词具有“人民的、民众的”含义,在这个词中有意识的强调“我们的”意思,这里涉及的是身份认同的问题,毋庸置疑每个人要知道他属于哪一个种群,但是如果这个词被滥用就会导致民粹主义/种族主义等在纳粹时代出现的问题。
当时阿德勒把整个音乐学分为两个方向:历史音乐学和体系音乐学,比较音乐学只是作为音乐学的一个辅助层面来看待,这与当时殖民主义的种族优越性和欧洲中心论有密切关系,在当时真正的音乐被认为是欧洲音乐。这里鲍曼强调,其实音乐学应该叫音乐科学,它是由多种学科组成的。当时的比较音乐学对其他民族的音乐研究被看成是对欧洲音乐之前的音乐研究。人们认为,通过这些研究可以更好的了解欧洲音乐的早期状况。这种研究在当代被理解为以各个地区的民族志为主的研究,前提是为了音乐历史的比较。在当时的音乐研究中,还有一个核心概念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就是探究绝对意义上的“艺术的美”。在阿德勒的文章《比较音乐学的范围、任务和目的》中可以看出,阿德勒将欧洲音乐放在中心的位置上,他也是受到汉斯立克“艺术的美”中阶段论思想的影响,既与其他民族的音乐进行比较,是为了证明进化论中的“从开始简单的旋律”到越来越复杂旋律的理论⑤Guido Adler:Um fang,Methodeund Ziel der Musikwissenschaft,P.9.。阿德勒在他的音乐学导论中,将“原始的原住民”的音乐作为复杂的欧洲艺术音乐发展道路上的初级阶段来看待。对于阿德勒的这一观点鲍曼认为非常可笑,因为印度音乐的旋律和节奏要比欧洲复杂的多,这说明就学术而言,它不能从真正意义上脱离偏见。伴随这种思想,当时的研究目标直接瞄准了音乐及其风格,人们开始记录音乐,对音乐在文化语境中的关注直到1950年代之后的梅里亚姆才真正开始。
历史上比较音乐学除了维也纳学派之外,还有以卡尔·施通普夫(Karl Stumpf,1848—1936)为代表的柏林学派。维也纳学派的阿德勒与柏林学派的心理学家卡尔·施通普夫交往频繁。阿德勒对不同民族音乐的探究在后来施通普夫的两部著作中也有所体现。施通普夫当时在柏林对来访的印第安和蒙古音乐家的歌唱进行了录音,之后将其记录为五线谱,形成了1885年的《巴拉库拉—印第安人的歌曲》(Liederder Bellakula-Indiane)和1887年的《蒙古人的歌唱》(MongolischeGesänge)两本歌集。虽然这两本歌集对异民族的音乐进行了记录,但文化的语境并没有对研究起到影响。他的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声音心理学》(Tonpsychologie)⑥Karl Stumpf:Tonpsychologie,Leipzig:Barth,1883-1890.是受到格式塔理论(Gestalttheorie)的影响,另一部著作《音乐的初学者》(DieAnfängerderMusik)⑦Karl Stumpf:Die Anfänger der Musik,Leipzig:Barth,1911.是关于人类是怎样发现并创造音乐的,从进化论的角度来探究人类早期在音乐上的进化发展。
比较音乐学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是在维也纳出生,在德国工作的埃里希·冯·洪博尔斯特(Erich Moritz von Hornbostel,1877—1935)。他早年并不是一位音乐学家,而是德国著名化学家本森(Bunsen,1811—1899)的学生和施通普夫的助手,他发明了“吹奏五度理论”(Blasquintenttheorie)来测量音阶和音高,但完全脱离音乐的文化语境。他还和卡尔·萨克斯(Karl Sachs,1881—1959)一起发展出乐器分类体系。对于洪博尔斯特来说,比较音乐学要关注以下一些问题:音乐的起源、对世界上所有民族的音乐进行记录和保存、音乐的材料(音高、音阶、音序、音体系、和谐与不和谐的原则)、节奏与旋律、旋律与段落中的动机、不同文化区域中的理论体系、不同的乐器、创造音乐的目的与原因、演奏音乐的人、音乐与语言和舞蹈三者的关系以及音乐发展的不同阶段,也就是音乐的风格与历史等等。可以说洪博尔斯特对比较音乐学的建设进行了拓展。鲍曼认为,洪博尔斯特提出的这些研究领域其实到今天都有现实意义。他提出听觉现象心理学这一概念,并将听觉划分成两种类别:一种是生物式的听觉,另一类是文化人类学的听觉。生物式的听觉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然听觉,其功能对每一个人而言都一样,都能听到从20到2万赫兹之间的频率;而文化人类学的听觉,是指不同文化语境中生长的人对声音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除了当时德国的研究之外,鲍曼还介绍了英国人亚历山大·艾利斯(A lexander John Ellis 1814—1890)。1885年,也就是阿德勒发表他的文章之际,艾利斯也发表了一篇名为《不同民族的音阶》(OntheMusicalScalesofVariousNations)⑧Alexander John Ellis:Über die Tonleitern verschedener Völker,in Vergleichende Musikwissenschaft,München:Drei Masken-Verlang,1922,pp.5-75.的文章,该文于1922年翻译成德语,收入《比较音乐学文集》。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运用比较音乐学的方法,提出了不同民族不同音阶的划分方式,例如欧洲以全音阶为主,而其他民族以五声或七声为主。第一次意识到,导致形成不同音阶体系的原因不是自然现象,而是文化现象。不同文化的语境会产生出不同的音阶体系。身为物理学家和语言学家的艾利斯就此发明了一种测量音乐的方法—音分体系,但他还是以欧洲十二平均律的标准去分析其他民族的音阶体系。鲍曼认为,如果按照这种思路,今天巴厘岛上的人也可以以他们的音阶体系为标准,去测量欧洲的音乐。以上的种种现象对于鲍曼来说,表明了观察者在改变被观察者,因为观察者用自己的标准去观察被观察者时,在很大程度上将自己的影像投射到了被观察者的身上。由于人们有了不同民族的音乐录音,便得出了一个结论:不同的文化其音乐的划分是不同的。在艾利斯对古希腊、波斯、阿拉伯、叙利亚和苏格兰、印度、新加坡、缅甸、西非、爪哇岛、中国和日本的音阶做了比较之后,得出了一个结论:“世界上不存在一种‘自然’的音阶,甚至一种音响法则体系,就像赫尔姆兹所持的观点那样,而是根据不同的地区,呈现出非常不同的,非常艺术的,非常个性的特征。”⑨Alexander John Ellis:Über die Tonleitern verschedener Völker,p.75.学者们开始认识到,音阶和音乐体系不是自然现象,而是文化现象。
三、从音响档案的收集到田野调查的转变
鲍曼认为对于音乐研究来说,具有革命性的时刻是艾利斯音高测量法和爱迪生留声机的发明,为我们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促进了田野调查的实地展开。但必须强调的是,那个年代的田野调查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田野调查,只是利用技术对音乐进行记录而已。很多传教士将他们工作过的地方的音乐收集记录下来并带回了欧洲。研究者利用这些资料从声音和旋律的角度去研究当地的音乐,完全脱离音乐的文化语境。至于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完成录音无从考证。在讲座中鲍曼提到,世界上第一个田野录音是1889年由约翰·瓦尔特·菲魏克斯(JWalter Fewkes,1850—1930)对北美洲印第安人帕萨马科迪与祖尼部落旋律的录音,在将这些旋律转记到乐谱上后,1891年哈佛大学的本杰明·吉尔曼(Benjam in Ives Gilman,1852—1933)将其冠名为《祖尼旋律》(ZuniMelodies)并出版,⑩Benjamin Ives Gilman and J Walter Fewkes:Zuni Melodies,Hemenway Southwestern Archaeological Expedition,Boston:Houghton,Mifflin and Co.,1891,p.68.它为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样板并在世界各地流传。为了便于学术研究,1900年,以搜集到的音乐资料为基础,成立了“柏林音响档案馆”,1963年,该馆更名为柏林民俗博物馆的“民族音乐部”。1900年,泰国皇家乐团在柏林访问,卡尔·施通普夫利用爱迪生留声机完成了他的第一个田野录音,录下了当时泰国皇家乐团的演出。在讲座中鲍曼教授将这段当时录在唱筒上的珍贵音频分享给了大家。
在此鲍曼教授还列举了一张很有名的照片,一位女音乐学家费兰茨·邓斯莫尔(Frances Densmore,1867—1957)1916年3月在施密尼森研究所,用爱迪生留声机对一名印第安酋长的歌唱进行录音的场景。从照片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当时对音乐的记录只是关注到旋律上,而缺少与之相关的文化背景。在录音时,印第安酋长很不自然的正襟危坐,一定与他平时在唱歌时的状态大不一样。至此人们开始对音乐进行录音和保存,将被录音的人请到录音室来录制,音响档案被传遍世界各地,成为研究的对象。之后录音棚中的录音慢慢转到真正意义上的田野调查阶段。这期间女音乐学家费兰茨·邓斯莫尔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07年她成立了美国民族音乐研究所,建立了美国音响档案馆。

图2 1916年3月音乐学家费兰茨·邓斯莫尔对一名印第安酋长的歌唱进行录音
鲍曼认为,在对印第安人的采访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双重性。一是大量的印第安人在美国的殖民过程中被消灭,只是将一部分地区作为印第安人的聚居区,允许他们在此生活,而这一地区的印第安人就成了美国民族音乐学家们的田野调查对象。在介绍完美国之后,鲍曼又将视线拉回欧洲。19世纪末,欧洲对陌生民族以及他们的文化的兴趣越来越浓厚。1887年荷兰政府将一套嘎美兰乐队送给了巴黎音乐学院。在1889年巴黎世界博览会上可以看到和听到多种原生乐队和舞蹈团的演出,其中就有给法国作曲家德彪西(1862—1918)留下深刻印象的爪哇岛上的嘎美兰乐队。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北美印第安人音乐的研究报告是美籍德裔音乐学家特尤多·贝克(Theodor Baker,1830—1915)在德国莱比锡上学时,撰写的博士论文《关于北美野蛮人 的 音 乐 》⑪Theodor Baker:über die Musik der nordamerikanischen Wilden,Leipzig:Breitkopf&Härtel,1882.,New York:AMSPr.1973.(überdieMusikdernordamerikanischenWilden),1882年这部著作以德语出版,为后来的比较音乐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当时在世界各地还相继成立了音响档案馆,例如在维也纳、柏林、巴黎、布达佩斯、英国、圣彼得堡以及美国的各个大学。这时的比较音乐学也慢慢与文化圈理论联系在了一起。
四、比较音乐学与文化圈理论
在世纪转折之际,“比较音乐学”诞生之时,“文化圈理论”(Kulturkreistheorie)对维也纳学派与柏林学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罗伯特·拉赫曼(Robert Lach 1892—1939)为代表的维也纳学派开始将民族学、文化圈理论和“比较音乐学”联系起来,至此,柏林和维也纳之间的协作关系越来越频繁。文化圈理论由维也纳的民族学家威廉·施密特(W ilhelm Schm idt,1868—1954),费利茨·格雷布纳(Fritz Graebner,1877—1934)以及李·费勒宾纽斯(Lee Frobenius,1873—1938)提出。对于比较音乐学与文化圈理论的关系鲍曼引用音乐学家阿尔布莱希特·施耐德(Albrecht Schneider)的话:“如果没有比较音乐学早期的探索,就不可能形成后来的文化圈理论,如果没有比较音乐学的帮助,文化圈理论在1910年到1930年间的民族学中就不会有如此重要的意义。”⑫Albrecht Schneider:Musikwissenschaft und Kulturkreislehre:Zur Methodik und Geschichte der Vergleichenden Musikwissenschaft(音乐学与文化圈理论:比较音乐学的方法与历史),Bonn:Verl.für Systemat.Musikwiss.,1976,p.66.
文化圈理论的核心是“原始家园”(Urheimat)。音乐有一个“原始家园”,从一个地方原生出来,然后扩散到其他地方,它是与进化论联系在一起,与人类学中的“走出非洲论”类似,既人类起源于非洲,之后扩散到世界各地形成了后来的不同人种。这里鲍曼打了个比喻,就像人们给水里扔下一颗石子,会泛起涟漪一样。中心地带的文化是最古老的文化,然后向外扩散,最远的边缘地带的文化是最年轻的文化。根据这个理论,当时的人们认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还停留在石器时代,离这个中心文化稍微远一点地区的人们还生活在青铜和石器时代,依此类推生活在古代、中世纪直到最后一级也就是最年轻最发达的欧洲。根据这个理论也就是说最古老的民族,它的文化也最落后最原始。鲍曼指出这个理论有很大缺陷,世界不同的地区,它们都在早期发展出了自己的文化,从地层学上也找不出由中心向四周扩散的证据。另一方面鲍曼认为,文化圈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就是音乐在中心与边缘中的意义。大城市相对来说占据较多的资源发展较快,有些音乐最早产生于城市,又扩散到边缘地带,所以“中心源发扩散论”在特定的时空里有它特殊的意义。早期在学术界还出现过一个概念“自然民族”的文化,这个概念的提出是相对于“文化民族”而来,鲍曼认为这种提法证明当年的方法论存在问题。
对于文化圈理论的来源和假设鲍曼大致归于三类:一是生物学中的无性繁殖概念借用到文化中;二是移民假设,即人口的移动使得音乐传播成为可能;三是进化论。我们虽然批判文化圈理论,但是近年来利用DNA分析技术发现原发性又有了一定的合理性。一位人类学家史蒂芬·欧本海默(Stephen Oppenheimer)通过人类基因测定,最早的人类是在非洲源发,后扩散到世界各地。所以鲍曼认为,洪博尔斯特的理论对我们今天还是有借鉴的意义。从生理和文化两方面去分析听觉。过去文化圈的扩散论是确定某个地区有某种音阶,然后扩散到其他地方,但现实中,同一种音阶体系在世界各地都有存在,例如在中国有五声音阶,在非洲,在美洲、欧洲也都存在,同样的音阶可能是原发地产生,未必受了扩散的影响。在此鲍曼提出,我们必须追问生理上的听觉是否与文化上的扩散有必然联系,是否对其改变有直接的影响,还是音乐是从各自的原生地区自发产生的。
文化圈理论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是库尔特·萨克斯(Kurt Sachs,1881—1959),他在1929年出版了一本书《乐器的精神和演变》⑬Curt Sachs:Geist und Werden der Musikinstrumente,Berlin:D.Reimer,1929.(Geistund WerdenderMusikinstrumente)。对这本书的名称鲍曼提出质疑,因为精神是与人有关,而不是与乐器有关。所谓的乐器精神应该是使用、演奏和发明这个乐器的人的精神。萨克斯在这本书中也是接受了中心扩散论的思想。他利用乐器形态的相似性,试图证明乐器也是由中心向四周扩散的理论。除此之外萨克斯的一个伟大贡献是1913年出版的《乐器百科全书》⑭Curt Sachs:Reallexion der Musikinstrumentezugleich ein Polyglossar für dasgesamte Instrumentengebiet,Berlin:Bard,1913.(ReallexionderMusikinstrumente:zugleicheinPolyglossarfürdasgesamteInstrumentengebiet)。由于他是犹太人,二战时他流亡到美国,1943年在美国纽约出版了《古代世界东西方音乐的起源》⑮Curt Sachs:The Riseof Music in the Ancient World East and West,New York :Norton,1943.(TheRiseofMusicin theAncientWorldEastandWest)一书,书中的很多理论有待商榷。但就学术而言,他的研究为后人奠定了基础。这里鲍曼借用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l,1902—1994)的话:“科学是在不断证实它的正确性,永远站在历史的开端处。”
当时在文化圈理论的影响下,早期的音乐传播研究出现了两个对立的观点:扩散说和趋同论(Konvergenztheorie)。扩散理论的假设是音乐在某一个地方生发,然后扩散到各地。在此鲍曼举例琵琶,这件最早在阿拉伯地区产生的乐器,后来传播到中国、日本、韩国等等国家。就琵琶的传播过程而言并不是简单的扩散,而是在传播的过程中又吸收了当地的文化和代表地域特征的东西。与扩散相对立的是于19世纪80年代提出的另一个理论——趋同论,也就是并生/并存论。并生的观点是在不同的时空,各自生发出类似的东西,就如蒙古有一种乐器叫口弦,类似的乐器在南美和非洲也有,这些乐器是各地原发产生还是扩散而来,到今天为止也很难定论。鲍曼还提到了现代物理学中的一种假设论,即扩散可能是由意识决定,而不是由人决定的。人可以从一个地方运动到另一个地方,意识也同样可以,例如萨满教中的巫师。根据萨满的理论人类早就登上过月球,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设。如果我们今天用量子力学来看的话,一切都有可能。这里趋同论从生物学的角度被民族学所接受。对于鲍曼来说,音乐研究无论哪一种理论都是一种方法,无论是扩散论还是趋同论的并生观念在逻辑上都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将所有文化中的相同的现象看成是一样的发展过程。
当文化圈理论着眼于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时,与之相对的是将视角放在地区和区域上的地域边缘理论。对此鲍曼介绍了1869年成立的柏林人类学学会创始人之一的德国医生阿道尔夫·巴斯蒂安(Adolf Bastian,1826—1905)在1886年出版的《地理区域论》(ZurLehrevon dengeographischenProvinzen)⑯Adolf Bastian:Zur Lehrevon den geographischen Provinzen,Berlin :Mittler,1886.。他的基本观点是,人类的精神和禀赋具有普遍一致性,地理、民族、人种、历史和经济的整体空间造就了不同“民族间的思想”差异。在这个理论基础上,1936年德裔美国民族学家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 1858—1942)在他的著作《人类学的历史与科学》(HistoryandScienceinAnthropology)⑰Franz Boas:History and Science in Anthropology,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EW SERIESVol.37 OCTOBER-DECEMBER,1935 No.4.中提出了“文化区域”(Cultural Areas)的建构理论。他作为现代美国民族学的创始人(在美国民族学被称为人类学),有意识地回避进化论和扩散论的历史定义,提出了文化历史学上的“关系研究”。虽然部分借鉴了扩散论的一些研究方法,但不认为文化只有某一个源发地,而是在世界特定的多个地区有自身的文化中心;由这些中心再扩散到各个地区,同时受到不同地区条件的影响形成边缘区域(marginal areas)。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理论上的变迁,由早期学者对异族音乐作简单的录音记录到田野调查鲍曼认为这里有一个视角的转向,即进化论的历时视角转向了共时视角,在当下的情景中去观察各地不同的音乐传统。
在文化区域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博厄斯的方法论与法国结构主义哲学家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1908—2009)的方法论很相近,他关心的是当下某一个地区人类生活的形式,对此进行一种结构性的分析。每一个结构相互影响形成文化整体,每一个个体被作为关系体来定义,这样就打破了文化圈理论的一个文化中心的观点,变成多个中心。所以在结构主义的影响下,形成了一种叫“民族关系”的新方法,它更多的是一种功能主义上的研究方法,探究文化是怎样运作,而不是文化如何发展。这种研究方法有几个代表人物,例如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 ski,1884—1942)1922年出版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ArgonautsoftheWesternPacific),拉德克立夫·布劳恩(Radcliff-Brown,1881—1955)1952年出版的《原始社会的结构和运作》(StructureandFunctioninPrimitiveSociety),德国理论家理查德·图恩瓦尔德(Richard Thurnwald,1869—1954)从1931到1935年之间先后出版的《人类社会的民族社会学基础》(DiemenschlicheGesellschaftinihrenethnosoziologischenGrundlagen)系列丛书共5册,以及他的学生威尔海姆·米勒曼(W ilhelm Em il Mühlmann)在1956年出版了《民族学作为民族间关系的社会学理论》(EthnologiealssoziologischeTheoriederinteretnischenBeziehungen)。
五、音乐民族学
以前“比较音乐学”主要认同的是文化圈理论,伴随世纪的转折这门学科越来越倾向于功能主义的模式。在德国这门学科有了新的名称“音乐民俗与民族学”(M usikalische Volks-und Völkerkunde),鲍曼解释到,在德语中对本民族音乐的研究叫音乐民俗志(Musikalische Volkskunde),对世界上不同民族的音乐研究叫做音乐民族学(Musikalische Völkerkunde)。这个名称可能出自弗朗茨·博厄斯,他在音乐研究中将民族学和人类学的方法结合起来,为了区分历史音乐学,他从1953年便开始使用“音乐民族学”(Musikalische Völkerkunde)这一称谓。在此,鲍曼强调,德国人特别喜欢造词,每造一个词是为了与前面的词形成区别,也是对学科新内容的重新界定(在此笔者必须强调,德语中的很多词从中文翻译上看都一样,但在德语中是有不同理论重心的区别)。音乐民族学的角度更多的是民族志与种族志的研究,民族音乐学也可以称之为民族的音乐学。但这些名称都归属于音乐科学的范畴。1950年代,在文化圈理论、民族学、功能主义和历史音乐学中发展出了民族音乐学。就民族音乐学这个概念来讲,鲍曼认为它一方面有结构主义的特征,但也不忽视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待音乐的发展。1959年,荷兰的孔斯特(Jaap Kunst,1891—1960)使用了民族-音乐学这个概念,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圭多·阿德勒早期的关注点。1964年,梅里亚姆(A·P·Merriam,1923—1980)完成著作《音乐人类学》⑱A·P·Merriam :The Anthropology of Music,Evanston,Ill.:Northwestern Univ.Pr.,1980.(TheAnthropologyofMusic),它涉及的内容与民族音乐学一致,只是在美国叫法不同而已。鲍曼认为,这里各种不同学科名称的出现是人类在不断的制造语言上的巴比伦塔,它使得我们的语言越来越混乱。
随着学科的发展,学者们对音乐流传的技术和学科分类开始加以思考,美国的民族音乐学家查尔斯·西格尔(Charles Seeger)将传承技术/记录技术的传统划分为纯粹口传、以口传为主、口传笔传混合、以笔传为主、纯粹笔传。民族音乐学主要依据三种传承方式展开研究:口传、口传笔传以及笔传,它有别于历史音乐学主要以笔传资料(文献)为主。来自柏林的德国民族音乐学家迪特·克里斯腾森(Dieter Christensen)将音乐学的关注对象、方法和相对的学科建制分为三类:(1)音乐作为物理现象,与之相对的是自然科学的方法(声学、音乐心理学与体系音乐学);(2)音乐作为文化现象,与之相对的是社会科学的方法(音乐社会学、民族音乐学与音乐心理学);(3)音乐作为艺术作品,与之相对的是人文科学既艺术史和哲学的方法(历史音乐学)。鲍曼认为音乐作为艺术作品来研究的思路符合汉斯立克的观点,这里他解释了德语中的艺术有两层含义,即艺术和人为的事物与自然形成的事物相区别。无论音乐学的建制怎样分类,在实际研究中,一定是与不同的学科方法相结合的。例如在做田野调查时,首先从地理的层面出发,然后会用到观察、测量与记录的经验主义分析方法,以及历史音乐学和比较音乐学的方法等等。
六、民族音乐学作为区域研究
1992年,斯洛伐克的一位民族音乐学家奥斯卡·艾尔施克(Oskar Elschek)提出了以区域为主的民族音乐学。他将音乐学分为非洲音乐学、东方音乐学、汉文化圈音乐学、欧洲音乐学等等。在每一个特定的区域性音乐学下面还分为了艺术音乐、社交音乐、民间音乐和部落音乐。2000年西蒙·布劳顿(Simon Broughton)主编的《世界音乐指南》(Weltmusik:Roughguide)一书中,有一张图表就是将音乐按不同区域进行划分。讲到这里,鲍曼也随机提到,他在2017年12月1日参加的中国世界民族音乐学会年会的开幕式上得知,以管建华教授为首成立的东方音乐学系就是以区域研究为主的很好的例子。
随后,鲍曼对二战前和二战期间,比较音乐学在欧洲不同国家的研究情况作了介绍。随着早期比较音乐学家埃里希·冯·洪博尔斯特流亡瑞士和库尔特·萨克斯离开德国流亡美国,比较音乐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在德国销声匿迹,研究工作被迫中断。在德国唯一幸存下来的音乐研究机构是设在弗来堡的“德国民间音乐资料库”,由当时德国民俗学会委托约翰·迈尔(John Meier)在1914年建立,这里成为了收集和研究德国民间歌曲的中心。这个研究所之所以保留下来也是受了纳粹德国的影响。德国民间音乐在当时被理解为德意志的民间音乐,这里可以看出它是对自身音乐的强调。
在匈牙利,音乐家巴托克将以前的“文化地域理论”运用到系统的田野调查中并且对其结果进行了分类,。例如,他在1905—1906年间,对匈牙利和它周边国家的田野进行了调查,1906年,前往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收集民歌;1908年,在罗马尼亚收集民间音乐;1913年,第一次去了非洲的阿尔及利亚;1932年,参加了在开罗举办的阿拉伯音乐研讨会;1936年,在土耳其进行了田野调查等等。遗憾的是,音乐话语的语境在巴托克的研究中并没有得到重视。
这里鲍曼强调,随着国际音乐学会和它的分支比较音乐学在世界范围内的不断交流,研究者们越来越有意识地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世界音乐地图的空白点上,尤其强调的是对地域的研究。遗憾的是,对不同地区音乐上的比较研究,从一开始并没有与世界主义的理论接通,这使得比较音乐学在实践上面临绝境。由于比较音乐学方法上的缺陷,1950年代随着学科范式的转变比较音乐学被民族音乐学取而代之。
德国前柏林音响资料档案馆馆长西蒙(Artur Simon)教授对学科转向曾做过总结:(1)从进化论到文化主义,从历史的研究到文化人类学的研究;(2)从历时的到共时的;(3)从“早期形式”的欧洲音乐到文化形式的人类整体;(4)从对音乐的史前史到对音乐的当代研究;(5)从原始主义到相对创造主义;(6)从欧洲中心论到民族-建构主义;(7)从形式主义到社会文化语境研究;(8)从静态的到动态的;(9)从音乐产品到音乐过程分析;(10)从音响记录/文本的音乐结构分析到音乐行为方式的结构分析;(11)从偶然的记录到有目的的田野调查;(12)从单一的到双重文化的音乐性;(13)从单纯的比较到客观的差异;(14)从思辨抽象到经验实证;(15)从全局到具体细节的研究。二战结束后,西格尔、梅里亚姆、孔斯特、胡德以及内特尔对民族音乐学在1950年代的范式转折做出了贡献。音乐研究由以前的音乐客体(音乐文本)转向了音乐语境,人类学的观察方式对德国的民族音乐学研究也产生了影响。
最后鲍曼总结到,以上各种研究方式和观点的梳理告诉我们,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一直都处在不断的变化当中,我们不应该将自己的研究放在静态的框架中,而是应该从动态的变化中不断地去探索前进的道路。
总 结
讲座中,鲍曼教授将整个历史比较音乐学的发展脉络和不同的观点与方法做了细致的梳理和详尽的阐释。整个讲座给笔者留下的印象是,鲍曼对不同时代音乐观察者视角的思考,在某种程度上将焦点聚集到了对观察者即音乐研究者自身的思考上,而这一反思恰恰是研究者们自己很少关注到的方面。近年来德国学者们渐渐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于2016年在瑞士卢塞恩召开的首次德语区民族音乐学联合年会上就研究者是如何影响学科发展进行过讨论⑲麻莉:《音乐中的多种权威形式——“国际传统音乐学会德语区2016年联合年会”述评》,《黄钟》2017年第4期,第150-155页。。
鲍曼对音乐学名称更倾向以“音乐科学”来表述,为的是突出对音乐研究的多种可能性和不同学科视角的合作性。正如讲座开始时,他对“音乐女神”图画的分析一样,旨在提醒和指出现代学科的研究是否对传统的理解过于单一化,忽略了事物本身的多重含义。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次讲座仅限于历史比较音乐学的发展和观点的梳理,没有对当代“新比较音乐学”的方法做出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