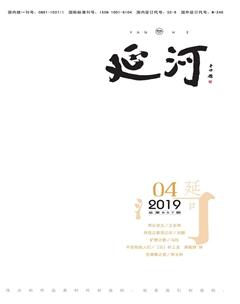大寒记
张静
1
夜里十点多,外面起风了,很冷。依着窗户,可以看见昏黄的路灯下,街边梧桐树上残留的叶子被卷得到处乱飞,偶有的士疾驰而过,把刚刚飘落在路边台阶下的叶子又卷得在原地打着转儿。待那风儿过去后,小城褪掉了喧嚣一天的外衣暂且安歇下来,天空黑压压一片,使寒气逼人的夜晚又多了几分沉静和寂寥。
对门一群女人上楼了,带跟的鞋子在楼梯上滴答滴答响着。然后是开门,关门,再然后,是窸窸窣窣声音,之后,安静下来。她们是一群打工的女人,群居这里有两年多了,看样子是在一家饭店打工。两年来,我几乎从来没有正面碰到过她们,留给我的,只有声音。有时是门开条缝,里面是说话声,笑声,叽叽喳喳,絮絮叨叨,无外乎在老家上学的孩子考上县里最好的高中,感谢婆婆在家照顾有功,马上快休假了,想回去看看孩子和老人,赶紧抽空上街买了件新衣裳,料子款式颜色如何,让同伴看看,顺道引来一片啧啧和赞叹声;有时候是吵架声,类似于压在床下的几十元零钱找不到了,相互猜忌,掉脸,发脾气,话不投机,或者话赶话的,就吵起来了;有时是某个月水费不能平摊,原因是有同伴家里来人了,吃喝拉撒,洗洗涮涮,自然消耗多等等鸡毛蒜皮和女人长短,不大能听得清,吵几声,总会有人劝住,不至于撕破脸皮打起来。毕竟还要像一锅粥一样掺和在一起,白脸唱完了还得唱红脸,亦属正常;更多是谩骂声,主要针对饭店老板,诸如老家亲戚眼睛不好来四医院看病,请不下假,悄悄乘下午客人少的空档奔医院看了一下,还让老板发现了,全勤奖没了,扣了二百,咽不下这口气,骂老板没人性,不要脸,拿老娘的钱买药吃了;也有盘子边的破损原本是李四碰的,却扣了张三的,则骂老板狗眼长后脑勺了;还有厕所的卫生巾没及时清理,被扣了十元的,骂声很粗糙,除了骂老板八代祖宗以外,连入厕女子也捎带上了,什么肯定是让男人干了,卫生巾,手纸胡乱扔,恶心人,不得脏病才怪,等等……这种骂声,往往一声比一声高,一声比一声气愤,也没人劝,直到骂的人累了,自个就歇下了。
歇不下的是我。我坐在自家的客厅里,听着对门时断时续时高时低的声音,忽而闪过一个念头,这是怎样一群女人,有着怎样的故事?我在一遍遍想象她们脸上的表情。比如丢了钱的,满脸沮丧;扣了钱的,歇斯底里;至于那个花了钱,给婆婆买衣服的女人,定然是满脸的阳光灿烂……有了这种臆想,我最初滋生出的厌烦莫名褪去,相反逐渐适应了这种喧嚣和吵闹,自家长期以来独占七楼公共空间那种宁静感当然一去不返了。每晚十点半左右,只要我在家,准会听到她们三三两两上楼的声音,轻快有之,沉重有之,喘息有之,大抵和当日在饭店承受的劳碌程度和心情寡欢有关吧?
我已经很习惯这鞋跟声。是她们让我觉得,有这么一群人,在我的小城里,怀揣梦想,像蝼蚁一般群居着,顾不得炎炎夏日的溽热,更顾不得西风猎猎的漫漫冬夜,我顺其自然地耳听她们放纵的骂,恣意的笑,八小时之外的宅居日子竟也有了几分活色生香。
照旧是寒夜,对门早安静下来。我看了一会儿书,有些疲倦,靠在沙发上打盹。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忽而楼道传来打电话的声音,先轻轻缓缓,后来越说越急促,越说越激动。我不由起身,走到门口,隔着一扇门,侧耳听。几分钟后,听出事情缘由了,是两口吵架,男人動手了,女人赌气出来打工,娃在家里没人照管,男人撵到老丈人家里求助,让赶紧回去。电话应该是女方家里打来的,只听得那女的一会儿哭喊,一会儿叫骂。哭喊的时候,委屈如窦娥,什么孩子小,一把屎一把尿都要从自己手里过;他老娘瘫痪好几年了,一日三餐,递碗递筷子,一点帮衬都指望不上;更有家里的,地里的,忙活一阵子,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还要落一顿脚踢拳,没良心的东西,这次绝对不能轻饶了他,他不八抬大轿来请我,想让我回去,没门。说完,狠狠挂了电话,一个人靠在墙角生闷气。活脱脱一幕独角戏,在空荡荡的楼道里演绎着。
知道对门有男的和女的一起混居的事实,还是几日前的夜里,洗漱完,准备要睡了,对门传来敲门声,一声接一声。可明明有人,就是不给开。那敲门声就咚咚咚,咚咚咚,越来越响亮,越来越急促,最终还是不开。于是,敲门声变成西府腔调的叫喊声,姨喔,开门,姨喔,开门。
声音是男的。对门竟然男女混住。我和老公都吃了一惊,顺着门眼看过去,还真是一小伙,正趴在门上,不停歇地用拳头砸。
我和夫被吵得实在忍不住了,开了门,提醒他,这么晚了,能小声点吗,还让不让人睡了?
兴许是小伙儿半天敲不开门心里着急吧,犟着脖子,嘴里嘟囔着,咋地,她们不开门,我喊喊惹谁了,又没敲你家的?夫一听,当然不愿意了,拽起他衣领,瞪着眼就说,说啥哪,大半夜咋咋呼呼的,影响别人休息,还有理了,再喊一声试试,看我不收拾你!
应该是夫明显强硬的气势压住那小伙儿了,他的态度马上变了,怯生生地说,叔,我不是故意的,她们不给我开门,我明天还得上工呢!
毕竟是孩子,错也认了,夫的语气也降了下来,随后问了一句,你干啥去了,这么晚回来?
没干啥,就是下班了,没处去,上了一会儿网。叔,要不,能帮我敲一下吗,楼道冷的,我已经冻了好长时间了。
夫早已面色温和,说了声,都是一伙儿女人,我咋能敲?让你阿姨帮你敲吧!
我这才仔细打量那小伙儿,十五六岁,黑色旧夹棉衣裹着清瘦单薄的身子,腿细得跟麻杆一般。身为母亲的我当下动了恻隐之心,就先让他进家里暖一会儿,然后帮他敲。
他犹豫着,不敢进来。不过,还是进来了。从他嘴里得知,家住在是西山,山大沟深,穷乡僻壤,父亲患肝病两年了,医生说没几个月活头了,母亲早就跟贩烟叶的跑了,家里还有两个妹妹在上小学,他是老大,只能辍学出来打工,赚钱养家。
当我问他怎么和一帮女人一起住的时候,小伙脸红了,说秋天里才出来的,没钱租房子,只好住在老板租的这间屋子里,他在阳台支张床,其他十二个女的分别在房间和客厅里,尴尬的很,好几回想换个工作,可一没手艺二没技术,就先这样了…
我不再说什么,从阳台的储物柜里翻出两件小子的旧棉衣、旧毛裤给了他。起身,替他敲开对门。对门看不见人,灌进我耳膜的,依旧是其中某个女子熟悉的、粗糙的叫骂声,从门缝里传了出来。
这一夜与我而言,注定是寂静而不平静的。
2
又至周末,碰上再次降温,蜗居。午饭后,太阳竟然出来了,乘着风儿不冽,气温稍微回升,拽着夫说,出去走走吧!
蜗居的这一片,能去的地方很有限,徒步走走,常择居所对面不远处的北坡。
北坡位于渭河以北、铁道以北,当然和秦岭不能比。尤其是冬天,北坡上草木不但稀少,且很少有常绿植物,使得绵延起伏的土塬整体显得光秃秃的。好在,还有一条人工渠,叫“引渭渠”,属于宝鸡峡水利枢纽工程之一,常年注满了水,潺潺流动。
有了水,周边草木风物会湿润许多,也有了几分灵气。而且,通往北坡塬顶的那条小路,早已被打磨得硬邦邦的,一片白光。即便偶尔路面上不多的土和砂砾,风儿也吹不起来,与我一个喜欢安静的人来说,来这里走一走,还算惬意之行吧!
渠在半坡处,是当年毛主席老人家兴修水利的伟大工程。我的爷爷、父亲,夫家老太爷,他们都曾在这里大干过五十天,故而我每次走在这水边,心中多少都有些敬畏和亲切。毕竟,这里有我的父辈们曾经留下的足迹,是他们曾用自己的一双手,修建了这座渠,使塬上的雍州百姓,西岐百姓,甚至最关中西部最远的扶风百姓,靠着这水,来浇灌庄稼,五谷丰登,家畜兴旺,颐养天年,父辈们也算有功之民啊!
沿着蜿蜒的砂石土路缓缓而上,要经过好几处村民搬迁后废弃的窑洞,横亘在阶梯一般的土塬上,有的空荡荡的,灌满了风,灌满了尘土。靠近路边或向阳处的,早已住着一些人。好几年了,我在春天里,夏天里,都来过,他们一直在。我不知道他们是谁,来自哪里,多大年龄。可以说,我对他们几乎一无所知。
夏天里,我和夫从这里上塬,看到过其中一个带窑洞的院子。说是院子,其实是用篱笆围起来的,种了很多苦瓜,藤蔓交错,像一道绿生生的帘子,快要将窑洞遮蔽住了。窑洞口的门用彩条布和粗布遮掩着,洞口旁边放着一个蜂窝煤炉子,一只黝黑的烧水壶搁在上面。篱笆墙上挂着几件衣服,有男人的,女人的。可能是一家子,也可能是两家子。我正望着那一串串丰满的苦瓜出神,突然出来一个老女人,用一双戒备的眼睛打量着我。我回了一个笑容,匆匆走开了。
夏天过去了,我再次路过这里,我碰见的那个老人怀里抱着几个月大的小孩坐在窑洞前晒太阳。小家伙可能是太长时间没有看到外人了吧,小手指着我,咿呀咿呀,很高兴的模样。我摸了摸口袋,正好有两颗糖果,走过去,给了他。小家伙马上手舞足蹈起来。
我问老人,家在那里,住在这里多久了?
她告诉我,老家在河南,儿子是替人跑运输的,有一回在自家门口倒车,没留意,碾死了邻居家的孩子。邻居家没了孩子,带着人把他家砸了个稀巴烂,赔了不少钱后,还是不依不饶,不是指桑骂槐,就是往她家门口抹鸡屎猪粪的,实在住不下去了,只好锁了门出来了。这一住,就是三年了。
马上过年了,不想回去看看吗?
回不去啊,中间回去了一次,邻居家死了孩子的女人怀孩子夭折了,都能怪到他们家头上,说是遭他们家诅咒的,一个个恨得咬牙切齿,一天到晚骂骂咧咧,受不了啊!
村里没人管吗?
她苦笑了一下,现在的农村,都是各家过各家的,谁管谁啊!再说,这事原本也是自家理亏,村干部任凭那个女人闹腾,也站到他们一边,毕竟,人家是受害者嘛!
那你怀里抱的孩子是?
我孙儿呀。儿子和媳妇先出来的,跟着人学会养木耳了,没地儿,只能养到引渭渠上边的那个破窑洞里。
哦,那几眼窑洞,我是知道的,远远望过去,有的坍塌了,有的还残存着。洞外几乎没有空地,只有很窄一道土台阶,下面就是比较湍急的引渭渠水,本来没有路,是他家人,硬是从渠边踩出了一条羊肠小道,歪歪斜斜伸向窑洞。
我吃了一惊,忽而想起,前段时间,朋友说,自己亲眼看见七八个消防队员在引渭渠里打捞一具尸体,说是一个种蘑菇的男子不知咋的,掉下去被淹死了,年龄不大,三十多岁的样子。
老人说,那个男子,正是他儿子。儿子没了,儿媳妇一个人扛起了这个家,继续种蘑菇,起早贪黑。還说,来这里贩蘑菇的本地人,有的很不讲理,挑三拣四,故意找茬压价;有的不怀好意,乘往框子里装蘑菇的空挡,对儿媳妇动手动脚。媳妇只能忍气吞声,哎,作难人呢!
起风了,老人她抱着孙子进了窑洞里面,留下我一个人,在风中发呆。其实,再往上走一小段路,就是引渭渠。渠的上面,一眼窑洞里,那个死了男人的年轻女人,一定抱着一个个蘑菇棒子,像抱着一家子的希望。
发了一会儿呆,原本想去探究的新奇欲望戛然而止。相反,内心深处,有一种声音在告诉我,还是远远走开吧,不惊扰,抑或是对她们最大的尊重吧!
3
不觉间,大寒已至,小城开始充满年味。昨夜,公公来电话了,家里亲戚要嫁女,发了喜帖,意思让回去一下,撑个面子。想着得赶紧把给公婆买的新棉衣送回去派上用场,一口答应了。放了电话,算算日子,正好周末,于是,再次踏上回乡路。
夫的老家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旱塬。一路上,由于干旱少雨,冬日里,随意散落、尘烟四起的村庄和果园光秃秃的,充分写意出字典里一个叫做土黄色的色板,这单调的颜色,也只有在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才被熏染出一丝硬邦邦的暖意出来。
夫家所在的村庄叫西店头村,未及其身那一年,我固执地认为这一定是个曾经的江湖村落,比如会有刀光剑影,南调北歌,风花雪月,或者其他诸多的江湖故事。可当我第一次随着逶迤而上的土塬高坡慢慢靠近时,才觉得,其实,它就是一个在时光河流中缓慢行走的旧村落,慢到村庄的外衣依然旧得像我曾经十几岁的村庄颜色,老树,老房,老墙,老路,一切都是老旧的;慢到这里的老人们依旧每年冬天穿老棉袄,棉布鞋,戴火车头的旧棉帽,他们满身黄土,满脸褶皱,手背着,腰弯着,慢腾腾从高矮不一的土墙下或者宽窄不一的小路走过,太阳暖暖地照着,脚步缓慢,时光缓慢,慢得与世无争。
那一瞬间,我总有一种冲动,撑一副画板,握一支画笔,一蹴而就,成一幅沧桑油画。可我笨拙的手,只在空中画了几条弧线,便愣在那里迟钝不堪了,我只能呆呆望着他们的背影,和土墙、阳光一起矮下去。
要说的,身居乡下,思绪总平宁,故而包括城郭之喧嚣,工作之繁冗,人际之纷争,统统都放下了。夜晚,漆黑一片,静谧一片,偶尔几声狗叫,完毕又静下去了。好像还有风声,在院子里,溜了一圈,便躲起来了。或许,它原本是想把牛儿、猪儿、羊儿等牲口赶回圈里,可如今,这些属于村庄的活性之物,貌似没有几只了,风觉得无趣,便尴尬退去。风声听不见,夜便沉默了,村庄更寂寥了。乡里人关了门,蜷缩在炕头,脚对着脚,头对着头,前尘旧事,东家长,西家短,絮絮叨叨的,打发一夜时光。也有人家,儿孙都去城里住了,孤老两口,早早熄了灯,和夜一起睡了。诸多未了的心思、未说的故事,只在夜里,在梦里,泛滥不休。
我们一回来,公婆的炕头不安静了。公公说村子里吸毒的那家又死了一个,留下三十万的高利贷给两个未成年的孩子。我惊诧,哇,这么偏远的乡下还有吸毒的?
咋没有?咱周围好几个庄子都有,而且是一窝子,昨天埋的那个,弟兄两个吸毒,媳妇也一起吸。春天里媳妇死了,这回男人一死,一个家彻底没了。公公唉声叹气地说。
他的话刚落,婆婆又唠嗑上了,问我是否记得小叔子走的那一年来家里热心帮忙跑前跑后的五姨?我说,忘记了。婆婆说,人也死了,六十刚过,癌症,瞎瞎病,没钱看,咽气时,眼睛睁得像铜铃。这不,刚刚过了五七,魂魄不散,附在新娶的儿媳妇身上,好好的,突然说胡话,走路绊倒,睡觉乱喊,说话腔调简直和五姨一模一样,给念了一场经,算是安心送走了……这些村里或唏嘘或诡异之事,若放在之前,我是断然没有耐心听下去的。如今,许是年纪渐长,经历多一些的缘故,竟然也会陪着他们细细听过来,顺便附和几句,让一段时光在老人的絮叨里细嚼慢咽而过。
公婆说累了,回厢房歇去了,我卻清醒得无法入睡。心里一直在想:这些声音,在村子里,肯定不止一家的炕头有,你一句,他一句,就把村庄的夜晚填满了。难怪刘亮程在《一个人的村庄里》说,夜晚的村庄是醒着的。他只说,庄稼在夜里缓慢生长,小孩在夜里长得快,牲口在夜里也没命地长。可我还想说,在这寒气逼人的夜里,一些打上乡下人烙印的东西,隔着东墙,隔着西墙,被漫不经心一般地拽出来,发酵和膨胀。
正在愣神中,窗外,从村子北头传来的秦腔声,可以听出来,唱的是《周仁回府》里的哭坟,风生水起,哀婉动人。夫说,唱大戏的,是村子的外姓人家,姓张,都唤他张四,是当年从河南逃荒过来的,父母被饿死在逃荒路上了,孤苦伶仃,流落这里。村里人看他人诚实又勤快,就准许村边上的果园里搭了一个棚子,算是讨了活命。还好,这个张四有编篾席子、簸箕、笼子、耙子的手艺,靠做零活和走村串乡篾农具的手艺吃饭,算是讨了活命。几年后,娶了村子里最穷的一户人家的女子,腿和耳朵都有残疾,日子虽不富裕,但也平安和顺。后来,碰上村子搞联产责任制,分得几亩薄田,成了店头村真正的村民。
张四对村里人心怀感激。农闲时,经常免费为街坊四邻修补筛子、席子等,人缘很好,加之他手艺精,腿脚勤快,不出几年,盖了三间新瓦房,说媒的门槛都踩断了,很快娶到邻村队长家里漂亮贤惠的女子为妻,日子越过越红火。
很多年过去了,张四依然在做篾匠,他的两个儿子像泡桐一样高大壮实,日子安稳。不料三年前的秋天里,张四老婆去镇上赶集,横穿大路时,被一辆大货车碾死了,赔了不少钱,加上张四大半辈子积攒的家底,很快给两个儿子买了两院新庄子,娶了妻,生了子。儿子媳妇喜上眉梢,张四却经常对着老伴的遗像发呆。
张四渐渐老了,双腿患了风湿,自个蒙在心里。其实,他这病和这些年风里雨里跪在潮湿的地上做篾匠活有很大关系,可早已分家的两个儿子只顾自己的小日子,不闻不问。去年,病情加重,腿膝盖变形,想伸直动弹一下都钻心地疼,自然不能做篾匠挣钱了。儿子不高兴了,觉得是累赘,你推我,我推你,没有一个愿意给老人养老。后来,村委会出面调解,让轮换伺候,并白纸黑字按了手印,总算使张四的三顿饭和生活起居有了书面上的基本保障。
起先,两个儿子还能遵从调解,老大伺候一个月,完了老二。日子长了,都没耐心了,也不再接老人去家里了,只是顺道过来送一口饭,难免饥一顿饱一顿,冷一顿热一顿。这不,大寒降临,老人患风寒感冒,夜里,撕心裂肺一样的咳嗽声让两邻家听着不忍,过去看了看,给提了壶开水,炕眼里塞些柴火,让冷了赶紧点上。两日后,听不到一点声音了,觉得奇怪,又过去看。结果,张四蜷缩在炕沿下,手里拿着火柴,身子已僵硬。赶紧一路小跑给大儿通报。大儿媳妇一脸平静,和脚下踩死一只蝼蚁一般,轻描淡写地说,死了好,上天享乐了,不受罪了。接下来,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两个儿子从银行各自取出一万元,大手一挥,大操大办,摆大席,宴请街坊四邻。席上摆满了八凉八热,鸡鸭鱼肉,绿肥红瘦,吃是吃法,看是看头。这还不算,还请来周至的大剧团唱大戏,两天两夜,秦声缭绕,好不热闹!
从老家回来两日了,公公电话里说,村里人嘴上抹足了油水,背地里却在叽咕和骂娘,狗日的,活着舍不得花钱养老人,死了葬送那钱,阎王爷都不会饶恕的。
公公的语气里有愤懑,也有很多无奈。我一定可以想象到,戏台上面,戏子水袖轻扬,满脸油彩,咿呀咿呀,戏里戏外,人生几何?而戏台下面,伶仃几个老人,裹着臃肿的棉衣,侧耳聆听,秦腔里的绵长,一点一点舒展他们褶皱的眉头。风从台上刮到台下,刮起尘埃一片。院子里,一张彩条布搭的棚子里灯火通明,满脸通红满身油渍的胖厨师忙活着,几只鱼,扑腾在油锅里被火燎,被生煎。这样的场面,如今在乡下,已是司空见惯了。
责任编辑:马小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