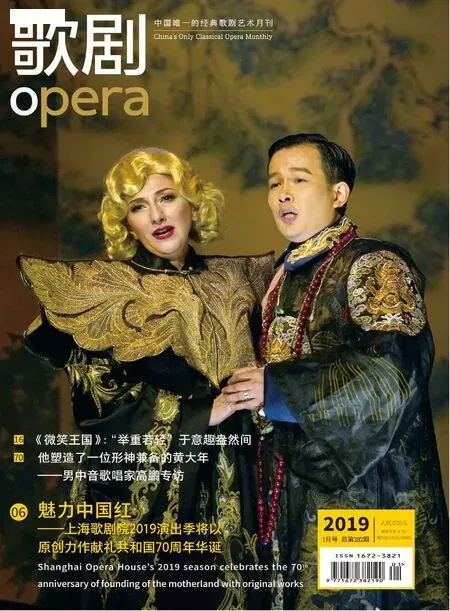《尘埃落定》:从小说到歌剧的再创作
文:栀 子 图片提供:重庆市歌剧院
现在有一种说法,那就是根据文学名著改编创作歌剧,比凭空想象一个故事要容易。因为有文学著作强大的底蕴和丰富的内容,想不成功都难。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纵观中外很多成功的歌剧作品,确实由文学名著改编的成功率会更高一些。但并不是所有的文学著作都适合或容易改编成歌剧。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就在此列。虽然这部小说可读性非常强,很吸引人,但是它的叙述方式、人物设定、故事结构与传统的文学名著还是有区别的。当我们跟随着作家的笔触一行行阅过的时候,也是跟着人物的心理、视角在感受、审视。宏观上看,这部小说讲述的是康巴藏区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一段经历,其实却是作家以一个小范围农奴制度的崩塌,来映照人类社会摆脱愚昧和压迫的历史必然。
歌剧艺术的特点,是不宜选择太复杂的人物和事件来进行结构戏剧的。尽管小说《尘埃落定》的人物相对集中,但是事件发展头绪多,人物年代跨度大,很多事件是从主人公的主观推理和判断生发出来,意识流的成分居多,这些都为《尘埃落定》的剧本创作设置了很多看起来难以逾越的障碍。所以,尽管选择《尘埃落定》为题材进行歌剧创作,会有非常新颖、独特且具有艺术性的视角,但是如何从文学到舞台,以原著的基础而言,难度确实很高。
当然,所有的难点都是因为思维的惯性会囿于原作的束缚,如果索性跳脱出来,那么这种束缚就有可能变为长袖善舞的自由。
歌剧《尘埃落定》中,每个人物、场景、事件似乎都来自原著,但是又与原著有很大的不同。原著中一句看似平常的描述,可以成为剧中相当规模的一场戏;而原著中一些笔墨丰富的人物与事件,在剧中又会变为一句台词或者转瞬即逝的场景一笔带过。编剧冯必烈、冯柏铭从歌剧艺术本身以及本作品所表达的主题立意出发,对于小说原著中的事件、人物进行了重新选摘、简化、重组,生发出的是一个接近原著的“全新”故事。本剧的故事和戏剧结构简单,重点围绕土司制度的消亡和奴隶的解放展开。种植鸦片、开辟交易市场等在原著中占有大量篇幅的叙述描写,在剧中都简化为戏剧事件发生发展的社会背景,而土司家族内部对于权力的争夺、土司“王国”笼罩在被复仇的阴霾下、二少爷以及被土司制度统治的百姓和奴隶的逐渐觉醒等方面,则成为本剧的几个核心事件重点勾连展开。
与相对简单的剧情对应的,是本剧在人物的设置和塑造上所形成的“删繁创简”的单纯。
麦其土司家的傻儿子二少爷,在原著中是贯穿全剧的核心人物,以他作为本剧的男一号顺理成章。但小说中二少爷总给人一种虚幻和不真实的感觉,他看似是麦其土司家族的一位成员,但是他的所思、所见、所为又充满着神秘与超现实的色彩。在歌剧当中,编剧对这个人物重新进行了定位,让这位二少爷走下神坛,变身为我们通常看到的舞台形象非常正面的主人公——纯真善良、对爱情忠贞、对事物有判断的富家子弟。卓玛也不仅仅只是原著中二少爷的第一位“侍女”“人生启蒙导师”,而是成为二少爷唯一钟情和珍爱的女人,正是在卓玛的引导下,二少爷最终觉醒并接受了解放军,因此卓玛也当仁不让地成为剧中的第一女主角。对于其他人物的设定,编剧也有很多新的设计,比如原著中的“塔娜”,只不过就是麦其土司相邻的女土司家漂亮的“公主”,因为粮荒心不甘情不愿被迫嫁给二少爷。但是在剧中,“塔娜”成为最终导致土司家族灭亡的关键人物,在剧的尾声,大少爷被杀,凶手就是“塔娜”,“塔娜”被设计为神秘的复仇者之一。


歌剧《尘埃落定》的剧本创作,基于原作又非原作,虽然看起来“似是而非”,但是原著想要表达的核心思想依然保留,在对于“尘埃落定”这四字的解读上,除了体现出原著侧重的“旧”的覆灭,也更加着重强调了“新”的诞生。同时,剧本非常歌剧化,为作曲家的音乐写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著名作曲家孟卫东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歌剧好听是第一位的,观众爱不爱听,演员爱不爱唱,这对我至关重要。”事实上,作为旋律大师的孟卫东,想写出难听的音乐估计也不容易。但是歌剧的好听和歌曲的好听是有本质区别的,因为歌剧不仅要有“歌”还要有“剧”。《尘埃落定》是一部既有旋律性同时又具有歌剧性的作品。很多藏地音乐元素的灵活化用,让这部作品有了鲜明的民族风情。而独唱、对唱、重唱、合唱等多种形式的戏剧性运用,也让歌剧的音乐更加丰富和立体。剧中二少爷与卓玛的几段重唱、土司夫人临终前的一大段咏叹调等,都给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有一场大少爷因为担心二少爷与自己争夺土司位而欲置二少爷于死地的戏,在激烈的冲突中,奴隶们挺身保护二少爷,这时的音乐以响彻天地的民众呐喊来体现,在众人“啊!啊!”的单字喊唱中,舞台上形成了非常强烈的音乐戏剧对立,在压倒性的气势当中,大少爷灰溜溜落荒而下。这段戏最出色之处,正是没有借用任何外在的因素,而用音乐和演唱充分体现了戏剧氛围。
在扎实的一度创作基础上,二度创作不仅有了充分发挥的空间,同时又对一度创作进一步补充、完善,锦上添花。其实,再好的一度创作,如果没有二度舞台的呈现,都只能是“纸上谈兵”。导演廖向红就好像是把“纸上”的“兵”拉到舞台上,精心排布,打出了一场漂亮的仗。这部剧的舞台呈现是运用写实同时蕴含深意相结合的视觉手法——盛开的罂粟花、藏族风格的土司官寨、远处起伏连绵的高山、富有年代感的着装及市井风貌,都能够把小说本身以文学手法描绘的那种时空状态,恰到好处地以视觉形象活灵活现地展现出来。官寨在剧中,既是最主要的舞台空间,也是土司制度的象征,两次地震代表土司家族为权位争斗引发的心灵震颤,是愚昧、落后的土司制度与现代文明碰撞所产生的阵痛、震动。而官寨最后在战火中毁灭,则象征着土司制度的崩塌与终结。
舞台调度层次丰富,流动性强,舞美实景与多媒体相结合,把一些比较重大的场面如地震、战争等很好地体现出来。本次演出除了二少爷由著名歌唱家王宏伟担任,其他角色、合唱全部是重庆市歌剧院的演员。近年来,重庆市歌剧院新作频出,演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水平也在渐次进步。廖向红原本对于演员的表演就教导有方,这次在她近两个多月的训练和指导下,演员们的舞台感、专注度又有了非常明显的提升。指挥家许知俊执棒重庆交响乐团演出。许知俊的指挥风格沉稳细腻,在他的掌控之下,乐队将音乐的丰富层次和各种情绪都较好地展现了出来。
歌剧《尘埃落定》初登舞台就已经具有了比较成熟的艺术风貌,若要精益求精的话,我想可能就是主要人物在音乐和形象塑造上还需要进一步深入与精准,舞台上个别场景的呈现需要有些微调。
从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到两个小时的歌剧,《尘埃落定》“落定”的过程一定不会太容易。富有创新和开拓的意识,把握每一个环节,夯实每一步基础,尊重艺术家和艺术规律,都是这部歌剧创作带给我们的经验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