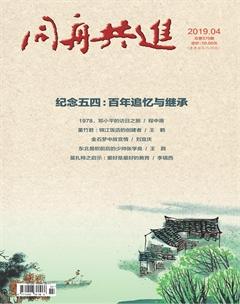戊戌余波在日本
尹敏志
1898年10月25日,康有为乘坐的“河内号”客轮缓缓驶入神户港,船上除了康家九口人外,还有从香港一路陪同的浪人宫崎滔天、宇佐稳耒彦。此时刚过午夜,万籁俱寂。前一晚上喝醉酒,正倒头酣睡的宫崎被船员猛烈摇醒,告诉他有人在外求见,步出船舱一看,外务省书记高桥橘太郎已在巡查汽艇上等候多时,身旁还有一名警察署的官员。两人没有过多解释,只说船上的人不能继续休息:“要乘黑夜上岸。”
宫崎回到船舱,叫醒康有为,帮他扶老携幼乘坐巡查汽艇上岸。“万船灯火海冥冥”,后来在一首诗里,康有为回忆起凌晨一点神户港明灭的篝灯道:“人民城郭梦如醒。”在警察署楼上,他们度过了来日本的第一晚——通宵未合眼,被警察问讯到天明。清晨六点拂晓,康有为褪去长衫,换上西服,仍由宫崎陪同搭火车直奔东京。晚上十点半他们到达新桥站,平山周在这里迎接,并告知康有为,五天前梁启超、王照一行人也已安全抵达。
三个月后在东京早稻田明夷阁里编写《我史》,细细回想从北京逃出,经烟台、上海、香港等地抵达日本的经历时,康有为总结自己总共“身冒十死”,“事后追思,无一生理”,种种机缘巧合集于一身,让他产生了承载天命的神秘体验:曲曲生之,留吾生以待其兹,中国不亡,而大道未绝耶?”他相信拯救万民的任务远未结束,囹圄中的光绪终有复辟的一天,虽然孤悬海外,依然可以继续自己未竟的维新事业。
梅崖先生的援助
梁启超、王照、康有为三位戊戌变法核心人物先后成功逃到日本,背后离不开彼国民间志士、政府官员的合力营救。变法运动初兴时,持亚洲主义立场、主张中日联盟的日本人就密切关注着清国局势。1898年4月香川悦次、井上雅二两名干事牵头成立“东亚会”,声援清国改革,并吸收康有为、梁启超、康广仁入会。6月以近卫笃麿为中心的“同文会”也成立于东京,在上海设立同文会馆。9月21日慈禧太后回紫禁城发动政变,这一噩耗传到日本后,他们立即展开营救活动。9月30日东亚会主要成员在东京万世俱乐部召开紧急会议,十多名主要成员与会,经讨论决定尽一切力量营救梁启超、康广仁。两天后,该会派代表向首相大隈重信递交请愿书,紧接着拜访外务次官鸠山和夫,提出人道主义救援请求。
东亚会的行动紧锣密鼓,影响力亦不容小觑。然而放眼全日本,最早致力于营救康、梁的其实不是他们,而是关西大阪府的山本宪。9月27日,山本惊闻清国政变,立即赶往东京拜访外务次官鸠山和夫,询问康、梁和王照的安危,半月后又上书大隈首相,猛烈抨击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称两国原本唇齿相依,慈禧此番政变“贻欧美可乘之机”,政府却毫无作为,着实令人痛心。这封信的内容后来由《大阪每日新闻》披露,却未收入《大隈重信关系文书》中,也没有在山本宪档案中见到大隈的回信,应该是首相根本没有理会。
山本宪字永弼,号梅崖,1852年出生于高知县,早年当过小学教员、电信局技师、军人、报社记者,1885年因参与自由民权运动被投入监狱,三年刑满释放后为维持生计在大阪开设“梅清处塾”,招收生徒,传授儒学。戊戌变法前一年山本宪曾游历清国,他在《燕山楚水纪游》中描述北京“城郭邑里、园池寺观,莫物不壮大,而莫物不败坏。其壮大可以征明以前之盛,其败坏可以验清以后之衰也”,他认为清国的人心、风俗、制度各方面亦已败坏,甚至“将举国败坏焉”,非下决心变法不可扭转。临回国前在上海的一场宴会中他得与梁启超同席,虽然没能搭上话,但却对梁留下了“年未壮,文名甚高”的深刻印象。
戊戌年春,康有为族兄康有仪以四十岁“高龄”来到日本留学,7月拜入山本宪门下,每日苦学日文,课余以译书自给。有趣的是,前一年年末康有仪之子康同文刚入学梅清处塾,父亲竟然成了儿子的师弟。通过这两位父子生徒的关系,在政变刚发生的一个月内,山本宪得以迅速了解清国的最新情况。据9月27日康有仪的来信,保守派大肆钩捕康梁,索其项上人头。然而,梁启超被捕一事实际上是假消息。据日本大使馆代理公使林权助回忆,慈禧发动政变当天下午2点左右,他正在使馆内和伊藤博文吃饭,梁启超忽然闯了进来,“颜色苍白,漂浮着悲壮之气”。因为双方言语不通,梁示意林拿纸笔来进行笔谈,因为速度太慢,中途又换成翻译。梁最开始准备“三日内即须赴市曹就死,愿有两事相托”,但伊藤为中华惜才,觉得这样白白送死无益,就和林公使好言相劝。翌日梁启超剪掉辫子,换上猎装,在郑永昌領事、平山周等人的护送下潜往天津。因为保密工作做得很好,连亲朋故旧都不知道梁启超已经获救。28日山本宪还从康有仪处得知,康有为离开清国后必将来日本。得到这个关键情报后,10月21日山本宪在大阪备一亭召集同志,宣布成立“日清协和会”,为康有为来日后的中日提携活动做准备。
康、梁、王到达东京后,29日山本宪携康有仪一同上京,与三人会面。清国亡命客们对屡次出手相救、现在又特意赶来的山本感激不已,此后对他推心置腹,几乎知无不言。山本宪档案中保存着一封康有为7月19日变法期间致康同文的信,可能是由康同文转交给山本的,信中康有为说光绪帝现在力变新法,“于我言听计从”,自己现在奉旨专摺奏事,所受之信任为本朝绝无仅有,“外论比之谓王荆公以来所无者,此千年之嘉会也”。然而来日本后,康有为发现日本政府虽对他礼遇有加,每月提供丰厚的生活费,但似乎毫无兴趣听取他的政治主张。
12月8日梁启超致信山本宪,告知康有为在此已经一个半月,只见到了胜海舟、近卫笃麿、副岛种臣等少数几位政界人物,“其余各子,求见而未得外,此诸公多未修谒,因不审住居也。若先生能一一示之,并以书绍介,幸甚。”只是山本宪自己也不过一介布衣而已,对于这个要求自然无能为力。山本曾劝梁启超在与人交往时应有所取舍,“恐为滥交之累”,梁启超则回复目前身不由己,“虽然仆之来贵国也,志在诵诗读书,友天下之士,其势不能不多所接见”。
在日周旋
梁启超所说的“势”,是指被软禁的光绪帝目前形势危急,别说皇位难保,连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国内改革派的力量已经被全面整肃,此时他能做的只有效仿明末清初黄梨洲、周鹤芝“日本乞师”之举,借外国力量向保守派施压,警告他们不要肆意妄为。
还在亡命途中时,康有为就向日本政府传达了这一请求。10月1日宫崎滔天致信犬养毅,告知康目前安全抵达香港,寄寓警察署中,自称离开北京时带着光绪帝的衣带诏,切望日本出手救皇上。对此宫崎毫不客气地评论道:“我认为康借日、英之力,再度拥立天子之意甚明。对中华而言此举实是愚策,徒开外国干涉之端。然今日之情形暂且勿论其是非,先予以周全之保护,使其安全抵达日本为宜。”犬养读后,又将此信转寄大隈首相。
康有为自然不知道宫崎背后对他的这番评价。刚在东京安顿下来,他就开始从四书五经中寻章摘句,向日本人宣传营救光绪帝的合理合法性。康预言慈禧太后就是西汉的吕雉、唐代的武曌,终将重蹈覆辙,导致天下大乱。从三纲观念来看,慈禧太后虽是同治帝的生母但不是嫡母,“于今上则为先帝之遗妾耳”,因此她与光绪根本就不是什么母子关系,而是君臣关系,此次慈禧太后所发动的政变也不是什么“训政”,而是以下犯上的废立篡位。康有为向山本宪倾诉道,他坚信日本与中国“同教、同文、同俗、同种、同文,在地球万国,未有若贵国之亲者也”,所以这番“三纲大义”其他国家的人都听不懂,唯有日本是知音。在日本的康门弟子也异口同声,在很多场合都重复上述说法。
11月27日,梁启超在东亚同文会(为便于取得日本政府资金支持,月初东亚会、同文会已合并)成员柏原文太郎、中西正树的陪同下拜访近卫笃麿,作申包胥秦庭之哭,近卫却在当晚的日记中冷淡地写道:“我不了解中国之内情,怎能没有顾忌。从此次政变发生的样子看,可疑之处甚多,决不可轻率行事。否则想为东亚缩短祸期,结果却可能适得其反。当下诸国相互窥隙之际,最须慎重。”他从本国的自身利益出发,担心日本轻易介入会给英国、俄国等列强可乘之机。
正如近卫所言,对于戊戌政变后的东亚政局,日本政府有自己的情报来源与考量,不会相信清国亡命客的一面之词。就在不久前的11月5日,特命全权公使矢野文雄、书记官林权助等一行十多人赴故宫仪鸾殿拜谒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他们传回来的消息,与康、梁、王的说法存在不少出入。从矢野发回国的报告上看,当天慈禧坐在殿内中央最高处,“精神跃如,音度浏亮”,光绪则坐在她的左下方稍低处,“龙颜苍白,面瘦如玉”,看上去身体衰弱。两人都与日本公使亲切交谈,看不出什么异样,慈禧还当场夸奖“贵使臣的名声甚好”。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矢野认为慈禧目前只是垂帘听政,没有其他企图。除了矢野外,当天另一名团员井深彦三郎也认为太后与皇帝没有交恶,弑逆说、废立说、幽闭说皆不可信,这名东亚同文会的会员甚至相信,两个月前太后发动政变情有可原,主要是因为康有为的变法太过激进,侵犯到了大部分人的利益。在随后与庆亲王面谈时,矢野文雄建议清政府最好对外宣布今后不会走守旧路线,也不提倡排外主义,政务次官都筑馨六还嫌他说了不该说的:“我认为应以我邦之利害为唯一的标准,好好利用此次(清国政变的)机会。”
平心而论,矢野使团的上述看法不完全准确,多少有被清政府的表面工作误导的迹象。但考虑到1898至1900年间日本国内政局不稳,大隈重信、山县有朋、伊藤博文内阁依次更迭,这种小心谨慎也不无道理。此时以青木周藏外相为代表的高层更倾向与清政府保守派合作,对于康梁的主张不感兴趣。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康有为来日本以后,大隈、山县、青木等实权人士都没有与他会面,与他打交道多的是在野政客、中下层官员及大陆浪人。
由于迟迟得不到日本政府的积极回应,梁启超在1899年1月30日再度上书大隈首相,连发两声悲鸣,向大隈提出两点请求:一是让矢野文雄大使继续向清政府施压,“言苟立新君,则日本必不认,则彼顽固者,或有所惮”;二是大隈本人亲自致信湖广总督张之洞,“劝其当待正义,勿徇伪命也。张氏本大吏中最可语之人,向与改革派相提携。启超及殉难六士中之杨锐、谭嗣同,皆其所为荐也。政变以后,畏罪避祸,乃大反其平日所为,以媚政府。”
在康、梁心目中,政变后改变立场、背叛朋友的又岂止是张之洞。梁启超曾对山本宪痛骂曾经的维新同志汪康年,指责他在政变发生后“即于其所立《中外日报》中,日日颂扬伪后,谓为四千年未有之圣母。颂扬政府,谓为知时。诬谤一切改革当人,谓为急激。其意不过欲图自免而已,血性男子,岂可如是!”由于汪康年是钱塘人,梁启超对他的厌恶上升为地域歧视,称浙江、江苏两省人都不愿冒死以对抗当道,他们的实务其实与救国无关:“不过为稻粮谋耳,是江浙人之性质也。”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本邦最可用者,湖南、广东之人,陕西、四川、云南等次之”,這些地方人的共同特征是淳朴沉毅,平时不善言辞,木讷有若村夫,但关键时刻却可以任大事、应大变。梁启超还借用日本幕府末年长州藩、萨摩藩结成萨长同盟,联手发起讨幕运动,开启明治维新伟业的例子云:以湘拟长(州),以粤拟萨(摩),未敢多让也。”此番大言犹在耳,广东籍华人圈中就发生了一连串分裂与风波。
办报、办学
除了四处游说和投书外,康有为、梁启超还通过办报和办学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争夺戊戌变法的历史解释权。当时全日本华人最多的城市是横滨,其主体又是经商的广东移民,他们大多聚集在狭窄的元町中华街内,甲午战败后受到日本当地居民的巨大压力。能否得到他们的支持,关系到每个华人政治团体的生死存亡。由于康、梁皆考取过功名,又有光绪帝前顾问的耀眼光环,横滨华人迅速为之倾倒,用政治支持和捐款力挺两位“帝王师”。然而这些占用的,却是原本该属于孙中山的资源。
横滨华人纷纷弃孙投康,最典型的是冯氏兄弟。1895年11月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被迫逃亡到日本,无处下脚,横滨市文经商店老板冯镜如就将他还有同伴陈少白藏匿在家中二楼。正是在这个位于横滨山下町五十三番地的逼仄阁楼里,孙、陈两人创办了兴中会横滨支部,推冯镜如为会长,胞弟冯紫珊为干事。虽然在清政府的压力下这一组织仅维持了十个月就被迫解散,冯氏兄弟仍然是孙中山在横滨最重要的赞助人。
然而风水轮流转,到1899年时,冯镜如、冯紫珊转而觉得康、梁的政治主张更合胃口,对正打算大展拳脚的康、梁来说,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和普遍依赖“三把刀”——即拿剪刀的裁缝、拿菜刀的厨师、拿剃头刀的理发师——谋生的在日华人不同的是,冯氏兄弟经营的是技术含量更高的印刷与出版业,且综合实力之强劲,足以支撑横滨与东京并列,成为晚清海外华人两大传媒业中心。
在冯氏兄弟的支持下,1898年12月23日梁启超在横滨发刊《清议报》,自任总纂述,康门弟子麦孟华、欧榘甲辅之,由冯镜如任总理。考虑到日本东亚会、同文会背后的支持,创刊号上梁启超执笔的《清议报叙例》试图在民族主义、亚洲主义之间寻找平衡点:一方面希望《清议报》“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呼吁四万万同胞团结一致,同时也主张全体黄种人联合,奋起寻求亚洲自治。在表达了对捐款人的谢意后,梁启超期待报纸能够“交通支那、日本两国之声气,联其情谊”,“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
这份双周刊包罗万象,囊括中外新闻、日欧论说、中国哲学等多个领域,文笔晓畅,发行量很快就突破了四千份。在1901年10月被迫停办前,谭嗣同《仁学》、章太炎《儒术真论》、梁启超《戊戌政变纪事本末》、伯伦知理《国家论》、加藤弘之《各国宪法异同论》等等,都是在横滨元居留地一三九番地化身千万,不仅风靡日本华人圈,还被偷偷带回国内。1900年正月,闽、浙、粤各省督抚联合发布公告,悬赏重金捉拿康梁,并严禁民众购买或阅读《清议报》,称其“种种悖逆情形殊堪发指。”
康有为刚到日本时,犬养毅、大隈重信曾希望他与孙中山见面,商讨联合事宜,却被康以不与逆党暗通款曲为由一口拒绝。而到1899年时日本的康派和孙派已经势同水火,双方各自的机关报,即横滨的《新民丛报》和东京的《民报》各执一词,论战持续了将近十年。
教育领域是双方的另一个战场。1897年秋冯镜如、邝汝磐等横滨侨商与孙中山商议,准备在横滨创办“中西学校”以培养人才。当邝汝磐拿着孙中山的介绍信来上海找康有为,请他推荐几位老师时,康一口气提名了几位弟子,包括未来成为第一任校长的徐勤。这批新老师刚到就彻底颠覆了孙派的教学理念,甚至连校名都被改为“大同学校”。众所周知“大同”是康有为最核心的理念,康派在上海经营的出版翻译公司也叫“大同译书局”,孙派创办的学校就这样被康有为的弟子们据为己有。
1898年初徐勤就任大同学校校长,并列名东亚会会员。3月18日学校正式开学,首批招收了一百多名学生。学校既提倡国际化、现代化,又不放弃尊儒,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幅刊载于1898年《东京每日新闻》的图画显示,课堂上男女混坐,穿着三件套西装的老师正站在黑板前讲解,身前摆着地球仪,身后挂着孔子像。地球仪、男女同校、孔子像和老师身上得体的西装,这些都是课堂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保皇派的元素在这里随处可见,比如被当做教材使用的康有为诗集、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还有每间教室孔子像两旁悬挂的康氏手书对联:“同种同文复能同教相联未许西欧逞虎视,大清大日从此大成并合遥看东亚庆麟游。”
孙中山派当然不能坐视康有为派为所欲为,他们试图夺回学校的控制权。学校暂时陷入停顿,没法再继续运营下去。犬养毅和大隈重信密切关注此事,不但扮演康、孙两派间话事人的角色,还给予学校资金支持。而犬养毅的政治立场更接近于康派,他是东亚会最早的成员之一,向来主张清日联盟。客观上来说,这一维持现状的做法对康有为派更有利,自此之后,革命派势力再也不能踏入学校半步。为了以示感谢,大同学校授予犬养毅名誉校长的头衔,犬养毅亦欣然接受。
在彻底失去了对于大同学校的控制权后,1908年孙派在横滨建立了另一所学校,即后来的“横滨华侨学校”。华侨学校是大同学校的死敵,处处针锋相对,它除了招收同盟会及后来国民党成员的在日子女外,还特别允许工人家庭子女入学,并削减贫苦学生的学费,而大同学校往往将他们无情地拒之门外。
一方面是属于康有为派、富家子弟上的大同学校,另一方面是属于孙中山派、穷小子上的华侨学校,这两种形象在横滨渐渐根深蒂固。两校的学生通常在毕业前都老死不相往来,若恰好在街头狭路相逢,则要相互詈骂,偶尔大打出手,令路过的日本人看得目瞪口呆。
离开日本
在康有为来之前,日本国内就不乏反对的声音。比如同是亚洲主义团体,同文会的看法就与东亚会有分歧,1898年10月16日该会开会讨论此事,会长近卫笃麿在日记中记载:像梁启超那样直接投奔日本的尚可,但像康有为那样曾受英国之保护,后来又转托日本的,其真实意图极为可疑。从这次事变的结果来看,康的策略恐怕是成则自收其功,败则归罪日本。故虽可以给康有为一时之救助,但不能让他长居我国,与各方人士接触,以后最好将他礼送英国或美国。这是今晚与会者大多数人的意见。”即准备尽快把这个烫手山芋甩给别人。
12月12日,同文会另一位会员宗方小太郎执笔的报告也认为,日本如果允许康有为长居,很可能引发清国人的恐惧心和猜疑心:“康有为等人逃亡到日本以来,怀抱为己复仇之意志,屡屡向内地旧知飞檄,教唆他们举事。我认为日本为了庇护此等少数亡命客的结果,其实是伤害了大部分清国人的感情,就对清国方面而言,这可以说是很不讨好的。”
文中“伤害大部分清国人感情的”,主要是10月康有为逗留香港期间通过媒体发表的一系列攻击慈禧太后、宣称光绪帝厌恶她的言论,张之洞对此极为恼怒,他通过上海代理总领事转告日本青木外相:若不驱逐康有为,则两国以后的军事合作免谈。后来清政府还派刺客刘学询、庆宽潜入日本,伺机暗杀康有为,12月矢野文雄大使得到情报,显示慈禧太后命令清国驻日公使“运用一切手段将康及其党人捕拿或暗杀”。
随着来自清国的压力越来越大,为防止出现更严峻的外交危机,12月16、20日,日本外务省翻译官楢原陈政两次以个人身份拜访梁启超,劝他顾全大局,劝说康有为主动离开日本,旅费日本方面可以负责,但被梁启超拒绝。月底犬养毅与伊藤博文商议后决定采取折衷方法,康有为必须离日,梁启超则可以留下。作为康、梁在日本最重要的保护人,犬养毅的这番表态极为关键,这意味着康有为离日已经进入倒计时。
1899年1月19日,近卫笃麿再次接见梁启超,重申楢原陈政、柏原文太郎、伊藤博文、大隈重信和他自己的意见一致:“这不是胁迫,而是诚心诚意为康有为的将来考虑而提出的建议。”2月12日伊藤博文致信第二次就任首相的山县有朋,将此事前因后果做了详细汇报,主张让康有为前往美国。
但即使到了这个地步,执拗的康、梁仍然不愿屈服。最后日本政要们只好决定让山本宪出面——他的官方色彩最弱,也是康梁在日本最为信赖的人之一。如同冥冥之中有天意一般,这个最早奔走四方、积极营救康梁的大阪布衣,无意中又成了促使康有为离开的最后一环。3月14日山本赴东京与楢原陈政会面,当楢原说完要求后他犹豫良久,只说了一句话:“穷鸟入怀,猎夫不忍杀之。”回到大阪后,山本宪将自己的这番回复告知康有仪,康有仪又转述给康、梁、王,三人听后大为感动,通过康有仪表达“辱荷竭力周旋,感不可言…以旧交之故,而情义兼尽”之意,下决心不再让朋友为难,相约一起离开日本前往美国。出于各种原因,最后成行的只有从日本外务省拿到一万五千日元旅费的康有为,梁启超和王照则以旅费不足为由继续待在日本。
1899年3月22日樱花盛开之时,“和泉丸号”在横滨解缆,带着康有为横渡太平洋。康在抵达加拿大后寄赠东国诸公七律两首,其中有“大灜万里隔游尘,上野莺华照暮春”,“半岁看花往三岛,盈盈春色最相思”的句子,未见一丝怨尤之态。由深秋至仲春,他在日本前后待了半年左右时间,成功避开了政变后最危险那段时间。
维新的终结
康有为的离开对保皇派是巨大的打击,他们意识到通过外交途径不可能达成目标,必须穷则思变。恰好天高老师远,作为改革派的新领袖,大弟子梁启超转而寻求与孙中山合作。
1899年4月底,梁启超通过冯镜如的中介与孙派人物杨衢云会面。但据冯自由的记载,这次会面双方谈得很不愉快,回来后杨大为不满梁启超,称“康党素来夜郎自大,常卑视留学生及吾党,且欲使吾党仰其鼻息”,又贬低梁虽负大名,却没有什么真才实学,“与之合作,实為有害无利”云云。然而到春秋之交,梁启超与孙中山的来往更密,受孙影响,梁甚至有些倾向于革命,其同学韩文举、欧榘甲、张智若、梁子刚等,主张尤形激烈。”革命派与保皇派的合作方案不久后出台,拟推孙中山为会长,梁启超做副手。对此另一派康门弟子徐勤、麦孟华坚决反对,他们寄信给康有为,告知梁卓如“渐入中山圈套,非速设法解救不可。”康有为阅信后大怒,勒令梁启超立即赴夏威夷办理保皇会事务,梁无奈整装前往,一去就是半年,两派的合作计划就此夭折。
游历诸国后梁启超仍然回到日本定居,眼看着革命派势力日盛,保皇派光焰日衰。清末新政让他们看到了一丝希望,但形势的发展每况愈下:1908年光绪帝身故,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年底南北议和成功,清帝准备逊位,至此维新运动已走到尽头。1912年9月底,梁启超由神户启程回国,十四年的日本流亡岁月终于划上了句点。
10月24日,梁启超写信给长女梁令娴,称自从经天津入北京那天起,都人士之欢迎,几于举国若狂,每日所赴集会,平均三处,来访之客,平均每日百人”,他不得不对见面时间做出严格规定,政要二十分钟,普通人止五分钟而已:“得罪人甚多(架子似乎太大),然亦无法也。”众人纷纷拉拢这位维新健将,是因为进步党、国民党之议会党争即将拉开大帷幕,向来不惜“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的梁任公,即将再度成为弄潮儿。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