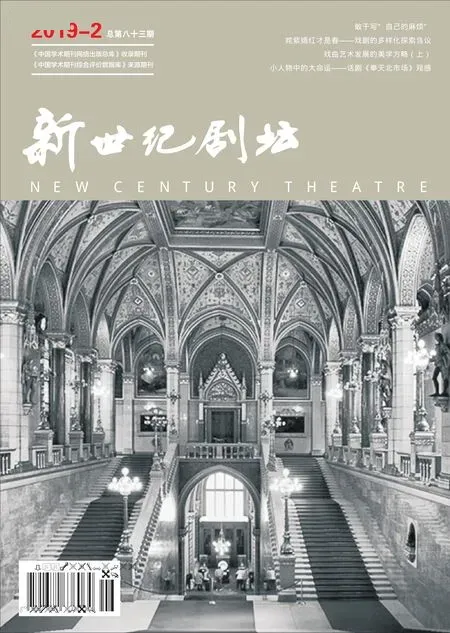写在戏剧边上
——看戏随笔之一
刘恩波

话剧《纪念碑》剧照
小 引
生涯旅途,百事倥偬,唯有戏剧滋味悠悠,令人牵念于心,难以割舍。看戏经年,闪忽已近三十载,幕后台前,往事成串成珠,立体造型,挥洒书卷,想来都别有情怀,遂不揣冒昧,于孤陋寡闻里,略叙看戏品戏一二。
关于《纪念碑》
这出话剧最早看的是剧本译文,由吴朱红女士翻译,笔调奇崛,苍凉遒劲,读后心灵受到极大震撼。战争题材,但又超越战争本身,通向了人性更深层次的把握,其抵达触发的文化语境是发散性的,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
在国话先锋剧场观看《纪念碑》,等于完成了从文字到舞台造型的具体而微的超拔和转换。由衷感谢查明哲赋予了剧本以别开生面的探寻、开掘和重塑。该剧既有“残酷戏剧”的原始爆发力,又有“贫困戏剧”的简约别致,让我们体味到话剧自身强大的气场和能量。废墟,焦土,旷野,尸体,流淌的音乐,袅袅上升的纪念碑造型,母亲和杀人犯的激烈对质冲撞,直到最后时刻的趋于沟通,一出剧获得了多视点多角度的生命张力。《纪念碑》是写实主义的,人物的大幅度开阖的肢体动作,粗放原始的语言表达,舞台布景的高度逼真,尤其是高潮段落对尸体具象化的展示,使得置身现场的观众感受到精神的极度挤压、磨砺和扭曲的张扬,而另一方面它从主题立意上又大大超越了一般传统现实主义拘泥于具体战争环境的有限性,从而把对人性的质疑拷问推广到永恒超越的终极维度,去揭示、印证、勾勒人在历史处境里的复杂表现和生命难题。
关于《初恋》
孟京辉的音乐剧《初恋》很难说可圈可点,但是毕竟差强人意,算是满足了我对孟氏戏剧观的另一层体验。音乐剧既然是舶来品,国人的尝试就可以在立足本土和接轨时尚这两个方面做文章下功夫。何况《初恋》请来了天使,让男女炽热的初恋在尘世和幻境之间来往穿梭切换,品味起来还是跟西方的文化情调有所牵连。再说,“老孟”的追求总是要在涕泪悲欢里寻觅一丝人性的两难和纠结,笑中带泪的效果在这出音乐剧中尽管没有制造出准经典的段落,但是丁洋的“心疼”与黄围脖的“执拗”,还是形成了错位的共鸣。值得推敲的倒是女一号和女二号的人物形象,不是在天国里还吃人间的醋,就是一见钟情得一塌糊涂,很显然,编剧在此笔力不足,立意不妥,没有给我们塑造出个性鲜明一点的女性形象。概而言之,两位亚当还算生猛可爱,两位夏娃则生拉硬扯,多多少少显示了她们的机械、呆板和无聊。
关于《永远的微笑》

音乐剧《初恋》剧照
没有在现场看,是在影碟机里欣赏的,然而它那么棒,彻底颠覆了以往固执的戏剧必须要在现场看的顽固理念。金士杰有你的!看你编导的故事既古典又现代,既嬉皮扯淡又抒情浪漫,既喜剧化,又带上了人性深处的凄凉和悲哀。这是契诃夫与迪伦马特的对话,是黑色幽默与存在主义的对撞拼贴。“天方夜谭也有讲到天光乍现的时候”,人生的梦幻迟早会与冰冷的现实发生扭结和错位的嫁接。
剧中的主人公何来、王大可、伦伦、阿芳、露露,还有伦伦的父亲那个老浪子,现在一闭上眼睛,就好像他们的喜怒哀乐,还在自己眼前徘徊晃荡。这就是戏剧最原始的魔力了。它不灌输,也不宣告。它不故意疏离,也不刻意强加,它就是给你一点痛,再给你一点痒,给你生命的洗礼和来自岁月深处的触及灵魂的摇撼。
“每个人现在这张脸都是自己的故事写出来的”,剧中摄影师何来不经意的一句话,就点亮了沉闷日子里的诗意的火花。《永远的微笑》最牛气的地方大概在于它追求诗意,又解构诗意,追求浪漫,又解构浪漫。这是人性的两难,存在的背反,也是戏剧张力最终极的表现所在。
在戏里,何来的妈妈是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草地、树林、蓝天、大海……大概是她心里永远的故乡,永远的梦想。未经世故和世俗的熏染,但是必经世故和世俗的冒犯。她那经常出海的丈夫在书信里对她说的那些浪漫的情话,何其动听,但其实根本上就是经不起事实检验的谎言,真实的情形是有一天儿子撞到了酒醉的父亲跟欢场女人厮混的场面,天方夜谭必定是梦,天光乍现,人性的真相开始浮出水面。金士杰不是琼瑶阿姨,他有耐力和信心,面对生命的惨淡和荒芜,保持心酸的淬炼与酿造。
谁能留住永远的微笑?
在戏里,何来的妈妈和那个阿芳已经或者将要留住。儿子隐瞒了真相。他妈妈最后走向了水湾,走进了大海。获得了人与自然的归一。那个阿芳如果不被现实套牢,也许还会把发自内心的微笑保存到久远。但代价一定不小。
目前,冠心病作为一种老年疾病,具有猝死率高以及病情进展迅速等特点,通常由心脏供血不足、冠状动脉狭窄以及心肌收缩功能减弱等所引发,能够对患者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1]。现代研究表明,应用他汀类药物能够对冠心病患者的临床症状以及血脂指标进行有效的改善,并有助于减少其发生心血管事件的风险[2]。此研究,笔者将着重分析瑞舒伐他汀和阿托伐他汀在冠心病中的应用价值,现报告如下。
至于其他的人,几乎都带着一颗破碎的心在尘网里挣扎着,寻找着入口和出口,寻找着无望的希望。
露露和王大可是醉生梦死或者及时行乐的典型。他们身上,印证了物欲横流年代“空心人”存在的诸多症结,快乐和消费不是问题,问题是他们的归属在哪呢?露露后来好一点,她在阿芳身上确乎找到了自己丢失已久的纯真。她有所醒悟,这离觉醒的归途已然很近。
伦伦没有父爱,结果是在男友王大可身上寻找替身的满足,而王大可玩儿的是现代多恋症的把戏,你赢不起,也输不起,那你可怎么活呢,这说的就是王大可这类人。伦伦的父亲就是剧中那个老浪子,由老戏骨曾江饰演的,爱过那么多女人,阅世玩世一直玩到人间尽头,却发现生命中最大的遗憾在于没有偿还对亲生女儿的爱。他之所以出钱筹备“永远的微笑”摄影展,无非想给父爱留下最后一点脚注和回音。二十世纪最了不起的大诗人之一奥登在那句著名的诗中写道,“我们只有相亲相爱,否则就该死亡”。这掷地有声的发言,算是指明了功利主义和物欲至上追求狂潮里人心的终极归属所在。
《永远的微笑》,让我们目睹了人类失魂落魄后的心灵寻找,情感投靠,还有信仰的源泉究竟来自何方。
这不是问题剧,也不是伪装的现实主义命题的剧,而是触及到了生命根本情感走向的戏。
金士杰大胆犀利而且有深度地展示了戏剧的疼痛与形而上的迷茫,这才是真正戏剧应该做的,需要做的。
关于《十三角关系》
根据导演赖声川自己的说法,这出戏是向伍迪·艾伦致敬的作品。
“记得大约在1985年左右,现已不在世上的好友杨德昌弄到一卷伍迪·艾伦新片《开罗紫玫瑰》录像带,我们在我台北的家一起看。回想起来,那是影响我很深的一段时间。《暗恋桃花源》就在第二年问世了,而很多年后的《十三角关系》还是充满伍迪·艾伦创意手法的影响。”
影响当然是无所不在的。荷马之后,谁都不再是创世诗人。毕加索说,“最好的艺术家善于偷。”

话剧《十三角关系》剧照
赖声川并不讳言传承和发现,继承和开发的辩证关系。没有规则和前人的手脚不行,但是囿于规则和前人的手脚,你自己就玩不转了。
《开罗紫玫瑰》那种创意手法,就是让剧中人物从电影的屏幕上走下来,来到现实人间去经历一场悲喜命运的的洗礼,这就太有意思了。
“我爱你,你爱他,这叫三角关系。我爱你,你爱他,我求她教我怎么让你爱我,这叫复杂的三角关系”。赖声川用丰富的人间表情和弹性有余的剧情架构的人生悲喜剧,穿透了命运的帷幕,带给我们笑料背后的生命剪影和灵魂的呼吸。
喜剧的骨子里应该是疼,而不仅仅是痒。绝大多数的中国当代喜剧,也就剩下痒了,不痒之痒。《十三角关系》里那个女主播在直播间里开导众生,哪料到自己有一天也会成为被别人开导的众生中的一员。而开导她的又是自己的情敌,这戏核首先就好,不为寻开心而炮制笑料,要知道,麻花拧过头了,吃着也倒胃口,也不开心。赖声川的好,好在喜剧在让人笑的时候,心里可能在流泪,高级的喜剧就是这样。伍迪·艾伦这样,卓别林也这样。从前有个班尼黑尔,追求市井化的喜剧风格,为搞笑而搞笑,为搞怪而搞怪,后来就剩下那些看腻的标志性的桥段,终于演砸了。
《十三角关系》在故事的创意上就体现了好的故事原意中要生发寓意的真正魅力所在。角色的错位,背后是人生的错位,喜剧的错位背后是价值观的扭曲与变形,根本上是精神的错位。当被开导的女主播重新爱上了自己的丈夫,却是以他们两个人身份的置换为前提的,一个成了女佣,一个成了水电工,然后这两个人擦出了爱情的火花,真是啼笑皆非里充满了人性的是是非非,地地道道和颠颠倒倒,不言之言,不堪之堪。可笑好笑的背后是不可笑不好笑的生命逻辑与伎俩。戏剧是逃离现实的出口,梦想是对抗绝望的解药,说这话的人肯定是一位不凡的智者,以此找到通往《十三角关系》的通行证,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关于《安魂曲》
谁说戏剧就一定是为了演出的呢?谁说戏剧就不该在案头上阅读呢?谁说不能上演的戏剧就注定不是好的戏剧呢?别听那些人胡扯!
我读《安魂曲》,就醉过不止一次。要命啊,好戏!
身处外省,没有得风气之先的便利,不能到剧场观赏以色列卡梅尔剧院的精彩绝伦的呈现,但是,编剧和导演汉诺赫·列文的魂灵已经渗透在他的剧本里,目击可以为证,呼吸可以为证。读好的剧本,是生命的深呼吸!
这个戏来自契诃夫的创意,由他的三个故事组装化合而成:一对老夫妇的死;年轻母亲的悲哀;马车夫失去亲人的痛苦。

话剧《安魂曲》剧照 以色列卡梅尔剧团话剧演出
这样的作品注定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的果实,从故事的枝头掉落到地上,被读者和观众捡起来,沉甸甸的,散发着质感的苦涩与芬芳。大地的纯净厚重,带着罪孽一般的烙印与刻痕,人心的贪婪叵测、阴险、狡诈与美好,欲念的层出不穷的变幻,这就是世道,这就是人道,你写出来了吗?列文借着契诃夫的手,为我们点开了存在的迷津。生有生的味道,死有死的格调,爱有爱的遗憾,恨有恨的饱满……
阅读《安魂曲》,几乎有一种福至心灵的美妙,当然那种幸福里面发酵着心酸的成分,那种美妙里面长出了忧患的触角。契诃夫的作品几乎是不动声色的,细微里见证人性的惊悚,命运的落差,这苍凉的悠远的俄罗斯情调,在以色列大师笔下,获得了另一种魔力,另一种再造。
剧中的几个人物都面临着生存的巨大迷失,老夫妇中有一个得了重病,徘徊在生死之际,另一个感到说不出来的亏欠与哀伤;年轻母亲孩子死掉了,母亲的悲痛和绝望,那是无告的只有面对苍天才能有的哭诉情怀;还有那个马车夫儿子没了,可是他找不到一个听自己讲述这件事的有心人……
其实,真正的艺术家是打开人类灵魂密室的那个拿着金钥匙的人。汉诺克·列文在一个物欲横流、良知湮没的时代,为我们讲述了情感的不容践踏,生命的值得关怀,细微心灵颤动的任何一个细节和任何一道涟漪,都会构成艺术的一场风暴。
无人倾诉,也无人倾听,才是最黑暗最可怕的人类顽疾,那么现在当我翻动着《安魂曲》的每一页,就觉得自己沉睡的许多感觉醒来了,诗醒来了,命醒来了,魂醒来了……如果说太多的戏剧让自己麻木,腻歪,反感,沮丧,那么《安魂曲》则是流淌在天使眼角的泪花,是安静地消融在我们心之旷野里的雪花,晶莹剔透,混沌苍莽,无边无际,那是晚祷的钟声吗,那是嘶哑悠扬的小号吗,还是灵魂的不安的喧响?
读着《安魂曲》,不由得想到李泽厚先生的美感三层次说,曰悦耳悦目,曰悦心悦意,曰悦志悦神。上品乃至神品的戏剧,当在第三层次,它是前两者的融汇超拔和提升。
读着《安魂曲》,觉得有许许多多的假大空可以放弃了,那些欣赏中固有的定式和规则可以告别了,那些貌似贵族貌似平民化的伪装的艺术可以弃之如敝屣。
关于《良宵》
1999年东三省第三届话剧节在沈阳举行,有一出剧目是由哈尔滨话剧团演出的,叫《良宵》,获得金奖。时隔多年,在百度上搜索这剧目的信息,结果另一部戏逍堂演出的同名剧目赫然在目。看来,哈话的《良宵》被遗忘了,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如今倘若让我仔仔细细历数该剧的剧情结构,舞台呈现和导演风格,也仿佛很难还原最初的印象了。但是那剧的生命氛围,或者说留存的气息还在。不容低估和抹杀。说心里话,这些年看过百十来台戏,中外古今的都有,大多数几乎没有什么痕迹地就消失了。能够有印记的,就证明了其生命力。
《良宵》贵在细节的传神,还有表演上的张弛有度。辽艺的戏好,但有时候失之于紧,紧张,紧巴巴,紧绷绷,大开大合之间的容量,大气磅礴的气势,容不得舒缓纡徐。北京人艺的戏,追求京腔京调,但偶尔变成了一板一眼的话剧腔,也会感觉雷同和复制的不可救药。哈话的戏,讲究尺度,收束,节制,尤其是《良宵》,就三个人的戏,一对老夫妻和一个老朋友,在一个宁静的晚上,吃顿饭的事儿,却吊住了人的胃口,想起来有点像《洋麻将》,朱琳和于是之的绝唱。都是平易中见功力,质朴里透视着人生的底蕴。《良宵》就三个人聊着聊着,动作性很少,冲突也不见棱角,绵里藏针的那种,竟也显示出戏剧的足够魅力。这是吃透了话剧的内在规律所致。大吵大嚷,大包大揽,大红大绿的东西看多了,有时候小巧精致的玩意更是艺术欣赏所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