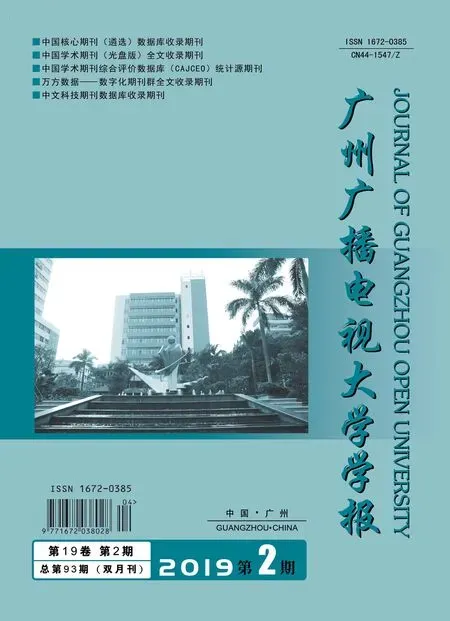互动视角下负面态度立场标记“还说呢”研究
王 悦
(哈尔滨师范大学 文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
一、引言
“还说呢”在现代汉语中使用频率较高,主要有两种用法。一种是用于转述他人话语,如:
(1)田老大道:“我那口子还说呢,家里正抻面条做炸酱面,快下锅了,咱们喝过了酒,回我家吃炸酱面去。”二和微笑了一笑,也没说什么。(张恨水《夜深沉》)
例(1)中的“还说呢”是一个结构松散的短语,其结构和意义都是由内部组成成分简单相加构成的,其中“说”是引述语标记,主要用来转述别人的话语。
另一种是用于标示言者负面态度,如:
(2)冯婆婆道:“夫妻无隔夜之仇,打架吵嘴,那都算不了什么。没有见你这两口子,吵了一回嘴,仇就种得这个样子深。”毛三婶道:“还说呢,都是你这两位老人家千拣万拣,拣了一个漏灯盏!凭我冯翠英这种人才,哪里就嫁不出去,偏是嫁了这样一个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好赌、好酒的一个肮脏鬼。”(张恨水《北雁南飞》)
例(2)中的“还说呢”结构和意义都较为凝固,功能也较为虚化,主要用来标示说话人抱怨、责怪的负面情感态度。例(2)中的“还说呢”是本文的研究对象。
学界以往关于“还说呢”的相关研究,如樊中元(2014)[1]、郭智慧(2016)[2]、罗黎丽(2018)[3],主要集中于“还说呢”的话语功能和形成过程、机制两个方面,但上述研究并未关注到“还说呢”交互语体分布特点,更未结合“还说呢”的互动属性深入讨论“还说呢”的互动模式与人际功能。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展开进一步讨论。
近几年,对立场问题的研究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立场表达形式丰富多样,话语标记是其中的重要手段之一。立场可以分为认识立场、态度立场和风格立场,态度立场指语言形式所表达的个人态度或感觉,包括各种评价和情绪。[4](参看方梅、乐耀2017)参照这一界定,本文认为“还说呢”是一个负面态度立场标记,主要标示言者抱怨、责怪的情感态度。立场与互动性、主观性密切相关。[5](参看柳淑芬2017)本文在全面考察语料的基础上①,从互动视角出发,将重点研究汉语负面态度立场标记“还说呢”的互动模式与人际功能。
二、“还说呢”的互动模式
“还说呢”主要出现在交互式语体中,具有明确的互动属性。在会话序列中,“还说呢”主要分布在应答话轮中,表达言者对听话人、第三方或言者自己的抱怨或责怪。根据礼貌原则中的一致性准则,“还说呢”是一种非顺应性的应答话语,其后续话语多是解释言者负面情感态度产生的原因和理据,形成了“还说呢+释因性话语”这一典型模式②。“还说呢”的引发语也有不同的类型,表达了不同的言语行为。刘虹(2004)关注了引发语和应答语之间不同的匹配关系,归纳出了十五种对答类型。[6]参照刘虹(2004)的分类,我们将负面态度立场“还说呢”的互动模式分为以下几类。
(一)询问—回答
“询问—回答”模式的引发语由疑问句充当,表示交际的一方向另一方索取信息。“还说呢”及其后续话语对听话人的疑问进行回答的同时,也表达了言者抱怨、责怪的主观态度。
(1)李:“诶,老刘,昨晚儿没喝多吧?”刘:“还说呢,非灌我,回家就全吐了。那么好的东西,一点儿也没剩。多可惜啊!”(《编辑部的故事》)
(2)他笑了半晌,然后问我:“你找到袍子了吗?”“还说呢,找到了然后又丢了。”我答道。“这怪不得你啊,世间之物就是这样来来去去。”(玛哈公主《图拜与苏丽娅》)
例(1)中引发语是李对刘昨晚情况的询问,应答语中刘不仅对李的问题进行了回答,也表达了对李昨晚行为的抱怨和责怪,“还说呢”就用来标示这种负面的情感态度。例(2)中言者不仅对对方的疑问进行了应答,还用“还说呢”标记言者自责的负面情感。
需要注意的是,反问句也可以作为引发语要求说话人进行应答,反问句虽然是无疑而问,但是依据其表面的语言形式,我们依旧把它归入到“询问—回答”的互动模式中,如:
(3)“你们不是刚刚上过北海吗?”“还说呢”韵梅答了话:“刚才都哭了一大阵啦,二爷愿意带着他们,胖婶儿嫌麻烦,不准他们去,你看两个小人儿这个哭哇!”(老舍《四世同堂》)
例(3)中问话人通过反问句表示不希望两个孩子去上海,答话人通过叙述两个孩子哭闹的行为,间接表明了两个孩子非要去上海的意愿,也对问话人进行了回应。言者用“还说呢”标明了对两个孩子的抱怨。
(二)陈述—抱怨/责怪③
“陈述—抱怨/责怪”模式的引发语是交际的一方陈述某种情况或观点④,应答语用“还说呢”及其后续话语表达言者对某人的抱怨或指责。刘虹(2004)指出,当引发语为陈述时,言者进行陈述是优先的应答方式,质疑、否定等都是非优先的应答方式。[7]可见,“还说呢+释因性话语”是一种非优先的应答方式。
(1)马伯乐说:“等他们上了洋车,才发现一只大箱子不见了。”太太说:“还说呢,那不是你提着往车上扔嘛,你不是说,扔上去一个算一个,多扔一个是一个,也不知道你哪来的那么一股精神,一听说逃难,这就红眼了。”(萧红《马伯乐》)
(2)“最近我们好象比较疏远。”“还说呢,你男朋友来了,他都不让你腾出时间来陪我们。”(亦舒《一把青云》)
例(1)中马伯乐先陈述了他们上了洋车后的情况,太太将造成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归咎于马伯乐,“还说呢”标示了太太抱怨或责怪的负面态度,“红眼了”等负面性话语也为此提供了证明。例(2)中参与交谈的一方先发表了自己对说听双方关系的认识,言者用“还说呢”表明了对第三方的不满和抱怨。
值得注意的是,在筛选的合格语料中,还存在引发语是某种评价的情况。刘虹(2004)认为评论型语句的应答方式与陈述型语句的应答方式比较接近,所以评论型对答和陈述型对答可以归入到一个模式中,统称为陈述。[8]
(3)“不会有事的,明威一向很懂分寸。”“还说呢,你知道现在外头都在传说些什么吗?”麻麻很不高兴地说:“明威最近常跟一个住在邻镇的女孩子在一起,也不避讳别人的眼光,两个人还经常骑着单车在镇上招摇。”(林如是《十七岁的纯情》)
例(3)中参与言谈的一方先对明威进行正面评价,而麻麻用“还说呢”和反问句表达了对听者评价的反驳,表达了言者负面的情感态度,从而构建了与听者不一致的立场。
(三)抱怨/指责—争辩/反驳
“抱怨/指责—争辩/反驳”模式引发语是参与言谈的一方对另一方的抱怨或指责,应答语是言者通过“还说呢+释因性话语”的典型模式来对听者抱怨/指责进行争辩或反驳。刘虹(2004)认为指责这一言语行为优先的应答方式是道歉,争辩等言语行为是非优先的应答方式。[9]由此可见,“还说呢+释因性话语”这一应答结构是一种有标记的形式,其中“还说呢”标示了言者抱怨或指责的负面情感态度。
(1)晚香用手搓着鼻子,睁眼醒了过来。一见凤举站在面前,不由得伸了一个懒腰,站起来道:“走进来了,也不言语一声,吓了我一跳。”凤举道:“还说呢,坐在这里就睡着了,炉子里火是这样大,稀饭一熬干,烧了房,我看你也不会知道。”(张恨水《金粉世家》)
(2)“还是昭蓉好,哪像你!哼!”家璐顺势勾住昭蓉的臂弯,这才抱怨道:“你们两个好慢才来啊!我等你们等好久哪!”“还说呢,我的研究工作还没做到一个段落就提早跷班了,昭蓉则是正好没课,可见我对你多好。”文静一脸“你实在不知好歹”的表情道。(紫琳《咕噜月亮》)
例(1)引发语表达了晚香对凤举行为的抱怨,而凤举因为晚香的行为会导致不如意的结果的发生,所以用“还说呢+释因性话语”表达了对晚香的指责。其中,“还说呢”标示了言者对晚香抱怨的反驳。例(2)中家璐先对昭蓉和文静二人迟到的行为进行抱怨,文静用“还说呢”及其后续话语不仅解释了迟到的原因,还抱怨家璐“不知好歹”。同时,也对家璐的指责进行反驳。
(四)道歉—指责
“道歉—指责”的引发语是参与言谈一方对另一方施行了道歉的言语行为,应答语是言者对对方的指责。刘虹(2004)指出,面对一方道歉的言语行为,宽慰和接受是优先的应答方式,指责是非优先的应答方式。[10]言者用“还说呢”标示了负面的态度立场。
(1)似此美慧,定是主人心腹爱婢无疑,便笑说道:“多谢姑娘,先前我实不知来历,望你不要见怪。”紫燕朝窗外天空中,看了一看,微愠道:“还说呢,你如果早点收风,何致被恩主撞上。”(于东楼《蜀山剑侠新传》)
例(1)中参与言谈的一方先对紫燕进行道歉,紫燕没有接受道歉,反而用“还说呢”及后续话语对对方先前的行为或话语进行指责,“还说呢”标示了说话人强烈的负面情感态度。
本文对以上四种互动模式进行了频率统计,频率统计的结果如下:

表1 四种互动模式频率统计
如表1所示,“询问—回答”模式所占比例最高,是“还说呢”典型的互动模式。“道歉—指责”模式所占比例最少,仅有1.19%。我们对这一现象是可以作出合理解释的。基于礼貌原则和面子准则,面对对方的道歉,我们更倾向于接受对方的歉意,这样有助于弱化交际双方的分歧。然而,面对对方的道歉,依然对对方先前的行为或话语进行指责,是一种非优先的应答方式,这样会威胁对方面子,扩大交际双方的心理距离。虽然,“还说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面子进行补救,但是依然改变不了言者不礼貌的言语行为。
三、“还说呢”的人际功能
“还说呢”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和交互主观性,在会话序列中可以标示言者负面的情感态度,也可以构建不一致立场,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补救面子。
(一)标示言者负面的情感态度
语言的主观性指说话人在说出一段话的同时表明了自己对这段话的立场、态度和情感。[11](沈家煊2001)“还说呢”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可以标示说话人抱怨和责怪的情感态度,构建说话人的负面态度立场。通过考察语料我们发现,在“还说呢”分布的典型模式中,“还说呢”后续话语大多为言者抱怨或责怪的原因,其中会明示或隐含言者抱怨或责怪的对象。根据抱怨或责怪对象不同,我们将“还说呢”标示言者的负面情感态度的功能分为三个方面:对听者的抱怨或责怪、对第三方的抱怨或责怪、对言者自我的抱怨或责怪。
1.对听者的抱怨或责怪
“还说呢”多数情况下标示言者对听者的抱怨或责怪,和前文分析的互动模式存在着一些倾向性的对应关系。“抱怨/责怪—争辩/反驳”模式和“道歉—指责”模式中的“还说呢”都标示了言者对听者的抱怨或责怪,如:
(1)小冯说:“好小子,敢背后骂我!”小冯变样了,穿着一身粗布军装,扎着皮带,手里提着一根独撅枪。接着打量小冯。小得说:“好你个小冯,还说呢,你这一当兵,家里什么活都落到我身上,我不骂你骂谁?”(刘震云《故乡天下黄花》)
(2)“对不起,烟烟。我好像让你做的事情太多了。”“还说呢,我都快被你累死了。”(寄秋《冰心戏石心》)
例(1)中“还说呢”后续话语是小得抱怨小冯的具体原因,“还说呢”标示了小得的抱怨的负面情感态度。例(2)中前一话轮的说话者对言者进行道歉,言者对对方先前的要求产生了负面态度,对听者进行抱怨和责怪。
“抱怨/责怪—争辩/反驳”和“道歉—指责”两种互动模式,引发语中的言语行为都是针对言者直接进行的,并需要言者对听者进行直接的、有针对性的互动反馈。所以,在这两种互动模式中“还说呢”都标示了言者对听者的责怪。
“询问—回答”模式和“陈述—抱怨/责怪”模式中,“还说呢”也能标示言者对听者的抱怨或责怪,如:
(3)“对了,妈,您打电话给我干嘛?”“还说呢,妈妈一大早就准备了你最喜欢吃的人参粥,谁知道你床上连个影子也没有,你到底跑哪儿去了?”(岳盈《媚眼杀机》)
(4)“为啥打你?”“尿了裤子。”“还说呢,还有脸?七八岁的姑娘尿裤子。滚下来,墙头踏坏啦!”(萧红《家族以外的人》)
例(3)中“还说呢”表达了母亲对儿子不在屋子里情况的抱怨或责怪,例(4)是“陈述—抱怨”互动模式,在这一模式中“还说呢”表达了言者对对方七八岁还尿裤子这一行为的责怪,隐含了言者对听者的责怪。
此外,“还说呢”还存在变体“你还说呢”,如:
(5)萧金哎了一声说:“都怨我太大意了。”秀芬嗯了一声说:“你还说呢(还说呢),你就不应该让李铁同志在后边掩护!”(雪克《战斗的青春》)
例(5)中“你还说呢”和“还说呢”可以相互替换而不改变句子的原义,都标示了言者对听者抱怨或责怪的情感态度。
需要注意的是,基于礼貌准则和面子原则,说听双方在交际的过程中会尽量避免使用第二人称代词“你”。然而,在用“还说呢”表达说话人对某一对象的埋怨和责怪的负面情感态度时,可以将“你”凸显出来,形成“你还说呢”的形式。第二人称是一个有标记的形式,往往体现了言者特定的交际目的。言者通过突出强调第二人称代词“你”来把听者拉到台上,意在将言者和听者区别开来,增强话语的针对性和语气的强调性。[12](汪敏峰2018)
2.对第三方的抱怨或责怪
第三方指言谈中除说听双方外的对象。“还说呢”在“询问—回答”模式和“陈述—抱怨/责怪”中,可以标示言者对第三方的抱怨或责怪,如:
(1)道静坐起来,紧紧抱住俞淑秀瘦削的肩膀,扳过她的脸孔审视着:“啊,吃胖了一点。你妈妈都给你做什么好东西吃啦?”“还说呢”小俞咕嘟着嘴,忿忿不平地说,“妈妈骂我,爸爸也说我。”(杨沫《青春之歌》)
(2)长安在门口赶上了她,悄悄笑道:“皮色倒白净,就是嘴唇太厚了些。”闹新房的人围着打趣,七巧只看了一看便出来了。进了洞房,除去了眼镜,低着头坐在湖色帐幔里。七巧把手撑着门,拔下一只金挖耳来搔搔头,冷笑道:“还说呢,你新嫂子这两片嘴唇,切切倒有一大碟子!”(张爱玲《金锁记》)
例(1)为“询问—回答”互动模式,“还说呢”标示小俞对自己父母的抱怨,同时对道静的问题进行间接的否定性回应。例(2)为“陈述—抱怨/责怪”模式,“还说呢”表达了七巧对新嫂子的负面的情感态度。
3.对言者抱怨或责怪
对言者抱怨或责怪主要是言者自我的抱怨或责怪,但是这一类型的例子较少,如:
(1)胡凋仁连忙问道:“你这样鬼鬼祟祟的有什么事?”吴卜微道:“还说呢,天天在外头逛,这样内行,那样也内行,今天在阳沟里翻了船了。”(张恨水《春明外史》)
例(1)中“还说呢”一方面引导后续话语对胡凋仁的疑问进行回答,另一方面表现了言者对自己“阳沟里翻船”的自责。
(二)构建不一致立场
“还说呢”可以构建说听双方之间的不一致立场,这种功能多出现在“抱怨/责怪—争辩/反驳”的互动模式中,也可以出现在引发语为反问句的“询问—回答”模式,以及引发语为评价的“陈述—抱怨/责怪”模式中。
(1)李祖平叹了好大一口气说:“好苦哦!又要拍你,又不能被你发现。有时候,看到你的镜头好极了,我们两个赶快架机器,机器才架好,你一转身走掉了!又不能把你叫回来重拍。”“还说呢”刘枫叹了更大一口气:“在荆州古城的城墙上,我们远远地对着你架好机器,刚开始摄影,熊源美拦在机器前,说要先帮你照张相,结果我们拍到熊先生的屁股,等熊先生走开,你也走开了!”(琼瑶《剪不断的乡愁》)
(2)“我不是一直平平安安到现在吗?”沈母看他说:“还说呢,你上衣脱掉给希康看看,那一道由左肩横到右腹下方的刀痕曾经使你差点没命,昏迷了三个月才清醒,又休息了半年才复原,更别提那些枪伤了。”(席绢《吻上你的心》)
(3)“我不觉得我有什么狼狈!”我没好气的说。“还说呢”姐姐叹息的。“你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吗?你生活得像什么人呢?”(琼瑶《水灵》)
例(1)是“抱怨/责怪—争辩/反驳”互动模式,李祖平抱怨刘枫当时的表现,刘枫也对李祖平的表现进行责怪,同时,也对李祖平的话语进行了反驳。二者在交际互动过程中表达了不一致的意见,从而构建了不一致立场。例(2)中儿子用反问句表达了自己很平安的观点,母亲用“还说呢”标示了对儿子的抱怨,通过“差点儿没命”等后续话语表明对儿子认识的反驳。说听双方对儿子的平安这一立场客体进行了不一致的评价,构建了不一致立场。例(3)是引发语为评价的“陈述—抱怨/责怪”模式,“我”先进行自我的评价,认为自己并不狼狈,姐姐通过“还说呢”及后续话语表示对“我”观点的反驳。二者对同一立场客体表达了不一致的意见,构建了不一致立场。
(三)面子补救功能
“还说呢”在会话序列中分布在应答话轮中,其在话轮中的典型模式为“还说呢+释因性话语”。“还说呢”的后续话语无论是对听话人还是对第三方的抱怨或责怪,这些都是违反礼貌原则和面子准则的,会威胁到他人的面子。直接用负面性的话语对引发语进行应答,会和对方产生直接强烈的冲突,扩大交际双方之间的矛盾。“还说呢”具有标示作用,能够标示言者抱怨或责怪的负面态度。同时,“还说呢”也能起到提醒和预示的作用,会让对方在心理上有所准备,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双方冲突,弱化双方的分歧,在一定程度上对面子进行补救。唐雪凝、张金圈(2016)指出,如果说话人无缘无故或无正当理由对听话人作出批评,往往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听话人的面子;相反,如果说话人能够说明自己做出的批评或赞许性言语行为是充分的,那么会在一定程度上挽回听话人的面子,使其更容易接受说话人的评价。[13]“还说呢”后续话语多为言者抱怨或责怪的原因,“还说呢+释因性话语”这一模式正是言者为挽救面子而采用的言语策略。
四、余论
“还说呢”通常出现在交互式语体中,与后续话语共同和不同类型的引发语进行匹配,形成了不同的互动模式,具有较强的互动属性。“还说呢”不负载命题意义,而是标示言者抱怨或责怪的负面情感态度,具有较强的主观性。“还说呢”在一些互动模式中,构建了与参与交谈的另一方不相一致的立场。“还说呢”的标示和提醒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避免说听双方出现直接威胁对方面子的行为,从而缓和矛盾,补救面子。学界对言说类话语标记的研究较为丰富,多数成果是围绕书面语材料进行的,基于互动视角从立场出发对言说类话语标记进行的研究较少。话语标记在言谈互动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它传递的并非话语的命题意义,而是表达对话语理解起引导作用的程序意义,为话语理解提供信息标记。[14](曹秀玲、杜可风2018)可见,从互动视角出发研究话语标记的互动模式与人际功能是有积极意义的。本文的研究恰恰是这方面具体案例研究的一个有益的尝试。
注释:
① 本文的语料选自北京大学CCL现代汉语语料库和北京语言大学BCC语料库。
② 根据对语料的考察分析,我们发现“还说呢”在话轮中的分布位置较为灵活,可以位于话轮之首、话轮之中和话轮之末,也可以单独充当话轮。其中,“还说呢”位于话轮之首是其分布的典型情况,“还说呢+释因性话语”是“还说呢”与其后续话语构成的典型的话语组配模式。
③ 抱怨和责怪功能相近,本文对此不进行区分。
④ 刘虹(2004)指出,陈述表面看来似乎不具有生成应答语的能力,但是语料分析表明,陈述话语也会具有相应的应答语,只不过不会像其他引发语那样,没有应答语会让人感到奇怪。参照李广瑜(2018)可知,“陈述”也可以看作是“以言行事”的一种。由此,我们认为陈述可以看成是一种言语行为,有别于询问、责怪和道歉三种言语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