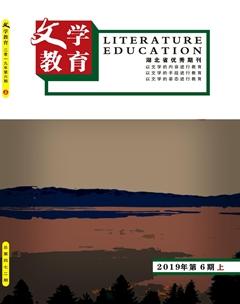《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中的两性特质融合与冲突
内容摘要:在《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中,昆德拉以探寻的目光讨论了多种人生哲理,包括生死、灵肉、两性等。在女性主义视角下看,小说中的两个女性形象——萨比娜和特蕾莎,分别体现着两种不同的性别姿态:对两性特质的融合和超越以及两性特质的冲突。与多数研究不同的是,这里侧重分析两种性别姿态及结局,并由此探讨在昆德拉看来,性别超越实现是否可能。
关键词:两性特质 融合 冲突 性别超越
在学者杨乐云和李欧梵的介绍下,昆德拉进入了中国读者的视野。此后,中国国内掀起了两次“米兰·昆德拉研究热”,学者们分别对这种现象的出现以及昆德拉的作品做了评论和研究,思考角度纷繁复杂。
发表于1984年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是昆德拉的代表作之一,目前学者对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一、对作品中涉及的“轻与重”、“灵与肉”等几对主题的研究;二、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对比萨比娜和特蕾莎的爱情观、人生观;三、小说艺术的研究;四、小说与电影的对比研究;五、作品的诗学研究和音乐性研究。
笔者在阅读过程中,更多关注小说的女性主义问题。关于小说两个女性形象的研究已有许多,总体认为萨比娜代表着女性的自我探寻,而特蕾莎则代表着女性主义的沉沦。笔者认为,尽管二者在形象上有明显的差异,但都在一定程度上透露出两性特质的碰撞,或交融,或形成冲突。本文将从特蕾莎和萨比娜两个形象入手,分析两性特质在二者身上的分别体现,进一步挖掘两性特质呈现背后的性别超越意识及其可能性。
一.从“两性特质”到“性别超越”
两性,即指代表着构成生命形态的不同元素或者两极的男性和女性,二者辩证交融。两性特质,顾名思义,则是男性特质与女性特质。凯特·米利特在《性政治》一书中列举了一部分约定俗成的两性特质:男子代表着积极进取、智慧、力量和功效,而女子则代表着顺从、无知、贞操和无能;男性相对于女性而言,更多意味着暴力、强权,等等。[1]33-77这些特质都可以称之为性别规范,正如朱迪斯·巴特勒所说,“规范是一种尺度,一种制造普遍标准的方式。”[2]51西蒙·波伏娃也曾在《第二性》中提到:“女人不是天生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3]309实际上,这一说法并不限于女性,对于男性而言同样适用。性别就是一种规范,通过这种规范,把人区分出男性和女性两种属性。
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历史里,男性总是作为强于女性的权力机制的存在。凯瑟琳·麦金农提出:“性别是男女不平等被性化后的凝固不变的形式。”[4]54这也就说明存在一种可能,即如果不提前对男女性进行一种定义,男性就不一定对女性构成性别压制,同时为实现性别超越提供了契机。由此延伸,打破性別的二元对立是女性反抗男性权力的一种方式。女性主义者在面对男权的压迫时,有时采取“女尊男卑”的姿态,以此解构男性强权;有时两性各自独立,保持特性;有时双方互取互补。杰西卡·本杰明寻求找到主体之间相互承认的可能性,在她看来,“承认是一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主体和他者认为彼此相互反映,但这种反映并不会使他们成为彼此或是通过投射来消灭他者的他者性。”[5]136简单说来,这种观点里隐藏着一个概念,即性别互补,通过自我和他者的相互认同来达到一种融合和对自身局限的超越,呈现出两种气质。这种承认更进一步讲,是对现有的性别规范的打破。
上文讲到,两性气质的融合来源于一种“承认”,这种融合又进一步产生性别超越,呈现出一种“双性”的审美。“双性同体”又称“双性共体”、“雌雄共体”、“雌雄同体”等,是女性主义思想家关于融合两性特质的完美人性的表达,最早由弗吉尼亚·伍尔夫提出。“双性同体”的理念无疑是对性别二元对立的消解,尽管有人批评伍尔夫这一理念是男权社会里的乌托邦,但仍不可否定这一观点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思考的向度:即从两性特质的对立走向双性融合、实现性别超越的可能。
当然,两性特质的冲突并不因有这一向度而彻底消失,相反,两性特质冲突的大范围存在使得性别超越打上了巨大的问号。在《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一书中,昆德拉并没有明确地否定二者中的任何一者,他给两种向度(即融合与冲突)都以细致的描写,将两性特质的发展趋向作为同“灵与肉”、“轻与重”等一样的命题,留给读者以阐释空间。萨比娜无疑是两性特质融合的代表,而特蕾莎则作为两性特质冲突的容器,二者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从她们的经历和结局看,我们似乎也能窥探昆德拉在这个问题上的情感倾向,这也是本文最后引出的,性别超越在昆德拉看来究竟有无可能。
二.两性特质的融合——萨比娜
1.圆顶礼帽——两性特质流动的象征性展现
弗吉尼亚·伍尔夫曾在《奥兰多》中提到:“一些哲学家会说,换装与此有很大干系……衣服能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也改变世界对我们的看法。”[6]107同样的,圆顶礼帽作为萨比娜一个特殊的饰物,其指涉的意义早已超出了装饰的范围。
这顶圆顶礼帽是她独立与个性的标志。小说对于萨比娜头戴礼帽的场景有反复的描写:“她打开门……除了短裤和胸罩,头上戴着一顶圆礼帽。”“出现了一个只着内衣的女人,美丽而又冷漠,难以接近,头上戴的那顶圆礼帽显得很不协调。”[7]33、79圆顶礼帽作为男性的一种象征,与萨比娜绝美的女性酮体在外表上产生了交汇。显然,在昆德拉看来,这是一种滑稽的结合——“如同为圣母玛利亚像拭去顽童涂上的胡须”。许多论者在谈及萨比娜的帽子时沿用了昆德拉在文中的观点:圆顶礼帽变成了暴力的象征,是对萨比娜女性尊严的否定和凌辱,并得出了男性权力话语对于女性压制的论断。
但在笔者看来,萨比娜对于圆顶礼帽的接受与其说是对于男性压制的顺从,毋宁称为是以一种性别超越的姿态接受两性特质在她身上的交融。文中提到:“她并没有反抗这种侮辱,反而以撩拨挑逗的骄傲姿态对它加以炫耀,仿佛她心甘情愿让人当众施暴一般。”[8]105这一说法充满悖论。萨比娜确实将礼帽作为她的标志以及调情物,却并非抱有“甘于被当众施暴”的心理。小说总体上把萨比娜的形象定义为一个独立的背叛型女性,奉承于男性的性暴力与萨比娜的反抗媚俗格格不入。从另一角度讲,男式礼帽下竟是女性的酮体,这首先成为萨比娜对于男性施欲的阉割和对于男性的调笑;其次,萨比娜既葆有女性身形的魅惑,又接受了带着男性气质的圆顶礼帽对于女性魅力的“入侵”,实现了一种双性共存的外化,从而达到一种性别超越的尝试。
2.独立、征服——女性内核下的男性特质体现
昆德拉在书中写到:“身为女人,并不是萨比娜选择的生存境界……在她看来,对生来是女人这一事实进行反抗,与以之为荣耀一样,是荒唐的。”[9]108萨比娜的想法与传统性别观念恰好相反,突破了性别规范对她的束缚,她选择了轻逸、灵肉分离。这些选择使她的内在灵魂呈现出独立与征服的男性特质。
背叛性是萨比娜的特质之一,也造就了她不同寻常的独立。在她看来,“背叛,就是摆脱原位,投向未知。”[10]110反观她的一生,“背叛”成了萨比娜永恒的“独立宣言”,无所依附令她达成了对于轻逸的追求。萨比娜的独立,涉及物质和精神两种层面,“圆顶礼帽”便是一种隐喻,是萨比娜在经济上独立的宣示,她无需乞求被哥哥霸占的财产。在与托马斯的暧昧关系中,她也不依附托马斯的爱情。这既是对托马斯精神的解放,也是她自我独立的体现。西蒙·波伏娃在论述“独立的女人”时提到:“使女人注定成为附庸的祸根在于她没有可能做任何事这一事实……当她成为生产性的,主动的人时,她会重新获得超越性。”[11]771萨比娜的反对媚俗让她摆脱附庸,其独立特性是对传统女性特质的一种挑战。她在葆有对异性产生吸引的女性内核的同时,自身凸显出来的男性的独立特质又使她超越了女性特质的某种局限。
征服是萨比娜的另一特质。在萨比娜这里,征服是她打破男性性别奴役的手段,是对于性别超越的尝试和追求。表现之一便是女性在性面前的“反客为主”。如果说圆顶礼帽是萨比娜对于托马斯压制的反抗,二人在此过程中达到了一种平衡的状态,那么在萨比娜与另一个情人弗兰茨之间,则更多体现为征服感。性爱向来是被视为男性对女性进行性别统治、占有女性、甚至实施暴力的最直接的方式,而弗兰茨却在和萨比娜进行性爱时选择闭上双眼、陷入黑暗。在他的男性权力最为凸显的时候,却被萨比娜蔑视、厌恶。弗兰茨闭上双眼之时,萨比娜不费吹灰之力地解构了弗兰茨对她实施性别压制的潜在可能,完成了对于男性压制的征服,这种征服感远比对托马斯的压制进行的反抗来得更为彻底和深刻。萨比娜的征服对象不仅是异性,她对同性的特蕾莎也造成了一种迷醉。在一次摄影中,萨比娜和特蕾莎互相展示裸体。毋庸置疑,特蕾莎是惊艳于萨比娜的身体的,她更着迷于发出这种男性命令的女性,“这份疯狂又是如此美妙,因为命令不是出自一个男人的口中,而是一个女人之口。”[12]81可以说,萨比娜身上体现出来的两性气质的融合才是吸引特蕾莎的根源。
总之,萨比娜是小说两性特质融合的典型代表,她包含在女性内核中的男性特质不仅感染了异性,也使同性产生了迷醉感。
三.两性特质的冲突——特蕾莎
1.反复的梦魇——两种特质的冲突
对作为小说“技术手段”之一的“梦的叙述”[13]68,昆德拉不仅高度重视,而且也极为擅长[14]78,这部小说的运用就是典型的一例。此处扼要探讨与特蕾莎、托马斯相关的一些梦。
这类梦可分为如下五种:一、关于猫。“猫”意为漂亮的女人,特蕾莎始终处在对于托马斯女友众多的嫉妒之中。二、关于泳池。托马斯站在泳池监视着特蕾莎以及其他一群女性绕着泳池走,并朝她们开枪。三、关于死亡。特蕾莎在托马斯的指引下上了彼得山上接受枪杀,千钧一发的时刻放弃“自杀”。四、关于坟墓。特蕾莎被活埋,而托马斯每个月会来看她一次,不过逐渐对她产生失望情绪。五、关于野兔。特蕾莎在乡村生活时,曾梦到托马斯变成了一只温顺的兔子被抱在怀里。
五种梦境的共同点是,都隐藏了特蕾莎内心深处对于托马斯强势的畏惧。特蕾莎固守着“性别规范”,使她对于托马斯的爱患得患失。无论是在经济实力还是社会地位方面,特蕾莎都无法与托马斯相称,托马斯甚至是她的“拯救者”。在爱情面前,托马斯的强势对特蕾莎形成了一种逻辑暴力。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提到,即使是梦中焦虑的、不愉快的内容,都是梦者愿望的变形呈现。据此,两性特质的冲突给特蕾莎带去了无法调和的痛苦,情感进一步将特蕾莎对于忠诚爱情以及平等身份的渴望进行伪装,以梦魇的形式展现,而特蕾莎的惊惧则是女性面对男性强势的性别压制时反抗无能的体现。另外,在最后一种梦中虽然呈现出和睦的氛围,但细究之下,托马斯变成兔子的隐喻实际上是特蕾莎对于二人不分强弱的渴望,而这种渴望又衍生自现實的性别压制。总而言之,特蕾莎的五种梦境,都暗喻了男女两性特质的冲突、女性反抗性别暴力时的无助,以及对于两性平等的一种“牧歌式”的幻想。
2.两性特质冲突的消解尝试——出轨及自我凝视
特蕾莎是矛盾的。一方面,特蕾莎顺从自我对于灵肉统一的追求;而另一方面,她对托马斯有着强烈的依赖,且不得不容忍托马斯的不忠。二者形成了巨大的张力,并强化了她的痛苦及逃离托马斯的愿望。在小说中,特蕾莎的反抗主要通过两种手段:一种是与工程师出轨;一种则是不断地自我凝视,欲从中得到一种对于自我存在意义的肯定。
(1)灵肉分离的失败——出轨的惊惧
特蕾莎的出轨是她对于灵肉分离的一种尝试,尽管她努力完成了这个不愉快的背叛灵魂的过程,但仍以失败告终。工程师带给她的并非灵肉分离的快感,而是背叛灵魂、亵渎肉体的愤恨和厌恶。特蕾莎的出轨并非出于类似托马斯的猎艳心理,而是为寻求与托马斯的情感共鸣,企图用肢体的放纵实现理想中的身份和情感平等,以此对托马斯的强势进行一种反抗。
特蕾莎灵肉分离的失败不仅在于无法达到预期身心愉悦的体验,更在于事后纷至沓来的多疑、猜测、无法释然。当特蕾莎意识到工程师可能是警察的伪装时,失去托马斯的恐惧立即袭来,“他们脆弱的爱情大厦会彻底坍塌,因为这座大厦仅仅建立在她的忠贞这唯一一根柱子之上。”[15]202在这恐惧中暴露的是特蕾莎对于托马斯的强烈依赖。西蒙·波伏娃提到:“她把自己献给了他;但他必须完全配得上接受这种礼物。她把每一分钟都献给他;但他也必须时时刻刻都在身旁。”[16]741毋庸置疑,特蕾莎的付出与回报的不对等使她采用极端的方式进行反抗和宣泄,而当她担忧出轨对彼此爱情造成的隐患时,向男性屈服已直接宣告反抗失败。
(2)自我凝视——消解两性冲突的尝试
如果说出轨是特蕾莎对两性特质冲突进行的外在反抗,那么她的自我凝视便是一种向内发出的挑战,企图通过自我寻找消解两性特质的冲突。
镜子作为特蕾莎反观自身最重要的工具,成了她思考灵肉的对立统一、企图消解两性特质冲突的手段。特蕾莎母亲不符合女性气质的行为作风使特蕾莎极端厌恶,以至于她每次照镜子时都想摆脱母亲的影子。正因如此,她才渴望在托马斯那里寻找到属于自己的真正的女性地位。然而当她面对托马斯时,她又陷入了一个新的困境——在托马斯的强势前迷失了自我,找不到自身存在的独特性以及意义。与背叛母亲相似,特蕾莎欲通过出轨的方式摆脱托马斯造成的痛苦。小说中特蕾莎对出轨一事既担忧又带有欲望,当她站在镜子前回想起与工程师的经历时,一种对于自我的欣赏使得她短暂地寻找到主体存在意义。文中说:“她喜欢自己的身体,喜欢自己的身体突然被暴露在外,越贴近、越陌生就越兴奋的身体。”[17]191这是特蕾莎为数不多的自我欣赏,也是一种在两性关系中主动性的体现。她通过对自我存在的肯定,来消解男性眼中女性身体的客体地位。虽然特蕾莎的这次反抗仍以失败告终,但她流露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却不可忽视。总之,特蕾莎的自我凝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她对于母亲的背叛是为了寻求真正的女性特质,而对于托马斯的背叛则是为了寻找两性冲突的消解。
四.绝对的轻逸和牧歌式的宁静——性别超越的可能
上文详细分析了昆德拉笔下两个不同向度的女性典型形象。毫无疑问,萨比娜过着一种自由而无所束缚的生活,特蕾莎则相反,痛苦和矛盾的反复上演编织成她永远的梦魇。然而昆德拉却在小说结尾给了二人戏剧性的逆转:萨比娜背叛完父亲、丈夫、情人、祖国之后,陷入了一种生命的虚空;特蕾莎则和托马斯远遁城市,过上了牧歌式的田园生活。这种结局和二人先前的经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禁引起我们的思考:在昆德拉看来,超越了性别规范的萨比娜和回归性别规范的特蕾莎,究竟谁更有意义?换言之,两性特质的融合及性别超越是否有可能?
(1)萨比娜的绝对轻逸
“萨比娜感觉自己周围一片虚空。这虚空是否就是背叛一切的终极?”[18]144正如昆德拉所言,造成萨比娜悲剧的,正是她执着追求的轻。托马斯、特蕾莎的离开使萨比娜意识到自己对于“重”的需求,甚至开始反思与弗兰茨之间的误解。此时的萨比娜,逐渐远离了背叛的潇洒,而陷入一种越来越抽象、孤独的境地。她身上呈现出来的独立和征服的男性特质,并没有使她超脱、自由,反而使之陷入一种虚无的痛苦。
如果读到小说的结尾处,便会发现,萨比娜前期所呈现出来的男性特质的一面,更像是遮盖住女性柔软内心的一层幕布,而托马斯、特蕾莎、弗兰茨的离开便是揭开这层幕布的手。萨比娜内心仍是存有柔软的,它并非指萨比娜不该有女性特质,相反,正是在萨比娜身上,后期女性特质占据上风,使她身上男性特质的一面受到挫败,“看到薄情的少女紧紧搂着遭遗弃的父亲,看到慕色苍茫中幸福人家的闪亮的窗户时,她不止一次地感到双眼被泪水打湿。”[19]304无论萨比娜如何看待自己的动容,泪水作为最直接的身心反应,它都说明了萨比娜内心对于温暖家庭的渴望。萨比娜对于过往所背叛的追忆,为这种性别超越的可能性打上了一个巨大的问号:若她的独立和征服是一种性别超越的尝试,那么最终的结局与自我反思便是对这种超越的存疑甚至否定。
(2)特蕾莎的牧歌式宁静
尽管特蕾莎做了许多超越自身的努力,但最终仍选择与托马斯回到乡下,过着一种与世隔绝的牧歌式的生活。有研究者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角度对这种结局进行了解析,认为感性的牧歌最终消解了两性冲突。特蕾莎回归乡下后,摆脱了嫉妒、噩梦、灵肉困惑;她不再感到托马斯的强大,而得到了完美的爱情,感到幸福。[20]47-50这种说法固然有道理,但在笔者看来,特蕾莎虽然摆脱了种种痛苦而获得了幸福,本质上不在于她回归了田园生活,而是这种没有外界打扰的生活使之回归女性规范,继续顺从自己对于忠诚爱情、对于家庭、对于托马斯的依赖。与其说牧歌式的田园生活消解了两性冲突,不如说它只是暂时提供了隐藏两性冲突所需的环境条件。特蕾莎仍旧没有真正超越两性特质,超越性别规范,而是在一种符合她性别规范的环境中获得了期待中的幸福。而特蕾莎期望的消解托马斯的强势也仅是发生在梦里,托马斯变成野兔也仅是一种未付诸实践的乌托邦式的幻想。毫无疑问,这种牧歌式的宁静与幸福,不仅没有助益两性特质的融合、超越,反而为性别规范提供了栖息之所。
虽然昆德拉并没有明确表示他对于女性的关注,但通过他笔下的女性形象我们也不难发现,昆德拉对于女性的权力话语、生存处境仍投入了思考。分析到这里,昆德拉对于性别超越这一问题的情感倾向也便不言自明。尽管他塑造了萨比娜这一女性姿态的另一可能向度,但最终仍给予这种向度以质疑和否定。也许在男性中心主义依旧有其态势的情况下,女性对于性别超越的渴望只能暂时是种乌托邦的理想。
五.结语
通过《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中的人物群像,我们不难发现,昆德拉擅长描绘互为对照的形象。除了小说的主题“轻与重”、“灵与肉”互为对照之外,萨比娜和特蕾莎更是代表两种女性之思的向度:萨比娜代表着两性特质的融合,而特蕾莎则是两性冲突的容器。昆德拉用了大量篇幅细致地展现了这两个女性不同的人生经历,并以戏剧性的结尾暗寓了他对于萨比娜和特蕾莎人生的看法,也是他对于二人所代表的不同向度的深度思考。
参考文献
[1]参见(美)凯特·米利特.性政治[M].宋文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33-77.
[2][4][5](美)朱迪斯·巴特勒.消解性别[M].郭劼,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51,54,136.
[3][11][16](法)西蒙·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309,771,395,741.
[6](英)弗吉尼亚·伍尔夫.奧兰多[M].林燕,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07.
[7][8][9][10][12][15][17][18][19](捷克)米兰·昆德拉.生命不能承受之轻[M].许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33,79,105,108,110,81,202,162,191,144,304.
[13]郑惠生.文艺学批评实践[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68.
[14](捷克)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孟湄,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78.
[20]谢永鑫.感性牧歌对两性冲突的消解——《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J].阴山学刊,2012(03):47-50.
(作者介绍:许涵,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