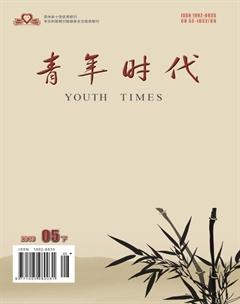域外中华:李氏朝鲜主体意识的萌生
管习化
摘 要:“华夷之辨”是儒家政治哲学的重要内容,朝鲜王朝受朱子学影响颇深,囿于自身的政治地位和民族文化,对于这一命题的接受有着缓慢而又复杂的过程。本文试图以韩儒“子欲居九夷”章注疏为文本,从地理位置、道之有无、夷狄之有君等角度,考察明清易代之际李氏王朝对于“华夷之辨”的接受史。
关键词:接受史;华夷之辨;子欲居九夷;韩国儒者
华夷观在东亚的传统政治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对于华夷观的解释,自古以来大致有两种相互对立的倾向一是重视华夷之辨,强调“尊中华,攘夷狄”二是重视华夷一家,强调春秋大一统。华夷观的这两种思想倾向在秦汉以后,随着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华秩序的建立、发展,不仅影响到中国,同样也影响到东亚各国的国家观念和国际秩序认识。但是到了近代,在西势东渐的冲击下,中华秩序也受到西方万国公法秩序的挑战,最后因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导致了中华秩序的崩溃。在这一过程中,韩国等周边国家的知识分子也开始检讨、清算传统的事大关系。
在日常语言中,人们习惯将“中国”与“中华”等同,但在中国哲学的视域下,二者有本质区别,“中國云者,以中外别地域之远近也;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此处既言明“中国”与“中华”的区别,又提及“华夷之辨”。朝鲜王朝与中国在政治上是宗藩关系,文化上也深受儒学熏染,但对于“华夷之辨”并非主动接受,而是随着历史的进程不断演变。
近年来,“华夷之辨”成为朝鲜--韩国学的一个热点。中、日、韩等国学者从不同视角解析华夷观念的产生背景、内容、流变过程和意义,进一步探讨了“天朝礼治体系”、“华夷秩序”、“华夷情结”、“华夷变态”等一系列问题,其中很多问题都围绕着“华夷之辨”展开探讨。总体上看,韩国方面主要是对“小中华”的论述,以满足本国的政治、文化需求;中国方面的研究则以儒家典籍为中心,多维度阐释其正统地位;而日本方面侧重于文献的整理与细读,将朝鲜的燕行使与通信使联系起来进行研究。
华夷之辨因何而来?上溯至春秋,“夷夏之辨”主要基于“内诸夏而外夷狄”立论。至汉武帝征战匈奴,将农耕文明区拓展到极致时,族群问题亟待解决,此时,以何休、董仲舒为代表的“春秋公羊学派”与史学家司马迁等先后登场,汉儒在“夷夏之辨”之外,又增加了“王者无外”思想。其中,“春秋公羊学派”的“从权而变”影响着后世王朝和儒生;司马迁则在无形中给后人增添了许多想象的空间以及再诠释策略。
一、“边缘进入中心”的朝鲜王朝
就地缘政治而言,大明与李氏王朝建立起了极为稳定的宗藩关系。明太祖朱元璋建国之初即遣使到高丽、日本等国宣诏称:“朕既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宇如一”后来,又指示其子孙:“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明朝对外采取羁糜政策,把朝鲜等列为不征之国,这在宗藩体制下两国关系可见一斑。
即便如此,朝鲜还是十分在意身份上的认同,他们无法改变地理意义上的“夷”,进而从经典中寻求依据。在《四书答问·论语》篇中李惟泰说:“箕子居于辽东九夷之地,其教条风俗,至汉犹存,夫子之时,又当纯固。”丁若镛的《论语古今注》也言明:“君子居之,指箕子言之,非孔子自称君子也。”此处“子”的指代尚有商榷,但李氏与丁式直接化约为“子→君子→箕子”,代表了当时一批儒者的想法,他们将“箕子朝鲜”与“小中华”联系起来,此举既加强了李氏朝鲜与明朝为中心的中华世界体系联系,又给李氏朝鲜提供了一个提高自身在中华世界体系中地位的重要保证。据《肃宗行状》载“予今讲《洪范》书,箕子传道于武王,以叙彝伦,及其受封于东,大明教化,礼乐文物,灿然可述。使我东国,至今冠带,克明五常,以得‘小中华之称者,箕子之力也。”李氏王朝认可的“中华”的内涵仍然是以“冠带”“五常”为代表的儒家礼仪制度,但朝鲜这一“中华”制度得于何处则自有说法,依肃宗言,得于箕子。箕子传道于武王,使中国得以成为“中华”。中国授封朝鲜,大行教化,使朝鲜得以成为“小中华”。由此,这一类注疏认为朝鲜虽是九夷之地,但箕子居此,礼仪尤备,异于诸夷。
二、“异端翻为正统”的朝鲜儒学
明清易代,李氏朝鲜根据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的需要来调整对华策略。在积弊日深的明代中后期,李朝君臣依然向往中华文化,也需要明朝的政治影响力,所以仍然奉行“慕华事大”的原则。满清灭明,成为朝鲜新的宗主国,但李朝心怀悲愤,认为中华故地已沦为腥膻之域,满目疮痍,在《捣椒录》等文集名称以及其中的“胡”、“清主”等称呼不难发现“华夷之辨”已经逐渐模糊。
宋时烈《论语或问精义》:“君子所居则化,道无内外,不择地而处,则虽九夷可居也。”鱼有凤《论语详说》:“当时伤道之不行,中国之陋实起欲居九夷之念,不去亦是顺理,都无私意。”金楻《论语存疑》:“以为道既不行,而欲为退藏计。”这几处提及的“道”,在部分韩儒看来孔子所处的时期礼崩乐坏,道之不存者久矣,而朝鲜却是风正民淳,礼仪之乡,再者李氏王朝以儒学立国,承接朱子,也是斯文所在。申维翰更为激进地强调朝鲜人不仅读中国的四书五经,学周、孔、程、朱之学,不仅是中国人,更是洙泗人,是孔子之嫡传,所以朝鲜已是“诗书中国,衣带中国”。
鱼有凤《论语详说》:“当时中国未尝不被圣人之化,但时君不用,不得行其道耳。”丁若镛《论语古今注》:“孔子以时无明君,故欲居九夷。”金楻《论语存疑》:“妄谓中国,既历试而不可行,则于是又思夷狄海外之地,或有可试之处否,故云然即圣人不言命,不轻弃人之意吁。”此处进一步言明,“行道”必须“得君”,中华虽被圣人之化,但不得位,亦是无奈。朝鲜虽是海外之地,化与不化,为未可知。宋时烈毫不避讳地提出中国人称朝鲜为东夷,名号虽然不雅,但是事在人为,如果朝鲜能出圣人贤人,自可以变为邹鲁,“土地之昔夷而今夏,惟在变化而已”。①以此摆脱“中华主义”,成就一片域外春秋。
我们以韩儒注疏为研究对象,是为了将“华夷之辨”具体化,将“华夷之辨”的接受过程限定在明清易代,是因为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华夷秩序”开始出现动摇,藩属国以自身为视角审视东亚的主体性意识已在酝酿之中。明清鼎革,加速了周边主体性意识的成形。明朝灭亡,权威消失,满清一时难以建立起权威。这样,就造就了一个权威缺失、中原无主的局面,李氏朝鲜重新塑造的“华夷观”和“小中华”意识得以滋长。
注释:
①宋时烈:《宋子大全》,韩国文集丛刊,民族文化推进会刊印,1993年版
参考文献:
[1]费正清.传统与变迁[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2]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3]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4]朱云影.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5]李朝实录.太宗实录[Z].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
[6]严从简.殊域周咨录·朝鲜篇[M].北京:中华书局,1993.
[7]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Z] .北京:中华书局,1980.
[8]中韩文化交流三千年[M].北京:中华书局,1997.
[9]韩东育.“华夷秩序”的东亚构架与自解体内情[J].东北师大学报,2008.
[10]许纪霖.天下主义、华夷之辨及其在近代的变异[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