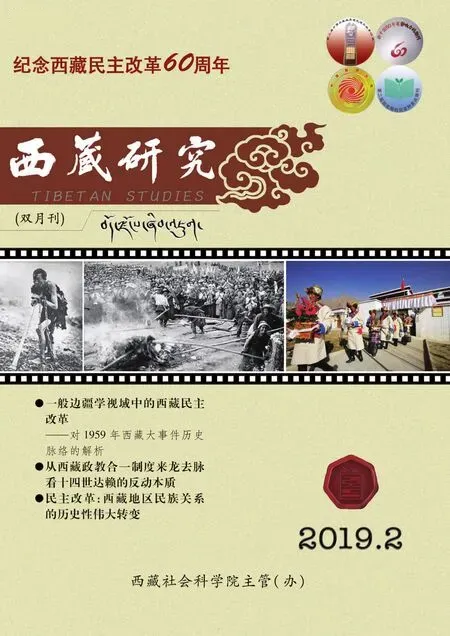记者欧福钦著作《1955年西藏纪行》的话语分析
廖云路
(西藏日报社,西藏拉萨850000)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至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期间,是西藏社会时代变革的关键时期。面对国际社会关于所谓“西藏问题”的各种不利舆论,中央于1955年首次组织了一批外国记者团赴西藏采访报道,苏联《真理报》驻华记者欧福钦便是成员之一。他的采访著作《1955年西藏纪行》见证了当时西藏社会的真实面貌,反映出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经济社会取得的显著进步、中央和西藏工委遵守“十七条协议”,以及西藏进步人士和贫苦大众渴望社会变革的态度,为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的发生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依据。同时,邀请外国记者赴藏采访是中国对外宣传工作中的一次“大胆”尝试,外国记者的报道对国际社会的不实言论进行了澄清,对如何开展好西藏的对外传播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特殊时期的赴藏采访报道
自晚清以来,中华民族饱受内忧外患,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不断滋扰我国边疆地区,妄图把西藏在内的领土分裂出去,而西藏部分上层势力不甘心权力和利益的失去,与帝国主义势力内外勾结,在国际社会制造“西藏独立”的舆论。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十七条协议”,西藏实现和平解放,从而维护了民族统一和领土完整,为西藏地区的发展进步带来新机遇。
出于东西方意识形态差异和对新生社会主义政权的敌视等,西方主流媒体将西藏和平解放大肆曲解为对西藏的“占领”“入侵”,置“十七条协议”不顾而称“侵犯人权”“限制宗教信仰自由”,这些给尚未较多了解新中国的受众造成了负面印象。为展现西藏和平解放后的真实面貌、粉碎国际社会的不利言论,应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邀请,来自苏联、意大利、波兰、法国、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记者组成代表团,于1955年8月至10月间对西藏进行了访问,代表团成员中就有《西藏的转变》作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和《1955年西藏纪行》作者欧福钦。
欧福钦是周恩来总理为他取的中文名,他的本名是弗谢沃罗德·弗拉基米洛维奇·奥夫钦尼科夫。欧福钦生于1926年,1953年至1959年任苏联《真理报》驻华记者。在华工作初期,北京只有12名外国大使和14名外国记者,所以欧福钦有很多机会采访到中国的高层领导人[1]。他在1992年至1996年担任新华社的俄文改稿专家,2001年6月采访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大会,担任《俄罗斯报》政治评论员后,他撰写了大量分析中俄关系、介绍中国改革开放的文章,2007年撰写的《中国的腾飞与俄罗斯的未来》一文获得了俄罗斯“中国年”俄文报道新闻特别奖。半个多世纪来,欧福钦堪称“中国通”,是著名记者、汉学家、知名国际问题专家。
1955年的赴藏采访从北京坐飞机到重庆,由重庆坐火车到成都,再从成都坐汽车经川藏公路进藏。欧福钦写道:“不久以前,从中国内地省份前往西藏还需要骑马沿着令人眩晕的道路走上三四个月……我们在新建的公路上疾驰,可以在7至14天内行驶近2500公里的路程。”[2]7最终,他们花了12天到达了拉萨。当时西藏还没有实行民主改革,依然是封建农奴制[3]。欧福钦采访了西藏工委领导干部、宗教上层人士、农奴、建设工人、科技专家、藏族青年等,记录了西藏和平解放后的种种变化,并将这些见闻汇总成《1955年西藏纪行》一书出版。
学界关于国外记者对西藏民主改革的记录集中在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采写的《百万农奴站起来》一书。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斯特朗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积累的名气,有“纸老虎女士”之称;二是《百万农奴站起来》写于1959年民主改革期间,在新闻发生的时间点上更具显著性。然而,欧福钦《1955年西藏纪行》一书的价值并不能被忽视:一方面,此次采访是西藏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之间的“承上启下”时期,见证了“十七条协议”的执行情况和西藏各族群众拥护社会发展进步的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回答了几年后“为什么会发生民主改革”,其史料价值相当重要;另一方面,此次采访是西藏和平解放以来首次对外国记者开放,采访和传播取得的效果为1959年斯特朗等人的赴藏采访奠定了基础,而此后在重要时间节点上邀请外国记者团赴藏采访报道也几乎成为西藏外宣工作惯例,因此通过《1955年西藏纪行》探讨此次采访报道的成功之处,也是对西藏对外传播的经验总结。
二、《1955年西藏纪行》的话语分析
话语分析是上世纪中叶提出来的语言学研究方法,并逐渐影响到社会学科的研究。话语分析关注的是单词、小句和句子层面以上的语言知识,以及文本间的语言组织形式、语言与使用语言的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的关系。荷兰语言学家梵·迪克在《作为话语的新闻》一书中提出新闻话语图式(见图1),为新闻话语的分析提供了重要线索[4]。
图1:新闻话语图式
梵·迪克认为,新闻话语最明显、最典型的特征之一就是其组装性,受众从各个组成要素中获得对整个新闻话语的理解。借鉴新闻话语图式,可以分析《1955年西藏纪行》的话语特征和功能。
(一)新闻主题
新闻主题也即概述,一般从标题和导语中概括出新闻的主题。《1955年西藏纪行》分为“乘车赴藏”“拉萨的聚会”“念青唐古拉山的牧区”“雅鲁藏布江的源头”“种子和幼芽”五个部分,从作者的记述中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主题:
解放军战士对西藏群众的帮扶。在川藏公路修建和养护工地上,欧福钦记录下解放军战士和藏族群众一起劳作,教他们唱歌,提升劳动干劲的场景。在年楚河谷发生洪涝灾害时,解放军战士为灾民们搭建帐篷,随行医生帮群众检查治疗,并与当地干部一起登记受灾情况,发放赈灾粮食。藏族女孩达瓦布日回忆起1935年在四川甘孜第一次见到解放军战士的情景,她在西藏和平解放后加入了在江孜的解放军后勤机关,为部队购买粮食和运输饲料,后来被推选为妇联主任。军队文工团还邀请藏族群众参加文艺演出等。在和平解放西藏后,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对西藏群众的帮扶集中在应急救援、买卖公平并吸纳地方群众参加工作等方面。
科技工作者助力西藏发展建设。面对当时封建农奴制下极为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中央派出了一批科技工作者进藏工作,改善西藏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欧福钦写道,他们中有医生、兽医、农业学家和地质学家,“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无论是在游牧地区还是在旅途之中,我们常常可以见证响应祖国号召来到西藏的人们的英勇壮举”[2]151。其中,兽医谢玉生给患病的牦牛注射药剂,排除宗教和巫医等因素的干扰,抑制了疫病的蔓延;农业专家试种了80余种农作物,西藏自然条件不适宜发展农业的说法不攻自破;科考队在西藏发现大量矿源地,其中蕴藏着约40种不同类型的可利用矿产等。科技工作对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起到了重要作用。
宗教上层势力对西藏前途的主张。欧福钦等一行记者分别在拉萨采访了十四世达赖、在日喀则采访了十世班禅等宗教上层人士和噶厦官员。十四世达赖认为,“从签订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那一刻起,西藏就放弃了过去那条引向黑暗愚昧的老路,而走上了一条新的、通往繁荣和光明的未来之路”[2]58,他相信中央政府会给西藏各个方面的帮助,全体中国人民灿烂的前景就是西藏人民的未来。十世班禅则认为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得到了严格遵守,西藏人民不仅获得了宗教信仰自由,工、农、商、牧业还得到了极大发展。欧福钦采访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在民族问题上所实行的政策是英明且成功的”。这些史料既反映了“十七条协议”的执行情况,又与1959年以十四世达赖为首的上层分裂势力蓄意破坏协定并悍然发动武装叛乱形成了鲜明对比,充分说明了十四世达赖的反动本质。
西藏农奴和普通群众的生活面貌。西藏在1955年还是封建农奴制社会,这一社会制度下有大量农奴和奴隶,构成了欧福钦采访的重要主题。他从铁匠次仁平措口中得知,寺院和地方贵族要向农牧民和手工业者收取乌拉,无偿地完成一切劳作,虽然次仁平措认为“这种劳役既不正常又不合理”,但也只能抱怨几句。由于宗教因素,铁匠、屠夫等被认为是最低贱的职业,他们还要忍受辱骂。解放军进入西藏后,次仁平措从银行贷款为战士们订做镰刀和锄头,第一次感受到劳动的尊严与光荣。出身贫农的金正诺布的父亲在地震中去世,母亲离家出走,家里没有粮食,还要缴纳税收,后来他跟随解放军修路,不仅免于赋税,还可领取糌粑和工钱。从寺院赎身出来的琼珠先是在地质考察队里担任翻译,学到了地质测量技术后又担任测量员,感受到为祖国工作的担当和荣誉。这些农奴和奴隶的经历带有强烈的对比,反映出西藏社会的改革是西藏各族人民的心愿和历史进步的必然。
除上述主题外,欧福钦对西藏的建筑、工商业、藏医、媒体等领域进行了简要概述。
(二)新闻情景
情景包括情节和背景。新闻的情节经常使用“在……的时候”“与……同时”或其他表示时间、地点的状语引出。《1955年西藏纪行》中有许多情节的描述,如金正诺布在筑路工地上的情节:“每天早上,工作队长将工人们领到工地上,将每10人分成一组并量出一段距离作为他们的工作定额,这就是白天的工作任务。同伴们相互打趣,开玩笑。竞赛意识很快便进入了金正诺布的头脑中。”[2]35又如,铁匠出身的农奴次仁平措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解放军战士的情节:“中午时分,一旁挖地的战士们带着藏族铁匠们去吃午饭。值班战士给他们每人盛了一大碗热腾腾的米饭。在次仁平措看来,作为餐桌美味的米饭,他这一辈子只在逢年过节时吃过一两次。但现在他却吃不下,因为还不习惯使用筷子。坐在饭桌旁,次仁平措有些手足无措。”[2]83在此基础上,欧福钦继续挖掘次仁平措的心理活动,使情节进一步深化和丰富。“次仁平措头脑中产生了许许多多的疑问:为什么这支军队不但不抢劫掠夺,而且购买一件小东西也要付钱,甚至还要自己养活自己呢?!为什么他们来了以后就开始给手工业者贷款,还在市里开办了医院免费提供医疗服务呢?!”[2]85
因独特的自然和人文环境,西藏在历史、文化、制度、社会发展轨迹等方面与内地存在差异,再加上西方社会长期以来的“香格里拉”想象,西藏被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5]。新闻报道中如果不加入背景资料,受众就难以理解,新闻也缺乏说服力。在采访宗教上层人士时,欧福钦多次对政教合一的制度背景进行了介绍:“那时的寺院已经占有大部分耕地,这使得成千上万的人脱离了生产劳动。寺院年复一年地聚敛大量财富,这些财富皆被藏放于寺院的地窖内”[2]49“不难想象,宗教压在这些总数廖廖的民众肩上的担子有多重,而他们的生产水平一直处于封建社会的初级阶段”[2]49“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时,西藏还保持着带有奴隶制度残余的早期封建社会制度的社会经济关系。寺院和地方贵族集中掌握着所有耕地和牧场。所有农户和牧民都被领主牢牢地束缚在其赖以生存的土地上”[2]57等。
对于农奴次仁平措的铁匠身份,欧福钦介绍到这是一种最低贱的职业,因为佛教认为杀生是最大的罪孽,而铁匠正是制造杀戮工具的人。近代以来,西藏饱受帝国主义侵略,欧福钦在日喀则采访时插入了1904年荣赫鹏带兵侵藏和江孜保卫战的背景,称这是“爱国主义情感的根源”。相对于西藏的旧制度,西藏和平解放的“十七条协议”是当时重要的社会背景,在对宗教上层人士、解放军战士的采访中,欧福钦得出“中央政府驻藏代表在工作中坚定不移地遵守着这一协议”“这一政策是符合现阶段西藏发展的特点”的结论。这些背景既是新闻叙述的需要,使情景更为立体化,又带有强烈的对比,体现出西藏社会的进步是深得人心的。
(三)新闻评价
评价是新闻话语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表明新闻的导向和立场。为显示新闻的客观性,记者通常会直接或间接地引用他人的观点;在基于大量事实的基础上,记者有时也会作出预测和评判。农奴和奴隶在《1955年西藏纪行》一书中的口头反应十分活跃。铁匠次仁平措说:“干活时人们称呼你是不可或缺的人,而干完活之后,则在背后骂你是‘嘎啦’。这是对铁匠的鄙称。”[2]81铁匠格桑说:“逢年过节,你穿戴一新,带着孩子们一起上街,周围的人都会对你指指点点……想到孩子们将来也要经受这些,心情就更沉重了。”[2]81这些引语生动、朴实,反映出人物的内心感受和不平等的社会制度。当铁匠们给解放军战士制作工具后,解放军战士指着胸前佩戴的徽章告诉他们:“镰刀代表农民,锤子代表工人。这是我们的旗帜,共产党员的旗帜,因为我们是在为工人和农民谋福……我们把你看作我们的朋友,像尊重其他工作一样尊重你的劳动。”[2]85前后引语之间形成强烈反差,铁匠坚信“孩子们将不会再听到‘嘎啦’这样的诨名了”,传达出对旧制度的改革是民心所向之意。
在口头反应中,有的是对客观事实的表达,有的是说话人的主观感受和观点。欧福钦对后者的捕捉也十分到位。例如,金正诺布和解放军战士一起筑路,他对筑路这件事的评价为:“我将永远保留有关工地的记忆,不仅是因为我在那里干过活,还因为它一定会给我们带来一条新路。”[2]38由兽医、医生和文化宣传队员组成的工作队在基层开展流动帮扶,队长张同志说:“对我们来说,最大的颁奖就是各地的牧民都像送别朋友那样为我们送行。”[2]103这些引语反映了采访人物的精神面貌,他们眼中的社会也是充满朝气和希望的。在没有引语的情况下,欧福钦从大量的观察、采访中提炼出对西藏社会发展的观点。他写道:“我们看到了人民医院、国营公司、银行、印刷厂和学校。无需求助降神师,我们也能从这些事物的背后看到拉萨的明天和未来”[2]89。在书的最后,他认为:“在经受贫困的折磨、中世纪剥削制度的压榨以及偏见与迷信的影响之后,如今,在祖国母亲的亲切关怀下,藏族人民也为了新生活而重生了。”[2]164这种述评的写作方式既没有脱离新闻的客观性,又增加了报道的导向性和厚重感。
三、《1955年西藏纪行》的对外传播意义
1955年的外国记者团赴藏采访是西藏和平解放后首次对国外媒体开放。当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在对外传播方面的经验还很缺乏,面对国际社会来势汹汹的舆论,外国记者团的报道起到了较好的激浊扬清作用,也使得邀请外国记者在重要时间节点上赴藏采访报道成为西藏外宣工作的重要方式。那么,《1955年西藏纪行》一书中有哪些西藏对外宣传的经验?
(一)善于记录细节,以小见大
建国初期,中国的社会百业正在复兴之中,生活开始呈现丰富多彩的一面。但由于宣传的政治属性,不少新闻报道延续了战争时期的特征,拘泥于公式化,缺少细节和生活气息。对外传播的专家、记者爱泼斯坦认为:“从方法上讲,编辑、记者在接触事物中,要把自已的耳朵、眼睛和脑子都放开。把看过的东西,吸收的东西,以及你对历史和有关知识的了解等等都集中起来。写出来的东西才会对读者有吸引力。”[6]
欧福钦在采访写作中善于抓细节。新闻人物一些一闪而过的动作、神态,他都捕捉得到。例如,他在对农奴次仁平措的采访中写道:“他那浓密、凌乱的头发被编成小辫盘在头顶。说话时,他的双眼微微眯缝着,仿佛在揣摩对方,而双手不停地比划着……”[2]78观察是记者不可或缺的能力,也是获取细节的主要方式,在对藏族农奴的采访中,欧福钦特别留意观察铺在他们房顶上等待晒干的粮食,只有看到粮食丰收,他才相信藏族人民过上了丰衣足食的日子。当时还尚未进入“读图时代”,听觉是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方式,欧福钦的报道中融入了多处听觉叙事。例如,他对拉萨街道的见闻是“街上的喧嚣时而被淹没在被人踩到的狗发出的尖叫和狂吠中”、在寺院听到“僧人们成队地盘坐在油迹斑斑的蒲垫上,大声地吟诵祈祷并以有节奏的摇摆”等。这些细节在人物、事件之外,突出了与之相关的周围环境和记者当时的想法,增添新闻可读性和趣味性的同时,又反映出当时的社会面貌。
(二)站在受众视角,善用比较
当时,国际社会把西藏和平解放说成是“侵犯人权”“限制宗教信仰自由”,除了意识形态因素外,还在于对外传播的方法问题。中国媒体的对外报道常常被当作“宣传”,效果不尽如人意。必须承认的是,中西方社会在文化环境、历史背景、风俗习惯等方面存在差异,需要站在受众视角,采用欧洲人和美国人比较容易理解的方式报道西藏。
在对川藏公路筑路工人、农奴、牧民、宗教上层人士等采访中,欧福钦注重了新闻背景的运用。更难能可贵的是,身为外国人的他,深知国外受众的知识结构,可以把在西藏所发生的事件与其他国家的同类事件加以比较,进而说明其国际意义。例如,他在写到铁匠的社会地位时联系到印度的种姓制度,“西藏不存在像印度社会那样的种姓制度,但是却有受人鄙视的职业,从事这些职业的人被迫世世代代延续这份职业,于是,形成了社会上一支闭塞的、类似于低阶种姓的群体”[2]80。长期以来,西方社会对藏传佛教怀有一种神秘化、理想化、浪漫化的想象,虽然“十七条协议”对“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进行了明确规定,但国际舆论依然喜欢拿宗教抨击中央在西藏的政策。欧福钦深知这一背景,他在兽医谢玉生的经历中写道:当时基层发生牲畜疫情,兽医站想给牲畜注射防疫,但村民却请巫医施法和僧人祈祷。眼看牲畜陆续病死,村民同意兽医在僧人祈祷时进行治疗,后来村里的80多头牲畜全部治愈了。这种鲜明的对比手法,既体现出基层干部对宗教信仰的尊重,又破除了部分人对宗教不切实际的幻想,表明科学才是西藏进步的方向。
(三)关注民生领域,以民为本
西藏幅员辽阔,人口居住呈“马铃薯式”分布,再加上受宗教因素影响,社会生产力水平长期落后。西藏和平解放后,最能反映西藏社会发展进步的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欧福钦在采访中十分关注民生领域,他没有只满足于向地方部门“拿材料”,而是深入到西藏的田间地头“抓活鱼”,用事实说话。
欧福钦在索娜姆多日家中了解到春耕用的种子是国家发放的,还可以贷款购买农具;农民萨莫谷东在农业技术站的指导下试种番茄、南瓜和卷心菜,并向其他农民推广种植经验,高原上长出的第一批蔬菜作物和高产粮食所使用的现代化农具也被公开展览。在教育方面,藏族泥瓦匠的女儿达瓦布日和其他藏族一起被送到成都的西南民族大学学习,回藏后成为了商务部门的少数民族干部;年轻的藏医令青平措跟随军医高大夫学习外科,参与完成手术,初步掌握了现代医学知识。在卫生防疫方面,拉萨人民医院声誉越来越高,群众免费接种了天花疫苗,改变了人们过去对医院的态度;西藏还建成了7家牲畜防疫站,首要目标是降低幼畜的死亡率。在文化方面,电影放映队走村入户放电影,群众可以从收音机、报纸上获悉新华社的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使用的小学教科书被翻译成藏文发到学生手中等。总之,欧福钦笔下展现了一幅幅生动的民生画卷,这是西藏和平解放带来的变化,受到了西藏广大群众的拥护,燃起了人们对新生活的希望。
四、结语
在西藏和平解放后至民主改革前夕,西藏社会正处于时代变革的历史关键时期,欧福钦等外国记者1955年的赴藏采访记录了当时西藏社会的发展面貌,反映出西藏各族人民渴望摆脱封建农奴制度的束缚、向往新的社会制度的民心所向。这既为回答“为什么会发生民主改革”的提问提供了依据,又为民主改革前的藏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史料。
这次采访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为国际社会了解西藏提供了窗口,澄清了事实,消减了误会。基于此次采访的成功,路透社、合众社、CNN、彭博新闻社、英国《金融时报》、德国《时镜》周刊等媒体的记者都曾在此后的不同时期赴藏采访,但经翻译出版的采访报道著作还相对有限,仅有欧福钦的《1955年西藏纪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百万农奴站起来》和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的《西藏的转变》等少数几部,相关领域研究十分缺乏。随着近年来中西方围绕我国西藏开展的文艺演出、座谈会、科技合作和实地考察增多,西藏官方和民间的对外传播重要性日益凸显,对传播技巧和方式的研究也是亟待拓展和加强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