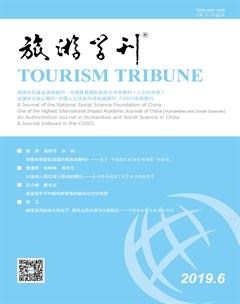大众旅游现象研究综述与诠释
董培海 李庆雷 李伟
[摘 要]MacCannell开创的旅游现代性研究范式,通过对大众旅游现象的关注,极大地推动了旅游社会学学科的发展,然而,这一研究范式在赋予旅游现象和旅游研究普遍性意义的同时,很大程度上又忽视了对大众旅游之外其他旅游现象和行为的描述与关注。旅游被视为一种均质的现象,由此也导致了旅游现象的社会学研究失去了应有的学术张力和想象力。该研究以旅游现代性研究为切入点,在综述国内外大众旅游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剖析大众旅游的概念、特征,并对大众旅游的发生及发展予以探讨,以期通过对大众旅游的阐释,以之为透镜,拓宽旅游现象认知的视野,推动旅游现代性研究范式的扩展,进而对旅游基础理论的研究有所启示。
[关键词]大众旅游;旅游吸引物泛化;娱乐;大众旅游趋向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2-5006(2019)06-0135-10
Doi:10.19765/j.cnki.1002-5006.2019.06.017
引 言
20世纪60-70年代,Boorstin和MacCannell关于本真性(authenticity)的争论受到广泛关注,成为社会学领域关于旅游研究的最大热点。在这场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学术争鸣中,MacCannell无疑占据了上风,面对势如破竹的大众旅游现象,Boorstin对于“旅行艺术的失落”(the lost art of travel)和旅游是“伪事件”(pseudo-events)的感叹更像是一种无病呻吟于历史变迁的哀婉情调。对于旅游吸引物和旅游现象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MacCannell尝试从现代性的背景下来理解旅游,将旅游视为现代性背景下的一种朝圣。他的研究激起了英语世界对于旅游社会学的深入关注,进而从大众旅游现象的关注中,开辟了旅游研究的新范式。细数20世纪70年代以来旅游社会学和旅游人类学的繁荣与理论原创,莫不与其旅游现代性研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研究范式也主宰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旅游社会学20余年的发展。在社会学中,旅游成为了现代人的一种隐喻(metaphor),而追求“前现代世界”(pre-modern world)的差异性被认为是现代性治愈的一种手段。正如Aramberri所说:“要将当今的大众旅游与其之前的形式区别开来,一个‘现代的前缀不可或缺,因为在今天大众旅游与现代性已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然而,旅游现代性分析范式在赋予旅游现象和旅游研究普遍性意义的同时,却又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对大众旅游之外其他旅游现象和行为的描述和关注。旅游被视为一种均质的现象,由此也导致了旅游现象的社会学研究失去了应有的学术张力和想象力,理论研究止步不前。继20世纪90年代初Urry的旅游凝视(tourist gaze)理论之后,旅游社会学乃至整个旅游学研究再无重大的理论原创。
回顾国外旅游研究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在西方旅游社会文化研究的话语体系中,对于旅游现象的认识和研究一直存在精英旅游(elite travel)和大众旅游(mass tourism)两种不同维度。不管是Gray对漫游癖( wanderlust)旅游和享受癖(sunlust)旅游,Cohen对非制度化旅游和制度化旅游,Urry对浪漫主义凝视旅游(romantic gaze at tourism)和集体凝视旅游( collective gaze at tourism)的区分,还是王宁旅游“真实性”研究中对客观主义真实( objectiveauthenticity)和存在主义真实(existentialauthenticity)的探讨,相关研究莫不如此。现代大众旅游的成功之处在于其通过产业化和制度化的安排,满足了现代人对于天堂的追求与想像,使旅游成为一种全球的愿景和深刻影响人们生产、生活的重要力量。毫无疑问,大众旅游已经成为旅游研究中最为宏大和值得關注的一种现象和事实。然而,对于大众旅游现象的研究和关注亦不能陷入以偏概全的境地,在纷繁复杂的旅游现象世界中,朝圣旅游(pilgrim tourism)、背包客旅游(backpackingtourism)、黑色旅游(black tourism)、灵性旅游( spiritual tourism)、志愿者旅游(volunteer tourism)、善行旅游(good tourism)、扶贫旅游(pro-poor tourism)等均不能简单地纳入大众旅游的范畴。
问题意识是从事旅游学术研究的基础,是旅游学术创造活动的精、气、魂之所在,是旅游研究者从事学术研究的一种知性、理性,更是一种悟性。问题意识源于理论与经验之间的张力,旅游学术研究的深化不仅高度依赖于旅游基础理论层面的探索和创新,同时也离不开对错综复杂的各种旅游现象的深描和解释,二者唇齿相依。本研究在综合国内外大众旅游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剖析大众旅游的概念、特征,并对大众旅游的发生与发展进行简要梳理,研究聚焦于大众旅游现象的探讨又不完全囿于此,而希冀于通过对大众旅游的阐释,以之为透镜,拓宽旅游现象认知的视野,进而能对旅游基础理论的研究有所裨益。
1 何为大众旅游
1.1 大众旅游释义
在各种旅游学术研究乃至普通的报刊和新闻媒体宣传中,大众旅游都是一个耳熟能详的词汇。但是,在中外、不同学科、不同语境下使用大众旅游,其范畴所指却有所差别。从严谨的学术层面对大众旅游的探讨,要追溯至历史学家Boorstin在1962年出版的《镜像:美国伪事件导览》(The Image:A Guide to Pseudo-events in America)一书中,在“旅行者到旅游者:旅行艺术的失落”一章,面对“如日中天”的大众旅游发展势头,Boorstin将大众旅游( the mass)称为是旅游部门所组织的一种消费形式( governed by the agents of tourism),在大众旅游中,旅游者与景观之间处于一种隔离状态。对于Boorstin所描述的大众旅游的组织化(organized)特征,以色列社会学家Cohen用“环境泡”(environmentalbubble)的概念来予以形象的概括,“旅游者在导游、空调大巴、饭店集团、旅行社的安排下,透过自己熟悉的环境去观察和体验他者的地方与文化。旅游被打包后以标准化的方式来进行大规模的生产和出售”。Nunez和Aramberri都与Boorstin持相同的观点,他们将大众旅游看作是与精英旅游(行)(elite tourism/ elite travel)相对的一种旅游形式。另外一些研究者则认为,大众旅游是一种传统的( conventional)旅游形式,其带来了一系列消极影响,必将为新的(new)、可替代(alternative)的旅游形式所取代。然而,正如Mustonen所调侃的:“研究者都在强调要重新寻找大众旅游的替代,却很少有人对其进行清晰的界定”。相较而言,在这些研究者中,Poon对大众旅游的界定可能是最为系统和全面的,他认为“大众旅游是以固定的价格、标准化的服务、大批量销售给大众顾客的包价旅游”,大众旅游以大众化(mass)、标准化(standardized)、包价(packaged)为特征。此外,还有一部分研究者从“mass”的字面意义,即人口数量特征上来解读“大众旅游”。Boissevain和Selwyn就认为大量旅游者去旅游目的地度假,这种稳定的游客流动现象就是大众旅游。Youell认为大众旅游是出于闲暇和商务目的而产生的大规模的客流。英国社会学家Sharply通过综合前人的研究,认为可以从3个层面来理解大众旅游:
(1)大众旅游是一种独特的被制造、营销和出售的旅游产品类型。
(2)大众旅游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而大众旅游者是指那些追求在一些人看来属于最低级旅游共同点的人。
(3)大众旅游是指与特权阶层的少数人相对的,生活在西方发达工业国家中的大众所能享受的旅游。在Sharply看来,大众旅游不仅是一种社会经济和政治现象,同时也是一种表征为大规模人口移动的地理现象。
相较而言,国内学者对大众旅游的概念解析则非常薄弱。张凌云在综合考察了国外大众旅游相关研究成果后,提出“大众旅游是指由于环境和条件的改善以及休闲需求的增加所产生的大规模的旅游客流”。王兴斌说:“大众旅游就是大众都去旅游”。在国内旅游学术研究语境中,提及大众旅游强调的往往是“人数”的概念。这不禁会让我们质疑:“多少人或多大规模比重”的旅游才能称之为“大众旅游”?在西方学术研究中与中文语义“大众”对应的有“popular”和“mass”两种表达,且鲜有研究者将其等同于“数”的概念,而更多地强调其“质”的特征。Defleur和Rockeach在《大众传播学理论》一书界定“大众社会”时就强调:“大众社会的概念不等同于数量上的大型社会,大众社会指的是个人同社会秩序的关系”。Gasset也说:“不能把大众简单理解或主要理解为劳动阶级,大众是平均的人(the average man)”。大众旅游作为现代性背景下席卷全球的一种“社会事实”,涉及了规模空前的人口流动,然而,这只能作为大众旅游的表象形式,过度强调大众旅游的人口特征,无疑是简单而粗暴的,人口数量本身并不能为大众旅游提供一种衡量和描述的尺度,无益于增进大众旅游现象的认识和研究。
1.2 大众旅游的面相
事实上,“大众”一词在西方研究的话语体系中本身即“不受待见”。Le Bon把大众称为是一群“乌合之众”,Moscovici则以“群氓”称之,Riesman把大众看作是“孤独的人群”。国外旅游研究者对大众旅游的理解同样充斥着贬义,基于对大众旅游的不同界定,我們可以将其大致区分为两类: 一类以Poon对大众旅游的定义为基础,研究者多为地理学、经济学和环境科学背景,他们从宏观产业层面强调大众旅游所带来的诸如旅游活动组织的无序化、社区发展不平衡以及环境破坏等消极影响,强调大众旅游亟须以新的旅游形式替代,在他们看来,替代性旅游、生态旅游、软旅游(softtourism)、负责任旅游与绿色旅游作为可持续旅游的重要形式无疑是更佳的选择。与此同时,鉴于志愿者旅游、扶贫旅游、善行旅游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和普世价值,它们也成为了大众旅游的诟病者们所倡导的旅游方式。
另一类研究则继承和延续了Boorstin对大众旅游的看法,基于社会学和文化学的视角,他们以旅游者体验为切入点,从微观层面剖析大众旅游的局限性。在他们的研究中,大众旅游往往与肤浅、低俗、狂热与无约束相联系。如,Culler将现代大众旅游者称为“符号大军”,他们对旅游吸引物和旅游的意义不求甚解,而仅仅满足于旅游符号的表面滑行。Ritzer和Liska将大众旅游称为“迪斯尼化的旅游”(McDisneyization tourism),旅游者被分类、组群然后打包,集中运送到目的地,一切都被预先安排好并像工业产品一样在流水线上不断生产。Urry也说大众旅游就是一个收集照片、收集符号的过程,旅游凝视就是某特定景点意义符号的生产与消费。
由于认知角度的不同,提及大众旅游的时间缘起,研究者之间也存在较大分异。Poon认为大众旅游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Boissevain和Selwyn认为大众旅游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工业化国家,Graburn认为大众旅游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30]83,Sharply说大众旅游是20世纪晚期的特征,Urry则认为大众旅游起源于19世纪欧洲的温泉疗养和海滨度假。大家的观点莫衷一是,具体到各个国家的大众旅游起源就更是众口莫辩。学科立场和学术视角的不同,导致了研究者们对大众旅游的认识始终存在一定差异,然而从众说纷纭的前人研究中,采用归纳的逻辑,求同存异,我们也可以总结出大众旅游在以下5个方面的共性特征和表现:
(1)人口特征。现代大众旅游涉及历史空前的人员流动,正如Nash强调的:“正是鉴于涉及的人口数量上的绝对规模优势,研究者们倾向于将现代的大众旅游看作是所有旅游形式的雏形(as a modelfor all tourism)”。大众旅游与人口的数量和阶层结构密切相关,其消极效应与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空间集聚关联在一起。
(2)技术特征。技术的发展不仅为现代大众旅游提供了重要的通行条件,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使人们得以从工作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并开展常态化的旅游。
(3)产业特征。大众旅游通过对旅游吸引物、饭店、交通要素等的组织,将旅游以“包价”(package)的、标准化的方式进行大规模的生产,从而提供物美价廉、安全可靠的旅游产品和服务,使旅游由特定阶层特有的一种生活方式变成普通大众所共享的生活经验。
(4)社会结构特征。工业革命不仅促进了中产阶层的壮大和可自由支配收入的增加,伴随着工业化所带来的异化、失范和工作条件的程式化,生态环境的劣质化,人际关系的淡漠化等,更是成为人们对现代性的存在条件下不满与怨恨的社会原因。大众旅游成为现代性所固有的结构性“好恶交织”的反映与体现。
(5)娱乐特征。现代大众旅游是以观光为基础的休闲娱乐,大众旅游者是追求快乐而旅行的人。休闲、娱乐是大众旅游区别于许多“前旅游”(pre-tourism)和新兴旅游形式的一种重要特质。
2 大众旅游的源起
对于大众旅游的源起,研究者们一般会溯及生产力的提高、交通技术的进步、假日制度的改革以及Cook所推动的产业化等因素,而很少从社会文化的视角来审视大众旅游的发生机制。即使有,也往往落入MacCannell旅游现代性的分析框架中。不管是王宁“旅游是现代性好恶交织的反应与体现”,Urry将旅游看作是现代社会的地位标志(themarker of status),还是Rojek把旅游看作是人们在现代性条件下的“解脱方式”(ways of escape)和弥补现代性所带来的失落感(a sense of lost)的产物。相关解释均显得过于概括和宏观,对于大众旅游的源起有必要从社会文化变迁和旅游行为本体意义的更加具体的层面来展开探讨。以观光为基础的休闲、娱乐是大众旅游的核心标志之一,观光( sightseeing/trip)、休闲(leisure)和娱乐(recreation)也一度成为了“旅游”的代名词。《韦伯斯特大学词典》将旅游定义为“以娱乐为目的的旅行”,而“旅游者”是“以娱乐为目的而旅行的人”。但是,早期的旅游(或旅行)与观光和娱乐之间却联系甚微,到了大众旅游阶段这一状况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2.1 “大众旅游”与旅游吸引物的泛化
Urry的“旅游凝视”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旅游社会学研究中被引用最多的成果,在Urry看来,旅游者所有的感觉器官中,眼睛无疑是最为重要的。Urry说:“通过考虑典型的游客凝视的客体,人们可以利用这些客体去理解那些与它们形成反差的更为广阔的社会中的种种要素”。与Urry不同的是,在另一篇更早且同样被广为引用的研究文献中,Adler在追溯了观光(sightseeing)的起源后发现:在17世纪以前,旅游(travel)最先被视为一种艺术,其为欧洲的精英份子们所实践,旅游更多的是出于获取知识和增长见闻的目的。在旅行前需要大量阅读、搜集信息,并学习他国的语言,在旅游活动中,相较于视觉上的审美和愉悦,增长见闻和知识获取居于更加重要的地位。18世纪这一情况发生了深刻变化,Adler认为要理解这场变革就必须还原到欧洲的文化变迁语境中,即“知觉的视觉化”过程(the visualization of perception)。
爬梳历史,在18-19世纪之交,对于欧洲文化变迁影响最为深远的莫过于浪漫主义思潮( romanticism)。这场肇始于18世纪中后期英国文坛的反新古典主义文学运动,在19世纪席卷欧洲,影响遍及文学、艺术、哲学等各个领域。在旅游研究中,功绩卓著的旅游社会学研究者,UITy、Frow、Sharply、王宁等都一致强调了这场文化思潮运动对于风景观光(sightseeing)的影响。如果说文艺复兴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助催了人们了解外部世界的渴望,为现代旅游提供了全球性的基础。那么,浪漫主义运动则进一步推波助澜,作为现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运动,其彻底改变了西方世界的生活和理想。浪漫主义关于自我的扩张,艺术的自足,生活世界的诗化和审美化,进一步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原则。在这场运动的影响下,风景旅游(scenic tourism)开始出现,对美丽和壮观的体味更加私人化、更富激情,旅游知觉走向视觉化。18世纪末之前被认为是充满荒凉、丑陋、恐懼的阿尔卑斯山被旅游者浪漫化,转变为充满景色、形象和新鲜空气的地方。昔日被看作是恶魔和盗匪藏身的森林,成为了充满魅力的吸引物。在英国乡村,对于湖区的看法,也从毫无吸引力、充满危险之地变成了一个弥漫着祥和、乡村气息,虽贫穷但幸福得一尘不染之地。各种自然景观成为了旅游凝视的对象。在19世纪的发展中,一方面,浪漫主义以怀旧的心理惦念着“质朴”的过去,并进一步孕育着对民间生活和民族传统的浓烈兴趣。另一方面,随着东方学的兴起,全球敞视主义( panpticon)被塞进西欧人的旅游包里,在全世界昂首阔步,升华为旅游热。到了19世纪后半叶的
欧洲,百货商店也成为了空间常设化的博物馆,各大城市竞相举行的博览会成为重要的旅游吸引物。与此同时,Cook所推动的铁路旅游不仅消除了旅行带来的不便与危险,而且结构性的改变了人们对于风景的知觉,风景得以向着更为遥远的地方延伸。印刷技术的进步更是赋予了人们没有去过的地方一种想象的被照片所截取的美,起到了风景名胜旅游的大众化效果。景观和旅游体验被进一步视觉化,旅游吸引物在全球范围内被建构,其结果正如同MacCannell笔下所描述的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巴黎旅游那样,游客被带领游览下水道、陈尸所、屠宰场、政府印刷局、造币场、证券交易所以及正在开庭的高级法院。在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旅游景观成为没有边界的范畴,而旅游景观的建构和营造的过程也成为了大众旅游市场不断扩张,大众旅游现象不断普及的过程。
2.2 大众旅游与娱乐
Boorstin在对旅行者(traveler)和旅游者(tourist)进行比较时强调:旅行者是积极投身工作的人(anactlve man at work),而旅游者则是追求娱乐和观光的人(a person makes a pleasure trip)。在他看来,大众旅游者是那些借助于大众媒介的宣传和产业的组织,以开展定点的拍照、娱乐、观光和消费的一群人。Aniculaese在研究美国休闲旅游发展时提出:“在产业革命前,人们外出旅行无外乎两种原因,贫穷者(the poor)为了获得物质上的自由(material freedom).而富有的贵族则通过旅游来丰富知识和学养以标示他们的社会地位”。Urry在追溯了漫长的人类旅游史后,也认为:19世纪以前,上层阶级以外的人,很少会出于与工作或生意无关的原因而去旅行,去观看各种事物,出于与工作或生意无关的原因去旅行是现代大众旅游的主要特征”。“旅游”的词源学考证也能支持他们的观点。旅游对应的两种基本表达中,“travel”与“travail'原本是同一个词,本身即表示辛苦、劳动、痛苦。“旅游”的另一表达词根“tour”则源于拉丁语的“tornare”和希腊语的“tornos”,其含义是车床或圆圈,围绕一个中心点或轴的运动,意指按照圆形轨迹的运动。根据Haulot的观点,“tour”一词起源于圣经的《民数记》,与探索、旅程和探险等概念相呼应,这一过程充满了各种艰辛和苦楚。直到《简明牛津英语词典》于1800年首次发布了“tourist”一词后,“旅游”(tour)才用以特指以愉悦或文化为目的而旅行的人。
大众旅游阶段,旅游得以与娱乐之间建立起了普遍的关联。如果追溯对后世影响较为深远的几种“旅游”形式,可以发现它们与娱乐之间关联甚少。例如,节事旅游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腊,奥林匹亚是古希腊最为流行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在公元前776年举办的首届运动会就吸引了成千上万来自希腊和其他国家的参观者,但是古希腊人并不将休闲视为放松和调整,而是将它看作通过教育、运动和音乐达到自我提升的方式,拜访圣人和参加节庆都是希腊生活的一部分,而追求愉悦的旅行并不常见。朝圣(pilgrim)可能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种自愿旅游形式,以至于有学者甚至认为现代旅游源于朝圣。早在3世纪时基督教徒就前往伯利恒( Bethlehem)参观,10世纪后,这种跨国旅游的人数开始大量增加,然而,朝圣的旅程总是充满艰辛,它是一种苦修的方式。教育旅行(the Grand Tour)作为16世纪到19世纪早期欧洲贵族最重要的跨国旅游形式,其目的也是在于帮助年轻贵族实现完整的教育,只是到了19世纪,随着中产阶层的壮大,教育旅行才从教育走向观光和娱乐。从19世纪开始,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社会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开始发生分化,时间变成一种资源,并被分割成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与此同时,旅游作为一种逐渐为大家所熟知和喜欢的休闲活动也从社会生活中分化出来,旅游的地点与工作、家庭的地点同步发生分化。“旅游”被视为一种“另类”的生活,它为身处现代性背景下的人们提供了一种“逃逸”(avoid)和“再造”(recreat)机制,正如Pieper所说:“辛劳工作,欢乐收割,假日就是可以免除像奴隶般工作的日子”。各种各样的旅游形式也越来越多地与娱乐、享受联系到了一起。
3 大众旅游的趋向
作为旅游现代性研究范式的发起者,在2001年出版的《东道主与游客》(Hosts and Guests)(第三版)一书中,MacCannell感叹道:“人们在地球表面任何两点之间旅行时的体验越来越相似,随着旅游业本身将人们的旅游体验以及旅游目的地变得同质化,这一过程是否将最终使得人们的旅行动机消失”? Cohen也认为,目的地“地域性”的散失,后现代情形下来自不同意义领域的体验同质化,以及仿真技术的进步将对旅游作为一种独特的活动形式构成威胁,可能导致旅游的终结。这是否意味
着大众旅游将在其到达历史的最辉煌时刻走向灭亡?诚然,如果仅仅将旅游等同于大众旅游,即传统意义上的以寻求差异性为目的的娱乐和观光,那么对于大众旅游最终发展趋向的预测难免陷入悲观。问题的关键却在于旅游现象并不是“均质”的,一方面,大众旅游仅仅只是诸多旅游形式中的一种。朝圣、探险、修学等旅游形式多元并生,它们在现代性及后现代性的语境下与大众旅游互动共生、不断演化,呈现为新的旅游形式和现象。另一方面,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背景下,大众旅游本身也正不断发生着变化。Mowforth和Munt曾具体描述过这种变化:旅游产品需求由福特主义走向后福特主义(fordist to post-fordist);现代性走向后现代性;包价旅游(packaged tourism)走向个性化旅游(individual tourism)以及旅游的社会、文化和生态责任意识日益凸显。Uriely和Urry则倾向于用“后现代”来形容当前旅游的新变化。在Uriely看来,后现代旅游表现为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是“虚拟后现代性”(simulational postmodernity),其倾向于追求超真实的旅游体验(hyperreal experiences).另一種是“另类的后现代”(other postmodernity),其有别于传统旅游形式而强调可替代( alternative)、真实( real)、生态的(ecological)和负责任(responsible)这样一些概念。
相较而言,Urry对后现代旅游的描述则更加具体,他认为“后现代旅游”的结构特征是“去差异”(de-differentiation),其表现正如Turner和Ash在The Golden Hordes -书中所描述的那样,“人们在寻求永远新鲜的旅游目的地的过程中,建立起的只是一套酒店和旅游景观,平庸乏味,缺少反差,对奇异性和差异性的追求却以缺少奇异性和差异性的始终如一而告终”。后现代旅游的另一个特征是玩乐,后现代旅游者在大量的选择中感知变化和快乐,他们不受高雅文化的约束,以无止境的追求快乐为原则,用快乐的心态对待一切。Sharply则认为,在后现代旅游中,旅游消费也发生了变化,由于消费者的支配角色的不断强化,对于个性化旅游产品的需求增加,生产和消费的关系变得无关紧要,消费被视为梦想的实现,对愉悦体验的追寻以及逃离日常文化和社会的刻板与结构方式。这种变化导致了Campbell“想象的享乐主义”(imaginative bedonism)中所描述的:“幻想和期盼成了消费的重要过程,人们并不从产品和他们实际购买和选择的使用中寻求满足,相反,满足源于期盼,源于一种想象愉悦的追求过程”。与此同时,大众旅游的审美特征也正悄然发生变化。快乐哲学和快活主义大行其道的当下,人们的旅游审美需求也开始不再超脱,逐步远离静观和无功利,趋向以休闲为中心的体验和参与。旅游走向全民化、普及化和生活化,褪下获取知识、陶冶性情、实现价值的神圣外衣,而走向放松身心、怀乡念亲,追求欢娱的世俗体验。审美目的世俗化、审美标准模糊化、审美情趣符号化和审美意识多元化成为了当下日常生活审美文化的显性表达方式。以此来看,Aramberri对于大众旅游发展的评价或许更显客观:“现在宣告大众旅游的死亡显然为时过早,现代大众旅游的寿命应该更持久”。
事实上,如果对旅游的本质稍加审视,“大众旅游终结论”无疑是显得过于悲观和武断了。旅游作为一种异地追求身心自由的体验,是合乎人性的一种存在,是人的天性的一种反映。作为一种理想性、创造性和超越性的存在,人生而具有摆脱本能决定其行为而追逐自由的天性。旅游中的求新、求异、求体验,在本质上正是人类对有限生存时空所产生的生命期待和生命本能的内在冲动,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基本需要,旅游许诺给人们一段悠闲的时间,摆脱工作、物质和心灵的羁绊,在理想中度过,实现日常生活的回归和精神短暂超越。旅游是使人达到诗意的栖居不可或缺的生命维度。既然自由是人的生命本能,那大众旅游就永远不会消失。
4 结束语
事实上,讨论“大众旅游”而又缄口不言“何为旅游”,这多少显得有些牵强。然而,一旦溯及“旅游”,又不得不陷入旅游的概念争议和旅游史的讨论窠臼,类似的研究在国内外旅游学术积累中早已“汗牛充栋”,当然也莫衷一是。本研究试图搁置这些争议,而从大众旅游现象的表征及其发展进行直观的归纳和剖析,以期能进一步窥视旅游现象的多元特征及本质属性。旅游社会学是通过建立旅游与现代性之间的关联而得以从学科边缘走向中心的,对于大众旅游现象的关注是旅游社会学研究获得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关键所在。然而,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之后,当我们重新回顾MacCannell所建立的旅游现代性研究范式会发现,它虽然极具概括性,却将旅游活动的“参数”设计过于狭窄,“对工作/休闲(旅游)简单的二分导致了一些严格意
义上来说既非旅游又非工作的特定旅游形式被忽略”。Kuhn说只有当科学家发现研究对象的一些或者全部组成部分无法相协调时,他们才会着手于寻找其他替代的解释或更佳的理解方式。旅游现象从来就不是均质的。
一方面,朝圣、教育旅行以及Cohen笔下的漂泊者(drifier)、探索者(explorer)穿越历史,在新时期以宗教旅游、修学旅游、探险旅游等面目出现,在现代性背景下,它们可能掺杂了一些大众旅游的观光、娱乐性,但在审美、组织形式和行为动机与特征方面仍有别于大众旅游。
另一方面,誠如Urry所言,工作与休闲相分离是大众旅游的主要特征,新时期我们看到的却是旅游(包括大众旅游)越来越多地走向与工作、生活相融合。作为普遍存在的背包客、探险旅游、灵性旅游和黑色旅游等,有时看来不仅不是享受,甚至带有一种自我折磨的特征。作为新兴的志愿者旅游、善行旅游、扶贫旅游等形式也不能归人大众旅游的行列和旅游现代性的研究框架。
长期以来,我国旅游学术研究主要是对欧美发达国家学术话语体系的单向输入和模仿。对于大众旅游的研究同样如此,无论是改革开放后对入境旅游的关注还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旅游研究,国内旅游学界的研究重心一直聚焦于大众旅游,旅游相关学科的知识谱系构建也多以大众旅游为主体。由于国内旅游经济发展的实践需要,研究者的视角也表现出了极强的经济学学科偏向特征。相较而言,对于大众旅游之外的其他旅游现象的研究则往往散落于生态旅游、体育旅游、背包旅游等现象的研究之中,且对“非大众旅游现象”的关注也主要聚焦于经济学、管理学和地理学等应用性极强的学科,而较少从社会学、哲学、文学等角度去进行阐释。
从长远来看,这样一种状态并无益于增进国内旅游现象研究和旅游学科发展。相较于欧美发达国家,我国旅游业起步相对较晚,目前仍处于大众旅游市场规模急剧扩张的阶段,且正经历着一场历史性的变革。旅游者动机多元化、旅游资讯技术化、旅游吸引物无边界化以及旅游体验定制化等一系列的变化正深刻地影响着旅游发展的方方面面。2018年全国旅游工作会议更是明确指出我国的旅游发展要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优质旅游发展阶段”,并提出了深化供给侧改革、推进全域旅游、绿色旅游、乡村旅游、旅游扶贫,开发海陆空旅游新业态等系列举措。面对着这样一场规模空前的变革,国内大众旅游必将随之发生变化,对此,国内旅游研究是否也应该同步给予更多关注和思考,并尝试诉诸理论的探讨和创造,以探索适合于我国旅游产业发展实践和特色的旅游理论,在实现对西方大众旅游传统研究范式(尤其是旅游现代性研究范式)借鉴和反思的基础上,构筑一个专属于我们自己的旅游学术研究话语平台和体系?这无疑是非常迫切且令人期待的。
A Summary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SearCh On MaSS TOUriSm
DONG Peihai1,2,LI Qingleil,LI Wdi3
(1.School of Tourism and Geography Science,Yunnan Normal University,Kunming 650500,China;
2.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Baoshan University,Baoshan 678800,China;
3.International College,Yunnan University,Kunming 650091,China)
Abstract: The research of modern tourism created by Dean MacCannell, which was brought forwarddue to the attention on the phenomenon of mass tourism, has great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tourism sociology. Although this paradigm gives full scope to tourism phenomenon and tourismresearch, it ignores the description of other tourism phenomena and behaviors beyond mass tourism. Infact, pilgrimage, backpacking tourism, black tourism, spiritual tourism, volunteer tourism, good tourismand pro-poor tourism are not included in the discussion of mass tourism. Due to multiple research onmass tourism, tourism is regarded as a homogeneous phenomenon, which leads to the lack of a properacademic tension and imagination regarding sociological studies of tourism.
Based on the study of modern tourism,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mass tourism inChina and abroad, and it analyses the concep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it, frnally arguing that we can'tsimply equate mass tourism with the number of tourists, and that large-scale population flow is only themanifestation of mass tourism. The phenomenon of mass tourism needs to be understood consideringfive aspects, namely, popul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social structure, and entertainment. Thedevelopment of mass tourism is not only influenced by the improvement of productivity, the progress
of transportation technology, the reform of holiday system and the industrialization promoted by Cook,bu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ulture, the origin of mass tourism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xpansionof tourist attractions and the "entertainment" of the tourism. The Romantic Movement at the turn of the18th and 19th centuries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scenic tourism. Natural landscapes, traditions,historical heritage, museums, department stores and other natural and artificial locations had becometourist attractions. Since the 19m centur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ourism' s pursuit for knowledgebegan to weaken and became more popular, and a univer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and"entertainment" had been established. 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s had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mass tourism.
In the final part of the paper, the trend of mass tourism development is discussed. It is pointed outthat mass tourism is only one of the many forms of tourism, and other forms, such as pilgrimage,exploration and drifting should not be neglected.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ty, theseforms of tourism interact with mass tourism and evolve continuously, presenting new forms andcharacteristics of tourism. At the same time, some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aestheticcharacteristics of mass tourism. Traveling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opular, the sacred significanceof acquiring knowledge, edifying sentiment and realizing value has been weakened, while the secularexperience of relaxing one's body and mind and interest in entertainment has been strengthened. Thestudy hold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mass tourism in the future will not go to extinction, since tourism isa reflection of human nature, the development of mass tourism will increase in the future. Finally, thispaper appeals to Chinese researchers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some new changes in tourism, to activelyexplore and create theories, to promote the expansion of modern tourism research paradigm, and toexplore tourism theories that are suitable for the development practic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tourism industry.
Keywords: mass tourism; the generalization of tourist attraction; recreation; trend of mass tour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