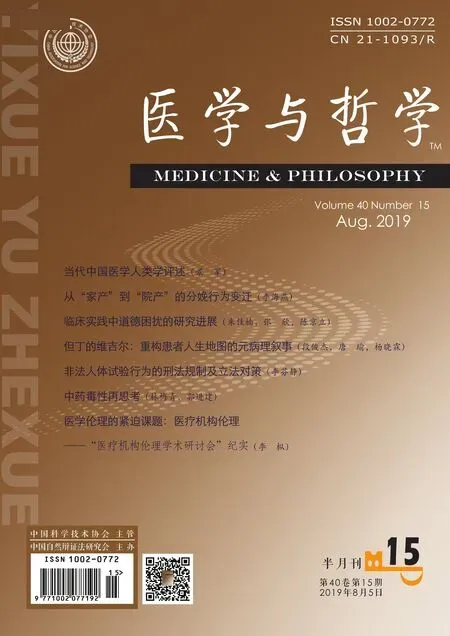从“家产”到“院产”的分娩行为变迁*
李海燕
近几十年来,我国孕产妇分娩经历了一个由在家生娃向住院分娩的转变过程: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家生娃是主要的分娩方式,而据《2018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8年全国住院分娩率达到99.9%(市100.0%,县99.8%)[1]。在两三代人的时间里,分娩地点何以发生了如此大的改变?带着疑问,笔者以重庆Z村为田野调查点,采用文献研究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法,试图通过对Z村有生育经验的妇女及其家属、接生员(婆)、计生干部等人的深度访谈,再现Z村分娩由家庭走向医院的过程,及其背后观念的变化。
Z村位于重庆市丰都县北部董家镇,近年来人口变化幅度不大,共七十余户,近三百人。村民传统生计为农业种植,改革开放后年轻人逐渐外出务工。1953年,在离Z村仅步行10多分钟的乡场上建立了乡卫生院,20世纪末21世纪初,随着“撤乡并镇”的推进,医疗资源逐步转移到车程7公里之外的董家镇上,并入了董家镇中心卫生院[2]15。建国以来,先后为该村接生的人有XZL、QGS、WQR、DXZ四人。XZL在建国前开始接生,建国后参加了新法接生培训,现已去世。QGS(女,70岁)在1969年在乡卫生院参加培训后,成为接生员,采用新法接生。但近年来,政府严禁私人接生,QGS也已不再从事接生工作。WQR是飞龙乡卫生院的医生,现已退休。DXZ是当地的赤脚医生,在20世纪90年代,诊所发生了医疗事故后不再从事医疗活动。
笔者于2016年1月和8月~9月两次前往Z村做田野调查,根据访谈对象的年龄分为了60岁以上、40岁~60岁、20岁~40岁三个小组,调查显示分娩地点和负责接生人员如下:60岁以上村民分娩的地点是在家里,请接生婆XZL接生;40岁~60岁分娩的地点有家里、卫生院、务工地诊所等,接生人员分别有接生员QGS、卫生院工作人员、诊所接生员;20岁~40岁分娩地点有务工地诊所、务工地医院等,接生人员有务工地诊所接生员、医院工作人员等。
通过对Z村分娩地点的梳理,可以得到如图1所示的分娩地点变化图景,即分娩地点从家里走向家外的过程。大体可以说,Z村分娩分为“产婆请进来”和“产妇走出去”的过程。在家生娃又有“请进来”是旧式接生婆和新式接生员的区别,产妇“走出去”也分为去务工地诊所和医院分娩两种情形。

图1 Z村分娩地点变化图景
1 在家生娃与请“产婆”还是请“观念”?
1.1 接生员(婆)与新、旧法接生
在当地,分娩被称为“生娃儿”,传统分娩行为多是在家进行,“在家生娃”在村民的眼中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临产时,家里人都会为产妇请接生人员来,即便是在熟人社会中没有人去请,接生人员是不会自己来的。接生后所付给的接生费用也是凭主人家喜好,没有定标定价。对于请来的接生人员,根据其是否经过了国家妇幼体系的培训以及对产妇、胎儿的不同处理方式等,有了新法接生员与旧法接生婆之别。采用新法接生的被称为接生员,旧法接生的被称为接生婆。“新法接生”中“新”是与“旧法接生”比较而言的,两者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是否注重消毒和采用何种分娩姿势上,新法接生强调消毒,而旧法接生不注重消毒;新法接生躺着分娩,旧法接生坐着分娩[2]31。新法接生一般可概括为“一躺三消毒”,即采用躺着分娩的姿势,并对接生人员的手、接生用具、产妇外阴部进行消毒灭菌。
中国传统认为分娩是一件“脏事情”、“晦气”的事情,因此旧法接生的人大部分是没有文化的“接生婆”[3]。为了推广新法接生,就必须对接生婆进行培训。贺萧[4]在《生育的故事:1950年代中国农村接生员》中谈到,到1956年,旧产婆一词就从官方资料中消失了,出现的只是培训和复训接生员。尽管如此,国家对接生员的重视不能等同于农村接生就真的如国家计划一般完美,在Z村也是一样,20世纪50年代经受过复训的接生婆即使提着培训结束后获得的接生箱出来接生,也不能说明她们的接生方法是新法接生,因为传统接生方法及观念已根深蒂固,很多时候消毒都不被重视。并且很多家庭还存在女性长辈或者产妇自己接生的情况,她们凭以往的经验接生。
Z村60岁以上的人,分娩的场所是在家里,分娩的经验主要是从女性长辈处习得。她们普遍认为生孩子是自己的事情,临产时由女性长辈负责照顾孕妇分娩,男性家属去请接生婆,接生婆来后主要负责给新生儿剪脐带和挑口。挑口是为了预防脐风,一种新生儿破伤风,又称“四六风”、“七日风”,当地人称“七风”。DFZ(女,74岁)认为接生婆也没干啥,主要就是给新生儿包脐带、挑口,往嘴里抹下紫药水(访谈资料:DFZ20160206F74)。分娩后,接生婆会处理小孩,产妇则几乎不需要处理,只需好好坐月子,而当时的条件似乎也不能很好的满足。
Z村40岁~60岁的产妇,分娩的场所主要是在家里,调查对象中有1人去镇卫生院分娩以及5人在务工地的诊所分娩。诊所和医院分娩的情况后文详述,在此主要阐述在家分娩的情况。这个年龄段的妇女在家分娩请的产婆已经是经过国家培训过的接生员、卫生院医生、赤脚医生等人,她们采用的是新法接生,注重消毒环节以及对产妇的处理。使用新法接生的接生员通常采用碘酒等消毒,接生时还会根据需要滴宫缩素和会阴侧切、缝线等。因害怕感染脐风,当地人仍然会注重新生儿挑口。
1.2 生育胎次与接生观念
据调查,当地60岁以上的老人每家育有3个~4个子女,在第一次分娩时请接生人员到家里接生,后面分娩时由产妇家属辅助产妇分娩。家属接生的消毒知识源自于头胎分娩时接生员消毒操作的模仿。
案例1:村民DFZ(男,72岁)这样讲述他家的生育故事:“我有5个子女(3女2男),生大女儿的时候请了接生婆XZL来接生的,后面四个就没喊人来接生了。都是我自己接生的,怎么接生呢?就按照生老大时接生婆的接生方法来做,消下毒。把接生要用的东西(剪刀等)放锅里煮一下,然后再用碘酒消毒,没有碘酒就用酒,就是我们平时喝的这个酒都可以。消毒后就可以用了。”[2]39-40(访谈资料:DFZ20160902M72)
由此可见,在当地请接生人员上门接生,并不完全意味着是请经过国家新法接生培训的接生员接生,更是意指“请消毒观念接生”。新法接生所宣传的消毒知识,也随着接生员和乡卫生院的人际关系进入到当地的人情网络之中。陈志潜的定县试验也是使用“本村人”推动,让村民对西医治疗方法更信任,更容易接受[5]267。为了推广新法接生,依靠本村人担任妇幼保健员建立保健体系。新法接生所强调消毒灭菌的知识和药品、工具等经由接生人员以及乡卫生院医生同村民的人情交换,进入到当地人日常生活之中。
案例2:村民DFS(男,74岁)讲述了他作为丈夫后来敢于为老婆接生的底气和心态:“生老大时,我们请了接生员的。后头再生时,乡卫生院一个很熟的医生对我说,不用请接生员,只要自己做好消毒就可以了。他就教我怎么消毒,还给我拿了碘酒、药水和纱布这些。现在想来那时候胆子好大,就凭着生老大的经验和熟人医生教的消毒方法,真的就是我自己处理的,也没觉得生娃是个好危险的事情。”(访谈资料:DFS20160831M74)
在当时的各种宣传中,将细菌描述成是导致产妇和新生儿感染的根源,像“洪水猛兽一般”。赵婧[6]认为在西医细菌学的审视下,产婆未消毒的手就是使产妇感染产褥热而亡的主要原因。村民有了对细菌的“科学”认知,也逐渐形成了“消毒灭菌”观念。当地广泛熟知和使用新法接生,在已往的分娩行为中加入了消毒环节。也就是说,国家大力推广新法接生过程中,村民请接生员上门接生的行为,事实上是对细菌更加“深刻而科学”的认知之后,请的一种“消毒”观念上门接生。医学上消毒灭菌的知识、方法等,因纳入到当地人情网络之中,而被广大村民接受,新法接生得以推广和落实。
2 产妇“走出去”的时代背景与分娩选择
2.1 住院分娩——难产与高危时的选择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Z村村民通常会在家分娩,但遇到难产的时候,会将产妇送往医院。他们觉得医院会更加安全有保障,能为难产的孕妇提供帮助。临产时,如果在家生了两三天都生不下来,便会认为是难产,进而送往医院。另一种情况是接生员(婆)在接生的过程中,判断分娩有困难时,也会建议将产妇送往医院。接生员QGS(女,70岁)的接生体会是:在接生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有些可能直接影响分娩结果,因此,在她去接生的时候,首先要判断这次接生是否能顺利完成,如果觉得可以才会替产妇接生,如果不可以的话则建议家属直接送往医院。不仅如此,她认为就是送往乡镇卫生院,有时候也不一定能行,还得送往上级医院(访谈资料:QGS20160205F70)。由此可见,她认为医院比接生员更专业、更安全,层级越高的医院越安全。下面有两个难产送医院的案例。
案例3:DZH(男,51岁)妻子在1986年第一次分娩时,最初也选择了发作后请接生员接生,但生了两三天都没能成功娩出,后将产妇送往医院,入院后,新生儿未能保住。有了此经历后,第二次怀孕临产时直接去医院,分娩成功,母子健康(访谈资料:DZH20160210M51)。
案例4:村里DZH(男,64岁)妻子则没这么幸运,第一次分娩1972年。他们家每一次分娩都是难产,胎位不正,横位、臀位等情况都出现过。分娩几次大都是新生儿死亡的结果。中途有一次难产送往医院,也没能改变新生儿死亡的命运。最后一次怀孕分娩时,请接生婆XZL守着分娩,终于生育儿子DZB,但生下来时也快不行了,接生婆采用人工呼吸等方式才将他救活(访谈资料:DZH20160831M64)。
这两个案例都是难产时选择送往医院分娩,然而她们去医院分娩的行为,并没有带动当时周围的人都去医院分娩,大家仍旧在家分娩,并且大家对她们去医院分娩的记忆都很模糊,没有成为当时社会的集体记忆,大家觉得是因为她自身的缘故(孕妇自身不好生,胎儿过胖、过大等原因),才导致分娩困难,其他人没有必要效仿。
除了难产时送往医院的临时救急行为,后来Z村因计划生育政策的强制妇科检查塑造了“高危孕产妇”这一人群,接生员和村干部则动员这部分人群主动选择住院分娩。现代医学通过一系列的检查来“制造”数据,在怀孕之初便建卡入档,纳入系统管理,将孕产妇个人从有血有肉的生命转换成众多冷冰冰的数据,医务人员试图透过这些数据来掌握孕妇的身体状况以及体内胎儿发育情况。孕产妇在选择接受检查的同时,也将自己置身于医学的监控之中。
2.2 务工浪潮下的分娩场所选择
育龄妇女外出务工加快了住院分娩的实现过程。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Z村人就开始到福建、广东等沿海省份打工,到了90年代末,Z村各家青壮年、年轻夫妻都出去打工了,而且务工地基本上都在福建省晋江市。对于农村外出务工妇女怀孕后是返乡分娩还是在务工地分娩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农民工大都会返乡生育,而Z村返乡生育的人并不多,几乎都选择在务工地分娩。原因在于,务工地的诊所既符合新法接生的基本安全诉求,也能满足村民躲避计划生育政策超生二胎的生育需求。另外,Z村地处西南,与沿海的务工地相隔千里,返乡生育会有一笔不小的路费开支,当时的交通在路上也需要耽搁两三天的时间。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务工地诊所成为了村民分娩地的新选择。
经调查,在晋江务工的Z村人居住地相对集中,在那里,一位当地的个体医生开了一家诊所,主要给农民工看病,诊所医生的儿媳妇会为务工的“老乡们”接生。但诊所条件有限,只能顺产分娩,如有剖腹产需求,则会去当地医院。1999年~2016年,Z村共有12名婴儿在该诊所出生,在务工村民眼中,诊所接生员很专业,在这里生孩子很安全。不过,这家诊所的接生员因为一次接生事故而被起诉,后来这里便不再接生。这次事故也让务工村民意识到在私人诊所分娩还是不够安全,从反面强化了正规医院分娩的安全性。他们认为医院“背靠国家”,是非常强有力的保障,医学可视化也可满足村民对胎儿风险的所有想象。
经济条件也是影响村民选择分娩地点的影响因素。对经济条件日益变好的村民来说,医院分娩更好、更安全,因此住院分娩越来越多。
案例5:在2010年,村民ZHJ(女,25岁)在务工地医院分娩了她的第二个小孩,而她大女儿是在前面所说的私人诊所出生,她前后选择分娩地的原因在Z村具有代表性:在她生育大女儿之前,她的嫂子曾在私人诊所生了一个女儿。在她生大女儿时,她的婆婆(丈夫的母亲)建议她也去诊所生,因为大家都在诊所生的,而且费用便宜,也便于照顾。她和丈夫考虑到当时家里没多少钱,也就选择在诊所分娩。后来,他们开了一个店铺,收入大大提高,在生第二个孩子时就选择去正规医院了。对此,她的丈夫感慨道:“生老大的时候穷啊,没钱,生老二的时候条件好些。”[2]61-62(DXW20160211M30)
可见,村民在分娩选择时会考量经济因素。此外,新生儿上户口必须出具《出生医学证明》,这一制度设计也促进了住院分娩。根据《母婴保健法》规定“医疗保健机构和从事家庭接生的人员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出具统一制发的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但是在医院出生的小孩可以很方便地办理《出生医学证明》,而在家出生的孩子需要提供一系列证明材料才能到县级以上卫生行政管理部门或指定《出生医学证明》管理机构办理出生证,比较麻烦。
3 话语、观念与行为规训
福柯认为权力有多种形态和运作方式,话语就是权力的一种形态和表达方式。在话语中,权力与知识结合到一起[7]。话语产生于实践,又反过来对实践产生影响,它甚至参与建构话语的主体身份,建构着社会关系和社会观念[8]。通过对Z村分娩地点考察,可以看到从在家生娃到住院分娩的这一变化过程。生物医学知识以科学话语的形式进入我国,并在孕产行为中得以不断深化和扩展,最终实现了从在家生娃到住院分娩的转变。
“一躺三消毒”是新法接生的重点,也是关键话语,它从分娩姿势和消毒灭菌上规训产妇和接生员的行为。“一躺三消毒”话语潜藏着异常孕产现象知识体系的变化,产后大出血被认为是坐着分娩的姿势导致了血液下流,新生儿脐风归因为细菌从脐带剪断处跑进了婴儿体内,产褥热也是由于细菌从接生员的手、产妇外阴部等进入产妇体内。“细菌”作为一种微生物,原本就长期存在于村民的生活世界之中,然而在西方医学进入之后却被认为是影响分娩结果的重要因素。罗芙芸(Ruth Rogaski)[9]指出,西方医学知识塑造了中国人的现代卫生要求。
细菌在分娩中被如此高度的重视,不仅仅与分娩高风险性有关,更来自于“细菌战”的宣传,细菌被建构为洪水猛兽、战争武器。苍蝇被认为带有很多细菌,在细菌战的语境下,出现“打死一只苍蝇,就是消灭一个敌人”[10]的宣传话语就不足为奇了。杨念群[5]495-500认为细菌战使防疫成为日常生活政治,使卫生进入日常话语,“爱国卫生运动”更是成为一种经久不息的正式制度和国家话语。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到了1970年代,卫生防疫、消毒灭菌已完全进入了Z村的日常话语和生活实践之中。不仅如此,Z村还“扩大”了细菌的概念,细菌逐渐等同于村民认知中的“脏”,是不卫生的、不洁的。在分娩时这种脏的东西会污染产妇和新生儿,导致产妇得产褥热、新生儿感染破伤风等疾病,因此,细菌逐渐被污名化,消毒灭菌不可抗拒地成为了村民的主流认知。在这种知识体系和大众认知下,躺着分娩和消毒灭菌在分娩过程中成为最优选择。
“一躺三消毒”话语改变了人们分娩姿势和消毒操作,“优生”和“分娩安全”话语则进一步影响着村民的孕产行为,使得在家的消毒分娩逐渐走向住院分娩。“优生”和“分娩安全”话语通过一系列的时间、空间、制度等形塑了分娩要求。医学检查对时间(如检查定期)、空间环境(如无菌器皿、检验设备)、身体状态(如空腹与否)和检验指标等都具有严格要求和规定,这是对医务人员和孕产妇的直接规训。定期妇检制度更是以国家权力要求育龄妇女必须定期进行妇科检查并接受分类管理。医务人员对所得信息和数据进行分析和筛查,数据是否在正常范围内成为医务人员判断孕妇并发症的主要依据,并以此筛选高危孕产妇来重点监控。若发现高危孕产妇,则要重点监控和干预管理。在一次次的医学检查中和政策舆论中,知识、权力和话语相互交织,孕产妇被“全景式”监控,“优生”理念也不断得以内化,高危孕产妇更是面临被强化的生育风险,只能寻求专业的医疗救助,她们的孕产行为被规训。
“分娩安全”的话语与医院的专业知识、专业环境和专业人员等知识条件一起,促使村民们接受了围产期保健和住院分娩的基本要求。杨念群[5]612曾注意到西方医学分娩技术早期进入中国传统社会时,对人们的价值和观念有较大冲击与挑战。孕产行为控制权从女人那里转移到医学专家手上,怀孕妇女对自己身体和胎儿的具身知识被更为客观的医学检查手段所取代,她们所拥有的知识的价值也逐渐被贬值[11]。村民们越来越意识到,医院不只是一个严格消毒灭菌的场所,而是具有专业人员、专业知识、高科技设备、完善救治体系和丰富经验的专业场所,能降低分娩风险,有效化解风险,实施紧急救治,保证母婴安全。对医院的“专业”认识程度越深,村民住院分娩的行为就越彻底。
4 结语
“一躺三消毒”话语形塑了村民对细菌的认知,规范了新法接生的分娩姿势和消毒操作。在具体实践中,村民将消毒灭菌操作纳入到原有的接生知识中,在传统的接生步骤中添加了“消毒”环节。推广新法接生时,医疗机构和村民认为做好“消毒”就行,只有遇到难产等紧急情况时,才会送到当地医院。随后计划生育政策严格执行的阶段,在“少生”的目标下,“优生”是国家和村民共同的心愿,为此所实行的强制妇科检查及“高危孕产妇”管理机制,是村民从在家生娃到住院分娩必不可少的一环。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通过政策(妇幼保健政策、计划生育政策等)与法律法规(婚姻法、妇幼保健法等)在地方的落实中,与医学话语达成共谋,形成了以住院分娩为核心的“分娩安全”话语。加之外出务工、收入增加、医学出生证明制度等现实条件的作用,使得人们主动住院分娩。
在现代知识强势背景下,地方性知识在逐渐消失[12],不断发展的现代生物医学知识不断进入乡村社会网络,通过对传统孕产知识的融入、转化和替代,逐渐形成权力知识话语,规训孕产行为。面对不同的孕产知识话语规训,Z村村民并非被动接受,而是在不同的社会发展背景和经济条件下,出于人情交往与实用主义考虑的主动应对与合理选择。围绕孕产知识形成的各种话语在乡村社会网络的权力运作实践,与村民们对各种话语规训的积极应对与主动选择,共同促成了从在家生娃到住院分娩的孕产行为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