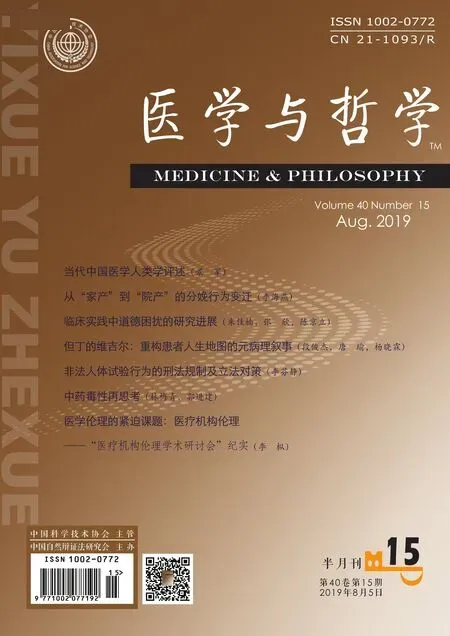遗传与进化视角下人类“失配现象”之辨析*
邓芳芳 贺竹梅
人作为最高等级的生物,在很多情况下,总是充满自信和自豪感,赞美人体结构的诗歌和艺术作品也是丰富多彩。然而,实际上人类还是存在许多“不合理生理结构”的,如智齿、秃顶、脊椎结构与直立行走不兼容、高度近视、甲沟炎、心肌炎等。那么,从遗传与进化的角度怎样解释这些结构的存在呢?它们会以什么样的趋势在人类中演化呢?
“自然进化”强调生物中群体的变化过程,是某一生物群体的遗传构成发生了变化,并将这种变化遗传给后代的过程[1]163;而文化进化是具有类似于生物进化过程中相对应的传播、创新、随机波动和选择过程,其“结构重组受时间影响,最终产生一种在本质上与祖先形式”不同的结构或形式过程[2]。文化进化领域是一个基本的跨学科领域,能弥合各学科之间的差距,促进不同学科的相互联系[3]。人受到“自然进化”和“文化进化”的双重压力,因此,只有从“自然进化”与“文化进化”的双重视角来审视人类的发展进程,才能理性地看待人类“失配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及其可能的发展趋势。
本文试图从智齿、秃顶、脊椎结构与直立行走不兼容、高度近视四种人体“失配现象”出发,以遗传与进化的视角,探讨其功能及存在的意义。并以其为基准,理解类似“不合理生理结构”的大致发展规律及其存在意义,以期与相关研究者进行共同探讨,并为相关人士提供心理慰藉。
1 智齿也许是生物进化中“失配性疾病”的一个佐证
智齿在医学上定义为人类口腔内牙槽骨上最里面的第三颗磨牙。智齿的萌出时间比较晚,一般在18岁~24岁,在这个阶段,人的生理、心理发育都接近成熟,所以是“有智慧到来”的象征,故得名。从发育的角度来看,所有乳牙和其他恒牙都开始于子宫内发育,但智齿的发育开始于外胚层齿板,该齿板在发育中的5龄儿童口腔中向远端迁移,在空间上与颌骨间充质相关并相互作用[4],其发育起源与时间均与乳牙和其他恒牙不同,所以也将智齿称之为第三套牙齿。
许多研究表明,骨骼和牙齿结构存在不同程度的遗传性,如Harris等[5]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颅面形态具有较高的遗传力,而牙齿特征却具有较低的遗传力,更易受环境的影响。这又与后牙的减少和变异的形态发生场理论一致,即由于共同场的影响,每颗牙齿与附近其他牙齿存在相似性,但由于位置不同就会存在等级差异[6],所以牙齿形成分生组织序列是与场梯度的生物学特征密切吻合的[7],一旦牙齿出现异常(即打破形态发生场),则环境因素对异常牙齿的影响增加,而异常因素对其影响减少。
人类牙槽骨由于长期面临进食的精细化而在长度、宽度和强度上呈现不同程度的退化,致使下颌骨越来越窄,但牙齿数目依然如故,所以下颌骨由于无法提供充足的供智齿萌出的空间而造成智齿萌出异位、阻生。有研究表明,在瑞典20岁~30岁人中,75%的人至少含有一颗阻生智齿[8],说明阻生智齿的发生率是较高的,加上智齿本身的退化也会导致萌出数目不足、呈现不对称萌出等,情况则因人而异。这些萌出的异常加上清洁的困难,通常在临床上表现为智齿冠周炎,并可能破坏邻近的牙齿,造成邻近牙齿的龋齿、牙周炎、牙髓炎等疾病,引发剧烈的疼痛、肿胀和感染。此外,Tevepaugh等[9]研究指出:有第三磨牙的下颌骨比没有第三磨牙的下颌骨发生角度骨折的几率要高3.8倍,而Reitzik等[10]提出,阻生第三磨牙的下颌骨断裂所需的力比第三磨牙充分萌出下颌骨断裂所需的力少40%,并认为未萌出的第三磨牙占据了更多的骨间隙,而这可能会削弱下颌骨,使其更易断裂。所以面对智齿可能带来的危害,Srivastava等建议,当智齿近中成角(mesial angulation)在30°~70°,且会造成第二磨牙远端龋齿的时候,则需拔除[11]。有文献表明,智齿的拔除率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估计每年每1 000人中有4人,使其已成为十大住院病例之一[11]。但在拔牙过程中又容易出现神经损伤等医患问题,这就使拔牙的恐惧感进一步加大,智齿被人厌恶的程度进一步加深。
从上来看,智齿的存在似乎是“女娲造人”所忽略的一个漏洞,那智齿的存在又有什么意义呢?其又是如何随着人类进化而被淘汰的?从进化的角度来说,牙齿有其个体发育及系统发育过程,才能形成相对应的形态及功能,这是与环境相适应的结果[12]。早期古人类主要以浆果为能量来源,也就形成了铲子形状的宽门牙(非常适合咬果子)和臼齿齿尖很低(形状极其适合研磨富含纤维的果肉)的外在特征[13]29。而随着气候动荡变化,森林、草原面积逐渐减少,古人类能够获得的食物来源锐减,在食物匮乏进而上升至生存压力情况下,古人类开始寻求次要食物,如植物的茎和叶来延续生命,虽然这种后备食物碳水化合物含量高,但纤维含量更高,所以就需要不断地咀嚼来获取其中的营养物质,为了更好地咬碎更坚硬、更紧实的食物,牙齿也就进化得宽大、厚实且平坦。到了旧石器时代,人类学会使用工具及火的出现,使其能对块茎、肉等营养含量丰富的食物进行简单粗加工,加工的目的是增加食物的食用度、健康度及获得更丰富的营养,但食物加工反过来又使人类的牙齿和咀嚼肌变小;到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现代社会时代,颌骨和牙齿尺寸减小驱使的牙齿咬合变化越来越明显,预期将来颌骨尺寸会进一步减小[14],也就意味着智齿萌出空间会进一步减少。结合Sasso等[15]对智齿发展趋势分析,指出与过去30年相比,智齿已有明显的成熟趋势,且主要体现在矿化时间提前,其中,男性上颌骨智齿矿化平均提前了0.8个月,下颌骨矿化提前了8.7个月,而女性上颌骨和下颌骨则分别提前了2.6个月和2个月。由此可以看出,未来智齿萌发后的命运是:由于矿化时间的缩短,对人们造成的伤害可能会更严重,预计被拔除的可能性会更大。人类从食物缺乏过渡到食物充足也只有几百年的时间,世界上尚且还有很多地区处在食物匮乏的状态,所以这个转变过程太快,以至于人类的身体还没有来得及“进化”出相应的结构来应对外界环境的改变,也就是人类还没有形成阻止智齿生长或规避其生长的途径,所以智齿就成了人类进化过程中遗留的“化石”,其悄无声息地生长在身体的某一部位,只有其突如其来的疼痛,才能让我们意识到其存在,它以自我厌恶的形式完成了自我的凸显,恪守着人类进化长河中其应处的位置。因此,智齿也可以解释为是生物进化中“失配性疾病”的一个佐证。
2 高度近视是人类文明遗留给人类的外在枷锁
高度近视是指单眼屈光度高于 -6.0D(600度) 的屈光不正。虽然不同文献对高度近视屈光度的定义存在一定的偏差,但其典型特征是轴向长度延长,并能引起各种特定的并发症,包括白内障形成、近视性视网膜凹陷和青光眼等[16]。这些并发症大多会危及视力,常导致不可逆转的视网膜光感受器损伤,从而致使视力丧失。
高度近视患者占近视人群的27%~33%[17]。鉴于目前全球教育力度逐渐加大和网络科技的发展,近视有一定的上升趋势。为了预测未来近视甚至失明的可能性,相关研究者进行了大量的元分析以估测其流行趋势。其中,Holden等[18]的研究表明,随着社会文明的推进,近视和高度近视人数在全球呈急剧上升趋势,预计到2050年,近视人数达50亿,高度近视则将突破10亿。由于近视越来越呈现普遍化、低龄化的趋势,所以很多准妈妈们开始担心父母倘若是近视,会不会遗传给孩子?有文献表明,近视眼父母比非近视眼父母更容易产生具有近视的后代,且与西方国家相比,亚洲发达国家的近视眼患病率较高,说明近视眼的发展具有遗传易感性[19]。因此,可以说近视是可以通过双亲遗传给子代的性状,但目前人们对近视的遗传机制尚不清楚。家系研究发现,近视为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或常染色体隐性遗传,也有观察为罕见的X性连锁隐性遗传[17]。大部分学者都支持遗传和环境因素均对促成高度近视起到一定的作用,并且是由多基因控制的数量性状遗传,但两者在高度近视中的相对作用却一直存在争议[20]。既然环境因素影响眼发育的概念已在动物实验[21]和流行病学[22]中都得到很好的肯定,那么大多数研究者趋向于选择研究与高度近视显著相关的高危遗传位点来窥探其内在机制,连锁遗传分析发现,由于群体的异质性,一系列潜在候选基因的遗传位点与高度近视眼有着模糊的关联[19]。目前已证明有些遗传位点是可能的候选基因,如转化生长因子(TGF)-β诱导因子基因(TGIF)[23]、钾通道蛋白基因(KCNQ5)[24]、胶原I型基因(COL1A1 rs2269336)[25]等,但都存在所选样本数量不够大,造成统计结果与预期不相符。随着全基因组连锁分析的深入研究,与高度近视有关的高频区域的发现可为未来越来越严峻的近视趋势提供分子机制的解释甚至候选解决方案[17]。如Li等[26]利用基于单核苷酸多态性(SNP)连锁的全基因组分析来鉴定高加索人与近视相关的基因位点,为全世界确定与高度近视和眼生长有关的基因提供补充;Li等[27]采用全外显子与全基因组测序,发现长波敏感性视蛋白-1(OPN1LW)的独特变异与高度近视显著相关等。
就近视这样一种复杂的遗传性状而言,户外时间的减少和短距离工作活动的增加等因素的综合作用所导致的生活方式的改变是不容忽视的[28],否则不能解释短期内急剧上升的高度近视比例[29]。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在原始社会,早期人类生活在一个开阔、视野所及都是“青山绿水”的环境,加上为了维持基本的生存条件,早期人类需不断外出寻找食物,且在寻找的过程中,视力较好者往往更易抢占先机而获得更多的食物,而视力较差者可能因为得不到基本的食物而面临着被淘汰的“自然选择”。在农耕文化开始之后,人类开始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这种生活方式并不会对视力产生负向选择压力。所以经过上百万年的自然选择,人类眼球结构几乎达到完美地步,但是,与任何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一样,细微的变化就可能损害其功能,近视也不例外[13]186。随着社会进步,当食物、常规疾病等已构不成威胁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时,世界人口开始呈现指数式增长,但地球总陆地面积是有限的,所以人均陆地面积开始急剧缩减以致个人活动范围受到限制;另一方面,高楼大厦已成为城市化的一个外显性标志,其在很大程度上阻挡了人类的视线,加上光污染、大气污染等因素,所以在现代化氛围下人类的眼球变得过长,晶体需要收缩睫状肌使晶体凸度加大,才能聚焦近处物体,但是,当眼球过长的人试图通过放松睫状肌而聚焦远处物体时,被扩展后的晶体由于不能很好地恢复到原状而使焦点落在视网膜的前方,结果是,一切远处物体(通常超过2米)都失去了焦点[13]186。所以,近视也就成了社会文明进步所遗留给人类的外在枷锁。
3 人类脊椎结构的进化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吗?
人类的脊椎结构与直立行走是不兼容的,通俗点说,就是伴随着人类大脑的发育,人类开始从爬行向直立方向转变,但脊椎结构并没有跟随直立的进化而同步进化,因为脊椎结构感知变化的时间要比直立时间晚,只有直立之后才会给脊椎递送变化的压力,从而定位进化的方向,所以,当人类站起来之后,脊椎还处于爬行所适应的那种状态,却不得不承担起全身重量的责任,所以现代人类的脊椎问题也就接踵而至。
为了研究直立行走的转变过程,相关学者运用了一些简化模型,如双足弹簧质量模型来预测人类及鸟类的步行动力学,研究表明,人类可以通过引导质点(centre of mass,COM)高于地面反作用力的某一点来稳定行走,并将这一点称之为虚拟支点(virtual pivot point,VPP),根据VPP的位置来调整如何稳定两足动物身形,因为位置的改变会引起地面反作用力对相对躯干角度(即躯干和臀部之间测量的角度)产生正反馈或负反馈,如VPP高于质点,那么髋部扭矩会降低躯干和髋部与受力点之间的偏差,呈现负反馈状态,而负反馈又反过来稳定了垂直和前叉步态的VPP模型,反之亦然[30]。VPP很好地解释了人类是如何从爬行稳定为直立行走的。
人类已有600万年的进化历史[13]190,且在不断经历行走锻炼过程中已逐渐适应直立行走的地面生活。那么,已经适应四足生活的人类为什么会改变其生活方式,选择两足方式?目前比较普遍认同的假说有如下几种:第一,警戒说(the watching out hypothesis)[31],由Dart于1959年提出。其背景前提是人类离开丛林来到了宽阔的草原,在这种情况下,采用直立的姿势存在观察周围环境的视觉优势,更利于狩猎和防守食肉动物,有益于在草丛的生活和繁衍。第二,解放双手假说(the freeing of the hands hypothesis)[32],该假说可追溯到达尔文所著《人类起源》一书,其背景是早期人类还生活在丛林中,认为解放双手用于工具使用、武器处理、食物收集和自卫是人类采用双足姿势和运动的主要原因。第三,投掷假说(the throwing hypothesis)[33],由Kirschmann提出。专门使用武器是早期古人类的关键适应,而直立行走则是作为一种后继适应而发展起来的。此外还有婴儿携带假说(infant carrying hypothesis)[34]、热调节假说(thermoregulation hypothesis)[35]和携带食物或供给说(carrying food or provisioning hypothesis)[36]等。上述假说的背景都是在广袤的大草原展开的,但近年来研究者们逐渐提出应考虑海岸这种生境,并提出了海岸居民假说(shore dweller hypothesis)[37],该假说认为在森林破碎造成的食物日益短缺的情况下,海岸有大量的优质食物,又能周年供应。且双足涉水能使后肢关节从一些非生理压力中释放,加上水能够提供粘性和浮力,在“四足-两足过渡的平衡阶段”减少伤害等有利于产生直立行走正向选择压力的优势。结合Adolph等[38]关于“为什么婴儿在熟练掌握爬行后要坚持行走?”的研究结果,即与历史上熟练的爬行者善于规划他们的物质世界的观点相反,爬行是有限制的,而行走可以让婴儿看得更多、玩得更多及与他人的互动也更多,所以婴儿在熟练掌握爬行后也要坚持行走,而婴儿从爬行向行走的转变又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缩影。所以这些现象表明人类选择两足方式并不是偶然,而是适应更好生存的自然选择。
但人类还没来得及在这伟大站起来的里程碑前欢呼时,相对应的“失配性疾病”也就紧随而来。首先,椎间盘突出及女性分娩难度加大。当人类处于爬行时,其全身的重量在四肢,所以早期人类的前肢会特别长来配合腿的运动,靠近肩膀部分会很粗壮,但当人类以直立的姿势行走时,全身的重量就降大任于脊柱和骨盆,一方面会使脊柱过度负荷,易发腰肌劳损、椎间盘突出等并发症;另一方面从解剖学结构来说,由于骨盆的负重成倍增加,迫使盆骨的髂骨翼向两侧扩展,脊柱腰段出现明显的前凸性弯曲,从而导致骶骨岬显著突出,同时使骨盆上口做了大约90°扭转,并且还在骨盆的某些部位加强了若干韧带装置。这些措施使得人类骨盆的负重能力和平衡能力大大加强了,但由于其失去了必要的灵活性,所以骨性产道的分娩难度也加大了[1]204。其次,人类的垂直运动使人体各部位受地心引力不尽相同,所以会使腹腔、胸腔内的器官下坠,从而引发胃下垂、子宫下垂,甚至流产等。第三,脑供血不足引起的头痛、头晕、眩晕等。伴随着人类站起来的同时,人类的头骨也得到了迅速的进化,并且头骨的重量也逐渐增加,为了维持大脑正常的生理需求,其正常运转所需的供血量也就比进化前相应地要增加,加上心脏在大脑的下方,需要克服地心引力向大脑供血,难度也就进一步加大,所以当人类在地上蹲一会儿起来后会感到大脑供血不足,出现眩晕等现象。尽管人类从爬行到直立行走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但在人类进化过程中还是存在种种进化失配问题,这也间接表明了人类目前的状态并没有进化到最佳,人类进化的脚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话虽如此,但人类文明的发展特别是现代信息科学的高速发展也许已经扼杀了这种趋势。
4 秃顶的优势与折磨
秃顶解释为头顶脱发或头顶无发的现象,是一种永久性脱发。秃顶通常认为是从性遗传(sex-influenced inheritence),虽在两性中都有表现,但在两性中的发生频率及杂合子基因型在不同性别中的表现是不同的,在现实生活中,男性秃顶的人数要远大于女性[39]。造成秃顶的原因除了与遗传基因相关外,还与雄性激素的分泌水平相关。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不同部位毛发的生长受不同雄性激素的控制,如腋毛及阴毛的生长受睾丸酮控制,而胡须及双颞部、顶部头发的生长则受二氢睾酮(dihydrotestosterone,DHT)的控制[40]。另一方面,每个部位毛囊行为和特征对激素的反应存在差异,例如,头皮前部毛囊被认为是激素敏感型,会随DHT升高而发生小型化,造成雄性遗传性脱发,但枕部头皮毛囊却对DHT无反应,所以在做植发时,需注意每个部位成纤维细胞发育起源的不同决定该部位毛囊对激素的反应也存在差异[41],要避免由于激素差异所引起的植发失败。
毛发是表皮的外在屏障,在外界环境压力下有利于保护身体免受伤害。随着人类站起来所带来的另一显著性变化是:人类进化出与大多数其他哺乳动物相比有着根本不同的毛发分布模式[42]。为了适应站起来的进化压力,人类逐渐淘汰和缩小了体毛,有些学者认为人类体毛的减退与狩猎活动有关,他们推测早期人类的狩猎活动通常需要在整个白天持续地进行,而这种生活方式就要求人类有配套的高效控制体温的装置,所以就需要汗腺大量地排出汗液,以便在水分蒸发过程中带走体内的热量,倘若人类的皮肤表面仍覆盖着厚厚的长毛,则会影响体热的散失,这可能部分解释人类淘汰体毛的原因[1]208。而人类头部毛发因为其有利于改善大脑的热隔离,却长得更长、更浓密[43]。
除了人类进化所带来的毛发分布模式变化,由于某些不适当文化习俗的影响也会导致头部毛发的退化即秃顶,如过度理发或特定类型理发会阻止头发相互之间或与外界环境的联系,从而触发了不同人群皮脂滞留在发根的差异[43],而皮脂分泌过多又会造成毛囊和毛孔被填塞,日积月累,毛发就会发生营养障碍从而停止生长,所以不同人群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脱发。
随着文化进化的影响越来越大,似乎人们的发际线也越来越上移,其优点也是存在的,譬如说,脱发能减少寄生虫的寄生,可能降低患心血管疾病和患骨质疏松的风险,可能更聪明甚至更长寿。话虽如此,但由于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的外在形象,所以人们面对越来越稀疏的头顶产生越来越多的苦恼,脱发已经成为了折磨全球人类的一种极度情绪化的疾病。
人们试图阐明不同人群不同类型脱发的确切病理原因,以便开发出针对该性状改良的药物。然而,目前并不能完全解决秃顶遗留给人类的困扰。从进化的角度来说,秃顶是如何逐渐进化失配的?首先,在人类进化过程中,食物是决定生存与否的一个关键因素,人类身体结构不仅能将多余的碳水化合物转变成脂肪储存起来,并且还对“糖”存在无尽渴望,犹如“毒药”却甘之如饴。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因生活富足食物糖分含量较高,机体主要通过胰岛素/胰高血糖素的相互制衡进行调节,但倘若糖分的摄取量长期超过调节系统阈值,就易使激素调节系统出现故障,机体除易患糖尿病外,还会存在秃顶的风险。胰岛素造成秃顶的原因在于:(1)胰岛素抵抗(insulin resistance,IR)及过量都会降低性激素结合球蛋白含量,导致高水平游离睾酮[44],而睾酮又是DHT前体,从而为脱发提供诱导剂;(2)IR引发的血管效应,如产生血管活性物质导致内皮功能障碍、微循环衰竭、滤泡周围血管收缩和血管壁平滑肌细胞增殖,这些都会造成毛囊水平的微血管功能不全和组织缺氧,从而促进毛囊的小型化[45];(3)高胰岛素血症还会增加局部雄性激素含量及睾酮向DHT的转化[46]。另一方面,数百万年来,人类一直在伴随着微生物及许多种类的蠕虫共同进化,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人体内的微生物群大多是无害的,甚至负责一些重要的功能,如帮助消化、清洁皮肤和头皮[13]175,但随着抗生素及其他类似药物的广泛使用,会消灭一些有益的微生物和虫类,也就会影响着该类微生物的功能。有研究表明,脱发与皮肤微生物菌群失调是存在内在联系的,如用卟啉类药物刺激对照组与雄性遗传性脱发(androgenetic alopecia,AGA)患者组发现,与对照组的12%相比,58%的AGA患者的皮脂腺导管中发现了角质杆菌产生的补体[47]。这些现象加上使用抗菌剂后脱发得到改善,表明脱发可能与头皮微生物区系之间存在内在联系[48]。其次,另一条脱发的可能机制是某些微生物群落引发的局部免疫反应会干扰免疫球蛋白的免疫功能,从而引发炎症和皮肤屏障功能障碍[42]。最后,由于目前食物匮乏已不再成为问题,人类不必为了寻找食物而远途跋涉,运动量的降低会减少肌肉质量,而这又有利于骨骼肌的IR[49]。
随着环境污染的加剧,脱发这样一种极度情绪化的疾病好像仍在加剧。在美国,每年用于治疗脱发的费用超过35亿美元[50]。
5 结语
虽然人类处在食物链的顶端,但目前人类的身体结构并不是臻于完美的,还存在许多亟待修补的细枝末节,但是文化进化的进程如此之快,以至于人类与按着自然界中既定进化轨迹的动物不同,人类的进化方向会受到现代文明因素的干扰,可能偏离轨道也可能原路返回,只是原路返回的可能性要小很多,更多是“超速进化”。这也就意味着人类身上需要修补的结构是否会按既定的套路来进行完善还是未知的,但我们也无须对此感到困惑或难过,因为当人类身体的某一结构出现问题时,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人类并不是自然界的主宰,请善待自然;病痛的折磨是痛苦的,请爱惜生命;个人的一生是短暂的,请努力实现人生价值。
科学的发展需要进化论的指导,加强进化生物学伦理意识,对于科学沿着有益于人类演化的方向发展,才是科学追求的真正目标。
(感谢程焉平教授为本文提供的建设性建议和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