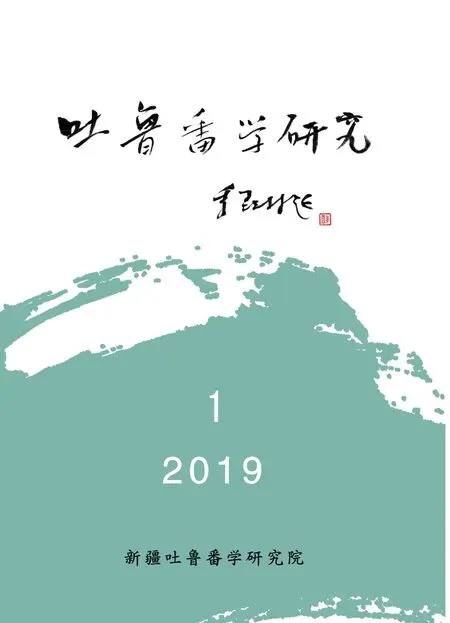胜金口千佛洞第5窟壁画中花鸟画浅析*
王小雄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胜金口千佛洞,位于吐鲁番市二堡乡巴达木村北的火焰山南麓木头沟东岸一处河湾地内,河湾呈南北向狭长条状。木头沟河从河湾西侧潺潺流过,沟内草木丛生。昔日那些脱离世俗的僧侣,在这幽静的沟谷之间开窟建寺。整个窟群依山而建从下到上分为四层,每层洞窟上、下层之间有踏步连通。除南、北寺院尚可看出部分初始形制外,中区部分因为坍塌被淤土和流沙掩埋,形成了一座高达12米多的半圆锥形土山(图片叁,1)。
近年来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两次对部分洞窟进行发掘和保护。在该区域发掘寺院两组、生活区一组、洞窟十三座、居址二十七间。此外还清理出纸质文书百余片,以及木器、陶器、绢画、织物等大批珍贵遗物。现存的13个洞窟里,有壁画的洞窟5个。由于年代久远和人为的盗掘破坏,石窟中的壁画已经漫漶不清。但是编号为第5窟的壁画中残留的几棵树木,造型准确生动,线条活泼流畅,色彩对比鲜明。这种绘画风格在新疆地区的佛教壁画中比较罕见,所以笔者以为应该予以特殊关注。
一、第5窟的现状、窟形、壁画内容及绘画特征概述
第5窟位于木头沟窟群区中段北侧,整个洞窟呈长方形,纵券顶,分为前室和后室。前室呈长方形,长约13米,宽约9米。在洞窟左、右两壁下部,各开凿有对称布局的三个小型洞窟,根据形制判断,此窟应为供僧侣们读经坐禅的禅窟。由于年代久远和保存不好,整个窟内除券顶和窟壁连接处的上半部残留部分壁画以外,其余地方的壁画已经漫漶不清。墙体底下部分的壁画被抹了一层黄泥(图片叁,2)。根据考古发掘报告得知,1960年代,玉门石油管理局在此进行石油勘探时候,将第五窟改为住房,不仅在墙上抹草拌泥遮挡壁画,还在后窟内修炕,贴报纸,钉铁钉,所以窟内塑像、壁面几乎毁灭殆尽①吴勇、田小红:《新疆吐鲁番胜金口石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6年第3期,第385页。。因此壁画主要内容已经不可考究。主窟前室左右两壁各开凿三个小型洞窟,空间较小,无壁画或其他装饰,应该是供僧尼进行禅修的洞窟(图1)。
(一)洞窟顶部
洞窟券顶部分绘有大朵团花的连续卷草纹装饰图案,窟顶和两侧壁连接处,绘有连续的对称三角纹和垂帐纹。团花和三角纹之间有一圈连珠纹,三角纹的边沿飘着流苏,边上用赭红色的细密线条画出垂挂的帏幛。由于烟熏和部分地方脱落,图案里面的细节部分漫漶不清(图2)。
(二)前室正壁
前室正壁的中间有一扇门洞,门洞里面有一处像是床一样的平台。根据墙面破损处露出的墙皮底面,可以看出整个洞窟的壁面敷了一层由麦草、黏土等混合成的泥层做地仗层,然后再涂一层白色石灰,增白墙面。
门洞的顶上部中央,绘有两棵相互交叉的树。前面的树干用白色的颜料画成,就像花鸟画的“没骨”画法,树干自然的向左伸展,树枝上画了一些红色的树叶(或者是果实)。树下面站立一面朝洞窟身着白色僧袍的僧人,面部和下半身部分因色彩脱落而漫漶不清。
后面的树干用深赭石色画出,树梢部分五根枝条自然地向右边伸展,柔软的细枝自然地下垂,摇曳生姿。两棵树干前后交叉,黑白对比强烈,突显出两棵树之间的距离感,构成一幅双树图。树的右边部分留有一小块榜题,内容漫漶不可辨认(图片叁,3)。
对于此双树的描述,考察报告认为这种树木的表现风格应该是摩尼教的洞窟壁画。《新疆吐鲁番胜金口石窟发掘报告》中写到:“在编号5号窟内,考古人员发现了摩尼教典型的生死树壁画,即同株大树一半生,一半死。在吐鲁番的伯孜克里克石窟群的第38窟也有一幅展现生死树的壁画,两者如出一辙,此种表现方法,应该是摩尼教典型的生死树壁画。”②吴勇、田小红:《新疆吐鲁番胜金口石窟发掘报告》,第358页。并用距离此窟五公里处的柏孜克里克石窟群第38窟的树木形象来对比。
对于此观点,有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柳洪亮在《吐鲁番胜金口北区寺院是摩尼教寺吗?》一文中说,该窟所见交叉树采用的是白描写实手法,与摩尼教概念化的“光明树”不同③柳洪亮:《吐鲁番胜金口北区寺院是摩尼教寺吗?》《吐鲁番新出摩尼教文献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238页。。杨富学在《吐峪沟半白半黑人骨像“摩尼教说”驳议》一文中通过文献论证也指出:“……以上足以说明,胜金口第4窟之交叉树当与摩尼教无关”①侯明明、杨富学:《吐峪沟半白半黑人骨像“摩尼教说”驳议》,《吐鲁番学研究院》,2013年第2期,第90页。。
对于以上两位研究者的观点,笔者非常赞同。同时笔者认为,该窟所见交叉树以及前室左右墙壁上残留着六棵不同表现技法的花树,采用的是五代宋元以来流行的“没骨”画法,树木的表现内容和回鹘时期的树木崇拜观念有一定的联系。
(三)前室左壁壁画
主窟前室左右两壁各开凿三个小型洞窟,洞窟宽大约为0.8、高0.7、进深0.45米。龛顶部为券形,空间较小,仅能容纳一人,窟内用白灰粉进行简单的粉饰,无壁画或其他装饰。这类小型的排列组合禅窟,是供僧尼进行禅修的洞窟,性质与寺院的禅房相同。禅窟的左右墙壁上,各画了三组花树,可能表现的是僧侣们在树林中坐禅修行。树木的上部部分保存的较好,下面树干和树根部分被新抹黄泥层叠压覆盖。
门左壁的第一个禅窟C1墙面,用赭石色颜料勾画了树的树梢,线条随意生动。可惜的是由于烟熏和色彩脱落,树叶的形状和颜色已漫漶不可辨认。树的右边部分留有一小块榜题,内容已不可辨认(图片叁,4)。
左壁第二个禅窟C2墙面,树干用红赭石色颜料勾勒,树冠部分用白色的颜料,密密麻麻的画了好多对称的树叶,显得枝繁叶茂。树叶的形状和柳树叶子比较相似。树上结了一串串成熟的葡萄,由于年代久远和烟熏,葡萄的色彩呈黑色。树的右边部分留有一小块榜题,内容漫漶不清(图片叁,5)。
葡萄,又名蒲桃,最一种古老的果树树种之一。《史记·大宛列传》载云:“大宛以葡萄酿酒,富人藏酒万余石,久者十数年不败。张骞使西域,得其种还,中国始有。”②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41页。说明在汉代张骞使西域时候,西域已有葡萄的种植,并由此传到了中原。葡萄纹样大多出现在工艺品的装饰部分。在佛教造像和佛教壁画中,葡萄树的形式很少出现。胜金口千佛洞壁画中滕枝上挂着一串串沉甸甸的葡萄,令人奇怪的是,葡萄树上长以白色的却像是柳树的叶子,这种葡萄树的造型和表现方式,在吐鲁番地区以外的地域很少见到。
左壁的第三个禅窟C3墙面,一株用白色颜料勾画的树,叶子也用白色的颜料画成,树叶的形状由于风化严重而看不清楚。树枝之间有一只白色的飞鸟展翅在林间飞翔。相同的飞鸟形象在高昌故城壁画和吐峪沟壁画中也有出现。壁画侧面有汉文和回鹘文题记框,榜题文字已经不可辨认(图片叁,6)。这种题记方式较明显地具有西北敦煌地区石窟壁画的特点。同时这种用白色颜料来直接表现树和叶子的画法,在敦煌壁画中有相似的表现方法(图3)。
(四)前室右壁壁画
右壁的第一个禅窟C4墙面,树干用红赭石色颜料勾勒,树上用白色的颜料画出对称的树叶,枝干、树叶的形状和柳树叶子比较相似(图4)。
柳树是古人最早认识并大量栽植的树种之一。柳树是春天的标志,在春天中摇曳的杨柳给人以欣欣向荣之感。在佛教壁画中,有关柳树的图像很多。敦煌壁画第402窟中的隋代壁画里,就有柳树形象的出现。第217窟为盛唐时期的壁画,在图中也有大量的柳树,而且树干的表现技法和此窟的技法极为相似,所以笔者认为,这种技法应该受到敦煌壁画的影响。
右壁的第二个禅窟C5墙面,树干用红赭石色颜料勾勒,树上用白色的颜料画了好多对称的树叶,树叶的形状和柳树叶子比较相似。树上结了一串串的葡萄,由于烟熏和风化,葡萄的色彩呈黑色(图片叁,7)。
这种带柳叶状葡萄纹在胜金口千佛洞的壁画上比较常见。葡萄的形状和色彩在整个壁画中没有大的变化,仅在不同树木中造型略有区别。所以笔者认为,这种带柳叶状葡萄纹的基本形式应是此期壁画中经常出现的装饰纹样。
右壁的第三个禅窟C6墙面,有一株用赭红色颜料勾画的树干,树干左右伸展,显得生机勃勃。树上用白色的颜料画了树叶,树叶的形状模糊不清,分辨不出树的种类。此窟的里面还有一个小洞窟,窟内用白灰浆进行简单的粉饰,窟三面墙上开有小龛。整个窟内无壁画或其他装饰(图片叁,8)。
二、壁画中“花树”的表现内容和技法风格特点
关于对胜金口千佛洞壁画中的树木,有研究者认为具有摩尼教绘画的风格特点。也有研究者认为,该窟所见交叉树采用的是白描写实手法,与摩尼教概念化的“光明树”不同①柳洪亮:《吐鲁番胜金口北区寺院是摩尼教寺吗?》《吐鲁番新出摩尼教文献研究》,第238页。。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胜金口千佛洞壁画中树木的表现内容,应该和回鹘时期的树木崇拜观念有一定的联系。同时壁画中交叉的树木以及前室左右墙壁上残留着六棵不同种类的花树,是五代宋元以来流行的花鸟画中“没骨”画法的表现技法。
(一)佛教艺术中树木崇拜的观念
树木是古印度佛教绘画中的的主要装饰景物之一,尤其是有关释迦牟尼一生的传说,从无忧树下降生,到菩提树下降魔、成佛;再到七叶树下的转轮传道,以及在婆罗双树下涅槃,和树木有密切的关系。佛教典籍《增一阿含经》中记载“佛陀也开示世人,种植华果树木,能使人清凉,功德也会日夜增长。”树除了美化环境,也是佛门修道助缘的一种方法。因此在佛教绘画中,动、植物与佛教艺术结合以后就有了特殊的佛教意义。或者说佛教的一些思想就寄托在这些植物上,进而形成了佛教中树木崇拜的观念。
吐鲁番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和古代西域天山南北最重要的交通枢纽。从西汉至宋元时期,这里一直是西域地区的佛教中心之一。受到古印度佛教艺术的影响,古代回鹘人也有对树木崇拜的观念。《周书·突厥传》记载,回鹘祖先是由树而生;《乌古斯可汗传说》里面记录了9-10世纪时期的回鹘的源起、成长和壮大以及回鹘汗国的创始人骨力裴罗就是由树所生的传说;元代虞集作于至順二年(1331年)的《高昌王世勋之碑》;至正八年(1348年)黃溍撰《辽阳等处行中书省左丞相亦輦真公神道碑》;《马可·波罗行纪》等文献也都记载了回鹘君主由树而生的传说。这些文献证明了回鹘时期人类与树木始终保持有密不可分的特殊关系,并形成了崇拜树而出现的各种有关树木的神话。在周边的柏孜克里克石窟、伯西哈尔石窟、七康湖石窟、吐峪沟石窟、大小桃儿沟等石窟壁画中,也出现了许多的树木图像。
(二)胜金口千佛洞壁画独特的艺术风格和表现技法
花鸟画是中国传统绘画中以描绘动、植物为主的一种表现方式。其描绘的对象除了花卉和禽鸟之外,还包括了飞禽、畜兽、虫鱼等动物以及树木、花卉、蔬果等植物。花鸟画表现技法,以描写手法的精工或奔放分为工笔花鸟画和写意花鸟画;写意花鸟画是用简练概括的手法绘写对象一种画法。也就是不用墨线勾勒,直接以彩色绘画物象。
五代宋元时期是花鸟画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以徐熙、黄筌为代表的“黄筌富贵,徐熙野逸”两大流派,确立了花鸟画发展史上的两种不同风格类型。黄筌在画法上工细,设色浓丽,显出富贵之气;徐熙专画山野花鸟草虫,开创了“没骨”画法,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徐熙画“以墨笔为之,殊草草,略施丹粉而已,神气迥出,别有生动之意”。这种略施丹粉而神气迥出的画法,对文人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在佛教壁画中也经常出现。
胜金口千佛洞壁画中的花鸟画,主要以写意画法为主,绘画技法用“没骨”画法,画面看不到墨线,直接以不同的色彩来区分前后树干或花叶之间的关系。画工们努力地把最能代表现实中熟悉的树木细节,纳入了画面,表现出一个美好而现实的修禅环境。
结语
吐鲁番据于古代西域天山南北最重要的交通要道,是多种文化交汇的十字路口,为不同种族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吐鲁番胜金口千佛洞壁画上的这几组花树,构图饱满,特征鲜明。壁画的内容,与回鹘人在漠北时对树的信仰有一定的关系。在绘画表现技法上,运用“没骨”画法,笔触细腻,线条生动。这些壁画对研究回鹘时期花鸟画在西域的传播和风格的演变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