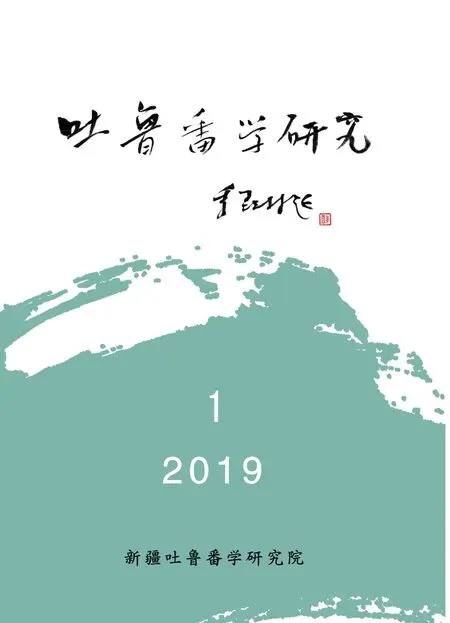新疆壁画中的药师佛图像研究
贾应逸
新疆是我国最早信仰佛教的地方,佛教艺术也最先在这里发展起来,并影响了我国中原,甚至韩国、日本等东亚各国。同时,中原地区的佛教及其艺术也反馈至新疆,在新疆生根并发展起来,东方药师净土变和药师佛图像,就是其中之一。新疆地区现存的这种图像随着岁月的流逝,自然力的破坏和宗教的变迁,很多壁画早已脱落、剥蚀无存,现仅知在库车县和吐鲁番市石窟中保存有这种图像。其中库车县位于渭干河沿岸的库木吐喇石窟有一幅大型东方药师净土变画,描绘得细腻精美,阿艾石窟的单尊药师佛像保存完好,色彩仍鲜艳。吐鲁番市柏孜克里克石窟内的药师净土经变图残留画面较多,内容丰富,但被德国人勒柯克拿走,现存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虽然现存这种图像的数量较少,但其内容、画面各具特色,现分别叙述如下。
唐代安西的药师经变和药师佛图
公元7世纪,唐朝政府统一新疆后,建立安西都护府,并于贞观二十二年(648)迁安西都护府治所至龟兹首府伊逻卢城,下设龟兹、毗沙、疏勒、碎叶(后为焉耆)四镇,总管新疆一切军政事务,推行唐朝政令。正如慧超所记,“龟兹国,即是安西大都护府,汉国兵马大都集此处”①(唐)慧超:《往五天竺国行记》,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2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66页。。同时,唐王朝又在这里设立“四镇都统”,管理整个新疆地区的宗教事务。现知在库木吐喇、阿艾石窟等处保存着的一些唐代壁画就是这一时期描绘的。库木吐喇石窟距安西都护治所较近,成为安西大都护府官员及其眷属礼佛求福的一处佛教圣地,也是唐代佛教艺术的中心。阿艾石窟则可能是唐代屯垦士卒集资修建的礼佛殿堂。
库木吐喇石窟中的东方药师净土变
东方药师净土变图描绘于库木吐喇第16窟。它与第15、17窟共享一个前室,三个窟呈“品”字形排列(图1)。这个洞窟开筑在渭干河畔的峭崖下部,千百年来河水泛滥,盐碱渗透,壁面严重脱落;又饱受外国“考古”“探险”家的盗割。日本大谷探险队的渡边哲信、堀贤雄于1903年5月在该窟入口处割走一幅汉僧供养像的题名“大唐□(庒)严寺上座四/镇都统□师悟道”①[日]香川默识:《西域考古圖譜》下卷,东京:国华社,1937年。,“四镇都统”即前述总管新疆宗教事务的官员。其中第17窟壁面大部坍塌,画面无存。第15窟壁画残损严重,仅存正壁中心柱上方的华盖和主室券顶的部分千佛和莲花纹图案。只有第16窟仍投射出昔日的风采。
第16窟是一座平面呈长方形的纵券顶窟,有右、后、左三甬道。主室正壁无壁画,前部残存长方形低台,可能原置立佛塑像,窟顶中脊饰莲花和流云纹,两侧各绘16排、每排36身千佛像。主室左、右两侧壁绘经变图;主室前壁、门侧有供养人像;前部门上方绘涅槃变。
大型东方药师净土变图就描绘在该窟的右侧壁。其构图形式是:在横长方形的图中央描绘佛国世界,两侧配以纵向立轴式条幅,分别描绘十二大愿和九横死。这种构图与敦煌莫高窟第148窟的药师变相同,是同类经变画的移植。遗憾的是画面被切割,遭受破坏,中堂的主尊——药师佛已经无存,现仅残存:右侧协侍菩萨的华盖及其上方的四身飞天(图版壹,1、2),画面左侧下方的建筑物和菩萨(图版壹,3)。华盖四周镶以层层莲瓣,上面绿色宝珠光腊闪烁,垂悬着串串璎珞、彩铃和帐纹。重重帔帛后扬的飞天,搏击长空,舒展自如,其中保存较好的两身飞天(图版壹,4),前面的双手捧花盘,回首盼顾;稍后的一身左手上扬散花,彩色飘带荡漾。其形象和绘画技艺可与莫高窟同时代的飞天相媲美。左侧建筑物的回廊中菩萨聚集,有的凭栏了望,有的正卷珠帘,有的双手捧盘供养……
右侧的条幅仍残存“十二大愿”之局部:画面右边一幅,身披绿色袈裟的佛立于莲台上光芒四射,下方可见五身戴幞头、穿烂衫的世俗人顶礼膜拜,有的五体投地,有的合十颂赞,有的抬头仰望,目光中流露出希冀的神情。应为第一愿,可惜榜题的字迹剥落,据日人渡边哲信录文“第一愿者使我来世……自身……/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令一切众生知我”②[日]渡边哲信:《西域旅行日记》,[日]上原芳太郎《新西域记》上卷,东京:有光社,1937年。。第二幅,穿赭色袈裟的佛立于莲上,下方是俗人和绿色夜叉等跪拜。榜题“第二愿者使我来世自身光明□□/琉璃内外明彻净无瑕妙□□大/功德巍巍安住十方如日临世幽冥/众生悉蒙开晓”。下方塌毁,可见榜题“第三愿者”(图版壹,5)。下方的均已剥蚀不清或不存。
左侧条幅内的“九横死”图,仅可见建筑中的屋宇和回廊。屋顶的筒瓦排列规整,回廊台基上的砖砌线平行,红色的立柱,绿色的窗帘,表现出唐代富丽堂皇的景象(图六)。榜题全部无存,渡边哲信记录有“一者横病/二者横有口舌/三者□□□/四者□□□为鬼神/王(五)者□□劫贼剥脱”①[日]渡边哲信:《西域旅行日记》,[日]上原芳太郎《新西域记》上卷,东京:有光社,1937年。。
日本学者熊谷宣夫曾将该窟上述榜题与隋达摩笈多所译《佛说药师如来本愿经》、唐玄奘译的《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义净译《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相对照,发现文字均不甚符合,而与《佛说灌顶经》第十二卷中《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的文字相同②转引自马世长:《库木吐喇的汉风洞窟》,《中国石窟:库木吐喇石窟》,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207页。。该经说“第一愿者,使我来世得作佛时,自身光明普照十方,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而自庄严,令我一切众生如我无异。”“第二愿者,使我来世自身犹如琉璃,内外明彻无瑕秽,妙色广大功德巍巍,安住十方如日照世,幽冥众生悉蒙开晓。”“第三愿者,使我来世智慧广大,如海无穷润泽枯涸无量众生普使蒙益,悉令饱满无饥渴,想甘食美膳悉持施与。”至于“九横死”该经中称“一者横病,二者横有口舌,三者横遭县官,四者身羸无福,又持戒不完,为鬼神之所得便;五者横为劫贼所剥。”此两者相对照,该经与第16窟图像吻合。
我们知道《佛说灌顶经》是东晋时,僧人帛尸梨蜜多罗所译。《高僧传》卷二记载:“帛尸梨蜜多罗,此云吉友,西域人,时人呼为高座。”关于帛尸梨蜜多罗的故乡,日本学者羽溪了谛说“其人也来自龟兹国”,学界大多以龟兹僧人论之。《高僧传》又说“传云,国之王子,当承继世,而以国让弟,暗轨太伯。既而悟心天启遂为沙门。”他于东晋永嘉(307—313年)中至建康住建初寺,译出《孔雀王经》。《开元释教录》卷三记载,该《佛说灌顶经》也是帛尸梨蜜多罗所译。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这幅《药师经变》画的图像布局结构,壁画风格,绘画技艺等,均与中原地区的同类图像相似,尤其与敦煌莫高窟148窟的《药师净土变》画相同,但榜题却录自公元4世纪时、当地人翻译的《佛说灌顶经》。同时,库车县还发现过唐代时用汉文抄写的《佛说灌顶经》,看来该经直到唐代仍在当地广为流行。
阿艾石窟的药师佛尊像
药师佛的单尊像现知仅在阿艾石窟有保存③郭梦源、傅明芳:《20世纪末的新发现 阿艾石窟》,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1年。。
1999年发现的阿艾石窟位于库车县城北面阿格乡依塔克村北、天山山脉库木鲁克艾肯沟克孜利亚峡谷的西崖。峡谷曲折幽深,沟内细涓潺潺,崖壁疏松,洞窟距谷底30米,洞窟口砂砾成堆,低矮不规则。现仅发现了一座洞窟。洞窟平面为长方形,窟顶为纵券式。主室地面中央设方形基座,台基上的主尊塑像早已无存。台基与左、右、后三壁形成供礼佛右旋的行道。在右行道的堆积中出土有石雕佛像。
整个洞窟的壁画已经剥蚀不清,但透过那斑驳的画面仍可辨识内容和领略精美的绘画艺术。正壁描绘的观无量寿经变图与敦煌盛唐时期莫高窟第171窟的壁画相似,粉本也可能来自敦煌,是受中原佛教艺术影响而出现的壁画。窟顶残存千佛像,两侧壁描绘佛和菩萨尊像,其间还添绘禅定千佛,并墨书汉文和古代民族文字题记。该窟残存17处汉文题记,其中较完整的有:“梁信敬造十六佛”、“寇俊男善庆造七佛供养”、“妻白二娘造七佛一心供养”、“申令光敬造十六佛供养”、“李光晕造十六佛一心供养”、“文殊师利菩萨似光兰为合家大小敬造”、“清信佛弟子寇廷俊敬造卢遮那佛”等,为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主室右壁残存5身佛和菩萨像。从左至右依次为:(1)坐佛像,(2)药师琉璃光佛立像,(3)文殊师利菩萨像,(4)卢遮那佛立像,(5)药师琉璃光佛立像。在这些像的右侧,以墨线勾出竖式榜题框,内墨书汉文题记。
该壁描绘的两尊药师琉璃光佛立像。左侧与(1)坐佛像相邻的药师琉璃光佛像(2),呈立姿,但腹部以下残损。现存蓝、绿色晕染的头光,顶有肉髻,面型长圆,大耳垂肩,眉弯,鼻隆,双眼和嘴被损,上唇有短胡,下唇留山羊须。内穿缝缀卷草纹绣花边饰的棕色僧祇支,白蓝色帛带在腹前打结,外披的绿色袒右袈裟,绕过前腹,搭在左臂上。左臂屈曲,手置胸前,托一钵;右臂举向前上方,掌心向外,拇指与中指相捻,持锡仗。右侧汉文题记“清信佛弟子行官杨(?)崖(?)□年五月十五日□拜记”。左侧绘禅定佛8身,分5排排列。左侧与第(3)身文殊师利菩萨相邻(图版壹,7)。
描绘于(4)卢遮那佛像右侧的另一尊药师琉璃光佛立像(5),面相与上述的相同,但面部保存完整,眼呈鱼形,嘴小,唇厚。内穿的绿色僧祇支刺绣着莲花纹边饰,外披赭色偏衫式袈裟,白蓝色的帛带绕过腹部,置于左肩。执持与上述药师佛相似,只是锡杖由右手的拇指和食指相捻而持。右侧的榜题为“清信佛弟子寇庭俊敬造药师琉璃光佛”(图版壹,8)。左侧壁面坍塌,画面无存。
这是一座唐代时期的石窟,从现存的17处榜题来看,这座洞窟是一般民众与中下级官员联合捐资开凿的洞窟。在东距石窟所在地十几公里处,就有唐代屯田和冶炼遗址——阿艾遗址。该石窟可能就是居住在这里的这些汉族士卒集资开凿的,其中“行官”题名,说明也有一般小官吏参与。洞窟右侧壁、卢舍那佛的右下方有游人刻划的题记“己巳年五月十五日/白光□”。这显然是洞窟废弃后的游人题记,以干支纪年,在吐蕃时期较多见。看来,该洞窟修建的时代与库木吐拉16窟的时代较近,应在“安史之乱”及吐蕃占领龟兹之前,即公元8世纪中叶,大约9世纪时,该窟已经废弃。
上述现存唐代安西的东方药师经变图和药师佛尊像的艺术风格相同:人物造型准确,四肢圆浑,凝练健康,反映出封建经济文化繁荣昌盛的唐代,崇尚雄强健壮之美。头颅方圆,面相丰满,发际至眉间较窄,眉修长,眼略上斜,唇厚嘴小。佛的姿态庄严,举止端庄,袈裟色泽丰富,具有装饰性。菩萨虽然“素面如玉”,但体形优美潇洒,头梳高髻,束宝冠,余发披肩而后垂,耳饰珰,项佩圈,腕戴环,仪态万千。壁画中自由自在地翱翔的飞天,双腿舒展的体姿,向后漂荡的披帛和遮盖腿的长裙与云雾平行摇曳,透露出动人的美感。这些刻划精细的壁画,表现出画师对生活深入细微的观察力和惊人的创造力。
吐鲁番市柏孜克里克石窟中的东方药师净土变图
另一幅东方药师净土变图描绘于吐鲁番市柏孜克里克石窟第18窟。这是一座较大型的中心柱窟(图2),现知曾经三次维修彩绘,该图原位于第18窟主室右(南)侧壁的最上层,应是最后一次维修时绘制的。20世纪初,被德国“吐鲁番探险队”的勒柯克等割取,盗回本国,现存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①Le Coq,Die buddhistische Spatantike in Mittelasien,Ι-Ⅶ,pp.17;巫新华译:《新疆佛教艺术》Ⅳ卷,图版17,乌鲁木齐:新疆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97页。。
我们知道,公元840年,游牧于蒙古大草原的回鹘人,因遭天灾和黠戛斯进攻,离开漠北“诸部逃散,其相职,特勒庞等十五部西奔葛逻禄,一支奔吐蕃,一支奔安西”。这幅图像正是回鹘政权迁居高昌(吐鲁番),并信仰佛教后绘制的,大约描绘于元代,是其尊奉净土思想的真实反映。
这幅药师净土变图中上方画面无存或破损,只存药师佛和协侍菩萨及其下方的内容(图版壹,6)。药师佛位于现存壁画上方,有多层彩绘图案的圆形头光和背光,内穿绿色僧祇支,腰结带,外披红色田相袈裟,头缠巾,左手置腹前,右手上举,结三界印,结跏趺坐在六边形的莲花纹狮子高座上正在说法,菩萨、弟子围绕。日光和月光菩萨分别侍坐于两侧的台上,周围也有菩萨围绕。药师佛前方两侧侍立着八大菩萨,每侧各四身,每身旁边都有竖向的题跋条,但未见字的痕迹。左侧四尊菩萨的后方,十二神王敬立;右侧四身菩萨的后方立有九曜形象。十二大愿与九横死内容绘于下方的横式长条中。
佛经中相关药师佛的经籍不少,《大正藏》将其分别归在“经籍类部”和“密教类部”。这幅东方药师净土变图像是依据多部佛经,主要是帛尸梨蜜多罗译《佛说灌顶经》第十二卷《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唐代玄奘译《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元代沙啰巴译《药师琉璃光王七佛本愿功德经念诵仪轨供养法》和《净琉璃净土摽》等绘制的,其中协侍菩萨为日光和月光,《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称为“一名日曜,二名月净”;《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中说“一名日光遍照,二名月光遍照”,即日光、月光菩萨,可以说是多部经的共识。图中位于佛左侧的协侍菩萨保存较完好,头梳高髻,结花鬘冠,卷发披双肩,颈佩项链花鬘,腕戴钏,下穿红色长裙,披袈裟,饰帛带,高雅华丽。
至于八大菩萨,只有《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有具体的名称,经中说“有八菩萨,其名曰:文殊师利菩萨、观世音菩萨、得大势菩萨、无尽意菩萨、宝坛华菩萨、药王菩萨、药上菩萨、弥勒菩萨,是八菩萨皆当飞往迎其精神”,图中位于药师佛前方两侧,每侧四尊,仅存头光、花冠和前面几身的长裙和袈裟。
位于药师佛前方左侧的十二神将(图版壹,9),《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称为神王,《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元代沙啰巴译《药师琉璃光王七佛本愿功德经念诵仪轨供养法》等称药叉大将,是守护诵持药师经的大将,佛经说,每一神将各拥有七千药叉,计为八万四千护法神。他们曾立誓言:“我等相率,皆同一心,乃至尽形归佛法僧,誓当荷负一切有情,为作义利,使其饶益安乐。随于何等村城、国邑、空闲林中,若有流布此经,或复受持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恭敬供养者,我等眷属卫护是人,皆使解脫一切苦难。诸有愿求,悉令满足”②(唐)玄奘译:《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大正藏》第十四册(No.0450)。,是药师经变故事画的主要内容。十二神将的名称,各经不尽相同:《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译为金毗罗、和耆罗、弥佉罗、安陀罗、摩尼罗、安林罗、因特罗、波耶罗、摩休罗、真陀罗、照头罗和毗伽罗。《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则称为宫毗罗、伐折罗、迷企罗、安底罗、頞尔罗、珊底罗、因达罗、波夷罗、摩虎罗、真达罗、招度罗和毗羯罗。十二神将的形象在唐及以前的敦煌壁画中均作金刚力士状,但该幅壁画十二神将形象却与习见的身著甲胄的装束完全不同,而是身穿文官服,双手笼在宽袖内,手执笏,头上置十二辰头像,即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和猪。把十二神将与十二辰相对应,见于《净琉璃净土摽》,其称“十二神将形”:第一宮毘罗驾虎,第二伐折罗驾兔,第三迷企罗驾龙,第四安儞罗驾蛇,第五安底罗驾两翼马,第六珊底罗驾羊,第七因达罗驾,第八跋伊罗驾金翅鸟,第九摩睺罗驾狗,第十真达罗驾猪,第十一招杜罗驾鼠,第十二毘羯罗驾牛①《净琉璃净土摽》,《大藏经》第十九册(No.0929)。。这一叙述与该图像吻合。《淨琉璃淨土摽》为何时、何人所译,目前不得而知,仅见它收集在《大正藏》第19册中(No.0929),经末“端题下云/元睿山本(云云)/二校了/长治二秊六月二十五日奉写毕”,有待今后研究。这十二辰形象又与我国盛行的十二生肖相关。有些佛典说,这十二神将在昼夜十二时辰及四季十二个月份里,轮流率领眷属守护众生。
佛右侧立于四身菩萨右面的是九曜图(图版壹,10):第1排,两身,日曜和月曜。日曜即太阳,男像,戴冠,两手捧日,配之于丑寅方。月曜为太阴,女像,头饰花蔓,披巾,双手持圆月,配之于戌亥方。第2排3身,从上至下依次有:水曜,也称为辰星,女像,头戴猴形冠,手持笔砚,配之于北方。金曜为太白星,也为女像,头有高髻,饰鸡,弹奏琵琶,配之于西方。木曜为岁星,男像,头戴猪冠,双手捧华果,配之于东方。第3排2身,上方有土曜为镇星,老婆罗门像,戴牛冠,配之于中方。下面火曜为荧惑星,罗刹形,头戴马冠,应为4手,仅见两手上举,左手持箭,右手执剑,配之于北方。以上七者,称为七曜。最左端2身:计都即彗星,又称豹尾星,罗刹形,左手持剑,配之于丑寅方。罗睺即黄旛星,又称蚀神、罗刹星,右手拿剑,左手执蛇,足下踏狐,配之于丑寅方②(金)俱吒撰集《七曜攘灾诀》,《大正藏》第21册(No.130)。。九曜即九种照耀之天体,又称九执,即随逐日时而不相离,具有执持之义。日本人松本荣一所著《敦煌画の研究》中指出,这幅图像可能与玄奘所译的《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相关,其中的九曜可能是经中“星宿变怪难”,“日月薄蚀难”的反映。其实所有药师经中与此内容相近的只有《药师琉璃光王七佛本愿功德经念诵仪轨供养法》。该经中有天主帝释、火神、水神“等供养赞叹而敬礼药师佛”的内容,但所述九神与此图像不完全相同,除前述三神东方是帝释,东南火神、西方水神外,其余是“南方焰鬘阴母王”,“西南离谛夜叉王”,“西北风神婆耶毘”,“北方施碍矩毘罗”,“东北具主魔罗王”,“下方龙王主地神”③(元)沙囉巴译《药师琉璃光王七佛本愿功德经念诵仪轨供养法》,《大正藏》第十九册(No.0926)。。这种差别也许与译名相关,也许还有别的回鹘文译本,有待今后的发现和研究。
在这幅主图下方以屏风式描绘十二大愿和九横死。但这些小画不是常见的21幅,而是30幅,且画面模糊不清,虽然每幅画旁都有竖式题榜框,但未写字,目前难以一一辨识。从左边每幅小画中都有佛像、佛塔来看,描绘的应该是十二大愿,那么右当为九横死图了。
这幅药师经变图是唐代安西壁画艺术的继承和发展,人物造型上,强调健壮之美,同时,也体现了回鹘人的特点:长条形面孔丰腴莹润,修长的眉毛稍翘起,柳叶形眼睛,黑色眸子,嘴小,鼻梁高直。该壁画中,佛、菩萨和人物的服装大都是赭和红色,以绿、白、黑色衬托,是回鹘人喜欢赭、红、茜、黄等热烈色泽的体现。强调图案纹样的装饰美也是这幅药师变的特点,药师佛的头光、身光以火焰、圈点、水波纹装饰,佛和协侍菩萨的六角形莲花座上彩绘着圈点、垂帐、水波等各种纹饰。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区,所有民族的文化艺术都植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沃土。新疆境内现知的药师佛图像数量不多,但它却反映了多民族文化并存的特点。同时,在我们这个多民族长期共同生活的历史进程中,文化艺术的发展存在统一性,如龟兹地区唐代的药师经变画,与敦煌莫高窟148窟的同类图相似,而高昌地区元代的药师净土变也与敦煌莫高窟12窟同类壁画的布局相同,其所本经籍又与藏传佛教相联。各民族文化在新疆汇集,融合,并形成富有地区特色的艺术,丰富了中华民族整体文化艺术的宝库。
——苏氏琉璃作品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