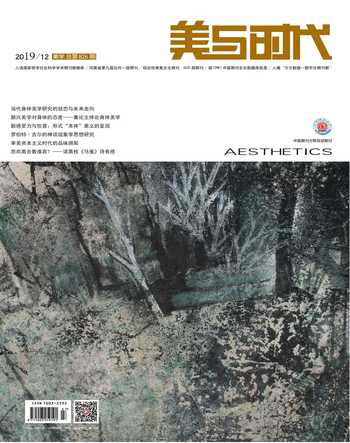论顾恺之的“形神论”
摘 要:魏晋以降,对于人物画的创作、品鉴无不把“传神”作为绘画表现的最高标准,“传神”自顾恺之以后,成为中国人物画创作与品鉴的绘画法则。但有关顾恺之的“传神”概念,人们往往将其等同于哲学本体论中的“形神”概念,忽视了其在绘画理论中的特殊性。“形神”理论进入到绘画中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为哲学本体论的形神,其次是作为人物品鉴的形神,最终才延伸至绘画理论中的形神。顾恺之“传神”理论不仅仅是绘画艺术的宝贵财富,其背后蕴涵了当时社会丰富的人物审美及哲学思想。
关键词:顾恺之;人物画;形神论
顾恺之是中国绘画理论的奠基人,在他之前还未有一篇完整的、正式的画论。他不仅拥有高超的绘画技法,而且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画论主张,他所提出的“形神论”标志着中国绘画理论的一个大飞跃。顾恺之画论的建立,乃是中国绘画艺术大发展的起点,其形成一定有其背后的原因。这个理论是怎样一步步从出现到成形,它又包含着什么样的思想内容,本文尝试对此进行讨论。
一、“形神论”的生成
魏晋南北朝时期,按宗白华先生的说法,是“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1]208。顾恺之的理论在这一阶段形成并得到发展,但我们不能仅仅着眼于魏晋时期的思潮,只有追根溯源,才能够真正明白这一绘画理论的含义。在汉代一些文献中,关于形神关系的谈论很多。
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合,故圣人重之。由此观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2]
夫精神者,所受于天也;而形体者,所禀于地也。[3]153
故以神为主者,形从而利;以形为制者,神从而害。贪饕多欲之人,漠眠于势利,诱慕于名位,翼以过人之智,植于高世,则精神日以耗而弥远,久淫而不还;形闭中距,则神无由入矣。[3]29
汉代对于人的形神关系的讨论是一种有关身体美学的讨论,其所强调的是人是一种形与神的结合体,这种结合所体现的形神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二者的结合也有其内在的规律。正如刘成纪在《形而下的不朽——汉代身体美学考论》中所说:“如果说人是一个形神合一的整体,那么这种合一必须是内外贯通的合一,否则就成了一种机械的组合。”[4]汉代有关形神关系的讨论受到黄老道学的影响,已逐渐有了“重神轻形”的倾向。
魏晋时期对于人物形神的讨论尤为盛行。对于人物评论的盛行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很深的历史根源,其中最为主要的原因就是魏晋名士的清谈,而清谈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对人物风貌的评价。宗白华说:“晋人的美,美在神韵。神韵可以说是事外有远致。”[1]208魏晋时期审美风格受到那个时代各个方面的影响。法国艺术史家丹纳曾经指出:“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的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5]东汉末年,由于长期的战乱,“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社会动乱、政权更迭使得人才选拔制度发生了极大的转变。由于汉末的“以名取人”和“以族取人”对历史产生的深刻影响,造成了士族政治势力的不断扩大、士族政治和官僚政治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选官制度变更主要表现为由“九品中正制”取代了汉代的“察举制”。“察举制”,顾名思义,就是在官员选拔的过程中首先对其进行考察,也就是说,各级政府部门通过专项制度从民间选拔人才进入官府工作,虽然不同时期对其考察的内容侧重点不同,但是对人物的观察和品评是察举制度实施的关键。对于人物的品评议论在汉代已经有了体现,汉末国家设立的太学引起了朋党交游活动,“清议”风气已然出现。
汉代对于人物的品评重点放在人的道德、操守、气节上,而曹魏时期,儒学受到了挑战,人的才情、格调、气质、能力逐渐成了人物品评的重点。举荐制度上的巨大转变影响着当时的社会风气,内在精神性成为了每个人所追求的目标。美的理想在于讲求超凡脱俗的风度神貌,在于追求内在的“神”而不是外在的“形”。这种追求直接促成了人物画中“重神”的审美取向。东汉的人物品藻主要集中在对人的内在德行的考察,而魏晉时期的人物品藻则对人的内在神气把握较为看重。所以,汤用彤先生说:“魏晋识鉴在神明”“识鉴乃渐重神气。”[6]33人物品藻到了魏晋南北朝已经完全转移到了对人的风度仪表和神气的把握。对此,在南朝刘义庆编纂的《世说新语》中的《容止》《赏誉》等篇章里有着重要体现,可以说魏晋人物品藻对于人物画的影响是巨大的。
在晋,人伦鉴识由政治上的实用性渐渐变成对人的欣赏,士人论人的行为在当时的记载中随处可见,对于人物姿态的记录非常详细。由此可以看出,魏晋时期对人物风貌的刻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衍俊秀有令望,希心玄远,未尝语利。王敦过江常称之曰:“夷甫出众中如珠玉处瓦石间。”顾恺之作画赞,亦称衍严严清峙,壁立千刃。其为人所尚如此。[7]1238
魏明帝使后弟毛曾与夏侯玄共坐,时人谓“蒹葭倚玉树”。[8]255
时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怀”,李安国“颓如玉山之将崩”。[8]256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8]256
类似于这类的描写还有很多。从这些描绘我们可以看出,魏晋时期对于人物的品评不同于汉代。汉代对于人物的品评主要体现在道德层面,而这一时期对于人物的评价多从容貌风神等方面进行评价。从汉代的重儒学到魏晋时期的重玄学,社会思潮发生了巨大转变。魏晋的哲学思想以玄学为中心,认定内在精神本体才是根本,才是无限和永恒,而一切物质的现实性的内容都在这种内在精神本体之后产生。汤用彤曾说:“汉人朴茂,晋人超脱。朴茂者尚实际。故汉代观人之方,根本为相法,由外貌差别推知其体内五行之不同。汉末魏初犹颇存此风,其后识鉴乃渐重神气,而入于虚无难言之域。即如人物画法疑即受此项风尚之影响。”[6]32
作为哲学本体论意义上的“形神”是针对现实中的人物进行的,作为现实的人,其形神关系不是十分密切,很可能是若即若离的。魏晋时期形神问题的讨论有很大一部分集中在对人物的谈论中。而人物画作为人的绘画,形神观念自然也就引入到了画论中。绘画中人物的存在是一种抽象的存在,这种人物不同于现实的人物,绘画理论中的形神也不同于哲学本体论讨论中的形神,在绘画中,形与神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其关系更加紧密。
二、形神关系
“画,形也”(《尔雅》);“形,象形也”(《说文》)。绘画作为一种造型艺术,正是追求一种与绘画原型符合的状态,这个符合的基础就是形似,通过一种摹仿造像的方式来反映现实。因此,在绘画艺术的早期阶段,都是从对“形似”的追求起步的。例如《韩非子》中记载:“客有为齐王画者,齐王问曰:‘画孰最难者?’曰:‘犬马最难。’‘孰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马,人所知也,旦暮罄于前,不看类之,故难。鬼魅无形者,不罄于前,故易之也。’”[9]这是重点强调如实描绘具体的事物形状,对于对象内在的神采尚未引起注意。
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说:“图画之妙,爰自秦汉,可得而记。降于魏晋,代不乏贤。洎乎南北,哲匠间出。”[10]2 绘画有着悠久的历史,秦汉绘画也有着各种各样的内容与形式,但是魏晋时期的绘画不同于秦汉乃至更早的绘画,无论是汉画像石还是壁画,大都是对于人物轮廓的描画,停留于对人物外在的描绘上。西汉时期出现的“君形”说虽然对于人物描摹具有一定的反思意义,但在实际绘画中没有起到很大的影响。因此,魏晋之前的绘画很多都是通过画来表现一定的价值意义,达到“成教化,助人伦”的功用。
山水画在魏晋时期虽然已萌芽,但在此时期,主导的绘画类型还是人物画。今道友信在《东方的美学》中说:“即使在这个时期,如魏晋时代的绘画,山水画与其说是描写自然,不如说是作为象征性图形的背景陪衬罢了。有名的顾恺之的《史女箴图》的狩猎背景,它作为自然表现,也显然不过是类型化的图像罢了。”[11]人物画作为魏晋时期绘画的主要形式,以描写人物为对象,对于人物的描绘主要涉及了人的两个方面,即形与神。
我们对于顾恺之画论的理解主要来自于他的三篇画论:《魏晋画流胜赞》《画云台山记》和《论画》。在这几篇文章中,顾恺之提出了人物画“以形写神”的重要命题,并且阐述了其可行性与实践性以及具体的操作方法。“形神论”的提出也具有漫长的过程。王充在《论衡》中说:“人好观图画者,图上所画,古之列人也。见列人之画,孰与观其言行?置之空壁,形容具存,人不激劝者,不见言行也。古贤之遗文,竹帛之所载粲然,岂徒墙壁之画哉?”[12]王充认为,艺术品的使用价值首先在于欣赏。汉代时期的人物画主要是关注政治和道德价值,在儒家观念的影响下,政治和道德教化成了两汉人物画的最突出的主题。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关注的主要是绘画的价值,而不是审美这一维度。顾恺之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指出了人物画的关键在于“传神”,而外形、服饰、用笔这些技法都是为“传神”服务的。“传神论”代表了魏晋时代绘画的大飞跃,顾恺之指明了绘画艺术的本质是传神,当时的人物画也不再是由画的故事来表现其意义,而是通过画中人物的神来决定其价值。
“以形写神”是顾恺之美学形神论的核心命题。顾恺之解释道,描绘人物形象“其于诸像,则像各异迹,皆令新迹弥旧本,若长短、刚软、深浅、广狭与点睛之节,上下、大小、醲薄有一毫小失,则神气与之俱变矣”[10]53。顾恺之强调替人画像当做好每一笔,如果在点睛上有所不慎,那么神气就会丧失。很显然,顾恺之不是一味强调传神,而是在“形神并重”的基础上更加追求“神”的意味,这是要求把“传神”和“写形”统一起来。形、神相依是一切事物和生命存在的根本规律,在艺术中亦是如此。顾恺之提倡“以形写神”,“形”为外相、“神”为内涵。“形”是外在的、具体的,“神”是内在的、抽象的。“神”是依托“形”来体现,无形则神不存;“神”使形具备了神气。“形”与“神”是相互依存、对立统一的关系,二者缺一不可。但是,在对“神”的表现中一定要通过“形”来实现。
谢赫在《古画品录》中认为,顾恺之“除体精微,笔无妄下,但迹不逮意,声过其实”[13]。后人认为谢赫的评论有失公允,且和张彦远等人对于顾恺之的记载有所冲突。但从谢赫的评价可以看出其对于顾恺之笔法的肯定。此时期对于“意”的追求一定是建立在“实”的基础之上的。顾恺之的“以形写神”理论终究到底还是继承“写实”的绘画传统。同样地,在“以形写种”的另一方面,对客观形体忠实的描写,同样是被强调的。因为神是在形上表现出来的,形是神的物质基础,只有形体描绘得正确,才有表现神的可能。除此之外,形的正确,最终目的是为了写神,而不是为写形而写形的。关于这一点,俞劍华认为:“顾恺之所讲的‘以形写神’,并不是描绘表面的现象而是通过艺术对这一现象的认识,加以概括综合并用艺术形象传达给观众。既然要综合就不可能是纯粹直观的,不可能只是建筑在观察力的基础上的。只有善于明确地思索,善于根据观察到的东西,作出合乎逻辑的结论的艺术家,才能作到综合。”[14]这就说明当时的人物绘画已经突破了对人物的刻板描绘,而是一种能动性的摹写,加入自己的理解只是为了更好地反映所描绘的人物形象,而非一种歪曲。《世说新语》中记载:“顾长康好写起人形。欲图殷荆州,殷曰:‘我形恶,不烦耳。’顾曰:‘明府正为眼尔。但明点童子,飞白拂其上,使如轻云之蔽日。’”[8]305看画者不会认为顾恺之的绘画不符合对象的原型,而是认为顾恺之的绘画更加能表现出裴叔则的形象,直达画中人物的内心,这种真实相比于刻板的反映显得更加重要。
顾恺之对于形神关系是有深刻理解的。他在提出“传神”观点的同时也没有忽视“写形”的价值,又进一步指出要“以形写神”,画家在刻画“形”的特点的基础上尽可能地表现出“神”来。我们从顾恺之所提出的“以形写神”可以看出,他是主张形神并重、形神兼备的。他所提出的“以形写神”,这个“形”肯定不是照相式的形似,而是能够反映事物真实状态的那种形似。与此同时,他要求在形似的基础上达到神似,通过画家的绘画能力与技法与表现事物“形”中的“神”。顾恺之的形神观主要是对人物画的探讨,他通过传神的观点主张绘画要表现人物的精神状态和性格特征。可见,顾恺之对“形”与“神”的要求是平等的,两者缺了任何一方面,都是不完整的。徐复观在《中国艺术精神》中谈到顾恺之的画作,讲到“作者以自已之目,把握对象之形,由目的视觉的孤立化、专一化面将视觉的知觉活动与想像力结合,以透入于对象不可视的内部的本(神)。此时所把握到的,未尝舍弃由视觉所得之形。但已不止于是由视觉所得之形,而是与由想像力所透到的本质相融合,并受到由其本质所规定之形在其本质规定以外者,将遗忘而不顾”[15]。“以形写神”是顾恺之绘画理论的一个主要层面,其含义就在于对人物描绘的过程中对“形”的重视,这里的形体是经过作者内化之后、通过绘画进一步表现出来的形体。
顾恺之在绘画领域中首次明确提出了影响深远的“传神论”,阐述了形与神的辨证关系。顾恺之认为,人物画要想获得传神的艺术效果,抛开所描绘对象的形,是绝对不行的。《晋书》记载顾恺之有一则轶事,“尝悦一邻女,挑之弗从,乃图其形于壁,以棘针钉其心,女遂患心痛。恺之因致其情,女从之。遂密去针而愈”[7]2405。从这一则轶事可见顾恺之高超的绘画技法,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已经达到了极高的水平,能够准确地把握人物的形象。
三、写实与表意
绘画作为一种艺术表现方式,主要在于传达绘画者的思想。而思想传达的前提一定是建立自己所画对象确定性的基础之上的。“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16]古人绘画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用来表意,绘画作为与文字不同的造型艺术具有独特的表现方式,能够更加确切地传达作者的意图,画家充分利用了造型艺术的特点,克服了诗歌语言艺术在塑造可感的具象方面的弱点。正如黑格尔在《美学》说:“绘画作为表现这种内容的手段,在形象上就应该运用一般外在形象,不管是自然界的现象还是人类有机体的现象,只要它们能把精神的东西表现得晶莹透澈就行。”[17]这一切的表意是建立在绘画技巧基础之上的。如果没有高超的造型技巧,就不可能达到这样的成就。
《晋书》中记载,“恺之每画人成,或数年不点目睛。人问其故,答曰:‘四体妍蚩,本无阙少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7]2405顾恺之非常重视人物形象的刻画,他认识到如果随意下笔,那么就无法真正描绘出所刻画人物的形象。在这里,顾恺之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即“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阿堵”是顾恺之家乡无锡的方言,指眼睛。他这里讲形体打扮得再漂亮,也不能传神,要想画出神韵,要重视画眼睛。有的人认为是顾恺之技巧有限,如陈传席由谢赫的记载和世说新语中关于顾恺之创作的几个故事中认为顾恺之在技巧上的局限给他的创作造成了影响。关于顾恺之的创作能力我们暂且不论,根据顾恺之所提出的“以形写神”以及“数年不点睛”,我们可以看出顾对于“神”的重视程度以及在人物画中“眼睛”的重要性,这也是“传神写照”的重要体现。
《晋书》记载,“楷风神高迈,容仪俊爽,博涉群书,特精理义,时人谓之玉人,又称见裴叔则如近玉山,映照人也”[7]1048。裴楷仪容不同常人,长得俊秀,风神也不同于常人。顾恺之在为他作画时,需要更加突出其内在的精神风貌。“顾长康画裴叔则,颊上益三毛。人问其故,顾曰裴楷俊朗有识具,正此是其识具。看画者寻之,定觉益三毛如有神明,殊胜未安时。”[8]304顾恺之善于把握人物对象这种形神的统一,大胆突出裴楷颊上三根毫毛,传神效果尤佳。从对于形的描绘到神的写照,最终达到了表达画家意图的目的,达到“立象以尽意”的表达效果。
“又为谢鲲象,在石岩里,云,此子宜置丘壑中。”[7]2405顾恺之在作画中,不仅要对人物进行精确的描绘,为了更加能够表现对象的神情,在对人物背景的处理上已突破原先的理论,注重人物所处的典型环境。这种对人物环境的重视其目的也是为了突出画中人物的神采,能够更好表达出画家的意图。
“传神写照”这个命题是顾恺之在相继形成“以形写神”之后提出来的。通过理解顾恺之的艺术主张可以感受到,“以形写神”是顾恺之客观描绘人物时要达到的目标;而“传神写照”是掌握绘画技巧之后,达到的一种自由境界。“传神写照”是将艺术家主观感受到的心中之感淋漓尽致地传达到所描绘的人物身上,形式和内容高度统一、互相转化,“形”就是“神”“神”就是“形”。“以形写神,而空其实对,荃生之用乖,传神之趋失矣。空其实对则大失,对而不正则小失,不可不察也。一像之明昧,不若悟对之通神也。”[10]53顾恺之认为在绘画中想要传神则离不开写形,随意表现,就不可能达到传神的目的,画家要善于领悟对象的特点。传神离不开写形的基础,这一点在绘画理论与实践中也是毋庸置疑的。
在现实人物的谈论中,形神的关系就不如绘画中那样紧密。《世说新语》中记载,“王佛大叹言: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8]326。无论是绘画理论还是绘画实践,形神之间的“一体性”关系更强。由此可见,形神问题原先作为哲学的本体论问题逐步影响到了绘画理论,但是二者所代表的含义有所差异。笔者试图对这种差异进行分析,绘画中的形神与哲学上所讲的形神有所区别,在绘画中,形神是作为人物描写的一体两面而存在的,二者是相辅相成、不可分离的。但人们通常一味地追求神采导致了对于绘画基本方法的误解,形的存在经常被人们忽略,这种误解也亟需矫正。
四、结语
我们从以上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哲学中的“形神”观念与画论中的“形神”观念有着较大的差异,中国绘画中的形神理念与作为哲学本体的形神理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作为哲学本体的形神观念往往重视神而轻视形,这和生死观有联系,形体虽不能长久,但人们渴望精神能够永久存在。因此,形与神是可以分离的。绘画中的形神理论仅仅是就画中人物而言的,画中人物已成为一个与生命无关的存在,此时画者的意图旨在表意,为了表意的准确性,其人物神采一定是建立在形的基础之上的。此时的形神在人物中是合二为一的。其次,从有关顾恺之的文献中可以看出,顾恺之认为在创作中,形是基础,形的存在是为了表现神,讲究“以形写神”,而二者在他那里几乎是同等重要的,“形神并重”是為了说明绘画作为艺术方式不能仅仅局限于刻板的描绘,而要突出画中人物的神采,这样对于人物的绘画才能更加符合现实中的人物形象。最后,通过顾恺之和当时的画家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绘画继承了“写实”传统,但已与之前有所区别,在时代风气的影响下,这个时期的写实已经从人物外形的描绘转向了人物内在精神世界的刻画,这也是此时期绘画理论的一大进步。
参考文献:
[1]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2]班固.汉书[M].颜师右,注.北京:中华书局,1999:2053.
[3]刘安.淮南子[M].许慎,注.陈广忠,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4]刘成纪.形而下的不朽——汉代身体美学考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54.
[5]丹纳.艺术哲学[M].傅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8.
[6]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7]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1.
[8]刘义庆.世说新语[M].黄征,柳军晔,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9]韩非.韩非子[M].秦惠极,校点.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102.
[10]张彦远.历代名画记[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11]今道友信.东方的美学[M].蒋寅,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29.
[12]王充.论衡[M].陈蒲清,点校.长沙:岳麓书社,2006:174.
[13]谢赫.古画品录[M].姚最,王伯敏,标点注译.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59:13.
[14]俞剑华,等.顾恺之研究资料[C].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14.
[15]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167.
[16]李学勤,主编.周易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91.
[17]黑格尔.美学:第三卷 上[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8.
作者简介:许多多,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