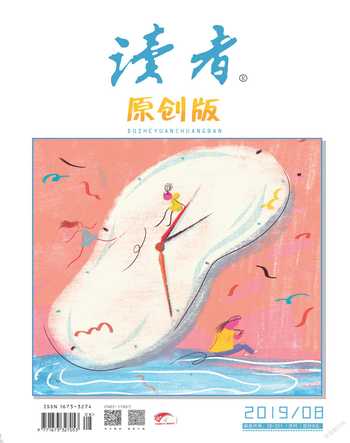路途上
刀口

很多年前,我在云南兵团当知青,从家乡重庆到西双版纳,单程需要7天,即火车2天,到昆明后候车1天,再乘长途汽车去景洪要4天。那条国道叫昆洛公路(昆明一打洛),一路崇山峻岭,到景洪全程700多公里。这样算来,汽车平均每天行程不到200公里——那可是从清晨7点开到下午6点啊,你说车速有多快呢?每小时也就二三十公里吧,哪像今天,走高速路全程只要六七个小时。
因此,当年去景洪沿途得找客栈歇息,全程歇三晚:第一晚在新平县的杨武镇,第二晚在墨江县的通关镇,第三晚在边城思茅(今普洱市)。那时可没宾馆,当然,即使有也住不起。而客栈格局大同小异:一间房住4人至8人不等,设单人铺,挂蚊帐,公用卫生间在走廊尽头,另设供洗漱的大水槽。每至清晨,满槽都是刷牙声,甚为壮观。
这样的客栈5毛钱一晚,我住过多次,从未涨价。
歇栈者多是二十啷当岁的小青年,正值精力旺盛期。每到黄昏,大伙儿吃过晚饭就去“压马路”:北京知青大多严肃,然而一开口,要么是国家大事,要么是前途忧思;上海知青则一口吴依软语,讲“的确良”衬衣如何挺括,或怎样烧糖醋带鱼才好吃;重庆知青年龄最小,个性最躁,他们在公路上大声唱着歌,相互追逐打闹。然而最迟到晚上9点就都歇了,满屋鼾声如雷,脚臭烘烘,却不无深睡中的香甜。
客栈一般备有伙食,早餐卖米线,1毛1碗;晚餐3毛1份,饭管够,配素菜一盘。路途全程唯有过玉溪县时伙食才大好,荤菜2毛1份(不要肉票),素菜仅5分,红红绿绿叫上一桌才三四元,七八个知青尽可大打牙祭。那时玉溪卷烟厂还没产红塔山,牛人褚时健尚在玉溪行署当科长。
玉溪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一望无垠的大坝子,以及坝上葱茏的庄稼与纵横的沟渠。我们连队的北京知青王克饭后打着肉嗝、剔着牙指着坝子说:“看见了吧,这鱼米之乡是上苍给的,大寨再干50年也赶不上它!”
这话够邪门的,却不幸言中。
通关客栈也值得一说。通关镇位于哀牢山区的一处山巅,四野层林密布,全镇只有几排平房,唯客栈是两层,显得气派。1978年年底,景洪农场知青丁惠民率20余人赴京,请求让知青返城,一行人曾夜宿通关。中国知青大返城的序幕,正是由这20余位代表拉开的。历史的阴差阳错及命运的兴衰沉浮,得益于政治的清明和最高领导层的仁怀,知青的路途从此画上句号。
回城了。进工厂、考大学、当秘书、考公务员,等等,我都经历过。其间,免不了出差,免不了在路途上的日子。
在工厂时,第一次出差就赶上了列车卧铺。兴奋自然难免:车厢整洁,铺设三层,毛毯虽有他人气味,但毕竟冷了有得盖,哪像当知青时,回家只能硬坐,两天下来腿都麻了。如今是公家人了,待遇就是不一样呢!但卧铺让我迷惑:脱鞋上去后,究竟该睡哪一头呢?便盘腿等着,直到见邻座熟练地将毛毯一抖,仰头睡下后,我才依样画葫芦。
1988年去北京,第一次坐飞机,波音737从歌乐山下的白市驿机场起飞。同行的头儿问:“没坐过飞机吗?”我说没有。他说那你坐窗边,看看大好河山。这一看不要紧,两个小时的飞行,我的眼睛几乎没离开舷窗,看山川平原,看城镇村庄,下飞机前,差点儿成了歪脖子。
正是8月,那时京城平房多,胡同密集,自行车满街跑。合资的高档宾馆已经有了,如长城、昆仑等,一天得三四百元,我们出差的住宿标准每天仅30元,哪敢住?于是选择了友邻单位的招待所:两人间,铺人造革地毡,有落地电风扇,还有18寸北京产牡丹彩电,每晚25元。第一次住这样豪华的标间,我却失眠了,担心鼾声惊扰了头儿。毕竟,两个^一间房,与当年8个知青挤一块儿不同,谁有声响能不清楚?
伙食不用掏钱,友邻单位全埋单。后来才知这叫行规,乃礼尚往来的对等接待。吃了些啥菜印象不深,只记得每顿的凉菜都是黄瓜拌海蜇皮。我就纳闷了:那海蜇皮嚼起来像塑料,北京人咋就那么喜歡?
及至20世纪90年代考公务员进入局机关,天南海北走得更多了。最喜欢的地方是广东和海南:气候好,满眼绿,美食精。第一次去广州,满街车流如潮,不少青壮汉子手持“蜂窝式移动电话”(即砖头般的“大哥大”),气宇轩昂;到处霓虹闪烁,灯红酒绿,更有高第街的各种舶来品,让人眼花缭乱,恍惚中,还以为到了港片中的香港。进入宾馆,冷气凉爽,房间铺有毛茸茸的地毯,卫生间的落地大镜子永无水雾,原来镜后设有加热装置;餐厅里,粤菜的精致和鲜美,比起火爆的川菜,又开辟出味蕾新天地。
回到房间,电视里正播《渴望》,刘慧芳和宋大成的恩恩怨怨仿佛是另一个世界,蓦然明白了什么叫“得风气之先”。
而在海南三亚住海景房,那落地的窗,那辽阔的海,那无边的蔚蓝,让我一觉醒来有些恍如隔世——这是在哀牢山区的客栈呢,还是在云雾中的天堂?
这世道,真是一天一个样,让这一代人都赶上了。
人的个性,决定了他的路途。
出于对文字的热爱,离开局机关后,我选择去了报社。
“不在新闻现场,就在去现场的路上。”那些年,《南方周末》的这句新年献词让很多记者热血沸腾。我亦不例外,“远方的路”总在召唤我,啥时能去看看呢?机会终于来了,新调来的头儿姓姜,兰州大学中文系1985级校友,人胖,小眼炯炯,思路开阔,我私下称他“胖胖”。胖胖有个观点,即重大新闻本报不能缺位,不能仅守着本市的一亩三分地,得把眼光放远。我欣然领命。胖胖要求我:“你算大哥了,外出时得带上小兄弟们一起去历练。”
于是,在新的路途上,天地向我展开新场景:那些亲历过战争的老兵和老军工,那些深山中的护林人和养路工,那些流浪的歌手和画家,那些为他人奉献了生命的年轻学子…--他们向我走来,让我读’瞳行走与新闻的意义。
但这样的路途有时非常艰苦,堪比知青年代。
譬如在新疆兵团。那是古尔班通古特大漠边的一个产棉连队,我和小李去采访拾花工。我俩从石河子租车北上,越走越荒凉,心想这儿哪适合人类居住呢?未承想,到了连队,白杨树高耸,棉田逶迤至天边,拾花工星散于大田,一行棉丛拾过去再拾回来,得一整天!
我俩被镇住了。
拾花工的艰辛与期待、从以色列引进的滴灌技术、电脑对水源的全程控制、机械化采棉和一个团场竟建有一座农用机场等,全新的信息让人应接不暇:这可是找到了好题材!
采访未完,当夜留宿连队。连队的仓库都挤满了各地来的拾花工,我们只能与指导员同宿一屋。指导员姓杨,壮实,白天的交流增进了认识。临睡前,他指着另一张单人床说:“你俩就凑合一晚吧,没水,不能洗漱,两个大男人,睡一头不像话嘛,于是与小李脚对脚。那味道够邪乎,且只有一条铺盖,便只能背靠背,闻着味,渐入梦乡。
清晨6点起床,没找到水刷牙,只能用昨晚剩的矿泉水漱了漱口,拿起两个馒头,跟着拾花工一块儿下大田。晚上回来,又没洗脚,与小李再挤一床。如是三天,反而习惯了,不禁暗笑:早年当知青时,也没这么邋遢呀!
这没办法,云南水多,随处可洗;新疆缺水,只能省着,更何况,一个产棉连队哪来的招待所呢,能有床睡就不错了。但就是在这艰苦的路途上,我和小李写出了系列报道《追你追到天尽头》,获全市新闻大奖。
最心悸的夜宿是在川西红原县。那是松潘草地边缘,九曲黄河从眼前流过,过河就是青海玛多县了。我和摄影师冉文为追寻长征足迹来到这里。是夜,红原县搞宣传的老陈接待我们,一听我当过知青,他来劲儿了:“我也当过,插队到红原后,就扎根在这儿了。”说罢,打开酒瓶。我说海拔太高,不敢喝。老陈正色道:“天下知青是一家,你能不喝吗?再说啦,我还想听你讲云南知青返城的故事呢!”于是喝,三个人一瓶白酒没喝完,我已头昏。
回招待所后沉沉睡去,半夜忽然觉得胸膛上像压了一块石磨,重得透不过气,不禁大喊一声,醒了,身子却动弹不得,石磨的压迫感仍在。“这是要死的前奏吗?”第一个念头是起了高原反应,不禁汗如雨下,把冉文吓坏了。
还好,那一通汗流出后,人就轻松了。忠告一句:初上高原的人,最好不要喝白酒!
还有一次是在甘肃庆阳。我和冉文赶到时已是夜里10点,找了两家旅店居然都满了。第三家是石油招待所,前台工作人员说:“今晚没热水,住吗?”我说住啊,这么晚了,还洗啥呀。房间里的床虽是席梦思,但中间高,两头低,睡下后感觉人是倒悬的。晨起,脸肿了。去街头吃早点,庆阳的油饼很实在,大得像张飞的脸。冉文看看饼,又看看我,突然笑道:“哥,我咋觉得这油饼胖得就像你的脸呢?”
行走川西、甘南几千里,我写出长篇报告文学《重走长征山地》。
记者的苦乐往往就在路途上,而路途即人生。这些年一路走过,看到了无限风景,更看到了时代的变迁。大地,已发生亙古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