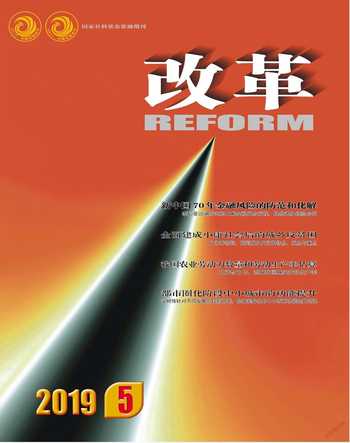新中国70年金融风险的防范和化解
李稻葵 陈大鹏 石锦建


内容提要:新中国成立70年来,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没有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这离不开对金融风险的积极防范和化解。新中国70年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基本经验包括:及时识别和处置金融风险,对于暴露出来的体制机制问题加以改革,着力处理好社会稳定问题,增强经济主体信心。下一步,要着力改革基础设施投融资体系,强化不良资产处置机制,推进股市法制建设,完善上市公司退市制度,妥善处理企业间“三角债”问题。
关键词:金融风险;金融危机;金融体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F83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43(2019)05-0005-14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三大攻坚战”,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其中,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2019年2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回顾新中国70年光辉历程,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没有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这离不开我国对各种金融风险的积极防范、及时应对、妥善化解。回顾新中国70年积极应对高通胀风险、外汇相关风险、银行体系风险、国内债务风险和股市剧烈波动风险等金融风险的历程,并梳理其基本经验,对于当下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具有重要意义,也可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找寻方向。
一、新中国70年积极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历程
70年来,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和一系列金融风险事件,我国积极防范、及时应对、妥善化解金融风险,避免了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发生。
(一)积极应对高通胀风险
高通胀风险是指经济体出现物价水平快速大幅上升的风险。这里使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数据,考察我国的年度通胀率(见图1,下页)。由图1可见,虽然我国有过较高通胀时期,例如新中国成立初期、1959~1961年、1988~1989年、1993~1995年等,但这些高通胀时期持续时间不长且通胀水平也远低于“通胀危机”标准①。总之,我国积极防范化解高通胀风险,较好地控制了通胀问题,这与我国综合利用行政手段、改革手段、市场手段,进行精心的宏观调控密不可分。
1.改革开放前的高通胀问题及其应对
1949年10~12月,我国发生了“物价大波动”,以上海、天津为中心,波及华中地区和西北地区,主要原因是投机商抢购商品、哄抬物价、囤积居奇。面对重要物资价格的快速上涨,政府指导各地国营贸易公司以市场价格足量供应粮、布、煤、盐等物资,凭借雄厚的实力使得物资价格开始下跌,这导致投机商不得不开始抛售物资,从而导致了物价进一步下降,该轮“物价大波动”得到平息。1949年12月至1950年3月又发生了物价大波动,其主要原因是政府超发货币来补充财政赤字以及投机商哄抬物价等。政府积极应对,着力收紧银根,减少贷款额度、催还欠款,并规定国营企业资金一律存入国家银行,不得向私营银行和私营企业放款;另外,在财政上开源节流、减少赤字;同时,取缔地下钱庄,截断投机商的资金来源。在这些措施的综合作用下,该轮物价大波动也得到平息[1]。总之,新中國成立初期,国家在防范化解高通胀风险的同时,建立起了符合当时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需要的物资周转秩序和物价管理体制。
在计划经济时期,虽然主要生活物资都是国家定价、定量供应、统购统销,但仍有通胀风险。例如,“大跃进”运动中的盲目建设导致1959~1961年发生严重的物资短缺,尤其是粮食供应严重不足,通货膨胀严重,集中体现为黑市价格或集市价格的大幅上涨。为了缓解群众生活困难,政府采取“低价+平均分配”和“高价+敞开供应”相结合的策略,一方面通过行政手段,对于基本日用品尤其是粮食进行严格定量供应,强调“凭证供应”(如发行“粮票”等)和“平均分配”(按照人口数分配),保障群众日常生活、维护社会稳定;另一方面,有选择地供应高价商品(如海参、火腿等高级副食品和钟表、名酒等高级用品),使得黑市中的通货膨胀在官方商品价格上体现出来(表现为官方通胀率激增,从1960年的2.5%上涨为1961年的16.1%),达到了回笼货币、抑制通胀的目的[2]。
2.改革开放后的高通胀问题及其应对
改革开放后,我国分别在1985年、1988年和1994年前后出现过较大规模的通胀,政府主要通过行政手段和货币政策等工具进行积极调控。
1985年高通胀的背景是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投资热潮以及工资制度改革。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到20世纪末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5年开始实行“拨改贷”政策,导致地方政府和企业有强烈激励和自主能力来扩大投资规模,固定资产投资大幅增加,同时货币供应大幅增加、信贷规模明显扩大;另外,国务院实行工资改革,大幅提升了居民收入。以上因素叠加,导致社会总需求过旺、物价水平快速提升,1985年CPI增速达到9.3%。为了抑制通胀,国家减少货币发行、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限制消费能力扩张、加强物价监管,通胀率下降到6%~7%。
1988年,国家理顺价格机制,提出进行“价格闯关”,逐渐放开肉、蛋、菜、糖价格和烟酒价格,物价又出现较大上涨,甚至发生抢购,加之信贷政策由严转松导致的固定资产投资重新上马、货币供应提速,CPI增速达到18.8%。面对这一挑战,1989年,国家开始整顿经济秩序,控制贷款规模紧缩银根、提高利率回笼货币,减少社会总需求,最终控制住了通胀。值得说明的是,“价格闯关”在本轮通胀中的作用需要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方面这是从价格管制状态走向市场决定机制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当时经济体制的不完善之处。
1994年,我国经济出现过热,通胀率再次达到高位,超过24%。其原因包括:1992年南方谈话之后全国掀起新一轮投资热潮,利率下调、银根放松、信贷扩张,货币发行明显提速,以及1993年进一步放开价格管制,推行税制改革、汇率并轨和工资改革等,消费需求急剧膨胀在推升物价的同时强化了通胀预期并引致“抢购潮”。在高通胀背景下,政府把抑制通货膨胀问题定位为“首位经济问题”,采取“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提高银行存贷利率,减少货币供应量,整顿金融秩序,打击房地产投资和基建项目重复建设,抑制社会集团的购买力,成功将通胀率降低到1996年的8.3%。
(二)积极应对外汇、外债和资本外逃风险
货币汇率风险是最为重要的金融风险之一,且往往伴随资本外逃风险。汇率快速、大幅贬值往往导致资本外逃加剧、外债压力增大、央行外汇储备快速缩水、国内利率急剧攀升,会对经济体造成较大破坏。70年来,我国积极防范化解了货币汇率风险,避免了“被动”式的汇率快速、大幅贬值,且较为成功地应对了资金外逃风险,外债也一直控制在较低水平。
1.汇率波动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需要指出的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经历了若干次改革,政府干预色彩较浓,在定量分析的同时我们需要考虑到外汇政策的主动调整,把汇率双轨制时期基于汇率政策调整的“主动”贬值与汇率并轨后基于市场预期和市场机制的“被动”贬值区分开来分析。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实行单一汇率制;1981~1984年,我国实行双重汇率制度,官方汇率与外汇内部结算价并行;1985~1993年,仍然实行双重汇率制度,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的结算价并行。可见,1994年之前的汇率更多是政府主观意志的体现,而非市场价格。1994年,官方汇率和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且取消了外汇留成和上缴制度,实行银行结售汇,并建立了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3]。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开始,人民币汇率钉住美元,波动区间较窄。2005年,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结束了人民币汇率钉住美元的临时政策。2015年,我国进一步完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
研究货币汇率危机的文献往往以“一定时期内的贬值幅度超过某一临界值”来界定危机发生。例如,Frankel & Rose研究1971~1992年105个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危机,定义“货币危机”为一年内当地货币兑美元汇率贬值超过25%且贬值幅度超过上一年度至少10个百分点[4]。Reinhart & Rogoff认为贬值幅度25%的标准太高,从“二战”后各国发生危机的经验来看,更小的贬值幅度也可以导致恶劣后果,所以其界定货币危机为一年内汇率贬值超过15%[5]。在了解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历史的基础上,我们使用外汇管理局公布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年度平均值数据,来考察人民币汇率波动是否曾达到货币汇率危机的标准。
1981~2017年人民币汇率波动情况如图2(下页)所示。由图2可见,1981~1994年为实行“双重汇率”制度的时期,人民币汇率有过较为剧烈的波动,贬值率数次超过15%,1994年“并轨”当年甚至超过30%。但正如我们之前所述,该时期汇率并非“市场价格”,事实上主要体现了政府的主观意志和主动调整,不宜认为是货币汇率危机的体现。1994年并轨以来,人民币汇率基本维持稳定,尤其值得指出的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我国承诺并保持了人民币汇率稳定,为区域金融稳定和经济恢复作出了巨大贡献。2005年汇率改革导致人民币明显升值。2015年汇率改革导致人民币出现贬值,但年度贬值率最大仅为-6.2%。
2.资本外逃风险及其应对
70年来,我国也一直在积极防范化解资本外逃风险。资本外逃风险既可能“风起云涌”,例如1991~1994年伴随人民币汇率的剧烈波动而酝酿的资本外逃风险;也可能“暗流涌动”,例如1995~2004年人民币汇率维持相对稳定,但同样存在资本外逃风险。面临资本外逃风险,我国加强外汇管制,严格执行强制结汇的银行结售匯制度①以及进出口台账核销制度②,打击通过进出口“伪报”和虚假贸易等方式汇出外汇的行为,从而稳定币值、稳定信心,降低投机者对于“汇差套利”的预期。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逐渐对强制结售汇制度松绑,并于2012年取消强制结售汇,允许企业和个人自主保留外汇收入。为了推进贸易便利化,我国对货物贸易外汇管理体制作了系列改革和试点,例如2010年,我国开始试点进口付汇管理由逐笔核销向总量核查、由现场核销向非现场核查、由行为监管向主体监管转变,并允许境内企业将具有真实、合法交易背景的货物贸易出口收入存放境外(包括港澳台地区)。2012年,全国正式实施新的货物贸易外汇管理制度,对企业实施动态分类管理,对企业的贸易外汇管理方式由现场逐笔核销改变为非现场总量核查。2015年汇率改革后,人民币出现贬值预期,叠加经济下行压力、反腐深化推进等因素,资本外逃风险加大,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境外旅游交易以及“误差与遗漏”账户都可能隐含了大量的资本外逃[6]。我国一方面动用外汇储备来稳定汇率,另一方面严格审查海外并购行为,增强对外汇交易的真实性审核,维护了汇率和跨境资本流动的稳定。
3.国外债务的控制和风险防范
与货币汇率风险和资本外逃风险紧密相关的另一个金融风险是外债风险。国外债务风险是指国内公共部门或者私人部门无力偿付外国投资者持有的到期债务(往往以外币计价),从而发生大规模违约的风险。我国一直对外债持慎重态度。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曾向苏联贷款引进技术和设备以支撑新项目建设,但规模有限。“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实行“既无外债,也无内债”的方针。改革开放之后,我国重新开始发行外债,但一直采取慎重态度进行严格监管。例如,为了准确、及时、完整地统计全国的外债信息、加强对外债资金流出入的管理,我国于1987年发布《外债统计监测暂行规定》,于1989年发布《外债登记实施细则》,于1997年发布《外债统计监测实施细则》,建立和完善了外债登记和监测制度。从整体来看,以外债总量占GDP的比例衡量,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处于较低水平。1985~2018年,我国外债与GDP之比最高值仅为17%。
研究国外债务风险的文献往往侧重公共部门(政府)直接或者间接负有偿还义务的债务。Kraay & Nehru定义国外债务危机为满足如下条件至少一条:发生利息或者本金拖欠,且相对外债总量数额巨大;发生主权债务重组或者债务减免;求助于IMF非优惠性的常备借款安排或者扩展借款项目[7]。我国显然没有发生类似事件。从债务人类型来看,我国政府作为直接债务人或者提供担保的国外债务没有发生过违约事件。企业作为直接债务人且没有政府担保的国外债务发生过违约,但只是极少数个案而非系统性违约,不构成国外债务危机。
(三)积极应对银行体系风险
银行体系风险是指发生大规模的银行挤兑和破产的风险。银行体系风险往往由信贷大规模违约、银行资产剧烈贬值引致,表现为银行资本充足率严重不足、银行发生大面积挤兑、被迫重组甚至破产。Reinhart & Rogoff定义银行危机为以下两类事件:挤兑导致一家以上的金融机构破产、重组或者被政府接管;虽然没有发生挤兑,但是有一家以上的重要金融机构破产、重组或者被政府接管,并引发了后续更多家金融机构发生类似事件[5]。
我国积极防范化解银行体系风险,避免了系统性银行危机的发生。诚然,个别银行曾经爆发风险。例如,1998年初,受房地产泡沫拖累、兼并信用社引入高息存款造成额外资金压力,海南发展银行陷入财务困境,发生挤兑事件,最终导致中国人民银行于1998年6月决定关闭海南发展银行。海南发展银行成为新中国历史上唯一一家破产的银行,但其对其他银行和整个金融体系的负面影响有限,并未造成系统性的恐慌①。这里以2000年左右剥离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以及2009年以来积极治理“影子银行”体系为例,说明我国对银行体系风险的积极防范和主动化解情况。
1.剥离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
1992年后,我国改革开放进程加快,经济迅速发展,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持续扩大,但地方政府对银行的行政干预较多,不良贷款率走高。加之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国内国外的经济形势同时对银行业带来冲击。根据施华强测算,从账面上看,1999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已经高达39%,不良资产余额达到2.5万亿元(接近1999年GDP的30%,约为当年财政收入的220%);如果考虑按照五级分类标准调整,不良贷款率还要高5个百分点左右[8]。另外,正如李德指出,不良贷款存量中有大量长期积淀形成的呆滞贷款,所对应的企业已经停产、项目已经停建,实际上是应该加以核销的“坏账”[9]。虽然该段时期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长期在高位徘徊,但我国没有发生系统性的银行危机(银行挤兑、破产)。其关键原因是,我国政府帮助国有商业银行扩充资本金并成功剥离不良资产,维持了银行体系的稳定。
具体而言,我国于1998年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补充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1999年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长城、信达、华融、东方),一次性剥离和收购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1.4万亿元。国家给予这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以政策优惠,具体包括:资金来源上,财政部核拨资本金,并划拨部分央行发放给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再贷款,同时发行金融债券;在风险承担上,资产处置损失由国家财政“兜底”;在税收上,免交不良资产收购、承接、处置等业务的应缴税项和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赋予灵活的资产处置手段;且财政部承诺以回收现金的1%~1.2%作为资产管理公司的奖励基金。资产管理公司运用各种手段处置不良资产,截至2003年9月末,累计处置不良资产4000多亿元,其中回收现金860多亿元(现金回收率超过1/5),取得了一定成效[9]。在这些政策的作用下,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明显下降,按照五级分类标准2003年末的不良贷款率降为19.74%,但仍处于较高水平[8]。于是,国家于2003~2004年对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再次进行不良资产核销和剥离,并向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进行了225亿美元注资;2005年,向中国工商银行进行150亿美元注资;2008年,向中国农业银行进行190亿美元注资。至此,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都降低至合理范围,且后来均成功上市,我国逐步建立起现代商业银行体系。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下,我国政府及时处置银行不良资产,在成功防范系统性银行危机的同时,促使银行再次焕发活力、继续支持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商业银行体系,也对稳定亚洲经济作出了突出贡献。
2.积极治理“影子银行”体系
2006年以来,我国银行体系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商业银行广泛参与“影子银行”活动,且存在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这使得影子银行体系成为“银行的影子”,增大了银行体系风险。银行理财产品是影子银行体系最为重要的资金来源之一。银行发行理财产品所募集的资金可以投向信托公司信托计划或者证券公司资管产品,从而形成“银信合作”和“银证合作”,使得银行可以绕过存贷款、资本充足率、拨贷比、贷款额度等监管指标开展表外业务,实现“监管套利”。根据银保监会数据,2018年底银行理财总规模约为32万亿元,其中非保本的理财产品高达22万亿元。这些理财产品多采用“滚动发售、集合运作、期限错配、分离定价”的资金池模式管理,产品期限短、资产期限长,期限错配带来的流动性风险增加[10]。
为了应对这一风险,我国推出了一系列措施,规范银行表外业务,治理影子银行体系。为了管控“银信合作”,原银监会发布《关于规范银信理财合作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进一步规范银信理财合作业务的通知》等,控制银信理财合作规模,推動银行表外业务回表,要求增加银行拨备和信托公司风险资本计提。在这种情况下,通道业务由信托公司转向证券公司。原银监会积极应对,发布《关于规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投资运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对银行理财资金投资非标资产的规模作出了直接限制。2014年以来,大量银行理财资金流入同业市场,造成资金在金融体系“空转”。鉴于此,监管部门发布《关于规范金融机构同业业务的通知》,逐项界定并规范同业拆借、同业存款、同业借款、同业代付、买入返售(卖出回购)等同业投融资业务,并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进行管理。同时,监管部门着力打破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推动银行理财回归代客理财的本质。例如,原银监会发布《关于规范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资产收益权转让业务的通知》,要求转让收益权的银行不得承担显性或隐性回购义务。2017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管局发布《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并于2018年4月正式发布,统一同类资产管理产品监管标准,明确资产管理业务不得承诺保本保收益,严格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这一文件出台后,对影子银行的治理整顿初见成效,但金融过度收紧也导致实体经济严重承压,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调整。
(四)积极应对国内债务风险
国内债务风险是指公共部门或者私人部门无力偿付本国投资者持有的到期债务(往往以本币计价),从而发生大规模违约的风险。我国及时、有效地监测并化解了相关风险,例如20世纪90年代清理企业“三角债”、2000年左右处置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主要是企业贷款)、2013年以来积极稳妥化解累积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等,避免了地方政府、企业、金融机构的系统性破产。
1.20世纪90年代清理企业“三角债”
1990~1992年,我国曾发起了一场清理“三角债”运动。其背景是20世纪80年代末企业间“三角债”问题快速凸显。到1991年,全国90%的企业被卷入“三角债”链条,即使只统计“不正常的拖欠”,1990年初也达到2000亿元的规模,占GDP的10%以上[11]。
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从政府本身来看,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地方政府有强烈的冲动大办工业、扩大投资,而财政力不能支。为了绕过中央监管,地方政府在项目申报期“漏报少报”,一旦项目上马,就会出现严重超支,但上级政府(以及国有银行)不得不持续补充资金、维持项目运转,这导致大量银行信贷资源被占用。如果信贷资金也不够,就必然拖欠企业货款和工程款,被拖欠企业又不得不拖欠他们的供应商,由此形成大量企业间债务拖欠。从企业来看,因为产权关系尚未厘清,大量企业的投资行为由政府主导,一方面,投资项目缺乏后期流动资金支持,无法正常投产,另一方面,很多项目不符合市场需求,产品缺乏销路、大量积压,企业大量亏损。这些都导致企业现金流吃紧,不得不依赖银行贷款和商业信用融资。在信贷宽松期,这一局面尚能维持。但1988年以来,为了遏制经济过热态势,政府加大宏观调控力度,严控信贷规模,压缩投资和消费需求。这直接导致企业融资和经营愈发困难,相互欠款无法及时归还,引发连锁反应,波及原材料、能源、轻纺、机电、交通运输以及商业和基本建设等各行各业,使“三角债”问题愈发严重。
1990年3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理“三角债”工作的通知》,并成立了清理“三角债”领导小组,负责组织领导全国清理“三角债”工作。最初,清理工作的思路是全国全面铺开,但出现了“前清后欠、边清边欠”的问题。为了进一步化解“三角债”风险,我国把清理“三角债”作为搞好大中型企业、提高经济效益的突破口,并把清欠的突破口定为清理固定资产投资资金缺口,由国家注入贷款、地方政府承担最终偿还责任。虽然在所有应付和预付货款中,基建和技改项目只占20%,但是这些项目的欠款处于“三角债”链条的尾部,尾部企业拿到资金,归还中游企业的欠款,中游企业进一步归还上游企业的欠款,这就形成了连环清欠的“叠加”效果,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按此思路,国务院召开全国清理“三角债”工作会议,设定了债权债务“两头清”、固定资产投资拖欠和流动资金拖欠“两手清”、各级政府和企业“思想清”的方针。对于产销不对路、亏损严重的企业,政府在清理“三角债”的同时,要求这些企业停产,投资升级设备、高薪吸引人才,回归良性運转。1991年和1992年,全国共注入清欠资金555亿元,其中银行贷款520亿元,地方和企业自筹35亿元,共清理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拖欠款2190亿元,“三角债”问题得到改善,企业经济效益逐渐提升。
2.2013年以来化解累积的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
2008年后,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我国推出经济刺激计划。其中,中央政府安排资金1.18万亿元,地方政府配套1.25万亿元。利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获取银行贷款成为重要的资金来源,地方政府负债(尤其是隐性负债)大幅增加。
2013年,审计署对地方政府债务进行了摸底。根据其发布的《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截至2013年6月底,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约10.9万亿元,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约2.7万亿元,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约4.3万亿元。对于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从举债主体看,融资平台公司占比最高;从债务资金来源看,银行贷款占大多数,其次是BT(建设-转交机制)和发行债券。2013年我国GDP为59.3万亿元,地方政府负有偿还、担保或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总量约为当年GDP的30.2%。
201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要求“疏堵结合”,加快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具体措施包括:第一,举借债务限于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市县级政府如果需要须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代为举借。第二,政府债务只能通过政府及其部门举借,不得通过企事业单位等举借。第三,地方政府举债采取政府债券方式,有收益的公益性事业发行专项债券融资,没有收益的则用一般债券融资。第四,鼓励PPP方式,利用社会资金减少政府负债压力。
从2015年开始,财政部组织“置换地方债”,把贷款和非标的债务置换为政府债券,2015年、2016年、2017年、2018年(前十月)分别发行置换债3.2万亿元、4.9万亿元、2.8万亿元、2万亿元,累计近13万亿元。对照2013年审计署公布的数字,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基本置换完成。
按照财政部数据,截至2018年10月,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存量约18.4万亿元。2018年GDP约为90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存量约为GDP的20.4%。这些债务绝大多数为政府债券,剩余平均年限为4.5年。按照用途分,一般债券为10.9万亿元,平均利率为3.49%;专项债券为7.5万亿元,平均利率3.52%。债券利率相对之前贷款和非标类政府债务利率有大幅下降,减小了地方政府的融资成本。
(五)积极应对股市剧烈波动风险
参考Barro & Ursua等文献[12],本文用经通胀调整的股市年度真实收益率来研究股市剧烈波动风险。我们使用流通市值加权、考虑现金红利再投资的综合A股回报率作为股市名义回报率,并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剔除通胀,计算股市真实收益率,发现A股真实收益率有较大波动。Barro & Ursua定义“股市大幅下跌”为经通胀调账后的年度或者连续下跌的几年累积下跌幅度超过25%[12],按此定义,A股多次发生“大幅下跌”:1993~1995年(-72.7%)、2001~2005年(-58.4%)、2008年(-68.5%)、2010~2011年(-34.2%)、2018年(-26.5%)。另外,2015年年内,A股市场发生大幅异常波动,上证综指从2015年1月5日的3351点一路上涨到2015年6月12日的5166点,上涨54%;随后大幅下跌,2015年12月31日跌至3539点,跌幅超过30%。
需要指出的是,股市剧烈波动风险虽然是一种较为常见且备受关注的金融风险,但不一定给实体经济造成严重不良影响。实际上,文献中对于是否将股市剧烈波动作为“金融危机”来处理的意见不一。Eichengreen & Bordo认为应该从经济“实际影响”而非“名义影响”的角度来界定金融危机[13]。Schwartz认为,单纯的股指下跌、房地产价格下跌等,都只能算作“伪危机”[14]。但是Aliber & Kindleberger认为金融危机的范畴应该更广,包含资产价格的暴跌[15]。Reinhart & Rogoff把Kindleberger的理念引入了对金融危机的系统性分析,以Barro & Ursua的方法来定义“股市大幅下跌”,但对“单纯的股市下跌”(例如2001年美国IT泡沫破裂)的分析依然着墨不多[12]。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A股历次大幅下跌均没有导致系统性的企业破产、金融机构倒闭、居民生活水平严重下降等,对实体经济的传导有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股市剧烈波动对实体经济没有负面影响。股市快速上涨时期,出于投机性的逐利动机,银行信贷资金可能违规流入股市,影响货币政策的正常传导、助长股市泡沫、挤出实体经济的融资[16]。而股市快速下跌时期,出于恐慌,投资者可能进一步抛售股票,并拒绝为上市企业提供新的融资,加重企业融资约束;尤其是当上市公司存在大股东股票质押时,股价的“自我实现式下跌”可能导致股价崩盘、资金链断裂[17]。另外,股市剧烈波动可能破坏股价反映公司经营状况的“信号机制”,股价信息质量的下降将导致资源配置效率降低。
鉴于此,我国采取综合措施应对股市剧烈波动,标本兼治、双管齐下,避免股市风险向实体经济的传染。一方面,当股市剧烈波动可能传染到实体经济时,政府采取果断措施着力稳定股价。具体而言,在面对股市大幅下跌时,政府采取调整货币政策释放流动性、动用政府资金直接入市、限制新审批IPO、放松投资者管控和交易限制等策略来“救市”,防止股价进一步下跌。例如,2018年A股下跌明显,深圳市人民政府斥资百亿,建立上市公司债权融资支持机制,设立优质上市公司股权投资专项基金,从债权和股权两方面入手,按照市场化运作原则,采取过桥贷款、委托贷款、债权收购、股权收购等多方式、多渠道构建风险共济机制,帮助符合一定条件的上市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化解股票质押流动性危机。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有证据表明类似的“救市”策略短期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奏效[18],但其长期影响尚需进一步研究和讨论。另一方面,针对股市的剧烈波动,我国除适当平抑波动、稳定投资者预期外,更加强调针对暴露出来的问题深化改革、完善制度。
二、新中国70年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经验
(一)及时监测和识别金融风险,并全力以赴把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
金融风险的累积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一旦爆发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危机传染性强、扩散速度快。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底线,需要对金融风险进行及时的、全面的、有效的监测和识别,并在此基础上,针对可能爆发的金融风险采取果断措施,将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
及时监测和识别金融风险要求监管部门“下沉”到基层,对各地区、各类别金融机构的业务进行全面有效监管。原银监会系统有36个银监局、306个银监分局和1730个监管办事处,另加4个培训中心,总人数超过2.3万人;原保监会则设有36个省级保监局、13个地市级保监分局,总人数在3000人左右。2018年末,银保监会派出机构增设县局,改为省、市、县三级架构,监管力量进一步下沉,有助于更快、更好地监测各地区、各业务线的金融风险。
同时,当金融风险开始暴露时,政府快速响应、及时干预,将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例如,面临1994~1995年的高通胀,政府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和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中心,采取果断手段抑制通貨膨胀,包括行政限价、定量供应、价格检查等,避免物价进一步上涨威胁群众正常生活和社会稳定。又如,面对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我国积极果断地采取措施,较为成功地阻挡了危机扩散和恶化,保持了我国金融体系的基本稳定。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我国对货币市场加强宏观调控,同时央行2次降准、6次降息,1998年新增发国债1500亿元,用成功的调控维持了宏观稳定。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国务院成立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小组,建立了旬会制度,进一步加强“一行三会”的协调配合,密切关注和着力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央行4次降准、5次降息,通过大规模一揽子计划加大对国内市场的刺激,扩大内需,投资民生领域,促进经济平稳过渡。在近年来经济金融形势不稳的背景下,国务院层面专门成立了“金融发展稳定委员会”,行政级别高于“一行三会”,国务院副总理任委员会主任,专门协调金融稳定和改革发展的问题[19]。
(二)对于暴露出来的体制机制问题加以改革,采取综合措施、标本兼治,增强金融体系的稳健性和完备性
我国从风险积累的根源入手,对于暴露出来的体制机制问题加以改革,治标治本双管齐下。
例如,1985年在控制通胀的同时,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在农业领域推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工业领域深化企业改革,在金融领域促进金融要素的市场化配置,这些改革促进了进一步的经济增长。1989年“价格闯关”导致高通胀时期,我国在着力抑制通胀的同时,着力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例如1989年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指出要“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各项改革措施,逐步建立符合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原则的,经济、行政、法律手段综合运用的宏观调控体系”,为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了基础。
又如,1992年8月深圳因“新股认购抽签表”发放问题发生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暴露了全国统一监管缺位导致的地方金融市场乱象。基于此,我国于1992年10月设立了国务院证券管理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并于12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证券市场宏观管理的通知》,明确了中央政府对证券市场的统一管理体制,这标志着中国证券市场开始逐步纳入全国统一监管框架,全国性市场由此开始发展。同时,开始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从法制上对证券市场进行规范。
再如,2000年左右国家剥离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使得处于“技术性破产”的银行体系免于彻底破产和瘫痪,同时国家启动了国有商业银行的综合改革。在这一系列改革措施作用下,国有四大商业银行“脱胎换骨”,先后成功上市,我国逐步建立起现代商业银行体系。
另外,2015年A股市场发生大幅异常波动,在积极应对、平抑波动的同时,证监会从根源入手、全面清查场外配资,并基于清查结果,于2016年底对13个涉案主体及其相关负责人实施严厉的行政处罚,并持续加强对交易的全过程监管尤其是异常交易监控。
(三)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过程中着力处理好社会稳定问题,维护经济主体的信心
社会稳定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我国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过程中也十分注重保持社会稳定、维护人民信心。我国尤其重视积极化解与银行相关的金融风险,以维护人民对银行体系的信心。因为银行体系事关大量储户的切身利益,一旦信心动摇,很可能发生恐慌的系统性扩散,严重影响社会稳定。我国对扰乱银行体系正常秩序的行为给予严厉打击,例如曾对非法集资行为给出“死刑”和“死缓”判决。当银行系统风险开始显现时,政府及时化解,例如2000年左右剥离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当发生局部的银行挤兑风险时,央行及时干预,例如20世纪90年代后期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以及国内经济自身问题困扰,局部地区的银行尤其城市信用社挤兑风险上升,央行发布《关于城市信用社动用存款准备金有关事宜的通知》,允许动用存款准备金来兑付储户存款,提升了储户信心,避免了大规模挤兑。当具体金融机构破产时,政府往往为储户的存款提供偿还支持,例如1998年廣东国际信托破产案中,中国银行代为清偿境内自然人存款7亿多元本金;在2004年南方证券破产案中,央行专门提供87亿元再贷款,以帮助南方证券全部偿还之前挪用的股民的保证金。
三、当前我国金融风险及其防范策略
2019~2021年是我国由“第一个一百年”向“第二个一百年”过渡的重要历史交汇期。我国应认真研判当前形势,着力深化改革,决胜“第一个一百年”奋斗征程,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打下坚实基础。目前我国面临的金融风险主要包括:地方债期限错配、投融资脱节,僵尸企业不能及时退出、不良资产处置不力,股票市场违规成本低、违规行为多,上市企业“退市难”、“优胜劣汰”机制不通畅,企业间“三角债”(尤其是大型企业、国有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款项)问题较为严重等。金融体系改革是当前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牛鼻子”,全面推进金融体制现代化建设,是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促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是我国决胜“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并继续推进“第二个一百年”奋斗征程的关键。
(一)针对地方债期限错配和投融资脱节的问题,应推动基建融资需求从银行信贷市场转移到债券市场,并成立专业性的基建投资公司负责基建项目的论证、管理与运营,实现基建投资的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逐步形成了一套地方政府主导的、银行信贷驱动的基础设施建设模式。这种模式在改革开放以来的较长时期发挥了积极作用,使我国在短短几十年内迅速崛起为全球基建大国和强国,支撑了我国经济连续多年高速增长。但随着我国经济增速下行及杠杆率走高,传统的基建增长模式已经难以适应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一方面,现有的基建融资渠道虽然较多,但这些渠道资金追根溯源主要来自银行体系,而银行资金的“短期限、高利率”性质很难与基建资金的“长期性、低成本”需求相匹配,造成了较严重的期限错配风险。更严重的是,基建项目对信贷资金的占用加剧了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推升了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另一方面,当前地方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缺乏统一、高效的可行性分析和管理运营,存在项目成本收益分析流于形式、监督难和追责难等一系列问题。
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体制亟待改革,应该从根本上打造现代化的基础设施投融资模式,走出一条高质量、可持续的基础设施建设之路。这不仅有助于保证基础设施投资平稳、高效,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稳定器,而且将为世界各国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中国方案。具体而言,一方面,要将基建融资需求从银行信贷体系中剥离出去,转而依赖债券融资。目前十年期国债的年化利率在3.5%左右,低于地方政府从银行贷款的利率;我国债券市场规模与主要发达经济体相比也明显偏低。在中央政府的担保下,以发行基建债券的形式从资本市场上大规模、低成本融资具有可行性。这也可以释放出大量银行信贷资金,不仅可以缓解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困境,而且有助于化解银行资金期限错配风险和投融资需求的不匹配问题。另一方面,要成立全国性的基础设施投资公司,统一管理地方基建项目的规划、融资、建设与监督,由这一公司对地方基建项目进行市场化成本收益分析,发行债券或组织社会资本为项目融资,并行使出资人权利对项目进行监督、追责。
(二)针对僵尸企业不能及时退出、不良资产处置不力的问题,应建立金融体系高效处置不良金融资产的内在机制,促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我国金融体系在支持企业进入和成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积累了较多经验,但在推动无效、低效企业退出方面能力不足,尤其体现在无效率的僵尸企业“僵而不死”和一些行业低效率企业众多。根据国资委数据,2016年中央企业需要专项处置和治理的“僵尸企业”和特困企业超过2000家,涉及资产3万亿元。有文献测算我国工业部门的“僵尸企业”数量占比约为7.5%,且大中型企业中僵尸企业的比例高于小型企业[20]。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年12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总计约为113.4万亿元,如果按照5%的比例计算,僵尸企业涉及的资产约为6万亿元。而根据银保监会数据,2018年商业银行累计核销不良贷款近1万亿元。我们推算2018年化解不良资产的总量约为1.5万亿元。按此速度,即便不考虑新增,也需要4年才能消化完全部的不良资产。如果按平均贷款期限三年计算,6万亿元不良资产不处置,意味着每年将占用2万亿元贷款规模,这占到了2018年新增贷款的13%。如果低效、无效企业不能及时从经济体系清理出去,大量的资金、土地、劳动力等要素资源将被占用,价格信号也会被扭曲,进而影响整个经济体系运行的效率和质量。
然而,僵尸企业的自发退出数量少、比例低。例如,李曙光研究发现,2016年全国适用破产程序退出市场的企业占所有退出市场企业的比例只有0.5%左右[21],存在大量资不抵债企业未经破产程序即退出市场,且存在大量“休眠企业”①。我国低效企业的退出情况同样不如人意,大量中下游制造业行业企业数量多、产能过剩严重、低效竞争普遍。以电梯行业为例,根据相关报道,目前国内电梯年产能已超140万台,而全球年需求量仅有110万台左右,已经发生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22]。截至2015年底,我国电梯行业共有整机制造企业约600家,其中最大的合资企业(奥的斯、上海三菱、广州日立)和外资企业(如迅达、蒂森克虏伯等)占据了55%的市场份额,民营企业中大型民企(如康力等)占据约25%市场份额,剩下20%由其他500多家中小型民营企业激烈竞争[23]。我国经济要完成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必将提高行业集中度,而这意味着一大批企业要退出,或被兼并重组,或进行破产清算,这要求我国金融体系在清退低效无效企业方面必须提升能力、持续发力。
为此,应建立金融体系高效处置不良金融资产的内在机制,疏通金融系统的“排毒”管道,协调推动实体经济的重组与金融资产的重组。如果金融体系不能提高化解不良金融资产的能力,就会制约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进程。我国金融体系必须做好准备,动员资产管理公司等专业机构消化风险与不良资产。应下决心帮助僵尸企业破产或重整,不能任其债务无限展期、越滚越大,无限制地消耗金融资源;鼓励银行利用现有拨备消化不良贷款、核销坏账。另外,需将国有企业积累的市场化、法制化债转股经验推广到民营企业,动员各类金融机构参与市场化债转股工作。资本市场要主动发力,支持企业并购重组和行业整合,助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同时,加快法院破产重整案件的审理进度,强化司法跨区域执行。
(三)针对股票市场违规成本低、违规行为多的问题,应推动股票市场法制建设,加强执法力量和力度,从根本上保障股市的健康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解决金融领域特别是资本市场违法违规成本过低问题。从美国、英国等发达经济体经验看,资本市场是实体经济融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但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依赖于众多基础制度条件,尤其是法制基础的逐步完善,不能急于求成、一放了之。经过近30年的发展,我国的股票市场法制建设已经取得一定成效,但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夯实法制基础是当前我国股票市场健康发展的关键。2018年8月,上海金融法院正式揭牌成立,迈出了金融司法专业化的重要一步。但仅有金融法院还不够,还应该建立证券检察院,并与公安机关经侦部门密切配合,专业化地侦查、处置资本市场违法违规行为。同时,应加大执法力度,增加处罚的威慑力。与银行系统执法力度相比,股票市场处罚力度明显偏弱。比如,非法集资罪最高可判处死刑,但股票市场操纵、内幕交易等违法犯罪行为罕见长期徒刑。另一方面,股票市场作为专业化程度高、运行极其复杂的市场,客观上对执法人员的素质和执法队伍的规模要求也很高。比如,与银保监会相比,证监系统监管力量明显薄弱。银保监会合并后,派出机构改为省、市、县三级架构,监管力量进一步下沉,监管人员超过2万人,而证监系统只有36个证监局,以及2个证券监管专员办事处(上海、深圳),监管力量仅3000人左右。因此,资本市场监管力量还需壮大,监管队伍的素质还需要提高,如此方能以适应我国资本市场进一步发展的需要。
(四)针对上市企业“退市难”、“优胜劣汰”机制不通畅的问题,应完善和严格执行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确保股票市场的健康运行,更好地服务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上市公司退市制度是资本市场重要的基础性制度,我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始于2001年证监会发布《亏损公司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实施办法》。但长期以来,我国上市公司“退市难”问题突出。根据RESSET数据库数据,截至2018年末,我国A股累计仅97家上市公司退市。美国股票市场平均每年IPO大约150家,而每年因兼并、破产、私有化等原因退市等的公司约为400家。我国作为大国经济体以及仍处于中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尽管资本市场已经推出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但IPO的供给仍难以满足不断成长壮大的企业上市融资的需求。一些已经不具投资价值和成长空间的企业却始终在股票市场继续占用资金和上市资源,不仅扭曲了市场定价和估值体系,而且对股票市场运行的活力和效率产生了负面影响。上市难和退市难的并存导致上市公司的“壳”本身成为稀缺资源,即使上市公司本身经营不善、陷入财务困境,也能享受较高的“壳价值”。因而,资本市场“有进有出”的机制必须通畅,确保存在于A股中的企业始终是各行业、各领域有竞争力的优质企业。完善和强化上市公司退市制度成为资本市场下一步重点提升的方向之一。
2014年,证监会正式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并严格实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若干意见》,要求健全上市公司主动退市制度,实施重大违法公司强制退市制度,严格执行不满足交易标准要求的强制退市指标,严格执行体现公司财务状况的强制退市指标,并完善与退市相关的配套制度安排。2018年,证监会作了相关修改,新增关于发生危害国家公众健康安全等重大违法行为时的强制退市规定。下一步,还应从如下方面着手:第一,进一步完善退市的法规和制度,对符合退市条件的企业要严格执行退市程序;减少地方政府对上市公司退市的干预,妥善處理上市公司退市后的人员安置等问题。第二,用好退市企业存量“壳资源”,给拟上市的优质企业更多的上市选择。在严厉打击壳资源炒作的情况下,探索合法合规盘活更多存量壳资源的路径。第三,完善科创板和注册制相关的配套措施。作为我国资本市场的增量改革,科创板和注册制意味着资本市场的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升。只有上市制度真正市场化了,退市制度才能真正市场化,因而在科创板和注册制试点取得经验后,应该逐步推广到整个A股市场。这是形成股票市场有进有出、新陈代谢良性循环的重要途径。
(五)针对企业间“三角债”问题,应该加快“清欠”工作,并加强法制建设,对企业间付款模式进行规范,塑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商业文化
2018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14.3万亿元,占当年工业增加值的47.0%,占企业总资产的12.6%,占主营业务收入的14.0%,从比例上看企业间负债重回20世纪90年代初清理“三角债”时期的高位,且突出表现为有市场势力的企业通过商业信用占用其他企业款项问题,该种“拖欠”行为在降低供应链效率的同时,增大了“三角债”可能引致的金融风险。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示要纠正一些政府部门、大企业利用优势地位以大欺小、拖欠民营企业款项的行为。2019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的若干意见》,其中要求“加快清理拖欠民营企业账款”。随后各地区、各部门广泛开展“清欠”行动。除了直接的行政干预式的“清欠”,还应该加强法制建设,利用法制手段改善企业间付款模式,塑造“准时付款”的商业文化和营商环境。一方面,可以借鉴欧盟“打击企业间延迟付款令”(Directive 2011/7/EU on Combating Late Payment in Commercial Transactions)的模式,对账期进行外在约束,设置默认账期和账期起算时点等,规范企业间付款行为;另一方面,重点打击逾期不还款的行为,可以借鉴欧盟的模式对拖欠行为强制罚息,同时借鉴德国的模式采用“法庭付款令”,简化中小企业在被拖欠时维权的程序、降低成本。另外,应该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完善应收账款保理和应收票据贴现等融资服务体系,使得核心企业的商业信用能够惠及其中小供应商。
参考文献
[1]高璐.建国初期四次物价大波动背景、对策探析[J].价格月刊,2017(2):38-42.
[2]王永魁. 20世纪60年代初特殊形态的通货膨胀[J].党史博览,2013(6):40-41.
[3]赵志君.人民币汇率改革历程及基本经验[J].改革,2018(7):43-52.
[4]FRANKEL J A, ROSE A K. Currency crashes in emerging markets: an empirical treatment[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6, 41(3-4): 351-366.
[5]REINHART C M, ROGOFF K S. This time is different: eight centuries of financial folly[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6]余永定,肖立晟.解读中国的资本外逃[J].国际经济评论,2017(5):97-115.
[7]KRAAY A, NEHRU V. When is external debt sustainable?[J].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2006, 20(3): 341-365.
[8]施华强.国有商业银行账面不良贷款、调整因素和严重程度:1994-2004[J].金融研究,2005(12):25-39.
[9]李德.我国银行业处置不良资产的思路和途径[J].金融研究,2004(3):28-36.
[10]林晶,张昆.“影子银行”体系的风险特征与监管体系催生[J].改革,2013(7):51-57.
[11]宋怡青,李欣.周正庆回忆清理三角债始末[J].发展,2015(3):60-62.
[12]BARRO R J, URSVA J F. Stock-market crashes and depressions[J]. Research in Economics, 2017,71(3): 384-398.
[13]EICHENGREEN B, BORDOM. Crises now and then: what lessons from the last era of financial globalization?[A]. Monetary History, Exchange Rate and Financial Markets: Essays in Honor of Charles Goodhard[C].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03, 2: 52-91.
[14]SCHWARTZ A J. Real and pseudo-financial crises[A]. Mone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271-288.
[15]ALIBER R Z, KINDLEBERGER C P. Manias, panics, and Crashes: a history of financial crises[M]. Springer, 2017.
[16]陈松林.信贷资金流入股市对货币政策的影响[J].中国金融,2001(4):22-24.
[17]谢德仁,郑登津,崔宸瑜.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是潜在的“地雷”吗?——基于股价崩盘风险视角的研究[J].管理世界,2016(5):128-140.
[18]李志生,金凌,张知宸.危机时期政府直接干预与尾部系统风险——来自2015年股灾期间“国家队”持股的证据[J].经济研究,2019(4):67-83.
[19]石锦建,刘康一,李稻葵.中国金融发展的经验与展望[J].中国金融,2019(7):83-85.
[20]聂辉华,江艇,张雨潇,等.我国僵尸企业的现状、原因与对策[J].宏观经济管理,2016(9):63-68.
[21]李曙光.论我国市场退出法律制度的市场化改革——写于《企业破产法》实施十周年之际[J].中国政法大学学報,2017(3):6-22.
[22]谢欣,姚治宇.中国已成全球最大电梯市场未来仍存三大机遇[EB/OL].(2017-09-27)[2019-04-09].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7-09-27/1151171.html.
[23]智研咨询. 2017年中国电梯行业发展现状分析及未来发展趋势预测[EB/OL].(2017-08-09)[2019-04-09]. http://www.chyxx.com/industry/201708/548760.html.